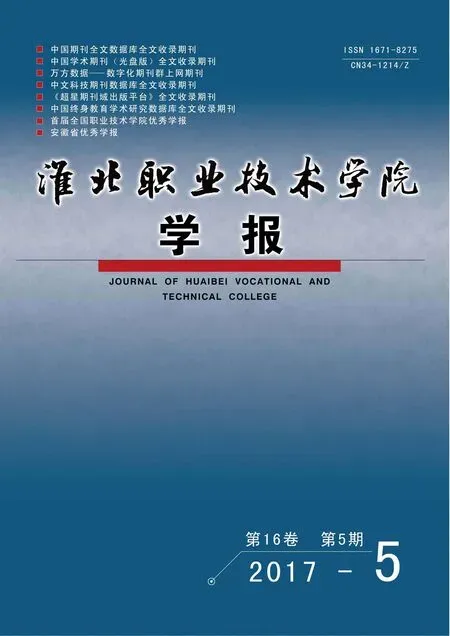元代山西婚俗初探
——以收继婚和贞节观为切入点
剧锦阳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元代山西婚俗初探
——以收继婚和贞节观为切入点
剧锦阳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一个由异族统治的大一统时代,因此,在各个层面都呈现出多样性、繁杂性的特征。婚俗作为礼俗之本、人伦之道,对于研究社会史、文化史具有重要意义。山西作为当时重要的腹里地区,在婚俗方面研究者较少。在此以蒙古族的收继婚和汉地已婚妇女的贞节观为切入点,结合山西地方志进行初步探究。元代山西婚俗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元初山西部分地区受到蒙古族收继婚的影响较大,二是元朝中后期,收继婚逐渐在山西销声匿迹,已婚妇女的贞节观念增强,同时表现出晋中、晋南地区贞节烈妇多于晋北的现象。
元代;山西;婚俗;收继婚;贞节观;晋中;晋南
一、元初蒙古族收继婚对山西婚俗的影响
元朝是蒙古人统治的朝代,他们自身有其独特的婚俗习惯并且呈现出多样性、繁杂性的特征,其婚姻形式多样,如抢婚、议婚、交换婚、入赘婚、收继婚、冥婚等。伴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这些婚姻形式或多或少地渗透到中原地区,山西作为元朝腹里地区的重要部分直接受其影响,其中对山西影响最大的是蒙古族的收继婚。
首先有必要解释什么是收继婚,收继婚又称为“转房婚”“转亲婚”等,一般是指父死妻其后母、兄死妻其嫂、弟死妻其弟媳的婚姻习俗。收继婚俗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族外婚时期,与人们的财产继承观念紧密相关,当时各部落不仅把本部落的已婚妇女作为本部族成员的妻子,还更多地把她们视为部落的财产和劳动力。收继婚的盛行是为了保证本氏族充足的劳动力,同时也为部落发展提供足够的后备资源。
山西是元代重要的腹里地区,离元大都非常近,在元初深受蒙古族收继婚的影响。至元初年,元朝统治者以法律形式准许汉人实行收继婚的习俗。元朝统治者在汉地推行收继婚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山西部分地区的婚配状况。山西部分地区地少人多、经济困难的现实原因导致他们积极响应元朝统治者的这一号召。“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太原路临州军户王仲禄之子王猪僧娶到贺真真为妻。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王猪僧身死停尸在家之时。其父王仲禄便将儿媳贺真真过房给王仲福之子王唐儿,并令王唐儿与贺真真‘拜讫王猪僧尸灵,收继成亲’,直至二月初二日才将王猪僧殡葬了当。对此,有司依例对王唐儿‘不候葬讫伊兄,于停葬之夜与嫂贺真真拜尸成亲,大伤风化’,且经都省准拟,‘令王唐儿与贺真真离异。’”[1]显然,河东山西这种停尸成亲的现象不是传统的汉地风俗,是蒙古族收继婚影响下的产物。
元朝中后期收继婚逐步衰落,在《元史》中亦有记载,例如脱脱尼,其夫哈剌不花卒,“前妻有二子皆壮,无妇,欲以本俗制收继之,脱脱尼以死自誓。”并对二子加以训斥,“二子惭惧谢罪,乃析业而居。三十年以贞操闻。”[2]4496因此,虽然收继婚一直与元朝相始终,但到了元中后期,由于受中原汉族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宋以来理学思潮的影响,实行收继婚的情况越来越少。与之相应的是,元中后期收继婚在山西的实行也随之减少以至于完全退出山西这一历史舞台,这一政策转变的重要原因是元朝颁布了一些政令禁止汉地实行收继婚、对汉地实行收继婚进行严厉的惩处。据《元典章》记载,至元十四年(1277年)刑部所准兄收弟媳刑杖断离之例。同时记载“守志妇不收继”“抱乳小叔不收继”“嫂叔年甲争悬不收”“姑舅小叔不收嫂”“兄亡嫂嫁小叔不得收”等规定。《元史》卷一百三《刑法志》二“户婚”:“诸汉人、南人父没子收其庶母,兄没弟收其嫂者,禁之。”另有规定:“诸兄收弟妇者,杖一百七,妇九十七,离之。”甚至规定“诸姑表兄弟嫂叔不相收,收者以奸论。”
收继婚逐渐退出元朝乃至山西的舞台,究其根本原因是汉族传统伦理道德对元朝统治者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有宋以来理学思想在婚姻方面对妇女提出更为严苛的要求。宋代理学家程颐大力提倡“贞操”,甚至把守节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把“守节”和“去私欲”联系起来,视妇女再嫁为羞耻之事,以致出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说法。宋代重视妇女贞操成为一股潮流,延续到元朝,无论蒙古族内部或山西这样的中原地区,收继婚现象均明显减少。
二、元中后期山西已婚妇女贞节观问题
(一)元中后期山西已婚妇女贞节观明显增强
元中后期河东山西妇女贞洁观念强化,不少死了丈夫的妇女能守志不改嫁,并且此种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元史·烈女传》记载了周术忽之妻崔氏的故事,周术忽在平阳为官,金将来攻城,克之,下令官属妻子敢匿者死。崔氏抱其子祯在土窖中躲避三日,躲过一劫,后与周术忽相见。但不久后周术忽病亡,崔氏年二十九。她“誓不更嫁,斥去丽饰,服皂布敝衣,放散婢仆,躬自纺织,悉以资产遗亲旧。有权贵使人讽求娶,辄自爬毁其面不欲生。四十年未尝妄言笑,预吉会。”[2]4484这则记载是山西地区当时妇女贞洁观增强的一个典型,诸如此类事件在《元史》中还有很多处,例如:“白氏,太原人。夫慕释氏道,弃家为僧。白氏年二十,留养姑不去,服勤继絍,以供租赋。夫一日还,迫使他适,自断发誓不从,夫不能夺,乃去。姑年九十卒,竭力营葬,画姑像祀之终身。”[2]4495可见,山西已婚妇女的贞节观在当时影响已十分强烈。纵观《元史·烈女传》这一章节,山西节妇烈女占有较多部分,山西妇女婚后守志的现象由此可见一斑。
光绪《山西通志》中也有大量元代山西妇女婚姻情况尤其是婚后情况的记载,记载婚后情况的多集中在烈女传中,它们集中反映了山西地区妇女浓厚的贞洁观念。例如:举人恪忠之妻王氏,年二十三岁时其夫忠亡,发誓不再改嫁。当时有向她求婚的豪贵,王氏曰“吾为士人妇,以孤幼不及死,志未可夺也。”[3]11218大德八年被当地旌表。又如,“郑和甫妻段氏,年少,夫卒。家甚窘,氏守义自矢,终身如一。至正七年旌表。”[3]11218再如,贾贤的妻子刘氏,本籍朔州,丈夫死后抚养二子福义、福礼。刘氏勤于女工以供祭养,茕居五十余年。至正年间受到旌表。此类例子在《山西通志》中比比皆是,充分反映了元代中后期山西妇女从一而终、终身待一夫的婚姻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就整个山西在元代的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妇女的守节观念较先代明显强化,我们可以从地方志中找到相关依据。《山西省太谷县志》记载:兹自元明以迄民国,凡节烈孝贤之昭昭在人耳目者,述其事迹以次编纂,庶潜德幽光不至湮没无闻,而贞魂烈魄亦可无憾于泉壤矣。《山西省浮山县志》亦有浮邑自元马氏而后代多节烈,其他女德母仪胥足树壶范,而辉彤史者亦并志之志节烈的记载。由此可知,元朝是山西妇女贞节观念得以强化的过渡时期,究其原因是理学思潮婚姻观对妇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前文已提及,在此不再赘述。
(二)元中后期,山西晋中、晋南地区贞节烈妇多于晋北
通过查阅山西地方志,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晋中、晋南地区关于贞节烈妇的记载多于晋北,下面列举几例具体说明。《山西省朔州志》记载:刘氏为贾贤之妻,夫亡刘氏年二十,有二子,次子尚在襁褓。“刘氏服丧抚子誓不二天,惟事女工以营祭养,茕居五十余年,始终一节,至正间旌其门曰贞节。”[4]除此以外,由成文出版社印行的山西省地方志有关晋北地区的贞节烈妇鲜少被涉及。
晋中有关贞节烈妇的记载多于晋北且主要集中在太原、太谷两地。《山西省太原县志》记载了齐氏以节殉夫的事迹,齐氏不仅自己以节殉夫,与之患难的萧氏、吕氏及二女面对敌寇亦能保持贞节,充分反映了当时妇女贞节意识观念浓厚。此外,太原白氏亦是婚后守节不适的典范。白氏,其夫为僧氏,年二十留养侍奉姑不去。另有安氏,名正同,王时之妻。至正十九年王时以参知政事分省太原,安氏从之。“遇贼攻太原,城陷,众皆逃。氏与其妾李同赴丼死,事闻赠梁国夫人,谥庄洁。”[5]《山西省太谷县志》卷六《烈女传》有“孟氏,李鼎新妻,夫早殁,孟孀居奉姑抚子,闺门端肃”[6]的记载。由此可见,晋中地区妇女的贞节观念较强,且主要集中在太原、太谷两地,山西地方志中并无晋中其它地区关于婚后妇女守节现象的记载。
山西地方志中有关元代晋南地区妇女婚后守节的记载明显多于晋北和晋中地区,主要集中于今天的临汾市和运城市。
《山西省浮山县志》记载了元代该地旌表的薛门三节和杨门双节。薛门两代三妇即王氏、杜氏、赵氏均秉持夫死守节不再适的原则,说明当时浮山一带妇女节烈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无独有偶,杨门双节的事迹与此类似。“杨恩,妻赵氏,生子彦,九月恩亡,赵养姑育子,甘贫守节,如澹攻苦,皇庆中旌表其门。彦娶杜氏,亦早亡,遗子思渝方五岁,杜年二十四,誓不再蘸,守节如姑,比赵寿终,杜礼葬如仪,姑妇守节始终无玷,至正四年旌为双节之门。明玄德间山西按察使张政并三节为着五节传。”[7]486自此浮山县薛门三节和杨门双节成为当地妇女婚后守节的标杆性人物,之后也涌现出许多贞洁烈妇。《浮山县志》卷二十八《节烈传》记载:“马氏,卫旗妻,年十八夫故,子贞甫二岁,舅姑且老,氏赖纺绩以供甘旨,守志三十余年,贞白无玷,至正八年旌表其门,祀节孝祠”。[7]749“杨氏,杨贞女,年十三,宇邑人卫。贞既受聘,贞以商卒于外,讣闻女哭之恸日,妾通名于卫即卫妇也,誓守终身至正八年旌表其门,祀节孝祠。”[7]749浮山杨氏因为父亲收取聘礼而承认与卫氏的婚姻关系并且誓守终身,这反映了当地妇女对婚姻严肃的态度及婚后强烈的守节观念。以上为以浮山县为代表的临汾地区已婚妇女婚姻观念的具体体现。
元代晋南运城已婚妇女的贞节观念相比临汾则更为突出。据《山西省新绛县志》记载:“韩筠,妻刘氏,年二十七筠亡,筠有弟氏,依邻母旁,舍居县治,枲以抚孤,及子有室女有从,乃复归于娣姒,同居优游以老,大德二年昭旌之。”[8]497此外,《新绛县志》还记载了段希贤之妻李氏守节不再适的事迹,“段希贤,妻李氏,年二十四夫亡,子荣甫四岁,奉亲育子守志不渝,至正间旌其门。”[8]497仅新绛县的这两例足以看到当地妇女的婚姻观念即终身侍一夫的观念,运城其它地方也有相关的记载。例如《山西省平陆县志》:“进士孙某,妻吴氏,幼年夫亡,无子,所亲欲夺其志,再蘸巨室王氏,子氏坚拒不从,后兵难投崖死。”[9]305《山西省万泉县志》:“周氏,其先上蔡人,适本县忽梁图,夫从军江汉,殁于王事,周氏守义抚孤,年八十卒。”[10]387《山西省虞乡县新志》:“颜氏麻怀祖,妻十七夫亡,抚男绍先,守八十八而卒,至大四年旌表其门。”[11]536上述无论新绛、平陆、万泉、虞乡均属今天的运城地区,由如此多的县志记载可以看出,运城地区已婚妇女浓厚的贞节观念,有些妇女甚至为保持贞节不惜赴死,其精神可歌可泣。
从以上县志记载可知,山西大部分县志记载元以前已婚妇女贞节方面的内容少之又少,自元以来贞节观念才日益深入人心,且晋中、晋南节妇烈女的记载多于晋北,晋中集中于太原、太谷一带,晋南集中于临汾、运城一带,且运城较临汾更为突出。
综上所述,元代山西婚俗呈现两个鲜明特征:第一,元初山西受蒙古族收继婚影响较大;第二,随着统治者一系列政令的颁行和惩治措施的出台,尤其是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河东山西妇女的贞节观念得以强化,并且表现出晋中、晋南地区的贞节烈妇多于晋北的现象,于此同时,以山西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已婚妇女贞洁观的盛行也对蒙古族的收继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元中后期,蒙古族传统的收继婚现象也大为减少。
[1] 瞿大风.元朝统治下的山西地区[D].天津:南开大学,2003:225.
[2] 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 王轩,纂修.光绪山西通志[M].许泗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4] 王泗圣.山西省朔州志(石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雍正十三年:685.
[5] 员佩兰,杨国泰.山西省太原县志(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道光六年:592.
[6] 刘玉玑,仇曾祐,胡万凝.山西省太谷县志(铅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二十年:778.
[7] 张桂书.山西省浮山县志[M].任耀先,修.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三十四年.
[8] 杨兆泰.山西省新绛县志(铅印本)[M].徐昭俭,修.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十八年.
[9] 韩夔典.山西省平陆县志(石印本)[M].言如泗,总修.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二十一年:305.
[10] 冯文瑞.山西省万泉县志(石印本)[M].何燊,修.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六年:387.
[11] 周振声,李无逸.山西省虞乡县新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九年:536.
责任编辑:张彩云
2017-05-10
剧锦阳(1992—),女,山西大同人,中国古代史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史。
K247
:A
:1671-8275(2017)04-0108-03
——以直省民人为中心
——以方志为中心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