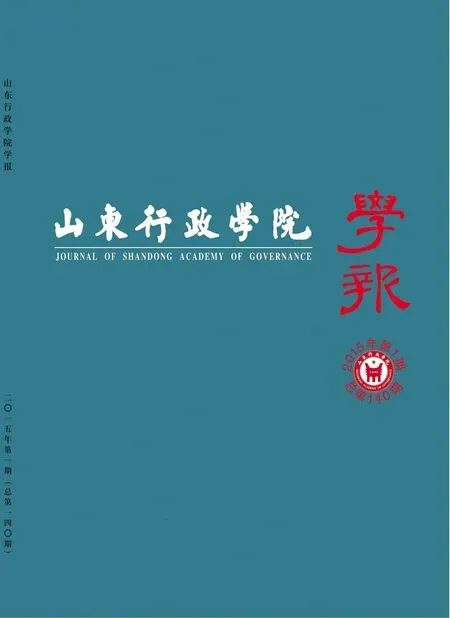墨家思想探析——以中国农村社会的价值重构为视角
张岩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墨家思想探析
——以中国农村社会的价值重构为视角
张岩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墨家学派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思想长河中熠熠生辉,“兼爱,非攻”的思想构成了墨家思想的理论核心,“尚同”、“尚贤”的思想构建了社会运行的良性机制,“节用”、“节葬”和“非乐”的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倡俭节约的风尚的形成起到了理论支撑作用,“明鬼”、“天志”及“非命观”孕育了中华民族虔诚的自然观和奋斗不止的民族上进心与使命感。在现代化突飞猛进的今天,墨家思想对于转型农村的建设和治理能够起到价值重构、理念革新、人文回归和公德重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墨家思想;兼爱;非攻;农村构建
一、引言
春秋末年,诸侯争霸,战事绵绵,各诸侯国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与此同时,学术思想领域也在孕育着一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战争。诸子论战,思想击撞,各学派都在纷纷探究经世治国之道和明理普世之学。墨家学派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大显学也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作用,以“兼爱,非攻”为理论核心的墨家学说理论丰富,具有浓郁的人文精神,兼爱非攻的普世哲学和爱好和平稳定的理想追求不仅彰显了与儒学、道学的不同,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更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当今社会转型中的农村文化的构建和人文精神的培育更是起到一种价值标准的功能。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的潮流席卷了中国的各个角落,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在城市化浪潮的面前表现出一种无措手足的现代性尴尬。中国农村在城市化的征途上引进了先进的技术、文明的理念和前沿的价值观念,但是正是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的渗透撕破了几千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形成的稳定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现代性的生活逻辑尚未形成,而传统的生活状态已被摧毁得体无全肤。先进的理念还是在社会表层发挥着工具性作用,而未成为一种抽象的价值信仰体系,传统的儒家思想在这种形势的面前已经无法起到统领大局的作用,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建设陷入了一种精神空虚的困境。
墨家思想提倡“兼爱”、“非攻”,主张毫无等级的爱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当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种潜在问题和矛盾的化解以及社区情怀和集体记忆的建构起到一个很好的胶合作用;“尚贤”思想对于当前农村社区民主建设和社区管理的科学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节用”等倡俭节约的思想不仅符合我国的宪法精神,更有利于维护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公德。“明鬼”、“天志”等观念也是重塑农民信仰和人文精神回归的一个前提。
二、兼爱、非攻思想——引导价值重构
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向来一直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强大的稳定器和蓄水池而存在,因为农村有大片的农业土地和蕴含着无限生产力的农业人口,信息流动的缓慢性和文化的单一性、同质性使得农民思想和观念更趋向于单纯质朴,更有利于为社会的现代化创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大环境,以及为现代化建设积累物质条件和社会财富。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农村再也不是费孝通老先生眼中的乡土中国那样,“捆绑在土地上的乡下人”,由于现代传媒、市场经济的进入和对乡土社会的渗透“感染”,中国农民的义利观和价值观逐渐出现异变,单纯质朴的观念被商业化的理性观念所代替,传统的人情关系开始变得更加理性化,衡量标准更加明晰,私的观念占据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领地。农村社会逐渐呈现多元化发展模式,同质性减退,异质性增强,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农村的“地方性共识”(1)的减弱也加剧了村庄内生秩序能力的丧失,村民对于村庄的主体感逐步丧失,越来越难以依靠内生的村庄秩序来维持世世代代在乡村土地上生存的人们之间共同的价值理念和信仰,农村和农民、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农村社会正在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乡土中国向法理中国过渡。
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人与人之间高度原子化和人情关系冷漠以及地方性共识的丧失,农民群体呈现机械化和无机化,团体行动力变弱。正是墨家所倡导的“兼爱”、“非攻”思想所预防和避免的,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君臣、臣臣之间毫无等差的爱,消除阶级、阶层之间的隔阂,主张平等和爱。另一层意思是爱利相兼,即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墨子在体会到人的本性的基础上主张在彼此获利的基础上去爱,在平等爱人的过程中彼此受益。农业社会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农民从感性人和情感人向理性人和商业人转变的过程中,势必会发生传统观念和现代商业观念的冲突,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潜在的社会矛盾,继而会引起短时间的农民群体性精神焦虑和紧张,但是墨子主张在这种社会转型和身份过渡的过程中注意平衡公和私、人情和利益的关系,做到义利共生共存,打破小农原有的宗族观念,将分散或分裂的农村群体碎片用墨家的思想进行拼接粘合,用社会或集体本位来代替狭隘的宗族主义,倡导人人平等、兼爱,具体到市场活动中,就是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场诚信体系,呼吁诚信的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感,买卖双方平等公平交易,使形成的“农业-商业”二元交易体系(2)在促进农民增收的过程中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同时也使得农民在和谐稳定的市场秩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之中彼此获得收益,这也就是墨子所说的“兼相爱,交相利”。
三、尚同、尚贤——推动理念革新
墨家的尚同和尚贤的思想观念相对于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具有鲜明的民主进步色彩,是由墨家的兼爱思想催生衍化而来,国家的治理,从下到上,从小集体到到大国家,从县邑到中央,从诸侯到君王,都倡导贤人理政,即所谓“能者上”,任人唯贤,所谓“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墨子·尚贤中》)。从历史的角度来纵观,墨家尚贤的思想较儒家“尊尊君为首”的思想更具有进步性和理论性,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更能与近现代的法制观念相呼应,排除了世袭官制,贤人治国总比家族治国在理论上更具说服力和先进性。而尚同就是在尚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尚同思想的孕育和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侯割据、战事频频的年代,国家四分五裂,而统一国家,统一政令是很多人的一种理想,人民希望建立一个君主一统的国家,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争得社会地位,渴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的迫切愿望。“这是当时墨学平民意识的集中体现,道出了平民要求参政的呼声,是有进步意义的”[1]。其实,对于尚同的理解也可以解释为人们否定个体化,推崇集体同一的一种价值观和理想。不能说“尚同”是一种完美无缺的社会理想,这种思想容易发展成为君主高度专制制度,进而成为阻碍民主发展的因素,但是尚同尚一的观念对于现代转型过程中高度原子化的农民个体来说不失为一种值得的制度。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根据村干部个人的品行和治村能力将村级治理的形态分为四种类型,即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和能人型。好人型治理是“从村干部的品性上来讲的一般具有良好的人品和人缘,不愿意用粗暴的手段去惩治村中任何一个村民,也缺乏让一般村民畏惧的力量”,强人型治理是指“性格强悍之人治理村庄,这种人敢于与村中不良倾向作斗争,他往往具有令一般村民畏惧的健壮身体或暴烈个性”,但强人更容易向恶人转化,所谓恶人治村,指的是“由恶人对村庄进行的治理,与强人不同的是恶人的私欲更重,捞取本来不多的村中公益或损害私益”,而大多数情况下,村民更期望能人治村,能人指的是“那些有特殊经营头脑和一技之长的人,尤其是指那些已经发家致富的村民。为了不辜负村民对自己的热望,这些能人也有参与村务的热情。能人治村的好处有很多:第一,在个人已经富裕起来的情况下,他一般不会打村中公益的主意;第二,他有带领村民致富的能力”[2]96-97村民的这种推崇能人治村的愿望与墨家的“尚贤”思想是一致的,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教育水平不是很高,村民素质也只是在中等水平线上下浮动,村务只能由品行优良和有政治主见、治村策略的人来治理。同时,村里又存在数个以宗族为单位的在数量上多于村干部但又少于普通百姓的大社员阶层,这部分大社员大多是村内同姓宗族的代表人,有治村的才能,在品行和威信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各自代表自己宗族的利益,往往对村主任或村支书的威望造成威胁。但是,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还是善于推举一个最有才能的人和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来担任村内的最高职务(3),带领全体村民致富。这就是墨子所说的“贤人”。在贤人的统一领导下整个村庄的村民在一个相对团结的集体中共同生活,这可以说是墨家的尚同思想在现代村民自治之中的体现,也可以说是村民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
四、节用、节葬和非乐——促进公德重塑
墨家的“节用”、“节葬”和“非乐”思想也是以其“兼爱”思想为基础的,“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韗鞄、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股钳纳之衣,轻又暖,夏服絺绤之衣,轻又清,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孟子·节用中》)这说明了节用就是人们的衣食住行只要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生产需要就可以了,一切以享受为目的消费都是奢侈和浪费,提倡大家反对铺张浪费。节葬同理,反对过分夸张奢华的葬礼,主张葬礼从简。非乐也是从节俭的角度来告诫统治者在解决人们温饱问题之前,不应该把君主和贵族的淫乐放在首位,即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体现了在社会发展初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侧重点的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4条规定:“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也说明了节用、节葬和非乐思想中所体现的节约思想不仅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基础,也是具有明确的宪法依据的。费孝通老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曾经提到过:“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文化提供了各种手段来获得消费物资,但同时也规定并限制了人们的要求。它承认一定范围内的要求是适当和必要的,超出这个范围的要求是浪费和奢侈”[3]95,这准确地体现了墨家学派所称的“节用”一词的含义,“安于简朴的生活是人们早年教育的一部分。浪费是要用惩罚来防止。孩子们饮食穿衣服挑肥拣瘦就会挨打或挨骂。在饭桌上孩子不应拒绝长辈夹到他碗里的食物。母亲如果允许孩子任意挑食,人们就会批评她溺爱孩子。即使富裕的家长也不让孩子穿好的、价格昂贵的衣服,因为这样会使孩子娇生惯养,造成麻烦。”[3]95这体现了中国农民家庭传统的节俭观念,中国农民将节俭教育从自家的孩子抓起,将节俭的理念融入到人一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树立和培养计划之中。浪费,是村庄集体舆论所禁止和批判的,而节约不仅是一种美德,一种习惯,更是成为衡量一个人品性优良、一个家族荣辱兴衰的重要标准。他指出“知足和节俭具有实际价值。一个收入全部用完毫无积蓄的人,如果遇到歉收年成就不得不去借债从而可能使他失去对自己土地的部分权利”[3]96,“在日常生活中炫耀富有并不会给人带来好的名声,相反却可能招致歹徒的绑架,几年前发生的王某案件便是一个例子”。[3]96这说明节俭在物质层面上也会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和价值,只有节俭,农民才会有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能力,才会有生存主体感和安全感。可见墨家所提倡的节用也不是只着眼于品德养成的,也更具有其实用和功利主义的价值。勤俭节约的传统习惯不断向人们内心深处内化时,便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即所谓的农民的乡土逻辑“中庸、平和、不出头”[2]7。
但是,每逢婚姻丧礼场合,勤俭节约的观念似乎就淡了。婚丧礼仪看起来仅仅是一种民俗活动,实则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意义,中国人通过这种婚丧之礼来获得精神价值的体验。费老说:“人们认为婚丧礼仪中的开支并不是个人的消费,而是履行社会义务。孝子必须为父母提供最好的棺材和坟墓。如前面已经提到,父母尽量为儿女的婚礼准备最好的彩礼与嫁妆,在可能的条件下,摆设最丰盛的宴席”[2]96。贺雪峰教授说:“一直以来,丧葬都是农村社会(也许是任何社会)中最为重大的仪式,是阴阳相交,是生离死别,是人生结算,是联系亲友的大事,甚至是人生的竞赛。生养死葬,这个死葬实在太重要了。”[2]40自古至今,尽管墨家不断地呼吁节葬,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世界上最勤劳简朴的古老民族却实行铺张浪费式的礼仪,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孝德情结,所谓仪式的本质就是婚葬仪式所包含的象征价值,与参与者投入仪式活动所获得的主体感受有关。但是近几年,随着无神论思想的传播和商品经济思想的传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了现代化的洗礼,死,变得不再那么神秘;婚礼,也不再那么神圣。对于现代的丧葬礼仪,只不过是商品关系在人际关系领域的一种外化罢了,所有的仪式都成了活人之间的一种攀比和金钱竞赛,所有的仪式都失去了其应有的魅力和神秘。当仪式活动失去了精神价值意义,徒具形式,变成农民进行社会性竞争的手段或丧失其严肃性而变成十分恶俗的活动时,都是仪式活动的一种异化,这种异化的仪式丧失了其本有的价值,成为纯粹的铺张浪费。这也是墨家所批判和反对的。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尤其是面对商品经济和现代传媒的冲击,中国农民应该培养一种良好的消费观念,辩证地看待仪式,注重仪式的精神价值,反对铺张浪费和仪式的商品化,注重墨家提倡的“节葬”,来构建中国农民文明的仪式价值观。
五、明鬼、天志和非命——呼唤信仰的回归
“故鬼神之明,不可为幽闲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墨子·明鬼下》)。这一段话指出了墨家的明鬼和天志观,墨家认为鬼神无处不在,鬼神控制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人们的各种行为受到鬼神的监督,因此统治者应该顺应民意,推行仁道,实际上这里的“鬼”只是墨家进行自我证成的一个工具,他希望通过鬼神对统治阶级的制约和监督,来督促统治者大行天道,实施利民之政。中国古人一直都有一种朴素的鬼神观,他们相信本体之外还存在一个超自我的神,这也是古代社会治理过程中规则之外的一种治理方式,这种鬼神之治比显见的规则之治要有效得多。费孝通老先生在调查1980年代中国的农村时提到过:“节俭是受到鼓励的。人们认为随意扔掉未用尽的任何东西会触犯老天爷,他的代表是灶神。甚至米饭变质发酸时,全家人还是尽量把饭吃完。”[3]96正是这种朴素的鬼神观造就了中华民族自省、自制和自觉的民族意识,以及朴素的正义观。有人说,中国是一个缺乏抽象信仰的民族,笔者并不是很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传统的鬼神观念,中国人对鬼神的各种祭拜仪式寄托的是中国人对生命的信仰和敬畏,就像西方人通过宗教来获得精神上的救赎是一样的。中国人那种朴素的鬼神信仰自五四以来被德先生和赛先生驱逐了,这种信仰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无神论的普及以及商品化大潮的冲击使这种信仰逐渐销声匿迹,原本敬天畏地的中国农民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开始大言不惭“人定胜天”,最后是人战胜了天,还是天报复了人,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农田因大量化学肥料的使用而板结,大量的毁林荒使得土地沙化,许多村庄变成了空壳村。同时,缺失了这种信仰,官不为官,民不像民,子不像子,父不类父。社会陷入一种潜在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不仅仅是生态危机,更是社会伦理危机。面对人类从大自然中劫取的物质财富,面对着体无全肤的农庄和农田,农民会陷入深深的焦虑和精神空虚之中,又谈何新农村建设?因此,呼唤农民群体信仰的回归,重塑对天地的敬畏之情,这对于农民群体统一价值观的形成和团体协调性的加强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墨家的“非命”观看似与其“明鬼”、“天志”观念相互矛盾,其实他们是统一的,只不过非命观是注重人本身的意念,明鬼和天志的观念注重的是人外在的事物。墨子“非命”而尚“力”,更是一种对人的主体的自觉、克服命运安排的自觉,其基本精神是否定天命,追求真理,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从墨家“强力”的观念出发,“非命”并不是否定天和鬼神,而是与其“天志”、“明鬼”观念相结合,主观上借“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在客观上利用“鬼神”的宗教权威来曲折地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转型时期应当注重向农民宣传不要屈从于命运、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非命观,这种观念也有利于中国农民勤劳、艰苦奋斗性格的养成。
在现代化大潮汹涌澎湃,农村社会转型的关节点上,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七零八落,现代观念尚未形成,农民普遍陷入一种群体性焦虑和精神空虚之中,因此,应该从墨家兼爱、非攻的层次上来合理引导农民进行一种新的和谐观念的重构,避免农民个体的过分原子化,注重群体活动的一致性,关注边缘群体,推动贤人民主,重构敬天保民的传统观念,呼吁人性和信仰的回归。
注释:
(1)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提到,地方性共识指的是由熟人社会的信息全对称状态而产生的公认一致的规矩。地方性共识包含价值与规范,是农民行为的释义系统和规范系统,由其形塑的行为逻辑,称之为乡土逻辑。
(2)“农业-商业”二元交易体系,是指在农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部分农民经商,而部分农民依旧务农,从而形成的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务农经商二元化的一种格局,是为充分利用大量的农村剩余闲散劳动力而出现的一种农民增收体系。
(3)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村都是实行村支书和村主任任职“一肩挑”制度,即村内支书和主任通常由一个人来担任。
参考文献:
[1]薛柏成.墨家思想的起源及历史影响新探[D].吉林大学,2006.
[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上海世纪集团出版社,2007.
编辑:董蕾
哲学·文化
收稿日期:2014-10-20
DOI:10.3969/J.ISSN.2095-7238.2015.01.013
文章编号:2095-7238(2015)01-0078-05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D9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