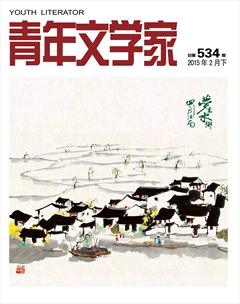“仁爱”、“兼爱”之比较研究
李晶鑫
摘 要:儒家的“仁爱”强调爱的推行要依据身份的现实存在,讲究差别等级式的推行;而墨家的“兼爱”强调爱的推行不应受制于身份的限制,讲究没差别的、普遍的推行。然而爱的推行既要以身份为基础又要超脱身份的限制。在推行爱的过程中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存在着这样一种辩证关系,即“仁爱”要以“兼爱”为目标,而“兼爱”要以“仁爱”为前提。爱的推行应是“仁爱”与“兼爱”的融合。
关键词:仁爱;兼爱;身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06-0-02
一、儒家的仁爱及其体现出的身份观
《论语》颜渊篇有一段对仁爱内涵的论述,一段是“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由本段可知与人交往处处按照礼来行事即为仁。另一段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由此句可知孔子认为仁就是用一颗向善的心来关爱别人,来与人交往。还有一段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由此句可知孔子认为仁政的要义就是使君、臣,父,子各居其位。总结上文可以得出孔子仁爱的大致内涵,即以爱人为出发点与归宿,运用礼乐等来规范君臣父子等人际关系,使每个人的行为都与其身份地位相符的一个过程或状态。《孟子》公孙丑上有一段话:“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2]由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也就是孟子所主张的“性善论”。第二,把我们这种先天的善不断地而又层次分明地扩充到父母、朋友、他人以及天下之人时,则“天下可运于掌”,而这个过程也就是孟子主张的仁爱的实施过程。故孟子仁爱思想的大致内涵是:以性善论为出发点,把这种天然的“善”不断地而又有差别地扩充到家人、朋友以致天下人身上,以达到上下同善,和谐安宁的状态即是社会仁爱的状态。
无论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仁爱观都是建立在一种对自身身份的特定认同上的,一个人既然有了这些既定的身份,那么他的行为举止就要符合这些身份的要求,而这个社会的和谐就是依托于社会成员都按照各自的社会身份来行事。因此儒家所推行的“仁爱”也是以社会成员各自的身份存在为基础的,仁爱的推行受制于身份的限制,儒家仁爱的推行即以身份为本源和导向,又是对身份的巩固和强化。
二、墨家的兼爱及其体现出的身份观
兼爱是墨子哲学的宗旨。墨子认为兼爱就是无差别地平等的爱,也就是说,天下每一个人都应该同等的、无差别的爱别的一切人。在《墨子》一书中,有三篇专讲兼爱的思想。墨子在其中区分了“兼”与“别”。坚持兼爱的人则称为“兼士”,坚持爱有差等的人则称之为“别士”。《墨子兼爱下》中说:“谁以为二士,使其一士者执别,使其一士者执兼。是故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3]在做出了这种区别后,墨子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兼”与“别”那一个对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墨子提出了“三表”来判断兼与别的是与非。所谓三表,就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墨子非命中》)“于何原之?下原查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行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3]三表之中,最后一表最重要。“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墨子判定一切价值的标准。这个标准,也正是墨子用以证明兼爱最可取得标准。墨子认为,如果以别人为不对,那就必须有东西去替代它,如果说别人不对而又没有东西去替代它,就好像用水救水、用火救火。这种说法将必然是不对的。所以墨子说:“兼以易别。”既然如此,那么用兼相爱来替换别相恶的原因何在呢?墨子回答说:“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由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3]
从上文墨子对其兼爱思想的诠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墨子的“兼爱”思想是超脱了个体特定的社会身份的认同的,主张人与人之间实现一种无差等、无身份局限性的爱。一个人存在于世上虽然有着许多特定的、无选择性的身份,但如要实现兴天下大利、除天下大害就必须要超越社会成员间特定身份的限制,推行最广泛、无差别的“兼爱”。
三、仁爱与兼爱的辩证关系
仁爱与兼爱都涉及到社会成员的社会身份问题,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什么是身份。伏尔斯泰在他的《哲学词典》中关于“身份”一词写道:“此词不意味着‘同样的事物。但可用‘相同性表示。”他还写到最重要的一点:“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个人的相同性。”我的记忆由回忆构成,但不仅仅是回忆,它还包括了很多因素,吸收了我们称之为“集体记忆”的东西。“集体记忆”是后天的习得和传承,它通过家庭、阶层、学校和媒体来传承。“集体记忆”对于过去历史的简化,无论是简化成集体痛苦还是抹消消极方面,都使得面对着具有同一属性的男性和女性或者面对着其他群体成员的某种诉求变得合理。然而,仅仅因为就从一种对过去简约化的视角来提出要求平等地位,平等待遇的合理诉求,这种理由充分吗?[4]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都是为了推行爱,不同的是二者推出爱的方式的不同,前者是主张以社会身份为基础的渐进式的有差序的推行,后者是主张超脱社会身份的普遍的无差序的推行。那么对于爱的推行,应该采取哪种方式呢?是“仁爱”还是“兼爱”,抑或是二者的融合。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我们的身份不是绝对的,特别是我们对待我们的身份以及别人的身份所包含的信息并不是绝对的,而是“集体记忆”所育化的。因此我们不应限制于我们的身份,不应把身份中所包含的信息放在绝对真理的位置而不可逾越。“如果身份认同缺失是先前抹消影响的证据,只需要创造出大量的、新的身份认同来将其复活。但是,如果的确存在被迫异化的情况,人们难道不应该质疑压制的影响吗?”
其次,我们要明确的是,虽然我们的身份不是绝对的,但我们也不能没有身份而存在,我要超脱身份而不是脱离身份。“与自身思想保持距离,旨在帮助人对自我和自己所在阶层产生意识,而不是为了让人与社会脱节,因为只有融入才有社会,才能对社会采取行动,这也是所有政治(行为)的目的。”[4]
从上面两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推行爱的过程中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存在着这样一种辩证关系,即“仁爱”要以“兼爱”为目标,而“兼爱”要以“仁爱”为前提。因此对爱的推行应是“仁爱”与“兼爱”的融合。社会存在着既定的身份,人们一出生就有着某些特定的身份,社会化即是形成和完善我们的特定身份的过程。社会的存在需要身份,而人们的生活需要社会,因此我在推行爱的过程中,也必须立足与身份,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在传统的维系下实现稳定和秩序,只有这样爱才能在一个和谐有序的环境下推行。不过虽然我们是在社会身份的环境下来推行爱的但我们推行爱的目的确不是维护我们既定的身份,我要超脱我们不是绝对真理的身份,而实现“兼爱”。
参考文献:
[1]张燕婴.论语:中华经典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万丽华,蓝旭.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李小龙.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著,王鲲/译.身份认同的困境[M].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