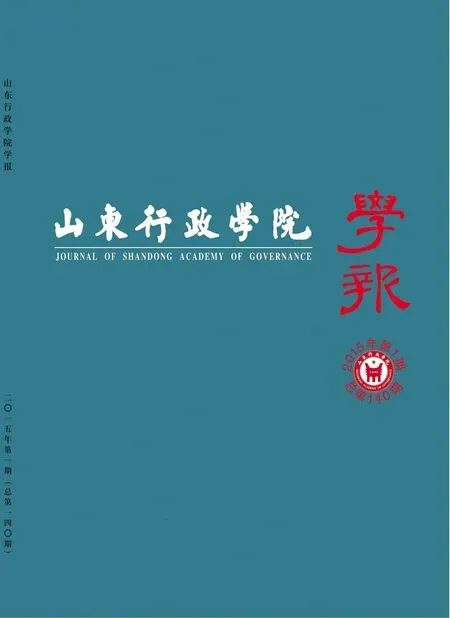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评估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基于AHP分析法的运用
李彦娅(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昌330031)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评估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基于AHP分析法的运用
李彦娅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昌330031)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评估的研究中,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是检验政治参与效能的关键,而政治参与效能的评估又是一个难以量化分析的复杂问题。层次分析法能够为其提供一种有效的思路。该方法能够通过目标层次的构建来确定各个评估指标的权重,进而科学检验政治参与的效能。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评估;AHP分析法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从事以非农劳动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据统计,在整个农民工群体中,有近六成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于传统农民工,他们因为一般拥有较高的学历,多数渴望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所以对于事关自身经济、社会利益的问题,有着更为强烈的诉求欲望,而政治参与是实现其目的渠道或途径之一。政治参与是通过影响政府或企业的公共决策,维护或改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利益,进而实现政治权利的有效保障机制。检验新生代农民工改善自身状况的实际效果,需要对政治参与效能进行分析和评价,而指标体系的构建在政治参与效能评估中居于核心地位,其科学性关系到政治参与效能评估的实现及评估结果的科学性。
一、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评估的研究现状及其局限
根据已有的研究资料,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尚无一个明确的定义,当前只能以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政治参与的内涵和外延对其描述,所以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是指农民工利用各种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参与渠道,如村民选举、职工代表大会、合法抗争等方式,对流出地或流入地社区、单位的政治运作、政治决策、政治结果所表达的关心、利益表达和施加影响的行为及过程,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政策结果的产生以及公共决策形成的政治行为。而政治参与效能,简单地说是指公民参与政治的效率、效果、效益。目前国内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文献资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政治参与的现状或困境,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以及提高政治参与的对策。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和困境方面,邓秀华[1]、张永刚[2]、于水[3]、徐志达[4]、高洪贵[5]等认为:由于受制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经济收入水平较低、以及参与的效能感较低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普遍存在着边缘化、淡漠化和非制度化等问题;在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方面,因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程度低的客观原因,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导致参与程度低下的原因上,朱光磊[6]、赵排风[7]、邵德兴[8]等认为: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内输型”决策体制、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势,以及权益组织的缺失等因素是导致农民工政治参与程度低下的主要原因;在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对策方面,聂月岩[9]、胡庆亮[10]、史成虎[11]等认为: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以消除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身份障碍,完善法律制度以保障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建立相关组织以提高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探索网络参与以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通过这些方面的多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程度,从而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
上述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详细考察各学者的研究脉络,本文认为:一是已有的研究较少有从政治参与效能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分析,而政治参与效能作为衡量政治参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政治参与的研究中不可或缺;二是缺乏对政治参与效能的评估分析,而效能评估分析则是检验政治参与程度和状况的一种有效方法;三是尤为缺乏较成熟且可操作的对政治参与效能进行评估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拟构建一套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评估分析的指标体系,以期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评估的研究提供一些工具性支持。
二、构建评估指标体系的方法:层次分析法的选取
(一)政治参与效能评估的维度
我国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评估分析的研究文献资料较少,因此,有必要借助于对政治效能感的研究。根据坎贝尔(Cambell)的定义,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人认为其政治行为对于整个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觉或者信念[12]。换言之,政治效能感就是公民对自身在政治生活中所能产生影响力的心理感知。结合前述政治参与效能的概念,本文认为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效能可以作为一个互通的概念来使用,因为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是互为因果的,具体表现在政治参与与政治效能感的关系上[13]。也就是说,它们既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客观效应指标,也是对将要参加的政治活动会产生何种结果的心理预期。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和特点,本文把参与渠道的多寡、参与程度的高低、影响单位或政府的决策程度和利益诉求的实现程度作为政治参与效能评估的基本维度。
(二)评估指标的选择
在上述效能评估基本维度的基础上,以社会科学田野调查方法为参考依据,进而把上述四个维度细分为十二项可量化指标来对政治参与效能进行评估分析,这十二项指标变量分类如下:参与渠道多寡分为很多、很少、没有;参与程度分为经常、偶尔、从不;影响单位或政府决策的程度分为很大影响、有些影响、没有影响;利益诉求的实现程度分为基本实现、实现一些、没有实现。在此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每个指标变量所占的权重,再以此来分析各指标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提出一条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评估的可操作路径。
(三)层次分析法的选取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萨蒂(T·L·Satty)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它作为系统工程的一个分支,通过综合整理人们的主观判断,把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是一种能够有效处理那些难以仅用定量分析方法解决的复杂问题。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把要研究的问题看作一个大系统,然后再根据问题的性质和需要达到的总目标,将问题分解为不同的组成指标元素,再按照各指标元素间的相互关联和隶属关系,将各元素聚合成不同的层次,从而形成一个多层次结构分析模型,最终是把系统分析量化为最底层(方案、措施、指标等)相对于最高层(决策总目标)相对重要程度的权值或者相对优劣次序的排列组合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充分体现了先分解后综合的系统思维,目的是把无法量化的指标按照权重大小进行排序,把彼此区分开来以利于分析。
层次分析法的优点是能够把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因此具有高度的逻辑性、系统性、简洁性和实用性,是一种针对多层次、多目标规划复杂决策问题的有效分析方法。应用层次分析法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进行评估分析,亦能够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并且可以使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相对合理,从而增加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三、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评估指标的设计
根据前述对评估基本维度的选取,本文拟将四个基本维度,进一步细分为十二个评估指标,分别对其进行分析,以期做出一个总体性的客观判断。
1.政治表达的状况是衡量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则是政治表达实现程度的重要前提。参与渠道的多寡(A1)是指是否有多种利益表达和诉求的渠道,参与渠道越多相对政治参与就越畅通。渠道的多寡势必影响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效能感,因为参与渠道越多,政治效能感会越强。它包括很多(x1)、很少(x2)和没有(x3)三个指标层次。其中,参与渠道很多表明政治参与效能很强,而参与渠道很少或者没有则反映出参与效能的低下。
2.参与程度的高低(A2)和参与渠道多寡是一个类似的概念,它表示农民工政治参与率的高低和参与意愿的强弱程度,会受到政治效能感、社会制度、自身经济条件以及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包括经常(x4)、偶尔(x5)和从不参与(x6)三个指标层次。其中,经常参与表明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热情很高、效能感很强,而偶尔或从不参与则显示出政治参与的淡漠化、边缘化以及效能感的低下。
3.影响单位或政府决策的程度(A3)是政治参与的产出和效果,它能够切实地反应政治参与的效能,包括很大影响(x7)、有些影响(x8)、没有影响(x9)三个指标层次。其中,很大影响表明政治参与的效能很高,一般会激励后续的参与,而有些影响甚至没有影响则会大大降低参与的效能感,当遇到极端情况时,农民工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必然转而寻求暴力等非制度化的参与。
4.利益诉求的实现程度(A4)是农民工进行政治参与的终极目标,是鉴别政治参与效能的关键维度,它包括基本实现(x10)、实现一些(x11)、没有实现(x12)三个指标层次。其中,基本实现表明了政治参与的目的基本实现,而实现一些或没有实现则是表明政治参与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利益诉求的实现程度往往与影响单位或政府决策的程度息息相关。因为如果政治参与所表达的利益诉求不能有效影响政治决策,那么就很难实现自身的利益表达,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表达,必然会影响政治参与的效能感,低下的政治效能感会则反过来影响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所以,这个维度同其他维度一起共同影响着政治参与的效能。
(二)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研究涉及参与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国家的政治制度、公民的政治权利、户籍制度、劳动就业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作,因此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时,要充分利用系统思维尽量选取有代表性的因素作为分析指标,然后才能构建分层结构式的指标体系。基本思路是:首先,确定评价指标;其次,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最后,根据最终计算结果对指标进行比较排序,找出差别,突出重点,以利于提出有针对性的政治参与对策。
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根据影响政治参与效能的主次要因素来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其中最高层为目标层O,表示解决问题的目的;准则层C设定为中间层次,表示为实现某种方案目标所采用的准则;最底层是方案层P,表示为解决问题所采用的各种方案。如图1所示。
2.构造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的构建首先是根据各层评价指标对应于上一层次准则指标的影响程度之大小来排序,然后是再依照层次分析法的步骤来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本文设置判断矩阵为A=(aij)(ij= 1,2…,n),其中aij表示i指标对j指标的相对重要性,且有aij>0,aij=1/aij,aij=1即A为正反矩阵。
在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评价分析中,由于许多影响因素涉及制度设计等法律规定,致使许多指标难以直接进行量化,因而采用萨迪提出的1~9标度方法,即用上一层次的某个因素为准则,再根据它对下一层次诸个因素的支配关系,两两进行比较下一层次诸因素对上一层次某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赋予一定的分值。其具体含义如表1所示。

图1:层次结构模型图

表1:层次分析法相对重要性的判断标度
3.计算相对权值并作一致性检验
特征向量代表本层次与之关联因素重要性次序的权值。判断矩阵A对应于最大特征值λmax的特征向量作为权向量w,也即Aw=λw,经过归一化以后即为同一层次上相应指标对于上一层次的某指标相对重要性的排序值。由于政治参与效能评价指标体系的复杂性,而且作为个人的专家评价在认识上多有主观性,故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还需要用一致性指标来进行检验,它计算公式为:

式子中CI表示:一致性指标;
n表示:判断矩阵A的维数;
CR表示:一致性比率;
RI表示:随机一致性指标,其值可以通过表2查出。

表2:随机一致性指标的取值
当CR<0.1时,则认为设定的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矩阵可以接受,否则需要调整判断矩阵,以使其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4.计算组合权向量
设上一层(A层)包含A1,…,Am总共m个指标,它们的层次总排序权重分别是a1,…,am。又设其后的下一层次(B层)包含n个指标B1,…,Bn,它们关于Aj的层次单排序权重分别为b1j,…,bmj(当Bj与Aj无关联时,bij=0)。然后求B层中各个指标关于总目标的权重,即求B层各个指标的层次总排序权重b1,…,bn,计算按照小标所示的方式进行,即bi= ∑mj=1bijaj
5.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检验
虽然各层次均已经进行层次单排序的一致性检验,但综合进行考察时,各层次的累积仍然会导致最终分析结果的非一致性,所以层次总排序也要做一致性检验。
设B层中与Aj相关指标的成对比较判断矩阵在单排序中已经经过一致性检验,求得单排序一致性指标为CI(j),(j=1,…,m),那么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为RI(j),CI(j)、RI(j)已经在层次单排序时求得,则B层总排序随机一致性比例为:

表3: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评估指标的权重

再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评估指标,就可以计算出的各个指标的权重,见表3。
四、结语
上述分析表明,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分析中,参与程度的高低和参与渠道的多寡,所占比重相对较大。因此,在推动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工作中,应该着力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其中一是要清除如户籍分割等制度性障碍,二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加便利的途径进行政治参与。尽管影响政策的决策程度和利益诉求的实现程度是农民工进行政治参与的最终目的,但从指标权重上看,明显低于前两个观察维度。这是因为无论政治参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实现程度有多大,如果没有参与的制度性保障,最终都无法实现正常、有序的参与,从而也不利于参与效能的提高。这完全等同于在法律制度中,程序正义的权重往往大于实体正义的意义之所在。由此可见,在推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工作中,要把制度建设置于首要地位。
参考文献:
[1]邓秀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15-20.
[2]张永刚.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州学刊,2011(04):32-34.
[3]于水,李煜玘.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对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20-29.
[4]徐志达.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及对策[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58-65.
[5]高洪贵.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分析:以哈尔滨市为例[J].党政干部论坛,2010(06):41-43.
[6]朱光磊,赫广义.农民工意见表达的限制性因素及其对策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1):42-47.
[7]赵排风.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问题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08(04):106-108.
[8]邵德兴.当前城市外来人口政治参与的若干难点分析[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4(04):42-45.
[9]聂月岩,宋菊芳.农民工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J].城市问题,2010(06):75-78.
[10]胡庆亮.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出路:以深圳龙岗区为例[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03):31-33.
[11]史成虎.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45-51.
[12]李蓉蓉.政治效能感:内涵与价值[J].晋阳学刊,2010(02):122-123.
[13]Steven E. Finke.Reciprocal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fficacy: A Panel Analysis[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85,29(04):891-913.
编辑:李磊
作者简介:李彦娅(1982-),女,湖南宜章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管理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2YJC840023)。
收稿日期:2014-07-27
DOI:10.3969/J.ISSN.2095-7238.2015.01.002
文章编号:2095-7238(2015)01-0007-05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D6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