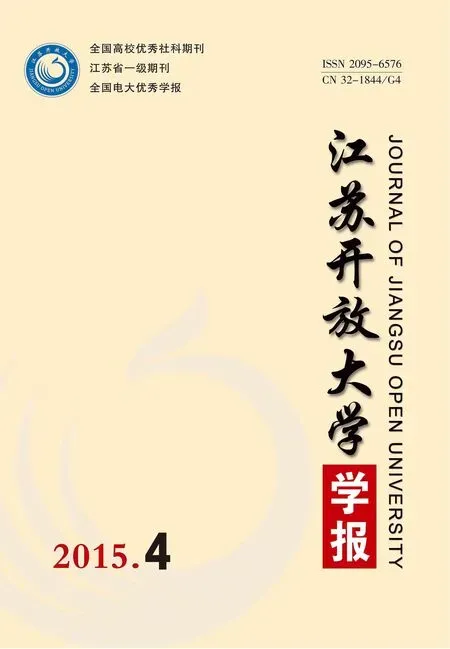“外史”之小说价值补考
王以兴
“外史”之小说价值补考
王以兴
“外史”由最早的史官演变为文学尤其是古代小说的一个文体概念,具有十分积极且重要的小说价值。首先,“外史”作为小说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神怪化的叙述方式;二是生活化的故事内容。其次,“外史”作为小说,实乃当时一批小说家试图摆脱小说为正史附庸的努力,表现出了强烈的尊体意识,具有积极的小说史意义。最后,“外史”这种独特的小说价值在与“演义”“野史”“艳史”等题名的比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外史”;小说;尊体;演义
“外史”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史官、野史和文学不同名义的演变,而表示文学之义时,“外史”更多的是作为古代小说的一种文体概念而存在。[1]除此之外,笔者还发现“外史”的小说价值尚不止于此,仍有许多值得发掘的内容,以下思考求教于方家。
一、“外史”作为小说的两个基本含义
笔者曾总结中国古代以“外史”为题名的小说共有十八部,[1]这些小说作品除《外史志异》和《外史新奇》之题名稍有特殊外,其他“外史”题名一般有两个基本含义,试总结如下:
其一,“外史”特指与正史“实录”精神相对,以虚构、夸张和想象为主的神怪化小说叙述方式。班固最早用“实录”作为对司马迁修《史记》的最高褒奖云:“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此后“实录”就成为了正史写作最重要的一个标准。而作为小说题名的“外史”含义之一即与此相对。明金阊舒载阳本《封神演义》题为《武王伐纣外史封神演义》,该书以历史上著名的武王伐纣为题材,运用大量的夸张、想象手法,如虚构女娲遣三妖惑商纣及阐教、截教斗法等情节,神怪杂出,奇幻瑰谲。鲁迅先生即认为此书:“似志在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2]可见,该小说题名中的“武王伐纣”是基本史实和故事素材,而“封神演义”则是对它的艺术化加工。那么,从题名看,《武王伐纣外史》就相当于《封神演义》,而冠以“外史”之名则指对正史中武王伐纣史实的神怪化叙述,从而使之成为一部有关姜子牙斩将封神的神魔小说。另外,小说的最后修订者李云翔虽然非常清楚姜子牙封神之事乃民间传说,却依然积极为封神一事的书写找借口:“俗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说,从未有缮本,不过传闻于说词者之口,可谓之信史哉?……语云:‘生为大(上)柱国,死作阎罗王。’自古及今,何代无之?而至斩将封神之事,目之为迂诞耶?”[3]按,“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乃隋朝大将韩擒虎临终语,见《隋书·韩擒虎传》。这充分说明了李云翔对小说神怪化叙述方式的认同和张扬。虽然我们不好判断明金阊舒载阳刊本的“外史”之名是《封神演义》原本就有,还是出自李云翔之手,抑或是书坊主刻书时所加。但是,“外史”题名的选择本身就表明了取名者借此对小说叙述方式进行定位的用心和意图。因此,“外史”即可看作为一种对历史题材进行神怪化艺术加工的小说叙述方式。
清初吕熊的观点更具代表性。他在《女仙外史》开篇即指出小说命名的缘由:“女仙,唐赛儿也,说是月殿嫦娥降世。当燕王兵下南都之日,赛儿起义勤王,尊奉建文皇帝位号二十余年。而今叙他的事,有关于正史,故曰《女仙外史》。”[4](第一回《西王母瑶池开宴 天狼星月殿求姻》)可见,此处“外史”是对“正史”某种方式的叙述。然而作者这句话说得还很含糊,没有明确说明“外史”对“正史”是如何叙述的。这一空白在作者自跋中得到了补充,他说《女仙外史》的创作是“托诸空言以为‘外史’。夫托诸空言,虽曰赏之,亦徒赏也;曰罚之,亦徒罚也,游戏云而……曷云游戏哉?第以赏罚大权,畀诸赛儿一女子,奉建文之帝号,忠贞者予以褒溢,奸叛者加以讨殛,是空言也,漫言之耳”[5]。显然,吕熊的“外史”观与《封神演义》以“外史”为名体现出来的意图一脉相承。此类作品尚有:《蜃楼外史》写明朝奸相严嵩门下赵文华抗击倭寇事,其中仙妖杂出、人鬼并举;《禅真逸史》以东魏、南朝梁至隋朝为历史背景写绿林好汉归顺梁朝事,其间亦颇有神怪情节。这数篇“外史”小说从题材上看均取材于正史,然采用的却是小说所特有的虚构、想象甚至神怪化的叙述方式。
其二,“外史”专指小说与正史相对的、更为广泛的生活化内容,以及由此而来的细致、生动的叙述笔触。我们知道历代正史均以国家大事、朝代兴替及著名人物的功业成就、历史贡献为书写内容,一如《旧唐书·职官志·史馆》所云:“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既终藏之于府。”[6]而“外史”小说则正好相反,它主要取材于普通人物的日常琐碎生活,即便是以历史名人和事件为题材,叙述角度和关注点也颇有不同,以《儒林外史》《武则天外史》《菲律滨外史》和《驻春园外史》为代表。闲斋老人解释《儒林外史》之“外史”题名时说:“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7]由该句话可知,“外史”是对书中所述“儒林”人物、故事的具体界定,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传主不是正史中那些经学大师,而是平凡的文人士子;其二,“外史”所描述的是传主日常的人情事理,而非正史中经学大师们深厚的经学造诣和远大的学术影响。因此,“儒林外史”所描述的是一般儒林人物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真实情态。与此相似,《武则天外史》叙述历史上唯一女皇武则天的生平经历,比正史所记更细腻更生动,“颇有依据,笔亦佻冶,可与《隋炀艳史》相匹”[8];《菲律滨外史》描写菲律滨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革命斗争,笔触涉及广泛且生活化,比如对主人公的爱情描写;《驻春园外史》是一部爱情题材的才子佳人小说;而《黄奴外史》则记叙鸦片战争期间一些中国人丧尽天良大发国难财而沦为汉奸、洋人奴才的社会现实。总之,这类“外史”小说仍采用如正史一般的写实笔法,然而故事题材和叙述角度与正史大为不同,主要涉及小说人物更加私人化和生活化的方方面面,诸如爱情、家庭、社会活动等,笔触细腻、生动,且深入到主人公内心,淋漓尽致地展现他们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事实上,有时候“外史”题名也同时包括了以上两种情况,即取材内容与正史相对,同时又采用虚构甚至神怪化的叙述方式,以《燕山外史》和《蝶阶外史》为代表。清陈球《燕山外史》是以四六骈文写成的一部非常有特色的才子佳人小说,窦绳祖和爱姑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涉及非常广泛的生活面,有封建家长制度和门第观念对“情”的扼杀、贫穷女子的悲惨境遇、农民起义及侠客精神等,但始终以二人爱情遭遇为线索。由此可见《燕山外史》在题材内容上的非正史取向。而小说结尾二人看破红尘尸解成仙,采用的又是与正史“实录”精神迥异的虚构、想象手法。虽说仅是一个简短的神话尾巴,但也表明了作者对此叙述手段的认同和接受。清高继衍《蝶阶外史》是一部文言小说集,内容博杂,既有现实性的民间传说,又有志怪类的神仙妖异故事。该小说题名中的“外史”不仅是对其复杂内容的概括,也暗示了作者对神怪化叙述方式的认同。正如高继衍在《蝶阶外史小引》中自云:“茶余酒半,朋友家谈,遇可传可敬可喜可愕之事,归辄篝灯笔之,积日既多,遂而成帙,命曰《蝶阶外史》。予本餐腐之人,亦自罄其腐谈,聊供阅者喷饭而已。”[9]可见作者消遣娱乐的创作动机,命名为“外史”也即取其与正史严肃、庄重相对的轻松、自由的创作风格。
另外,对于“外史”题名的以上两种含义,我们还可以结合明清小说作家、评论家和作序者以“外史”为名号来理解。笔者曾在《“外史”名义的历史变迁》一文中粗略统计过以“外史”为号的小说家有十位左右,比如清篯壑外史(著有《海天余话》)、云槎外史(著有《红楼梦影》)、惜花外史(著有《美人奇计》),夏敬渠在《野叟曝言》第一五四回中也自称“外史氏”,等等。此类情况必然还有许多,这些实例已足以说明问题。试想,这些小说家们既然自封为“外史”,那么他们在创作和评论这些小说时强调的自然也是与正史相对的内容。比如,以虚构、神怪化为叙述方式的《韩湘子全传》和以日常生活如婚姻爱情为叙述内容的《红楼梦影》《后红楼梦》,以及兼而有之的《野叟曝言》《情史》等。因此,小说家们的“外史”名号也为我们理解小说“外史”题名的两个基本含义提供了一个参考角度。
总之,“外史”以上两种基本含义正是与正史最主要的特点,即宏达的历史题材与其所需要的写实风格或者说“实录”精神相对照而来的。在小说家那里,原来表示史官及野史意义的“外史”,其语法结构已由原来的单纯词变成了偏正结构的复合词,也就是说“外史”之“外”是对该词的修饰成分,表示“正史之外”的意思。
二、“外史”作为小说的理论价值和小说史意义
如上述,“外史”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文体概念,具有两个基本含义,其彰显出的理论价值和独特的小说史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中国古代小说领域内,“外史”被固定化为一种小说文体概念,体现了这些明清小说家们对小说本质特性的自觉探讨和较为准确地把握。他们视小说为“外史”,即小说本质上是史书之一种,只不过与正史相对罢了。“外史”作为小说的理论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小说方法论,以《封神演义》和《女仙外史》为代表;一是小说素材论,以《儒林外史》为代表。众所周知,虚构的创作方法和生活化的素材内容正是小说的本质特性。法国小说评论家阿贝尔·谢瓦来在其《当代英语小说》中解释小说就是“用一定篇幅的散文写的一种虚构作品”[10]。当然,此处的“虚构”是指在符合生活情理基础上对故事素材加以典型化的创作过程和方法。然而,在具体表述上“虚构”也不排斥“外史”所特指的对历史事实进行神怪化的叙述方式,二者不完全相同,却又有相通之处。19世纪英国著名小说评论家亨利·詹姆斯(1843-1916)在其《小说的艺术》中也认为:“一部小说按它最广泛的定义是一种个人的、直接的对生活的印象:这,首先,构成它的价值,这个价值根据印象的强度而或大或小。”[11]可见,明清小说家们将小说定位为“外史”,且分别从“外”也即与正史相对的上述角度来强调小说的两大特性,是一个大胆的理论突破。如此一来,小说自然具有了“史”的意义,却是虚构的历史或者生活化了的历史,抑或是虚构了的生活化的历史!我们知道,正史采取的官方叙述角度和评价态度毕竟与普通大众不同,所以小说家们希望在小说中能够用另一种方式对历史现实进行主观化的叙述。例如,《女仙外史》将明朝历史上原本不相关的“靖难之役”和唐赛儿起义捏合在一起,虚构出一个仙女下凡以维护正统、扶持名教的历史神话。作者对历史事实如此叙述,就是“致慨于《明史》秉永乐之旨意削建文一朝之年号,名为翻历史旧案,实为当世南明一段历史不得官方承认发泄不满”[12]。
另外,小说往往采用更细微、更具生活质感的笔触去描述和反映社会、人生,实际上这本身也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主观化揭示和观照。因为,生活原本即是历史,人们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经历和感性体验恰是对某一历史真相的直观表达和补充。如《武则天外史》中的武则天已非正史中高高在上的威严女皇,而是被还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为了能够爬上权力顶峰而变得心狠手辣的女人,她特殊的心态变化、情感生活等不见于正史的内容在小说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也可以说,该小说采用不同于正史的独特视角来观照和透视武则天这个颇具历史争议的女皇帝,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这一段历史和人物的主观认识和思索。
因此,不论是对历史题材的虚构和夸张叙述,还是对日常生活的真实书写,与正史相比较,“外史”小说都是对某一历史真实做出的另一形态的观照,体现了作者对该历史的主观态度和严肃思考,称之为“外史”再不为过。总之,“外史”对小说的两大本质特性作了积极的探讨,并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显示出当时小说理论探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二,从纵向看,“外史”作为一种文体概念,本质上是中国古代小说为摆脱正史之附庸、争取文体独立而努力的表现,凸显出一种强烈的尊体意识。当然,这是某些明清小说家因小说创作渐趋繁荣而信心大增,以及对小说性质较为准确把握而导致的自然结果。何悦玲在《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传关系认知的历史变迁》一文中总结了宋代以降尤其明清时期人们对通俗小说虚构本质的认识,认为这其中隐含着区分“小说”与“史传”的积极努力。[13]伴随着明清时期一种大胆肯定小说文体独立的理论主张呼之欲出,小说即为“外史”的观念在该情形下应时而生。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尊体意识具有积极的小说史意义,这在与前代小说理论的比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唐代正统文人如长孙无忌和刘知几等均视小说为正史所遗,其功能一般即为补史书之缺和增广见闻;而小说家如李公佐、李翱则从小说角度肯定其史鉴功能,认为小说也具备与史传等同的教化作用,以此来力争小说的社会地位。[14]可见,当时文人(含小说家)强调小说的补史和史鉴作用,是从小说的功能角度向正史靠拢。然而,唐代文人这种努力把小说附骥于正史的批评,本身就恰恰说明了他们自信心的严重不足和小说尚未摆脱正史之“偏记”(刘知几)地位的事实。当然,这与唐代小说创作仍没有达到足以突破正统史传文化束缚的局面有关。降至明清时期,视小说为“外史”这种观念的提出,表明此时某些小说家们已不再满足于小说只是正史附庸的尴尬地位,而欲与之并驾齐驱,且他们对小说本质特性的把握已经较为准确,这就使得小说无须再借助正史求得自身价值的确认。换句话说,这些小说家们清醒地认识到正史与小说是两种不同的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文体形式,二者所采取的叙述方式和角度截然相反,而地位则在伯仲之间,不分高下。
总之,明清时期小说等同于“外史”的理论观点从小说方法论和素材论方面对小说的本质特性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从而为小说摆脱正史之附庸、获得文体独立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自然也就具有了独特的小说史意义。
三、“外史”与“演义”“野史”等题名的比较
明清小说的题名五花八门花样繁多,尤其“演义”“传”及“野史”“艳史”“逸史”等以“史”为名者居多。因此,我们在探讨“外史”题名的价值和意义时非常有必要将其与另外的题名做一番比较。
1.外史与演义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下,明清以“演义”为名的历史小说创作蔚然成风,这也导致了在一般读者心目中“演义”就特指“历史演义”。其实,据谭帆先生考证,在小说领域内“演义”已经演变为古代小说的一种文体概念,概指明清通俗小说,不仅指历史小说,而且也包括世情小说。[15]可见,“演义”与“外史”均演化成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文体概念,只是后者的范围要比前者更为宽泛。此外,像陈鸿《长恨歌传》这样属于历史题材的文言短篇小说在明清也被视为“外史”小说,还有冯梦龙和长白浩歌子尹庆兰以“外史氏”身份点评题材各样的文言小说,也说明在他们心目中,“外史”小说还包括文言小说在内。
虽然“演义”与“外史”都是小说家们积极、努力提升古代小说地位的表现,然而二者却存在角度和程度的差异。“演义”小说主要通过强调小说具有与正史相同的教化功能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对此谭帆先生先后引述朱子蕃《三教开迷演义序》、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尤其是东山主人《云合奇踪序》,并对后者的理论总结道:“由此可见,以‘通俗’的形式来实施经书史传对于民众所无法完成的教化使命是‘演义’的基本特性和价值功能。明人正是以此来确立‘演义’的存在依据及其地位的。”[15]可知“演义”小说理论与隋唐时期的小说理论比较并无二致。究其原因,当与彼时人们对小说的偏见有关,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云:“史统散而小说兴。”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则直接称:“小说者,正史之余也。”于此可见,他们本来就只是将小说作为正史的附属品来看待,那么为了提高小说之地位,必然要从功能角度去强调。相反,“外史”虽然也强调小说的教化功能,但更突出与正史不同的方面。他们坦然宣称小说的叙述方式和题材选择与正史相反相对,且借用渊源有自的“外史”一词来命名,所体现出来的魄力和勇气要比“演义”高出甚远。
同时,明清“演义”小说数以百计,与“外史”小说的寥寥十数部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这样的事实恰恰说明了与古代小说创作的日臻繁荣相比,对小说本质特性和自身地位的理论认识却难以摆脱正史长久以来的影响而略显滞后。“外史”独特而又积极的小说理论价值和小说史意义显得尤为可贵。
2.“外史”与“野史”“艳史”等其他诸“史”题名
除“外史”以外,明清通俗小说还经常选择“野史”“艳史”等其他“史”为作品题名。因此,在讨论“外史”的小说史价值和意义时,也需要跟这类作品作一比较。笔者特根据《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等大型小说论著对“野史”“艳史”等小说作品进行总结,并制简表如下:

表1 明清以“史”为名小说分类统计
由表1可知,在明清以“史”为名的诸多小说作品中,“外史”小说在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而这本身恰恰说明了“外史”作为小说题名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即“外史”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正统的出身对饱受传统史官文化熏染的小说家们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下面我们将这些题名逐一分析,以见它们与“外史”在小说理论价值和小说史意义上的差距。
先看“野史”,按《辞海》的解释,野史是指旧时私家撰述的历史,在古代有“稗官野史”的说法。因此,“野史”原本是出于补史之缺而成的私人史书,这与隋唐之后文人对“外史”的理解一致。在小说领域内,“野史”小说中《三朝野史》《历朝野史》和《玉壶野史》则为历史小说,而小说家们也依然强调“野史”的补史意义,如刘鹗所云:“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虚证诸实在。”[16]也就是说,“野史”进入小说领域后其意义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可见,“野史”小说仍自觉地从补遗的功能角度来附骥于正史,这是与“外史”最主要的不同。个中缘由就在于“野史”固有的自卑心理使之不得不向正史靠拢以确认自身的存在价值。而其他“野史”小说均属于情爱题材,其中大量的低俗情色描写使得“野史”一词几乎成了艳情小说的代名词。总之,这两点使得作为小说题名的“野史”无法与“外史”相提并论。
再看“艳史”“浪史”“媚史”等题名。这数个题名比“野史”更为直接地标明了所叙故事的艳情性质,“艳”“浪”“媚”等词即是对故事性质的说明。显然,“艳史”“媚史”还有其他像“秘密史”“趣史”等题名,都没有任何的小说理论价值和小说史意义。
最后看一下“小史”和“逸史”等题名。这类小说同样属于历史和情爱题材,“小”“逸”及“佚”“遗”“剩”等明显暴露了它们与正史相比之下的底气不足,而且《禅真逸史》和《驻春园小史》在后来刊刻时又分别改题为《残梁外史》和《驻春园外史》,这也充分表明了“外史”要比“逸史”和“小史”等更有分量和意义。
比较可知,明清作为小说题名的诸“史”几乎没有任何的理论阐发,有的仍自视为正史之附庸,有的则只是纯粹地对故事性质作了说明。于此更可见“外史”意义的独树一帜。后来民国时期不肖生《留东外史》和张恨水《春明外史》等“外史”小说的相继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对“外史”作为小说的小说史意义进行简单的补充总结:第一,在小说领域内,“外史”题名的使用实际提出了一个小说等同于“外史”的小说“外史”观,并从小说虚构的创作方式和生活化的取材角度对小说本质特性有了一个较为深刻准确的把握。第二,“外史”作为古代小说的一个文体概念,体现出了古代小说积极摆脱正史之附庸、争取文体独立的小说史意义。第三,在明清时期,“演义”小说引领一代风潮,却仍然固守着唐代以来视小说为“史之余”的观点,通过强调小说具有与正史相同的教化功能来保证其地位的确认和价值的提升;而“外史”在这样的氛围中却开创性地宣传小说是与正史迥然有别却又平起平坐的文体形式,意义非凡。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和批评史上,“外史”的价值和意义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以上所论,如有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学者赐教。
[1] 王以兴,杜贵晨.“外史”名义的历史变迁[J].求索,2014(4):169-173.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129.
[3] 李云翔.钟敬伯评封神演义序[M]∥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401.
[4] 吕熊.女仙外史[M].刘远游,黄蓓嶶,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
[5] 吕熊.女仙外史自跋[M]∥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214-215.
[6] 刘昫.旧唐书(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53.
[7] 吴敬梓.儒林外史汇校汇评[M].李汉秋,辑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87.
[8] 黄人.小说小话[M]∥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170.
[9] 高继衍.蝶阶外史[M]∥晓园客.清人稗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2.
[10] 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方土人,罗婉华,译.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203.
[11] 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44.
[12] 杜贵晨.《女仙外史》的显与晦[J].文学遗产,1995(2):118.
[13] 何悦玲.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传关系认知的历史变迁[J].思想战线,2011(1):117-120.
[14] 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45.
[15] 谭帆.“演义”考[J].文学遗产,2002(2):101-112.
[16]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77.
责任编辑 虞晓骏
The Supplementary Verification on the Value ofWaiShi
WANGYi-xing/ShanXiNormalUniversity
WaiShi, evolving from the earliest historiographer to literature, is especially a stylistic concept of ancient fiction, which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value of fiction. First,WaiShi, as a fiction, has two basic meanings. One is the fictional narrative mode, the other is the stories of living. Secondly,WaiShi, as a fiction, is actually an effort of novelists breaking away from the situation of fictions being the vassal of official history, showing a strong sense of respecting for the style. Finally, the special fictional value ofWaiShiis especially prominent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itles such as Yan Yi, Ye Shi and Yan Shi, etc.
WaiShi; fiction; respect for the style; Yan Yi
I207.41
A
2095-6576(2015)04-0074-06
2015-05-13
王以兴,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小说研究。(zhilihui198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