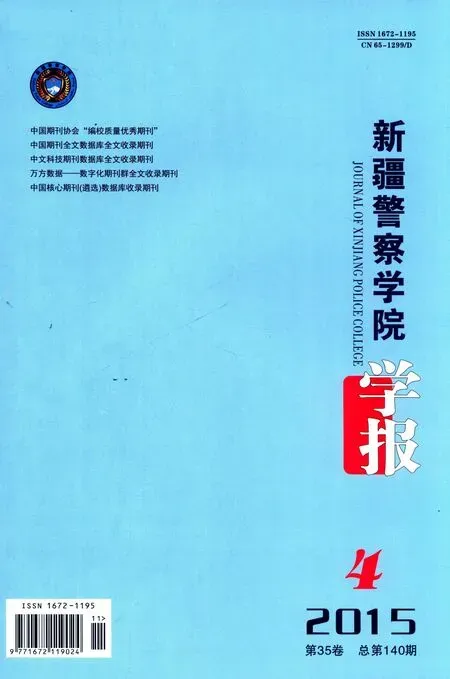执行中追加共同被告为被执行人问题的探讨
——以执行权的合理配置为视角
姬梅
执行中追加共同被告为被执行人问题的探讨
——以执行权的合理配置为视角
姬梅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新疆乌鲁木齐830000)
共同诉讼制度是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领域。被执行主体的追加与共同诉讼被告分属执行、诉讼两大不同阶段。在执行实务中常见一些当事人因单一之诉的生效判决作为执行依据遇到执行障碍,转而在执行阶段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况,由于缺乏具体规定,从而造成审判与执行实务的困惑。应在完善我国共同诉讼制度理论的前提下,在执行程序中提出追加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的共同被告为被执行人,以合理配置执行权。
追加被执行人;既判力与执行力;必要共同诉讼类型;执行裁判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基于当事人责任财产所及的第三人作为既判力与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对象而被追加的情形,同时又在实体法、程序法规定的共同诉讼人的范畴内。本应进行共同诉讼,却以单一之诉的生效判决作为执行依据,遇执行障碍时,再依据实体法、程序法关于共同被告的规定追加未参与诉讼的人员为被执行人,超越了既判力与执行力的主观扩张范围。执行裁判权在该领域的权利范围是受限制的。
一、被执行人追加制度理论基础溯源
执行当事人的追加,是指在执行程序中,执行依据所确认的被执行人无能力履行义务,被执行人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由执行机关依法裁定将其他与被执行人直接相关联的,具有权利、义务关系的案外主体加入到执行程序中来,与原被执行人共同履行义务的制度。
(一)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理论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理论界普遍认为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是执行当事人变更与追加的法理依据。既判力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是指确定的终局判决所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双方当事人和法院都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是指判决所涉及主体的效力范围,确定判决并非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其约束的人应当有明确的范围,此即既判力主观范围研究的范畴。
(二)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理论
既判力、执行力和形成力属于民事判决的实质法律效力的三个方面。判决的执行力有狭义和广义之分,通常所说的执行力是狭义的执行力,即为了实现裁判中所命令的给付内容而可以利用强制执行程序的裁判属性。①判决执行力的主观范围是指基于某债务名义,何种范围的人可以申请执行或者可以对何种范围的人进行执行。有学者将其称为判决执行力的扩张或执行根据的扩张。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与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在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但二者效力不同。其一,执行力扩张的主观范围大于既判力扩张的主观范围。生效的法律文书作为执行根据,在我国并不局限于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还包括不具有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既判力效力的仲裁裁决书、调解书以及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故执行力扩张的主观范围包括与既判力扩张的主观范围相同的主观范围和在既判力扩张的主观范围之外扩张的主观范围两个层次;其二,两种扩张理论具有不同的目的。既判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重复判决或者做出前后矛盾的裁判,不直接涉及到第三人能否执行的问题。执行力主要是调整前诉与强制执行的关系,其目的是,对于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所及的特定人员不再通过新的诉讼程序,而是通过执行中的裁定追加程序直接依据原生效法律文书为特定第三人实施执行或者对特定第三人实施执行。
二、我国被执行人追加制度的立法现状及评析
我国被执行人追加制度的法律规定,散见于《民事诉讼法》第232条、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5年《民诉法解释》)第472条至475条和《执行规定》第76条至83条中。关于执行当事人变更、追加对象,学理界概括为以下几类:一是权利义务继受人;二是为当事人及其继受人利益占有标的物的第三人;三是基于当事人责任财产所及的第三人;四是基于执行公权力本身特性而引起执行当事人变更。①沈志先.强制执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19—122.
笔者认为,前述分类中的第三类,即基于当事人责任财产所及的第三人作为既判力与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对象而被追加为被执行主体,实务中存在诸多理解及适用的混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无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个人合伙组织及合伙型联营企业、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开办单位及股东的对外责任主体问题,在相关实体法,即《民法通则》第3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45条,《合伙企业法》第2条、第39条,《个人独资企业法》第2条、第31条,《公司法》第14条、第35条中均有共同诉讼被告的规定。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执行实务中常见一些当事人因单一之诉的生效判决作为执行依据遇到执行障碍,转而在执行阶段申请追加被执行人时,超出《执行规定》的前述现有范围,直接依据实体法关于共同被告的规定追加未参与诉讼的人员为被执行人。例如,随意扩大《执行规定》第76条的适用范围,不区分有无法人资格的前提条件,不区分个人独资企业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将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直接依据《公司法》第63条,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近年来,当事人依据《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不经诉讼,直接追加被执行人的现象增多。
与前述执行实务中一些当事人依据实体法共同被告的规定,不经共同诉讼直接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现象形成对比的是,学理界有观点认为《执行规定》第76、77、78、80条规定的追加或者变更执行债务人是基于连带责任,这与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理论是不同的,将其规定在民事执行的其他制度或者其他的部门法中,逻辑上更加严密。
(二)诉讼阶段,对于实体法规定为共同被告的案件,是否为必要共同诉讼存在模糊认识。往往出于诉讼效率的现实考虑,不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释明而以单一诉讼的方式结案,这类案件,包括《执行规定》中亦可裁定追加为被执行主体的情形。以在执行中可直接追加为由,对于个人独资企业为被告的案件,不列投资人为共同被告;对于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公司为被告的案件,不列总公司为被告。但是对于合伙类案件,出于实务中的普遍共识,往往在诉讼阶段就已按照必要共同诉讼进行审理。执行中要求追加合伙人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则鲜见。
笔者认为,解答上述实务中的困惑,不仅要从诉讼法的角度分析,更应从实体法中关于权利义务承受人的规定出发,探寻共同诉讼制度的原理。共同诉讼与既判力扩张的关系问题是研究的一个侧重点。
三、我国共同诉讼制度的立法现状
我国关于共同诉讼的制度从程序法层面看,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第52条、第132条以及2015年《民诉法解释》第73条、第74条、第76条中。在该程序法框架内,将共同诉讼划分为诉讼标的为共同的必要共同诉讼以及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的普通共同诉讼两种类型。2015年《民诉法解释》有关诉讼参加人中的共同诉讼人问题在保留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意见》)第43条至56条列举的9类共同诉讼人的前提下,仅细节上有所修改,共同诉讼制度本身未有新的发展。
程序法继续将共同诉讼人之间原来没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诉讼标的虽不同一,但由于当事人之间存在事实上或法律上的牵连关系而在彼此之间产生了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情形,都作为诉讼标的共同情形,而列入必要共同诉讼的范围,这些增设的必须合并审理的连带责任的规定及大量扩张的共同诉讼的规定,给出了“连带责任←→强制共同诉讼”的公式。2015年《民诉法解释》在因挂靠、代理而产生的连带责任中,适时强调了根据债权人的请求来确定当事人,赋予了债权人对连带债务人起诉时的选择权。
我国实体法对于共同诉讼表现出的是对共同被告进行单一诉讼的容忍。共同诉讼领域的相应实体法变动也呈现出明显的权利保护趋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5条)标志着“连带责任←→强制共同诉讼”的公式不再具有普适效力。此后,《担保法》《票据法》《产品质量法》《专利法》等部门法进一步奠定了“连带责任≠强制共同诉讼”的结论,同时促成了司法政策的改变。《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的实施更进一步明确,即使连带债权人或连带债务人内部不具有合同关系,也不一定要采用共同诉讼的方式进行诉讼,从而基本实现了与大陆法系相关制度的对接。
我国实体法与程序法在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上的不和谐与分离,突出表现在连带之债上,一些被强制合并,一些又被任意合并。从深层次上看,其根源在于我国现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实质上是仅仅按照大陆法系最原始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理论所设置,该制度已经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我国程序法上现行的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司法实务的需求。
四、以完善我国共同诉讼制度理论为前提,合理配置执行权,对被执行人追加制度的几点思考
借鉴国外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对我国的必要共同诉讼进行改革,通说认为,我国现行的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应当借鉴大陆法系的分类方法,分解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如遗产继承纠纷、赡养纠纷、共有权人诉讼)和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如股东派生之诉、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关于实践中存有争议的连带责任问题,应建构牵连性的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即准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准必要共同诉讼是介于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之间的特殊诉讼类型,同时也是一种与争点效力①争点效力,是指前诉判决理由中的主要争议事实,双方当事人积极举证质证后,经法院审理于生效判决中认定的事实,对由相同当事人参加的后诉中对法院的约束力。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将判决的确定效力限于判决主文,但想要实现确定判决的遮断效果,往往必须考虑整个判决的内容,包括判决理由,而这正是争点效的势力范围.在我国,与争点效的概念对应的则是判决的“预决效力”,主要是从证据的角度出发,认为预决事实具有免证的效力。主要体现在《民诉意见》第75条和《证据规定》第9条中。扩张相配合的制度。在诉讼标的牵连型诉讼中,民事实体法追求对权利人加强保护,而民事程序法要求尽可能地合并处理诉讼标的牵连纠纷的不同价值追求,二者应有主次之分——以加强权利保护为主,以统一裁判为辅。我们虽然可以承认民事程序法有其独立于民事实体法的价值,但其价值体现亦应以不抵触实体法追求为底线。如果原告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应对诉讼标的牵连型诉讼时,首选应该是共同诉讼,这是争点效力片面扩张使然。
在完善我国共同诉讼制度理论的前提下,再回到被执行主体的追加制度中来,笔者认为,可以在执行程序中提出追加实体法、程序法规定的共同被告为被执行人。
第一,必须遵循法定原则,追加被执行主体要遵循法律、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不能超越既判力与执行力主观扩张范围,应合理配置执行权裁判权在该领域的权利范围。当然,今后的立法以具体列举和抽象概括相结合的方式规定被执行主体的追加范围确为务实之举。需要指出的是,执行实务中普遍存在的基于《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实体法规定,对于夫妻共同债务在执行阶段直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的做法是对《执行规定》突破的一个例外。对于执行实务中,大量出现的当事人依据《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追加被执行人的现象,笔者认为,公司解散、清算纠纷在《公司法》解释(二)中,专项规定了公司债权人通过诉讼以公司股东等相关人员为共同被告的救济途径。未尽清算义务的股东不属于被执行主体追加的对象。对于《公司法》第20条规定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案由规定明确公司债权人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这一诉由进行救济。故执行程序中,不能直接否认公司法人人格。公司股东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在《公司法》解释(三)关于股东出资纠纷中,明确规定了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明确规定了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同时基于《执行规定》第80条的扩大解释,该情形亦在执行追加的范围内。近些年的执行实务表明,执行追加程序中,认定公司股东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往往是通过调查验资户进账、出账往来信息,验资报告、评估报告等直观证据、表面证据作出认定。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简化公司注册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删除原《公司法》第29条,即“股东缴纳出资后,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的规定。删除原《公司法》第33条中将出资额应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规定。解释(三)第12条,将“股东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的行为”从条文所列举的五种抽逃出资行为中予以删除。那么,鉴于《公司法》的上述修改,“出资不实、抽逃出资”作为待证事实,其认定将会趋于复杂化。通过执行裁判权听证程序中对外观证据的表面审查予以追加勉为其难。该领域应完全由审判权进行规制。公司债权人应以必要共同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而不应在执行程序中进行追加。故《执行规定》第80条应作相应调整。
第二,共同诉讼案件在诉讼阶段,针对原告方的诉讼请求,经识别涉案的法律关系,判断合一确定的必要后,对原告方应尽到释明义务,依法及时追加或通知必要的当事人参与诉讼。通常为充分保障生效判决的履行,原告方首选的应该是共同诉讼并及时采取诉讼保全措施。避免日后未被诉讼的共同被告做出藏匿转移财产等规避执行的行为,导致执行程序的拖延,执行难度的加大。例如,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公司为被告的案件,如在诉讼时就将偿债能力不足的分公司与其所属的总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其效率远高于在执行阶段因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再追加分公司所属的企业法人总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方式。
第三,救济途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中遗漏共同被告,属于诉讼主体不适格,生效判决应当被依法提起再审。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准必要共同诉讼如果按照单一诉讼已进行完毕,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判决效力能否扩张?例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被告的案件,执行中该公司无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执行中不能直接追加其法定代表人即股东为被执行人,理由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属于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所及的对象,即不在生效判决的判决主文针对诉讼标的所作的判决的范畴。那么,是以股东为被告另行提起诉讼,还是以遗漏共同被告为由,对原单一之诉的生效判决提起再审?由此引发的争议在于,另行提起诉讼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我国经过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正式规定于2015年《民诉法解释》第247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再次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诉讼,判断标准在于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是否均相同。一事不再理原则包括诉讼系属的效力和既判力消极效果的效力。诉讼系属是诉讼的起点,也是禁止重复起诉适用的前提。后者指的是判决确定后,当事人不得就同一案件再行起诉,禁止重复诉讼和重复审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被告的案件,股东不属于强制合并的范围。故笔者认为以股东为被告另行提起诉讼是可行的。当然,原单一之诉中裁判理由确认的事实属于判决的预决效力,在以股东为被告另行提起的诉讼中,经当事人申请提出后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该已决事实具有的预决效力属于相对免证事实。
[1]韩波.论执行异议之诉中的“利害关系人”[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3):27.
[2]陈娴灵.许可执行之诉:强制执行程序中当事人适格之救济[J].法商评论,2010,(6):129.
[3]童付章.共同共有财产的执行与代位析产之诉的制度构建[J].政治与法律,2014,(5):145.
[4]马登科.初创与完善:对民事许可执行之诉的解读[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5):117.
On Adding Co-defendants as Person Enforced in Execution——Taking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executive power as the angle of view
Ji Mei
(Criminal Court,People's Court,Shayibake District,Urumqi,Xinjiang 830000,China)
The common litigation system is the field where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and the civil substantive law play roles together.Adding the subject enforced and common litigation defendants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stages:execution and litigation.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ecution practice,based on the effective judgment of single action,some parties encounter barriers in the enforcement,so in the later implementation stage,they require to add the person enforced.But the lack of specific provisions results in the confusion during the trial and execution.On the premise of perfecting the theory of the common litigation system in our country,we put forward to add the joint defendants as the person enforced in the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so as to configure the executive power reasonably.
adding person enforced;judgment and execution;type of necessary joint action;execution right of judgment
D925.1
B
1672-1195(2015)04-0051-(04)
责任编辑:王梅
2015-08-28
姬梅(1972-),女,满族,甘肃天水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①杨小利.民事判决法律效力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98.
【doi】10.3969/j.issn.1622-1195.2015.04.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