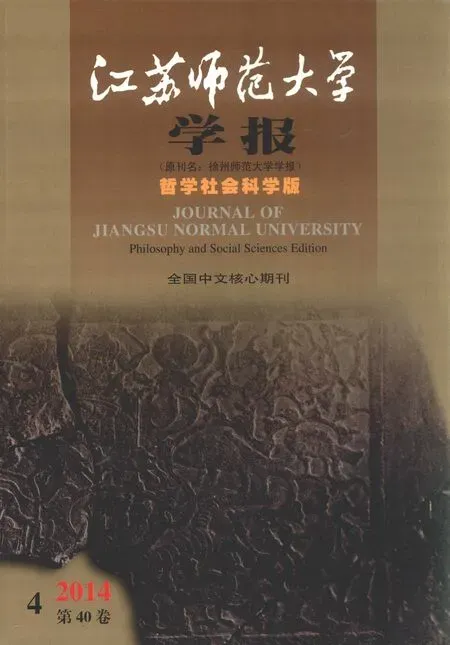道光朝旌表贞节及其争议
陆益军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241)
道光朝旌表贞节及其争议
陆益军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241)
道光;贞节;未婚守志;嫁殇;旌表
贞节是一种传统的价值观,是传统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受反封建的思维定势和学术范式的影响,学界往往将此贴上封建礼教的标签,视之为压迫妇女的精神枷锁。在论及清代妇女的贞节问题时,有人认为当时封建礼教表现出回光返照的凶残性,社会对贞节的崇奉达到宗教化的迷信程度。然而,从道光朝旌表贞节及其引发的相关争议来看,当时社会对于妇女的贞节问题,观点是多样化的。赞成者有之,批判者也有之,甚至批判者观点的激进程度并不亚于近世。调和论者认为,无论改嫁还是守节,都是符合礼制和法律精神的正当行为,人们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和选择,而选择守节意味着选择了艰难,并非一般妇女所能承受,其所蕴含的情义、责任、忠贞等道德价值,是值得敬重和旌表的。他们还分析了贞节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原因,在于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早婚陋习,并呼吁革除陋习以摆脱贞女的道德窘境。这些观点,超出了我们对于传统社会的认识和想象,既丰富了清代妇女史研究的细节,也为审视清代妇女观提供了新的视角。
旌表贞节是清代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道光朝处于清代由盛趋衰、社会矛盾积聚、道德状况堪忧的历史时期。为扭转道德颓势,道光除大力表彰孝义、忠义、名宦、乡贤等外,还大规模地旌表贞节。其旌表贞节规模之大,超过清初以来任何一个时期,这引起了社会的密切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中的观点,为我们认识清代的妇女观,提供了重要视角。
一、道光朝大规模旌表贞节概述
道光朝(1821-1850年)旌表贞节,遵循着乾隆以降的定制,每年表彰一批守节合制、夫亡殉节、未婚守志的妇女,各给银建坊,以励风化。守节合制,也称节妇,指妇女在丈夫去世之后,拒绝改嫁,守节达到政策规定年限者。夫亡殉节,也称烈女,指妇女在丈夫或未婚夫去世之后,殉夫而死者。未婚守志,也称贞女,指女子已经许嫁订婚,在未婚夫去世后誓志不再嫁者。据《清宣宗实录》记载,自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共旌表守节合制58,981人,夫亡殉节1,123人,未婚守志969人[1]。
降低已故节妇的旌表年限,是道光时期的调整措施之一。清初规定:“节妇自30岁以内守节,至50岁者,即行旌表。”[2]这个规定,对那些同样坚贞守节而亡故的妇女,因未达到政策规定年限而得不到旌表,未免令人惋惜。雍正时期对此作了调整,规定“节妇年逾40而身故,计其守节已逾15载以上者,亦应酌量旌奖”[3]。道光四年继续进行调整,规定对守节“已及10年”而身故的节妇予以旌奖[4]。门槛的降低,在客观上扩大了朝廷旌表节妇的规模。
最令人瞩目的举措,就是从道光七年开始,对那些已故的、未曾获得过官府旌表的节烈女性,进行集体旌表。这项工作,自雍正以来就试图开展,直到该年,江苏武进、阳湖两县的士绅经多年努力,搜采了贞孝节烈妇计3018人。“其中或系子孙务农服贾不知旌扬之典,或系该妇女清操苦志不求褒奖之荣,或后嗣式微,或乡间僻处,以致数百十年来,苦节久淹。”他们将这些节妇的事迹和名册上报,并提出具体的旌表办法:由各县士绅捐资建立总坊、设立匾额,将节妇姓氏全部刻在其中,进行集体表彰。江苏巡抚陶澍、两江总督琦善、江苏学政辛从益,将此事联名上奏,说“该节妇等性坚金石,节凛冰霜,或守义于终身,或全贞于白首,或未婚而殉烈,或少寡而捐躯,殉大节之无亏,亦舆情之悉协”,请求“推广皇仁,补请旌表,以励风俗而慰贞魂”。道光帝于该年七月十八上谕中予以批准[5]。
道光帝批准的上谕,拉开了大规模旌表贞节的序幕。自此,“江苏各属汇请者次第举行”。阮元(1764-1849,江苏仪征人)称此举为“前此所无”、“卓绝千古”、“旷代所未见也”[6]。
道光九年,安徽巡抚邓廷桢闻风而起。其后,河南巡抚杨国桢、江西巡抚吴光悦、湖南巡抚苏成额继而响应,浙江巡抚富呢扬阿、陕西巡抚史谱、四川总督鄂山、山东巡抚钟祥、护理贵州巡抚完颜麟庆、云南巡抚伊里布、广西巡抚惠吉、福建巡抚魏元烺、广东巡抚怡良、湖北巡抚赵炳言、宗人府、山西巡抚吴其浚等相继跟进。据《清宣宗实录》记载,自道光九年十月至二十七年五月间,各地建总坊旌表妇女的数目超过20万人,其中贞节数目为195,555人。江苏、安徽两省的旌表数目最大,各达5万以上,占总量的半壁江山。山东、江西、河南、湖南四省旌表的数目,均达万人以上[7]。
鉴于地方积极奏请而礼部审核程序繁琐,道光帝于二十七年六月谕令礼部简化程序,归入“年终汇题”,在“题本内声明汇建总坊字样,用昭区别”[8]。此后,《清宣宗实录》中不再出现相关的信息。其具体旌表的情况,可通过年终旌表数字的骤然扩大,略窥大概。如道光二十七年,旌表守节合制9,062人,夫亡殉节122人,未婚守志408人[9];二十八年,守节合制12,323人,夫亡殉节281人,未婚守志328人[10];二十九年,守节合制9,586人,夫亡殉节564人[11]。此前每年旌表的数目,最多不超过2,700人。这三年旌表人数之多,可见包括各类旌表在内。
二、对旌表活动的批判:无耻、非礼与嫁殇
道光朝旌表贞节规模之大、地域之广、人数之多、实为前所未有。这吸引了不少士绅投入其中,或钩稽往事,或记载见闻,或抒发议论。正如刘毓崧所说:“表微阐幽,令闾间有所观感,不独有司职所当为,即乡之士大夫亦与有责焉。”[12]
然而,一些政府官员和士绅在具体运作中的言行,出现极端的倾向。如张德馨(1800-1878,江苏仪征人)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了自己在任山西朔平知府时的一段往事。他认为,当地妇女“不知耻廉,名节甚轻”,竟然有守志多年忽思改嫁者,感慨“人心风俗之坏,莫大于此”。于是,他“将国初以来旌表节妇,查明姓氏,于城东旧官庙建立节孝祠,设立木主,令地方官春秋致祭。迎主入祠之日,用鼓吹仪从导引,俾妇始咸知愧奋”,期望以此“劝化愚顽”[13]。这种极端倾向,客观上对改嫁取向形成压抑。
现代学界津津乐道的俞正燮(1775-1840,安徽黟县人)之妇女观,正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道光十三年会试落榜后,俞在师友的帮助下刻成《癸巳类稿》。在《节妇说》一文中,他对要求妇女守节的言论展开批判,为妇女改嫁的取向进行辩护。他批评“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是对《礼记》经文“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的错误推衍,是“礼义不明”的产物。按照礼义,“夫妇合体同尊卑”。如果说妇女无“二适之义”,那么男子也应无“再娶之义”。如今的男子“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却要求“妇无二适”,实在是“无耻之论”。纵观历史,改嫁屡见不鲜,史不绝书。如唐朝贞观元年二月的诏令,允许妇女在丈夫去世后,办完葬礼、服制期满,可以改嫁,愿意“守志贞节”者则“任其情”。《通典》也记载,元朝之妇女改嫁,“人未尝以为非”。他强调,妇女改嫁是合礼合法的行为,世人“不当非之”,那些“怒再嫁者”,应该闭上嘴巴,“精力之斯可矣”[14]。在《贞女说》一文中,他叙述了一则贞女故事。安徽女子罗静因未婚夫朱旷办理其父葬礼而亡,“静感其义,遂誓不嫁”。他认为像这样不为名利、只因刻骨铭心的感动而誓死守志的女子,才是真正的贞女。对于那些既无感动,也未经亲迎、宴饮、庙见、同衾同穴等环节成为正式夫妇,却以年轻的生命为死者守志或自杀的女子,他感到“义实有难安”。旌表这种价值取向,必然会酿成悲剧,这不应成为社会的“荣耀”。他引用一首诗讽刺道:“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返魂。”[15]
与俞正燮持相似观点的人,实际上大有人在。他们祭出两大人物为其观点的代言人,藉以批判未婚守志、未婚殉夫为“非礼”的无意义行为。一是明朝的归有光(1506-1571,江苏昆山人),他在《女论》文中宣称,“女未嫁人,而或为其夫死,又有终身不改适者,非礼也”。根据《礼记·曾子问》的规定:未婚而男方父母去世,女子是可以改嫁的,何况未婚夫死呢?即使亲迎之后,女子未曾拜见舅姑,也不算是正式夫妇,死后不能葬于男家。这样,女子未嫁而不改适或为其夫而死,还有什么意义呢?实在是“无谓”之举。这样做,不但违反了阴阳和合的自然精神,也违反了以夫婿亲迎、共牢合巹、庙见舅姑为标志的婚姻原则,属于“非礼”的“私奔”行径[16]。二是清朝的汪中(1744-1794,江苏江都人),他在《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一文中,继承了归氏的观点,批判未婚守志为非礼行为,坚决主张改嫁。他说“亲迎也,同牢也,见舅姑也”,是夫妇名分正式确立的标志。根据《礼记·曾子问》的说法:未经亲迎,女子是可以改嫁的,包括男方辞婚、女方辞婚、男过期不娶、女过期不嫁四种情况;未经同牢合巹,就没有“三年之恩”,女子在解除服制后,是可以改嫁的;未曾庙见舅姑,女子的妻子与媳妇身份就未被正式承认,死后也不能葬于夫家。因此,“女子许嫁而婿死从而死之、与适婿之家事其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非礼也”。他嘲笑那些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的女子,好比齐楚之君死、鲁卫之臣号呼而自杀,两者之间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是悲哀的行为。“本不知礼,而自谓守礼,以殒其生,良可哀也!”他呼吁社会对此进行抵制:“女子欲之,父母若婿之父母得而止之;父母若婿之父母欲之,邦之有司、乡之士君子得而止之。”[17]他鼓励未婚青年女子摆脱名节的桎梏,勇敢地追求幸福美满的生活。
更有甚者,将未婚婿死而死与守志和迁葬、嫁殇联系起来,呼吁社会予以禁止。如陈立(1809-1869,江苏句容人)在道光二十三年编成《句溪杂著》,他在《禁迁葬者与嫁殇者考》一文中说:迁葬“谓生时非夫妇,死既葬迁之,使相从也”;嫁殇是“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礼相接,死而合之”;两者实属“一事”,都是“乱人伦者也”,“非礼之礼”也,为圣人所禁。夫妇名分的确立以男娶女嫁、同牢合卺、庙见舅姑为标志,这是《礼记·郊特牲》中“一与之齐”的意思。未“齐”而改嫁,不但符合礼制的精神,也符合法律的规定。当今法律明确规定,“未婚之女改嫁,仍得封诰”,女子不必为此焦虑。未婚守志是一种与死人的婚姻,与“嫁殇之义似,与迁葬相比”,是“非礼”之举。“礼之所非,即礼之所禁”,社会对此应予以禁止[18]。
三、调和与折中:对贞节价值的维护
旌表与批判旌表的对立观点,引起了当朝学者的思辨。礼制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夫妇关系确立的标志究竟是什么?妇女在丈夫或未婚夫去世后的三种取向,是否违反了礼制的规定?未婚守志与嫁殇迁葬的性质是一样的吗?贞节的价值是什么?
胡承珙(1776-1832,安徽泾县人)在《驳室女不宜守志议》一文中,对政府旌表未婚守志“而议者多非之”表示不满,发出“过矣”的感慨。他认为婚姻成于纳徵,而非亲迎、共牢、庙见。纳徵之后,婚姻存在诸多变数,如父母死或未婚夫死,女子改嫁还是守志,决定权在于自己。先王所制之礼,依据的是普遍人情,“不强人之甚难,亦不禁人以独遂”。如果有“艰苦刻厉以自遂其志者”,虽“圣人复起,犹将许之”,必然不会反对。对待礼文,绝不可拘泥,不可以“先王所未言者即为非礼”。对于批判者的言论,他认为是“不知先王之微意,而以其所未言者禁人之行”,是不符合礼制精神的。如此对待贞女,实在是“不仁之甚”[19]。姚莹(1785 -1853,安徽桐城人)在道光十八年撰写的《吴黄二贞女传》一文中,指出归氏后来改变了观点,在《张氏女贞节记》中肯定贞节为“圣人之所不禁”。汪氏“不见后说,反录前论”,实在偏颇。他认为先王制礼取乎其中,“至于非常之事,不能望之人人者”,先王则“不为定制”,而采取“表而旌之”的办法,予以褒扬。学者之于经文,切不可拘泥于文字之间。“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妇女“夫死听其改适,能守则旌之”,这才是礼制的精神。否定贞节,是诱导天下女子“不守其身“,是对礼制精神的严重歪曲[20]。
李惺(1785-1863,四川垫江人)在《霍勒霍屯氏守义》文中,记述了道光十三年间蒙古正白旗贞女霍勒霍屯氏“守义以终”的感人故事,对当时人们评论之为“未为人妇而守妇人之义,非礼也”的观点,表示愤慨。他认为,霍勒霍屯氏的行为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自我抉择,并以其毅然决然的姿态,诠释了对情义的理解。他指出:“义之所在,即礼之所在。”女子既已许嫁系缨,就表明身心已有所属,就应该义无可绝。“义不关乎嫁与未嫁,而视乎能守不能守。”他反驳道:“夫以守义者为非礼,岂义无可绝而绝之者之有当乎礼耶?”[21]王廷植(江西庐陵人)在《书归震川贞女论后》文中,认为归、汪二氏的观点悖谬至极。他指出,忠义贞节是天地“赖有为之柱础者”,乾坤得以不敝者。在贞女的身上,折射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光芒。“闻丧哀痛,仁也”;“不改适,义也”;“为夫持服,礼也”;“矢之以死,确然知此是而彼非,智也”;“盟书在前,生死不贰,父母不能夺其志,舅姑不能阻其来”,信也。纵观史册所载,贞女秉性温良,知礼守法,“以贞白自砥”,处境艰难而甘之若饴,履之若素。世俗的富贵贫贱、祸福利害、欢戚忧惧、患难死生,都不能动摇她们的决心。她们是“天地之完人”,“宜乎与忠孝节义同为国典所褒”[22]。这正是旌表贞节的价值所在。他不反对改嫁,但绝不容忍人们玷污贞女。
胡培翚(1782-1849,安徽绩溪人)在《周礼嫁殇说》一文中,批判了将未婚守志等同于嫁殇的观点,指出迁葬、嫁殇都是“生不以礼相接,死而合之”的非礼行为,而未婚守志是“生时已有夫妇之道”,两者不能相提并论[23]。刘毓崧(1818-1867,江苏仪征人)在《嫁殇非未婚守志辩》一文中,也批评“近代通人”将未婚守志等同于嫁殇的观点,指出两者“实则迥异”。“冥婚者,男女并亡;未婚守志者,夫夭亡妇在。冥婚者,本无婚姻之约;未婚守志者,早定夫妇之名。则未婚守志非冥婚可比,明矣。”[24]
刘毓崧的《嫁殇非未婚守志辨》一文,则堪称当时争论的集大成者。此文除批判“以未婚守志者为嫁殇”的观点外,还依据经史之籍,深入考证,澄清人们对于贞女的困惑和责难,阐明其价值。他列举了六条证据,否定归、汪二氏的亲迎、同牢共卺、庙见说,指出:夫妇名分“定于纳币,非定于亲迎”;《礼记·曾子问》称未婚夫为“夫”,可见未婚夫虽死而夫之名犹在,女子只有在改嫁之时,才与原聘之夫义绝;汉代郑玄认为未有三年之恩,“女服斩衰”,说明未婚夫妇之间存在服制,而且服制与已婚者相同。他举证反驳了归氏认为女子无权决定自己命运的观点,指出:女子许嫁之时,必在家庙举行仪式,表明将先祖之遗体许人;许嫁既是父母之命,也是先祖之命;根据《春秋》之义,先祖之命重于父命;女子如果决定未婚守志,“纵使父母欲夺其志,为女子者不肯以先祖遗体再许他人,亦得奉王父之命以辞父命。”他列举了两证,反驳汪中视贞女及其奔丧为“齐楚之君死,鲁卫之臣号呼而自杀”的观点,指出:贞女奔丧,由来已久,最晚出现在汉朝王肃的《丧服要记》中;女节与臣节本质相同。根据左氏《春秋》之义,“委质于庭”、宣誓效忠朝廷的官吏,君臣名分既定,则其志不移,“必死节于其君,而不敢怀贰”。女子既纳币,夫妇名分就已确立,犹如“臣之书名于策”、“委质于庭”。贞女“其志不移,如臣心之无二。其分已定,如臣节之莫渝。其不改适他姓,譬诸遗民之匿跡新朝。其以死殉亡夫,譬诸处士之致身故国。”刘毓崧列举了两条证据,证明旌表贞女的正当性,指出:《列女贞顺传》记载了卫夫人之事,留下“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的著名诗篇,证明“周时未婚守志之贞女,已得列于圣经”,后世诰命封赠未婚守志者,“实昉于此。”《后汉书·百官志》记载,“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皆匾表其门,以兴善行”,证明旌表制度最晚起于汉朝而非宋朝,“后世贞女请旌,法制实沿袭乎汉代”。至于礼制精神,他认为礼制虽对改嫁作了规定,但并不意味着“再受聘者为古礼所有”,“不再受聘者反为古礼所无”;“再受聘者为圣贤所许”,“不再受聘者反为圣贤所非”。他指出:那些贞节妇女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是值得敬佩和旌表的,是符合礼制精神的。刘氏在文末疾呼:“此义不明,吾恐继今以往,且有移周礼嫁殇之禁施诸未婚守志之女者,而旌表贞女之事,甚至欲沮格不行。彼流俗之朝死夕忘者,转得藉斯言为口实,于世道之污隆升降,大有所系也。是不可以不辩。”[25]
四、关于旌表贞节相关争论的思考
学界在反封建的思维定势和学术范式下,对历史上的贞节问题贴上封建礼教的标签。在论及清代旌表贞节问题时,认为人们对贞节的崇奉至此“已至极点”[26],达到“宗教化”[27]的迷信程度,封建礼教表现出“回光返照的凶残”[28],“守贞对妇女身心的摧残是何等的严酷”[29]。在论及清代的妇女观时,认为李汝珍和俞正燮是“两个女性同情论者”[30]。近年有学者指出,清代中期的学者钱大昕、汪中及晚期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持的妇女观,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先驱作用”,“功不可没”[31]。
从上述道光朝大规模旌表贞节及其引发的争论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后人深思:
首先,当时社会围绕贞节问题展开的争论呈现出严重的对立性。部分士绅推崇贞节,贬斥改嫁为不知廉耻,是人心风俗败坏的象征。部分士绅极力为改嫁辩护,痛斥贞节是社会强加于女性的偏见,视从死与守志为非礼,是与死人的婚约,是愚蠢、悲哀、毫无意义的行为,鼓励妇女冲破观念的束缚,抛弃名节的焦虑,追求幸福美满的生活,拒绝为之付出痛苦的代价。其言词之激烈,观点之激进,超出我们对于传统社会的认识和想象。
其次,参与争论的调和折中者显然代表了社会多数的意见。他们的贞节观和妇女观,至少有三点共同之处,即:无论改嫁还是守节,都是符合礼制和法律精神的正当行为,不应该互相歧视;无论改嫁还是守节,都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和选择,并维护其尊严;选择守节意味着选择了艰难,这条道路确实痛苦,并非一般妇女所能承受,其所蕴含的情义、责任、忠贞等道德价值,是值得珍视和旌表的。这种理解和宽容精神,也超出我们对于传统社会的认识和想象。
再次,当我们聚焦道光旌表贞节及其相关争论时,不但对俞正燮之妇女观所产生的社会环境及其指向性有了更全面的理解,还发现该时代与他持相似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有的甚至比他更加激烈。这显然突破了孤立研究个别人物观点的局限性,说明只有将人物置于其所生活的时代中进行考察,观点才能更加立体、丰满和生动。
最后,这场争论中还有两个观点值得注意。一是论者对未婚守志现象日益严重的社会根源的思考,指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旌表制度,而在于社会普遍流行的早婚陋习。如刘毓崧引用焦循(1763-1820)的观点说:“古之贞女少,今之贞女多,何也?古男女议婚晚,聘与娶一时事。故如卫宣夫人者,偶也。今人龂龂议婚,或迟五年,或迟十年,甚至二三十年。聘与娶悬隔甚远,其中死亡疾病,自不能免。”[32]这才是悲剧的根本原因。他呼吁社会改革普遍早婚的陋习,以摆脱贞女的道德窘境。二是论者对于夫死殉节问题的态度。道光之后,即位的咸丰帝即恢复康熙、雍正时期拒绝旌表夫死殉节的决定,以致在道光三十年未再旌表夫死殉节。但咸丰元年还是恢复了旌表,理由是“事后追思,该烈妇等身殉其夫,舍生取义,究属人所难能。而各省岁终汇题,不过二三十人,未必遽开轻生之渐。若给予旌表,亦足以激薄俗而励纲常”[33]。可见,政府终究摆脱不了旌表制度的传统思维。
综上所述,道光朝旌表贞节及其引发的相关争论,既丰富了清代妇女史研究的细节,也为我们审视清代妇女观提供了新的视角。
[1]统计资料来自《清宣宗实录》卷11、27、47、63、77、93、112、131、149、163、182、203、228、247、261、276、292、304、317、329、343、364、387、400、412、424、437。
[2][3]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23,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第4270、4272-4273页。
[4]《清宣宗实录》卷75,《清实录》第3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8页。
[5]陶澍:《武进阳湖绅士查出未经旌表之贞孝节烈妇女3018口请建总祠致祭题本》,《陶文毅公全集》卷19,《续修四库全书》第15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141页。
[6]刘文淇:《江甘贞孝节烈总坊录序(代)》,《青溪旧屋文集》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517册,第33页。
[7]据《清宣宗实录》卷161至卷442各省奏请旌表资料统计,其中江苏一次3,000余人、陕西一次2,027人,因名目混杂,未予统计。
[8]《清宣宗实录》卷443,《清实录》第39册,第557页。
[9]《清宣宗实录》卷450,《清实录》第39册,第684页。
[10]《清宣宗实录》卷462,《清实录》第39册,第845页。
[11]《清宣宗实录》卷475,《清实录》第39册,第984页。
[12]刘毓崧:《扬府恤嫠局新建总坊记》,见《通义堂文集》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546册,第371页。
[13]张德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页。
[14]俞正燮:《节妇说》,《癸巳类稿》卷13,《俞正燮全集》第一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629-631页。
[15]俞正燮:《贞女说》,《癸巳类稿》卷13,《俞正燮全集》第一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631页。
[16]归有光:《女论》,《震川先生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8-59页。
[17]汪中:《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375-377页。
[18]陈立:《禁迁葬者与嫁殇者考》,《句溪杂著》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76册,第565页。
[19]胡承珙:《驳室女不宜守志议》,《求是堂文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500册,第227-228页。
[20]姚莹:《吴黄二贞女传》,《东溟文后集》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第584-585页。
[21]李惺:《霍勒霍屯氏守义》,(清)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7,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468-1469页。
[22]王廷植:《书归震川贞女论后》,(清)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7,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472-1475页。
[23]胡培翚:《周礼嫁殇说》,《研六室文钞》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07册,第393-394页。
[24][25][32]刘毓崧:《嫁殇非未婚守志辩》,《通义堂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46册,第327、326-329、337页。
[26](日)山川丽:《中国女性史》,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27][30]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241、246页。
[28]汪玢玲:《中国婚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页。
[29]郭松义:《中国妇女通史·清代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页。
[31]王明芳:《清代学者的妇女观探析》,《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3]《清文宗实录》卷28,《清实录》第40册,第395页。
Dispute on Zhenjie in Dao-Guang Period
LU Yi-jun
(Department of Histor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Dao-Guang;zhenjie;virgin;marry the dead;dispute
Zhenjie also means chastity,it was a kink of traditional values and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raditonal morality education.Influenced by the mindset and academic paradigm of antifeudal,it was paste of the feudal ethical code label by academic circles,and was seen as the spiritual shackles of oppression women.Commenting the chastity of women in Qing Dynasty,academic circles claimed that feudal ethical code shows fiece and cruel as the last radiance of the setting sun,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worshiped chastity reach the extent of religion evolution and superstition.However,from the research tawards the activities of honor chasity and its controversial light in Dao-guang period,we find the social viewpoits on the chasity of women at that time was diversified.There was approver and repudiator as well,indeed the repudiator's viewpoints was so radical that was not less than the modern times.The reconciler advocated that it was reasonable act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ual of the Li and the law,no matter remarry or preserve chastity after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people should respect the will and choice of the parties,and the choice of chastity means the choice of a hard life,it was really not easy for common women to be able to support,the implication of moral value such as the friendship,responsibility and loyal,was worthy of deeply respect and honor by people.They also analyzed the reason which made the chastity became a problem,it was lied in the bad habits of early marriage which widespread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and called on abolish the bad habits to get rid of the vestal virgin's moral dilemma.These points of view beyond our understanding and imag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enriching the study of the Qing Dynasty women's history in detail,also providing new view angle to gaze at the view on women in Qing Dynasty.
K249.3
A
2095-5170(2014)04-0079-05
[责任编辑:刘一兵]
2014-03-11
陆益军,男,上海崇明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博士研究生。
——以直省民人为中心
——以方志为中心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