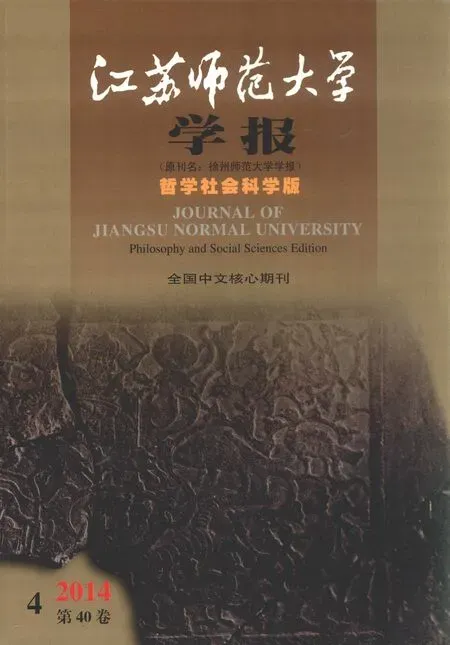转型期影响我国社会阶层流动因素分析
姜 力
(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吉林长春 130042)
转型期影响我国社会阶层流动因素分析
姜 力
(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吉林长春 130042)
转型期;社会阶层流动;所有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演变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频繁剧烈的社会阶层流动对社会发展和未来的政策取向具有重要的影响。导致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于体制转轨进程中的制度政策变革、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的经济社会结构演进,其中,所有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及身份制度改革是重要因素。而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先赋性与后致性因素对社会阶层流动也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阶层流动机制呈现出市场机制与再分配机制并行、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存的现状。
社会阶层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而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期,则显得更为频繁和剧烈,许多社会成员的职业和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对我国社会发展和未来的政策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此,有必要对转型时期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既要关注社会阶层流动的一般基础性因素,更要重视特殊时代背景、特殊国情下的一些关键性因素。
一、体制转轨进程中制度政策变革因素
制度政策可以影响社会成员的升学、就业、职位分配,影响家庭背景在代际传递中的作用。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制度政策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与其他因素相比较并不突出。而转型期间的我国,属于政府主导下的非完全的市场经济社会,在社会成员流动的途径与机会上,制度政策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左右着社会流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所作出的制度政策安排,不仅启动了我国社会阶层的流动,而且在阶层流动过程中持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系列旧制度的废除和新制度的确立,采用的是渐次到位的差别化政策。由体制外增量改革再到对旧的经济体制改革,由局部改革推进再到整体协调,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再到城市,从流通体制再到金融体制、国营企业体制。社会阶层流动也相应地呈现出渐进流动的特点,阶层流动最初是从拥有较少体制资本或远离体制核心部门的社会最低阶层开始,然后逐步转向较高的社会阶层。
(一)所有制改革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尝试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同时,也在积极扩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首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流动。我国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分化不是始于工业化,而是源于1978年之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出现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离乡遂成为解决问题的自然途径。第二,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引起了比较复杂的阶层流动。国有企业改革先后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造等阶段。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1988年承包制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国有、集体企业转制,部分职工被买断工龄、下岗、提前退休、内部退养,或者被迫转向各种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在企业改制中,相当部分产权交易是暗箱操作,国有资产被严重低估,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有关政府官员成为得益较多的群体,同时催生了更多的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据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20.3%的私营企业是通过改制或收购原国有、集体企业而发展起来的,其中,以1998~2003年发生得最为频繁,该时间段占到企业总数的70%以上。第三,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不断加强,增加了社会成员向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流动的机会。1979年国务院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1987年颁布了《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1988年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后,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由“允许发展”上升到“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所有制的改革,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从业人员比重下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从业人员比重明显上升,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兴社会群体大量出现。
(二)分配制度改革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倡导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分配方式从平均主义发展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原则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加速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一方面,社会成员在利益的驱使下,向有利于发挥个人优势的领域流动。另一方面,某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一是国有企业分配制度的变革,提高了经营管理者和垄断部门职工的经济地位。在企业中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工资分配政策,企业可以自主决定工资水平和内部分配方式,这为国有企业经营者自定高薪和不规范的职务消费提供了机会,也为垄断行业把获取的超额利润转化为部门利益和部门内职工利益提供了机会。二是权力资本所有者、经济资本所有者通过价格“双轨制”、炒原始股、炒地皮、矿产资源变相民营化等方式获得巨额财富。三是效率优先分配理念导致社会再分配政策缺失,拉大了社会阶层间的距离。1992年以后,政府从多个社会福利领域退出,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出现市场化取向,客观上加重了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负担。
(三)教育制度演变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尽管教育条件和录取政策上存在着影响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因素,但总的来说,不收费或者很少收费的教育政策为社会成员的流动提供了比较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在社会成员向上流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1980年代,每年录取的高等院校新生中,农村中的生源占到了30%多[1]。在中等专业学校、高等院校获得的文凭,成为谋取较好职位,进入较高社会层次的通行证。大中专毕业生作为人才被国家统一分配,保证了这些人无论什么社会背景及经济背景,都可以进入较优越的阶层。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期,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教育在个人水平流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提供上升流动机会的功能却在减弱,由教育导致的不平等和阶层固化的现象日益明显。一是教育收费的直线上升,增加了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难度,正规教育体系作为推进平等化的手段的作用在减弱。虽然近年来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了“一费制”和“两免一补”的政策,但重点中小学校依然实行“双轨”招生,多数名额还要高收费。1997年高等院校开始全面实行收费,费用一直呈上涨趋势。与学费水平逐年提高相伴的是重点中小学和高等院校中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比例在下降。二是随着大学扩招,在为更多社会成员提供了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人们之间的文化水平与能力的差距开始模糊,难以再用学历来区分人们的素质层次,社会底层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越来越窄。面对严重供大于求的就业市场,尽管教育在整体的收入水平上起着一定的作用,但起第一作用的还是家庭的社会背景,是人际关系和权力要素,没有社会背景的毕业生的就业机会相对减少,许多中低层家庭的子女无法实现就业,而即便就业的,其薪金水平也不能完全与教育程度相挂钩[2]。
(四)身份制度的松动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逐步深入,有关身份制度方面的限制也在逐步松动,从而为社会阶层流动提供了现实条件。一是户籍身份制的松动,便利了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流动,农业劳动者有了更多选择职业的自由。1984年至1987年,国家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稍有放开,在各级政府统一管理下,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但1988年至1991年,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国家对农民进城务工实行控制、严格管理。1992年后又开始改革、取消农民工进城的制度障碍,为农民进城务工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单位身份制的变革,改变了人们对单位的过分依赖,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流动的障碍。三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工人与干部之间的严格界限,为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提供了政策保障。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有一些制度性限制和障碍,但与从前相比已经大为改善。
二、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经济社会结构演进因素
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看,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是阶层流动的基础,经济社会结构变量引起的社会位置的增加和减少都会带来个人或群体社会位置的新的分布。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得到提升,职业结构层次得到升级,社会等级位序也得到整体提升。劳动力大量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进而又转向服务性行业。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经济组织和社会政治组织的科层化,以及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专业化。科层化组织和专业技术职位的扩张,减少了劳动力结构中纯体力劳动者的比例,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行政办事和管理人员的比例大大增加[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得到迅速推进,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1989年的26.2%,2011年达到51.3%。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产业结构的深刻调整,一方面,传统的第一产业衰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传统工业和农业也得到了改造和升级,技术密集度大为提高。这样,与传统工业和农业相关的社会阶层的比重在明显缩小,与第三产业和技术含量高的产业相关的社会阶层的比重则明显增加[4]。我国三种产业的就业结构比,由1980年的69:18:13,提高到2000年的50:23:27,2010年则为37:29:34。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引发了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较高等级职业的数量和比重大幅增加,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从我国第三、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2000年同1982年相比,在职业结构的总量中,初级层次职业(生产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比重下降8.1个百分点,而中层职业的比重则增加了7.2个百分点[5]。就业结构的变化带动了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了农业生产、城市白领群体迅速壮大。
三、个人成长进程中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
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是个人先天继承和后天获得的资本,表现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能力资本等。在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的比较中,先赋性因素一般被视为传统社会的主要社会流动机制,而后致性因素则被视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社会流动机制。但是,它们在社会时空中的存在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能完全排除对方的存在和作用,往往共同决定着社会流动。
改革开放初期,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对我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没有明显的差异。当时,各阶层之间的社会性差距很小,不同阶层的家庭之间的经济资本差距很小,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则为平等化的大众教育所抵销[6],所以家庭资本对下一代社会地位的影响并没有凌驾于个人能力之上。当时,人们实现上升流动的主要机会是体制内的升学和体制外的市场经营。1978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发挥了考生个人素质的决定作用,但在就业方面,父亲职业和社会关系对子女初职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7]。在体制外领域,家庭背景的影响还很微弱,缺乏优势家庭背景的人可以通过市场经营活动来实现经济地位的提升。
进入1990年代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逐渐凌驾于后致性因素,无论是家庭背景对子女的教育获得的影响,还是父代地位对子代地位获得的直接效应都在增强。这是因为中国社会迅速分化,不平等程度从一个比较平均的社会成长为收入分配最不平均的社会之一。在市场化进程中,中间阶层和弱势阶层凭借后致性变量有了较多的流动机会,但上升流动机会越来越少。而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阶层,代际间社会地位的继承占主导地位,阶层的继承性越来越强于后致性。强势阶层成员通过不同资本的交换、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其原有的代际之间的地位继承性在向市场转型的变革中得到保持或延续,再生产的能力不仅远远超出了自身流动的能力,而且与其他阶层相比较也远远超出了其他阶层[8]。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联合几家网站做了关于“谁在沦落底层”的问卷调查,针对造成“底层公众不能向上流动”的原因,绝大多数受访者把底层公众扩大的原因归结为外因,只有5.3%选择“个人因素为主,比如不努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转型期阶级阶层关系问题研究”课题组在2010年对部分学员的问卷调查显示,只有3.9%的人认为“市场的优胜劣汰,能者多得”是社会成员贫富差距的成因,其他人则都选择其他外部因素。可见,在社会转型期间,计划经济体制的“平均”理念并未很好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能力—业绩”理念过渡,以个人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后致性因素对近些年来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非常有限,而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强于后致性因素。
整个转型期间,主要来自于先赋性因素继承下来的社会资本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最为突出。社会资本是可以通过内部交换而获益的社会关系,具有向优势群体集聚的特性,通过已经拥有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可以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力,从而为自己提供更多的资源。社会资本的集聚特性强化了阶层的封闭性,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在历来注重社会关系的中国社会,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可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理想的工作和职位升迁。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社会资本通过与市场经济密切结合,形成了强势阶层以公共资源交换和赢利为目的的利益联盟。如:成功的私营企业主都有一张强大的社会关系网,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干部处于中心位置,与私营企业主最密切来往的亲戚、朋友中,干部占据最多数。朋友圈与亲戚圈相比,干部更多,而工人、农民更少。发展速度快、规模大的私营企业,往往是那些与当地政府各主管部门相处最融洽的企业[9]。
总之,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间,上述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社会流动机制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开放,而在另一些方面社会封闭性又有所发展,形成了同时对阶层流动产生影响的市场机制和再分配机制。在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市场系统领域,市场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支持着社会阶层在市场化的轨道上流动。那些在再分配系统中很难获得上升流动机会的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可以在市场系统中按市场运行规则来实现经济地位的上升,再通过经济地位的改善来实现社会位置的上升。而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仍然保持其优势地位,官员的权力和特权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以至于在一些重要的再分配系统领域,再分配机制占据着主导地位,强势群体通过国家公共权力市场化、权力与市场结合等方式,实现了强势阶层的再生产,从而保持着阶层地位的继承性和稳定性。
[1]孙立平:《1990年代以来社会分层的三大趋势——答友人问》,《天涯》,2004年第2期。
[2]王仲:《社会阶层流动途径的趋势与效果分析》,《学术探索》,2008年第2期。
[3]李煜:《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社会》,2009年第6期。
[4]彭劲松:《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新变化及其评价》,《福州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
[5]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点和障碍》,《职业技术教育》,2005年第15期。
[6]李春玲:《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城镇社会流动》,《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
[7]樊平:《社会流动与社会资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路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8]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9]戴建中:《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浙江学刊》,1996年第3期。
Analysis of Factors of Our Country's Social Mobil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JIANG Li
((Jilin Institute of Socialism,Changchun 130042,China)
transitional period;social class;factors;mechanism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in our country,there appeared frequently the violent social mobility,which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and the future policy orientation.The main reason for the social mobility resulted from the system policy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factors of personal ascription.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factors is that the hierarchical flow mechanism shows the parallel of a market mechanism and redistribution mechanisms,and the coexistence of open and closed status.
C912
A
2095-5170(2014)04-0108-04
[责任编辑:刘一兵]
2014-04-26
姜力,男,吉林大安市人,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