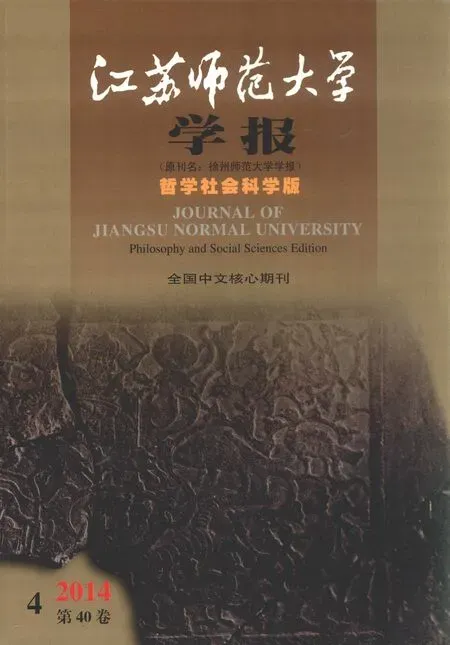从“至善”到“圆善”
——论牟宗三对康德之最高善的融摄与超越
张少恩杜 磊
(1.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2.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河北邯郸 056038)
从“至善”到“圆善”
——论牟宗三对康德之最高善的融摄与超越
张少恩1、2杜 磊2
(1.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2.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河北邯郸 056038)
康德;牟宗三;“至善”;“圆善”;德福一致;“无限智心”
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提出了“至善”论,其所论之最高善即德福一致。康德还进一步从人性论入手论述了善恶观、善与德福的关系等。康德之理论对牟宗三《圆善论》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灵感。牟宗三先生吸纳和融摄了康德“德福一致”的思想内核,在思想脉络上与康德的内在逻辑相一致,但是,牟宗三关于最高善的实现过程与康德的观点相差甚远。康德道德哲学体系的建构借鉴的是基督教模式,其凭借“自由意志”、“灵魂不灭”、“上帝存在”来确保“至善”体系的建立;而牟宗三则从“圆善”和“无限智心”出发对康德“至善”的实现路径给予批判,并最终展示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而超越于康德的“至善”进路。牟宗三以人皆可呈现之创生性的“无限智心”(仁心、道德本心)来消解康德的三大“设准”;然后,牟先生会通中西,分判儒、释、道三教,最后归宗于儒;他以“道德本心”来挺立道德主体,重铸了德慧一致的圆善论体系。牟先生对康德“至善”思想作了消融及提升,构建了现代性的道德理想主义哲学。
成书于1985年的《圆善论》是牟宗三先生晚年的著作,它是牟先生圆善与圆教问题的定论之作。其中,圆教思想是牟先生受天台宗判教的启示;而“圆善”思想,则是受康德最高善的启示;融合圆教与圆善的精神,则是秉承儒家之德性精神。牟宗三先生通过批判、消融并超越康德之“至善”思想,提出用“无限智心”来挺立道德主体,保证德福一致之实现,最后归宗于儒,重构了儒家之“圆善”体系。牟先生的思想开出了新的道德理想主义哲学。
一、“至善”之溯源与康德善恶思想之分判
(一)康德之“至善”思想
“至善”问题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有时被称为最高善。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曾经称其为“善的原则”、“真知即至善”等概念;柏拉图曾探讨过最高善即“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论述过幸福、最高善、德性等问题,并涉及到“道德”与“幸福”的完美结合;之后,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就德与福的关系问题进行争论,斯多葛派认为,“德”是最根本的,是最高善;而伊壁鸠鲁派则倾向于最高善即幸福。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西方的哲学家们很少谈论最高善问题,而康德的出现,则使局面大为改观。
康德在关于实践理性的论述中认为,平时生活中所践行的普通规范便是善,但普通规范只是基础性之善,它仅仅是德性的开始,并不是最高层级的善。要想获得真正完善的德性生活,就应该从普通的规范基础开始而展开向最高善的追求,直至实现最纯粹的道德——“至善”。“至善”作为最高善属于先天的道德律令,有的称之为“极善”(supreme good),这种纯粹的道德作为价值理性是我们践行的目标,无论是在普通德性还是在知识的理解等方面,其地位都是高于普通伦理的。纯粹理性追求一种称之为“无条件的总体”的目标,当然,这个最高目标既强调道德的寻求,同时也注重幸福的眷顾,德福一致,“作为人格的价值及其对幸福的配享”[1]。此外,人们不应该将至善的存在理解为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与方式,正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善应该是作为理性存在的人所想做的一件事。这一论断平衡了伦理学上“义务论”与“功利论”的关系,具有道德形上学的价值理性意义。
(二)人性论之分判及康德之人性论
在讨论康德“至善”思想体系时必然涉及人性论的分判,毕竟人性中的善与恶的观念是构筑至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于人性善恶的认识可谓是见仁见智、层出不穷。那么,究竟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呢?(无论是就某个人而言还是就整个人类种群而言)它有固定的形态吗?作为西方哲学思想的巨擘,尤其是在道德问题的思考上无人所能及的康德究竟是如何思考人性问题的呢?康德首先分析了人性中的善根(向善的可能的天赋因素):一是人的生存本能,也就是机械自爱,比如告子所说的食、色等等;二是人相对的自爱,通过与他人的对比,“耻不若人”,而追求自由、平等、发展、完善,并努力超越他人的一种带有人类理智的天赋;三是与责任相关联的人格的天赋,对道德和法律的敬重。前两种天性很容易走向反面:比如第一种天性可导致暴饮暴食、放纵肉欲,第二种天性可导致嫉妒、仇恨、尔虞我诈等;第三种天赋则不易出现这些问题,因而是可靠的向善因素。
在康德看来,人性中同时也包含有三种趋恶的因素:第一,人的懦弱,明知不对,却没有勇气去改变,如“见义不为”、“月攘一鸡”;第二,出发点不是纯然道德的,也就是动机不纯,孟子“义利之辨”涉及到的就是这类现象;第三,有意作恶,在道德观念上自欺欺人。如果说第一种因素算是“有心无力”的话,那么第二种因素就是“有心有力”了,只是不把道德当作出发点或唯一的出发点而已;如果说前两种算是无心作恶,那么接下来的一种类型便是有意作恶,道德败坏。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极可能是心中没有树立起坚定的道德原则或信条。善与恶的因子共同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二者的区别在于其对待道德的态度,一内在一外在。从根本上讲,善恶并不是指行为,而是指动机,或者说意念(康德的这种观点颇似天台宗的“性具善恶观”)。如此,判断一个人的善恶就变得复杂起来了(而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即使一个人的行为是善的(合乎伦理、法规),但如果从根本上说他仍可能是恶的,由于他的动机是争名夺利、自私或同情心泛滥。意念虽然是不可见的,但如果在以上恶的意念作用下,其行为就有可能对道德造成严重破坏。
二、康德“至善”体系之建构
我们知道,康德的“至善”是“德福一致”。人在作为理性存在者的同时也是感性存在者,作为感性存在者的本性而言,所有希望都指向幸福。从主观上讲,人有追求幸福的欲望;从客观上讲,幸福的满足也是履行道德义务的必要条件,幸福的匮乏则可以动摇人对违背义务的诱惑的抵制。德与福不是分开的,而是融为一体的,二者的综合即是“至善”(das hochste Gut,牟宗三译之为“圆善”),即道德与幸福的和谐关系构成了最高善。显而易见,实现“至善”首先是德行,其次是成德后的必然结果。那么,在理论建构方面,纯粹的德性目标是如何实现的呢?在此,康德理论体系的建构借鉴的是基督教模式,他凭借“自由意志”、“灵魂不灭”、“上帝存在”三大“设准”来确保“至善”体系的建立。
(一)“自由意志”与善恶观念
康德认为,形式的实践原则能够为意志提供普遍立法原则。“你应该这样行动,使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一种普遍立法的原则。”[2]道德出于自由,而自由也即自律,并且自由原则与人性之善恶密切联系。人的本性绝不是出自“自由意志”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它是“(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主观根据”[3]。(自律的)道德是以自由为基础的,而人的本性只有出于自由,才可能是道德的。这样,在道德的层面上,人应当为其本性负责。人性作为出于自由的行为,是内在的,并且先于自由在实践中的一切运用。
对于“自由意志”,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区分了意志(Wille)和任性(Willkur)。意志(Wille)作为实践理性,是客观普遍的立法者,能够产生道德法则;而任性(Willkur)则是主观个体的行为选择,只算是一种行为自觉;两者的关系是意志的立法通过任性的抉择来决定道德行为。如果基于意志与任性的立场来评判善恶的话,我们会发现,人身上恶的倾向并非天赋的恶,而是由任性咎由自取带来的结果,任性产生的行为违背了普遍道德法则,因此经常被定义为恶。而意志(Wille)作为实践理性是我们能够遵循道德规范的主观依据,因而,意志(Wille)必须为这种倾向(性向善)负责。如果把道德建立在意志基础上的话,人就可以作为道德上的真正主体,便可以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同时,一切道德、法律的使用也便有了内在而本源的坚实基础。
康德对“自由意志”的“设准”逐步清除了道德准则中的不纯粹动机,批评了那种求神拜佛的恩典论。不难看出,康德的识见,与儒家圣贤所见略同,如明明德、义利之辨、克己复礼等,都是通过艰苦的修身,克服人性中的根本恶,从而拨云见日、复其本心,并逐步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及良好的行为习惯,亦即培养道德责任和建立信仰。
(二)“灵魂不灭”与道德纯善
康德认为,每个人在主观上都渴望追求最高善,即力求使自己的德行修养完全符合最高的道德法则,日常行为与道德无违,从而止于至善。但康德又考虑到,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相对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来说,我们每个普通人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便实现道德的纯粹,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要实现道德的纯粹则迫切需要一个无限的进程,在无止境的“薪火相传”过程中来实现道德至善。然而,只有肯定了“灵魂不灭”,人的生命存在之时间的有限性方可被超越。因此,生命需要无限拉长,“而所谓‘灵魂不灭’正是指同一理性的存在与人格性的无限延续”[4]。由此可见,要保证“至善”的重要条件或者环节得以可能,必须将“灵魂不灭”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设准”(postulate)。
(三)“上帝存在”与德福一致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批判了传统神学哲学对上帝的本体论、宇宙论、目的论的证明,他指出上帝是物自体,是不可知的,而以上三种证明将知性误用于超验事物上,因此必产生幻相。在康德看来,人的行为既涉及行为自身的形式,也涉及质料。质料的实践原则只能归于自爱或幸福。自爱或幸福无法提供法则(Gesetz),而只能提供准则(Maxime)。而幸福作为至善中的质料因素统摄于道德之中,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认为,道德与幸福是异质异层的,两者之间并非统一性的关系,拥有道德良知并非预示着一定就会出现幸福,两者不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既有联系又迫切需要第三方角色的介入来协助实现德与福的链接。但是,这种关系无法从道德法则本身去发现,原因是道德法则虽然主宰自然意志,但并不能决定经验世界的幸福的实现。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必然受自然界的支配,因此不能空凭自己的自然意志就轻易实现经验世界的德福浑然一体,它需要有一个最高的存在来保证德福一致的实现——这便是上帝的存在。由此,康德推演出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为只有这个终极的本体存在,才能保证现世的一切。这颇类似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5],首先为上帝的存在预设了位置。借助于无限而神圣的最终意志,得以保证最高善的实现。这样,在康德实践理性的证成过程中,既然实现至善是人类的义务,而至善只有在上帝存在的条件下方可实现,所以,和肯定“灵魂不灭”一样,肯定“上帝存在”也是必然的。
在康德“至善”思想中,为保证德福一致必然需要预设“自由意志”、“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康德称之为实践理性的三大“设准”,这应被理解为实践意义上的主观肯定,而非认知意义上的客观证实,因此,肯定三大条件实则为信仰的需要,学界称之为“道德的神学”(moral theology)。
三、牟宗三创造性重铸圆善论
(一)牟宗三对“至善”之继承与批判
牟宗三在《圆善论》中充分论述了康德的最高善思想,且评价极高,“至善”是康德道德哲学体系完善的展示,牟先生还认可了“至善”问题的关键便是实现“德福一致”,同时他也认为,这是西方哲学史上道德伦理问题发展的高峰。牟宗三在德福关系方面与康德的思想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他吸纳了康德“至善”体系的论断,认为善作为道德的目标与行为准则,对我们的行为具有无条件的约束力,人们的行为受纯善的命令支配,如果只有践行道德但得不到幸福,便称不上圆满的善。“圆善”应该是道德与幸福的完美结合,“至善”是“综合德与福两者使它们之间有一种准确的配称关系,以成德福一致”[6]。牟宗三还确认了康德关于德福之间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关系以及两者的有机一致性只有在综合关系中才会得到完美体现的观点。
但是,牟宗三对康德的评价也持有保留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说,康德只是提出了问题,但在实际践行中难以真正地解决问题,因此,牟先生主张用“圆善”来融摄与超越“至善”。因为,康德在论证“至善”时,是以三种假设来保证“至善”的实现。康德诉诸“自由意志”、“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来实现道德的纯善,而牟先生则提出用“无限智心”来消解康德的三大“设准”。
首先,牟先生通过“无限智心”来消解“自由意志”与“灵魂不灭”。“自由无限心(无限智心)不立,在牟子看来,圆善终归是虚幻不实的,因此也就不能真正达到圆善”[7]。康德虽承认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但他预设了人是没有“智的直觉”的,难以超越现象界的一切存在,同时,由于“自由意志”属于道德法则,人性由于原罪而不具备纯善的潜质,因此,“至善”在现实中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但是,这种预设显示了人类不会自然而然地遵循道德准则,所以,自由意志难以保证纯善的实现。而“无限智心”的提出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缺憾。“无限智心”作为道德本心在中国文化中是修身成圣的根据,在此情况下,“自由意志”对实现至善的意义就不太显著了。“无限智心”在牟先生思想中成为道德主体挺立的依据,而在康德思想中却没有出现这种能够壁立千仞的主体性。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在康德思想中才会出现“灵魂不灭”的“设准”。牟宗三在其哲学体系中提出“无限智心”作为主体而确立,人作为理性存在,具有智的直觉,在此生此世便可以通过仁心的修德止于至善,有鉴于此,牟先生便消解了“灵魂不灭”存在的必要性。
其次,尽管牟宗三先生完全认可康德以超验的无限存在作为实现“至善”的重要条件,但他并不同意康德所提出的将“上帝存在”作为实现“德福一致”的保证。康德实现“至善”的模式依然没有摆脱西方宗教的羁绊。康德认为,上帝拥有智的直觉,并且只有上帝才能保证这一至善过程的显现,由于人类生来就带有原罪意识,因此难以超越现象界而得到纯粹的道德。所以“德福一致”的实现有赖于第三方的出现,而这只能从现实世界之外来寻找最高的无限存在——由此,人格神“上帝”便出现了。牟先生所提出的用“无限智心”来保证“圆善”的实现,这在儒家表现为“仁心”,“仁心”是君子修身的主体,此心不仅君子具有,而且一切人皆有之,甚至一切理性的存在皆有之,只是君子保存了,而小人不懂持存罢了。“无限智心”作为一绝对、普遍的理性之心,由实践理性而证立,当机指点,当下即可呈现,故能建立道德的必然性且能更新事物、创生万物。由此可以发现,康德以上帝来保障德福的配称与公道是虚妄的。而牟宗三以其“无限智心”来取代康德的上帝,这样就把保障“德福一致”的主宰权由上帝还至人本身,即“为仁由己”。由此,牟先生在其圆善体系中就以“无限智心”自然而然地消解了“上帝存在”。
(二)会通中西——重塑圆善论
牟宗三先生在《圆善论》中融摄了康德的“至善”思想,同时也整合了传统儒、释、道的道德哲学体系,并通过分判各派思想体系,使其最后归宗于儒。他以“无限智心”来寻求德福一致,最终作出了元伦理学的奠基性贡献,实现了儒家圆善论之重铸,从而为儒家伦理的现代转换发挥了重要作用。
牟先生之“圆善”思想来自康德的启示,而牟先生的圆教观念则来自天台判教。从前文对康德的论述可以看出,道德呼唤宗教,而关键是呼唤什么样的宗教。牟先生给出的答案是:圆善对圆教(道德形上学)。牟宗三认为,“圆善”是“哲学系统的究极完成”[8],他提出用“无限智心”来代替康德的上帝,以此进一步确立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的关系。“圆善”与“无限智心”皆充满理性精神。牟先生用“无限智心”涵摄整个中国文化体系。儒、释、道思想体系中都有对“无限智心”的重视,当然,儒家与道家的讲法不同,儒家是纵的方式,而道家与释家则是横的方式。尽管儒、释、道三家的道德路径迥异,各有特色,但几种体系皆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无限智心”在儒家便是良知之教,道德功夫成为“致良知”之学,仁者与天地为一体,在践行功夫中实现德性本体;依道家言,则是道心或玄智;依佛家言,则是般若智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9]。
儒家的“无限智心”是“道德本心”、“仁心”,“此道德性的无限智心,也即良知良能之本心”[10],它在孔子提出“仁”时便露出端倪,亚圣孟子在其思想体系中给予了发扬光大,而在宋明儒学中,陆王心学直承孟子,将其作为道德本体予以承接。大程的“识仁”、陆子静的“本心”、王守仁的“致良知”,上下贯通。儒家实现“圆善”主要是通过践行,“无限智心”(仁心)作为儒家的道德本体主要通过工夫得以显示,“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11],工夫涵养显得尤为重要,本体与工夫融为一体。从工夫上讲,牟宗三提出了“三系说”。有顺取和逆觉之不同,顺取的进路以程朱为代表;逆觉分两种路径,一路是陆象山、王阳明,另一路径是濂溪、横渠、明道、五峰、蕺山。而儒家的圆教,经过王阳明,到王龙溪始成。王龙溪针对王阳明“四句教”——心、意、知、物四者作出了全新阐述:“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12]此皆指以“无限智心”为体,以工夫为用;以感通为性,以润为用。正所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
“无限智心”一方面可以促进道德的完善,另一方面可以使天地万物获得存在的价值意义,从而保证道德的纯洁性,以道德“至善”促成“德福一致”伦理体系的实现,保证了“圆善”体系的有机性与完整性。“如此一来,既保证了道德的纯净性,又保证了万物的存在及其谐和于道德,德福一致便有了可能”[13]。通过德福关系来证成圆善与圆教,完全是一个理性的过程,这也是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先生所达至的至高境界。诚然,就哲学之为教的意义而言,“圆善”之证成便使之达到了高峰,道德形上学系统至此已基本完成,“圆善”之实现使道德生命提升至圆满俱足之境。
四、结语
牟宗三先生创造性地重塑“圆善”论,是他海纳百川、会通中西,集孟子、天台宗、王龙溪、康德等思想精华为一体,整合并重铸古今中外思想精华的重大成就。其中,康德对人性善恶的分判、对德福一致以及道德寻求宗教等一系列的论证,特别是他对“至善”和“德福一致”的洞见,为牟先生“圆善”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灵感和理路支持,促进了牟先生重构儒家德慧圆教的圆善论。牟先生也因此而将儒家哲学推向“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新境界,为儒家伦理的现代转换作出了重要贡献。
[1]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118页。
[2][3][德国]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5、21页。
[4][德国]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牟宗三译,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368-370页。
[5]苗力田、李毓章:《西方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4页。
[6][8][9][13]牟宗三:《圆善论》,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185、序言ii、255、186页。
[7]张俊:《牟宗三对康德圆善的超越与局限》,《孔子研究》,2008年第4期。
[10]徐岿然:《牟宗三“圆善论”之大境域实践信息阐释》,《长白学刊》,2013年第6期。
[11]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8页。
[12]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卷1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类98》,齐鲁书社。
From the Supreme Good to the Perfect Good——Mou Zongsan Assimilates and Beyond Kant on the Highest Good
ZHANG Shao-en1,2DU Lei2
(1.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2.College of Arts,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Handan 056038,China)
Kant;Mou Zongsan;the consistency of virtue and happiness;innate good and evil;supreme good;perfect good;infinite mind
In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Pure Reason,Kant proposes the highest good-supreme goods which is the consistency of virtue and happiness,then explores the human nature,the relation between virtue and happiness.Kant's"supreme good"thoughts provides an inspir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supreme good.Mou Zongsan assimilates the supreme good theory.There is great similarities and inner consistency between them.But MouZongsan disagrees Kant in the realization of process of supreme goods.There are three Hypothesis in Kant's system:Free will,immortality of the soul,the existence of God,which is typical Christian style.Mou Zongsan criticizes Kant with perfect good and infinite mind,exhibiting different route to reach supreme goods,and Mr.Mou proposes infinite mind(benevolence)to resolve and eliminate Kant's three postulates.Through intercommunciating the orient and the occident,he combines Confucianism,Buddhism and Taoism and eventually returns to Confucianism,reconstructing the perfect good system of consistency between virtue and wisdom,so as to construct modern moral idealism philosophy.
B261
A
2095-5170(2014)04-0103-05
[责任编辑:李文亚]
2014-04-11
本文系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中西文化比较视域的20世纪美国儒学研究”(项目编号:HB13WX017)、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国际儒学发展报告”(项目编号:10000083396010)的阶段性成果。
张少恩,男,河北邯郸人,河北工程大学荀子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杜磊,男,河北邯郸人,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