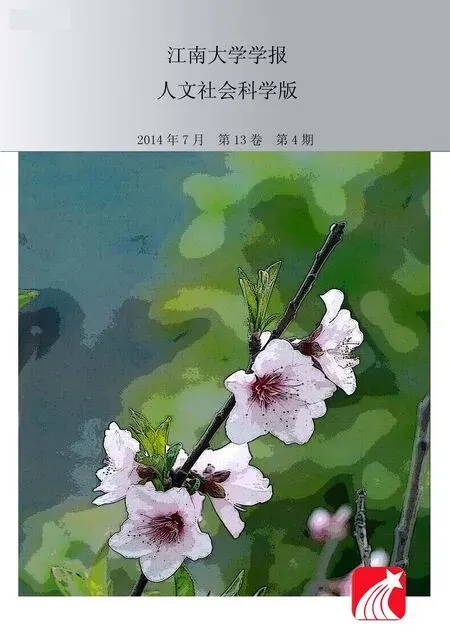古代中国哲学中的“自我”
吴晓番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0098)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自我(Self)的出现都是一个现代性的事实。中国的现代自我从哪里来?现代中国人的自我观,无疑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先验的,它也经历过诞生、形成和固定的过程。现代自我的理解离不开古代自我的比照,古代中国哲学中的自我理解是理解中国现代自我的关键。
一、两种不同质的“自我”
中国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中国哲学很早就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从殷商的宗教崇拜解放出来的西周“以德配天”观念,使人得以“与天地为三”,进而得以“参天地之化育”,先秦儒家的仁道思想是一种尊重人的地位的思想;而与其相对的墨子从功利的角度论证的兼爱原则也是注重人的思想学说。孔、墨都讲人类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和德性,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培养自己成为理想人格。不过中国古典思想对于人的地位的注重,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孔墨讲的人道原则都不是近代的人道主义。近代的人道主义是以个性自由为内容的,古代的人道原则没有这个观念。”[1]
这里需要澄清古代的人道主义和现代人道主义的不同特征。蒂里希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西方思想中的古代和现代的人道主义进行了比较[2]163。首先,在古代世界的形而上学的二元论(理念/现象)和宗教的二元论(彼岸/此岸)中,由于现象世界/俗世是污秽不堪的,而理念世界和彼岸世界是澄净光明的,对人的地位的肯认是肯认其在污浊的现世保持良好的自洁能力,即肯认其对于充满物欲的现实世界的绝缘感。对人的肯认的最好方式是精神生活的充实①这一点在马克斯·舍勒的《怨恨在道德建构中的作用》(《舍勒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和查尔斯·泰勒的《自我的根源》(Source of The Self,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中也有提示。。而现代社会本质上是感性对逻各斯的造反,它认为感性生活乃是合理的,对人的感性欲望的满足是人道的表现,不能像古代世界那样认为应当“灭人欲”,不应以精神取代物质,存理灭欲。其二,现代进步史观代替了古代的循环论,人们取得了一种现代意识,把眼光放在将来和创造性上,而不是放在三代和理想世界。在古希腊,历史循环论是主流的历史观,它认为不变的理念世界才是最完美的世界,而人的存在的现实世界则是一种流变不居的、易朽坏的。而在现代,由于时间被拉直,美好的世界在将来,所以人道的理想生活不在于那永远不变的黄金时代(理念世界),而是以当下为基础的将来的天国。其三,古代世界认为个人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某种普遍事物(如美德、神、天)的代表才有价值;近代世界把个人作为个体来看待,把个体看作是宇宙的独特表现,看作是无可比拟的、不可代替的存在物,是无限的意义的源泉。蒂里希论述的对象是西方人道主义,但是其结论具有一般意义。在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思想演变趋向②详细分析参见拙著:《龚自珍哲学新论》(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第9-11页。。
在这两种不同的人道主义类型下,对于自我的规定有两种不同的视角。这两种视角可以区分为古典思想视域和现代思想视域。在这两种视域下,自我有着不同的角色。按照蒂里希的分殊,人作为一种存在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部分而存在,即通过参与世界的行为来肯定人的自身存在;“自我之为自我,只是因为它拥有一个世界、一个被构造过的世界,它既属于世界,又与之相分离”[2]213。另一种方式则是作为自我而存在,即作为肯定可被摧毁但不可分割、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的自我而存在。“对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即对独立的、自我中心的、个性化的、不可比较的、自由的、自我决定的这样一个自我的肯定。”[2]212前者是古典型的自我,后者是近代以来才兴起的自我类型。前者是整体主义之下的自我,整体主义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但却把自我作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作为单个的自我看待,这个整体可以是国家社会,也可以是天命、道、神圣秩序、自然等等。而后者则是整体主义的对立物,它是独特的自我所具有的自我肯定,不考虑对外部世界的参与③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种形态,参见:腾尼斯的《新时代的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路易·杜蒙:《个人主义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自我是整体主义之下的自我,即便是现在这种整体主义的自我观仍留有痕迹。它也重视自我肯定,但是这肯定只不过是把自我作为一个更大的集体(国、家、或者神圣秩序、天命、历史洪流)的一部分而看待。它对于作为这更大的整体的部分的自我持肯定态度,主张“为己”、“由己”,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个部分,或者当这一部分与整体不相协调,那么他们就主张“无我”、“毋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思想中无我和有我的对峙。
二、有而无之的“自我”
中国思想一直都有无我或者大我(无我的变形)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如此流行以至于遮蔽了人们对自我的认识。从孔子开始一直到现代社会,我们对于自我的认识基本上都是在这种基调中。虽然有孤愤之辈意识到这种看似合理的和谐背后的乖离,不过由于他们是异端,自我的本质至今仍晦暗不明。
孔子曾提出“四毋”的主张。“子绝四:毋意毋必毋故毋我。”(《论语·子罕》)与大多数古代哲学语词一样,这里所说的“我”,既有认识论的意义,也有价值观的蕴涵。从认识论上来说,毋我含有消除主观成见之意,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有缺乏理性的反省精神的弊端,特别是对给定的意义和权威缺乏必要的警醒;从价值观而言,毋我意味着超越“小我”(作为个体的我),此处之我乃是“私”,毋我意味着不要太讲求个人的私利,“小我”应该为“大我”服务。这两重意义上的毋我,在后继的儒学发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异端讲“为我”、“贵己”,把个人的生命和社会利益对立起来,主张“全性葆真,不以物累行”,这显然与儒家的学说不同调,是隐逸之士的观点。子路批评这种隐者“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孟子批评得更为激烈,“杨朱为我,是无君也”,直斥其为禽兽。儒家在人伦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确认自我的认同,先有群、社、族,然后才有自我。按照安乐哲和郝大维的说法,这个自我乃是“作为区域和焦点的自我”,对于儒家而言,“由特殊的家庭关系,或社会政治秩序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特定的环境构成了区域,区域聚焦于个人,个人反过来又是由他的影响所及的区域塑造的。……作为焦点的个人与他将要造成的、反过来又被其塑造的环境融为一体。”[3]这个自我实际上是一种“无我之我”。
沿循这一思路,朱熹反对“为我”,力倡“大无我之公”[4]410,王阳明也一再地肯定毋我:“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而庸以成之。”[5]在王阳明看来,对一己之见与一己之利的双重超越,是成就理想人格(圣人)的基础。儒家非常重视现世,对于超越的彼岸并无兴趣,对于个体的生命和世界的实在性毫不怀疑。儒家思想讲求“无我”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的,“我”在此主要被理解为意见的主体和利益的主体,无我首先表现为一种认识论与价值论上的要求,它与存在论的认定有所不同。
道家对于“我”,也持有而无之的立场。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出“无己”之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夫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道家的无我说,唯有联系其自然原则,才能够得到比较具体的理解。和儒家一样,它也不是在本体论上对于我的否定。相对于儒家对礼乐文明的注重,道家更多地表现出崇尚自然的趋向,他们以自然为理想的存在状态,将礼乐视为对自然的戕害,主张由礼乐文明回归于自然的状态。庄子于此主张“至人无己”,这一“己”乃是经过文明洗礼的、在礼乐文化中成形的“我”,其特点是有所“待”,即他的存在需要依赖于一定的条件,这对于庄子的逍遥之境而言,无疑不是理想的生存状态。只有超越了这种为礼乐文化所束缚的己,达到合乎自然的境界,方能获得绝对的自由(逍遥),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在此“无我”的含义在于摆脱外在的束缚,达到逍遥之境,这表现出了一种修养境界论上的意蕴。在认识方面,道家一方面主张“吾丧我”,主张去除“我”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主张心斋坐忘、内省、去除“我”之影响,方能达道。但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真人与真知之间的辩证统一,生存与智慧的相互关照,重视认知的生存论基础,在这个方面,道家似乎注意到了自我在认识论中的本体论意义:“我”不可无。
作为外来的思想,大乘佛教也以“无我”立论。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三法印说:诸法无我,诸行无常,寂静涅槃。“我”作为法之一,也是无自性的。佛教所说的“我”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认识论上的,其二是本体论上的。在佛教看来,宇宙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本无自性。我亦是由五蕴和合而成,也没有自性。而万法皆空,由于我的执着而有,就其本体而言,亦空。故而佛教讲的“无我”,也相对有两种意义。其一,就是在认知上不要执着于我意,因为认知的世界本来是无,由于我执意为有,所以从本源上来说,认识本身没有真实性可言,只是人的一种构想,故而不应该执着于我。其二,由于我乃五蕴和合而生,没有自性,我只不过是妄执虚为实有。这是从本体论上对自我的存在进行消解。佛教的无我说在中国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影响。直到当代,牟宗三仍然以佛教的因缘说来否定自我的同一性问题,在本体论上否定自我之实在。
以上就是古代哲学中关于“无我”的学说大概,从毋我、无己到无我,对自我的消解和否定构成了其中共同的趋向①上述梳理参考了杨国荣教授的《伦理与存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六章。特此致谢。。不过对于这几种“无我”之说,须注意其侧重之点各不相同。大致而言,“无我”主要是认识论和价值观上的要求,它试图解构作为意见的主体、利益主体和人化主体(礼乐主体),其立场更多的表现为“有而无之”,它的特点不是要否定我的存在,而是要消解既存之我。也就是说,在这个层面上的我,就其本体论而言,无疑是实存的,无我并不否定这种实存,无我也不是在“我存在”这一实存论基础上的对我的解构。而佛家的无我与此不同,它从根本上认为我乃是不存在的,乃是因缘和合而生,是虚无。这个无我是在本体论层面来说的,它认为一切皆空,一切皆妄,从根本上否定世界的实存,否定自我的存在。这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不占主导地位。
三、作为部分而存在的自我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虽然没有作为哲学概念的自我,但是有着类似的一些概念:己、吾和我的说法。人类作为一种生物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存在,必然有着存在着“自我”的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没有被提炼为一种哲学概念。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哲学概念与观念不同,哲学概念是观念的固定化。“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现的。”[6]13-14由于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制度的缘故,自我之存在,完全取决于群体之在,“群在故我在”。由于群与我的区分不充分,所以我作为哲学概念不能充分发育;在古代哲学中“意志自由”虽不能说没有、却因其一开始就与选择无关,不是本体论的范畴,因而也是隐而不彰的。
从对于“无我”的梳理可以看出,传统思想中的“我”基本上是一种前哲学概念,并没有成为古代哲学的核心词。中国传统思维对自我的肯认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众所周知,弘扬人的地位与价值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是儒家文化的根本宗旨,对于人的认识和反思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所在。孔子通过对商周文明的改造将价值的重心由外在的神、天转向现实的人,确立了仁者爱人的基本理念。沿着孔子的方向,孟子对人何以为人、人如何为人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从而奠定了儒学发展的方向。荀子对人的内涵作了更为全面的考察,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中庸》讲:“唯天下之至诚,未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即是说,一旦人能充分地护持住自己的道德理性,他就能全面地发挥自己的本性,并且尊重每一个人及每一个物的生存,使之“各遂其性”;这样就能够回返天地之生命精神,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与天地鼎足而三,理性地适应并进而辅相天地。这里对人的地位的尊崇不可谓不高。到了汉代,董仲舒认为人与其他九种元素一起构成宇宙大全,这十种元素乃是万物的质料因,故而其地位在万物之上。
魏晋以来,特别是隋唐时期,佛道二教尤其兴盛,此二教的风行渐渐使人自身的价值变得模糊了,儒家的人文精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新儒家为纠正时风,重新肯认了人的自身价值。与玄学及其他二教的哲学相比,理学更加重视人的价值,重新借助先秦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的理论资源,肯定了“天地之性,人为贵”这一儒家传统。张载《西铭》是整个新儒家的思想纲目。按照张载的理解,在我与人、人与物所构成的宇宙中,每一个成员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个人都是天地气化而成。这个宇宙的大家庭犹如自我的小家庭一样,视天人之人为同胞亲子兄弟而加以教养保全,这无疑体现了对于人的生命原则的重视和对人在宇宙中地位的肯认。对主体力量的高度自信更为显豁的表达是张载的如下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7],立心、立道、续绝学和开太平之主语是我,这无疑是“人能弘道”思想的进一步加强。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一系更是高扬人的自作主宰之精神。陆九渊说:“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缺?”王阳明也判定只要是经过自我良知所权衡而得为“义”的,就可以勇往直前,无所畏惧。这无疑是对我本身的价值的一种肯定。此说直接接上了先秦儒家的 “为仁由己”之说。
这些儒家文献都表明,儒家非常重视“我”,重视“我”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①但这并不表明儒家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一种宇宙中心主义。参见范瑞平:《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358-372页。。但是这种对我的重视是有条件的,有限的,这里的“我”是作为整体的部分而存在的自我。在这里,整体可以是家族、国家、天命或者文化历史。在儒家看来,天命之谓性,人之为人,乃是由于人身上承担着天命。自我的本真性来源于自我与天命之间的终极关系。在天人关系中,天是受命者、给予者,人是聆听者、接受者。人生天地之间,这一关系便无逃于天地之间,人应当成为自己意味着人应该顺从天命。正是对于天命的认同构成了人的自我。儒家的自我是一种天命的自我,天命在现实世界便展开为人伦纲纪,因此,儒家的自我也是社会伦理中的自我。“自我的社会内涵包括与一定社会共同体所占位置及所承担的角色相应的义务和权利、社会规范系统通过认同及接受而在自我中所形成的行为定势和选择、评价的内在准则、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所赋予自我的关系性规定(自我作为关系中的存在而具有的品格)等等。”[8]自我只有在伦理中才成其为自我。自我是一系列“天合”和“人合”关系中的我,自我天生就是由与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伦理关系所规定的。
需要注意的是,先秦儒家虽然把自我视为天命承担者,但是并不意味着自我是一个凝固的现成性的自我。由于天命生生不已,所以自我也是性日生日成。在容许的限度内,儒家并不把天命自我看作是现成的自我,而是认为自我处于不断地生成中,换言之,人自身所承担的天命是不断展开、不断显现的。所以对应于天命的无限开放,儒家的自我也是无限地展开的。自我是一项永未完成的事业,正如天命是一项永未完成的事业一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正是儒家思想最为宝贵之处。因为它看到了人的本质在于其未完成性和可能性,而不是现成性和实体性的,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对世界开放[weltōffen]”
但也不可对儒家的这种“天命之我”估价过高。首先是因为,“我”前面有一个“之”,也就是说我并不是真正的主语,而是有着一个“天命”所笼罩。越到后来,天命就越是成为儒家纲常形上化的天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回复到天命之所与之本性。在性善论的预设下,这种存在似乎犹如苏格拉底所提问下“回忆”起其先天具有的知识一样。从根本上来说,人是预定之所是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其实是一种本质主义而不是存在主义。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学者往往把儒家的心性一系跟存在主义哲学相比较,实际上这种比较有其内在的困难。就自我而言,“中国心学的自我终究不可能是存在主义者的自我,它的道德努力的人生终究不是存在主义者的自由选择的、真实、坚决的人生,它的自由也不是存在主义者的自由。”[9]288在儒家看来,天命在社会意义上就是人伦纲纪。在纲常中,作为个体的自我并不存在。上述的天命之我虽然包含着按主体自身的理想来塑造自己的要求,但若将其视为独立的个人,那无疑犯了范畴错置的错误①关于中国古代观念史中的范畴错置的哲学讨论,参见高瑞泉教授在《平等观念史论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导言中的精彩分析,第25页。。尼采认为并非像现代人所想象的那样,个体在前现代时期遭到扼杀和窒息,在前现代,个体(现代意义上)根本就不存在。布克哈特在也断定:文艺复兴以前的“人”只是作为种族、民族、党派、帮会、家庭,或以任何其他总体和集体的形式才自我感知的。[10]
儒家虽然重视人在宇宙中的殊出地位,重视人的尊严,但是究其根本而言,儒家所说的自我并不是一种作为独立存在的自我,它是作为部分而存在的自我,不是个体(individual)。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杜蒙的看法,个体,其意义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语言、思想和意志的经验主体,人这种属类无法加以分割化的样本,这种情形可见之于所有的社会中。二是独立的、自主的,因此(在基本上)是非社会性的道德存有体。这主要见之于近代对人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上 。[11]儒家的自我如果离开了社会,那就走向了道家,相对于儒家价值体系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后一层意义上认为儒家的自我不是一种个体。
儒家的自我始终是在天命依托下的自我,虽然在道德践履和道德信念中儒家高倡自主,但是在道德领域之外,自我处在一种无主的状态。这尤其表现在力命之争中的宿命论倾向。在儒家的视域中,天命就是天理,它决定了人性、道德、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所有内容,一切“无不本于天而备于我”。由于天命是绝对的,所以人力并不是万能的。它总是有着自己的限度。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董仲舒还是韩愈,程朱还是陆王,虽然对人力的注重程度不一样,但都没有脱离天命的范围。按照程朱的看法,人在道德领域虽然有着自主选择的能力,“为仁由己”,但是道德生活并不是人生活的全部,道德生活之外的领域则在人力掌控之外。尽自己的职能、尽防虑之道而不免于困,尽人力而做不成,那么就只好归之于命了[12]2685。这里虽然有对人力的肯定,更多的却是在命运(气数)面前的无可奈何。
在传统哲学中,命还表示个体在现实中所承受的角色。在儒家看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朱子认为个人先天所赋予的资质不同,有高有低,有长有短,但是经过后天的习得教化,必然可以取长补短,各成其就。但是朱熹却由气禀对生命存在的先天决定性,引申出个体命运的被决定性,因而带上了宿命论的色彩。朱熹说:“死生自由定命,若合死于水火,须在水火里死,合死于刀兵,须在刀兵里死,看如何,逃不得。”[12]77在这种气数之下,人的主观努力完全无可奈何。
在社会历史领域,儒家更是主张人应该随着“天命之流行”,不应该逆天逆时。这基本上是把人消融在历史大道、宇宙洪流之中。因此儒家的历史观是一种历史宿命论。从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经董仲舒“王者承天命以从事”,到宋儒演变为天理史观——历史不过是理或太极的流行,它表现为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观和历史循环论,在朱熹那里则是历史退化论。这种思维方式至今不衰。因为中国人很是能够推天命以言人事,把天命之流行与人之嬗变直接等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近代思想家热衷于探讨历史规律的原因。个人在社会历史大道面前,有两种可能的反应:一是顺应,二是逆反。而在传统中二者都是一种宿命论下的反应。它们都没有否定天命之存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是其主要的结论。在传统的语境中,这种不可避免性是不可怀疑的,天命、宇宙神圣秩序是人的解释极限。
由此可见,在儒家思想中,我乃是天命之我,我乃是天命所与,本身绝没有主体地位,它只有作为天命或者天命的现实形式——君命纲常的一部分而存在,天命决定着自我的存在与否以及如何存在。虽然在善恶选择上儒家有着自主选择之权力,但是如果追问其善恶之本源,它终究还是会诉诸于天命,所以即便在儒家十分注重的道德形上学领域,这个自我仍然是有限的。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作用,由于人没有从天的笼罩下彻底地解放出来,天毕竟是人的存在根源,故而无论如何,人总归要顺从天命。在理论形态上,天命之谓性;而在现实形态中,等级制度所显示出的纲常伦纪更是规范着自我的各个方面,自我不能离开国与家,离开自己被规定好的角色。
四、古代自我观的转型
综而言之,中国古代思想主流的自我观是一种整体主义的自我观。“我”在古代哲学中并没有成为哲学概念,至少她不是古代哲学的核心概念,这一点在自然、历史、政治和伦理中都有表现。它在天人之辩上主张天对人的决定地位,人是天命的附庸。古代中国人都主张与天地和谐相处,主张天人合一,但这个和谐是以服从天命为前提的。天人之辩内在地蕴含着力命之争。古代思想都认为,人在有限的空间是自由的,在道德领域人是有主观权能的,但是其他领域人都被天命所笼罩。因此他们并不主张积极地改造自然,而是主张顺应天命,这表现为道德宿命论和历史决定论,人在天命面前毫无自由。在理欲之辩中,由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缘故,古代思想家普遍对社会培育的欲望持否定态度,他们都注重人的精神修养,主张通过精神修炼与天地同体,认为精神境界远远高于物质利益生活世界。在群己之辨上,自我本身就是以社会的角色为标志的,故而己完全地隶属于群,完全没有个体观念。
作为部分而存在的“自我”,随着社会的发展得到了松动。在晚明,我们发现“自我”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词[13]。晚明以降的思想变动,其大端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在天人之辩上,随着“天谴”的天观转向“天理”的天观,人对于天的附属地位有所松动。人逐渐获得一种独立的意识,在阳明后学那里,逐渐出现了人可以造命之说,它表明力命之争中力的因素有可能冲破天命束缚,走向自由的人格。在理欲之辩上,随着商品社会的发展和土地制度的变革,对物质欲望的肯定成为明清之际的热点话题。从阳明以降,大部分思想家都提出了肯定私的意见,这种对“私”的肯认意味着在价值领域的新的可能性。在群己之辨上,经济制度的变动使得个人有可能脱离家庭,生产的专门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契约化,从而使人得以从以往的家族关系脱离出来,开始构建新的共同体。较之传统的价值体系而言,明清鼎革之际对于传统儒学的批判和反思为新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建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种背景之下,一种新的自我观就呼之欲出了。
[参 考 文 献]
[1] 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09.
[2] 蒂里希.存在的勇气[M]//蒂里希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163.
[3] 安乐哲,郝大维.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44.
[4] 朱熹.西铭论[M]//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5]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32.
[6]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7] 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320.
[8] 杨国荣.伦理与存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10.
[9] 倪德卫.儒家之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0]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97.
[11] 路易·杜蒙.个人主义论集[M].台北:联络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93.
[12]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 傅小凡.晚明自我观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