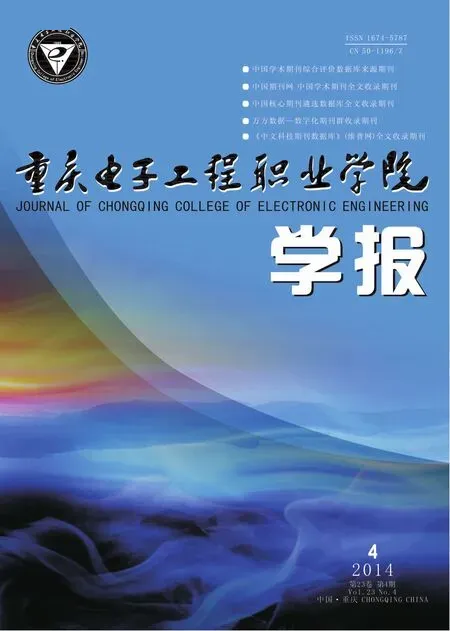试论《原野》的接受
承梦姣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225000)
1967年,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教授姚斯提出了“接受美学”理论,它的核心旨在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这一理论的提出将研究者们的目光引向了读者。而戏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它不仅有文本,而且还有舞台演出,在每一次受众的反馈中进行一次次的修改和润色,从而体现出戏剧特有的生命力。曹禺的第三部剧作《原野》不像《雷雨》《日出》一样广受好评,相反却遭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和批评,它的接受经历了异常曲折的过程。
1 评论界的接受:从否定到赞赏
《原野》从1937年4月在《文丛》第一卷第2期开始连载,并同时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同年8月,该剧由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在卡尔登大戏院进行首次公演,但评论界并没有对此剧做出任何的回应。直到1938年6月,南卓发表的一篇名为《评曹禺的〈原野〉》打破了这种沉默状态,但是迎接《原野》的并不是所谓的支持,而是声讨和质疑。南卓的质疑主要有三点:第一,他认为作者太爱好技巧了,使得他的作品太像一篇戏剧,缺乏现实的真实性;第二,质疑此剧模仿和抄袭奥尼尔的《琼斯皇帝》,否定了它的价值;第三,他认为剧中的人物因为过分分析,完全是理智的活动,以致人物都有点机械,没有活跃的个性。此后,评论界的质疑接踵而来。20世纪40年代杨晦的《曹禺论》和吕荧的《曹禺的道路》也分别论及了《原野》。前者认为,尽管《原野》写的是农民向土豪地主复仇的悲剧,但它却走进《原野》的黑林子里迷失了方向,由社会问题转为心理问题、良心问题及道德问题等的精神枷锁。吕荧则认为这部剧“仍然没有脱离观念的思维的领域,是一个纯观念的剧”[1]。而观念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文学来讲是毫无意义、玄而又玄的非现实的东西,从而遭到了诟病。此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原野》在评论界消失了近40年。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原野》出现的年代过于特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和阶级斗争此起彼伏,文艺被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必须反映当下最现实的革命问题。其次,在那个时代,对文艺作品的好坏评价只参考一条唯一的标准,即现实主义,而《原野》成为了远离现实,简直不像人间的故事。所以评论界对原野的象征,特别是第三幕的表现主义手法给予了激烈的批评。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和审美的变化,到了八十年代初,对于该剧的评价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从被曲解到慢慢得到肯定。1981年,华忱之在《论曹禺解放前的创作道路》中提到:“该剧反映出人间地狱的阴森丑恶和是非颠倒,真实地再现了现存社会中地主阶级及其政权残酷地迫害劳动人民的惨象,形象地展示了农民在当时的悲惨处境中向往美好生活但又找不到正确出路的状况。”[2]虽然这篇文章仍然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评论该剧,但在态度上却有了理解和宽容。除了继续从阶级斗争方面来肯定《原野》的价值外,也有不少学者试图从其他方面入手解读《原野》。1983年,潘克明发表了一篇名为《〈原野〉和表现主义》的文章,该文章就专从创作手法和艺术特色的角度来为《原野》翻案。潘克明认为,在这部戏剧中现实主义是基石,并且肯定了曹禺是一个勇于探索的剧作家,所以他有意借鉴表现主义手法来探索一条新的路子以拓宽现实主义表现的道路。此后,学术氛围更加自由,展现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以往学界一直争论的关于阶级斗争、社会学意义在此后的评论中被慢慢掩盖和消解,学术批评拥有了更大、更自由的空间。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关于《原野》的评论文章越来越多,切入的角度也千变万化。对《原野》多元化的解读最终使这部戏剧走向了经典化的道路。
2 导演的接受:从单一化到百花齐放
戏剧的生命在于演出,而《原野》在舞台上的呈现,其内容和形式最终是由导演决定的。导演接受的特殊性在于他不仅要对原剧本作自己的解读,而且要对剧本进行再创作,生成一个适于舞台表演的新作品。《原野》每一次的演出体现着不同导演对《原野》的不同接受。
建国前,《原野》的演出主要有三场。首次公演由于遭遇了淞沪抗战,这部戏剧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1939年,曹禺亲自导演《原野》。在这次排演中,曹禺将导演的重心放在“如何把人物的复杂心态表演出来,着眼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而舞台设计闻一多在舞台的布景设计上,采取“虚实结合”,“并运用了某些抽象的画法,在灯光下形成焦点透视,把大森林的阴森而恐怖的神秘气氛表现出来”[3]。1948年,清华剧艺社演出的版本对剧本有了较大的改动。导演的中心思想在于“强调仇虎、金子和焦家的对立,借以加强社会意义,反映出学生们的革命情绪和激进思想。”[4]由此可以看出,建国以前该剧舞台的演出,导演的重心大多放在农民复仇、阶级反抗层面,更多在于体现时代的特征和社会学意义。因此,该剧的舞台演出都是大同小异,直接导致观众对该剧的认识也都停留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解读。
建国以后一直到八十年代,社会学角度的解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1981年,该剧被导演凌子改编成了电影。在影片中仇虎成了配角,主角由花金子担任,该变化直接导致了电影所要表现的是封建社会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权利以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1984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原野》,张奇虹任导演,这次演出对曹禺的剧本有了比较大的改动。最大的改动在于焦母误杀小黑子变为误杀大星,仇虎的自杀改为他杀。张奇虹认为,大星被焦母误杀“为的是不致仇虎杀害焦大星,让他赢得观众的更多同情”[4]。仇虎自杀改为他杀为的是遵循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以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张导演这样的改动无疑仍旧以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为指导思想。尽管1984年已经离建国和文革很久,但是演出还没有脱离社会学的窠臼,仍然以政治斗争、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
这一接受现象得到改变来自于1987年曹禺的女儿万方把话剧《原野》改成了歌剧。在这次演出中,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没有多大的改动,只是增加了歌剧的形式,在唱的过程中剧作家所要表达的“诗”的情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万方的这次改编也跳出了以往惯有的社会学的解读。1990年,湖北潜江市荆州花鼓戏剧团将其改编为花鼓戏《原野情仇》,导演丁素华、余笑予。这次演出有意“淡化社会性冲突,着重在人性、人格的真、善、美上张扬”[6]。这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次演出主旨相比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创作方法上仍旧遵循的是现实主义模式。
对现实主义模式大胆突破和创新的无疑要属2000年北京人艺剧院演出的《原野》,导演李六乙,舞美设计罗江涛。这次演出可谓是对以往演出的巨大颠覆,显示出了荒诞的色彩:黑色的草长满舞台,白色鸽子自由地走动;一侧墙壁上悬挂着八九台彩电,反复播放1981年电影《原野》和美国影片《阿甘正传》的片段;大星、仇虎、常五、傻子从舞台中央的马桶里捞出几听可乐,围坐成一圈,说起了与剧情无关的话......[4]2006年,天津人艺剧院改编话剧《原野》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延松执导。王延松导演为了直接表现人性困苦的种种挣扎,把那种太具体、太现实的东西删除。所以原剧本中焦家厅堂上的种种摆设还有焦阎王像片以及两条铁轨、破旧的老屋、黑色的森林等意象被删除,导演要找到更加表现主义的方法来进入更深层次的人物内心。最后他找到了一种形式,即在舞台上用七个古陶类形象来参与表演叙事,导演想通过这些形象来突出整个剧的表现主义色彩。新时期的导演们用自己独特的智慧演绎着他们所理解的《原野》,该剧也在导演们孜孜不倦的挑战中走向经典化的历程。
3 观众的接受:热烈追捧
《原野》虽然在评论界褒贬不一,导演们对这部剧的接受也各不相同,但是这部剧却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从首演到今天,《原野》被不同的导演改编,被不同的剧团演出,被不同年代的观众观看,唯一不变的是反响都很热烈,可见《原野》有着无限的生命力。而这部戏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正如唐弢所说的那样,《原野》里面有戏。而这戏就是剧里面的冲突。首先,仇虎与焦家的冲突。焦阎王抢了仇家的地,烧了仇家的房屋,诬告仇虎是土匪并且叫人打断了仇虎的一条腿,仇虎的妹妹被送去妓院最后含恨而死,仇虎的未婚妻也被焦阎王抢过去做了他的儿媳妇。其次,花金子与焦母的冲突。婆媳矛盾古已有之,焦家也不例外。《原野》开篇就写到了金子问大星如果她与焦母同时落入水中,大星会救谁的这一经典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大多数观众都有生活体验,所以同样能提起观众的兴趣。再次,仇虎、大星与金子的冲突。这三个人的三角关系使得情节更加跌宕,更加复杂,也更满足了观众的期待。最后,仇虎内心世界的冲突。伤害仇虎与其家人的是焦阎王,而阎王的儿子大星是仇虎的胞弟,他是无辜的。仇虎更加明白大星的无辜,可是杀父之仇怎能不报,父债子偿的观念时时在他心中围绕。仇虎心中的无奈使得他杀死大星、又借焦母之手杀死小黑子之后变得精神崩溃,所以出现了很多内心交战的戏份,而这一切也紧紧揪住了观众的心。
第二,这部剧的好看点还在于里面的经典桥段和对白。曹禺深知怎样的对白才能抓住观众的心。例如剧中“捡花”那一段戏就非常有意思:
焦花氏:(忽然)回来,把花替我捡起来。
仇虎:没有工夫,你自己捡。
焦花氏:(命令地)你替我捡!
仇虎:不愿意。
焦花氏:(笑眯眯地)虎子,你真不捡?
仇虎:嗯,不捡,你还吃了我?
焦花氏:(走到虎的面前,瞟着他)谁敢吃你!我问你,你要不要我?
仇虎:我!(望焦花氏,不得已摇了摇头)我要不起你。
焦花氏:(没想到)什么?
仇虎:(索性逼逼她)我不要你!
焦花氏:(蓦然变了脸)什么?你不要我?你不要我?可你为什么不要我?你这丑八怪,活妖精,一条腿,罗锅腰,大头鬼,短命的猴崽子,骂不死的强盗。野地里找不出第二个 “shun”鸟,外国鸡......(拳头雨似地打在仇虎铁似的胸膛上)
仇虎:(用手支开她,然而依然乱鼓一般地捶下来)金子,金子。你放下手!不要喊,你听,外边有人!
焦花氏:我不管!我不怕!(迅疾地,头发几乎散下来)你这丑八怪,活妖精,你不要我,你敢由你说不要我!你不要我,你为什么不要我,我打你!我打你!我跟你闹!我不管!有人我也不伯![8]
这一段对白在《原野》中算是很经典的了。通过金子与仇虎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花金子的形象。她不仅美丽热情,并且大胆泼辣,她有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气,所以她的形象栩栩如生。再比如大星的懦弱、焦母的阴险,这些形象塑造都是通过对白来完成的。
第三,戏剧中出现的表现主义神秘色彩也使观众备感新鲜。曹禺在开篇序幕中这样写道:“秋天的傍晚。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8]紧接着用整个序幕来描写原野上的景物,最后仍然用“大地是沉郁的”作为收尾,为整个剧奠定了一个神秘的基调。而第三幕的表现主义手法更增添了神秘气氛。仇虎和金子在黑森林里苦苦找寻出路,但最终没有结果。此外,杀了大星的仇虎脑中出现了许多幻景:头顶平天冠,两手捧着玉笏的黑脸的阎罗王,披着青纱、乌冠插着黑翅的判官以及牛首马面、青面小鬼,都使舞台呈现出阴森恐怖之感。庙里不停敲打着的瘆人的鼓声,焦母追随而来的紧急的脚步以及她嘴里的叫喊,都使人的神经越来越紧绷。曹禺的这种创造无疑使观众觉得与众不同。虽然存在观众看不懂该剧的现象,但随着观众文化水平和审美欣赏能力的提高,剧中的表现主义也被人们所慢慢接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原野》的接受并不一帆风顺。不同时期的价值标准构成了对《原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的审视,虽然经历过责难和批评,但是《原野》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已然成为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继续被后人所欣赏和解读。
[1]古超强.《原野》主题意蕴研究述评[J].戏剧文学,2013(3).
[2]华忱之.论曹禺解放前的创作道路[J].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1(1).
[3]光明明.从演出史看《原野》的接受[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3).
[4]胡非玄.话剧《原野》改编的三阶段及折射出的问题[J].江汉大学学报,2009(4).
[6]丁素华.名著与花鼓戏——《原野情仇》导演构思[J].中国戏剧.1997(11).
[8]曹禺.原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0]田本相.《原野》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4).[11]欧阳弥生.一部充满现代“神话”美学理想的剧作——《原野》[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5).
——《原野》中焦母命运倒错的三重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