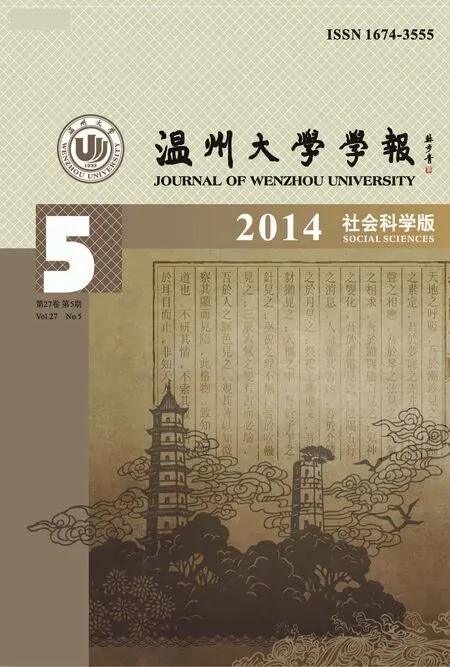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冯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古兰经》和《圣训》所规定的世界观、道德观是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包括“人类友爱互助”的理念、“平等协商共处”的准则、“重视交流合作”的策略三个方面。在21世纪,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仍是指导伊斯兰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行动指南。
伊斯兰;《古兰经》;国际关系理论
“伊斯兰是一种和平的宗教,它倡导宽容和普遍的兄弟情爱,并不把自己的宗教观念和意志强加于人,伊斯兰信仰者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1]215-216这个结论充分揭示了伊斯兰教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精神。但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一些东方学家对伊斯兰文化的误读和当今西方一些国家媒体的歪曲炒作,一些人把伊斯兰教与“战争”、“武力传教”、“宝剑”、“威胁”等话语联系在一起,宣扬“伊斯兰威胁论”,其目的是通过把伊斯兰教妖魔化,假想新敌人,混淆视听。由于《古兰经》所规定的世界观和道德观是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因此,本文以《古兰经》为主要依据,从理念、原则、策略三个方面对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探讨,并阐明其对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现代国际社会的重要价值。
一、“人类友爱互助”的国际关系理念
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以伊斯兰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为理论基础。《古兰经》明确宣示:“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1:2)①括号里的数字表示引文引自《古兰经》一书的某章中的某节, 参见: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 古兰经[M]. 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他是东方和西方的主。”(73:9)“人类本来是统一的民族,后来才分裂了。”(10:9)并认为:真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在和谐统一的世界中,人类相互依存、互为价值而存在。《古兰经》说:“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教,以便你们互相认识。”(49:13)并启示穆罕默德:“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21:107)在伊斯兰文化看来,真主创造的世界是由各民族、各国家人们构成的一个统一大家庭,人人都是真主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古兰经》要求穆斯林“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5:2)穆罕默德要求人们应该在真主之爱的阳光雨露沐浴下,彼此尊重、互助关爱、和睦共处,保持仁爱融融的兄弟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世界的和谐平衡,使之有序运转。由此,伊斯兰文化以真主统一性整体主义世界观为基础,以人际间相互依赖关系为价值取向,以维持世界的整体和谐为目的,形成了以“仁爱互助”为宗旨的处理人际、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正如西方学者古拉姆·赫瑞(Golam W. Choud Hury)所指出的:“根据《古兰经》,伊斯兰是一种宇宙秩序,是一种建立在普遍的兄弟之爱和道德价值基础上的国际体系。”[1]171正因以“仁爱互助”为宗旨,伊斯兰教主张在全世界建立一种“容纳民族、种族差异的和谐稳定、组织有序”的国际秩序,把实现“人类平等互助、和睦相处、团结友爱、怜贫惜弱、和乐盈盈”的大同世界作为最高理想追求。这种以世界相互依赖的整体性为基础、以“人类仁爱互助”为宗旨、以实现世界和平和人类团结为目标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伊斯兰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规定了伊斯兰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性质与方向。也正是从“人类仁爱互助”的理念出发,伊斯兰把“平等协商与和平共处”作为其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倡导国际社会中的“交流与合作”,反对战争、维护和平。
西方学者古拉姆·赫瑞(Golam W. Choud Hury)声称:“伊斯兰教把世界分裂为穆斯林世界和非穆斯林世界,命令其信仰者要进行‘圣战’,直到非穆斯林皈依伊斯兰,伊斯兰教是一种好战的意识形态,它具有征服世界的倾向,要把全世界都置于其统治之下。”[1]171著名东方学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甚至还说:“穆斯林和穆斯林之外的世界处于一种长期的宗教法定的强制性战争状态,这种状态只有在人类被伊斯兰征服后才能结束,穆斯林国家和非穆斯林国家是不可能缔结法定的和平条约的,战争永无休止,只能是为了利益需要才能有暂时的休战状态。”[2]这些观点都是以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误读伊斯兰文化的虚拟话语,是对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的严重歪曲,其失当之处在于:无视伊斯兰文化是重视人类相互依赖、仁爱互助、共生共荣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事实,是对伊斯兰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缺乏历史分析的任性结论。
二、“平等协商共处”的国际关系准则
从“人类仁爱互助”理念出发,伊斯兰文化形成了以“平等协商与和平共处”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关系准则,这是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和平特质的集中体现。具体体现为以下5方面:
(一)倡导民族国家间平等相待、和睦共处,反对以强凌弱
伊斯兰文化把“平等”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原则,《古兰经》反复倡导“真主面前人人平等”和“人类皆兄弟”的平等友爱原则,穆罕默德也一再强调“信士皆兄弟,他们的血统是相同的,伊斯兰教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①转引自: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第1卷[M]. 纳忠,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342.,“阿拉伯人不比非阿拉伯人优越,非阿拉伯人也不比阿拉伯人优越,红种人不比白种人优越,白种人不比红种人优越,除非凭借敬畏。”②转引自: 曹笑笑. 宗教因素对伊斯兰帝国民族关系之影响[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1, (2): 76-81.。伊斯兰教以这种兄弟关系原则处理国际关系,要求对各民族、各国都要平等相待,要“亲爱近邻、远邻”(4:36),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伊斯兰教坚决反对迫害弱小民族、欺侮弱小国家的不义行为。《古兰经》说:“除因复仇或平乱外,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5:32)“应受责备的,是欺侮他人、并且在地方上蛮横无理者;这些人将受痛苦的刑罚。”(42:42)《古兰经》对欺侮弱者、草营人命、发动战乱者给予了严厉的谴责,并为其安排了应得的惩罚:“迫害信士和信女而不悔过的人们,必受火狱的刑罚,并受火灾的惩治。”(85:10)这些教诲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教渴望全人类和平共处的殷切之情。
(二)提倡超越意识形态处理对外关系,反对狭隘民族主义
伊斯兰教主张对外交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古兰经》告诫穆斯林:“对于宗教,绝无强迫。”(2:256)“难道你要强迫众人都做信士吗?”(10:99)穆罕默德也说:“提倡宗教意识而进行战争者不是我们的信徒”①转引自: 艾哈迈德·爱敏.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第1卷[M]. 纳忠,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9.,他反对把本民族、本宗教的意志、意识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循循善诱人们要破除狭隘民族主义偏见,以宽广胸襟积极扩大对外交往。在历史上,早在穆罕默德传教之初,尽管一些犹太人对伊斯兰教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可是当犹太人和穆斯林发生纠纷时,穆罕默德命令穆斯林优待犹太人,不偏袒穆斯林。穆罕默德率军进驻麦加时,不仅直接发布通令,大敕首要之敌,而且制定了《麦地那宪章》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著名思想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尽管在当今世界中,确实充满了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冲突的例证,但是,阿拉伯世界和中世纪西班牙的穆斯林统治者们,都曾长期试图将犹太人融为当地社会群体中的安全成员,确保他们的自由——有时是领导地位——受到尊重。”[3]这些事实都体现了伊斯兰教与人为善、宽厚博大的和平精神。伊斯兰教强调宗教不只是民族的、种族的或个人的,而是属于全人类的。美籍伊朗裔学者舍里·亨特(Shireen T.Hunter)也指出:“伊斯兰反对通过战争宣传自己的教义。”[4]62《古兰经》中也没有让异教徒归顺伊斯兰宗主国且成为穆斯林的规定,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伊斯兰超越宗教、民族界限,关爱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博爱精神。
(三)主张通过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暴力和战争
“协商”是伊斯兰政治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伊斯兰处理内外事务的重要机制。《古兰经》指示穆斯林:“他们的事务,是由协商而决定的。”(42:38)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伊斯兰主张“以德报怨”,倡导“仇必和而解”,提倡通过协商解决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古兰经》说:“只因为从真主发出的慈恩,你温和地对待他们;假若你是粗暴的,是残酷的,那么,他们必定离你而分散;故你当恕饶他们,当为他们向主求饶,当与他们商议公事”(3:159);“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美的态度与人辩论”(16:125)穆罕默德说:“协商是悔恨的碉堡,是谴责的保障。”②转引自: 马明良. 伊斯兰文化新论[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7: 181.他认为只有运用“协商”的会议机制才能解决国际矛盾和争端,坚决反对使用武力侵略、征服其他国家。《古兰经》反复教导穆斯林:“你们不要侵略,的确,真主不喜欢侵略者。”(2:190)“除不义者外,你们绝不要侵犯任何人。”(2:193)这些内容也是伊斯兰国际关系原则所内蕴的维护世界和平的生动体现。
(四)强调对外交往要履行条约、讲信修睦,反对欺诈和爽约
“诚信守约”是伊斯兰规范人们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行为的重要道德原则,表现在国际关系中,主要是通过自我信守诺言,使对方诚服,从而实现国家间和睦共处、互助合作的一项行为准则。《古兰经》说:“当时,我(真主)与你们缔约,说:‘你们不要自相残杀,不要把同族的人逐出境外。”(2:184)“与你们订约的人们,其实是与真主订约。”(40:10)“你们当履行真主的盟约”(6:152),“不要互相背约”(49:12)。伊斯兰以真主的权威性确立了履行条约的神圣至上观念,通过宗教信仰对政治行为的核准,为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和践行条约找到了终极价值支撑,它不仅重视条约机制在协调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且以真主的律令作为履行条约的监督机制,这是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探索对外关系机制的一项重要成果。由此,伊斯兰教主张在对外交往中要灵活运用各种手段调整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重视条约机制的作用。美籍伊朗裔学者舍里·亨特(Shireen Hunter)指出:“穆斯林在历史上很重视条约关系,先知曾说,你们不能凌驾于阿拉伯人聚居区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之上。并最终与犹太人和基督徒签订了条约。”[4]65所以,正是重视条约机制的作用,“穆斯林国家能像对待自己的同胞兄弟一样对待非穆斯林国家,如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国际关系准则在诸如《阿拉伯国家联盟条约》(1945年)、《孟加拉条约》(1955年)、《伊斯兰会议组织宪章》(1972年)、《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条约》(1989年)等协定中得到认可。”[5]75这些条约机制及条约监督机制的确立使伊斯兰维护和平的理念有了机制化、制度化的保障。
(五)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伊斯兰教重视民族国家间和睦相处,反对战争,但在外部势力危及民族国家主权和利益时,绝不作无原则的妥协退让,而是坚决反对霸权强盗行径。《古兰经》说:“你们怎么不为(保护)主道和(解放)老弱妇濡而抗战呢?”(4:75)“如果这伙压迫那伙,你们应当讨伐压迫的这伙。”(49:9)“被进攻者,已获得反抗的许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22:39)由此,伊斯兰教为穆斯林规定了“吉哈德”义务,号召穆斯林勇敢捍卫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权益。但《古兰经》又反复告诫穆斯林在反抗暴行中要适可而止,在作战中应遵守“宽待俘虏、允许悔过、既往不咎”的宽容仁慈原则,“你当反抗他们,直到迫害消除,而宗教专为真主;如果他们停战,那么,除不义者外,你们绝不要侵犯任何人。”(2:193)“如果他们退避你们,而不进攻你们,并且投降你们,那么,真主绝不许你们进攻他们。”(4:90)这些内容都表现出一种宽厚仁和的人道主义精神。伊斯兰学者穆萨·赛里姆(Musa Saleem)指出:“在地球上迫害和压迫弱者是真主谴责的行为,真主不会宽恕任何方式的专制和暴力,一个压迫和迫害他国,给他国造成苦难的国家直接与真主在《古兰经》中的正义、虔诚和仁慈的戒律是相违背的,伊斯兰反对所有形式的邪恶和暴力。”[6]此论断进一步揭示了伊斯兰教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精神。
三、“加强交流合作”的国际关系策略
伊斯兰文化自古就善于吸纳周边及域外文化成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对世界各民族文化都能够“爱其所同,敬其所异”。一部伊斯兰文明史,就是伊斯兰文化与不同区域文明相互吸纳、相互融通、整合的历史。伊斯兰文明曾吸收和融合了波斯文化、基督教文化、犹太教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这使它成为一种深厚博大的开放系统,并由此培植了伊斯兰文化珍惜友谊、乐于交流的内在特质。《古兰经》颂扬理性,鼓励求知,号召穆斯林在理性之光照耀下,洞悉世界之奥秘,谆谆教导人们要“开阔胸襟”(94:1),树立“宽博浩大,怀来万邦”的恢宏气度和崇高境界,摒弃狭隘的民族偏见,加强与世界各民族国家的交流和友谊。穆罕默德也鼓励穆斯林:“求知,从摇篮到坟墓。”①转引自: 杨启辰.《古兰经》哲学思想[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0.113“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①111在这些教诲的激励下,伊斯兰教产生后不久,阿拉伯国家的友好使者就开始了与世界众多国家的交流,其中,与中国的友好交流尤其源远流长,在国际关系史上树立了和平交流的光辉典范。
为使世界和平得到制度化保障,伊斯兰教主张建立超越国界的合作性实体。“自伊斯兰教创立后,就探索废除民族主义的多神教义,试图创立一种建立在共同宗教认同基础上的穆斯林‘乌玛’。”[7]有学者甚至指出:“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是围绕《古兰经》中的‘乌玛'概念建构起来的。‘乌玛’这个词在《古兰经》中出现达64次之多,该词的最主要意思是具有共同特性和命运的活生生组织的存在物。”[8]公元622-632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立的第一个穆斯林国家已不是建立在家族、部落关系之上,而是一个以宗教道德和精神原则为基础,全体成员参与社会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实体,这也是穆罕默德亲自进行的第一次构建超民族政治行为体的实践。因此,“乌玛”正是伊斯兰最早构想的确保国际秩序、加强国际合作的一种原初国际组织范型。在《古兰经》中,“乌玛”这个词是用来代替“民族”这个词的,尽管许多民族可能属于同一种信仰的社会共同体,但其中任何一个民族并不一定只属于同一个种族、说同一种语言和在同一个地域,伊斯兰教为人类联合提供了一种模式。
四、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的现代价值
以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a1-Din a1-Afghani)、穆罕默德·阿布杜(Muhammad Abduh)和拉西德·里达(Rashid Rida)为代表的近现代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家为了回应西方的挑战,救亡图存,大力宣传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其目的也是要实现世界穆斯林超民族、超地域、超政治的联合。他们曾在其主办的《灯塔》杂志上宣传建立伊斯兰会议组织框架的主张,设想以麦加为中心,以朝觐为契机,举行全世界穆斯林代表会议,使全世界穆斯林友善交流,加强合作,其目的就是探索加强穆斯林国家沟通与合作的机制化手段。《古兰经》精神和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观念激励了全世界穆斯林,他们不仅践行着系统的穆斯林团结的思想,并逐步建构起了组织机制。从1926年5月在开罗召开第一次伊斯兰会议至今,在伊斯兰世界,曾先后召开了伊斯兰经济会议、国际伊斯兰会议、世界穆斯林大会、伊斯兰最高会议等国际性会议,并先后建立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伊斯兰世界联盟、穆斯林世界联盟等国际性和地区性的组织。特别是饱受1967年阿以战争创伤的穆斯林进一步认识到了加强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并于1969年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召开了第一次伊斯兰最高会议,这是第一次最大的伊斯兰共同体跨世界的交流,全世界穆斯林集中在一起讨论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挑战,象征着伊斯兰社会的团结、联合和力量。这次会议的结果产生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其目的是要创立一种国际伊斯兰论坛或组织,表明伊斯兰国家参与多边对话合作的范围和层次不断扩增,在这种论坛或组织上所发布的宣言所表达的原则和规范,有利于增强人们对国际关系空间的认同,塑造人们的新观念,从而根本上改变人们认知世界的范式,有助于抑制与缓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冲突,增强国际合作与协调。所以,“把伊斯兰视为好战的和武力的宗教是西方的话语,这些西方学者越快改变先入为主的观点越好。随着彼此的充分了解,伊斯兰与西方的合作领域会更加广阔,将从根本上改变矛盾和敌对状态。”[1]183而这正是人类和平的福音。
当前,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相互依赖、互动共荣已是大势所趋,但是一些西方国家仍然固守其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模式,奉行“零和”战略,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增添了不和谐的音符。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诸多现象,世界呼唤东西方文明的整合、对话与交流,国际社会越来越需要协调与合作,人类必须携手共建关爱其整体命运的新型战略思维框架。而伊斯兰教所具有的关照人类命运的整体观念、强调人类平等共处的和平精神、重视人类协调与合作的和合精神,必将为人类新型战略思维范式的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正如这些有远见的学者所说:“穆罕默德启示了一种理想化的思想体系,其作用是为大多数人有意识地合作提供理论根据。伊斯兰是与现代欧美文明不同的思想体系,这种历史悠久的独特文明,在世界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9]“在通行的国际体系中,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伊斯兰没有被降到次要地位,相反,它的普遍博爱思想主张将对人类生活提供一种指导。”[5]76“伊斯兰关于国际关系的原则、价值和目标能够成功地指导对外关系,并对对外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10]“在这个核武器存在、两种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伊斯兰教能够通过坚持它的普遍的兄弟之爱和宽容原则对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1]175“‘关于一统与一体化的伊斯兰精神’无疑对于建立一种创造性的和平可以作出实质贡献。”[11]这也正是我们向世人昭示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目的。
[1] Choudhury G W. Islam and the modern Muslim world [M]. London: Scorpion Publishing Ltd, 1993.
[2] Lewis B.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Politics and war [M].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4: 175.
[3] [印度] 阿马蒂亚·森. 身份与暴力: 命运的幻象[M]. 李风华, 陈昌升, 袁德良,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55.
[4] Hunter S. The Future of Islam and West-Clash of Civilizations or Peaceful Coexistence? [M]. Washington: Praeger Publishers, 1998.
[5] Sidahmed A S, Ehteshami A. Islamic Fundamentalism [M]. New York: Westview Press, 1996.
[6] Saleem M. The Muslim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M]. London: ISDS Books, 1993: 15.
[7] Faksh M. The Future of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M].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7: 10.
[8] Ahsan A.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 An Introduction To An Islamic Political Institution [M]. Herndon: Intl Inst of Islamic Thought, 1988: 2.
[9] Krdjci J. The Civilizations of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102-103.
[10] Sulayman A H A A. The Islam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Directions for Islamic Methodology and Thought [M].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slamic Thought, 1987: 141-142.
[11] [德]海因里希·贝克吉塞拉·希密尔贝尔. 文明: 从“冲突”走向和平[M]. 吴向宏,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25.
The Islamic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its Modern Values
FENG Yun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The Islam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is based on the world and moral outlooks defined by The Qur’an and Hadith, and constituted by the conception of “mutual aid and fraternal friendship among people”, the maxim of “negotiation and coexistence on an equal footing”, and the strategy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21stcentury, the Islam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is still the guideline for Islamic countries’ deal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lamic Culture; The Qur’a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D5
A
1674-3555(2014)05-0088-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4.05.014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13-09-10
冯雲(1988-),女,宁夏银川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