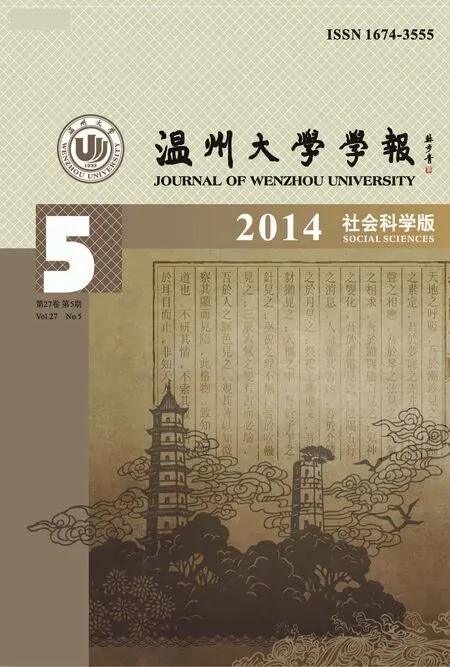有契于心:袁燮文艺思想之精神内核
杨万里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有契于心:袁燮文艺思想之精神内核
杨万里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袁燮文艺观的形成源于其心学思想。在文艺审美旨趣上,他推崇浑然天成之美境。为达到此种境界,袁燮提出“有契于心”的创作理念,并延伸出书以传心与画以写心的艺术命题。而且“有契于心”也是袁燮的鉴赏理念,他认为观者之于书画重点应在体悟省察作者之道心,从而使自己之本心有所感发。因此,他十分重视文艺创作主体之心性修养,认为这是使文艺作品“有契于心”的根源,也是诗书画是否具有宝藏价值的决定因素。
袁燮;心学;文艺思想;书画;有契于心
袁燮(1144-1224年),字和叔,庆元府鄞县(浙江宁波)人,“甬上四先生”之一。他于淳熙辛丑(1181年)登进士第,由此步入仕途,他是四先生中在朝最久者,这也决定了他朝着社会政治方向发展陆氏心学的学术特色。全祖望指出:“慈湖之与絜斋,不可连类而语。慈湖泛滥夹杂,而絜斋之言有绳矩。”[1]2525对袁燮的学术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袁燮存世的著述有《絜斋家塾书钞》《絜斋集》《絜斋毛诗经筵讲义》等。袁燮自身并不擅书画,但他的一些书画题跋资料为我们深入解读其书画思想提供了依据。且其书画题跋中论述他人书画作品时带有明显的心学色彩,可以说是其心学思想在文艺领域的延伸。因此,对其书画思想进行探讨,不仅有利于全面解读袁燮的学术思想,还可以借此管窥南宋心学之于书画领域的影响与冲击。且袁燮在书画题跋中反映出的书画观念有很多与其文学观念甚为相合,可以说他的综合文艺观均是建立在心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心学即是其文艺观的精神内核。
一、浑然天成:文艺美学追求
袁燮在书画审美旨趣上推崇浑然天成、不露痕迹之美。这集中体现在他的《跋林郎中巨然画三轴》中:“仆尝论技之精者,与人心无不契合。庖丁之解牛,轮扁之斫轮,痀瘘之承蜩,其实一也。今观此轩所藏巨然墨妙凡三轴,有无穷之趣,而无一点俗气,浑然天成,刻画不露,深有当于人心,可谓精矣,是以君宝之。”[2]104巨然是五代南唐、宋初著名山水画家,师承董源而能自出新意。刘道醇曾评巨然《故事》与《山水》二轴曰:“古峰峭拔,宛立风骨;又于林麓间多用卵石,如松柏草竹,交相掩映。旁分小径,远至幽墅,于野逸之景甚备。”[3]所谓“野逸”主要指一种自然之趣,晚唐画家孙位画水而能写其“活”,故而深得后人推崇。那么何谓逸品呢?黄休复释曰:“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4]可见逸品最得自然之真趣,不见法度与刻画痕迹,可谓天成。袁燮评其曰“浑然天成,刻画不露”也是推崇其自然之趣,只不过他将这种画风的形成归功于与人心相契,这是前人所未提的。
所谓浑然之境界其实有二:一为天籁自鸣,不烦雕琢之天成浑然;一为刻画精粹,痕迹不露之人工浑然。袁燮更推崇前者,《题臧敬甫所藏李伯时画观音佛》曰:“观音入定,一念不萌,龙眠写之,浑然天成。非观音之心至简至易,匪高匪深,或者神交默契,无间之可寻耶?”[2]104李伯时是宋代著名画家,号龙眠居士,尤擅画山水与佛像。李伯时擅画佛像与他精通禅法也有一定关系,他晚年隐居龙眠山庄,常与高僧来往谈论,因此可以与观音之心相契而能达浑然天成之境界。之所以说此处是一种不烦雕琢之浑然,还与李伯时的白描画法相关,他的人物画不敷丹青而纯用白描,虽高度简洁却可以效果明快,光彩照人。此处所画观音佛也应是这种白描笔法,这种画作既是神交默契,又是由几条颇具韵律的墨迹来完成,基本上是直己而发无需刻画的。对不烦雕琢之浑然美在袁燮诗论中更是推崇备至,如他在《题魏丞相诗》中曰[2]96:
“古人之作诗,犹天籁之自鸣尔。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直己而发,不知其所以然,又何暇求夫语言之工哉?……魏晋诸贤之作,虽不逮古,犹有舂容恬畅之风。而陶靖节为最,不烦雕琢,理趣深长,非余子所及。故东坡苏公言:‘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唐人最工于诗,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巧,去古愈邈。独杜少陵雄杰宏放,兼有众美,可谓难能矣。然‘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子美所自道也。诗本言志,而以惊人为能,与古异矣。后生承风,熏染积习,甚者推敲二字,毫厘必计。或其母忧之,谓是儿欲呕出心乃已。镌磨锻炼,至是而极,孰知夫古人之诗,吟咏情性,浑然天成者乎?”
袁燮提倡天籁自鸣之古诗,而对后人沉溺辞章、雕琢刻画以致显露出辛苦迫切之态至为鄙夷。因为在他看来后人过于执着诗歌技巧、刻画痕迹毕现的做法破坏了诗歌浑然天成之美境。袁燮虽无书画作品存世,但我们亦可从其自作诗文中窥探其文艺创作中的审美追求,《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文:“大抵淳朴质直,不事雕绘,而真气流溢,颇近自然。”[5]可见无论其诗画理论还是其创作均体现出对淳朴自然、浑然天成之美的追求。
所谓人工浑然即雕琢之极而又若不经意,镌磨锻炼而又不露痕迹。他在《跋西园诗集》中曰:“欧阳公言语妙天下,浑然精粹,无片言半辞舛驳于其间,可谓至矣。而张之壁间,往复观之,一字未安,改之乃已。譬之美玉,极雕琢之工,而后莹乎其可观也。”[2]99他以璞玉经切磋雕琢而成美玉来喻欧阳修之于诗文的刻画过程甚为贴切,他认为欧阳修的诗文之所以能浑然精粹完全是后期打磨的结果。不过欧阳修之打磨文字却能不露痕迹,这是难能可贵的。他接着说:“今观西园公之诗亦然,精丽高雅,无辛苦迫切之态,若不甚经意者,而阅其稿则窜定多矣。”[2]99可见追求自然之真趣与雕琢之工夫并非完全相斥,只要无刻琢痕迹,则亦可达到浑然之效果。这与同为心学派传人包恢的“磨砻圭角”论可谓不谋而合,如他评徐致远诗时说:“今泛观远斋诗,或者见其若出之易,而语之平也。抑不知其阅之多,考之详,炼之熟,琢之工,所以磨砻圭角而剥落皮肤,求造真实者几年于兹矣。”[6]这与袁燮之论可谓异口同声。
浑然天成之美又自有平淡滋味蕴蓄其中。袁燮在《资政殿大学士赠少师楼公行状》中评楼公诗文曰:“属辞叙事,以意为主,不事雕镌,自然工致。旧有诗声,晚造平淡,而中有山髙水深之趣。”[2]150宋人崇尚平淡之美,而理学家尤为推崇,如陆九渊称陶诗“来自天稷,与众殊趣,而淡泊平夷”[7]103;包恢也认为诗人应以“汪洋澹泊”为诗歌最高境界。可见浑然天成之美外在表现即为自然、真趣、无痕、平淡,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浑然天成之境呢?
二、技之精者,与人心无不契合
袁燮的文艺思想有着浓烈的心学色彩,他认为心是万事万物之本源,诗文书画等技艺之事也应自本心流出。书画作者技由心出,故与其心契合;而观者见其翰墨如见其心,故观者之心与作者之心也自然神交默契。
在袁燮的心学思想体系中,心是人生存之本,也是万物之源。如他说:“人生天地间,所以超然独贵于物者,以是心尔。心者,人之大本也。”[1]2526而且他认为人心至善至神,广大悉备,因此本心即道,天下并无心外之道。上至君臣治理国家,下至百姓生活日用,无不根诸本心:“古者大有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彻无间,九州四海,靡所不烛。”[2]4加上他所说的技之精者与人心契合之论,足见袁燮将心视为一切社会实践的本源。这样他的心学思想就不像陆九渊、杨简那样仅重心之体,而是沿着“用”的层面对心学进行了推进。这样心体就进入人们的经验领域,成为一个可以与实践联系起来的范畴。
所以在袁燮看来,一切器物、书画亦应发于人心。且看他在《跋赵侍郎三物》中所说:“余观古人所作,一器一物,靡不精致。诚心所形,非苟然者。今之器物,较之全盛时已不侔矣,况愈远者乎?即此可以观世变云。”[2]105上古三代世风昌明,人之本心未泯,故而以至善至神之心所作器物自然精致而又浑然天成。今之器物不如古,乃是人心不古,人之本心一旦被私意蒙蔽则所形器物自然难以与古人之物媲美。后人多自出新意而求变,崇尚雕琢刻画,追求技巧之工,殊不知人心本至正至善,正所谓“此心此理,贯通融会,美在其中,不劳外索。”[2]90后人之“新意”正是对本心的破坏,难怪形于物不能追踪于古。器物如此,翰墨亦然,袁燮题王羲之书法曰[2]99:
“钟鼎古篆,荘重有典则,如正人端士,对之令人起敬。篆变而隶,犹曰近古。自东晋以来,推王逸少为第一,不知篆隶之遗法欤?抑逸少自出新意为之欤?”
袁燮在这里提倡庄敬中正的钟鼎篆隶,而对近世遗弃古法之书颇有微词。联系其在《跋赵侍郎三物》中所说及技之精者与人心契合之论来看,所谓古法无非是出于本心的无法之法。王羲之以来世人多尚行草,多出己意而非发于本心,以致人工之美超越了浑然天成之美,这是袁燮所不愿看到的。而文艺发于本心一直是心学家所提倡的,陆九渊就经常提到诗文“直写胸襟”的观念。
不过,对于后人书画袁燮也非全盘否定,他认为只要是本心之所形,即具有宝藏之价值。如他在《跋涪翁帖后》曰[2]101:
“涪翁书大率豪逸放肆,不纯用古人法度。常称:‘杜周有言,三尺法安在哉?前王所是著为律,后王所是疏为令。’以此论书而东坡绝倒。雅意于不俗,有戈戟纵横之状,不得已焉耳。今观此帖,乃能敛以就规矩,本心之所形也。良可宝云。”
黄庭坚的书法瘦硬奇崛,甚至有欹侧怒张之态,所以袁燮以“豪逸放肆”评之。黄自称书本无法,颇有张融“恨二王无臣法”之意。但袁燮认为这是黄庭坚追求不俗之雅意的体现,而且黄庭坚论书常推崇胸中应有道义并广之以圣哲之学,可见其雅意与道并无二致,豪逸之书非其本心所发。而一旦发于本心,收敛精神以入规矩,黄之翰墨尤为可宝。
袁燮有契于心的书画思想其实有两个维度,即契于创作者之心和契于观者之心。创作者以其本心形于翰墨,则观者可以由翰墨窥探其本心。按照心学家本心即道心、本心无二的观念,作者之心与观者之心又可以默契无间。因此,袁燮提出了书以传心、画以写心的艺术命题。他在《跋高公所书孝经》中说[2]93:
“《孝经》一书,百行之根源也。赠特进四明高公尝亲笔之,以授其孙,传之至今。特进乃春官贰卿介弟,贰卿以学行之粹,著称于绍兴间,与秦丞相相忤,终其身不复用,屏居乡闾。士之得于亲炙有所启发者多矣,况其同气之亲乎。今观其遗书,楷而有法,无一点一画猝然而作者。扬子云言:‘书,心画也。’柳诚悬亦云:‘心正则笔正。’心者,一身之宗主,家传之要道也。人孰不爱其子孙与之爵秩,心不正则不能继;丰其财用,心不正则不能保。惟此心之传,精纯不杂,气脉不间,其将弥久而弥昌乎?公之曾孙国子进士指得此一编,保而藏之,所以宝此心也。高氏之兴,庶乎未艾,余是以嘉之。”
这是袁燮为高开手书《孝经》所作的跋文,其中提出一个重要书法价值,即传心。高开此书有几个特点值得指出:首先其所书内容为《孝经》,这是儒家经典之一,也是儒家伦理道德之集中体现;其次高公之德行虽无直接叙述,但通过其兄之学行忠义足以见之;再次其书楷而有法,说明高公创作时本心诚敬中正,无豪逸放肆之态;最后,高公后人非珍藏其翰墨,而是宝其字画中流淌着的道心。高公以本心而书,其子孙亦以本心乘之,袁燮所嘉亦是其“精纯不杂,气脉不间”的道心。可见,书以传心,观者自可由书而观作者之风流蕴藉,从而有所感发而唤起自我之本心。这就将书法翰墨也纳入到心学修养范围中来。再如其《题晦翁帖》也指出:“夫君子之善善恶恶,岂有私意?优于天下而喜,邦家殄绝而忧,根诸中心,形于翰墨,道夫宝藏之,时时览观有所感发,其用力于斯道者耶?”[2]104可见,翰墨传心几乎成为袁燮书画批评的一个核心理念,而这也几乎是心学家论文艺的共同特征。
书法可以传心,而绘画亦是写心,且“技之精者与人心无不契合”的理念即是在袁燮论画时提出的。他在《跋林郎中巨然画三轴》中,从画技之精湛的角度提出契于本心的理论,这主要出于对本心神灵妙用的考虑,并援引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几个例子以说明巨然技艺之出神入化。在袁燮看来,包括书画在内的一切技艺,要想真正达到入神的境界就必须与人心相契合。因为人之本心至为神明正善,是非曲直本心自辨,且心与万物浑融一体,神灵妙用以至于道。而技之最高境界即几于道,技而至于道则可以令观者心为之动。袁燮在《跋林郎中韩干马》中指出:“尝观杜少陵丹青引有曰:‘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所以咏曹将军画马之工也。……虽然将军之技几于道矣,弟子如韩干且不能及矣,况寻常之流乎。披图阅之,凛然生意动心骇目,可贵也哉。”[2]104韩干自称“厩马万匹皆吾师”,汤垕《古今画鉴》也赞其:“画马得骨肉停匀法,遂与曹韦(偃)并驰争先。”[8]可见韩干画马即使不及其师,也已达很高境界。由于其师法自然,心与物浑融一体,固其所画之马才能凛然如生而使人见之“动心骇目”。
其次,有契于心还体现在画家与所画人物的神交心契。袁燮在《题臧敬甫所藏李伯时画观音佛》中说:“观音入定,一念不萌,龙眠写之,浑然天成,非观音之心至简至易,匪高匪深,或者神交默契,无间之可寻耶?”[2]104前面已提到,李伯时能将观音之像画到浑然天成之境,根本原因在于他与观音之心能够神交契合。这在袁燮看来是可以达到的,袁甫在《絜斋家塾书钞序》中述其父袁燮的话曰:“吾之本心,即古圣之心,即天地之心,即天下万世之心。”又说:“圣人即我,我即圣人。”[9]470可见,龙眠之心是可以与观音契合的,而一旦全体浑融,了无间隔,则所画自然浑成至善。
再者,有契于心还体现在观画者的品鉴旨趣上,不是以画之技法或画面为中心,其落脚点在观画而能唤起某种心思意趣。历来以临画不如真迹为贵,而袁燮以为画的功能在写心,在传作者的风流余韵,故而真与临并不足为贵。如他在《跋家藏顾宏所临王摩诘雪江图》中指出:“后世率以临画不足为奇,惟真迹乃可贵。然韩退之《画记》有云:‘得阎本,绝人事而摹得之。’是非真迹也。失之于闽中,而往来于怀不能自释,何惓惓若是耶?王初寮生于极盛之时,所见名画多矣,而顾谓此图为珍玩,不以为临本而鄙之,岂其风流余韵有可贵者耶?”[2]104袁燮认为,王初寮宝玩王维《雪江图》之临本乃是贵其风流余韵,或者说王摩诘《雪江图》唤起了王初寮的超然出尘之心,所以说非贵其画乃有契于心也。袁燮之宝藏何尝有异于此?袁燮自己在观山水画时亦常因观画有契于心而起逍遥山林之思,这在其《谢毗陵使君惠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2]317:
“都尉风流贵公子,结交海内知名士。磨砻禁脔骄侈习,雅意登山与临水。十幅烟江迭嶂图,当时展玩忘朝晡。老仙一顾叹奇绝,落笔妙语春华敷。此诗千载传不朽,此画如今宁复有。我来薄宦大江滨,无价之珍俄入手。一山雄特倚天立,下视群峰如拱揖。断崖飞出玉虬龙,元气淋漓鬼神泣。山中乔木堪栋梁,山外烟波凝翠光。数间野店傍林樾,一叶扁舟浮淼茫。往时只诵苏公句,想象都尉图中趣。岂期今日见逼真,端与前辈同机杼。自怜老大无他求,尘劳羁绊空悠悠。安得千岩万壑里,寻幽择胜逍遥游。我心欲往足无力,纵观此画如亲历。毗陵使君真可人,嘉惠不啻千金直。平生辞受关钥严,兹焉讵敢伤于廉。毗陵万口皆归重,道义相与吾何嫌。”
此诗是一首完美的诗画融合之佳作。开始即对王诜的风流雅意进行了赞美,接着提到了苏轼的题画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中间几句对画中山林之景的描写可谓精彩绝伦,不但具有自然之真趣,且透露着一股超逸脱尘之情怀。当袁燮见到真迹时回想往日苏公之诗句,不得不感叹苏诗与王画之构思、胸臆契合如一。尤其是此诗最后可谓点睛之笔,袁燮观画而有契于心,唤起了自己“寻幽择胜逍遥游”之心。可谓足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观画而得到了心之慰藉。
三、创作主体之心学修养
袁燮既然以书画发于本心为浑然天成之根本条件,且其评论书画时也多次贯注以“有契于心”的理念,那么强调主体之心学修养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袁甫曾在《絜斋集后序》中说:“浑然天成者,有道有德之言也。道德不足,言辞虽工,所为天者已不全矣。君子奚尚焉?我先君子之属辞也,吐自胸中,若不雕镌,而明洁如星河,粹润如金玉,真所谓浑然天成者乎。”[9]329袁甫此处已经指明,袁燮所追求的浑然天成之境界是由主体的道德修养为根本的。
心学家向来提倡收拾精神、涵养德性的人格修养。他们认为本心至善,一旦蒙蔽本心则坏端始生,所以他们十分重视保养本心,不敢丝毫放情逸意。如陆九渊曰:“心之本真,未尝不善,有其不善者,非其初然也。”[2]90袁燮也承其说,推崇本心之至善:“人之一心,至贵至灵,超然异于群物。天之高明,地之博厚,同此心耳。此心常存,善则行之,如履康庄;不善则避之,如避坑谷。此心放逸,舍康庄而弗由,坠坑谷而不悟。”[2]118而且心学家早就注意到文艺创作与心性修养之间的关系,陆九渊就常称诗文类于作者之气质修养,他也很重视道心对文艺之决定作用:“主于道,则欲消而艺亦可进;主于艺,则欲炽而道亡,艺亦不进。”[7]433强调对道的追求即强调文章之理会本心,因为本心即道。袁燮在这点上也继承师说且多方面发挥,他也十分重视对本心的持守:“大哉!心乎。天地同本,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则亦可以与天地相似。”[2]111并认为人心本至刚至正,其受到物欲与邪念之蒙蔽则会落到“弱而不返,以顺为正,自同妾妇”之境地。他还把心性修养延展至书画领域,强调创作主体兢业以保养本心、涵养志气的重要性,如他在《跋范文正公环庆帖》中说[2]99-100:
“范文正公以英迈宏杰之才震耀当世,区置西事,具有方略。观此一帖,可推而知矣。夫人物伟特如是,而形于字画乃尔精谨,何也?志气要当恢张,保养务在兢业,缺一焉不可。兢业而不恢张则所志者狭矣;恢张而不兢业则所养者亏矣。古人有言:‘胆欲大,心欲小。’公兼斯二者,兹所以为一代之杰也欤?”
袁燮对心性修养的重视在其《题豢龙图》中也得到了集中体现:“人生天地间,良心实为主。利欲汩其真,甘与俗子伍。胡不鉴此图,保养虚明府。道义有真乐,不羨圭与组。于我如浮云,服膺圣师语。”[2]313在这首题画诗中,袁燮以龙之本心被物欲所摇而甘于被豢龙氏狎玩如同儿女妾妇为例,从而引出以上这段关于保养本心的议论。他认为良心为人生于天地间之根本,应该不被利欲所动而追求道义之乐,必须做到视物欲为浮云才能维持自己的一颗真心。袁燮对创作主体心性修养的重视还表现在不轻发言辞议论,他认为这也是敬谨持守的内在要求。在《跋西园诗集》中袁燮之所以对欧公和西园公之雕琢诗文不予批判而且给予“浑然精粹”之赞美,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对他们敬谨于心的创作态度的考虑,他评西园公之诗曰:“大抵似其为人,自律甚严,纤微有所必计,亷白之操,著称一时。宜其发于笔端,亦犹是也。”[2]99
袁燮在评论书画时还十分推崇作者先立其志,从而广大其胸襟,以确保本心不被俗氛所汩。对于立志的重要性,其《赠吴氏甥》(其一)中说:“男儿何所急,为学要立志。此志苟坚强,天下无难事。超然贵于物,万善无不备。厥初本高明,有过则昏蔽。”[2]309对作家志气的强调同样反映在他的论书题跋中,其《跋林叔全所藏东坡帖》说:“观公此帖,足以知其平生之志不在于区区口体之养,高名全节迄今炳焕,信非偶然。”[2]100对苏轼精忠之志与高尚气节给予了高度赞扬,且认为后人宝藏东坡帖也是出于对其心胸的敬重。在《跋林户曹帖》中他更明确指出,林公之遗墨之所以清雅可爱,乃是因其宅心仁厚乐善好施,志趣脱俗而感通神明,故而“灵台湛然,不为俗氛所汩,流露宜尔”[2]102。由此可见,袁燮在评论前人翰墨时,非常重视主体之志节与胸襟,并认为这对书法有着本源意义。在袁燮看来,收藏或观赏翰墨者也不再是以书法艺术为中心,其品鉴旨趣已然转移到创作主体之心源上来,由论其末端转而论其本根。这在其论诗时亦有体现,其《跋云巢王公〈续雅〉》指出:“云巢王公名卿之子也,嗜古书,有美才,而恬于荣利。凡世俗所乐者不入于心,而岩壑奇絶之趣,斯须不忘也。胸襟如此,发而为诗,清新俊逸,出乎尘垢之外,理当然尔。”[2]93可见,心学家论文艺基本可以互通,论书画亦是论诗文,论诗文亦可作书画论观之,因其有一个根源性的结合点——本心。
袁燮还特别推崇本心的正直品质。他认为人心本正直:“自早至夜,无一念而不敬,惟敬故直,惟直故清。直者,正直也,人之本心,其实正直如坦途,然安有一毫私曲?然人有许多偏私,有许多邪念,千机万械,纷纷扰扰者,何故?只缘是不敬。”[10]因此要想持守正直之心性必须兢业而不能有丝毫放逸。袁燮在自家西塾之丛竹间建一亭,并名之曰“直清亭”。对此他解释道:“直,天德也。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有不直。回曲缭绕,不胜其多端者,非本然也。率性而行,不劳巧智,可不谓直乎?表里昭融,洞彻无间,可不谓清乎?直则清,清则不累其初矣。”[2]130袁燮之文艺思想中也十分推崇主体之正直心性,其《题魏丞相诗》曰:“丞相寿春魏公,以诗名闻天下。清雄赡逸,而归于义理之正,其发有源,故流不竭。”并认为:“正直如是,诗律之严可推而知也。”[2]97袁燮论文艺特别强调源,而这个源只能是本心。义理之正乃源于本心之正,诗律之严亦根源于本心正直。论诗如此,论书法亦然,其《跋杜正献公帖》云[2]100:
“位乎百僚之上,当天下之重任者,孰为先务?秉公心,行正道而已。杜公居相位日浅,功业亦不多见,然至今天下推为正人。观其遗墨犹使人敛起敬,况亲炙之者乎?
呜呼!正人之可为贵也如此。”
杜衍清介正直,且在位时多引荐贤士而不与小人为伍,因此深得世人敬重。他不仅工诗,且《宋史》称其正书、行草皆有法。欧阳修云:“书无俗韵精而劲,笔有神锋老更奇。”[11]122苏轼赞其草书曰:“正献公晚乃学草书,遂为一代之绝。清闲妙丽,得晋人风气。”[11]122而袁燮在此却并不为正献公之书艺所动,而是对其正直清介之心性进行阐扬,并认为其书使人观之起敬亦源于其为“正人”。心学家论艺与文艺家其不同有如此者。
总之,袁燮是在其心学思想基础上构建其文艺观的。在文艺审美旨趣上他推崇浑然天成之美,并认为无论是天成浑然还是人工浑然,均应出于本心之所发。“有契于心”是他文艺思想的核心理念,基于此他提出了书以传心及画以写心等艺术命题。而且有契于心不仅是一个创作思想,也是袁燮的鉴赏理念,他认为观者之于书画重点在体验作者之心,从而使自己之本心有所感发。如此,则创作主体之心性修养超越其技法被提到至高地位,成为书画宝藏价值的决定因素。
[1] 黄宗羲, 全祖望. 宋元学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 袁燮. 絜斋集[C] // 纪昀, 永瑢. 四库全书: 第1157册. 文渊阁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3] 刘道醇. 圣朝名画评[C] // 卢辅圣. 中国书画全书: 第1册.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 454.
[4] 黄休复. 益州名画录[C] // 卢辅圣. 中国书画全书: 第1册.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 188.
[5]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377.
[6] 包恢. 敝帚稿略[C] // 纪昀, 永瑢. 四库全书: 第1178册. 文渊阁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760.
[7] 陆九渊. 陆九渊集[M]. 钟哲,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8] 汤垕. 古今画鉴[C] // 卢辅圣. 中国书画全书: 第2册.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 895.
[9] 袁甫. 蒙斋集[C] // 纪昀, 永瑢. 四库全书: 第1175册. 文渊阁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0] 袁燮. 絜斋家塾书钞[C] // 纪昀, 永瑢. 四库全书: 第1157册. 文渊阁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654.
[11] 马宗霍. 书林藻鉴[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Corresponding with Heart: the Spiritual Core of Yuan Xie’s Literatural and Artical Thoughts
YANG Wanli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China 030006)
Yuan Xie’s view on literature and art originated in his mind studies. On the Literature aesthetic, he admired the beauty like nature itself. To achieve such a state, Yuan Xie put forward the creative ideas of“corresponding with heart”, and extends the art proposition such as calligraphy can communicate heart and paint should write the heart. And “corresponding with heart” is also his appreciation of ideas, he thought that the viewer should focus on understanding the writer’s heart of hi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so that the viewer can be deeply moved. Therefore, h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writer’s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thought of this as the ideological root-cause of “corresponding with heart”, and also a determining factor of the value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Yuan Xie; Mind; View on Literature and Art;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rresponding with Heart”
I022; I206.2
A
1674-3555(2014)05-0055-07
10.3875/j.issn.1674-3555.2014.05.009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13-10-24
杨万里(1985-),男,河北沧州人,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与文论,中国文学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