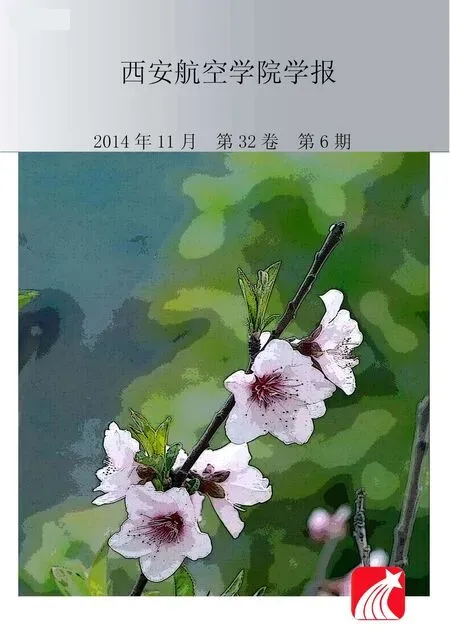“中庸之道”:德性与知性的平衡
许宁宁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中庸之道”:德性与知性的平衡
许宁宁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中庸”是儒家伦理的重要范畴之一。孔子认为“中庸”是最好的德,并把它提高到“至德”的高度,特别是在人身道德修养方面,孔子遵循“中庸之道”的修养方法,提倡对人进行德性与知性的双重培养,在仁与礼,德与智等多方面平衡发展,不偏不倚,行中正之道。
中庸;孔子;知性;德性
“中庸”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哲学范畴,它的本义应为“中道”,日用常行之道,是须臾不可离的行为准则,也是儒家道德修养论里面的重要方法,因而备受孔子推崇。孔子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他认为“中庸”是最好的德,且属于君子所当有之德。并且,孔子把它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评价准则,“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2]孔子一生坚守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生信条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君子之德,行中庸之道。在《论语·学而》首章中孔子便指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中庸之道贯串于日用常行之中,不偏不倚,不愠不戾,以君子之心爱人,将心比心,顺应天赋之性,行中正之道,由内而外,由德性的迸发转而促进知性的提高,完善君子的品格。也只有在中庸视域下完成对自身德性与知性的和谐统一,行“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结合的修养方法。
一、中庸之道——德性修养论
“中庸”思想并非孔子首创,我们可以在他之前的古代典籍,如《尚书》、《周易》、《周礼》等文献中发现有不少关于对“中庸”思想的论述。孔子吸收先贤对“中庸”的诠释并加以创新,赞美了中庸之德的崇高,并赋予了它在德性修养方面的意涵。我们可以进一步从《礼记·中庸》篇展开来讨论。《中庸》首章开篇即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2]主要是讲人的本性是上天所赋予的,能够遵从上天所赐的人之本性(即善行)行事就是符合道义,能够遵循人的道德修养原则来修养身心就是“教”。《中庸》承认人之本性来源于天,是天赋之性,这与出于思孟学派之手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性自命出,命自天降”[3]的思想相切合,它旨在强调把人的道德本源归之于自然的天道或天命的“天赋之性”,而且同时强调了后天通过“修身”而达到道德境界的重要性。《中庸》主张通过“修身”来进行道德修养的提升,既然每个人的本性即善性都是相同的,但是道德修养的程度与境界是不同的,主要区别在于后天的刻苦修习与提升,并且强调无论先天的资质如何,后天的学习和修行都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也只有通过修习才能达到最高的“至德”境界。
所以在后天德性修为中掌握正确的修身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庸》强调修身必须遵循修养之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2]此道者,之所以称之为道,是因为它是片刻不能离开己身的,如果可以离开己身这一实践载体,也就不能称其为道。朱熹解释此“道”为“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2]他认为“道”当为社会中一般之规律,此“道”常贯穿于人们的“日用事物之间”,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道,体悟道的存在,从日常生活做起,保持一颗平常心。平常心即是人之本心,人之本心即上天所赋予的善心,即恻隐之心,即爱人之心,即是孔子所重视的“仁心”。
此外,《中庸》认为修身的最高境界是达到“慎独”。其言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独慎其独也。”[2]这里以君子作为参照来强调,一个人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是很容易做出违背正道的事情的,君子如此,普通人更是如此。此处着重强调,越是在隐蔽的地方,越能够遵循人生正道来行事,就能更清晰的体现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状况,也只有在细微之处才能展现一个人的道德境界之高低。可见,“慎独”既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也是一种道德境界。孔子言“见不贤而内自省也”[1],“慎独”亦体现出了一种“内省”的道德修养方法。君子独处,必先“诚意正心”,明其诚义,正其诚心,做到不自欺欺人,不违心违仁而处事为人。可见,修身的根本是要做到“诚”。这与孟子所说“反求诸己”、“求放心”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是一种强调内自省的道德修养方法。《中庸》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2]“至诚”的境界,乃是“圣人”的境界,尽其本性使然,进而推己及人,推己及物,发挥世间万物的一切之本性,可以帮助天地赞化万物,达到与天地参的“至圣”境界。
可见,“中庸思想”不仅是一项重要的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更是其关于“修身”、“慎独”、“诚”等的德性修养论,指明了我们道德修养的方法与目标,更有助于我们以后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更高的生活价值追求。
二、“中庸之道”——知性修养论
《中庸》言:“君子…道问学…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2]“道问学”是以问学为道,通过后天的学习,不断地修正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提升自身的智慧和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把学习当作提高个人修养以成为君子之人的根本途径。“温故而知新”是孔子主张的学习方法,时时温习旧知识并从中开悟新知,此乃人之心智的开悟,其心有新知新悟自然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于是孔子在《论语》开篇就指出学习是一件“不亦说乎”[1]之事。孔子自身也是十分虚心好学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1],“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1],并且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1]作为自己终生的行身立命之根。孔子对知的崇上达到了一种痴迷的态度,“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学如不及,犹恐失之。”[1]也正是凭借着他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开悟新知,从而使得今天的孔子思想可以历久弥新,依旧活跃在当下的百姓日用之间。
孔子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古代的学者学习都是为了修养自己的品德,修习自身的善行。而今之学者主要是为人而学,孔子提倡“为己之学”,视为“为人之学”的基础和前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己未立如何立人,己未达更不可达于他人。所以,孔子主张修己在前,利人在后,只有自己不断的学习知识,提升自己的智慧与悟性,达致“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2]的师者境界,才可学而为人,学而达人。
《中庸》之为学亦孔子之为学,不学则心志不明,心志不明则是非善恶不分,则义利亦不分。所以,加强个人“知性”的培养,对提升自己的学识,开悟自身的智慧,明辨义利之分,在功利与超功利价值面前有所取舍,明辨二者的优良之分是至关重要的。
三、“中庸之道”——德性与知性的平衡
孔子认为“中庸”之德为百姓日常所用之德,其源于他们生活中的平常心,融入到普普通通的生活之中,须臾不离其身,主宰着人们能否对是非、善恶、美丑、义利、得失等伦理范畴做出正确判断与选择,此处着重分析“中庸”之道在维持德性与知性的平衡,帮助人们在确立人生价值追求上所起的有益的导向作用。
首先,孔子认为“中庸”之道是界定君子与小人之道。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2]孔子之所以以“中庸”思想来区分君子与小人,是因为君子在面对价值选择时能够依“中庸”之道而行事,做到“时中”。孔子认为,为君子者,当时时不失于中行,以“中道”存心,为人行事符合道义的原则,不偏不倚,即有遵从内心德性的约束而不妄为,又兼顾外在理性的欲求而有所取舍,从而避免了自身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中庸”之道并不是折衷,而是介于自身德性与知性之间的平衡而用中。中是恰如其分,在本末之间取其中,亦或做到本末兼顾。人生在世,需要以“食”为基础,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所以自身知性的引导下,通过正当的、合乎道义的方法获利,是无可厚非的。同时,为了更合理的控制自己对功名利禄的过度欲求,塑造完美的人格,提升人生境界,以满足内心的精神需求,这就更需要在自身德性的约束之下完成。这样既避免了因自身知性的不足而陷入无法自给的困境,又可以避免因过分的欲求而沦为失德妄行的禽兽。
其次,“中庸之道”是修身之道,亦是教人之道,培养君子之道。教人亲君子远小人,亲近对道德正义的向往,远离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中庸》言“修道之谓教”[2],即遵循道德修养原则来修养身心就是“教”。“中庸之道”教人行事当以“君子”的标准作为自己处事的准则。君子为人行事都是符合“道义”,遵从本心而动,时刻不偏离中道而行,谨小慎微,无过无不及,注重自身德性与知性的平衡,在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的同时充实内心的精神生活,进而体悟到人生的真正幸福和快乐。相应的,对于德性与知性失衡的小人而言,他们往往会心怀私心,求利心切,偏离中道而行,进而迷失自我,最终陷入价值迷茫的深渊。“中庸之道”在道义与利益的价值导向中更偏重于道义,更加注重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完满,树立更加高尚的人生欲求,通过不间断的学习来保障知性提升的同时,更多的是通过自身的道德实践过程来增加德性的修为,培养自身君子的品格。
孔子遵循“中庸之道”的修养方法,对人进行德性与知性的双重培养,《中庸》言:“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2]君子之修身在注重对道德的崇敬与修习的同时,又注重对学问的追求。“尊德性”即存心尽性,明其明德;“道问学”即致知穷理,切问近思。二者兼顾则是“修德凝道之大端”[2],为君子修身之法,如果仅强调“尊德性”,难免会像道家一样,有名而无实,心存大道而无所用行;如果仅强调“道问学”,也难免会出入皆曰功利,注重外王之学,而轻视内圣之术,急功近利,误国害民。所以,孔子主张遵循“中庸之道”,行“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结合的君子修身之法,加强知性和德性的双重培养,即养成心中“极高明”的道德境界,也具有为人处事“道中庸”的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二者的结合即达到了孔子所言的“至德”[1]境界。
总之,中庸之道对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追求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决定着人们在面对功利与超功利两种不同的价值观选择时,可以从德性与知性两个方面进行权衡,即要肯定一定的功利追求,保障自己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更多的则是对“超功利”的肯定与追求,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培养自己的君子之德,树立乐观向上、超越功利的人生价值追求。
[1] 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10:1,123,163,167,182,214.[2] 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25,27,50,51.
[3] 赵伟建.郭店竹简《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校释[J].中国哲学史,1999,(2):34-39.
[责任编辑、校对:王国成]
"Golden Mean":Balance of Morality and Intellectuality
XU Ning-ning
(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Golden Mean"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Confucian ethics. Confucius considerde "golden mean"the best virtue. In moral cultivation, he followed the way of "golden mean" particularly so as to cultivate both morality and intellectuality, thus achiev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benevolence and rite, virtue and wit.
golden mean; Confucius; intellectuality; morality
2014-08-10
许宁宁(1988-),男,山东东营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儒学史研究。
B222
A
1008-9233(2014)06-0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