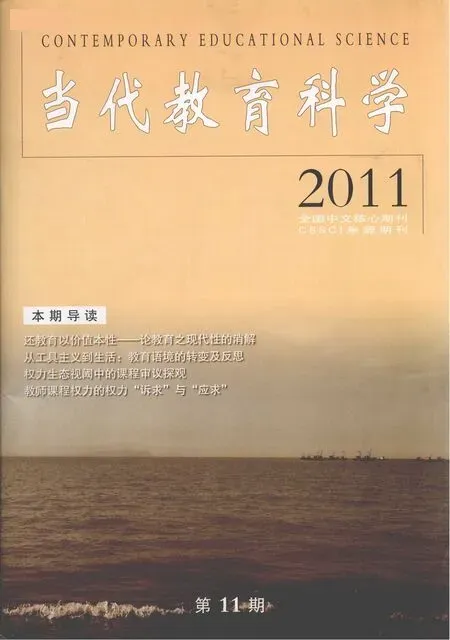大学管理模式的历史嬗变*
● 韩锦标
大学管理模式的历史嬗变*
● 韩锦标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以来,其管理模式大致经历了行会式管理、科层制管理和知识管理的历史嬗变。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管理模式的新范式,实现了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共轭。三种模式之间,后者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和抛弃,而是继承和扬弃;后者既有对原有管理模式的局限性的突破,又有对原有管理模式的合理性的传承。
管理模式;行会式管理;科层制管理;知识管理
管理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管理理念指导下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的统一体,是一种成型的、能供人们参考运用的管理体系。大学管理模式是对大学的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的高度概括,是大学管理理论化的结果。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以来,随着大学功能的变化以及社会对大学诉求的增多,大学管理模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
一、行会式管理模式:大学学术管理的滥觞
高等学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 “学园”甚至更早。在我国,则一般认为起源于西汉的“大学”或“稷下学宫”。但严格说来,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与大教堂和议会一样,都是中世纪的产物”[1],中世纪“大学的发展,与帝国、教会、教皇制、较旧式的学校和其他许多中世纪时代的制度之发展,无不密切相关。这些大学,是由旧式的大礼拜堂和道院各种学校发生出来的”。[2]“大学”(Universitas)一词的原意就是由教师或学生组成的行会团体。
中世纪大学主要是传承知识、培养人才,并且独立于社会之外,具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其主要的管理活动是学术管理,主要的管理模式是行会式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学生主导型管理,一种是教师主导型管理。前者以意大利的波隆那大学为代表,学生成立“学生协会”管理学校的日常活动,从教师的选聘、学费的数额,到课程的设置、学时的安排等,都由“学生协会”决定。后者以法国的巴黎大学为代表,“巴黎大学最初是学者们在巴黎圣母院教堂附属天主教学校讨论哲学和神学问题逐渐发展形成的教师行会”,[3]教师是学校的负责人,管理着学校的各项事务,如开设课程、管理学生、组织考试、颁发学位等。中世纪大学是仿照手工艺人行会的方式组成的教师或学生的团体(或协会),其管理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拥有较大的办学自治权。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不受政府、教会或其他势力干预,实行独立办学,它是大学的师生在与教皇、国王或城市当局长期争斗的过程中获得的一项特权。“大学是如何在这些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呢?首先靠它们的团结和坚定;同时它们威胁要采用并真的采用了罢课和分离出去的危险武器。”[4]“最初大学的特权主要是罢课权和迁徙权,以后特权的范围逐渐扩大,包括免除兵役、免税等。其中最重要的特权是‘内部自治’”,“就总体而言,在行政、学术、经济、法律诸方面中世纪大学均享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5]
第二,推行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指大学教师所具有的管理学术事务的权力。“学术自由思想的提出以及永久保护它的需要,可能是中世纪大学史上最宝贵的特征之一。”[6]公元1158年,罗马皇帝腓特烈一世颁布了一项保证学者安全活动的法令,规定学者在国内受到保护,如遭到任何不合法的伤害将予以补偿。该法令被看作是保证学者的学术活动不受干涉的最早步骤。公元1219年,教皇颁布敕令,规定未经许可,巴黎主教不得开除任何教师的教籍或学生的学籍。
第三,实行民主化管理。与中世纪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不同,中世纪大学组织结构比较简单,人员的组成成份也比较单纯,教师(或学生)往往兼大学校长和管理人员。大学里没有特权阶层,每个成员都有选举权,可以参加校长的选举,也可以决定学校的事务。校长职权很简单,就是保护师生的利益,负责对内协调管理,对外联络交涉。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向往的大学进行学习,随意在各地大学间游学,并不受学校的限制。
从总体上说,中世纪大学是学者民主自治的学术团体,学术管理是中世纪大学主要的管理活动,专门化的行政管理活动还没有出现。同时,中世纪大学作为一种简单松散的行会组织,倡导“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但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这种管理模式在导致大学内部交易成本过高的同时,也阻碍了社会对大学的有效干预与制衡。
二、科层制管理模式:大学行政管理的范型
“科层制”(Bureaucracy)也称为官僚制,它的历史源远流长,无论在古埃及、欧洲还是中国,科层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成为维持文明秩序的重要保证。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科层制组织的研究开创了现代组织理论的一个新领域,也为科层制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在韦伯看来,科层式管理体制是一种严密的、合理的社会组织,它具有熟练的专业活动,明确的权责划分,严格执行的规章制度,以及金字塔式的等级服从关系等特征。[7]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效率与合理化。这是科层制的核心思想,也是必然要求。其中,效率是科层制组织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合理化指的是组织内的一切行为都应该合乎理性,并在合乎理性的基础上服务于组织的目标。二是分工与专门化。这一特征是指“科层管理结构为达成其目的,以特定方式分配其职务的各种规则性活动”。[8]劳动的明确分工有可能为每一个特定的岗位雇用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并使每一个人有效地履行各自的职责。三是稳定的规章条例。规章条例是科层制的管理基础,它规定了组织中每一个成员的责任及其相互关系,保证了科层组织活动的常规性、稳定性以及连续性。四是权威等级制。存在着职务等级原则,“所有岗位的组织遵循等级制度原则,每个职员都受到高一级的职员的控制和监督”。[9]五是非人格化管理。组织内部各种行为都按统一的规定办理,不因人而异,不夹杂个人的情绪或偏见。在法规面前所有个体一视同仁,任何决定均应避开情感冲动或个人好恶,以有效达成组织目标为准绳。
应该说,韦伯的科层制组织不是日常意义上的文牍主义、墨守成规、效率低下的组织现象,而是一种理想类型的组织结构形态和行为模式。因此,这种组织模式由经济领域迅速普及到政治、文化、艺术、教育等社会各个领域,成为现代社会组织共用的一种管理范型。正如彼得·布劳和马歇尔·梅耶在《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中所言:“在当今社会,科层制已成为主导性的组织制度,并在事实上成了现代性的缩影。除非我们理解这种制度形式,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今天的社会生活。 ”[10]
科层制在大学的应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大学的理念和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相继成为大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能。同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基本力量的重压之下,高等教育已经由小规模的、选拔性的、关系松散的集团,发展成为具有重大社会经济意义的庞大系统”[11],大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逐渐从社会的边缘成为社会的中心。大学内部有组织的管理活动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化,单一的行会式管理已经无法适应大学的管理需要,大学必须依靠庞大行政组织体系的支撑才能维持自身的运转。大学的管理活动由起初的专门性学术管理变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互为牵制的耦合式管理,而适应大工业社会需要的科层制模式在大学管理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然而,科层制的理论出发点是合理的个人行为,没有更多地考虑严格等级和规章制度控制下的个人情感体系、制度遵从程度等方面的问题,这也体现了科层制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的弊端。特别是对大学而言,由于其二元权力结构的特殊性,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矛盾和冲突。
首先,科层理性与学术非理性的冲突。科层制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现代性的一种表征,适应了现代社会对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需求。但是,“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鼓励的是服从,削弱了团体的因素;培养的是有组织的人,而抹杀了人的感情因素,其组织体系很难使组织中个人的需要与组织自身的需要相协调”[12],“这种官僚制的理性模式无视了一个事实,即人并不总是以理性的方式行事或在理性的结构体制下表现的效率最高”。[13]而大学的学术活动是一种精神性的创造活动,非理性因素起着关键作用。随着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膨胀和工具理性的至上,必然使人的精神活动和创造力受到越来越多的禁锢。
其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冲突。现代大学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混合体,行政权力根植于组织以及特定职位的权力,作为一种外在的结构形式维系着大学的存在,其合法性来源于制度化的管理权力;而学术权力根植于高深知识,作为一种内生力量推动大学的发展,其合理性来源于专业和学术能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由于在性质和目标上的差异而存在明显的冲突。学术自治要求大学在处理学术事务上,不受政府和行政权力的干涉;而科层体制的行政权力则要求大学把一切活动都纳入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按行政组织的规章行事,以提高效率。于是,强调约束、效率的行政规范和注重自由、平等的学术价值产生了明显的冲突。
再次,权威等级结构与学术组织扁平化的冲突。在大学科层组织中,全部职位分成校长、副校长、处长、科长等若干等级,每一级职位赋予其承担者对下属进行合法控制的权力,管理人员与教职员工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建立在职位关系之上。这些特点构成了学校内部完备的权威等级系统。但对学术组织而言,追求的最高宗旨是学术自由,反对外部制约,排斥等级制度。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伊兹欧尼所言,“知识主要是一种个人财产,它不能依靠政令的形式进行迁移。创造性基本上是个体的,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围内被上级所协调和控制,给予专业人员的自治是保证有效专业工作所必需的。”[14]这就要求大学学术组织必须是扁平化和柔性化的: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和信息的基点,发挥教师个体在学术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使组织能力变得更加柔性化,以增强其在不确定环境下的适应性。而大学以权力为中心的“金字塔”式结构,显然对学术组织的发展构成了障碍。
总之,科层制模式作为大学行政管理的范型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只要大学存在,就必然存在行政管理活动,就必然需要健全的规章制度和明确的职责分工来保障管理工作的效率。但大学组织“科层化”的膨胀也对大学的学术活动造成了诸多钳制。特别是当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知识的价值日益凸显,知识共享和创新能力成为一个组织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源泉。而大学长期“科层化”倾向却日益成为知识共享和创新的障碍。
三、知识管理模式:大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共轭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管理作为一种新兴的管理思想与方法,已受到人们高度关注,它不仅是一种商业模式,而且是实现企业、大学、政府乃至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知识管理,就是以知识为核心的管理或运用知识进行管理。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它既是一种管理理念和管理策略,又是一种可操作的管理方法。就大学知识管理而言,是指把知识和知识活动作为大学最重要的资源,通过对大学内外知识的识别、获取、传播、扩散、创造,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流通共享,有效发挥师生员工的知识潜能以提高其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个体以及学校整体的知识学习、知识积聚、知识创新的能力,创造有利于知识共享的体制、机制与途径,增强知识服务的功能,从而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其实,大学从其产生之时起,便成为人类知识传播与创造的理想之地,并且具有了“知识管理”的某些特性,如知识的收集、保存、传播和创造等。时至今日,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来临使大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其中之一便是不断增加的市场压力和竞争压力,这要求大学充分发挥自身在知识创新方面的优势,加强学习型组织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而与此同时,大学组织“科层化”的弊端,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知识创新的活力。基于此种情况,大学借鉴当代知识管理理论,完善自身知识管理模式与体系,成为其内在的逻辑需要和历史必然。
在此,有必要分析一下大学知识管理与行政管理、学术管理的关系。
第一,大学知识管理与行政管理。大学行政管理是指对大学行政事务与活动的管理,目的主要是为了充分整合校内外各种办学资源,协调校内各方面力量,提高办学效益。其内涵主要有:[15]其一,行政管理主要是贯彻上级的工作意图和分派的任务,各行政部门之间及其内部有较为明确的分工,行政人员的职位按等级排列;其二,行政管理要求管理工作立足于整个学校,采取集中和划一的方式,用具有管理功能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对学校各个层次、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和各种力量加以组织、协调;其三,按照下级服从上级、首长负责制等原则处理各种管理事务;其四,在具体的常规管理活动中,遵守各种管理规章制度。相比较而言,知识管理弱化了行政管理的官僚式的等级制度,强调以人为本、发挥知识工作者的个体积极性而不是靠行政命令分配工作。当然,由于大学自身就是知识的集合体,因此行政管理也可以看作是知识管理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在组织设计、制度创新、知识协调等方面都可以按照知识管理的模式和要求进行改革,以提高管理效率。
第二,大学知识管理与学术管理。大学学术管理是指对大学学术事务和活动的管理,目的在于推动大学的学科发展,提高学术水平。与学术管理相对的是非学术管理,指对支持、规范和制约大学的总务、后勤等各种非学术事务的管理。学术管理可以采用多种管理方式,包括行政管理方式和各种非行政管理方式,解决的基本矛盾是自主与控制、民主与集中的矛盾[16],亦即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矛盾。相比较而言,大学知识管理主要是解决知识共享、知识创新与知识封闭、知识封锁的矛盾,提高大学知识活动的效率。知识管理贯穿大学全部活动中,包括学术管理和非学术管理。因为大学主要是一个学术组织,不管是教学、科研还是社会服务都与学术有关,学术水平是衡量大学水平的重要指标。所以,知识管理的重要任务就是加强知识的交流和共享,推进知识创新,提高学术水平。
大学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是一对矛盾,问题的症结在于谁对大学事务更有发言权,也就是说大学事务是行政权力说了算,还是学术权力说了算。从大学发展史来看,中世纪大学更侧重于学术管理,学术自治至上。近现代以来,随着大学功能以及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大学行政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大学形成二元化的权力结构,而且行政权力一度压制学术权力。然而就大学自身实际而言,二者都有必要性。正如布鲁贝克所言:“既然高深学问需要超出一般的、复杂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那么,自然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因而在知识问题上,应该让专家单独解决这一领域的问题。……教师就应该广泛控制学术活动”;同时,“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17]就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而言,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又各有其局限,比如学术权力往往带有散漫性和保守性,而行政权力则容易走向集权化和官僚化。知识管理应该说既整合了二者的作用,又化解了二者的矛盾,它强调学术知识的交流和共享,注重发挥知识工作者(主要是教师)的作用,提高知识的利用效率;同时又注重发挥知识组织、知识领导和制度创新的作用,使大学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提高管理效率和办学效益。可以说,知识管理实现了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共轭,因此,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管理模式变革的必然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行会式管理、科层制管理还是大学知识管理模式,都是大学理念不断发展、现代大学制度不断衍生的产物,它们既适应了大学功能变化的内在需要,也契合了时代发展对大学的外在需求。三种模式之间,后者不是对前者的抛弃和否定,而是继承和扬弃;后者既有对原有管理模式的局限性的突破,又有对原有管理模式的合理性的传承。在当今时代,行会式管理模式延续下来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始终是现代大学孜孜以求的目标,而大学的发展也离不开效率、分工、制度、服从等科层制模式的核心原则。所以,尽管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管理模式的新范式,但不是对行会式管理,特别是科层制管理模式的完全颠覆,而是一种融合和创新。
[1][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M].梅义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1.
[2][美]格莱夫斯.中世教育史[M].吴康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5.
[3]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72.
[4][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3.
[5]薛天祥.高等教育管理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0-31.
[6]Alan B.Cobban.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 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M].Methuen&Co Ltd,1975:235.
[7]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218-219.
[8]H.H.Gerth,C.Wright.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9]Max Weber.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
[10][美]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M].马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8.
[11][加]约翰·范德格拉夫等.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61.
[12]黄志成,程晋宽.教育管理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32.
[13][美]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M].项龙,刘俊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78.
[14]Etzioni.Modern Organizations[M].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64:75.
[15]孟丽.试论大学中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协调[J].辽宁教育研究,2003,(2):26-27.
[16]别敦荣.中美大学学术管理[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7.
[17][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31,32.
*本文系淮阴工学院高教研究重点立项课题 “基于知识管理的高校核心竞争力提升研究”(GK200803)阶段性成果。
韩锦标/淮阴工学院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副主任,副教授,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刘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