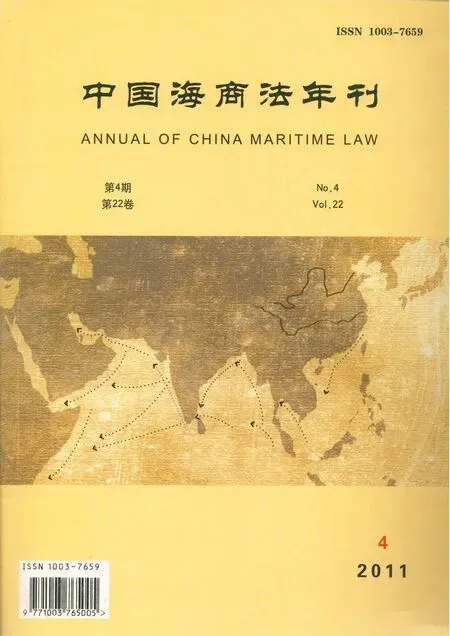船东可反驳的推定责任:《鹿特丹规则》承运人识别推定制度之考察——兼论中国海商法承运人识别制度的发展*
王秋雯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4)
一、引言:《鹿特丹规制》所创设的承运人识别推定制度及其问题
承运人识别(carrier-identifying)历来是海商法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题目,该问题不仅决定了货物毁损灭失时的索赔对象,且鉴于各国海商立法无不规定对承运人的索赔时效,告错对象很可能导致因错过时效而对真正的被告束手无策。但对于承运人识别问题,时至今日,国内国外海商界却尚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学者们进行了无数次尝试寻找承运人识别的通则性方法,如Thomas J.Schoenbaum在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一书中提及的美国最高法院在识别承运人时所确立的13项标准,John F Wilson在Carriage of Goods by Sea一书中更是通过英国判例推导出复杂的原则。[1]686,[2-5]但是,如果将上述学说应用到新近发生的案例中就会发现,个案的判决结论并不总是与“通则”一致,判例结论之得出仍主要依据具体案件情况,或许在这方面希冀于建立一种通行国际的识别标准未必是一种万无一失的尝试。
考虑到海上船货两方力量对比的非均势,联合国于2008年12月通过的《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又称《鹿特丹规则》)体现出强烈的货方保护倾向,将承运人无法识别时的责任施以注册船东,推定其为承运人,同时允许船东通过证明船舶业已光租或指明真正的承运人以推翻推定(《鹿特丹规则》第37条第2款)。让“注册船东可反驳的推定责任”成为承运人识别问题上的“兜底条款”,无疑等同于否定了识别通则的可行性,但是,这种“兜底条款”其本身合理与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在解决承运人识别问题上可否借鉴这样的立法技术?本文拟通过索赔人确定承运人可行进路的分析讨论上述问题,并阐释现行《海商法》在解释适用上的疑义及困难,再以此为基础,说明该条款对中国海事海商实践的可能影响。
二、构建承运人识别推定制度两种进路
货物索赔的根本就在于使承运人承担其应有的责任,但承担责任的前提是确定谁是承运人,因此,问题就演变成当运输合同或者运输单证没有写明当事人时,索赔人如何才能确定谁是那个身份不明的承运人。答案很明显,就是找到那个可能知道谁是承运人的人。《鹿特丹规则》采用责任转嫁的立法思路,在无法识别承运人时首先推定承运人责任于那些可能找到承运人的人,然后由这些人举证证明自己不是承运人(如证明船舶已经被光租)或者找到真正的承运人以免除责任。总体来说,路径有以下两种。
(一)进路之一:推定托运人为承运人
国际海运实务界与学界持该观点的有中国的朱曾杰教授,荷兰的Gertjan van der Ziel教授,英国的Paul Koronka先生等。
托运人一般被界定为与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人,至少通过一系列链条他可以找到承运人。因此,有观点认为,若必须有一个人承担承运人无法识别时的责任,此人也应是托运人,而非注册船东,因为托运人在与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时存在过失接受了未载明承运人名称和地址的提单而导致最终承运人无法识别,承运人无法识别问题的源头在于托运人的不审慎。[6]有学者曾特别指出:“索赔人应当从托运人而不是注册船东入手(寻找承运人),证明谁是真正承运人的责任应当施加于托运人一方,因为运输合同是经其处理的。”[7]
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解决方法存在如下问题:其一,要托运人在船东与承租人复杂的关系中找到承运人是困难的。可以假设这样的情况:货代分别向多个货主揽货,当货物足以拼装为一个集装箱时再去租船运输,货代向货主签发以自己为承运人、货主为托运人的货代提单,实际承运人向货代签发船东提单,最后当货物抵达目的港时由货主向货代在目的港的代理人换发提货单提货。在上述情形中,如果仅从提单表面的记载加以考察,对于最终受让提单的索赔人来说,原始货主是托运人,但原始货主就能够指明谁是承运人吗?承运人应当是货代,还是与货代缔结运输合同的人,实际从事运输的光船承租人或船东?显然,指出谁是真正的承运人从而推翻自己为承运人的推定对托运人来说是困难的,这种困难或许在某些时候并不亚于索赔人自己寻找承运人所面临的困难。若不能找出真正的承运人,就要被推定为承运人而承担赔偿责任,对托运人而言未免过于苛刻,毕竟托运人不是实力雄厚的船东或者船公司,他亦仅是海上运输的非核心主体货方。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货主看到的货代提单关于承运人的记载可能并无瑕疵,真正有瑕疵的是其背后的那份船东提单,此时如何因托运人“在与承运人签订运输单证时存在过失,本可拒绝接受有瑕疵的运输单证”为由而推定其为承运人?其二,由于海上航程相对漫长,尚在运输途中的货物会被多次转手,最终持有提单的索赔人与原始的缔约托运人之间可能存在多个中间贸易方,一旦其中某个环节提单背书人失踪,则寻找托运人的锁链就会被截断。而且海商法中提单法律关系规制的是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托运人与索赔人之间的关系严格地说应当属于转手贸易方间的贸易关系,应更多地受贸易法调整。其三,根据《海商法》第42条第3项的规定,实际交付货物予承运人的人(一般是FOB卖方)也被定义为托运人,若推定托运人为承运人就会使得因为根本无意牵涉运输而不惜放弃在途货物控制权的FOB卖方反而成为推定的承运人,这不尽合理。
那种认为承运人无法识别问题的源头在于托运人不审慎的观点也值得商榷。所谓的“审慎”并无法定的严格标准,只能通过航运习惯考察。《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习惯标准。分析UCP 600就会发现,它要求多式联运单证、提单、海运单、空运单、公路、铁路和内陆水运单据必须表明承运人(indicate the name of the carrier)①参见UCP 600第19a(i)条、第20 a(i)条、第21a(i)条、第23a(i)条和第24 a(i)条。,但租船合同提单是唯一的例外②UCP 600第22a(i)条。。正因为租船合同提单下承运人的复杂性,UCP 600并未将必须记明承运人作为惯例对待,因此,接受这样提单的托运人也就未必是后来问题的“祸首”。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依靠托运人寻找承运人,并在无法识别时推定托运人承担承运人责任的进路是走不通的,至少在海运立法中走不通。
(二)进路之二:推定注册船东为承运人
国际海运实务界与学界持该观点的有美国的Alcantara先生、意大利的Francesco Berlingieri教授、瑞士的Alexander von Ziegler先生、英国的Beare先生、美国的Michael FSturley教授和法国的Pierre Bonassies教授等。
注册船东与承运人直接或间接地打交道,而且几乎没有船东会在不知谁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同意将货物装上自己的船舶进行运输。注册船东往往可以从使用其船舶从事运输的承运人那里获得某种保证。《鹿特丹规则》就创造了这样一种激励机制,首先推定注册船东为承运人,然后允许注册船东通过提供真正的承运人或者证明在货损发生时船舶处于光船租船状态以推翻该推定,从而使更为容易获得承运人信息的船东指出真正的承运人,且该规定还可以迫使船东更加谨慎地保护船舶以防止货损。因此不能否认,《鹿特丹规则》所构建的注册船东可反驳的推定责任有其合理性。
除合理外,它还符合普通法国家对物诉讼的法律传统。对物诉讼是海事请求人依其海事请求权或海上留置权向特定的海上财产行诉的特殊的民事程序制度,是英美法国家特有的海事诉讼方式。[8]对物诉讼通过船舶拟人化理论的构建,将肇事船舶人格化,当船舶对他人造成损害时,让肇事船舶来承担责任,因此,一旦将货物装上船舶就等于船舶认可了运输合同。在对物诉讼中,船舶被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判决将对船舶作出,败诉的船舶将被拍卖以清偿债务。但事实上,因为船舶是船东的财产,所以,船舶承担责任的本质是船舶所有人承担责任。[9]另外,建立注册船东可反驳的推定责任也有其历史渊源。这种推定本质上类似于光船条款的历史由来。英国商船法(Merchant Shipping Act1894)允许船东或光船承租人在遇到重大事故对财产损失负有责任时申请责任限制,每船舶吨位以8英镑为限,但有权申请责任限制的主体却不包括期租承租人。因此,班轮公司往往在提单中加上此类船东负责条款,事故发生时可以由船东或光船承租人先赔偿受损害的提单持有人,然后再由承租人向船东或者光租人赔偿因此受到的损失。以此种方法,承租人虽不是船东,但事实上可获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纵然历史已经被改写,现在的海商立法几乎都允许承运人享有责任限制的权利,但这种历史进路上的分析无疑有助于理解将船东推定为承运人的精神传承。
三、推定注册船东为承运人的识别推定制度:对于质疑的再思考
建立注册船东可反驳的推定责任,将本属于承运人的责任通过立法技术转嫁到船东身上,首先受到质疑的就是其加重船方责任的公平性。注册船东可能既不是与托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人,也不是实际从事运输的人,可能与受损货物根本没有干系,且其亦无法控制其他区段以及其他人的运输行为,让他承担责任似乎有失公允。在航运业者看来,若仅因注册船东拥有船舶就成为被索赔的对象,则对于整个航运业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打击。因此,国际海运局(ICS)、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和保赔协会国际集团(International Group of P&I Clubs)在其两次建议稿中都强烈提议将该条款删除。他们指出:“在注册船东是船舶经营人以外的独立实体情况下,注册船东几乎对船舶的经营没有任何实际影响,而且事实上,注册船东通常是一个金融机构。”③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UNC ITRAL),A/CN.9/WG.III/W P.87-Transport Law:Preparation of a draft convention on the carriage of goods[wholly or partly][by sea]-Com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Shipping(ICS),B IMCO and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of P&IClubs;A/CN.9/WG.III/W P.73-Transport Law:Preparation of a draft convention on the carriage of goods[wholly or partly][by sea]-Comments and proposals by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Shipping,B IMCO and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of P&I Clubs on topics on the agenda for the 18th session.比如,银行为了获得船舶融资还款担保而将船舶登记于其名下。
其他质疑则主要来自于立法技术处理上的一些细节问题。因为《鹿特丹规则》第37条第2款采用的字样是:“货物已经装上指定船舶”(named vessel),假设提单中指定的船东是甲,但事实上货物装在乙的船舶运输,如果以“指定船舶”来确定责任,最终可反驳的推定责任事实上由甲来承担。若提单并未指明船舶名称,则无法确定注册船东,仍然不能彻底解决承运人无法认定时的责任归属问题①Agenda Paper for the Transport Law Sub-Comm ittee’s third meeting(July 2000),A rt 4.1(d)comment.。从整个《鹿特丹规则》来看,因其调整范围是“门至门”运输,若试图让船东承担整个多式联运中的责任,则责任将无法预期,他不仅要为海运段负责任,亦可能因为陆运段的货损而被诉诸承运人地位并须对全程负责。例如,美国代表团在UNCITRAL第三工作组于2006年4月3日至13日在纽约召开的第十七届会议上提交的参考文件就质疑:“货物装上多式联运交易中海运段船舶加以运输,却缘何创设对内陆运输段承运人身份的任何推定?”②U nited Nations Comm 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UNC ITRAL),A/CN.9/W G.III/WP.62-Transport Law:Preparation of a draft convention on the carriage of goods[wholly or partly][by sea]-Transport documents and electronic transport records:Document presented for information by the de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统观上述反对之观点,无非来自公平性和立法细节两大方面。鉴于《鹿特丹规则》仅是一种开创性尝试,并未形成甚具代表性之立法例,于此处探讨其立法技术完善与否意义甚微,故笔者仅针对公平性作以分析。对于注册船东可反驳的推定责任公平性最强烈的批判来自于国际航运局、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和保赔协会国际集团。作为承运人利益的代言人,上述机构的质疑势必有其立场。若并非站在一个完全中立的视角看待此问题,恐怕那些公平地施于承运人之责任亦会被反对。其次,海运法并非简单地采用商业合同与消费者合同的划分标准,虽承托双方均是商主体,但承运人却非普通商人,其几乎拥有海上的绝对话语权,在19世纪初一度滥用合同自由以致免责无边。因此,海运法中很多立法设计都旨在限制承运人,限制承运人的立法精神绝对不会因为加上了可反驳的推定责任而瞬间从公平转向不公平。再者,可反驳的推定责任不等于过错推定责任,过错推定责任中需要证明没有过错才可免责,但可反驳的推定责任只要证明船舶被光租或者指明承运人即可。该种反驳事由的证明非常简单,并未在举证责任上施以船东苛刻条件,意图就在于迫使船东帮助索赔人找到真正的起诉对象,因此也就谈不上不公平。可反驳的推定责任亦可被视为是与海上留置权对应的义务,同时船东亦可以港口超过租船合同范围、货物根本没有装上船等为由抗辩。
四、对于承运人识别制度的比较法考察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皆未建立注册船东可反驳的推定责任以解决承运人无法识别之困境,该可反驳的推定责任可谓是《鹿特丹规则》的独创,故只能收集船东承担货物毁损灭失责任的判例加以分析,采海运发达国家之案例,主要考察船东责任和导向船东责任的举证责任问题。将船东责任与承租人责任进行分析,以考证由船东承担责任是否为历史趋势或判例首选原则。在举证责任问题上,若船东负担证明自己与货物运送无关的举证责任,则类似《鹿特丹规则》中可反驳的推定责任。
(一)美国法下的承运人识别问题之解决
美国1999年《海上货物运输法》(Carriage of Goods by S ea A ct)对于承运人的界定本身比较宽泛,包括缔约承运人与履约承运人,包括船东与各种形式的船舶承租人③参见Section 2(a)(1)(2)(3)。。宽泛定义本身等同于承认了多个承运人存在的可能。比如在the“Hale Container L ine v.Houston Sea Packing”案中,货物通过租船合同运输,因为承认对物诉讼,船舶本身也被视为承运人④参见137 F.3d 1455(11th Cir.1998)。。在美国法下,认定船东为承运人的情况主要出现在航次和定期租船合同当中,如果船东对船舶保有占有和控制,则将被认定为《海上货物运输法》意义下的承运人。在the“Southern Block&Pipe Corp.v.M/V Adonis”案中,船东被认为完全控制船舶,因此应被视为海上货物运输法下的承运人,并承担相应责任⑤参见341 F.Supp.879,1972 AMC 1525。。除了对船舶的占有控制之外,提单是否代表船东签发也是船东是否为承运人的考量因素。即使承租人签发提单,若出现“代表船长”或“代表船东”字样并且承租人事实上被授权签发提单,则船东亦会被视为承运人①参见Pacific Employers Ins.Co.v.M/V Gloria,767 F.2d 229,237-38(5th Cir.1985)。。有时候,虽然船东并不能被视为海上货物运输法下的承运人,但是,船东所有的船舶可能会因为对物诉讼制度而被要求对货损负责。即便提单并不是船长签发或者未经船长授权,一旦将货物装上船舶,则船舶就被视为认可了提单的内容②参见Demsey&Associates,Inc.v.S.S.Sea Star,461 F.2d 1009,1015,1972AMC 1440(2d Cir.1972);Dow Chemical Pacific Ltd.v.Rascator Maritime S.A.,594 F.Supp.1490,1985 AMC 523(S.D.N.Y.1984)。。还有很多法院在其判决中突破海上货物运输法下只能有一个承运人的观念,将所有的船东和承租人都视为承运人。Thomas J.Schoenbaum就肯定了多个承运人存在的观点,指出:“当事方(船东与承租人)之间的关系是不甚清楚的,但无疑在签发提单时任何一方都未与托运人商议过该问题。那种认为涉及运输的任何当事方都将被视为海上货物运输法下的承运人的观点可以根除承运人识别问题上的争论,所有当事方都将被起诉到法院,由法院来进行最终的责任判断。”[1]688
综合上述美国的判例法制度,在美国法下,注册船东承担承运人责任主要存在于四种情况之中:一是船东实际占有和控制船舶,二是提单由船东签发或代表船东签发并有事实上之授权,三是因为对物诉讼而负承运人责任,四是被视为共同承运人。船东与承租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证明责任被施加在船东和承租人身上。法院将主要依据他们之间的租船合同来判断谁将被认定为承运人而须负承运人之责任,当然也会根据租船合同的具体情况对两者的责任进行合理分配。比如,如果承租人被认定为承运人对货损赔偿后,法院往往会允许其向船东追偿船舶不适航责任。因为无需证明船东与承租人的关系以判断谁是承运人,这种处理方法无疑有助于货方进行起诉,而且也有助于在船东与承租人之间合理分派承运人责任。
(二)英国法下的承运人识别问题之解决
英国法上,即使存在租船合同,一般情况下仍将船东视为承运人,因为船东应对船舶经营负责且船长是以船东代理人的身份签发提单的。[2]在the“M anchester T rust,L im ited v.Furness,W ithy&Co.,L im ited”案③参见(1895)2Q.B.282。中,虽然租船合同明确约定船长是承租人的代理人,但因提单本身并无该条款,故船东仍要承担承运人责任。即使承租人自己签发提单,若他在提单中指明是代船长或船东签发的,则船东也仍要负承运人之责任④参见Tillmans v.Knutsford(1908)AC 406。。同样,如果承租人的代理人或独立分合同人签发提单但在提单中指明上述内容,结果相同⑤参见The Berkshire(1974)1 Lloyd’s Rep 185;Alimport v.Soubert Shipping Co Ltd(2000)2 Lloyd’s Rep 447;The Vikfrost(1980)1 Lloyd’s Rep.560。。
英国法下,如果承租人以其本人名义订立运输合同并签发提单,或者在提单未指明是代船长或船东签发的,则承租人会被认定为承运人。但此时仍然有两种途径可以使承租人将其所应负担的承运人责任转嫁到船东头上:一是提单背面的“光船租船条款”(demise clause),二是提单背面的“承运人识别条款”(identity-of-carrier clause或definition-ofcarrier clause)。[10]应特别注意的是,前述讨论的美国法之所以不存在这样的转嫁责任问题,是因为美国法院往往以该条款违反公共政策或属于减轻或免除承运人责任而无效之由否定其效力,但英国法对其效力却不作否定。[11]但关于这两个条款,最近在著名的the“Starsin”判例中,英国上议院(House of Lords)推翻了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的判决,认为关键性的事实是提单表面承运人签名处的记载,而非提单背面印刷的小字,因此该提单应被视为承租人提单而非船东提单⑥参见(2003)1Lloyd’s Rep 578。。如果the“Starsin”案关于光船租船条款和承运人识别条款效力问题的判决被沿用,则英国法下船东承担承运人责任的情形与美国法极其相似。唯一的不同在于因英国法不承认多个承运人,故对索赔人起诉时的保护稍逊于美国。
(三)加拿大法下的承运人识别问题之解决
加拿大的判例法认定承运人可以分成三种情况:一是不存在租船时,船东往往被认定为承运人而须对货损货差负责。二是光租时承租人为承运人。三是航次租船和定期租船时倾向于将船东认定为承运人,但近年的判例表明法院更加倾向于让船东与承租人承担连带责任,亦有可能将承租人认定为承运人。[12]对于光船租船条款和承运人识别条款,加拿大法院虽认为其属于《海牙规则》第3条第8款所禁止的减轻或免除承运人责任而无效,但仍然认可船东与承租人的连带责任。[13]
就上述各国判例加以分析,有一种趋势需要说明:几乎所有的案例表明并不是直接推定船东有责任。必须存在可以推定船东为承运人的事实时,比如控制船舶或签发提单,才可令其承担承运人责任,因此有别于可反驳的推定责任。从判例的发展上看,如果说早期因为控制成本而倾向于认定船东为承运人,则近年越来越多的案例都倾向于在符合某些具体条件时认定承租人为承运人。但是,这种发展趋势亦未完全免除船东责任,而是出现了向船东转嫁责任的方法(英国)和向连带责任发展的趋势(美国和加拿大)。在连带责任时船东与承租人关系上,证明责任被施加在船东和承租人身上,他们之间租船合同之约定和提单条款将是法院主要考虑的因素。
五、《鹿特丹规则》的承运人推定制度与中国海商法的发展
(一)反思中国现行海商法对承运人识别问题的解决——要件主义与连带责任的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在承运人的认定问题上采严格的要件主义,必须符合《海商法》关于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的定义,方能被认定为责任人。
根据《海商法》第42条之定义:“承运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实际承运人”是指接受承运人委托,从事货物运输或者部分运输的人,包括接受转委托从事此项运输的其他人。同时,《海商法》也规定了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的连带责任。《海商法》第63条规定:“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都负有赔偿责任的,应当在此项责任范围内负连带责任。”但连带责任适用的前提是:首先能够认定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其次能够确定两者都负有赔偿责任。可见,《海商法》下对于承运人识别问题通过要件主义的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认定,并要求两者承担连带责任来解决。但是,与外国判例比较就会发现,上述美国和加拿大判例中确立的连带责任与中国海商法中的并不相同,前者的连带是船东与承租人连带,而后者是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连带。此两种连带的区别在于:在《海商法》下,索赔方若希望用连带责任获得更大程度保护,前提是要证明船东是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建立实际承运人与承运人连带责任本意在解决承运人无法识别的困难,但如果在具体案件中仍需要索赔的货主证明实际承运人的身份方能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那么,以连带责任解决承运人无法识别的立法目的恐怕难以实现。
《海商法》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在明确实际承运人的法律地位之前是有用的,因为在承运人身份无法断定,责任主体不明时,可以根据连带责任的规定追究多方责任,但实际承运人责任明确后,这种规定则失去了实际意义。[14]《海商法》第60条明确规定承运人就全程运输对货主负直接责任,第61条规定承运人责任适用于实际承运人,即实际承运人就其实际进行的运输部分对货主负直接责任。当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都有责任时,货主即可依第60条和第61条要求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承担责任。但《海商法》第63条则规定:“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都负有赔偿责任的,应当在此项责任范围内负连带责任。”此时责任的连带以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责任的存在为前提,但如果责任存在且明确,货主本可以依第60条和第61条要求赔偿,连带责任的规定未免多余。因此,在中国海上货物运输法下,不管是分别追究责任还是连带追究责任,责任的承担都需要货主证明两点:被告是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货物毁损灭失发生在被告责任期间,即其对货损负有责任。若无法识别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或识别后无法证明其存在责任,货主都不可能胜诉。
(二)中国现行海商立法和海事司法实践中并无注册船东推定责任的规定和判例
中国海事海商法律制度不存在直接要求船东对货损货差负责的规定,只有船东符合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的构成要件,才可以诉诸承运人责任,但货主首先要证明船东是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
在中国海事司法实践中,法院也不会在承运人无法识别时直接推定注册船东为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而是依据《海商法》关于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具体判断案件中的注册船东是否为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但对于这两者的构成要件来说,现行司法判例是存在若干争议的,该问题在海南通连船务公司与五矿国际有色金属贸易公司海上货物运输纠纷案的三次审理中表现尤为明显。在本案中,五矿的出口代理商与海通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运输货物,海通又与湛江外运订立航次租船合同,湛江外运又与五丰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在三份租船合同中均约定由“万盛”轮承担运输。“万盛”轮的注册船东为通连公司,实际交由万通经营管理并配备船员,由万通期租给五丰。船舶在目的港错误卸货,因此托运人五矿对注册船东通连提起诉讼。如何使注册船东通连承担承运人责任的问题上,一审法院将其作为承运人负责,二审法院则认为其是实际承运人,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时回避了该问题,仅以原告无诉权的理由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很明显,在本案中,湛江外运为承运人,但问题就在于能否将通连认定为实际承运人。学者郭瑜的观点是,虽然万通实际经营船舶和配备船员,但鉴于万通是通连的经营管理公司,通连应对万通负被代理人之责任并承担实际承运人的后果。[15]
然而,显然这一问题在司法实务中始终尚未解决,在2006年上海海事法院审理的德州开元进出口有限公司诉华泰海洋发展有限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物灭失赔偿纠纷案中,与五矿诉通连相似的案情再度出现。原告将华泰所有、交由丸吉经营管理的“福伸”轮运输,货物灭失。法院认为,丸吉虽与华泰订有“福伸”轮船舶管理协议,但该协议约定华泰授权丸吉在船舶营运期间可根据行业惯例的需要,以丸吉名义对外签署租约、协议、指定装卸港代理人等。华泰在本案中并未从事任何有关运输或经营的行为,故认定丸吉是以承运人代表身份实际参与涉案经营活动的船舶经营人。
虽判例观点并不统一,但却一致认为,若船东被视为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则必须证明其符合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的构成要件或者其他可以被认定为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的情况,而非直接推定船东为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
货主除了要证明船东是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外,还需要证明货损货差发生在船东运输期间或船东对此负有责任方能要求船东承担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责任(《海商法》第46条、第50条、第61条和第63条)。在广州海事法院2007年审理的台山市志高休闲用品制造有限公司等诉DSL星运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物交付纠纷案中,船舶在目的港无单放货,法院以原告没有举证证明从事区段运输的某些被告实际参与了货物在目的地的交付,因此对原告请求四被告连带承担赔偿责任予以驳回。
据上所述,中国海上货物运输法下并无直接注册船东推定责任的立法和判例,甚至有判例明确反对直接将船东推定为实际承运人,如2003年中化江苏连云港公司诉美国博联集团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损害赔偿案的二审判决。索赔人起诉时不仅要证明被告符合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的构成要件,且须证明货损发生在责任期间始能使法院支持主张。
(三)《鹿特丹规则》船东可反驳的推定责任对中国海商法律制度与海事司法实践可能产生的影响
目前《海商法》对承运人识别问题采构成要件主义与责任相结合的思路,承运人的构成要件采订立运输合同标准,较易判断,但实际承运人的构成要件则需要接受承运人委托或转委托兼具实际从事货物运输,最容易出现争议。实践中因难以认清谁是正确的被告,索赔人往往将包括船东在内的一连串可能的人全部作为被告,被告也往往都会应诉。船东会抗辩自己并未订立运输合同,因此非承运人;也未接受委托实际从事运输,因此非实际承运人。但抗辩不等于责任的转嫁,更不等于直接推定船东承担承运人责任。
如果《海商法》在承运人识别问题上采用《鹿特丹规则》中确立的船东可反驳的推定责任,就会完全颠覆现行法律框架下的责任体系和立法利益平衡的考虑。《海商法》要求索赔人证明谁是可以作为适格被告的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侧重船方利益之考虑;《鹿特丹规则》在索赔人无法证明谁是承运人时直接推定船东为承运人,侧重货方利益之考虑。因此,《鹿特丹规则》船东可反驳的推定责任对中国海商法律制度与海事司法实践可能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法律条文语词的变化,更在于立法意图的改变:是侧重保护船方以促进中国的航运业,还是侧重保护货方以增强中国的贸易出口?因此,这看似技术性的一个制度,对于中国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
(四)是否宜将《鹿特丹规则》船东可反驳的推定责任引入中国海商法以解决承运人识别问题?
笔者认为,从抗辩到推定责任看似仅一小步,立法做出这一小步的跨越却必须审慎斟酌。
首先,并非最新的就是要引入的,尤其是在现行法中引入,法律的先进恐怕远不及法律的稳定重要。新的东西反而更需要观察其实践效果,尤其是对于承运人识别上船东可反驳的推定责任这样存在争议的制度,纵观外国立法和判例尚无国家直接对船东采推定责任说。
其次,可以预见,即使有引入的立法意图,最终的条文也会因交通运输部、大型船公司和船东互保协会的反对而搁置,于立法技术上讲未必可行。因此,承运人识别问题只能交由司法实践去解决。以前在承运人识别上学说都只是立足于判例抽象出来的通则,它应当也只能适用于案例实践。
虽然在承运人识别问题上建立船东可反驳的推定责任可能不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法,于中国立法引入也未必可行,但其却不失为处理具体案件时的一种思路。可能通过对于注册船东的询问得知有关真实承运人的信息。《鹿特丹规则》的立法思路就是通过找到那个可能知道谁是承运人的人来找到真正的承运人。通过对于托运人进路的否定最终仍坚持从船东入手,显然这与传统上从与索赔方的关系入手以寻找承运人的思维方式相异。它从链条另一端展开排除性思考,首先判断船东,如果有光租关系就可以排除船东去思考光租人,以此类推,总可以找到真实控制船舶从事货物运输的人。因为如上文分析,从船东开始的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判断链条往往比从托运人开始更不容易被切断,且托运人很难证明船东与承租人之间的内部关系。
六、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鹿特丹规则》所构建的承运人推定制度有利于解决承运人无法识别的难题,但这样的直接将船东推定为承运人的制度却不宜马上引入《海商法》。一则因为该制度将从根本上颠覆《海商法》现行体制下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证明责任的分配,二则因为《鹿特丹规则》中的该制度尚新,需待司法实践进一步考察其合理性与可行性。承运人识别问题目前只能交由司法实践去解决。在具体海事案件中通过对于注册船东的询问得知有关真实承运人的信息,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案件处理技巧而有所裨益于司法界,因此,这种推定制度可以为司法界借鉴。
如果中国司法实践印证了将注册船东推定为承运人是解决承运人无法识别难题的可行办法,则这一规定就会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而最终影响中国的海商立法,因为中国海商法的发展不应定位于引进国际最先进的规定,而应定位于回应中国海事实践的需要。
[1]SCHOENBAUM T J.A dm iralty and marit ime law[M].4th ed.St.Paul,M inn.:W est Group,2004.
[2]W I L SON J F.Carriage of goods by sea[M].6th ed.London:Longman,2008:237-240.
[3]王炳蔚.论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的识别[J].当代法学,2000(5):117-120.
WAN G Bing-wei.Study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arrier under the law of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J].Contemporary L aw Review,2000(5):117-120.(in Chinese)
[4]曲涛.论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的识别[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7,17(1):152-153.
QU Tao.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arrier of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J].Annual of China Maritime L aw,2007,17(1):151-153.(in Chinese)
[5]郑蕾,阎晓辉.再论海上货物运输索赔中承运人的识别[J].世界海运,1999(6):27-28.
ZHEN G L ei,YAN Xiao-hui.Restudy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arrier under the law of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J].World Shipping,1999(6):27-28.(in Chinese)
[6]STURLEYM F.Phantom carriers and UNC ITRAL’s proposed transport law convention[J].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2006:435.
[7]Gertjan van der Ziel.The UNCITRAL/CM ID raft for a new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sea[J].Transportrecht,2006(25):269.(in Chinese)
[8]韦经建.评英美法对物诉讼的理论和实践[J].当代法学,1992(1):66-67.
WEI Jing-jian.The theory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action in rem in the common law system[J].Contemporary Law Review,1992(1):66-67.(in Chinese)
[9]郭瑜.海商法的精神——中国的实践和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0-107.
GUOYu.The spirit of maritime law practice and theory in China[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100-107.(in Chinese)
[10]刘俊,吕进良.论光船租赁条款及承运人识别条款的效力[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7,17(1):117.
L I U Jun,LV Jin-liang.The effect of dem ise clause and identity of carrier clause[J].Annual of China Maritime L aw,2007,17(1):117.(in Chinese)
[11]PEJOVIC C.The identity of carrier problem under t ime charters:diversity despite unification of law[J].Journal of Maritime L aw and Commerce,2000(31):391.
[12]GIASCHIC.Who is carrier?shipowner or charterer?[EB/OL].[2010-11-23].http://www.admiraltylaw.com/papers/Carrier.htm.
[13]TETL EY W.The dem ise of the dem ise clause?[J].M cgillL aw Journal,1999(44):807.
[14]郭瑜.论海上货物运输中的实际承运人制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3):84.
GUO Yu.Study on the actual carrier under the law of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J].L aw and Social Development,2000(3):84.(in Chinese)
[15]郭瑜.海南通连船务公司与五矿国际有色金属贸易公司海上货物运输纠纷再审案评析[J].海商法研究.2000(1):146.
GUO Yu.Case review:Hainan Tonglian Shipment Co.v.Wukuang International Non-Ferrous Metals Trade Co[J].Maritime Law Review.2000(1):146.(in Chinese)
——船舶承租人范围之观点厘清与浅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