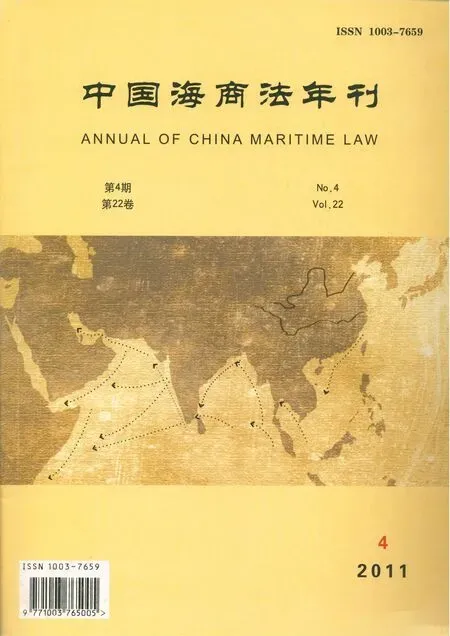航运公会起源于中国*
廖一帆
(福建志远律师事务所,福建厦门 361012)
一、引言
根据欧盟第1419/2006号法令,原第4056/86号法令所规定的班轮公会在反垄断体制中所享有的集体豁免(block exemption)的保护被取消,2008年10月18日以后经营往来欧盟成员国业务的班轮公会“将变为非法”。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班轮公会体制受到釜底抽薪的沉重一击,在此背景下,重谈航运公会的话题似乎显得不合时宜。
然而,正是在这个“万马齐喑”的转折时期,至少有以下4方面原因要求我们再度检讨公会制度的起源与兴衰,并根据行业发展规律把握将来可能出现的变数和机遇。
首先,据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统计,在2007年还有大约150家班轮公会,即使其中往来欧盟成员国的28家在宽限期前悉数解散,“毫无疑问班轮公会在世界海运中仍将保留一席之地”。
其次,1974年联合国《班轮公会行动守则公约》(简称《公约》)依然保护着班轮公会的继续存在,欧盟单方面的立法与《公约》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法律冲突。许多欧盟国家在通过反垄断法令的同时还是《公约》的成员国,更何况直到最近仍无迹象表明有哪个欧盟国家企图退出《公约》,它们本应恪守《公约》中的国际义务而不得提出相悖的动议,因此,欧盟反垄断法令本身的效力存在着重大缺陷。如果欧盟国家要对第三国“违反法令的行为”采取制裁措施,必将面临巨大的法律障碍。
再次,由于公会会员资格仍然是评估班轮公司市值的重要依据,[1]17欧盟国家的班轮公司因第1419/2006号法令被迫退出经营欧洲航线的公会,并不意味着它们同时会自甘放弃在其他公会的利益,而由非欧盟成员国班轮公司所组成的公会也不见得将随之解散,在欧洲航线上甚至可能出现欧盟船公司与“外籍”公会竞争的局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反垄断法规甚嚣尘上之时,已有欧盟法律专家敏锐地指出,欧盟鼓吹海运自由化和全球化并出台反垄断法规的前提背景是欧洲船公司目前在世界航运的市场中占据着其他国家的船公司所无法比拟的绝对优势,但这情形却很可能随着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演变而发生根本逆转,届时鼓吹航运自由化好处的欧盟“立法推手”必然出尔反尔,转而“典见颜”重新呼吁保留所谓“公平的”货载份额,[2]43,49,51,54-56横向协作方式(horizontal agreements)又将卷土重来。
中国远洋船队正在国际航运舞台展示前所未有的实力,因此,客观上也成为海运强国下一轮保护政策的主要“假想敌”,所以,公会制度目前在形式上似乎处于低潮,但其限制竞争的理念绝不可能就此淡出历史,公会发展与影响仍然是应当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二、关于班轮公会起源的传统说法
从西方的视角看,海运是随着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贸易规模的扩大,才逐渐从贸易中剥离出来而独立成为一个行业的,但帆船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班轮的,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还不足以抵御天气海况的影响。在轮船出现后,船东们才开始尝试定期发航并制定运价表,但一开始他们也只能保证“班轮”的开航时间而无法预计航程时间。产业革命引起制造、消费、市场规模等的急剧扩大,航运技术也随之不断进步。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又大大促进了欧洲与远东和印度的贸易与航运。到1885年,在英国登记的轮船总吨位超过了帆船,至此,现代意义上的班轮运输才渐渐摆脱了自然因素的影响。
轮船吨位与船速的提高,反过来造成了吨位过剩的新问题。19世纪初需要4艘帆船运送的货量到该世纪末时仅用一艘轮船即可承担,而运输时间则缩短一半。在运力投放不受调控的自由竞争时代,个体船东对日趋白热化竞争的本能反应就是降低运价以吸引货主,于是利润几乎不复存在;而运输经济的基本规律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制约的竞争总会导致资源浪费,最终的消费者也绝不可能从中受益,[3]140运费收入的短拙将使班轮服务的品质难以为继,最终的受害者还是货主。为在剧烈的竞争中求生存,船东们不得不抱团协调他们在航线上的经营活动、限制竞争并共同对抗其他船东。在此背景下,英国—加尔各答航线上的几个彼此竞争的船东在1875年首度集会,制定了统一的运价表,以保证各自合理的利润,同时为各船分配发航周期。这就是航运公会的滥觞。[1]441
其他论著也肯定这种论调,例如,“公会体系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1875年的印度航线,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波动、运力过剩与激烈的竞争后,经营由加尔各答返航英国本土航线的英国船公司商定征收同等运价”。[4]87“轮船的舱容迅猛增长,于是大约在1870年,它们之间开始发生激烈的竞争,结果导致了公会的出现。第一家公会,即加尔各答公会,成立于1875年,它规定了船舶从各个始发港开航的相同运价。”[5]187
中国的远洋业务专业教材先后更新数版,但也一直受西方的误导而沿用以下说法:“世界上第一个班轮公会是1875年由P&I、B.I.等7家英国船公司在印度加尔各答贸易中成立的‘加尔各答班轮公会’(Calcutta Conference)……班轮公会最先创建在英国。”[6]58
但是,笔者新近查证的史料却表明,最早的公会诞生于中国,华人商业智慧对全球航运发展的历史性贡献不应被忽略、抹杀。
三、清季班轮发展史回顾:航线协议的订立与实践
(一)中国早期班轮运输的发展
轮船虽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早在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即有外资商用轮船在广东伶仃洋一带活动的记录。[7]87-88
从1842年起,香港—广东各口岸、上海—香港、各通商口岸之间的沿海定期班轮业务陆续开辟,这些航线被统称为南洋航线。
到19世纪60年代初,先后有大英火轮船公司(即铁行),英国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即颠地洋行)、蓝烟囱公司、老沙逊洋行,合资的省港邮轮公司、美商旗昌洋行和法国邮船公司等经营中国南方沿海航线。其中,铁行在1845年开辟的南安普顿—香港航线更是亚欧航线上的最早的定期班轮业务,而当时定期班轮船在世界商船队中所占比重还只是一个小零头。暂不考虑这些外资洋行、船公司经营中国沿海航线的非法性以及它们在历次侵华战争、鸦片贸易中所充当的可耻角色,单就经营方式而言,中国的班轮运输业务在世界范围内起步很早。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军事、政治、外交上一败涂地,但还是竭力维护国家的经济权益,并在1858年《天津条约》的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勉强加入所谓的“豆禁”规定,“豆石、豆饼在登州、牛庄两口者,英国商船不准装载出口”,以此保护承担漕运重任的国内沙船业。这是笔者所查阅的国际条约中最早的沿海运输权和货载保留的明文条款。因此,北洋航线上(上海至北方各口)轮船航运业起步稍晚。但列强所庇护的外资航商早就觊觎这个巨大的市场,在1861年底英船就罔顾“豆禁”而擅自到牛庄、烟台装运豆石,到1863年总理衙门不得不奏准废弃“豆禁”,北洋航线于是向列强全面开放。从1865年起,上海各大洋行和外资轮船公司的轮船开始大批出现在北洋航线上。
1861年底,美商琼记洋行的“火箭号”从上海出发,溯游而至武汉,几乎同时英商宝顺洋行的“总督号”也进入长江航线,随后其他外资轮船公司也蜂拥而至长江航线。在1862年至1863年,上海有不下20家洋行,每家经营着1艘或2艘轮船。到1864年,则有10家洋行在经营这条航线,每家拥有1艘或1艘以上的轮船。[7]92某期《北华捷报》的“船期消息”则证实,在1864年某星期就有7家洋行的16艘轮船穿行于长江航线。[8]14另外,还有一些洋行在长江经营不定期轮船业务。沙俄自1854年起也有小型商用轮船非法航行在黑龙江。
在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国家主权及其派生的沿海、内河运输权也彻底沦丧。伴之而起的是,长江和南北洋三大航线上的班轮运输形成相当规模,一些航商还把国内定期航线与加尔各答乃至欧洲的远洋航线连接起来,形成远洋联运。这说明,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就已形成了早熟的班轮运输体系。
(二)竞争与对策:长江协议
由于长江是连接中国众多重要经济腹地的“黄金水道”,从1861年起大量轮船密集于长江航线。于是,这里最早出现了货源不足、吨位过剩的情形。
据统计,1863年,汉口进出货值约2733万两,1864年则为2552万两,比起轮船刚进入长江航线的1861年,货量只不过增长一倍左右,而进出口的船次则分别为1033和793次,轮船吨数次数则分别为395 312吨和417 855吨,远超合理的运力需求。据推算,在1861年,到港全部商船吨数绝不超过15万吨。这就造成了“三分之一的船舶吨位无货可装”,而且随着新轮船的继续投放,这个情形还在不断恶化。[7]94
与吨位过剩相对应的是运价持续下跌。1861年,在上海和汉口之间,上水(上海至汉口)的运价平均每吨10.5两,下水(汉口到上海)运价平均每吨20两。另有说法称:货运运费每吨高达25两,客位每人75两,“往来一律”,轮船下水时还可以拖带本地帆船4艘,每船装货五六百吨,每吨水脚又可得15两,“往返一次,所收水脚,足敷(购船)成本”。航速快、吨位大的轮船挤进长江后,各航商为争夺货源,竞相杀价。到了1864年,上水运费跌至每吨5两,下水每吨2.4两。按照往返合计,1862年就比1861年跌了49.19%。再往后两年,又跌了72.79%和75.74%,跌去了1861年运价的三分之二数。[8]21
激烈的竞争使一些航商无利可图,并很快退出了长江航线。长江航线上实力最强的旗昌轮船公司虽然从一成立(1862年)就成为跌价竞争的始作俑者,但长期的运价低迷也损害了其财务状况。于是,旗昌在1864年1月邀请有关洋行进行协商,提出停止价格战,以订立协议的方式,维持一个能够盈利的价格水平。几经博弈,当年12月10日,各船东与旗昌达成协议,规定:冬季,上海至汉口上水最低运价每吨6两,下水每吨4两;春、夏、秋季,上海至汉口最低运价每吨5两,下水3两。由于最低运费的实行情况令人满意,所以,在1865年12月又续约1年。
这是历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个运价协议,比加尔各答公会早了整整11年。“长江协议”的签订,使旗昌很快摆脱了财务困境,获利甚丰。协议的另一个显著效果是,虽然它没有对抗会外竞争的明文条款,但那些无法接受最低运价的小洋行被迫陆续退出长江航运。到1865年底,长江上的轮船减少至12艘,运力无序投放的局面得到控制;同时,旗昌的轮船增至6艘,占全部长江营运轮船的一半,在运力规模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这标志着在新兴的班轮运输业中,自由竞争开始向垄断竞争转型。
但旗昌的船队数量并不能确保其竞争优势,宝顺的“飞似海马号”(又称“富士山号”)与“气拉度号”(又称“广岛号”)与怡和的“罗拿号”和“格兰吉尔号”,无论在吨位或性能上,仍然对旗昌构成极大威胁,这可理解为后世“战斗船”的先驱。于是,旗昌利用主要竞争对手在1865年伦敦金融风暴中的困境和经营策略的调整,在1867年1月又与宝顺洋行和怡和洋行达成三方协议,其中除盘购对手的资产外,还有这样的内容:怡和、宝顺在10年之内不得以船主或代理人身份经营长江航运,旗昌则在10年内不经营上海以南的沿海航线,但上海至宁波航线除外;旗昌在长江上的上水运费每吨不超过6两,下水运费每吨不超过5两,并且要在长江上保持足够的运输能力。1867年2月,旗昌在长江航线上仅剩的竞争对手琼记洋行把“江龙号”卖给了旗昌,同时保证,琼记自此退出长江,10年之内不会重返长江,旗昌至此确立了在长江上的绝对垄断地位。
如果说,1864年的协议还只是纯粹的运价协定,尚不具备入会条件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只是形成松散的开放式公会的话,那么,1867年初的这两个协议则已对会员资格作出了限定,从而构成了日后主流的封闭式公会。
然旗昌绝对垄断的局面并没维持多久。1867年7月,专营长江航线的公正轮船公司成立,旗昌随即在1868年初与公正轮船公司达成协议:双方在长江货运价格上统一运费,双方同时达成默契,如果公正的船队限制在2艘以内,那么旗昌无意跌价竞争。但由于此前“长江协议”对竞争的限制,1868年长江货运市场又恢复红火,于是公正便急于添置轮船投入营运。由于公正不守约定,旗昌立即宣布中止协议,而且马上跌价竞争。公正无力同旗昌抗衡,只得妥协,把“罗拿号”调离长江,以维持在长江上不超过2艘船的限定。同年,因第一个“长江协议”而退出的同孚洋行试图东山再起;然而,同孚的船刚驶入上海港,旗昌的跌价竞争随之而起,其运价从6两骤跌至3两,从而使得同孚的计划流产。另外,1870年,公正轮船公司的代理商轧拉佛洋行发生资金危机,一直伺机重返长江的琼记洋行暗中收购了公正股票1040股,企图取代轧拉佛,成为公正的大股东兼代理商。旗昌探知这一消息后,坚决不允许企图违约的琼记借机重入长江。琼记无法达到目的,只得将收购到的股票转让给同孚洋行,同孚于是成了公正的大股东。1871年3月,公正召开董事会,正式授权同孚成为它的代理商。同孚总算满足了重入长江的部分愿望。旗昌则接受同孚成为公正的新代理人,并继续维持同公正的航运协议,但直到1873年太古轮船公司收购公正产业为止,公正一直遵守着在长江上保持2艘船的承诺。这一系列协议与较量表明,经营长江航线的公会会员与时俱进,对市场份额、发航次数、运力控制、平衡运量与运力等事项所做的各项具体安排并非杞人忧天。作为法律文件,协议的假定、处理和制裁三个要素都在实践中经受了检验。
1873年4月1日,新成立的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又在长江航线上启动轮运业务,从而把航线竞争推上一个新的高潮,其结果是旗昌在长江航线上的独家垄断局面被彻底瓦解。旗昌应对太古竞争的第一步是立即把上海至汉口的上水运费从每吨5两骤跌至2.5两,甚至要求太古也“不得超过二两五钱”。但太古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把运费降得更低,先从旗昌的每吨2.5两降至2两,以后更低,而且放出风声,他们不在乎运费多少,只在乎船要满载。但由于运价骤跌,许多轮运客户期待运费进一步下跌,或者驻足观望运价变动对后市的影响,以至于运费下跌后货源反而减少了。这一方面说明,随着长江线上班轮竞争态势的演变,老一套的跌价竞争做法已经失灵,结果除了两败俱伤外别无赢家,航线协议需要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国内货主对运价波动有了更为理智而成熟的认识,这正是后来托运人协会与公会协商机制的基础。
由于太古的沿海—远洋航线的联运业务、连环保险,特别是其强大的融资能力对旗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旗昌被迫转而寻求与太古的妥协,但把谈判的条件设定为:太古的轮船可以在长江营运,但条件是5年内不能超过4艘,而且应该提高运费。提价是垄断的目的之一,双方对此自然不会有分歧,但旗昌把太古投放的运力限定在5年内不超过4艘,其玄机在于,要在长江上维持一条每周发船3次的定期航线,至少需要5艘船,这个限制将使太古无法在长江上开辟势均力敌的班轮业务,从而使旗昌继续保持在长江上的优势。果然,太古对这个提议不感兴趣,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直到当年7月底才达成以下协议:双方共同将上海至汉口的运价提高到3.5两;旗昌改变原来支付回扣的方式,规定将10%的回扣按各5%分别付给经纪人和货主。
较之以往各个“长江协议”,这个协议有两个发展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协议不仅规定了最低运价,还对其他费用(运费回扣)的支付方式做了规范;众所周知,回扣是保持客户忠诚度(loyalty)的最重要手段,而协议将此一分为二,无疑大大削弱、分散了旗昌巩固客户忠诚度的努力。二是旗昌通过协议限制太古发航频率、周期的企图没能实现,当年夏秋太古又在长江上投放了3艘新船,“周三班”的定期航线很快形成,货运能力大大提高。另外,太古多管齐下,例如,雇用中文流利的高级职员和著名华人买办郑观应主管船务,拓展当地货源;旗昌付给客户5%回扣,太古就再多付5%;旗昌免收10天栈租,太古就免收15天;太古还接受大货主荐人进入洋行谋事。太古通过这些办法获得了很多客户和货源,甚至把一些旗昌的老客户也诱走了。
旗昌的反制措施则包括:暗示将再挑起运费战;利用在上海法租界工部局的势力,阻止太古建造堆放货物的仓库等。
为避免玉石俱焚,双方最终在1874年2月达成以下协议:双方在上海—汉口航线每周各发船3次;双方统一运费,收入合并,按月平分;平分份额按照每月海关记录的实际货运量来计算;在上海—汉口航线,上水运输“贵重商品”,如茶叶每吨5两,下水每吨3两,其他货物每吨2.5两至3两;旗昌须给太古提供各口岸码头船坞等设施。[8]21-32
与以往的运价协议相比,这个协议不仅规定了统一的运价,而且划分不同种类货物的运费标准,形成综合运价本体系,而发航班期的分配、收益共享与分配等内容更是复杂的、成熟的公会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特别是,岸上资源共享甚至还突破了现代公会横向合作的一切创意而率先标志着船公司联盟(consortium,北美通常称为alliance)雏形的出现。
(三)竞争与对策:北洋协议
在沿海航线上,竞争的出现要比长江晚几年,而且激烈程度也不如长江航线,其原因恰恰在于,长江上亏本竞争的惨重教训使得各航商理智地看到,跌价竞争只是经营的下策,共同垄断市场才可以让他们分享垄断利润,从而获得双赢,于是他们也更倾向于通过妥协实现寡头垄断。另外,沿海航线上的主要竞争者旗昌、太古、怡和以及后来居上的轮船招商局实力相当,一改长江上任意倾轧、无序竞争的局面。
旗昌在1867年取得长江航线上的绝对垄断地位后,便着手向北洋航线拓展,在1877年被新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收购前,它一直有6—7艘轮船航行于上海—天津—烟台的定期往返航线,每周自上海发船2次,一开始俨然成为北洋航线的主角。1868年8月,北清轮船公司成立并在北洋航线上投入了3艘轮船,于是旗昌随即采用“长江模式”,在北洋线上也同北清订立了运费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在从上海出发的750海里的北洋线上,将运费维持在每吨10两以上;如果有第三方进入北洋航线,双方共同跌价驱逐之。当年华洋行将“麦加号”和“天龙”两轮加入航线,旗昌立即把运费降到4两,不到两个月就把华挤出航线。至此,封闭式公会对抗会外竞争的做法已经与当代毫无二致。
1869年1月,怡和将“九绥号”投入上海—天津航线,同时又向英国订购新轮2艘,准备第二年也投入该航线。见此情形,旗昌和北清立即按照双方的运费协议,共同降低运价,吸收货源,以迫使“九绥号”退出北洋。但怡和有备而来,在1870年春夏说服一些华商买下“天龙号”,收购北清的“南浔号”,并把她们交给怡和代理,此时其向英国订购的第一艘轮船“亚平号”也抵达上海,怡和洋行实力大增。于是,旗昌、北清、怡和三方经过谈判,于1870年7月重订运费协议,由三家共同经营北洋航线。1871年2月,北清的代理商裕洋行终于难以为继,怡和洋行乘机接手北清,成为它的代理商。两年后,怡和洋行又以沿海船队为基础,设立了华海轮船公司。但由于旗昌和怡和在船队和客货源上各自的优势,双方都继续承认1870年达成的运费协议,以避免恶性竞争、两败俱伤,1874年还将运费协议再展期3年。
(四)竞争与对策:南洋协议
在南洋航线上,由于主要的经营者旗昌和怡和所辟航线不同,因此没有出现恶性竞争,但航商们也有上海至宁波、汕头、广东各口的“水脚最低者”以及抵制第三方竞争者联合行动的协议。良性经营与航商协议究竟孰因孰果,可以见仁见智。
(五)民族企业轮船招商局:公会制度集大成者
1873年初(同治十一年底),近代民族企业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它在1877年3月收购旗昌的产业,从此改变了江海航运由外商垄断的格局。自1877年12月至辛亥革命爆发,招商局先后同太古、怡和签订或续订7次“齐价合同”,与先前的长江协议、南北洋协议相比,其内容在客货载份额分配、运价标准、航线设计、运力投放、发航次数、排斥会外竞争的共同行为、违约制裁等方面也愈加丰富、细化。[8]127-133由于招商局齐价合同的订立时间都在1875年(即加尔各答公会成立)以后,故不拟进一步论述,但可以肯定的是,招商局从初具竞争实力伊始就能娴熟地运用公会机制,这正是此前公会在国内已发展成熟的明证。
四、清季航线协议的法律与实务分析
(一)国内航线上运价协议的订立均构成班轮公会
从上述概略可见,自1864年起,截至1874年初,经营中国长江、沿海航线的船公司在存在竞争的领域都达成了垄断协议,其内容也从最初单纯的统一运价逐渐扩展到航线经营权、运力投放、回扣支付、货物分等收费、发航次数分配、对抗外部竞争的联合行动、运费共享等事项,甚至还形成了早期的联盟,限制竞争的机制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脉络十分清晰,那么这些航线协议在法律上是否都构成公会?
按照《公约》第1章的定义,班轮公会或公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使用船舶的运输商的团体,这些运输商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在某一条或数条航线上提供运送货物的国际班轮服务,并在一项不论何种性质的协定或安排的范围内,按照划一的或共同的运费率及任何其他有关提供班轮服务的协议条件而经营业务”。据此,不管是长江协议还是南北洋协议,都还称不上是班轮公会,因为它们涉及的都是国内航线。但必须澄清的是,《公约》是个国际法律文件,该定义要受制于其适用范围。特别是,《公约》最重要目的之一是在各国间确立40%:40%:20%的货载分配原则,与之有关的公会只能是经营国际运输者,因此,其外延必然比行业的或学理的理解要狭隘得多。
通常认为,班轮公会是由两个或多个在特定地理区划中共同经营同种业务的船公司所组成的组织,会员船公司约定一套向托运人报价的运价体系,每个船公司都收取跟其他船公司一样的运费。[9]219可见,航线的国际性并非公会的要素。
如同其他存在竞争的商业领域一样,班轮运输中运力过剩的现象也促使经营者通过协商对内外部竞争作出限制,这便是公会机制。[3]139-140公会所采用的联合举措通常包括共同的运价、约定的发航频率和发航次数的分配、共同的入会标准、不同业务的安排、某种约束托运人的安排(或称之为忠诚安排)、关于附加费的共同做法。在更加正规和复杂的公会中,还有共享货源甚至通过某种综合的共同派船安排共享收入的做法,但公会在多大程度上采用这些“共同的要素”取决于该组织的发达程度。从公会的发展规律看,会员协调行动的“第一步就是统一报价;其次是分配挂港和调剂发航次数,接下来是与托运人签订特别协议,而如果这些措施都无法避免竞争,承运人就实行业务共享,最终可能导致收入共享”。[1]21因此,只要经营相同业务或航线的船公司按照某些基本原则形成自由组合即构成公会。[4]88公会并非法律实体,所以其组织形式不拘,有些公会订立协议并设立常设机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另一些公会则连正式书面协议都没有,[10]213甚至“口头的君子协定”都足以创设公会。[1]15北美航线上的“开放式公会”,除了确定运价外,基本上再无其他作为,而会外船公司甚至只需发个简短通告就可成为会员。[3]141
近年来,班轮公司为响应全球托运人的需求、提供更高效的服务、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在合作形式上做了“结构性调整”(structural change)而结成联盟,按照欧盟第823/2000号法令的定义,这是指船公司彼此合作以提供共同班轮运输服务的组合。发展中国家由于担心被这种市场竞争中“本能”出现的嬗递边缘化,试图淡化公会与联盟的区别,并强烈要求将会外联盟视为班轮公会,并对其适用《公约》的规定。[11]而欧盟等海运强国则认为,联盟的运作虽经常与公会竞合,但“显然”不在班轮公会的范畴之内。[10]215欧盟根据第870/1995号令、第823/2000号令和第611/2005号令一再强调,甄别公会与联盟,并对联盟适用不同的反垄断豁免的条件就是排除联盟成员之间的“任何价格或运价本协议”。[2]46这反过来说明,即使以“后公会时代”的标准衡量,判断船公司之间合作是否构成公会的核心依据或者充分条件仍然为是否存在运价协议。
据此可以断言,不管当事者是否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其合作的性质及历史意义,也不管旗昌及其竞争对手采用何种外观的合作,在1864年,世界上第一个班轮公会组织即已在中国大地上诞生,其组织形式为第一个“长江协议”。1867年初的协议还对班轮挂港做出了详细安排;1867年至1871年的协议则划分了特定的航线经营权和运力投放数量;1868年的“北洋协议”还有会员采取联合行动对抗会外竞争的条文;1873年至1874年初旗昌与太古达成协议时,不仅出现了班期安排、分类收费运价本、忠诚协议等高级公会的共同做法,其运费收入共享的条文更是现代西方所构想的公会的终极形式,该协议甚至还在西方所妄断的第一家“加尔各答公会”成立前一年多就已率先突破了公会机制而成为现代联盟的嚆矢。
(二)公会的理念实为华人首创
从外观看,长江及沿海航线协议的倡导者和主角似乎都是外国企业,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华商与外国资本彼此勾结,形成了错综复杂、相互制约的利益共同体,对买办的作用绝不能肤浅地理解为只是为虎作伥,现在必须从资本与经营两方面做客观的深层次分析。
如果可以暂时搁置这种“狼狈为奸”的关系在政治、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上的消极意义,仅就微观的企业决策层面而论,那么,笔者认为,班轮公会恰恰很可能是华人出于商业目的,利用其在这种微妙关系中对“外资企业”的话语权,将商业领域的国粹引入新兴而又早熟的国内轮船航运业的结果。之后,“外资”洋行随着远洋航线的延伸,又把这种航商联合行动、限制竞争并共同垄断市场的新理念(cartel)传播到印度,给还在自由竞争中茫然无措的英国船东指明了一条出路,从而催生了加尔各答公会及其后继者。
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起,伴随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外资洋行在国内取得了超国民待遇,于是,中国商人为了分享航运利润和逃避清政府繁重的税厘,早在1848年就有向外资轮船航运企业投资(称为“附股”)的传闻,在19世纪50年代后更是蔚然成风。据苏松太道丁日昌估计,有七到八成华商参与“附股”。
华人附股的第一种方式是投资于具体的轮船。例如,最早投入长江运营的琼记洋行“火箭号”就附有华商陈竹坪和阿庞的共1万美元直接投资。前者还在琼记的“山东号”附股69 700两、在“江龙号”附股7 200两,在另一艘海轮附股5 000两。粤商唐廷枢(景星)从1869年起投资轮船业,琼记的“苏晏拿打号”、怡和的“南浔号”、马立师洋行的“洞庭号”和“汉阳号”都有他的投资,这些轮船的大部分股权都属于华商。唐景星还与美国人共有“满洲号”的股权,在“永宁号”也有相当股权,这些轮船都经营长江航线。琼记的“苏晏拿打号”上附有10个华商的股份,“海龙号”有12个华商的股份,“汤姆·亨特号”上附有8个华商的股份,“江龙号”除了陈竹坪外,还有另两个华商各附股10 000美元。
其次,许多华商为逃避清政府税厘重剥,将完全属于自己的或主要属于自己的轮船委托洋行代理,比如,“南浔号”和“天龙号”系由中国商人买下,股权完全属于中国人,但先后委托清美洋行和怡和洋行代理;“信号”也由华商集资购买,而代理商为轧佛拉洋行。
华商附股的第三种形式是以认购外资轮船公司股票方式的投资,其发轫于旗昌轮船公司创办之时。旗昌先期筹集的三分之一股本就是由华商认购的,购买“惊异号”的第一笔资金45 000美元也来自华商投资。按金能亨的说法,旗昌在上海募集到的17万美元投资大部分就来自“中国的老朋友”,当旗昌的股本额扩大到100万两时,华商附股占60万至70万两,可考的华人股东至少有12人以上。其中,仅顾丰盛、陈竹坪就分别持有旗昌15%、13%的股份,原宝顺洋行买办、著名华商徐润在旗昌也有巨额投资,华人股东对旗昌经营策略的决定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北清船队一半以上的产权也为华商拥有。1867年以后,外资轮运企业基本上都以招股集资方式创办,因此,对大多数洋行来说,能否吸引华商附股实际上是创办“外资”轮船企业成败的关键所在。例如,公正轮船招股集资的17万两大部分就来自华商,华人董事占一半以上,而那些争取不到华商投资的创办计划大多铩羽而归。连英资的太古轮船公司也试图尽可能在中国寻找认股者,只不过此时华商的投资兴趣已转向轮船招商局才未遂。
耐人寻味的是,此时西方班轮运输仍由家族商行主导,习惯于单独的经营与竞争,“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的垄断相比,有着重大的差别”,[7]103-105联合垄断对这个新兴的行业还是个新课题。
反观国人早在封建时代的经商传统即有和气生财、和为贵的理念,作为一种市场行为或经营方式,横向协作、限制竞争的手段早已超越社会发展形态和技术条件而运用得如火纯青。远的不说,元泰定二年之后,“未及数载,有司屡言富商高抬价值之害,运司所言纲船作弊”,[12]7522洪武年间“商货至,或止于舟,或贮城外,驵侩上下其价”。[13]7991这些原始记载都是华商早期操弄供需与价格、联合垄断(cartelisation)的明证。
于是,当附股于新兴轮船企业的华商的经济利益受到竞争威胁时,他们必将本能地沿袭传统的经商经验,动用其在“外资”洋行中的决策权,向国外同行灌输、推介联合垄断的机制,从而在无意间促成了最早的航运公会,这是顺理成章的情理中事——毕竟连西方学者也承认,“就形式与目的而言,航运公会的大多数行动都与其他商业领域中限制性行业做法相似”。[3]140与同时代的国外航商相比,数千年的商业文化积淀至少使附股的华商在创设、推行、发展公会制度以应对新的班轮竞争时不存在任何认知的犹豫或行动上的障碍。
另外,即使是在“纯外资”的太古公司,主管船务的仍然是华人买办,它还吸收大量华人职员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华人的意见与主张必然是促成航线协议的决定性因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怡和在1873年将原北清船队盘入后扩充为华海轮船公司,此时华商股份占20%以上,后来成为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先后担任公正、北清、华海的董事,在怡和享有相当发言权,而华海的航线则延伸到加尔各答和东南
亚。[8]60-65
因此,历史的真相极可能是:华商筹划、创办了长江及沿海各公会,再通过华海的业务扩张,把这个创意推广到其他远洋航线。只是国内各公会均有特定的地域限制,而当时的买办资本又不具备向国外市场辐射的意愿和实力,这才导致国人的历史性贡献长期被西方攘为己有。
(三)中国的公会在实践中不断成熟
清季航商运价协议的内容是根据市场与竞争的演变而不断调整、细化和丰富完善的,各项安排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源于现实的需要,又都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学者总结了公会一百多年发展史后罗列了各条航线上的竞争手段或小动作,如支付过高代理费,送礼,招待,回扣,减免码头、装卸、搬移、仓储、转运、驳运、保险等费用,在船舶所有权、租赁、控制、经营等方面寻找借口直接或间接地对统一的费率或做法阳奉阴违,擅自降低运费,会员对其部分船舶适用不同费率或规定,代理对船舶或货物的不当利益,虚报货量,在运输单证上弄虚作假,套用代理或母公司名义做规避行为,与托运人的内幕交易,等等。[14]39-63而从上文的回顾可见,中国的航商们至迟在1874年前就已领略并通过协议解决了这些问题,甚至还出现了运费收入共享、联盟的超前对策。就可考文献而言,1875年的加尔各答协议,除了简单地规定单向返航的统一运价和班期分配外,再无其他创意,在发达程度上与中国早年的运价协定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五、结语
近代中国航运史研究往往侧重于宏观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务从业人士则埋头于打理日常业务而疏于检讨、总结行业发展规律,于是声讨买办阶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成过程中所起的消极作用几乎成为行业发展史研究的唯一目的和必然结果。笔者丝毫无意否认同业前辈嗜利忘义的本性及其在百年积弱中纵向的历史责任,但在口诛笔伐之余,恰恰由于商人逐利,是否还应该兼顾微观的市场、竞争、行业实务、技术、法律等因素,从大历史观的视角发掘各事件的横向行业价值,从而更加立体地还原清季航商的本来面目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民族产业的自信心呢?
《公约》出台后近40年里,班轮业的竞争与合作出现了始料不及的发展;在“国家船队”的政治色彩日益淡化的今天,欧盟的反垄断法令也好,公会限制竞争的努力也好,究其实质都回归为本位的经济权益博弈手段。作为新兴的海运大国,在经营中我们应跟进欧盟时下法令的具体要求,但更应清醒地看到,我们的航运市场仍有待完善,与欧盟国家的经营条件相比还存在相当的差距,如在某些航线上零运价的恶性竞争还不时耳闻。为此,以史为鉴,对市场行为做适当的规范或许有助于平衡船货各方的利益,实现共赢;而如果随着中国外贸海运实力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发达国家的航运保护政策重新抬头,那么,在下一场经济角逐中,如何实现横向协作、公平份额,又将对我们的商业智慧提出新的考验。
[1]HERMAN A.Shipping conferences[M].London:L loyd’s of London Press Ltd,1983.
[2]MUNARIF.Liner shipping and antitrust after the repeal of regulation 4056/86[J].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2009(1).
[3]MCINTOSH ACB.Anti-trust implications of liner conferences:alternatives to the regulation of liner trades with emphasis on the european approach[J].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1980(1).
[4]FARTHINGB.International shipping: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cies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maritime world[M].London:Lloyd’s of London Press Ltd,1993.
[5]BRANCH A E.Elements of shipping[M].5th ed.New York:Chapman and Hall Ltd,1983:187.
[6]胡美芬,王义源.远洋运输业务[M].4版.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6:58.
HU Mei-fen,WANG Yi-yuan.Ocean shipping practice[M].4th ed.Beijing: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2006:58.(in Chinese)
[7]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M].2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FAN Bai-chuan.The rise of Chinese steam ship industry[M].2nd ed.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Press,2007.(in Chinese)
[8]陈潮.晚清招商局新考——外资航运业与晚清招商局[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CHEN Chao.Revisiting China merchant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foreigner-invested steam ship industry and China merchant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M].Shanghai: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Press,2007.(in Chinese)
[9]BROD IE P.Commercial shipping handbook[M].2nded.London:In for ma Law,2006:219.
[10]CHUAH J.Liner conferences in the EU and the proposed review of EC regulation 4056/86[J].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2005(2).
[11]JUDA L.Wither the UNCTAD liner code:the liner code review conference[J].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1992(23):106,110.
[12]宋濂,王濂.二十五史·元史·食货志五(卷九十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522.
SON G Lian,WAN G Lian.Authoritative histories of twenty-five dynasties in China:yuan dynasty:the fifth account of economy(Vol.97)[M].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Press,1986:7522.(in Chinese)
[13]张廷玉.二十五史·明史·食货志五(卷八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991.
ZHANG Ting-yu.Authoritative histories of twenty-five dynasties in China:ming dynasty:the fifth account of economy(Vol.81)[M].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Press,1986:7991.(in Chinese)
[14]ODEKE A.Shipping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M].Aldershot: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L im ited,1988:39-63.
——基于FPS游戏《穿越火线》战队公会的网络诈骗行为研究
——以FPS游戏《穿越火线》战队公会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