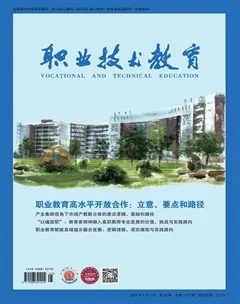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立意、要点和路径
摘 要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要求,稳步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深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的重要方式。理论上讲,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是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实践中要以完善一体化政策体系为逻辑前提、创建高质量对外开放平台为立足基础、构建多元协同的育人共同体为核心任务,构建一体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对外开放体系。据此,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实现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立足系统思维,构建制度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政策体系;优化国际化平台建设,稳步拓宽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新场域;注重生态塑造,打造开放协同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生态圈。
关键词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职业教育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25-0006-07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可见,高水平的开放对于彰显我国市场优势、整合国际资源、优化经济发展格局、建设新的经济体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优化职业教育办学理念、拓展职业教育办学资源、丰富职业教育合作形式等具有重要引领作用。随着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持续确立,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战略资源地位日益凸显。从内环境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变革和产能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迫切需要大量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与之相协调。从外环境而言,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稳步提升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入,亟须众多熟知东盟的本土化“东盟通”人才的稳固支撑。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区域,东盟与中国合作发展历经从睦邻互信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构建命运共同体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成为中国在国际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具活力的对象之一[1]。随着新开放格局的进一步深化,探索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对于深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校企合作、产能调整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作用。
一、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的价值立意
教育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受益者、助力者[2]。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作为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途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作用。高水平扩大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是要在现有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基础上,立足建设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通过跨区域职业教育合作与交流,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发展水平。
(一)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是助力国家外交大局实现的重要方式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和文化优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以来,双方关系由浅层化逐渐发展成为深层化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一系列政策文件和合作协议的发布,为双方职业教育合作带来新的场域。一是从国家层面来看,近年来我国从战略层面积极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推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合作和落地,在中国—东盟合作框架和趋势的指引下,双方不断发布相关的政策文本,不仅明确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和培养高级数字人才的决心,也拓展了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空间[3]。如:《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强调“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等平台,加强教育创新和学术交流”。诸如此类,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等的推进,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制度型开放框架逐渐形成。二是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作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推动者,其积极通过相关的政策支持、经济支持、人员交流等形式和途径促进双方合作的稳步推进。各地政府积极发挥自身主导作用,推进本地区职业教育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要求,引导本地区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积极推进与东盟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如:天津积极依托渤海“鲁班工坊”推动职业院校与东盟国家展开合作;2016年,泰国大城技术学院挂牌成立了“鲁班工坊”,这是我国在海外设立的首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孔子学院”[4];截至2024年,广西积极联合国内各高校和东盟国家,立项建设10个左右中国—东盟技术创新学院[5],在东盟国家共建17个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建设中国—东盟产教发展智库。三是从民间层面来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主要在学校层面开展,多采用合作联盟、交流周等形式呈现,立足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等,成立相关研究中心和智库,如: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中国—东盟教育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智库等。总之,在各方的不断努力和推进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成为助推我国大国外交建设的重要品牌和形式。2024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厅室主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万象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时指出,中国—东盟双方合作中呈现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人文交流迅速复苏、互联互通走深走实、新生动力不断涌现等特征[6]。由此可见,随着中国—东盟合作的进一步加深和推进,高水平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开放合作必然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方向。
(二)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是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
教育强国的核心在于人的强国,人的强是支撑教育强国高质量实现的基本支撑。本质上来看,人的强包含三个维度即人的身体之强、精神之强和能力之强。其中,身体之强是基础,精神之强是目标,能力之强是核心。对于个体而言,能力表现为自我的知识储备能力、从业能力等,贯穿个体能力的基本要素是自我以专业和职业为基本进行的学习。而职业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事业,其必然需要不断对自我的人才培养理念和人才培养方式进行优化和调整。这一优化和调整,既需要立足职业教育的自身特征,实现自我的净化和完善,还需要正确依托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开拓职业教育合作的新渠道。可以说,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本质在于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拓宽人才培养的站位视野。传统职业教育合作过程中人才培养立足本国经济发展需要,人才培养理念方式等强调对本国、地区产业的对标,职业教育合作和交流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而高水平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开放合作是要立足国际产能结构调整和产业变革需求的角度对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方式、模式等进行整体化重塑,进一步促成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和国际职业教育合作形式的深入衔接和协调,在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共性中探索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个性理念。二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延展职业教育合作域。高水平开放趋势下,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放置于中国—东盟合作共同体的实践框架内,共同体表现为立足共同发展目标而形成的联合群体,在这一背景下,必然要求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从浅层合作走向更深、更实的合作,从产业协同、院校合作、资源共享等角度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框架和任务进行深入凝练。三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重塑职业教育合作生态圈。高质量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开放合作,既需要立足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自身,还需要优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内外部生态结构,双方各参与主体围绕合作需求,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彼此间的利益共享及资源互换,实现双方在政府政策、文化与科技、基础设施、科技研发转化等方面的深度合作,真正实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开放合作的内外部生态体系的相互协调和彼此互生。
(三)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是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的本质目标在于形塑中国职业教育在国际职业教育合作和育人实践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具有“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与“以职业教育提升国际影响力”双重意蕴,前者指向国际社会对中国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偏重于在国际职业教育发展外环境中的中国职业教育的话语权,而后者则强调职业教育的自身质量,要求通过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增强中国职业教育的影响力,二者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的本质途径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内求和外塑,贯穿内求和外塑的核心元素是开放合作。以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为考察对象可知,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所呈现的国际影响力自然也由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自身和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发展的外环境所决定。一方面,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能够助力中国高职院校高质量走出去,实现国际化。高职院校国际化是国际合作进程中必须主动扮演的角色,高职院校国际化表现为高职院校主动参与国际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实践,自觉将自我的办学理念与国际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相互融合,同时也包括教师国际化,即通过不同类型、行业等教师队伍的组建和优化,提升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能够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国际化。中国—东盟合作的不断加深,必然需要众多熟悉东盟、了解东盟的国际化人才支撑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的发展。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与东盟贸易继续保持增长,规模达6.41万亿元,东盟连续4年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7]。经贸合作纵深发展的同时必然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人才,这就为双方职业教育合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报告,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交通设施建设将使沿线经济体的贸易增长2.8%~9.7%,并推动世界贸易额增长1.7%~6.2%[8]。由此可知,当前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熟知本地区文化的跨文化高技能新型国际化人才依然是制约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障碍。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合作,必然成为未来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国际贡献的重要途径。
二、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的逻辑要点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伴随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的深化而不断深化。近年来,双方围绕人才培养、留学生教育、产业合作、跨境办学等方面开展多方面的合作,但也面临着新机遇和新挑战。
(一)完善一体化政策体系是深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首要任务
政策是支撑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走深、走稳、走实的指向标,完善协同的政策体系能够进一步帮助双方进行高效合作。现有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开放合作进程中,因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进程中涉及面广、国家发展差异、社会体制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在实践过程中政策体系形成的融合性难以充分呈现。首先,政策统筹性不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属于跨区域范畴,具有跨域性和复杂性,需要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思考和把握。现有职业教育政策文本中虽然积极提倡职业教育国际化,鼓励职业院校和企业走出去,但对于具体的相关要求、措施、机制等并未作出明确要求和规定。整体来看,从国家到各地方层级之间对于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制度设计存在系统性缺失,使得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中合作规划、合作布局等难以发挥出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9]。其次,区域化政策制度定位不明确,缺乏详细的在地化合作规划。在地化职业教育合作是支撑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特色生成的重要元素,现有职业教育合作等多依托《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等合作文件实施,而对于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针对性文件却相对较少,同时,各区域内关于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相关文件也多是围绕整体性合作展开,针对本区域特色的挖掘和东盟十国中国别性合作的政策文件相对较少,导致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中政策的在地化特征难以彰显和呈现。最后,在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进程中,职业教育自身政策制定缺乏经验,行动者政策成本漠视化。受我国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历史和基础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经验相对不足。尤其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政策制定方面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参照,致使现有政策对双方利益的关照不足。
(二)创建高质量对外开放平台是深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立足基础
平台是支撑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高质量推进和实现的基础,也是高质量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重要载体,强化平台研究是当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围绕中国—东盟合作的深化,各参与主体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实践,创设了庞大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对外交流和合作平台。就平台性质来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平台可以分为三类,即理论主导的研究平台、实践主导的研究平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实践平台。其中,理论主导的研究平台多由政府、大学等主导,这类平台关注于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研究,如: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该中心的基本定位是面向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学术前沿研究,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开展精准化专业培训、搭建国际化平台。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深化和研究需要,又进一步针对东盟十国成立了以文莱为首的10个国别研究所,逐渐形成了针对东盟职业教育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研究的布局。实践主导的研究平台主要由职业教育实践的一线单位主导,这类单位多以职业院校为主,如:2022年北京唐风汉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在马来西亚建立中马国际教育学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平台主要由多主体共同协同和组建,这类平台具有综合性特征。如:中国—东盟技术教育合作平台(CATECP)、中国—东盟教育联盟、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等。其中,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由参与“中国—东盟双百职校强强合作旗舰计划(2018-2022)”的175个中国与东盟各国职业院校、应用技术大学、研究机构和行业企业共同发起,其中,中方单位98家,10个东盟成员国77家共同组成。众多研究平台在全面发展的同时也存在隐忧。一是区域间平台资源共享和联合程度有待进一步增强。就研究平台分布来看,多受地域要素和经济发展要素的影响呈现动态分布,如:广西利用区位优势,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和边境职业教育合作;江苏、山东、浙江等充分发挥产业和经济优势,积极同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进行职业教育合作等。而其他内陆省份,相较于这些地区往往存在劣势,虽有合作但效果不佳。二是平台定位不明确,扎堆化较为明显。从现有实践和研究成果来看,当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平台建立多立足于以自身专业发展为导向,受国际形势影响,2021年以来财经商贸大类平台数量迅速增长,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水利大类等专业领域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尚未建立[10]。三是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之间需要进一步加强。从现有研究来看,针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相关理论成果略显薄弱,随着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实践必然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以实现高效推进,而现实研究多是聚焦于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经验研究,而如何将经验研究转化为理论研究,这必然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中平台建设所应考虑的新问题。
(三)构建多元协同的育人共同体是实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质量对外开放的核心任务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开放合作是一项跨区域、跨文化、跨理念的育人合作实践,需要正确处理好各实践主体的关系,明确主体责任,规范主体权利,引导各参与主体自觉履行义务,进而形成相互合作、互生互促的合作共同体。共同体表现为各参与主体围绕共同目标,以某一途径为纽带所形成的关系集合,这一集合的最终目标在于实现彼此的共同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的要求,就是要通过不断地开放合作提升不同区域和国家同中国的合作水平和质量。于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而言,就是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深入探索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育人共同体,形塑中国—东盟合作的新质生产力。从现有研究和实践来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育人共同体呈现纵深化发展趋势,但仍存在亟待完善之处。一是价值共享机制不畅。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本质目标在于实现中国—东盟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凝聚中国—东盟合作的凝聚力。价值表现为育人价值、育人理念等方面的共享,因中国与东盟国家所属国家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差异因素的影响,致使在现实合作过程中往往会产生理念上的偏差,导致合作处于浅表层面,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办学的相关政府、企业、行业缺乏主动性[11]。二是产学合作内推力不足。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实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重要抓手,当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中学校和企业同步走出去的协同性不强,导致企业在走出去进程中高质量国际化人才的供给难以得到保障,最终影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在学历对接方面,合作方之间未能正确完善双方合作的对接机制,致使双方在学历上难以实现平衡,导致人才培养资源的浪费,直观表现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区域性资格框架缺失、校企协同“走出去”的机制还需优化等[12]。三是职业院校国际化水平尚需进一步提高。职业院校是深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主战场,其国际化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水平。受我国职业院校自身发展水平和国际化认知程度的影响,当前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下,职业院校多采取经验性的合作方式,在整体合作中盲目推进,局限于未经筛选的院校和契约合作,且相关合作多集中于对基础知识和简单技能的传授,停留在场地、课程资源与学习材料等浅层。相关合作项目开展较为缓慢,对于课程、学分以及资格互认等也十分有限[13]。
三、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的战略路径
(一)立足系统思维,构建制度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政策体系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是中国—东盟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要求,制度型开放是从制度的维度规范中国—东盟合作。而对于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而言,构建制度型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体系要从顶层维度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作出详细规划和设计,以避免现有实践过程中制度的无序化、断层化和脱嵌化。其中,无序化指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统一的要求和实施目标,使得政策制定和实施无法达到既定或预期效果。断层化主要指中央—地方、地方—学校等之间的衔接性不强,导致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相应的偏差。脱嵌化主要指中国—东盟国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能正确立足彼此的需要而造成实践过程中衔接不畅、对接错位等问题。基于此,实践过程构建制度化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政策体系,首先要立足政策本身价值,发挥政策的积极效应。在整体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正确提升政策工具的精度、特性、主体性。所谓政策工具的精度,即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积极坚持调查研究,立足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现实基础,针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现状,制定引领性、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开放政策,实现政策实施的有的放矢。政策工具特性指要根据职业教育特色和中国—东盟合作的需要,完善职业教育合作政策,避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陷入孤立化的局面。政策工具的主体性指在合作制定过程应当积极利用不同参与主体的作用和价值,避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主体缺失。其次,坚持体系化理念,实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政策的体系化。体系化指在政策过程中应当注重政策间的纵向贯通和横向融通,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政策的纵向贯通指要形成“中央—省域—市域—学校”的一体化衔接,中央(国家层面)应当积极围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制定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规范性文本,这一文本主要面向规范层面和统筹层面,具有把控宏观方向的作用。省域层面应当根据国家层面的宏观指向,结合本省的发展基础和产业结构,为本省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出台相应的指导性意见,同理,市域层面也应坚持这一原则。而对于学校层面而言,其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核心实施者,应当结合本校的发展情况,制定详细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操作指南和合作协议,以提升本校的合作水平。横向融通主要指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应局限于职业教育层面,还应当积极同其他政策进行关联,如: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经济合作框架、中国—东盟产业合作政策等,实现政策间的彼此协调和互相促进。最后,完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政策的借鉴机制和评价机制,确保政策的高效性和适应性。因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尚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在相应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上,应加强对其他国家职业教育合作政策的借鉴,提升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政策的国际化水平。同时,还应当强化对政策的评价机制,政策评价是指按照一定的主观价值判断和客观价值准则,对政策对象及其实施可能对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产生的积极影响和负面影响的综合评价[14]。不仅要定期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政策开展预测性评价和跟踪评价,还应当积极在不同阶段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等情况及时关注,以提升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政策的适应性,确保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公平和质量。
(二)优化国际化平台建设,稳步拓宽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新场域
国际化合作平台是确保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重要窗口,高质量的开放合作平台能够快速帮助合作双方获得合作方的前沿信息和合作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可见,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立足双边合作的基础开展深入的实践和探索,还应当通过不同领域的融合拓宽“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要建立体系化合作平台。根据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现状和规划,可以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交流平台划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形式。其中,前者具有政府性特征,以国家政策和双边发展需要为导向。这类平台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如:中国“一带一路”网,该网站是集资讯、政策、项目、数据、服务、国别、专区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交流平台。后者具有自主性,主要由研究机构和职业教育办学主体自动发起成立,其主要协同多个区域和团队,通过多渠道进行资源整合和互动的交流平台。这类平台权威性相对较弱,是综合性的联合平台,如: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中国—东盟职教院校合作联盟等;也有国别性、专业性的合作联盟,如:中国—越南职业教育产教联盟、中国—印度尼西亚职业教育产教联盟、中国—东盟交通职业教育联盟等。显然,在当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中多为自下而上的交流平台。因此,应强化两种交流平台的衔接和互动,实现二者的互相补充。另一方面,要立足“点—线—面”思维,实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平台的层级协调。“点”思维主要是中国—东盟双边合作中,以单一单位合作进行合作交流,这类交流多在学校层面开展,双方依托协议开展相应的合作,学校相关人员建立相对稳定的互访交流机制,定期召开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探索人才培养标准和模式等,这一形式的合作平台往往依靠双方内部资源支持,可持续性得不到保障。“线”思维主要是以行业、产业为主导所开展的合作和交流,亦可分为两种形式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主要由政府牵头开展,是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多元协同的合作形式。自下而上主要是在学校“点”合作的基础上通过行业协会、院校间的联合形成相应的合作平台,进而吸引外部团队和资源共同建设。自上而下地建立“线”式平台,优势在于合作中有项目和政策支持,劣势在于国外层面的合作难以迅速响应,致使部分合作不及时。而自下而上在这一层面则显示出其独特优势,在实践过程中更容易建立合作关系和双边互动机制。“面”思维则是强调从整体层面开展合作,这一层面包含国内平台和东盟国家合作平台两个方面,双方分别负责不同国家的合作事项,这类合作往往能够吸引双方优质资源参与合作,从而获得稳定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资源支持,但实践过程中要处理好合作的对接问题。
(三)注重生态塑造,打造开放协同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生态圈
质量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成功进行的前提条件[15]。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是一项综合性的育人实践探索,需要从整体性角度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诸多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和审视。立足中国—东盟全面战略合作的规划要求和区域经济动能变革调整的需要,未来必然需要从现有的浅层经验性合作转向深入的内涵式合作。通过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生态的塑造,遵循系统演化的多样性和稳健性逻辑,构建契合中国—东盟双边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合作新框架,提升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应对国际产能合作的韧性。首先,以培养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质人才为目标。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本质目标不应局限于中国与东盟国家,而应当具备国际化视野和全球竞争力,新质人才是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具备专业技术特质的创新型“塔尖”人才[16]。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新质人才对内表现为其能够熟练运用新技术和工具适应自我岗位的需要,并在不断实践中形塑自我的知识体系;对外表现为其能够敏锐捕捉中国—东盟产能调整的趋势,自主将自我融入变革之中,稳步提升自我的创新能力。对于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而言,以新质人才培养为指引,要通过对系统的课程理念、产教融合、实习实训等环节的优化,扩充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生态体系,进而完善人才的成长途径。其次,坚持跨区域协同治理,实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同向同行。跨区域协同治理是确保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要尊重东盟国家的中心地位,尊重中国—东盟的文化差异,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探索跨区域认同机制、产教融合协同机制、主体协同机制、利益共享机制等,确保各合作主体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应积极利用数字化资源,强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数字平台建设[17],提升新质人才培养的信息共享性,针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人才成长的全生命周期需要,打通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职前教育、职中教育和职后继续教育资源,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新质人才的成长打通渠道。最后,以内涵为归宿,积极探索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类型属性。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是中国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进程中重要的教育类型,其依托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展开而不断深化,实践中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积累了相对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智慧,但在理论研究、经验升华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因为,深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不仅要依据中国—东盟国家的现实基础深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凝练契合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特色的跨区域职业教育合作理论;还要强化人文育人途径,依托来华留学生教育,注重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推进,通过整体构建来华职教留学生培养类型框架、培养过程、保障机制等[18],实现来华职教留学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双向互动,促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走深走实。
参 考 文 献
[1]王屹.共建“一带一路”:全面走向世界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J].职业技术教育,2024(6):1.
[2]陈宝生.教育: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受益者、助力者[N].光明日报,2018-12-13(6).
[3]周敏,马早明.“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23(9):84-91.
[4]黎志东,张鹏.渤海“鲁班工坊”天津职教国际化发展的创新之举——职业教育活动周“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分享[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16):56-62.
[5]自治区教育厅.部区联合推动广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N].广西日报,2023-09-13(9).
[6]外交部.王毅介绍中国东盟合作丰硕成果[EB/OL].(2024-07-27)[2024-07-27].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407/t20240726_11460992.shtml.
[7]广西壮族自治区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海关总署:东盟连续四年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EB/OL].(2024-01-17)[2024-07-26].http://bbwb.gxzf.gov.cn/zwdt123/ywdt_1/t17869963.shtml.
[8]新华社研究院.“一带一路”发展学——全球共同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探索[EB/OL].(2023-10-19)[2024-07-26].http://www.xinhuanet.com/2023-10/19/c_1129924747.htm.
[9]张秋凤,杨满福.“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问题表征与推进策略[J].教育与职业,2021(7):12-18.
[10]王忠昌,侯佳.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建设的现状、困境及路径——基于254个平台的分析[J].教育与职业,2023(4):44-51.
[11]张成涛,张秋凤.“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现实透视与策略构建[J].教育与职业,2020(23):29-36.
[12]王琪,张菊霞.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实践样态与优化策略[J].职业技术教育,2020(27):24-28.
[13]曾茂林,陆潇原.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互动共赢合作机制研究[J].职教论坛,2019(7):165-169.
[14]刘海波.政策评价框架下的规制影响分析[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4(3):12-15.
[15]杨体荣,段寻,吴坚.“一带一路”倡议十年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成就与高质量发展路径[J].比较教育研究,2023(10):39-49.
[16]徐芳,李秉远.新质人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J].人口与经济,2024(4):1-6+18.
[17]周敏,马早明.数智时代深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研究[J].教育与职业,2024(6):32-37.
[18]梁晨,王屹.走好“一带一路”:来华职教留学生培养的理据、困境及路径[J].职教论坛,2023(9):21-29.
High-level Opening-up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ception, Key Points and Paths
——Taking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as the Investigation Objects
Wang Yi,Liang Chen,Chen Yemiao
Abstract" Improving the high-level opening-up system and mechanism is an important requiremen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steadily promoting the high-level opening-up of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deepen the China-ASEA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ory, the high-level opening-up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help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national diplomacy,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build a powerful vocational education country, and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improving the integration policy system as the logical premise, creating a high-quality opening-up platform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the foundation, building a diverse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community as the core task, and building an integrated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opening-up system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refore,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further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at a high-level needs to base on the system thinking and build an institutional policy system of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latform, and steadily expand the new field of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pay attention to ecological shaping, and build an open and collaborative ecological circle of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Key words"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level opening-up;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uthor" Wang Yi,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Guangxi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professor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Nanning 530001); Liang Chen, Ph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Education i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Chen Yemiao, assistant researcher 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