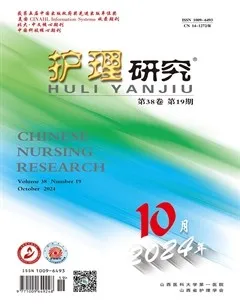社会工作视角下抑郁症病人服药依从性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n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Keywords" social work; depressive; medication complian; problem analysis; practice approach; review
摘要" 通过对抑郁症病人服药依从性进行综述,分析其影响因素包括:病人自身负性评价、疾病认知偏差、自我管理能力不足;家庭支持系统缺失;医疗场域内医患信任缺失及社会资源总量不足,资源配置不平衡与公众偏见。提出医务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践路径包括:帮助病人重塑认知、降低病耻感、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构建病人家庭支持网络;融入医疗场域,发挥社会医护角色的作用;链接社会资源,倡导基层医疗资源配置的优化及提升社会大众的疾病包容度。
关键词" 社会工作;抑郁症;服药依从性;问题剖析;实践路径;综述
doi:10.12102/j.issn.1009-6493.2024.19.022
抑郁症是一种以情绪低落、丧失愉悦感为主要特征,伴认知、行为或自主神经症状,显著影响个体功能的精神障碍[1],具有病程迁延、易复发及间歇性缓解的特点,严重影响病人的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给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医疗负担。世界卫生组织数据表明:全世界约有2.8亿人患有抑郁症,约占人口的3.8%,其中5.0%为成年人[2]。我国精神卫生调查显示,成人抑郁障碍终身患病率为6.8%[3]。抑郁症治疗倡导全病程治疗,包括急性期、巩固期和维持期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及生物物理治疗,其中药物治疗为主要的治疗方法并贯穿于整个治疗周期[4]。《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5]表明,抑郁症复发率高达72.1%,服药依从性为影响抑郁症复发的首位因素。服药依从性是指病人在行为上服从医生处方的程度,即病人要在理解的基础上执行诊疗决策[6]。抑郁症病人服药依从性较低,国外抑郁症病人服药不依从率高达50%~71%[7⁃8];我国抑郁症病人服药不依从率高达65.70%~70.59%[9⁃11]。抑郁症病人服药不依从易导致病人反复发作、延长治疗周期、增加致残和自杀的风险、严重影响其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而规范的药物治疗可以降低74.51%的复发率[12]。因此,抑郁症病人服药依从性问题亟须解决。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着生物⁃心理⁃社会新型医学模式转变,我国现代医学诊疗模式向公益性、服务性、连续性及社会性转变以及人民对健康需求向“提高生活质量”转变。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与个体心理、社会及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因此,在治疗抑郁症病人过程中将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恢复为主要目标,倡导预防、诊疗、康复的全病程治疗,而药物治疗贯穿病人的整个治疗周期,其服药依从性受到广泛关注。病人的服药不依从问题大多出现在院外的预防和康复阶段,而医疗资源多集中于院内诊疗阶段。因此,需回应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医疗场域内欠缺的社会性需求,要求医学与社会科学进行交叉整合,医务社会工作独特的社会性优势可回应目前抑郁症病人所需的社会性需求。基于抑郁症病人服药依从性问题的需求及医务社会工作的优势,现通过分析抑郁症病人服药依从性研究现状对其服药依从性问题进行剖析,并探讨医务社会工作服务抑郁症病人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提高医务社会工作者介入抑郁症病人的服务质量,进而提升抑郁症病人服药依从性,提高临床治愈率,降低病残率、自杀率,促进病人社会功能的恢复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1" 抑郁症病人服药依从性现状
抑郁症的发病率呈逐年升高的趋势,其中大部分为复发性抑郁症,若缺乏系统、持续的治疗,最终可能危及病人生命安全。服药不依从是抑郁症病人普遍存在的健康问题,也是病人复发的重要影响因素,关注抑郁症病人服药依从性问题十分必要。研究表明,简单的健忘、个体内化病耻感、疾病耻辱感、对抗抑郁药物的误解、有药物不良反应、医疗费用为自费、缺乏支持网络、不良的生活方式、不稳定的生活条件、社会适应能力弱、社区保健服务缺失及医患关系差等多种高危因素综合影响导致病人服药依从性差[13⁃16]。然而,目前对于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为横断面研究,尚无定论,仍需进一步探讨。社会心理干预是提高抑郁症病人服药依从性的有效手段,认知行为疗法、精神分析疗法、家庭疗法、多元联动护理、医师⁃药师联合门诊等均可以加强对病人的管理,减少病人减药和停药率[17-19],但其仅对提高短期依从性有效,长期效果目前尚未监测。此外,提高服药依从性的方法多集中于病人的健康教育和信息提供上,然而部分病人即使明确自身疾病及药物知识依然会出现服药不依从现象,精神卫生工作者需探究影响其依从性的真正原因,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帮助其探寻改变的动力,明确治疗内容并与病人达成共识,进而提高病人服药依从性。心理健康专业人员通过沟通和谈判技巧克服病人沟通障碍的效果更显著,医生的干预和指导可能导致病人对治疗的不遵守和敌对态度,而包括药物提醒功能的健康应用程序是提高服药依从性和降低传统依从性干预措施的有效工具[20]。研究表明,移动消息应用程序提醒显著提高了抑郁症病人的门诊就诊率和药物依从性[21]。同时,国内医务社会工作提高服药依从性研究主要针对整个精神障碍病人群体,通过服药管理个案服务、社区开展精神卫生三级预防服务提高病人服药依从性[22⁃23],通过参与多元联动护理小组提供入户探访、社区活动等服务提高抑郁症病人服药依从性[24]。然而,目前对改善抑郁症病人服药依从性仍然缺乏系统、规范的服务标准,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护理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婚姻家庭治疗师作为精神卫生领域的核心服务群体应改善目前碎片化、低水平的服务模式,通过提供整合性、连续性的个性化服务提高抑郁症病人服药依从性,降低复发率和就医成本,减少对医疗资源的浪费。2" 抑郁症病人服药依从性问题剖析
2.1 病人层面——自身病耻感强,存在非理性认知
2.1.1 病人自身负性评价
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与卫生事业的发展,精神卫生服务逐渐规范,社会大众对抑郁症的接受度不断增强,但具体实践中的现实性冲突及刻板印象使抑郁症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仍然背负污名[25],形成一种指向自我的负性评价。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负性情绪体验,一方面,病人会更加否定自我,认为患病是自身心理脆弱及个体无用的表现,并认为自身没有好转的可能性,治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另一方面,病人往往用逃避治疗掩饰自己患病的现实,将服药视为患病的表现,因此通过自行停药的方式营造一种疾病治愈的假象,从而导致了疾病的进一步恶化。
2.1.2 病人对疾病认知偏差
疾病认知是指病人自身对所患疾病的看法,决定其自身行动并影响疾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不同的疾病认知差异对病人适应疾病的程度有不同的影响,这种差异会导致病人不同的治疗态度、自我管理行为[26]。受传统观念、疾病教育缺失、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抑郁症病人对疾病的识别、治疗及康复存在错误认识,欠缺自我管理的意识和技能,不利于疾病的康复。
2.1.2.1 病人缺乏识别疾病能力
尽管抑郁症科普较为完善,但在患病时仍然有部分病人不自知。发病初期,病人通过不断地检查自身的生理指标渴望寻求病因及病情好转,但均未果,反而导致抑郁症的恶化及慢性化,当病人被确诊为抑郁症时通常症状较重或已发生不良事件,从而使病人耽误早期治疗时机、治疗周期延长,进一步加剧了病人的服药不依从性[27]。
2.1.2.2 病人对疾病治疗存在错误的认识
药物治疗作为目前抑郁症最主要的治疗方式,虽不能从根本上治愈抑郁症,但其可以有效地消散或缓解抑郁症状。因此,治疗中应遵循个体化及联合治疗并保障病人足量、足疗程用药[28]。而病人对抗抑郁药物的作用方式、起效时间、服药周期、停药减药指标、药物副作用等认识不科学,治疗过程中担心自身服药成瘾或个体药物副作用明显,且缺乏科学、合理的应对方式便自行停药。而抑郁症间歇性缓解的特点,使得部分病人在症状减轻时自行减药或停药,症状加重时自行加药,不规律服药使得病人体内血药浓度紊乱导致病情复发,复发次数的增多易导致疾病的慢性化,增加治疗的难度,造成终身服药的不良后果。
2.1.2.3 病人欠缺预防疾病能力
抑郁症需要坚持足量、足疗程的治疗,要求抑郁症病人在治疗期间遵医嘱规律服药,同时对自身的健康信息和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和预测[29]。通过科学合理的服药、饮食、运动、生活、社会适应及心理调适进行预防,并有效地利用自身资源使得健康效果达到最大化[30]。在具体实践中,病人并未将其视为疾病康复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急性期过后,病人的症状减退或消散,通常可以恢复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病人对疾病的关注度降低,病人开始漠视医嘱、拒绝规律服药及复查,并出现作息不规律等不良的生活方式,淡化医生对其日常行为的指导,增加了复发的风险。
2.2 家庭层面——家庭支持系统缺乏
家庭成员是抑郁症病人康复过程中最有力的联盟,其参与病人护理可改善病人的服药依从性[31]。部分家庭成员消极的应对方式加重了病人的治疗负担[32],具体表现为对疾病的接纳和认识不足及恶化的家庭关系。由于抑郁症存在病因及病理机制尚未明确、治疗周期长且预后模糊等特点,部分家庭成员在病人确诊后出现排斥或逃避的心理,加上病耻感、经济负担及迷信观念等多重压力的影响,出现要求病人终止治疗、停止服药等行为表现,从而降低病人的服药依从性。此外,由于抑郁症的发生可能与遗传、负性生活事件及童年经历等方面相关,因此在确诊患病后部分家庭成员会陷入自责或相互指责的恶性循环中,加剧了病人的愧疚感,从而降低了其治疗的依从性。
2.3 医患层面——医疗场域内医患信任缺失
医患信任是指病人在疾病诊疗过程中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医患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3]。良好的医患关系在抑郁症诊断、治疗、康复及预防过程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医疗场域内“医患信息差”及“病人多样化需求无法回应”等问题加剧了医患不信任,影响病人治疗的积极性。精神科医生有专业的医学知识及临床经验,对疾病的治疗有清晰的认知及整体的把握,而病人及家属仅能通过查阅资料、询问亲友及同事等方式对疾病进行揣测。当病人及家属对疾病快速治愈的渴求与医生的治疗节奏冲突时,医患信息的不对等激化了医患不信任,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产生抗拒医生治疗措施的心理及行为。此外,缓解症状、预防复发已经不能满足抑郁症病人的治疗需求,消除功能障碍及改善生命质量的健康诉求。然而,医疗场域内多学科服务的缺失,使得病人的多样化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进而降低了其治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4 社会层面——社会资源缺乏与公众偏见
社会是抑郁症康复的重要场所,然而医疗资源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以及公众的偏见影响了病人康复的进程[34]。复查是抑郁症病人治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精神科医生多集中于市级以上医院,基层精神卫生护理资源缺失造成了病人就诊不便,长期的奔波引起了病人的厌倦感从而中断了复查与服药。同时,社区缺乏对抑郁症病人的管理与检测服务,未帮助病人顺利适应出院后的过渡期和提供病人服药的提醒和监测服务。调查显示,超过70%的被调查者对精神疾病病人存在污名态度[35]。在院外的治疗过程中邻居、同事及亲友在背后对病人的患病原因及服药行为进行“指点”,为了避免自身语言、行为激化病人病情牵扯自身而刻意疏远病人,“身份的标签”加剧了病人的病耻感使其丧失治疗的信心,产生抗拒服药等拒绝治疗的行为。
3" 社会工作介入抑郁症病人服药依从性路径探析
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具有学科整合性的特点,是基于“大健康”理念和现代医学模式基础上的整合[36]。通过学科知识和实践理论的整合,医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理论知识、方法和技巧能改善抑郁症病人治疗过程中来自个人、家庭、医疗场域及社会层面的压力导致的服药依从性问题[37]。社会工作介入抑郁症病人的实践路径包括:帮助病人降低病耻感、重塑认知、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改善病人家庭关系,构建家庭支持网络;融入医疗场域,发挥社会医护角色的作用,打造多学科协作服务模式;链接社会资源,倡导基层医疗资源配置的优化及提升社会大众的疾病包容度。
3.1 社会工作介入降低病人病耻感,解构不合理认知
病人是疾病康复的第一责任人,其消除病耻感、构建疾病的正确认知、提升自我管理能力是坚持科学治疗的重要因素。社会工作者通过专业的方法和技巧为病人开展服务,帮助病人接纳、认识和管理疾病。
3.1.1 提高病人自我认同感,降低病耻感
社会工作者在修正标签理论、正念认知疗法、精神分析疗法等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结构化”对话的方式,运用举例、积极关注、角色扮演及放松练习等具体手段,唤醒病人潜意识的力量,积极引导病人自我赋权,鼓励病人摒弃病耻感的错误认知,学习合理方式,激发病人疾病治疗中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3.1.2 解构病人不正确认知,提升自我管理能力
社会工作者运用认知行为理论、小组动力学理论等方法,与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及康复师等专业人员共同成立多元联动小组,帮助病人了解疾病的相关知识。通过科普讲座、座谈交流等方式,使病人了解抑郁症病因、表现方式、治疗周期、复发征兆、抗抑郁药物作用机制、副作用及其应对方式等,掌握抑郁症及抗抑郁药物的相关知识。运用自我表露、示范引导、聚焦及强化等技巧,引导病人解构自身关于疾病识别、治疗及康复的非理性认知方式,协助病人重塑对疾病的正确认知。同时,运用优势视角、任务中心模式等理论,关注病人生理、心理及社会的多重恢复指标。开展抑郁症健康教育主题活动,提供关于服药管理、日常康复训练的培训,提高病人日常健康维护的个人意识和与疾病共存的日常生活能力。通过个案咨询、互助小组的形式,帮助病人掌握服药的正确方法,学习促进疾病康复及预防的健康生活方式,为病人提供适应性训练、技能训练强化病人行动,提高其自律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增进治疗的效果和疾病适应状态,提高病人的服药依从性。
3.2 社会工作介入提高病人家庭抗逆力,构建家庭支持网络
应对抑郁症治疗、坚持服药并不是病人个体治疗的过程,而是整个家庭系统的适应过程,抑郁症病人应对疾病时与家庭是一个整体[38]。家庭成员对病人疾病的排斥与逃避及恶化的家庭关系大多来自对疾病治疗的恐惧,其异样行为会降低应对疾病及看护的能力,不利于病人积极参与治疗[39]。社会工作者引导病人家庭成员的自我意识觉醒,正视病人疾病,提升抗逆力、强化家庭支持系统。
3.2.1 降低疾病恐惧,增强家庭抗逆力
社会工作者以个案会谈的方式,运用同理心、倾听、放松练习等技巧关注家庭成员,鼓励其宣泄负面情绪、减轻照护压力。在优势视角等理论的指导下,邀请精神科医生、康复治疗师及榜样家庭为病人家庭成员开展家庭健康教育专题讲座和座谈会,增强家庭成员对于疾病、服药、病人照护的认识,树立疾病治疗的信心。通过家庭作业的方式,引导家庭成员在与病人的日常互动和照护中进行强化训练,提高家庭成员的照护质量和问题解决技能,同时也让病人感受到家庭成员对于疾病治疗的信心,进一步提升病人的服药依从性。
3.2.2 改善家庭关系,强化家庭支持系统
社会工作者在行为学习理论、家庭治疗模式等理论指导下,在治疗过程中应重点考察家庭成员应对抑郁症的方式,并引导家庭成员觉察当前沟通方式、行为表现对病人疾病治疗带来的不良影响。运用家庭照顾、再标签及动机访谈、问题外化等技巧,引导家庭成员摒弃以往对于抑郁症的消极态度和看法、习得与病人积极的沟通方式和行为;鼓励家庭成员将病人患病看作是整个家庭需要共同解决的难题,让家庭成员从相互指责转变为共同对抗疾病,从而促使家庭成员间建立积极的沟通交流方式,完善病人的家庭支持系统。
3.3 社会工作介入构建医患信任关系,发挥社会医护角色作用
医疗场域是关乎病人健康的社会系统,良好的医患关系、多元化的医疗服务对病人积极治疗有促进作用。社会工作者是医疗场域内“全人照顾理念”的补充,应明确自己的专业角色并运用专业技巧影响病人、医护人员,协助医患消除信任危机,满足病人的多样化需求。
社会工作者作为医疗场域内重要的“沟通者”,从第三方为视角出发整合精神科医护人员、心理咨询师、康复师等形成多学科联动团队,提供心理关照、咨询、知识讲座及危机干预等服务,提升病人及家庭成员对疾病的认识;运用空椅子、反应、表达等技巧,通过病人与医护人员的互动,消除医患不信任、沟通不通畅等诊疗危机。此外,社会工作者与心理咨询师为医护人员开展减压赋能、沟通技巧小组服务,帮助其释放压力,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增进医患关系。同时,社会工作者应以病人为中心,调研并评估病人生理、心理及社会等多方面的需求,利用个案或小组社会工作的形式,组织并协调多元联动团队为病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在协助病人缓解症状、预防复发的基础上,通过认知训练、呼吸训练、康复训练帮助病人消除功能障碍和提高生活质量,并用家庭探访、电话咨询等方式将医疗服务延续到病人的日常生活中,满足病人的多样化需求,进而提高病人治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4 倡导医疗资源配置优化,提升疾病的社会包容度
优化基层精神卫生资源配置,提高精神卫生资源的可及性及减轻社会大众对疾病的偏见是病人坚持家庭康复的重要条件。社会工作者通过促进基层社区卫生服务医院和市级以上精神专科医院或三级甲等医院精神科医疗资源的整合,搭建医院⁃社区⁃社会一体的诊疗模式,扩大医疗服务范围,减轻医疗服务碎片化和不连贯的问题,回应病人在康复过程中健康管理的需求,缓解病人“复查难”“看病难”等问题。同时,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开展精神卫生护理知识、沟通技能的培训,引进以数字化为基础的介入措施,例如智能药盒、计算机视觉系统、可摄取生物传感器等电子检测设备;手机短信服务、电话干预、手机APP等移动设备;交互机器人等,为病人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提醒和监测服务,完善医患沟通的途径,提高服药依从性[40]。此外,搭建心理健康宣传网络,将抑郁症纳入社区宣传,加强对抑郁症病人康复的正面报道,提升居民心理健康素养,破除抑郁症污名化和偏见,提高社会大众对抑郁症病人的接纳度,营造友好健康环境。
4" 小结
综上所述,服药依从性是抑郁症病人全病程治疗过程中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对病人疾病康复、治疗周期、生活质量等都有重要影响。改善抑郁症病人的服药依从性,单纯靠病人个体的努力远远不够,更需要家庭、医疗场域及整个社会共同协助。社会工作者应发挥专业优势,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不干扰正常诊疗”为原则[41],协助医护人员与病人、家庭成员共同剖析导致病人“服药不依从”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因素。整合医疗资源提供专业、个性化的整合性服务,旨在解决病人医学范畴之外的社会问题,提升病人的服药依从性,降低复发率,改善生活质量,满足病人的整体健康需求,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参考文献:
[1]" 《中成药治疗优势病种临床应用指南》标准化项目组.中成药治疗抑郁障碍临床应用指南(2022年)[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23,43(5):527-541.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Depression[EB/OL].[2023-10-04].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depression.
[3]" 医政医管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年版)的通知[EB/OL].[2023-10-03].http://www.nhc.gov.cn/yzygj/s7653p/202012/a1c4397dbf504e1393b3d2f6c263d782.shtml.
[4]" 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等.抑郁症基层诊疗指南(2021年)[J].中华全科医师杂志,2021,20(12):1249-1260.
[5]" 健康时报网.《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发布应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EB/OL].[2023-09-09].http://www.jksb.com.cn/html/life/psychology/2022/0704/177205.html.
[6]" 张佩,夏勉.抑郁症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及影响因素[J].心理科学进展,2015,23(6):1009-1020.
[7]" SEMAHEGN A,TORPEY K,MANU A,et al.Psychotropic medication non-adherence and its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patients with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Syst Rev,2020,9(1):17.
[8]" BAEZA-VELASCO C,OLIÉ E,BÉZIAT S,et al.Determinants of suboptimal medication adherence in patients with a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J].Depress Anxiety,2019,36(3):244-251.
[9]" 涂艳,谢小云.抑郁症患者药物治疗依从性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23,20(1):107-111.
[10]" 王维,蔡幸芳,谢雪华.抑郁症患者抗抑郁药服用依从性与抑郁症状改善程度的相关性分析[J].心理月刊,2023,18(10):123-125.
[11]" 徐丹,周建军,禹婷婷,等.住院抑郁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及影响因素研究[J].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22,15(1):157-160.
[12]" 马玉娟,鲁陆.抑郁症患者院外服药依从性的影响因素与复发情况研究[J].健康之路,2017,16(7):7.
[13]" UNNI E J,GUPTA S,STERNBACH N.Reasons for non-adherence with antidepressants using the Medication Adherence Reasons Scale in five European countries and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2024,344:446-450.
[14]" [SHI J M,CHEN Y,JIANG Y C,et al.Stigma and its associations with medication adherence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J].Psychiatry Research,2024,331:115664.
[15]" CHONG W W,ASLANI P,CHEN T F.Health care providers' perspectives of medication adher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a qualitative study[J].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2013,48(10):1657-1666.
[16]" 龚婕,叶飞强,谢少玲,等.抑郁症患者服药依从性与家庭关怀度、病耻感及社会适应能力的关系研究[J].今日药学,2023,33(11):870-873.
[17]" XU S,LIU B,ZHANG Y.Effectiveness of mental therapy for poor medication adherence in depression:a review[J].Tropical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2020,19(8):1785-1792.
[18]" 罗春雪,袁朝霞,金翠梅,等.多元联动护理对抑郁症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干预研究[J].护理管理杂志,2022,22(8):550-554.
[19]" 万萍,史晓晓,吴剑虹,等.医师-药师联合门诊对抑郁症患者服药依从的作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1,35(1):8-12.
[20]" DEL PINO-SEDEÑO T,PEÑATE W,DE LAS CUEVAS C,et al.Effectiveness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a multicomponent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medication adherence in people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s--MAPDep:a study protocol for a clus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Patient Prefer Adherence,2019,13:309-319.
[21]" LOW P T,NG C G,KADIR M S,et al.Reminder through mobile messaging application improves outpatient attendance and medication adherence among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an open-label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The Medical Journal of Malaysia,2021,76(5):617-623.
[22]" 莫绫轩,李财君,覃英华.个案工作介入康复期精神障碍人士服药管理研究[J].社会与公益,2021,12(2):24-26;30.
[23]" 黄丹琪,施征宇,汪作为,等.社会工作在社区精神卫生三级预防中的作用[J].安徽预防医学杂志,2022,28(4):298-301.
[24]" 杨晶晶,徐柯柯,刘曦琼.多元联动护理联合正念减压对抑郁症患者服药依从性、正念水平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航空航天医学杂志,2024,35(1):114-117.
[25]" 丁艳虹,董强利,张兰.不同人群对抑郁症的认知及污名化态度的研究进展[J].新医学,2023,54(1):7-12.
[26]" 王丽婷,李强,魏晓薇,等.抑郁症患者疾病认知与自我护理的关系:希望和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1,29(4):744-747.
[27]" 周莉,曾如双,刘肇瑞,等.首发的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及双相障碍的治疗延迟(综述)[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4,38(1):50-54.
[28]" 苏红.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与常用抗抑郁药物的研究现状及进展[J].现代医学与健康研究电子杂志,2023,7(21):16-19.
[29]" 高英莉,张霞,申鲁霞,等.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抑郁症自我管理干预的研究进展[J].现代医学,2023,51(5):703-707.
[30]" 陈丽.支持型自我管理在抑郁症患者康复期的应用效果[J].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2019,4(33):165-167.
[31]" 张蕊.家庭护理干预对抑郁症患者预后的影响[J].心理月刊,2020,15(16):43.
[32]" 李展.基于医务社会工作对提升学龄前肿瘤患儿就医依从性的思考[J].现代医院,2022,22(10):1544-1547.
[33]" 张莉,荣芳等.北京市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医患信任现状调查[J].医学与社会,2020,33(1):85-88.
[34]" 马达飞,张蕾,高翔,等.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情况及发展建议[J].中国卫生人才,2023(1):16-21.
[35]" 江光荣,李丹阳,任志洪,等.中国国民心理健康素养的现状与特点[J].心理学报,2021,53(2):182-201.
[36]" 杨卿,齐建,闫智楠,等.医疗场域内医务社会工作整合服务的社会性优势和实践路径探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23,36(8):859-865.
[37]" 中国社会工作编辑部,汪昊.社会工作助力精神康复[J].中国社会工作,2022,(13):9.
[38]" 齐建,于玲,王素明,等.青少年精神障碍者日常生活实践的失序与重塑[J].医学与哲学,2022,43(6):52-56;68.
[39]" 赵月琰,缪群芳,仇凌晶,等.青少年抑郁症病人及主要照顾者疾病体验的质性研究[J].护理研究,2024,38(4):740-745.
[40]" 翟倩,闫芳.数字化技术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药依从性中的研究进展[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23,23(8):583-592.
[41]" 齐建,王素明,李文言.医务社会工作对医疗场域需求的回应分析[J].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2020,27(6):564-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