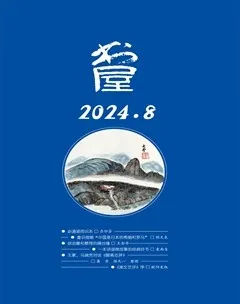诗人的情怀
方孝孺(1357—1402)是明初一代大儒,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他在南京殉道后,门人将其遗骸埋于南京雨花台梅岗,将其遗作编成《逊志斋集》。
方孝孺短暂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不朽的精神财富。《逊志斋集》中存有他的诗歌四百余首,既有咏史诗,感喟历史的多舛;也有诸多写景抒情诗,写得清新、脍炙人口;更有一些诗章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民生疾苦,例如这两首:
蕨箕行
并海饥民千百数,携锄上山斸山土。
蕨根已尽斸不休,力绝筋疲未言苦。
屋头五日无炊烟,十步九却行不前。
全家性命系朝暮,弱子假息阿母眠。
昨日斸蕨仅盈斗,今日蕨根不满手。
但凭斸蕨保余生,再拜青山感恩厚。
青山青山尔勿猜,明朝未死携锄来。
海米行
海边有草名海米,大非蓬蒿小非荠。
妇女携篮昼作群,采掇仍于海中洗。
归来涤釜烧松枝,煮米为饭充朝饥。
莫辞苦涩不下咽,性命聊假须臾时。
皇天不仁我当死,况乃催科急如矢。
来牟拟作日月期,欲保余生更徯尔。
呼呼弃止不复陈,椎牛酣酒何为人。
虽非荒年,海边饥民却成群结队上山挖蕨为食,艰难度日,“但凭斸蕨保余生”。采海草为食者,也是活一天算一天,“性命聊假须臾时”,不定哪天就突然被饥饿夺去了生命。这是血泪的控诉。不是荒年,仅此一地,就有“千百数”的“饥民”,那全县、全州、全府、全省乃至全国,该有多少饥民!原因何在?作者尖锐地道出原因:“皇天不仁我当死,况乃催科急如矢。”虽然这里的“皇天”从表面看不是指统治者,其实指的就是当朝!读到这里,读者也就恍然大悟:原来这么多“全家性命系朝暮,弱子假息阿母眠”的饥民,是朝廷的急征暴敛所致。
方孝孺的这两首诗与白居易的《卖炭翁》《杜陵叟》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思想性来说,也绝不逊色。
“并海饥民”这个典型所概括的,当然不只是“并海”一地的”饥民“,而是千百万平民的共同遭遇。诗中大段描写“饥民”以野生蕨类植物果腹,聊以活命,时当“文字狱”肆虐,敢于如此慷慨激昂地为人民鸣不平,不能不使我们敬佩作者的勇气。对官府的重租催逼、横征暴敛,方孝孺在诗中着墨不多,仅此“催科急如矢”五个字,殊属画龙点睛之笔,读之使人豁然明白。
至于“蕨根已尽斸不休,力绝筋疲未言苦”“莫辞苦涩不下咽,性命聊假须臾时”,更是催人泪下的佳句,真切地表现了方孝孺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所寄予的深切同情。“但凭斸蕨保余生,再拜青山感恩厚”,则十分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已经濒临生存绝境的“饥民”所能有的全部希望,这也是唯一剩下的一点求生希望。读此联,心中有种难以名状的沉重感。但凡是人,只要人性尚未丧失殆尽,就不能不作思考;倘若统治者了解此种情况,甚至明知道大量饥民饿死,仍然无动于衷,并继续横征暴敛,只能说他们已经不是“人”了。
朱元璋统治时期是不准农民随意流动、离开家乡的,农民外出须持有一种叫“路引”的证件,否则一旦为巡检司查获,即送官严办。朱元璋的这套统治手段,不仅窒碍了社会流动产生的勃勃生气,而且严重阻滞了经济流通。在封建专制政治体制下,全社会文明的按钮就控制在一人之手,社会的进步与否取决于最高统治者一人的行为决策。明代的这种制度实在再荒谬不过了。所以钱穆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否全由一个脑袋决定,各级官吏、全国人民都可以不思考。这就是方孝孺上述诗文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孟子说农民“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死亡”,也只能是“王道”政治下的小农经济生活的图画。方孝孺诗中关于民生疾苦的描写,其实正是对孟子所言事实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历史上灾荒严重之时,皇帝往往下诏蠲免租税,可颇常见的是地方官为了“政绩”,为了乌纱帽,为了加官晋级,往往置中央政府的命令于不顾,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加紧勒索,甚至超额完成征粮征税的“任务”,更有从中贪污救灾粮款的。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断上演,从未绝迹。苏东坡在《应诏言四事状》中说的“四方皆有‘黄纸放’而‘白纸收’之语”(黄纸指皇帝的诏书,白纸指地方政府的公文),即指当时蠲免政策与实施上的两面性。如用最通俗的话为苏东坡此语作个注解,就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坏了”。
范成大的《后催租行》里所描写的“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朱继芳《农桑》描述的“淡黄竹纸说蠲逋,白纸仍科不稼租”,说的都是蠲租问题的两面性。
明初,朱元璋也采取了不少蠲免租税的措施,下过许多诏令。然而,地方政府的官吏往往上下串通一气,“相习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府,奸弊百端”。一级骗一级,从下往上骗,中央政府给予农民的优惠,往往落到地方豪富和官吏的头上。这类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官吏们常用的贪腐手段,亦足以说明这不是官员胥吏们的个人道德品质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何况朱元璋反腐还带有自己的政治目的——翦除功高震主的开国元勋与手握重兵的将领,使江山社稷稳稳当当地传至子孙,千秋万代永远姓“朱”。
方孝孺的“催科急如矢”一句,有力地揭穿了这种瞒上欺下行径。关心百姓疾苦,予以现实主义的表现,但面对残酷的现实,却又无可奈何,使得方孝孺的诗歌平添了一分沉重的苦涩。
他忧国忧民,却无法施展抱负,匡正时弊,这种苦恼在他的《闲居感怀》诗中有淋漓尽致的表现:“我非今世人,空怀今世忧。”“哀哉万年后,谁为斯民谋?”翻开二十四史,能发现一种现象,只要还没有被异化,士大夫们大都有对弱势民众的人文关怀。
方孝孺的这类诗歌大多文辞朴实,很少用典,所以写得真切感人,让人有一种目睹现场的感受。
在方孝孺的四百余首诗歌中,占篇幅很大的,除酬答之作外,还有一些抒写个人情志的作品,主要是山水诗。这些作品题材很广泛,因为感从中来,情意真切,韵味很浓,不乏“绝类唐宋人的佳作”。
在一首名为《题山水》的古诗中,方孝孺写道:“昔隐林壑中,不知林壑美。今年在城阙,见之心辄喜。枫林新受霜,茅茨隔秋水。安得呼扁舟,遨游五湖里。”
起首两句,读了就不免令人想起苏东坡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紧接着的两句,看似平淡,直抒己见,然而细细品味全诗,一个“喜”字却让人有一种情感突兀而至。原本不知林壑美,可见了城阙,“美”就被衬托出来了。城阙有城阙的美,林壑有林壑的美,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美。一种是大自然的美,与生俱来,天造地设,不事雕琢;一种是人工的美,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巧夺天工。但人为的美,终不敌自然的美,于是作者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安得呼扁舟,遨游五湖里”的感慨。
诗写得自然流畅,没有刻意追求辞藻的华丽,也没有着意用晦涩难懂的典故。
“游五湖”典出春秋末的范蠡,他功成身退,经商致富,又散尽万贯家财,驾扁舟,游五湖,隐居不仕。不过范蠡驾扁舟,游五湖是不得已的选择,未必会有方孝孺诗中喜爱山水、崇拜自然的情趣。“枫林新受霜,茅茨隔秋水”,这大自然是何等的美!“遨游五湖里”,这又是何等的乐!陶醉在大自然的真实之美中,其乐无穷尽。这既是写意,也是写实。他羡慕范蠡,欲效而不能,是否也含有对政治、对自己前景的失望?
寒梅冻后放幽恣,何事今年花较迟?
昨日途中春意到,溪头才见两三枝。
这是方孝孺的一首咏梅诗《见梅》,写得清新、亮丽、蕴藉,刻画了梅花傲寒的品性、素艳的风韵。作者以此寄托自己迟迟未被起用却矢志不移,迟早要“放幽恣”的自信,表现出与《题山水》不同的思想情怀。诗不长,仅短短的四句,语言清润平淡,毫无纤秾之气、雕琢之痕。方孝孺在诗中突出了梅花不畏严寒、傲然独放的个性特征,创造了一种高远的意境,从而将诗人的志向蕴藏其中。
绝世丰姿不受尘,丹霞为质玉为神。
渚禽莫怪开时晚,一洗寻常草木春。
这首吟荷诗,描写的是客观存在着的具体事物形象,可是这事物形象在艺术上的再现,则是诗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感觉描绘出来的,多少带有一种借景抒情的意味。以抒情的心理咏物,于是,物中有情,情中有物,两相浃洽,融为一体。古往今来,写荷的佳诗颇多。方孝孺的这首咏荷诗,不仅写尽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含蕴之意,而且把“绝世风姿”写得玲珑剔透,寄寓了深刻的意蕴。
今人选咏荷诗的集子,笔者见过几种,未见到有选方孝孺这首咏荷诗的,而所选咏荷诗,多不及方孝孺的这首。如有个本子选了唐代诗人高蟾的咏荷诗《芙蓉》:“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后开。”远不如方孝孺的这首荷花诗。这个本子还选了宋朝王安石的咏荷诗:“水边无数木芙蓉,露染胭脂色未浓。正似美人初睡着,强抬清镜照妆慵。”诗把出水芙蓉比作刚刚睡醒的美人,诗写得美,在该选本中,王安石的这首最好,但与方孝孺的这首比起来,笔者认为还是后者更佳。
方孝孺生活的时代,正值明王朝创建不久,故而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朱元璋励精图治,然而并未达到他所预期的效果。他屡次掀起反贪巨潮,却始终未能杜绝“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的腐化现象。对此,朱元璋也感到困惑不解,他说:“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有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贪腐屡禁不绝,是鱼池里的水有问题,不是鱼的问题,朱元璋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而追求权势富贵的政府官员在淤泥里绝对成不了“出水芙蓉”。方孝孺这首咏荷诗,正是他对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的诚挚赞美。
方孝孺的一些咏物写景诗,都写得情韵天然,清丽雅致。如:“残月堕遥天,凉风在高树。人行野色分,鸟啭崖光曙。川平惬幽眺,境胜遗尘虑。日出小舟横,依依杨柳渡。”
又如:“窗开觉山近,院凉知雨足。淡月透疏棂,流萤度深竹。心空虑仍澹,神清梦难熟。起坐佛灯前,闲抽易书读。”
再如:“烟鸟归林已夕阳,野人相引度高冈。马头一片青山影,经过絺衣似水凉。”
而他的《题画》与《牧牛图》两首古诗,各短短二十四字,都极见情趣,特别是后者。《题画》:“茅屋东屿西屿,白云前山后山。为报溪头流水,落花休出人间。”
《牧牛图》:“谷口惊湍雨歇,柳阴芳草春还。试问太平乐事,夕阳牛背青山。”
方孝孺的《牧牛图》是一首古体诗,与元代马致远的散曲《秋思》在阅读体验上好有一比。《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当然二者是有区别的,首先在情调上是不同的,前者轻松愉悦,后者深沉古朴。另外《牧牛图》是题画诗,写实,表现的是太平时期社会稳定,人民悠闲自得;《秋思》是将十一种意象巧妙地连缀在一起,蕴藏着诗人思乡思归的感慨。
《牧牛图》以二十四字描绘了春日的暮色。作者以景物点染“春”,全诗虽无一“人”字出现,却以景物衬出了“人”。且诗着力写景,景中有情;侧面抒情,情中句句皆景。妙合无垠,天衣无缝。《牧牛图》虽不如散曲《秋思》有名,然也不失为一首传世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