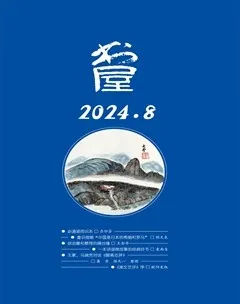《旧制度与大革命》译后记
按时完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翻译工作,我长长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这本书并非大部头的论著,篇幅相对较短,但是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作为译者就颇有顾虑,事实也证明翻译过程并不轻松,为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工作,译者必须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经典名作,已经存在若干译本,重译名著本身对译者来说就是一种挑战,有著名译本的珠玉在前,译者在着手翻译之前就会感到无形的压力。
其次,本书于1856年在法国出版,书中描写的法国社会更要追溯到1789年大革命之前。所言之事发生在二百多年前、距中国八千公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所以,书中提到的法国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行政机构、社会环境、人物事件等诸多方面对于译者来说相对陌生。虽然现在处于信息社会,资讯发达,但是译者仍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去查找资料、了解背景,才能顺利完成翻译工作。
再次,本书出版于1856年,恰好在那一年,清王朝和英法两国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末年距今年代久远,当时的汉语和现代汉语存在不小的差别,以此类推,没有学习过法语的读者也不难想象,当时的法语和现代法语的差别恐怕也不遑多让,所以对于译者来说翻译难度相应增大。单纯从文字出发,译者阅读原文、正确理解作者本意更加困难。
最后,就是翻译工作的时间限制。当今翻译市场普遍以“多快好省”为标准,很多翻译项目把时间压缩得很短,不利于译者安心工作,从长远看也不利于保证译文的质量。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却能够逆“唯效益论成败”的潮流,专注于作品本身。负责本书的董曦阳编辑充分信任译者,给予充足的时间,从不施加压力。对此,我感到十分幸运,更希望借此机会表达深切的谢意。
回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本身,作者在前言部分开宗明义,说明创作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记录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而是研究大革命这个给法国乃至世界带来深刻影响的历史事件。作者查阅了法国旧制度时期留下的海量档案资料,包括土地赋税清册、三级会议记录、陈情书、赋税记录、官员通信等,以坚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从中提炼、总结出旧制度的特点,分析大革命为什么在法国爆发、大革命为何呈现如此走向,以及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社会等主题。作者希望在这部作品中把历史和哲学结合起来,对这段历史做出思考与评价。
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家庭,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头衔,担任过众议院议员、外交部长等职务,亲历过众多法国历史的重大事件,本书是他的“立言”之作。在本书的前言中,托克维尔表示准备创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二部,并写出了部分草稿。但是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有时个人的命运要比民族的命运更加难以揣测”,托克维尔未能如愿,在本书出版三年后即1859年因病去世。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历史学上的价值和对今人的启示作用毋庸置疑,我在此不想赘述。就我个人来说,翻译本书时,某些片段引发了自己的一点思考。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中提到了中国,我作为中国人自然对这部分内容格外关注。书中讲到法国重农学派一厢情愿、理想化地看待中国:“在中国,专制的君主不持偏见,每年一次亲自躬耕,向农业这类实用艺术表示敬意;一切官职要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视为贵族。”重农学派觉得中国模式是法国政府应该效仿的完美典范。而作者对此不以为然,对清朝末年的中国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政府被一小撮欧洲人随意摆布,实际上既野蛮又愚昧。”此外,作者对美国从英国继承下来的自由思想和自治制度评价道,美国把“英国式的分权制度发扬光大:市镇变成了几乎独立的市政府,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民主共和国”,“政府几乎不介入任何事务”。并且通过在加拿大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人口的悬殊对比(“1763年,也就是在征服时期,加拿大法属地区的人口是六万人,英国殖民地各省的人口是三百万人”)加以证明。
在这里,法国重农学派对中国制度的憧憬,托克维尔对美国自由的推崇,似乎都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当然,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异。重农学派认为当时的中国制度完美无缺并没有多少真凭实据,只是凭借想象,托克维尔则对美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在1831—1832年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游历美国,而后创作了学术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尽管如此,二者似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心理学“晕轮效应”的影响。这种心理学现象指的是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从局部出发然后扩散得到整体印象,比如看到某人的优点之后就认为这个人完美无瑕,“以偏概全”“爱屋及乌”都是这种心理效应的具体表现。加上人们在各自的生活中会遭遇到种种挫折与不公,因此感到不满,于是倾向于认为远方未知的事物更加美好。
这种现象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清朝末年,古老的中国遭遇进入工业化文明国家的侵略;抗战时期,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新中国成立之初,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百余年来处在内忧外患之中,贫困如影随形,始终伴随着中国人民。而后,历经十年浩劫,中国迎来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国人生活水平欠佳,面对西方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自然心生羡慕。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国力如日中天,通过美元、美军、美国流行文化称霸全球,当时的一些国人尝到了美国的麦当劳,用到了美国的计算机系统,看到了好莱坞的大片,接触到了美国的物质享受,于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无限向往,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屑一顾。直到今天,飞速发展的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迈入了小康社会,但这种思想并没有绝迹。其实部分国人对外国盲目崇拜的思想和本书中法国重农学派对中国政府的幻想、托克维尔对美国自由的欣赏颇有共通之处。时至今日,中国国家强大,人民生活幸福,反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撕裂,危机重重。当年号称民主世界灯塔的国家,现在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亲手打破自己创建的国际规则,无所不用其极,其为自己树立的道德典范形象尽失。
其实,面对他者的优秀,大可不必盲目崇拜、羡慕、垂涎,乃至摇尾乞怜,希望得到一点残羹冷炙,绝对不会赢得幸福与尊重。正确的做法是虚心学习他人的长处,励精图治、奋发图强,靠自己的努力迎头赶上。我国传统文化早就讲出了这个道理,留给后人无数的名言警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个人希望成功需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国家要想强盛又何尝不是如此。托克维尔笔下清末的中国政府“被一小撮欧洲人随意摆布”,“既野蛮又愚昧”,而今天的中国强大而自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通向复兴的这条道路漫长而曲折,正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的国人凭借一腔热血,发挥聪明才智,挥洒汗水、流尽鲜血,方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清代的思想家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长处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如今时过境迁,国际形势已经迥然不同。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华文化要走出去,促进世界文化的欣欣向荣;同时中国也要选取优秀的外国文化产品,汲取养分,滋养中国文化。《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作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与知识宝藏的一部分,通过翻译进入中国与读者见面,今天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大力推动下得以重译,正是文明互鉴的具体表现。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本书获得所需的知识,而且能够将知识为己所用,不但获得前辈先贤留给后人的知识宝藏,还可以自出机杼,从中得出属于自己的感悟。
由于本人的才学与能力所限,对托克维尔在书中反映的思想可能存在误读,表达或许有不妥之处,译文难免存在错误、疏漏,欢迎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