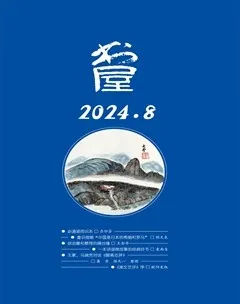《崖山》后记
大概在中学时代,我第一次听到“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当时自然是热血沸腾,充满了对蒙元的仇恨,更鄙夷的是“灭宋于此”的大奸臣张弘范。
我想,很多人在阅读南宋亡国史时,都曾经被带入这样一种情绪当中。
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之常情,一个伟大且精致的中原文明被门口的游牧民族毁灭,怎么说起来都令人扼腕叹息。
但是,历史毕竟不仅仅是情绪,或者说,不能由单一情绪主导。民族主义叙事是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宜成为唯一叙事。
在某些方面,“崖山之后无中国”自有些许道理,但不是唯一道理。
尽力避免单一的民族主义叙事,这是我写作《崖山》这本书的初衷之一。毕竟,写作是一件苦事,没有一点情怀驱动,很难宵衣旰食。
我想尽力规避的第二种叙事,是南宋中心主义叙事。
好看的历史应当是有多元视角的,但具体到南宋亡国这段历史,流行的历史叙事往往都是聚焦于南宋视角,从而遗忘了一个常识:南宋衰亡史的另一面,是元帝国的崛起史。
于我而言,写作《崖山》最大的难点也是蒙元史。在历史学科内部,蒙元史可能是最让写作者有“隔行如隔山”之感的断代史。但再难再有压力,我都一直提醒自己:既然要写《崖山》,写南宋亡国史,怎么可以不去努力深入学习探究蒙元史呢?
缺乏蒙元视角的南宋衰亡史,天然就容易堕入单一的民族主义叙事。
我不讨厌宋朝,在某种意义上我也算是一个“宋粉”,宋朝政治相对其他帝制时代的宽容与开放,令人心生向往,令我心甘情愿地“牺牲”部分客观。但这不等于,你在思考和写作南宋衰亡史时,可以将蒙元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他者,作为一个不想探究的毁灭方。
蒙元视角的难点之一,可能也是最有魅力之处在于,成吉思汗开创的大蒙古国,与忽必烈开创的元朝,自然有其天然的历史传承,但远不是一回事。回到历史现场,在蒙古人内部,那些“蒙古本位主义者”对忽必烈的“汉化”倾向一向充满疑虑,对忽必烈建立中原王朝的努力更是不以为然。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立国路线,为此也引发了漫长的蒙古内战。
但这与南宋衰亡史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万千重。当即位前的忽必烈在鄂州城下与贾似道缠斗时,当做了蒙古皇帝的忽必烈倾力灭宋时,来自“蒙古本位主义者”的军事挑战令忽必烈如坐针毡,不惜放缓灭宋大业也要先行专注于蒙古内战。
没错,对于忽必烈而言,战争并非优先级,南宋更算不上什么大敌。
这是南宋亡国的重要真相之一:蒙元和南宋从来就不是一个体量的对手。
以此而言,南宋在蒙元战争中的抵抗,尤其是襄樊之战中的坚韧更令人心生感佩,面对这样一个在人类历史上都无与伦比的征服帝国,南宋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过分贬低你的敌人,最终其实是贬低了自己,特别当你是输家的时候。
这里就牵涉到我想避免的第三种叙事:奸臣和汉奸叙事。
叹惋“崖山之后无中国”是浅白的感情流露,但喟叹之余,不去考量蒙宋双方的实力差距,不去细究两宋深入肌理的一些体制痼疾,简单粗暴地将亡国罪责往所谓奸臣身上一推了事,就不是什么体面的读书人了。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愤愤不平地说:“那些曾为贾似道所笼络、重用,而最终抛弃了他的南宋大官,大多都在仕元之后埋首著述,此辈往往对贾似道进行肆意谩骂,并将南宋的灭亡归结于其一人身上。”
奸臣叙事源远流长,其核心逻辑就是让贾似道这样的奸臣背上亡国的所有罪责,是最为便捷、最易于阐释、最顾及君臣大义、最容易被传播、最能迎合民间朴素情绪的“顾全大局”之举。
这样似乎也是一种民族主义式的心理补偿:我们本来可以轻松打败外敌,但奸臣当道,以至于大局糜烂。
汉奸叙事也是类似的逻辑。鼓吹者沉醉于这样一种情境:内有奸臣作祟,外有汉奸横行,因此国将不国。
有了这样简单畅快的叙事,一个人不懂历史细节,不知蒙元为何物都没关系,还能显得这个人特别深邃无所不通……
阅读历史、思考历史、写作历史,目的之一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可能性充满敬畏,保持开放心态,小心翼翼地为自己的每一种主张仔细论证,一旦有了更确切的事实,做好随时推翻自己前见的准备。
我会随时这样提醒自己,也希望用我的写作提醒我最敬畏的读者们。
我们都希望自己生活的世界更好一点,不是吗?
这本书照例献给我的妻子冰和女儿栖约,愿我们都宽容地看待彼此,看待我们的生活与世界;也献给我的妈妈,希望她身体健康,少看网上那些似是而非的养生学。
崖山之外,是更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