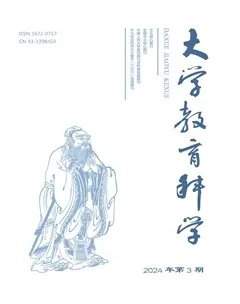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伦理诉求与实现
李洪修 蒋维西
摘要: 教育家精神具有深刻的伦理意蕴,其在目的论上蕴含“至善”的伦理归旨,过程论上体现“从善”的德性实践。它的提出为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伦理遵循。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具有三重伦理诉求:学术研究向度体现为从克己他律的被动约束到多种语境下的修身自为;教学育人向度体现为从单向的知识传输到师生人伦关系的情感重构;社会服务向度体现为从自我中心的身份取向到融入共同体的家国情怀。这需要大学教师追求学术实践的价值理性,达成“主体责任”与“自由意志”的契合;秉持学生主体立场的道德倾向,发挥公正的育人效力;挖掘教师身份的“社会价值”,实现公共与个体间的意义澄明。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教师专业发展;伦理诉求;学术研究向度;教学育人向度;社会服务向度
中图分类号:G640;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3-0004-08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并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六个方面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刻阐述。教育家精神是教师专业伦理的一种体现,是教师在成为教育家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专业品格。当前对教育家精神的研究大多从教育家精神的历史溯源[1]、概念演进[2]、价值谱系[3]等层面进行分析,对于高校教师如何践行教育家精神的研究较为单薄,少有学者从伦理的层面分析教育家精神与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关系。基于此,本文探讨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伦理诉求,尝试以伦理的视域揭示教育家精神对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定性指引,明确新时代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伦理遵循。
一、教育家精神为大学教师专业发展 提供了伦理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教育家精神是我国历代教育家师道文化的共同核心要义,凝聚了中国特色师者的优良传统,为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伦理指向。
(一)教育家精神的伦理意蕴
伦理学认为,精神是人的“自我意识”在“知、情、意”等领域中建构起来的“真、善、美”[4]。黑格尔将精神视为伦理,指出“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这种出之于自然的关联本质上也同样是一种精神”[5]。基于此,教育家精神以一种伦理范畴,揭示了教师职业核心的美德、关键的道德能力,是一种蕴含多重德性条目的精神载体。
首先,教育家精神在目的论上蕴含“至善”的伦理归旨。“教育的精神意向是对人性之善的执着追求。”[6]教育者致力于教人向善、探究真理。“善”成为教育家精神本质的规定性。至善既是教师专业活动的伦理目标,也是教师专业伦理的终极形态。一方面,教育家精神描绘了教育活动“至善”的理想图景。教育家精神中关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等相关论述是教师个人修身目标与教师育人效能发挥社会预期的有效统一,即对教师个人修养与社会效益的整体性认知。这一图景源于教师在社会中的伦理身份定位以及社会对教师的伦理诉求。另一方面,教育家精神明确了教师“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教师的教育活动是在内化教育家精神基础上的义务彰显与责任担当。教育家精神对师德等伦理准则进行时代革新的同时,也明确了教育活动中教师对伦理准则的践行使命,指明了教师在伦理价值上合乎道德的“善”,以及教师具备辨识何为善恶、何为应当的道德视野,以此实现自我内在道德律令的养成。
其次,教育家精神在过程论上体现“从善”的德性实践。德性论思想认为,德性的指向促使个体理智地追寻善的目的,行为者个体的美德是在这种追寻善的德性实践中逐步健全并完善的[7]。教育家精神映射了德性论中美德与实践的共生关系,并在过程论中阐明了教师作为道德主体“如何为善”的标准和实践途径。一方面,教育家精神提供了一种教师美德实践路径。诸如教育家精神中“乐教爱生、因材施教”等实践路径具有现实性和情景性,蕴含了教师德性能力的实践场域。教师达成德性之善的基础固然是对规范准则的习得,但意识的具备无法直接形成德性之伦,而是应落实于专业发展过程的实践中,包括道德推理、道德抉择在内的道德行为。另一方面,教育家精神延续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教师的实践智慧结晶。诸如“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等均是我国历代教育家所发扬的实践真理。这种历史经验的合理性延续能够由内而外浇筑教师稳定的道德信念和准则,并不断提升大学教师在复杂专业情境中具体行善的能力。
(二)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伦理诉求的内涵
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受多种意向的驱动,面临多种可能性,并非偏向个人喜好的一种定夺行为,而是一种受道德意识指导和影响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凭借特定的道德原则,以善恶、正义等为准绳调节课程与学生、专业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关系,从而成为一种大学教师主动自觉开展的伦理实践。伦理自觉意味着大学教师要主动对专业发展的多种取向和知识生产中的行为实践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抉择。因此,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不仅充满效率、均衡等理性维度,还无不渗透着道德、人文关怀等伦理维度。
伦理是“人在面对各种关系时所遵循的道德准则”[8],因为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埃德加·莫兰认为,伦理行为是一种连接(Reliance)的个体行为,即伦理主体与自我、与他者、与社会之间的关联[9]。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包括“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专业知识与精神”[10]。将“伦理”概念映射到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上可以发现,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伦理诉求是大学教师在专业发展的过程中秉持特定的道德规范妥善处理个体与自我、与他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大学教师在学术研究中实现对学者德性的塑造、在教学育人中履行对学生等他者的价值关怀以及在社会服务中契合社会利益、承担社会责任。教育家精神的提出为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一套指向明确的评价原则和规范体系,其以一种道德化的目标形态成为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然追求。在教育家精神的引领下,大学教师得以针对专业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进行考量,既能够保留符合道德价值的专业发展内容并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完成自身专业发展的诉求,又能够妥善处理专业实践中存在的显性道德问题和隐性道德风险,使专业发展成为一种开放空间下的自觉行动。具体而言,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伦理诉求可划分为学术研究向度、教学育人向度和社会服务向度三个维度。
首先,学术研究向度是指借助专业学术活动的历练,实现教师作为学者的德性之善。道德是对“善”的阐释,其根本目的在于规范个体行为及维护世界的和谐秩序,它依靠主体的专业行为使其意义获得彰显。教师要“借助专业实践在目的论意义上完整实现教育价值,将意念之善变为现实之善。”[11]教育家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引领,旨在帮助大学教师在对专业学术行为的调适中形成德性伦理的意识。具体来看,大学教师的专业实践贯穿于科学研究、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等学术活动的践行之中。教师作为学者的德性之善是教师在对自身学术使命的认知、认同、执行的过程中存在并被唤醒的。教育家精神以价值理性的逻辑关注大学教师专业发展过程本身所具有的德性关怀,倡导大学教师通过对学术研究的能动自为,养成具有教育家典范的学者风格,使学术权力在复杂的专业活动中有效彰显伦理品性。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教师会自觉权衡不同学术活动对自身专业的道德诉求,树立自身德性伦理的意识,从而预见性地发现不同价值取向的学术实践及其结果偏重。
其次,教学育人向度是指通过对人伦关系的调适,在教学育人过程中实施对学生等他者的价值关怀。尽管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从显性层面上是教师个体与专业活动之间发生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但这种实践活动的归旨在于促进学生的生命成长。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应该凸显其独有的育人属性,成为一种劝人向善并充满人性关怀的活动,进而实现学生的主体价值。一方面,以自身的专业德性涵养学生的德性。教育家精神蕴含了教师教学育人活动的目标定位,反映了教师育人范式的愿景构想。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旨在通过教学育人活动帮助学生领会价值观的理性法则,并将之内化为学生自身道德自律的意志。作为有道德能动性的学习者能够在教师“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帮助下对教师德行传递的道德价值进行有效吸收,加以内化,使之成为自身的行动准则。另一方面,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要展现一定的关怀伦理,凸显学生的主体价值。大学的育人模式不应该将学生与育人目标的关系视为工具对生产线的被动适应。教育家精神倡导教师的育人智慧。在其引领下,大学教师理应创造性地改变育人过程的内容布局和呈现形态,使之形成与学生民主对话的良性互动状态,从而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在此过程中,教师自身的道德魅力、道德精神也会融入专业活动,在获得学生主体认同的基础上逐渐孕育学生的主体精神。
最后,社会服务向度是指教师将社会价值嵌入自身专业身份中,以达成社会责任的目的。教师对专业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决断最终的归旨在于满足社会需求、契合社会利益。为国育人、服务社会等理念作为社会赋予大学教师身份的诉求决定了大学教师需要解决一系列关涉道德的伦理命题。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12]。而当下,“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面临着多元的、相互冲突的道德符号,面临着现时代的精神生活秩序与道德秩序的混乱”[13]。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既要适应社会生活的变迁,又要以自身独特的身份伦理抵御社会多元价值思潮的冲击。教育家精神既是传统社会对教师身份要求的确证和再现,又是新时代背景下对教师身份伦理的拓展。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旨在增强教师对社会主流价值的体认,提升自身专业与社会的嵌入,促进教师形成为党育才、服务国家的伦理抱负。一方面,社会价值的传递有赖于大学教师群体的自主与自律。在专业化发展过程中,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教师群体在自由意志下能够保持一种道德的自律性,使社会价值获得彰显和传递。另一方面,社会价值的更新依靠教师群体的道德实践。大学教师对教育家精神的践行过程就是融合了自身职业使命、专业理想后对社会责任的一种精神把握,能够形成一定的专业伦理标准来观察、评判和改变社会现实,使主观见之于客观。
二、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伦理诉求的基本表征
大学教师具有学术研究、教学育人、社会服务等三重职责。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伦理诉求需要围绕这三方面实现从被动到主动、从职责到情感、从个体到整体的转变。
(一)学术研究向度:从克己他律的被动约束到多种语境下的修身自为
大学教师在学术研究中所具有的良知、信仰、世界观等道德准则构成了自身专业发展的个体伦理。作为个人道德的观念底线,它指导和约束个体的行动指向。当前,部分大学教师对外在的学术规范呈现一种被动服从的状态,关注学术伦理外在的教条式行文约束,而忽视其内在深刻的伦理内涵,致使学术伦理异化为一种“克己”的力量,对主体发挥“他律”效应,难以深入到个体伦理的框架中。教育家精神以承续与创新、外在规范与个体修身的辩证互动,完善了个体伦理的时代适配,倡导教师主体形成内在的伦理自觉和道德习惯。例如,“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的理念,延续了我国历史长河中诸多教育家个体伦理的经验主义传统。因此,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既是立足历史与传统发掘教育家作为“学者”的实践德性,并达成“自为”的意识觉醒,又是扎根现实情景、谋求自我实现的修身实践。
首先,在历史语境中探寻教师个体作为伦理实体而存在的道德生活。“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是将历史语境中我国教育家的学者风范提取出来,使之成为新时代教师修身的遵循。大学教师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即是成为德才兼备的学者的过程。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作为一种伦理实践,不应脱离历史境遇中的“学者”属性。大学教师的社会性决定了其是历史传承中的道德主体。一方面,大学教师要从既往的伦理经验与传统文化中挖掘学者所具有的德性根基,并以此谋求自身专业发展的共识拓展。这种共识源自历史的回溯,能够引起自身专业的共鸣,摆脱个人主义的幻象。也即是说,通过对“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传统修身观进行现代性审视,形成一种“自我习得”的意识觉醒。另一方面,大学教师要结合自身专业发展实际对历史中教育家的传统个体伦理进行创造性激活。历史的场景性变革使得传统个体伦理在当今面临多种不确定性。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不是对历史中教育家个体伦理的简单重复,而是基于新时代教育生态的现实要求而推进的创新性转化。也即是说,大学教师不能机械地复制历史中教育家个体的性格品性和处事习惯,而应该立足新时代教育发展的独特性,探寻历史经验与现实情景的结合点,创新育人模式,将历史中普遍的教育家精神与当下教师个体独特的人格魅力相结合,生成自身个性化的育人智慧。
其次,在现实情景中追求学术真理,具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实践理智。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实践理智是“一种同人善相关的、合乎逻辑、求真的实践品质”[14],不仅关注总体层面的善,更聚焦实践行为的技巧性和适用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既有道德目标的形上性,又具有学术实践的针对性。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是具备道德判断的“转识成智”。一方面,对技术价值性的道德审视是追求学术真理的基础。技术在学术实践中并非价值中立。大学教师在从事科学研究、知识生产等学术活动时要判断、甄别各种专业技术潜在的道德风险,遵循研究过程与成果输出的技术伦理,防范自身的专业技术出现伦理失范。另一方面,对实践性知识的道德转化是具有实践理智的关键。即对“求是创新”的追求融入学术研究的实践体验中,将这种道德体验升华为自我实现的实践智慧。借助道德推理,大学教师在学术研究中凝聚的实践性知识能够在伦理情境的渲染下转化为具有坚定意志取向的学术发展信念,成为教师应对专业问题的实践智慧。
(二)教学育人向度:从单向的知识传输到师生人伦关系的情感重构
伦理源于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存在,又因各种关系的相互作用成为处理关系的意识形态,使“人与人以柔性规范建立良好关系并维持它的最一般意义。”[15]教学育人向度的伦理以道德主体间的关系为客观内容,呈现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相对于中小学教师而言,大学师生的交往较为短暂,通常以专业课程的教学关系为契约。传统大学教师在教学育人上单纯以知识传输为导向,忽视了师生人伦的情感建构。教育家精神中关于“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的论述,是对中华文化内隐人伦情结的彰显。因此,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应以深层伦理情感的人文情怀建构起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伦理关系,以“情感”与“智慧”为纽带达成育人的合理性。
首先,在师生人伦关系上生成“为他责任”的“教育爱”。列维纳斯认为,“伦理的核心是以‘他人为重”[16],道德主体在选择之前,为他人的责任已然存在[17]。教育家精神强调了师生人伦关系的他者取向,“乐教爱生、甘于奉献”指明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需要突出教师充当伦理主体的责任前提,以学生为中心传递教育爱的归旨。一方面,大学教师以教育爱作为伦理实践的契约形式。教育爱具有“先在”的应然性和自然性,它以教学契约、师生互动为效用机制建立师生间情感信任、道德认同的伦理文化。大学教师是将教育爱视为一种隐性的契约运用到其专业发展的道德实践中,使师生作为伦理主体的情感建构与伦理关系的规范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大学教师要关注教学过程中师生施受相遇的品质,在人文关怀上与学生的精神境界发生意义契合。这意味着大学教师基于育人立场对自身专业进行人伦视野的意义发掘,以谋求师生人伦关系从平行的事务性关系转化为情感交织的和谐人伦关系。
其次,保持自身育人实践的稳定性和完整性。“启润心智、因材施教”的教育家精神为教师的多种育人实践提供了行动的理由,并将规范性寓于育人实践的标识中。大学教师需要在多线交织的专业发展脉络中维持自身育人行为的连贯性。一方面,专业情景与育人行为的统一。教育家精神指向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行合一,大学教师需要维持育人行为在跨情景中的稳定性,不局限于单一课堂教学的育人范式,将片段式的专业情景与其特定的育人元素进行有效串联,使之形成跨界连贯的意义整体。另一方面,多种育人范式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均衡和协调。培育拔尖创新人才需要大学教师在专业发展中尝试不同的育人范式,也会面临不同育人路径引发的道德冲突。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大学教师专业发展需要在同一道德体系内协调不同育人范式的价值差异,使教育家精神介入、影响并统一于育人实践的各个环节。
(三)社会服务向度:从自我中心的身份取向到融入共同体的家国情怀
伦理以一种现实性的象征附着于身份的符号载体中,这种依存关系勾连着身份内在的价值内涵。“‘身份背后所承载的社会普遍性价值诉求构成流动性身份背后稳定的价值支撑。”[18]大学教师职业在不同情境中被社会框定为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框架中的价值属性也赋予大学教师自身独特的规定性。传统语境中部分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将个体利益作为首要发展要素,认为“个体应追逐个体之善,对个体而言的好也将有益于社会”[19]。然而,新时代背景下教育情景的复杂性要求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身份取向必须发生时代性的转变,即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不仅是要实现自己的完满生活,更要在深刻的意义上体现出他作为社会实践者的活动价值和身份意义。教育家精神揭示了教师作为一种社会身份所具有的美德形式。例如,“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还原了教师身份的社会价值,也是对天下和合的伦理共识。因此,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需要从自我中心的身份取向转向融入共同体的道德自觉。
首先,在服务社会中获得自我与社会身份间的同一性知觉。教育家精神着眼于教师专业发展中的身份张力,提炼出了一种对教师身份的整体性理解。“胸怀天下,以文化人”要求大学教师转换一种身份伦理的思考方式,以适应教育家精神内核的身份主张。一方面,反思地把握教师身份存在的个人与社会属性,形成对伦理身份的概念认同。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大学教师专业发展要把握社会对学科专业的需求导向,从碎片化的自我观念中抽离出来,凭借自我意识的反思结构在具体的教育情景中塑造引领社会发展的伦理身份[20],使之契合教育家精神中胸怀天下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将教育家精神以道德观念的形式转化为自我伦理身份与社会主流价值之间的同一性知觉。教育家精神作为教师伦理身份的现实表达,其对教师身份的道德规约定义了教师在服务社会的情景中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以文化人”就是要大学教师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教化人。也即是说,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咨政建言、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专业活动的解释框架中,使之成为大学教师专业身份背后的行动遵循。
其次,与国家的关系上形成心系共同体发展的家国情怀。中国传统语境下的共同体以“国”“天下”为主要形式,其“本质意志”为最高的善,也容纳了个体对善的追求[21]。共同体公共价值的达成离不开成员在道义上的共通、对集体的情感依赖以及由此衍生的地缘归属性。黑格尔认为,基于情感的相互“归属性”(Subsumtion)是共同体与成员间相互统一的关键[22]。教育家精神中关于“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论述是对教师身份与国家共同体情感关联性的直接呈现。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应回应国家共同体的伦理期盼,在服务社会中由“个体善”向“共同善”拓展。一方面,教师以价值共通的专业身份书写对共同体的情感性诠释:在伦理认知上,将家国情怀作为专业身份内在的价值序列,形成与共同体同生共荣的身份意识;在服务社会中,不把复杂普遍的个体诉求及其驱利的基本属性作为孤立的效益判断依据,而是强调专业身份服务社会的公共性目标以及情感性的意义追问。另一方面,教师将“小我”的专业身份诉求与共同体“大我”的利益目标相结合:摒弃自我中心伦理(egocentric)的预设,在社会服务中将个体专业发展的意义归置于共同体发展的框架下,凸显个体与共同体的生存关联性。
三、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伦理实现
(一)追求学术实践的价值理性,达成“主体责任”与“自由意志”的契合
专业发展是包含道德符号的实践性载体。大学教师作为一个道德性主体,其主体责任在于将道德维度融入专业价值的学术实践过程中,使学术活动的目的指向立德树人。当然,教师也拥有学术自主的自由意志。教育家精神既明确了大学教师作为学者“行为世范”的主体责任,同时又赋予教师学术自主达成“求是创新”的伦理期待。大学教师学术自主的自由意志具有鲜明的动态性、个体性和生成性,表现为个体对专业学术实践的独特建构和理解。而教育家精神赋予的主体责任则具有旗帜鲜明的规定性、普适性和示范性,体现为群体对公共利益的共识。因此,大学教师要将教育家精神视为自身学术自主的一种行为指向。
首先,追求学术实践的价值理性,在专业发展中将教育家精神蕴含的主体责任有效地通过实践予以转化。麦金太尔认为,实践是对“内在利益”(internal goods)的追求,它不是外在物质实体化的表征,而是通过能力的获取实现内心的“至善”[23]。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是“生命成长”而非“制器”的活动,需要追求价值理性的专业学术实践。一方面,大学教师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始终秉持耐心求真、严谨奋进的实践原则,不仅遵循学术研究的本真面目,而且使学术实践能切实促进自身德性的养成以及社会的进步。功利取向的学术研究常常把法理责任置于首位,而忽视道德责任。务实求真作为行动者的一种实践理性,其真正的使命是产生善良意志,达成与道德实践的默契,使行动者不易受制于外来的感性诱惑。另一方面,预防学术实践模式化引发的职业倦怠对专业发展的桎梏。单纯模式化、缺乏问题导向的学术实践难以适应复杂的时代变迁,极易引发专业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割裂。因此,学术的创新发展要求大学教师根据社会利益的动态变化及时调适研究取向和方法,始终处于一种持续更新的状态,以此适应变化发展中的专业发展实际。
其次,发挥自由意志的创生作用,不断丰盈主体责任实施的专业路径。教师个体是教育家精神的实践者,个体具有独特的自由意志,能够以自身内在的行为范式和感情意向作为专业学术实践的参照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种履行主体责任下的自主实践逻辑。一方面,教师的学术发展要以学术实践过程为补益,探求学术实践中个性化的实践智慧并不断加以丰盈。个体在学术实践中领悟的实践性知识是以零散的、碎片化的形式存在于个体意识中,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教师的专业发展需要及时、准确、科学地对这些存在于学术实践中的零散的价值要素进行判别和归纳。另一方面,教师的学术发展要弘扬学术实践的创新价值。个体实现自由意志不仅要挣脱内在惰性的束缚,更要加强对理性经验的创造性建构。大学教师的学术发展是基于社会经验意义上的主动建构,理应强调直接经验在学术实践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并以此成为教师主体责任的彰显。
(二)秉持学生主体立场的道德倾向,发挥公正的育人效力
不同情景对大学教师专业身份的要求逻辑并非完全重合,对其道德价值的诉求往往呈现交叉、重叠、兼具的样态。因此,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要探寻不同情景中隐藏的道德要素,秉持学生主体立场的道德倾向,及时进行专业行为的道德评价,维护育人效力。
首先,秉持学生主体立场的道德倾向。大学教师要重视自身专业发展对学生主体成长的重要内在价值,从而使得自身发展的取向服务于学生成长成人,包括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主体性以及挖掘学生的潜能等。一方面,在课程与教学中,教育家精神倡导的“因材施教”要求着眼于学生个体成人的发展性取向,谋求学生德性发展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统一。具体而言,在课程目标的设计中要求教师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重视课程对学生道德境界提升的功效;在课程内容组织中要求教师立足于课程内容与学生德性发展的适应性。教师应以适应学生道德学习的规律和道德发展的目标为旨趣,为学生建立一种可能的德性生活,在教学中谋求课程与学生精神世界的真挚对话,保障课程的理性与学习者的感性相统一。另一方面,在师生交往中,教师对道德价值争议等问题应保持一种持续的敏感性,有必要形成对“什么样的互动最有育人价值”的追问。教育家精神倡导的“启润心智”要求大学教师洞察学生学习情境、活动过程的细微之处,更需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教师要尊重学生表达学习需求的权力,给予学生表达需求的话语权并及时发觉学生自我意识与观念的变化与更新,从而有意识地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找准育人落脚点。
其次,及时进行专业行为的道德评价,维护育人的效力。“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阐明了大学教师的每一种专业活动“必然有着自己的道德责任,而且其道德责任的基本内容就是维护和提供正义”[24]。对专业行为的道德评价是教师以教育家精神的评价标准,直面自身履行专业职责的利弊得失,从而提升职业的道德效力。这种道德成效能够在情感、规范和意识方面给教师一种心灵上的精神约束,从内在道义上使教师专业发展产生向善的倾向。一方面,教师对育人效力的评价需要依据教育家精神的价值愿景。教育家精神提供一种合乎道德逻辑的、普遍意义上的标准和行动秩序。这种基于教育家精神的伦理评价是将独立的教师自我意志与主流道德准则以自由选择的形式达成条件性联结,使得大学教师将复杂的专业情境与道德准则进行反复匹配判定。另一方面,教师要善于对职责的执行结果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作为专业主体,大学教师在实践活动中对育人者的身份行为等进行分析、决断、管理时,要明确这一过程中多种结果所带来的责任,包括以何种态度和方式参与实践以及如何面对执行后的结果。在履行职责之后,教师要考量自身的专业行为是否符合教育家精神,是否有助于实现大学教师职业本身的利他性和服务性。
(三)挖掘身份的“社会价值”,实现公共与个体间的意义澄明
教师既是个体性的存在,也是公共性的存在。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既具有自身生存发展的“个体意义”,又具有贡献社会的“公共意义”。个体意义与公共意义之间的实践视域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耦合关系。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在面对公共与个体的双重维度中,必须权衡意图和结果之间的现实张力,规避二者的局限性,以共融性的整体思维将个体与公共进行统筹,避免使个体凌驾于公共意义之上。
首先,在既定价值的把握与动态价值的探寻中实现对身份价值的挖掘。具体而言,对“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等既定价值的把握能够彰显大学教师身份所承载的持续、普遍、共通的社会意义,使得教师身份所负载的既定价值被教师自身认同并内化。而对产教融合、咨政建言等不同情境身份中的动态价值的追寻则着眼于个性化、时效性、特殊化的意义附着。一方面,“胸怀天下”要求依据不同情境中服务对象的需求明晰教师身份的社会价值。这意味着大学教师的社会服务不仅要满足显性规章既定的合法性,更要在此基础上将学科发展、社会利益等诉求融入身份伦理中,使多元价值之间相互融合,和谐统一。另一方面,大学教师要始终保持一种对身份背后社会价值时代性意蕴的敏感嗅觉,并根据不同身份情境有侧重地对“以文化人”的方式进行拓展,补充时代性较强的专业身份伦理,增强身份背后社会价值的生命力。它旨在减少因时代发展、情境变迁而对大学教师身份造成的耗散、折损甚至异化,确保大学教师身份的社会价值有稳定的更新范式。
其次,将社会的发展诉求和个体的发展目标相统一。“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教育家精神要求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个体意义实现要以公共意义的落实为前提。在社会服务中,教师需要明确个体专业发展的初衷不是单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由意志,更不是被当下私欲捆绑的短视倾向,而是在道德主体责任和良心庇护下的自觉自由。一方面,在社会服务时需要判断个人生存目标与自身道德使命的协调。大学教师处于复杂公共情境中,因此需要以道德规范的视角及时反思自身专业决策在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冲突,适时调整专业行为运作的程序安排,使之为社会进步创设富含价值的环境,关注专业决策在社会情境中隐藏的价值要素。另一方面,教师在社会服务时需要以道德的方式缝合社会需求与学生发展的缝隙。这表现为教师以积极的方式实施专业服务社会的行为、以理性的思维审视育人过程中出现的与社会需求脱轨的问题,又表现在教师敢于突破自身固有的舒适区、以自身的专业行动为拔尖人才培养提供环境支持,兼顾学生能力培育与社会应用的有效统一。
参考文献
[1] 蒋纯焦,李瀚文.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4(1):106-111.
[2] 张志勇,史新茹.“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演进逻辑、本质内涵和时代价值[J].中国教育学刊,2023(11):1-6.
[3] 罗生全.教育家精神的价值谱系及塑造机制[J].南京社会科学,2023(10):135-142.
[4] 杜灵来.伦理精神的哲学意蕴及其基本特征[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34-40.
[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8.
[6] 樊浩.教育的伦理本性与伦理精神前提[J].教育研究,2001(1):20-25.
[7] 卫建国,高宇航.论公共服务精神的三重伦理维度及其统一[J].伦理学研究,2020(6):7-14.
[8] 李建华.伦理与道德的互释及其侧向[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59-70.
[9] 埃德加·莫兰.伦理[M].于硕,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35.
[10] 林杰.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与策略[J].大学教育科学,2006(1):56-58.
[11] 蔡辰梅.教师之善:本质特征、实践偏差及其完整实现[J].当代教育科学,2021(8):19-27.
[1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5.
[13] 金生鈜.德性与教化[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207.
[14]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72.
[15] 王中江.关系世界、相互性和伦理的实态[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71-86.
[16] 陈红,张福红.梁漱溟伦理责任观及其当代价值:基于“他者”视角[J].学术交流,2016(9):26-30.
[17] 张广君,宋文文.教师“为他责任”伦理:言说与批判[J].高等教育研究,2019(2):27-33.
[18] 窦立春.身份的伦理认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2.
[19] Merchant C.Radical Ecology:The Search for a Livable World[M].New York:Routledge,2005:64.
[20] 向玉乔,卢明涛.论身份伦理[J].伦理学研究,2023(4):28-36.
[21] 王晓丽,李琦.共同体的伦理之维及其当代中国诠释[J].学术研究,2023(5):29-35.
[22] 肖祥.社会主义:全球化视界中的伦理共同体及其世界意义[J].求索,2020(4):72-80.
[23]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龚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37.
[24] 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60.
Ethical Demands and Rea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eache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Educator Spirit
Li Hongxiu Jiang Weixi
Abstract: The educator spirit has profound ethical implications, including the ethical aim of perfect goodness in teleology and embodying the moral practice of good virtue in process theory. It provides ethical guidelines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eachers.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eache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educator spirit has three ethical demands. The academic research orientation is embodied from the passive restraint of self-denial to self-cultivation in various contexts. The orientation of teaching is embodied in the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dimension of social service is embodied in the self-centered identity orientation and the feeling of integrating into the community. This requires university teachers to pursue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academic practice and achieve the combination of subject responsibility and free will, uphold the moral tendency of students' prominent position and exert the objective effect of educating them, and excavate the social value of teachers' identity and realize the clarity of meaning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individual.
Key words: educator spirit;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thical demands; academic research dimension; teaching and education dimension; social service dimension
(责任编辑 李震声)
收稿日期:2024-01-11
基金项目:2022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双减背景下基础教育课堂形态及高质量发展研究”(22JZD047)。
作者简介:李洪修,山东沂水人,教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研究;蒋维西,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天津,300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