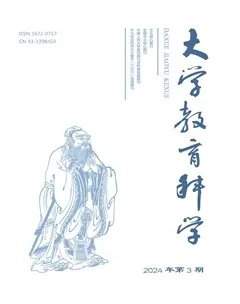“大思政课”运行的现实样态、价值旨归与路径优化
聂迎娉 傅安洲
摘要:“大思政课”运行,是指“大思政课”由理念走向行动的动态过程,在课程与社会融合贯通的视角下呈现出贯通运行、协同运行和全景运行三重样态。从大中小学学段间的思政课程贯通,延伸到思政课与社会系统诸要素的全景联动,“大思政课”运行不断突破课程界限,逐步澄清其与传统思政课的理念“大”“小”之论争,纾解“课”“社”联动之困境,解决制度“破”“立”之难题。推动“大思政课”高质量运行,应以促进师资队伍协同力、叙事力、转化力和“数智力”提升为运行赋能,锻造一支“认识同频、目标同向、行动同步”的高素质队伍;以强化问题意识和突出实践导向为运行纾困,为课程向社会有序延展提供抓手;以健全社会参与的动力激发机制、资源转化机制和支持保障机制为运行解题,从而更好实现立德树人、铸魂育人。
关键词:大思政课;“大思政课”运行;运行样态;运行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3-0055-08
“大思政课”运行是指“大思政课”由理念走向行动的动态过程。自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至今,“大思政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颇丰,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已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回归“大思政课”的出场语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的论断[1],有课程运行和社会运行相耦合的意蕴。一方面,“大思政课”作为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课程形态,伴随着学校课程决策、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课程实践,要解决的是如何增强思政课亲和力与感染力、针对性与实效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大思政课”作为思政课向社会延展扩容样态的动态描摹,强调的是课程根植于社会实践,彰显社会生命力,要回答的是思政小课堂如何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的时代命题。在课程与社会融合贯通的思想认识下推动“大思政课”运行,能够激活课程所依赖的“社会肌体”和社会所蕴含的“思政细胞”,促进课程与社会的深度融通,这对于真正做到理论有深度、实践有力度、情感有温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大思政课”运行的现实样态
“大思政课”运行的核心是“把握思政课在课程实施以及思政课与社会现实互动的过程中呈现出的关系样态”[2]。这内在地蕴含一个基本前提:课程作为教育要素,不是“非社会”之物,而是深嵌于社会之中。思政课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这种普遍联系,展现为“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3]。具体到“大思政课”运行来说有三个维度:一是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大思政课”要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实现贯通运行;二是事物不能孤立存在,“大思政课”要在学校立德树人课程体系和育人体系中实现协同运行;三是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大思政课”要在思政课与社会多要素、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中实现全景运行。
(一)“大思政课”贯通运行
“大思政课”贯通运行,是指在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开设的思政课课程体系内,大中小学要实现不同学段间的课程贯通。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组织领导,到教学管理,再到教学评价,思政课教学活动的运行更加规范”[4]。特别是2019年3月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以后,不同学段间课程贯通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是课程体系不断完善。目前,我国遵循“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原则,以培养道德情感,打牢思想基础,提升政治素养和增强使命担当为目标,构建了各学段层层递进、必修选修相互协调的思政课课程体系。中宣部、教育部印发的《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2020年),通过对课程体系的一体化设计,初步实现了各学段间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要素的有效贯通。二是教师队伍增量提质。近年来,思政课教师的社会关注度和社会认可度不断提升。以高校为例,教育部社科司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高校专兼职思政课教师超过12.7万人,较2012年增加7.4万人。一项关于2020年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调研显示,共有158人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荣誉称号,包括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最美教师等[5]。同时,随着各地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手拉手”集体备课等行动的推进,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三是课程制度不断夯实。自教育部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后,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课程建设的规范性文件,如《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年本)、《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意见》(2022年)等,还发布了《关于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的通知》(2022年)。这些制度、规范、通知的出台,为一体化推进思政课的教学组织、教学实施、教学管理和教学评价提供了原则标准。如此,以思政课为基础依托,诸课程要素共同形塑着“大思政课”的贯通运行样态。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6]6,“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6]27。因此,尽管“大思政课”的内涵溢出了传统思政课程,蕴含着大视野、大格局、大场域、大情怀,但其立足点和出发点仍是“课”,需要以思政课为基本育人载体,“通过学校的课程设置、通过教师的课程教学及相关活动来达到育人的目的”[7]。
(二)“大思政课”协同运行
“大思政课”协同运行,指向学校场域中显性思政课之外的其他课程,以及超越课程形态结构性制约的其他各类育人载体,是“大思政课”在遵循课程育人逻辑中发挥协同作用的动态过程。这突出地表现为以思政课为中心的“耦合”协同和以课程为中心的“三全”协同两种具体样态。
一方面,课程思政的走深走实,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热潮,不仅打造了一批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培育了一批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助推了基于学科分化的课程体系寻求“思政”价值取向上的统一,还从学理上揭示了课程“内在地蕴含着帮助学生认识事实世界和构建意义世界的双重属性”[8],凸显了课程建构知识、技能和理智等取向所遮蔽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并以此破解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背景下课程学习疏离青少年价值形塑与精神成长的困境。这种课程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耦合协同。另一方面,全员全程全方位协同育人机制的不断优化,打破了学校各类育人载体之间的壁垒,聚焦学生价值形塑和精神成长的全过程,“根据不同学生在思想政治素质发展起点方面的多端性以及发展时序上的差异性”[9],通过有针对性地制度化筛选将其他载体的育人资源转化为课程形态的育人内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发挥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等工作的育人功能。这十类育人载体,按照学生学习生活实践的关联度和客观需求度各自对学生施加影响,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同时通过管理体制和教育机制创新使各类载体相互交织、相互贯通,共同构建了一种多维交错互联、多层并行互补、多元参与互动的“三全”协同育人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既强调“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又要求“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10]。这彰显出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的“大思政课”,不能因其与思政课在发展源流和价值旨归上密切相关而简单等同,它应该被纳入我国“大思政”的育人体系中去理解,既要发挥好思政课在课程体系中的关键课程作用,又要发挥好课程在学校育人格局中的核心载体作用。
(三)“大思政课”全景运行
“大思政课”全景运行,是思政课进一步溢出传统“小”课堂和学校场域,“拓展至更大的社会空间,与社会系统诸要素发生联动而生成的课程形态”[2]。相较于贯通运行和协同运行,“大思政课”全景运行呈现出一种泛课程形态,“它充分把握了思政课的社会属性,是一种将课程设置与课程建设向社会敞开、扩容的思政课形态”[11],其实质和核心是在思政课程中融入现实、融入实践、融入时代,在课程和社会的相互验证和相互激活中发挥课程的思想引领、铸魂育人效应。
一是以“大课堂”有力回应青年学生的真实困惑。目前,现场教学、社会调研、志愿服务等常态化开展的实践活动,正在让丰富的社会生活成为课堂。在社会大课堂中,实践教学的体系化构建和系统化组织,使教学场域拓展至社会全域,教学内容贴近世情国情社情,教学案例取材于青少年日常生活,教学环节呼应社会热点问题,教学方法契合青少年思维习惯,有力推动着课程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和感性活动。二是以“大平台”共建共享教学资源的鲜活成果。近年来,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了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中的思政教育资源供给,着力搭建教学资源“超市”;各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发并推荐了一批科学实用的课件、讲义,畅通优质资源的供给;各地各校自主开发了丰富的地方和校本资源,推动教学资源建设走向体系化。这些教学资源既有理论张力又有实践魅力,能更好地帮助青年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2]等重大问题。三是以“大师资”充分激活典型人物的言传身教效应。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企事业单位的专业人才、社科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等多元主体已经成为大师资的重要构成。他们遍布于青年学生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各类场景中。通过其言传身教引导学生从小事做起,在细节深入,于实处着力,在课程与生活世界的有效结合中化“自发”为“自觉”、化“意识”为“方法”、化“精神”为“物质”,实现精神交往和实践创新。
马克思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3],现实生活是人的存在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客观地存在于人的全生命周期,离散地分布在各类生活场域、交往情境和环境体验中,不能脱离生活世界而单独存在。因此,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分工体系下已经“脱域”于社会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却仍应“融域”于社会,“积极地介入社会一切活动领域,特别是社会思想文化领域,通过一切教育载体实现对人的精神特别是思想政治文化需求的引导”[14],在回归社会中作无字之书,行无言之教。由此,“大思政课”全景运行内在地包含课程与社会开放共生、协同共进之意,着眼于社会全域,以最大限度地整合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二、“大思政课”运行的价值旨归
“大思政课”运行的多维样态,既彰显了“大”的特点,又扎根于“课”的形态。“大”要求将课堂置于宏大时代、生动现实和鲜活实践。“课”需要“充分发挥传统教材和课堂以外的资源与方式,进行课程资源转换”[15]。因此,“大思政课”在不断突破作为制度化知识形态的课程界限的过程中,逐步澄清“大思政课”与传统思政课的理念“大”“小”之论争,纾解“课”“社”联动之困境,解决制度“破”“立”之难题,以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一)澄清理念“大”“小”之论争
课程发展史上曾有过课程理念“大”“小”之争,其核心是讨论课程和教学的关系。不同于此,“大思政课”理念之“大”,是指相较于知识本位、经验本位、社会本位等“小”课程观,“大思政课”指向更宏阔的育人视野和育人使命。在传统学校课程体系中,思政课是一门“小”课。它在课程类别上属于国家统一开设的显性德育必修课,承载的是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与其他专业课、通识课共同构筑了学校的课程体系。但是,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探索,催生了丰富多样的特色课程。例如,基于延安精神、红旗渠精神等设计的地方课程,基于齐鲁文化、华夏文化等开发的传统文化课程,基于红色宣讲、红色研学等创建的活动课程等。从“小”课程观出发,思政课既难以把这些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特色课纳入课程建设范畴,也难以回答“为什么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为什么办好思政课意义重大”等国家之问、教育之问。
“大思政课”的出场,旗帜鲜明地指出思政课本是一门“大”课。回归课程本身,按照“八个相统一”的要求,思政课作为囊括了知识与价值、经验与活动、世界观与方法论等要素的课程载体,承载着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赋予的“在大中小学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重任,它应该从更宏阔的历史视野、空间视野、时代视野和学科视野中选取、吸纳并整合课程内容。课程理念的这种转向,实质是从重视知识与理性,转向重视个人及其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与此相呼应,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要求思政课在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础上,还要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因此,“大思政课”运行,必然呼吁课程理念从“小”思政课扩展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课程育人与文化育人密切结合的大视野。这需要牢牢抓住师资队伍这一中坚力量,发挥好他们在教学理念落实、教学载体创新等方面的作用,以更好达成“在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目标方面,育人功能实现的充分且完全的状态”[9]。
(二)纾解“课”“社”联动之困境
按照“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1]的要求,“大思政课”教学绝不能拘泥于“有规定的时间、指定的教室、固定的桌椅、既定的教案,以及确定的答案”的传统思政课堂[16],而是要从课堂走向社会,实现“课”“社”联动与同频共振,避免理论疏离实践、课程教学疏离个体体验等问题。具体而言,传统思政课堂的“课”“社”联动困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把社会生活引入课堂,让社会热点、时事政治等鲜活素材成为源源不断的课程资源;二是如何让社会生活成为课堂,在志愿服务、红色研学等实践活动中挖掘并拓展课程教学的有益空间。这不仅是一个课堂空间如何扩容的问题,还是一个课程教学如何超越空间形态的客观性而关注到人自身主体性的问题。
思政课的“理论性”“讲道理”等显性特质,曾一度造成教学空间拘泥于教室中的知识规训。后“实践性”“生活化”等内涵的备受关注,既推动了课程知识、技能、价值三维目标的完善,也观照了知识、经验和意义的交融。“大思政课”运行,特别是运行过程中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在进一步消解思政课教学物理—技术空间界限、突破理论课知识规训束缚的同时,呼应了生活德育倡导的教学生存论哲学转向,强调要“以知识为载体加强个体与生活世界的意义关联”,“以实践为尺度进入生活世界、改造生活世界的责任感”[17],即扎根教学对象所处的社会生活场境开展教学。这极大地丰富了思政课教学活动的在场形式。因为,空间不仅可以是教学所依赖的场所,还是一种关系存在,可以被理解为个体知识习得并获取情感归属、价值认同、意义生成的社会生活空间。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把空间理解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产物并见证着人的主体性”[18]中寻得论据,也可以从教育学关于空间侧重“对人作为主体的教育生活空间的分析”[19]中找到依据。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展现的是“凝聚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具体实践活动”[20],社会实践有助于增强个体与社会、国家的关联。当然,我们并非无限扩大思政课的课程边界,也无意泛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意义,而是遵照思政课教学意义生成、教育效果保障、立德树人任务落地的课程逻辑,在教学实践中反思课程社会实效性并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认同度的必备环节。
(三)解决制度“破”“立”之难题
回溯思政课的发展历程,“大思政课”是在经历了“从‘马列主义理论课程到‘两课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演变”[21]后,在新时代呈现出的崭新面貌。因此,“大思政课”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思政课的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中完成向“大思政课”的内涵式跃升。但是,随着“大思政课”的实践在全国火热铺开,一些问题和困惑随之出现。例如,课堂是否会因为各类实践活动的纳入而显得碎片化,教学是否会因为社会师资对课程内容的不了解而显得随意化,课程实践是否会因为过度追求博人眼球而陷入形式主义,等等。这些疑问,都指向了传统思政课制度体系不足以支撑“大思政课”运行这一核心问题。
“大思政课”运行既立足于思政课程,又通过“破”“立”并举不断推动课程制度的跟进、完善和优化,这体现在国家顶层设计与学校落细落实的各个方面。目前,我国实施的是三级课程管理制度。其中,国家课程制度强调的课程运行的普遍目标和共同价值,具有鲜明的强制性和规范性;地方课程制度总体上遵循“以省为主、分级管理、社会参与”的原则,具有承上启下性;学校课程制度是在创造性地落实国家和地方课程制度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符合学校特有的办学理念与发展目标的、关于学校课程系统运行的一系列规程和行为准则”[22],是具体化、校本化的课程制度。近年来,国家、地方和学校层面的制度跟进已初具成效。2022年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了《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各地也陆续出台了相应实施方案,着力突破传统思政课在时空场域、内容供给、教学主体等方面的限制,凸显了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大思政课”建设的导向,推动学校初步构建协同一体的贯通机制、全域融通的联动机制、开放多元的融合机制、优质资源的共享机制、实践拓展的创新机制等等。但是,“大思政课”的高质量运行,还有待各方主体在制度建设方面持续发力,回答好“社会力量如何实现全方位参与,社会情境如何实现多维度联动,社会资源如何实现多层次转化”等问题,为“大思政课”运行提供更为完善的、可操作的、可执行的课程制度体系供给。
三、“大思政课”高质量运行的路径优化
“大思政课”建设是一项动态系统工程。促进“大思政课”从理念走向实际运行再到形成高质量运行的长效机制,就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打造时间接续、空间交叠和情境轮替的育人共同体,汇聚育人合力。基于前文揭示的价值旨归,本文提出以下优化护航“大思政课”高质量运行的可行路径。
(一)持续赋能:促进师资队伍“四力”提升
推动“大思政课”理念落地的关键是锻造一支“认识同频、目标同向、行动同步”的高素质师资队伍。这支队伍既要发挥好思政课教师的关键作用,还要充分调动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中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在推动课程由“小”到“大”过程中将育人队伍的“单兵作战”转化为“协同攻坚”。
以协同力积极推动师资“破壁出圈”。“破壁”组建师资关系到“谁可以教”的问题。相较于“小”思政课,“大思政课”更加凸显课程的纵向贯通、横向协同、全景联动,这对师资队伍的协同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同课异构可以促进不同学段教师间的协同,在教师们的思维碰撞中推动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有机衔接,夯实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基础;异课同构可以强化思政课教师与其他教育工作者间的协同,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助力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同课同构可以推动专兼职思政课教师及其他社会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将身边榜样、道德模范、行业楷模等校内外典型的鲜活案例和生动叙事变为育人的有效增量,在优势互补中构筑协同育人新格局。
以叙事力不断激发思政育人活力。活力激发关系到“是否愿意学”的问题。师资队伍的叙事方式和叙事能力,不仅关系到“大思政课”是否会讲道理,能否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而且关系到课程能否有力回应学生的思想困惑和关注的热点难点,能否讲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故事,更直接关系到课程的亲和力和有效性。这要求教育工作者既要“提炼文本之识和凝聚读者共识”[23],克服思政课叙事政治性学理性强、实践性启发性不够的短板,灵活运用口头叙事、文本叙事、图像叙事和语图互文叙事等多种方式,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和表述风格,让叙事接地气、入人心,实现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向教学话语、生活话语转换,还要坚守思政课程的价值属性,在文化碰撞和舆论交锋中维护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在构建新时代“大思政课”话语体系中牢牢把握和维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以转化力持续促进资源系统开发。资源系统开发关系到“学习什么”的问题。“大思政课”要扎根于社会生活,但并非全部社会生活场境都适用于课程实践。这要求师资队伍不仅要对专业化、理论化和课程化的知识单元进行生活化、具体化、情境化转换,传递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表达时代和社会的重大关切,而且要不断提升将社会生活场境转化为育人资源的意识和能力,实时捕捉社会热点与重大历史事件中蕴含的教育内容,善用仪式教育、典型教育等手段,从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和发展全过程的整体视域,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选择并转化社会生活中的育人资源,创造性地开发和拓展“大思政课”资源。
以“数智力”主动开展情境有效创设。育人情境创设关系到“在哪里学”的问题。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以元宇宙、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热潮,极大地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丰富了思政课的教学方式。教育工作者也要因时而进,不仅应主动供给虚实结合的教育场景,创造开放的学习体验情境,创建优质的数字资源,构建虚拟现实相互支撑的全景交互育人生态,解决好课程资源与教学数据的一体化建设问题,还应在“总体性把脉和全方位审视数字化生存状态中人的思想和行为变化的规律”[24]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基于学生“精准画像”的沉浸式、体验式、交互式、个性化教学方案,在回归人的发展逻辑中推动课程内容、形式等要素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实现精准滴灌。
(二)延展场域:凸显课程延展两大准则
思想政治教育的边界性和课程容量的有限性,决定了在把固定场域的思政小课堂和开放场域的社会大课堂结合时,“大思政课”难以承载丰富且复杂的全部社会生活。因此,应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对社会鲜活素材进行有选择的“过滤”和加工,为课程向社会有序延展,在田野里“消化”书本提供有效抓手。
以问题意识贯穿教学环节全过程。问题意识,“就要在掌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又通过实践不断解决问题,是实践基础上思想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统一”[25]。这里的问题,“包括该课程教学所覆盖的、所相关的领域中,学生高度关注或存在困惑的问题;教师设置,但为学生所应关心和理解的问题;该课程教学必须解决的问题”[26]。思政课教师既要“迎着问题去”,以问题作为教学展开的起点、切入点,又要“沿着问题讲”,将问题意识贯穿课程教学的全过程,沿着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构成的逻辑设计并组织教学活动。“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着力于破解传统思政课教学空间的场域之困、教学内容的文本之困、教学方法的说教之困等问题,使课堂联系社会,理论联系实践。推动“大思政课”从理念走向运行,同样需要聚焦“课”“社”联动之困境,围绕学生在生活中感兴趣的热点焦点问题开启理论教学,化抽象理论为具体问题,解决教材理论宏大叙事疏离学生经验的不足;围绕教师在课程教学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组织教研教改,化共识为共为,解决课程改革缺乏动力难以提质增效的不足;围绕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组织设计特色课程,化课堂为社会,解决教学局限于教室难以扎根社会的不足,以增强“大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以实践导向打通育人过程全流程。实践既是课程育人的内生力,也是贯穿线,还是落脚点。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性实践活动,起因于人的思想需求,指向人的精神世界,最终应落脚于社会空间和人们的生活世界。同理,思政课既是课程助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也是促成个体接受、认同和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过程。“大思政课”运行的一大特色就是打通思政课和其他领域的边界,消解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之间的隔阂,充分利用社会赋予的理论生成力、问题阐释力和现实引导力,关切新时代青年的生活状态与思想动态,让青年学生在丰富的实践中淬炼成长,在推进思政课对社会的价值引领中增强课程的社会生命力。因此,“大思政课”育人要遵循学生从价值认知走向价值认同与价值实践的内在逻辑,在社会全域中获取和完善课程要素与环节。通过这些相关性要素与环节的系统化设计和结构性优化,让“大思政课”在多样化的教学实践中达成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形塑的内在统一,以更好实现课程育人的目标。例如,为了帮助学生更好理解“四个自信”,思政课可以充分利用革命旧址、红色文化遗址、基层社会治理典型等载体,让学生在生动的教育实践中感悟真理伟力,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三)完善机制:健全社会参与三维机制
“大思政课”运行同时关涉课程的社会性和社会的教育性。它既要把思政课置于人类社会历史与发展的宏阔视域中,以社会资源为课堂,还要在社会大系统中广泛且充分地汲取具有育人效应的社会资源,引社会资源入课堂,从而在实现价值引领的过程中促进学生精神成长。这要求不仅要优化既有思政课程制度,更要跳出传统课程形态,建立并完善全社会参与“大思政课”运行的多维机制。
以动力激发机制汇聚社会合力。一是以政策落实考评机制推动基层党委、政府从“被动”走向主动。在“大思政课”建设过程中,尽管地方党委、政府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但传达文件精神、部署工作安排等仍是其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细化基层党委、政府主要职责,将参与作为和结果纳入工作考评,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其职能动力。二是以双向合作机制推动企业和社会组织从疏离走向融合。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大思政课”的主要制约是疏离感较强。加强企业、社会组织和学校之间的双向合作,打通其与教育系统之间的通道,筑牢双方在育人、实践等方面的合作根基,是激发其参与动力的有效手段。三是以奖励机制激发校内外主体从协同走向增效。例如,专项津贴和奖励,可以鼓励教师不断提高教学能力和育人水平;表彰、嘉奖等荣誉,可以对热心参与育人工作的各方主体给予肯定,激发他们不断提高育人实效等。
以资源转化机制汲取社会资源。社会生活具有丰富的育人资源。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五百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一百多年的中共党史,七十多年的新中国史和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中蕴含着宝贵的历史经验,新历史起点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又不断生成着鲜活的现实素材。但这些社会资源并不会自发转化为课程资源,而是需要建立资源转化机制,及时捕捉、获取、整合社会中具有育人效应的高品质资源。当然,资源转化并非随意无序,而应重点把握好两对关系:一是要把握好“教育者集中阐释和受教育者自觉‘发现”[27]的统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关注的焦点热点案例,产生的疑难困惑问题,都可以成为资源转化的对象;二是要把握好资源体系化布局和学生个性化关照间的关系,既要根据课程规范和课程逻辑整体统筹,实现资源转化的全范围覆盖,又要根据教育对象的特色优势,实现资源转化的个性化编排。
以支持保障机制夯实运行基础。一是要加大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力度。党和政府要跟进关于“大思政课”相关文件、通知、指导意见等政策的落地情况,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师资培训、资源建设、社会实践等,确保专款专用,政策落地不打折扣。二是要强化资源供给和主体协同。各类主体要以精准满足学生需求为导向,加大内容供给,让鲜活实践和生动现实中的典型人、典型事走进课堂,为思政课提供取之不竭的素材、案例等资源。三是要夯实心理和舆论支持基础。只有“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6]24,才能推动全社会自觉参与“大思政课”建设。这既需要引导媒体关注,通过多元宣传渠道增加舆论曝光度,宣传典型做法和成功案例,还可以引导师生积极发声,分享学习经验和切身感受,提高舆论公信力,推动全社会形成关心“大思政课”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1] 杜尚泽.“‘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
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人民日报,
2021-03-07(01).
[2] 叶方兴.结构·运行·优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形态审视[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49-160.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2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3.
[4] 吴潜涛,潘一坡.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思政课建设的创新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7):77-87.
[5] 艾四林,吴潜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报告(202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94.
[6]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7] 刘建军.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育人格局[J].思想理论教育,2017(3):15-20.
[8] 聂迎娉,傅安洲.意义世界视域下课程思政的价值旨归与根本遵循[J].大学教育科学,2021(1):71-77.
[9] 杨威,田祥茂.“大思政课”的形态学考察[J].思想理论教育,2022(4):12-18.
[10] 张烁,鞠鹏.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刘云山讲话 王岐山张高丽出席[N].人民日报,2016-12-09(01).
[11] 叶方兴.大思政课: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延展[J].思想理论教育,2021(10):66-71.
[1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6.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
[14] 李合亮.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趋势[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2):22-23.
[15] 高国希.试论关于“大思政课”的几对范畴关系[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10):104-112.
[16] 冯秀军.善用“大思政课”的三个维度[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8):103-109.
[17] 潘理平,闫娜.从规训空间到生活空间:论知识教学空间的当代生存论转向[J].当代教育科学,2022(7):12-18.
[18] 邹诗鹏.转化之路:生存论续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18.
[19] 田晓伟.论教育研究中的空间转向[J].教育研究,2014(5):11-18.
[20] 许瑞芳,纪晨毓.“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社会生活省思[J].思想教育研究,2022(4):104-109.
[21] 张强军.“大思政课”的出场逻辑、比较优势与实践要求[J].大学教育科学,2023(2):33-40.
[22] 郭元祥.学校课程制度及其生成[J].教育研究,2007(2):
77-82.
[23] 徐益亮.意蕴、难题、任务:思想政治教育的诠释审思[J].思想教育研究,2021(8):57-63.
[24] 赵丽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范式构建与优化逻辑[J].思想理论教育,2022(2):46-51.
[25] 顾海良.深刻把握坚持问题导向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N].人民日报,2023-04-13(09).
[26] 沈壮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要论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6):1-8,155.
[27] 李敏.“大思政课”教育资源转化的方法论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 2022(10):74-79.
Realistic Pattern, Value Significance,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Nie Yingping Fu Anzhou
Abstract: The operation of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refers to the dynamic process of putting the thought of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to practice, which presents a multi-dimensional pattern of go-through operation, collaborative operation and panoramic 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and society.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between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to the panoramic linkage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social system, the operation of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constantly breaks through curriculum boundaries, gradually clarifies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all-round curriculum concept, relieves the dilemma of linkage between curriculum and society and solves the conundrum between "breaking” and “establishing" curriculum system.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operation of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we should enhance the synergy, narrative power, transformation power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of the teaching staff as operational empowerment, and forge a high-quality team of "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frequency, goals in the same direction, and actions synchronized"; strengthen problem awareness and highlight practice orientation to provide a starting point for the orderly extension of courses to the society; improve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upport guarantee mechanism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s operational solution, so as to better realize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Key words: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operation of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operating pattern; operating path
(责任编辑 陈剑光)
收稿日期:2023-10-22
基金项目:2023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课题“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进程中的‘大思政课共学·共研·共进教学模式研究”(23GXSZ034YB);2023年度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全社会参与‘大思政课建设机制研究”(23JDSZKZ05);2022年度浙江省教育厅课程思政教学项目“以文化人:统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建设的方法论研究”(浙教函〔2022〕51号)。
作者简介:聂迎娉,湖南邵阳人,法学博士,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与高等教育课程研究;宁波,315100。傅安洲,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