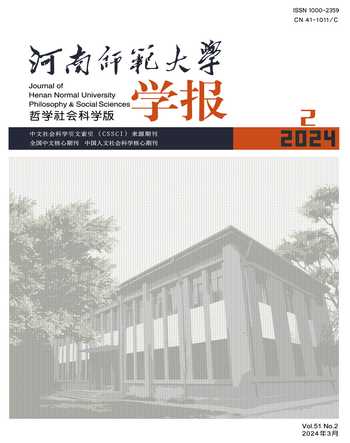论李贽对苏轼文学思想的辩证接受
梁博宇 朱万曙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4.02.18
摘要: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明代儒学思潮发生转向,以天理为本体的程朱理学开始退潮,而以情感为本体的苏氏蜀学受到空前关注。在此背景之下,李贽对苏轼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作为心学传人,李贽的“童心说”与王阳明的良知之说相去较远,而与苏轼的“情本论”比较接近。以此为基础,李贽对苏轼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深入体认,并分别从本体论、目的论、风格论和发展论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由于情理关系方面的差异,李贽在对苏轼文学思想的接受中又有所批评,形成了一种激进重情、影响深远的接受模式。
关键词:李贽;苏轼;文学思想;情本论;童心说;接受
作者简介:梁博宇(1993-),男,吉林长春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宋明文学与思想研究;朱万曙(1962-),男,安徽潜山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107)
中图分类号:I20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24)02013007收稿日期:20230708
晚明是苏轼接受史的高峰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引董其昌语称:“程、苏之学,角立于元祐,而苏不能胜。至我明姚江出,以良知之说变动宇内,士人靡然从之。其说非出于苏,而血脉则苏也,程朱之学几于不振。”随着阳明心学风行、程朱理学退潮,学理与阳明相通而与程朱对立的苏氏蜀学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作为苏氏蜀学的代表人物,苏轼在晚明士人心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人们不仅对其文学创作加以广泛认同,而且对其文学思想也表现出了深深的共鸣,泰州王门的传人李贽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
李贽对苏轼文学思想的接受并非偶然,而是时代环境、学理源流与人格取向三个背景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晚明是一个情感张扬、理性让位的时代,重理轻情的程朱理学在晚明的退潮是历史的必然。这一过程始于白沙心学对理学的剥离,成于阳明心学在理学之外的独造,炽于泰州学派向理学的激进冲击。苏轼的思想虽然在宋代不逢其时,但是在晚明则可谓是适逢其会。如果再从学理源流方面看,阳明心学本身与苏氏蜀学应有共通的学术立场。程朱理学曾以外在的“天理”为本体批判苏氏蜀学,而王阳明则在质疑理学的基础上纳理入心,主张天理不假外求,从而与苏氏蜀学在重视感性体悟的基本立场上达成同调。李贽属王门后学,其论学与苏轼相通,应属顺理成章之事。试举一例:李贽的《易因》多引用前人的《易》学论著作为附录,王畿和苏轼是其中被引最多的两位作者。王畿是阳明的嫡传弟子,李贽对其语录的引用频次略高于苏轼,但如以引用文字的篇幅与重要性而言,《易因》对苏轼思想的借用可能更重。在人格取向方面,苏轼与李贽之间大致属于本同末异的关系。若看表象,苏轼旷达、超越、圆融,而李贽则狂放、偏执、激进,二人性格迥异。然而从内来看,正如王水照所言:“旷和狂是相互涵摄的两环。但前者是内省式的,主要是对是非、荣辱、得失的超越;后者是外放式的,主要是真率个性的张扬。然而都是主体自觉的肯定和珍爱。”苏轼《东坡易传·同人卦》论人际关系云:“同人而不得其诚同,可谓同人乎?……天非求同于物、非求不同于物也……涉川而不溃者,诚同也。”李贽《易因·睽卦》则谓:“睽,天地之自然也。睽而合,天地之必然也。”“诚同”与“睽而合”同义,皆为无外在先验条件决定,不受任何功利因素影响的情感之同。李贽在阅读苏轼其人其作时,经常有与其情感相通之感,如与苏轼“披襟面语”。李贽论苏轼曾言:“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祗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我们从中不难看出李贽对苏轼人格的理解与认可。曾师事李贽的袁中道亦称李贽为“今之子瞻”,并谓之“才与趣不及子瞻,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其性无忮害处,大约与子瞻等,而得祸亦依稀相似”,可谓敏锐地抓住了二人人格上的共性。可以看到,人格取向上的同调构成了李贽接受苏轼思想的主要动力。
一
苏轼在历史上常以文学家的身份为人称道,李贽对苏轼的文学思想亦有精深体悟。他在《藏书》中将苏轼列入“词学儒臣”一类,并盛赞其文云:“嘻笑怒骂既是文章,则风流戏谑总成嘉话。”“奇正相生,如环无端。”但是,李贽反对人们只从文学层面去理解苏轼的思想,反对“无坡公之心而效其颦,无坡公之人而学其步”的浅薄行径。可以看到,李贽对苏轼文学思想的理解是建立在对“坡公之心”“坡公之人”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要全面认识李贽对苏轼文学思想的接受,就必须首先对二人哲学思想的异同做一番简要的梳理。
李贽虽为王门后学,但是其哲学思想中却有许多异于王学而同于苏学的成分,可谓是苏轼之学的异代传人,这其中最核心的层面就是本体论思想。程朱理学的本体论思想最为完善,但其立论基点却是难以确证、只能设定的“天理”;苏氏蜀学则主张以发自人类本能的情感为本体,即所谓“情本体”。苏轼在《诗论》中开宗明义:“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在《東坡易传·乾卦》中,苏轼系统阐述了“性”与“情”两个核心范畴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性”虽然是形上不可得而见的,但是却可以通过后天的善恶表现逆推出来。纯粹善与纯粹恶的个体在现实中都不可能存在,每个人的生命实践都表现为善恶行为。因此,如果从人后天的情理结构中去除一切的善恶属性,那么,就只能剩下“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之类的“性”。性不能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无法承担本体性职能,故人的本体只能是运动有为的“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以人的情感为人事活动的本源和根据,就是苏氏蜀学的“情本论”。这一本体论后来受到了程朱理学的批判,如朱熹谓之曰:“炫浮华,忘本实,贵通达,贱名检。”阳明心学经由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而建立,其对本体的理解有向苏氏蜀学回归的倾向。譬如,王阳明主张“心即理” “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作为人类先验的道德理性,始终是通过人类情感而呈现的。在重视情感、高扬个性、反对求理于外等学术立场上,王阳明与苏轼的态度是一致的;但是在对本体的伦理指向上,王阳明却和苏轼有着不小的分歧。苏轼认为作为本体的“情”没有先验的伦理属性,善与恶的行为,连同善与恶的观念本身,都完全来自后天的生命实践:“唯天下之所同安者,圣人指以为善,而一人之所独乐者,则名以为恶。”王阳明不反对“性善论”,他认为“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并进而取孟子“四端”中的“是非”一端加以阐发,认为“良知”先验地具备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由此,王阳明的“良知”虽在本体意义上无善恶可言,但是却具有导向善的倾向性。
李贽思想的本体范畴为“童心”。所谓“童心”,即“心之初”,或曰:“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李贽推求“童心”的理路,是从人类后天的表现入手,将一切外在设定和后天知识全部剥离之后再反推本性。他认为人生之初的心理结构中并无“闻见”“道理”,可谓是纯粹情感化的一颗“童心”,而随着年龄的成长,外来的“闻见”“道理”日增,人们的是非判断能力便不断地遭到外界信息的干扰,也就不免会导向“童心”失坠的结果。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童心”与苏轼所论的“性”一样,不可直接把捉,只能从人的后天状态入手去进行推求。与王阳明之“良知”相比较,李贽之“童心”受龙溪、心斋之说影响显然更重,即重本体而轻工夫。而李贽论证“童心”的模式,也是取自苏轼《东坡易传》中实行的消除善恶、复见本性的逆推理路,只不过苏轼以此论“性”,李贄则以此论“情”而已。立足于“童心”这一范畴,李贽的性情论便与苏轼有不谋而合之处。苏轼在《东坡易传·乾卦》中说:
情者,性之动也。泝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无我,则谓之命耳。
李贽在《易因·乾卦》亦云:
乾之为贞,实德也,所谓性情是也,人与天也,圣人也,皆具之,故不别其孰为性,而孰为情,孰为利,而孰为贞,使知其不可离也。
在苏轼的哲学体系中,命、性、情三个范畴是统一的。不但性无善恶,而且情亦无善恶,善恶只是情感活动的结果。由是推之,则无所谓天人之辨,每个个体的人格都达于天命,得以无所依傍地独立于世间。在李贽的思想中,他则将“命”这一不可知的形上范畴拆分成了“利”与“贞”,将性、情、利、贞四者完全放在同一水平线上加以观照,皆将其视为无伦理指向、无本质差异的范畴。至于对天人关系的论述,李贽更直接取自于苏轼,且将天人关系下推至圣凡关系,鲜明地突出了个体的道德自足性。苏氏蜀学“情本论”强调情感自由流动而无所约束,不对善恶作先验的规定,这就导致人们对人类人格境界的讨论就只能依赖其自身的道德自觉。朱熹对苏轼的人格才气颇为赞赏,却痛心疾首地批判苏轼“学术不正”,其担心之处就在于恐其养成后学险慢的习惯。阳明心学正是以有所约束的“良知”而非绝对自由的情感作为本体,以正面伦理属性否定了其中“恶”的趋向,才得以在与程朱理学的论争中不落下风。因此,从学理发展的角度而言,王阳明的“良知”之说在本质上是对苏轼“情本论”的深化和发展,但是李贽的“童心说”则更加激进,它在舍弃了王学的一部分厚重性之后,反向地趋近了早出的苏氏蜀学。从这层意义上说,较之阳明“良知”之说,李贽“童心说”反倒有某种混淆善恶的自然主义倾向。
二
在文学本体论方面,李贽与苏轼皆以人类本真情感为文学之本体。苏轼在《自评文》中,将其文喻为“万斛泉源”,并总结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创作规律。苏轼认为,并无一个具体确定的外物作为本源,故只能以自发自生的泉水为喻体。文似水无常形,随物赋形,变化往来,无始无终,其中的规律不受外在的理性支配。文即是情感的外化。对“所当行”与“不可不止”的判断,正如水的随处流动一般,只凭自然规律赋予人的情感随处发用即可。这样的情是“可知”的,相较于外在、蹈虚、设定的理,它具有内在、亲切、可证的优势,故当仁不让地构成了文之本体。他在《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中自述其创作状态时亦云:“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可见,苏轼视域中的文是人类情感的自然表达,文的创造之力来自人类无法抑制的表达欲望,而创作的整个过程即是对情感的直接吐露。李贽认同苏轼的情文思想,并在具体的创作中加以践行。汪本钶曾称其师的创作状态是“无有怀而不吐”“若茹物噎而不下,不尽至于呕出亦不已” 。这一创作状态基本上就是苏轼“必吐出乃已” 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376页。之说的再现。相较苏轼,李贽对文学本体的阐发更为直截、明快。他在《童心说》中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直接点明“至文”必须源于人类的原初之情,否则便会因虚假而失去其价值。对于矫情而为的文艺作品,李贽的批判更加激烈,表现出更为决绝的情本主张。
在文学目的论方面,李贽与苏轼皆主张超功利性的文学创作目的。苏轼在《答李端叔书》文末曰:“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具体而言,“非文”并不是指没有文采,而是指整个创作过程没有加以刻意的文饰;“信笔书意”仅指表露一刹那的那种最真切而无外物影响的情感;“不觉累幅”指文章长短不拘,不受外在格式的限制;“不须示人”更指那些没有功利指向,纯粹为内心自适的文章。苏轼的此论当然不是在反对实用性的文章,事实上,他的应用文写得极好,他所写的章、表、策、略皆已被明清文人奉为典范,尤其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他强调文章的现实价值,更提出了“有为而作”的创作宗旨。但是,从文章的艺术性角度而言,应用文基于接受的目的,不得不在格式、文法、措辞、用典等行文技巧上下功夫,以至于作者的真实情感常常被这样的技巧给掩盖住了。譬如,在《答刘巨济书》中,苏轼就曾对自己在应举时创作应用文的历程颇为羞愧,以为是不得已而作,而他最喜爱的无疑是那些能表现其个人真实情感,“未尝敢有作文之意”的创作。李贽欣赏苏轼的“大文章”,曾赞之曰:“真忠肝义胆,读之自然恸哭流涕。” 但是,他又会从文学创作的标准,认为那些“大文章”是“长公俯就世人而作”,“终未免有依亻放在” 。其实,李贽最推崇的正是苏轼那些“片言只字与金玉同声”的小品文。
在文学风格论方面,李贽与苏轼皆主张适应各人情性,自然而然地确定风格。苏轼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曾经提出一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并不指向某种固定的风格,而是基于个体内心独特情感自然生发而来的创作风格。李贽在《读律肤说》中更加具体地阐释了这种境界:“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在李贽看来,“礼义”不外乎“情性”,文学的价值应源于情感的自然流动,它不应受到某种具体风格的约束。除此之外,李贽与苏轼又都反对那些对文学风格有统一要求的外在规定。苏轼曾批评王安石的文学观,指出他的文艺创作未尝没有一种优美的风格,但是他错就错在对这种风格的有意推行,以至衍生出“弥望皆黄茅白苇”的创作倾向。以不同之情作同调之文,往往会表现出本体与现象无法吻合的情况,其结果必然使那些文艺创作失去直指人心的魅力。苏轼此论从反面的角度批判了个人情感与文学风格的割裂,李贽则经常从正面加以直陈:“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论中所谓的清彻、舒徐、宣畅、疏缓等语皆是泛指,真正需注意的则是“情性自然”四个字。各人的情性只有自己才最了解,所以,每个人创作风格不可能由他人决定,更不能去遵循某种外在的创作规范。由于李贽经历过“后七子”所引领的复古浪潮,对复古派一味模拟古人、缺乏个性风格的创作现象多有了解,所以,他常常会以此而论,将文与情一起提到价值独立的高度。
在文学发展论方面,李贽与苏轼皆主张文风顺时而变,反对守旧复古。古代文艺之正变,历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在苏轼看来,文学虽有正变之分,但所谓“正体”只限于某一具体的时间段。一旦世殊时异,则过去的“正体”必然会被时代所抛弃,而过去的“变体”或将成为新时代的“正体”。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苏轼举《离骚》为例,认为后者虽为“盖《风》、《雅》之再变者”,犹可争光日月,自成一家。苏轼以变化的眼光看待古代文体的发展,为各类文体之变体的出现进行了合理性的论证。需要注意的是,苏轼求新求变的本质,是让情感与文学本身的规律相合。苏轼认为创作者真正追求的,并不是文体的外在变化,而是文体变化的内在规律。进而言之,对变化规律的体悟最终导向的是境界的提升,即将变化规律内化于心,让情感的流动自然地与文学本身同调,“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至于為追求刻意出新而导致的造作破碎的文艺风格则是苏轼一直所坚决反对的。
李贽对此有深深的共鸣之感。在他看来,苏文之所以能做到独步千古,其原因正在于“下笔不作寻常语,不步人脚” 。李贽对于文学的发展亦采取一种任情所之、顺其自然的态度。在《童心说》中,李贽认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 ,并认真仔细地考察了各类文体的变化历史,他以“童心”为统领,不仅将六朝诗、近体诗、传奇、院本、杂剧等并举齐观,而且将“童心”提升到衡量所有文类的最高标准。另外,李贽也将八股文平等地纳入评判对象之列,显示出了较苏轼犹有过之的批判态度。
三
李贽对一己个性极为重视,反对盲从古人,所以,他对苏轼思想的接受也不会全盘照搬。具体而言,苏轼、李贽的思想虽然都赞同以情为本,但是在情与理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存有明显不同。苏轼以情理圆融的中庸之道为主,李贽则表现出对重情轻理的倾向。以情理圆融为目标,最终是以浑厚的境界为导向的,而以重情轻理为目标,最终导向的则是情理之间激烈的冲突。
李贽对苏轼思想的变革有时代、学理和人格三个方面的因素。从时代的视角来说,苏轼生活在北宋中期,正是君主“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时代。其时政治风气相对宽松,士人取向较为多元,国家忧患隐而未现,所以思想界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蓬勃气象,洛学、蜀学、新学、朔学等一时俱盛。李贽生活在晚明时期,其时君臣对立,士人对皇权的疏离与日俱增。
譬如,曲家宋承荫,史载“丙辰谒铨,曹考中花县,因误听改州倅,遂拂袖归,偃仰于水云居中,无复仕进意矣”。再如洪嘉植,史载“以布衣而谈理学,各公卿尝上章荐举,解以亲老不就”。李贽认为,当此“大过之时”,“不可寻常守辙,必有大过人之行,乃可所谓能为人所不敢为者”。传统儒学所标举的中正平和之道,至此已基本失去其现实意义。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大过之人”站出来,以他人之所不能为的激进姿态打破僵局,或许才能达到否极泰来的局面。显然,李贽与苏轼所面临的历史语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再从学理方面来看,苏轼尽管建立了以情感为本体的哲学体系,但是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主流思想的影响而重视理性;李贽则在一定意义上直接继承龙溪、心斋等,解放个性、脱略工夫的学统,不计较严密的理论,仅追求一己情性的无限张扬。最后从人格方面而论,苏轼虽有直言忤世的一面,但通常都是就事而言,不欲与人发生争执;李贽则有“性甚卞急,好面折人过”的狂傲之性,他和耿定向等人的争端已成为晚明公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苏轼论文学重情而不轻理。他曾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批评他自己所写的词,“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在他看来,凭借“豪放”的情感固然能写出“警拔”之词,但过犹不及,一旦让情感过于张扬而无约束,也可能会不符合自然之道。李贽论文学对情与理的理解不完全同于苏轼。李贽《坡仙集》选录苏轼之文,常常就其情感充沛之处圈点称赞,但是在其转入说理处则予以批驳。譬如,《赤壁赋》本为千古名篇,李贽却在“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数句之下曰:“正好发挥,可惜说道理了。……俗气甚。”而对苏轼一些似乎不合常理的论说,李贽则常常予以赞赏。譬如,苏轼《孔北海赞并叙》反对前人对孔融“才疏意广”的批评,认为孔融未能诛杀曹操,反被其害,实为天欲亡汉之故。从议论的严密性看,苏轼此论归因于天,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但是,苏轼不以事业成败而以对人情的揣度为批评标准,认为孔融真实而曹操虚伪,故前者理应战胜后者,鲜明地体现出一种情感驱动的道德史观,故李贽对此文大加赞赏,连连圈点,又批“可感”二字。从李贽对苏轼文章的批点中,似能洞见他在接受苏轼时的心理历程,即他平生自视极高,落落寡合,就连在当时引为同道的晚辈焦竑、袁宏道、袁中道等人,也都在其思想日趋激进之后与他渐渐疏离。于是,当无法在现实中遇到知音时,李贽便将数百年之前的苏轼当作了知音,一方面与其“披襟面语”,另一方面则由此滋生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遗憾的是,苏轼不能复生,他的中庸境界只能让李贽望而却步。他明知“道本中庸”,认为中行之道是圣人境界的体现,却又不得不慨叹“中行真不可以必得也”,黯然接受了自己被时人“谓之妖人”的命运。从这层意义上说,李贽对苏轼的接受是片面性的,他需要极度放大、张扬苏轼重情的一面,而又要刻意回避或批评苏轼不轻理的一面,以便让他心目中的苏轼能够真正成为他的同道。唯有如此,他才能“求以快乐自己”,然后“可托以不朽”,显示出了浓厚的孤独感和悲剧性。
李贽在晚明名震一时,影响极大。焦竑、汤显祖、董其昌、钱谦益、金圣叹等人,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都一度或始终心折于李贽的思想,并进而对它多有借鉴和发挥。因此,李贽对苏轼思想的接受与改造亦对时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客观地说,李贽对苏轼思想中重情一面的发扬,极大地迎合了晚明士人普遍重情轻理的风尚。晚明士人读苏、谈苏、学苏成风,虽不能说是由李贽所起,但李贽对苏轼思想的辩证接受的确于此有推动作用。曾受教或认同于李贽思想的晚明士人,几乎无不对苏轼赞不绝口。如袁宗道平生“嗜长公尤甚”;袁宏道更是称苏轼为“天西奎宿”,谓其诗文“有天地来,一人而已”,他们相关思想的形成应该都与李贽有关。
然而,李贽对苏轼思想的接受亦不乏负面意义。苏轼所始终追寻的儒家中庸境界,到李贽这里被彻底放弃了。经李贽圈点批评后的苏轼,实际上是一个李贽理想语境中的苏轼形象。这一形象在主体精神和自由人格的发扬上已超越历史上的苏轼,但是在情理冲突的弥合与中庸境界的求索上却断然止步。李贽对苏轼较为全面的体认,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诚同”人格的一种偶然,这难免会影响后人对苏轼的理解。譬如,苏轼的小品文在晚明得到了广泛的接受,编集批点者众多,而其对政治、社会等宏大问题的论述则往往被弃之不顾,袁中道对苏轼“小文小说”与“高文大册”境遇的对比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现象。更有甚者,公安派诸子在阅读苏轼时,会在李贽视角的基础上将其塑造成一个公安式的超然自乐者,而对苏轼深沉厚重的理性思辨进行了忽略处理。譬如,袁宗道喜读苏轼“山林会心语近懒近放者”之类的诗文,袁宏道便据此以为袁宗道与苏轼已形成境界上的呼应,“真是一种气味”。事实上,在苏轼文章的语境中,“懒”与“放”从来都只是其最浅层意境的表达,“懒”的背后是对庸常事务的超脱,“放”的基础则是对卑俗情感的超越,袁氏兄弟显然没有参透这一点。
总之,在晚明诸子中,李贽对苏轼文学思想的接受是最深入和最全面的。他的这一接受实践既证明了苏轼思想历数百年而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又体现出了晚明思想尤其是泰州王学的独特风貌。从这层意义上看,李贽对苏轼文学思想的辩证接受,不仅赓续了苏氏蜀学以情为本的血脉,也极大地推动了苏轼及其文学作品在后世的传播。
[责任编校海林]
——以黄麻士绅纠葛为中心的讨论
——《李贽学谱(附焦竑学谱)》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