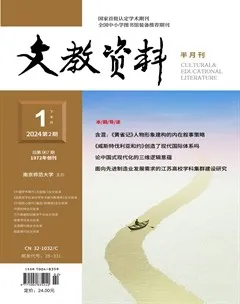新历史主义视域下对叶兆言小说《状元境》的解读
张双笑
摘 要:
叶兆言的小说《状元境》以民国时期为叙事背景,深入历史裂隙进行独特的开掘与想象,完成了主流之外的历史述说,建构了虚实相生的新历史叙事。小说有意疏离单线化的正史,通过不同立场的人物视角,再现了纷繁复杂的战争历史,同时聚焦于历史的个别之处和偶然事件,着意书写“英雄”的风流史和失意史,完成了复线历史的增值。小说搁置了宏大历史与重大事件的书写,转而观照和审视小人物的个体命运,聚焦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实现了大写历史的小写化,丰富了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图景,给读者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叶兆言;《状元境》
叶兆言作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作家,他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如《状元境》《追月楼》《半边营》等作品,以民国时期南京的风云激荡为背景,描写了战争与政治变革下旧式家族之间、男女之间的矛盾冲突、情感纠葛以及人性细微处的隐秘,体现了对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
与叶兆言其他作品相比,《状元境》虽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其独特性与艺术魅力依然不可忽视。目前,学界对叶兆言作品的研究主要包括从城市空间美学角度分析其作品中的“南京想象与书寫”[1],从叙事模式角度分析其小说中叙事人称的嬗变及美学意义[2],从悲剧美学角度分析叶兆言小说中悲剧意蕴的内涵及审美价值[3],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分析其小说中的回忆视角、“潜藏式”叙事等特点[4]。纵观这些研究成果,鲜有研究者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状元境》中历史的别样书写和小人物的命运起伏。《状元境》小说中潜在的民国历史背景、对俗世生活中边缘人物的刻画等,以及叶兆言的“南京主题”为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该小说增加了可行性。
一、深入历史裂隙间的独特开掘
传统史学认为历史是按照客观规律单线发展的,新历史主义则认为,已经流逝的历史极难重现,“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5]。而文本在构建历史时,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对过往历史进行事实筛选和梳理后成为“大写的历史”——正史(History)。这种“单声道”“一元化”的主流历史叙事不可能将历史过程的丰富多样性一网打尽,所以新历史主义者将目光投向那些游离于正史之外别样的历史景观,对普通史学家不曾关注的历史裂隙进行纵深开掘和独特阐释,这种新的探索把以往所谓的单线“大写的历史”拆解成无数复线“小写的历史”(Histories)。[6]
(一)主流之外的历史述说
主流书写的历史文本多着眼于重大的历史事件,注重阐释其深刻的社会意义。然而对一个历史时期的叙述,如果只关注已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和当时的风云人物,就无法涵盖历史的方方面面。叶兆言作为有意挖掘历史的小说家,他避开主流的历史述说,而在历史长河中打捞失落的细节。《状元境》讲述了民国时代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英雄”短暂的司令生涯,以及民间艺人张二胡与姨太太沈三姐的爱恨纠葛。“英雄”在一次行动失败后依着二胡声中寻至张二胡家,在他的家中躲过追捕,由此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命运轨迹发生了重合。“英雄”认为张二胡是自己乱世中的知己,因此让张二胡担任司令府的专职乐师。张二胡本是个性格懦弱的底层艺人,因会拉二胡而成为司令府的红人,并意外娶到被“打发”的美人沈姨太,可“抱得美人归”的他,婚姻生活中却充满了吵闹与耻辱。为了躲避家庭纷争,他外出经商并意外暴富,成为状元境中有钱体面的“老爷”,而沈三姐却在这时不幸染病,不久后离开了人世。小说中,无论是“英雄”成为司令的跃迁史,还是革命行动的起因或失败原因,抑或是张二胡经商致富的发迹史,作者都用模糊的叙述轻轻掠过,转而对司令身边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人生际遇倾注了大量笔墨,从历史的裂隙进行深入开掘和独特阐释,呈现出更复杂、更细微的侧面。
(二)虚实相生的历史建构
叶兆言以真实的历史素材为灵感来源,结合他对南京历史、文化的切身感受,在《状元境》中对民国时代的南京历史进行了“虚实相生”的建构。该小说开头以“走街串巷”的视角,实写南京状元境、夫子庙、秦淮河一带的环境,从状元境小小的一条街南去几十步,就到了历朝历代文人骚客牵肠挂肚的夫子庙,再就是桨声灯影的秦淮河,这繁华的沿岸无不透着六朝的金粉、烟水气。而立在文德桥上,那位“怜爱美人”的“英雄”,则是作者虚构的小说人物之一。这位“英雄”在状元境西头经营着同盟会的一个秘密据点,后来成了一名司令,在大大小小的战事中,仍保留着侠客骨子里的“英雄气”。在南北军交战中,他的队伍禁不住北军的运动而倒戈,他恨不得只身披挂上阵。在这十万火急的关头,“英雄”束手无措,便想去与自己的姨太太倾诉心肠,却无意间撞破姨太太与何副官通奸的丑事。作者将这些民国不同派系争斗的历史史实,与精心设计的后宅故事交织在一起,让沉睡在文本中无言的历史焕发出言说故事的活力。
二、单线历史的复线化书写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应该回归历史。文学文本作为时代的产物,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它反映了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7],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文本了解历史。但是传统的历史文本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这种“单声道”“一元化”的历史述说无法全面客观地覆盖历史真理,历史的真理性需要多元化的文本从不同的角度来共同体现。因此,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有意疏离权力话语撰写的单线的正史,提倡从一些历史碎片中挖掘真实历史的踪迹,或根据某一线索进行生发来完成复线历史的增值,以此努力恢复历史多元复杂的真实样貌。[8]作者在《状元境》中叙述二次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没有正面书写轰轰烈烈的革命历程和重大的历史意义,而是拨开主流历史的面纱,一一细数那些成败背后纷繁复杂的矛盾线。作者透过立场各异的人物的视角,关注历史的个别性和偶然性,多角度地展开对历史的想象,实现了单线历史的复线化书写。
(一)多重视角揭示复杂的矛盾线
《状元境》通过司令、军官、商绅等不同立场的人物的视角,再现了纷繁复杂的战争历史。“英雄”是同盟会的成员,偶然发迹成为革命党的一个司令,然而他骨子里本是个侠客,只懂得单枪匹马地蛮来,并不懂得调兵遣将的方法,也缺乏带兵作战的经验。而他手下那一批唯利是图的军官,向来就是谁有钱便为谁卖命,一经北军来运动便倒戈,“那些职业军官,有的准备作鸟兽散,有的准备鼓噪哗变,没一个用心是好的[9]”。连番的战火之下,驻守南京的“英雄”失去了后援,军费也难以筹集,商绅们不肯交军饷,他们“眼见着南军每况愈下,只差树倒猢狲散的份儿,有心省下一笔款子来,留着北军来时可以敷衍。”[10]“英雄”一时孤立无援,陷入了困局之中。作者借多重人物视角既揭示了战争中错综复杂的矛盾线,也阐明了革命失败的原因:战争双方不仅力量悬殊,而且革命党缺乏斗争经验、无指挥策略,军官们各怀私心,军队力量涣散。小说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正面描写战争的叙事模式,深入挖掘战争背后的各方矛盾,完成复线历史的创作尝试,使隐匿在“单声道”“一元化”历史述说背后的复线历史浮出水面。
(二)关注历史的个别性、偶然性
“在一般性的历史总貌、历史规律与个别的历史事件之间,新历史主义历史分析的兴趣、着眼点在于后者。”[11]新历史主义者不再追求整体把握历史的总貌和必然逻辑,而是从个别之处、偶然事件中尋求历史的踪迹。作为新历史主义历史观的践行者,叶兆言从民国历史的边缘地带出发,串联起个别的、偶然的事件,试图还原历史纷繁复杂的本来面貌。
《状元境》的开头从一处特殊的地点——南京的“状元境”展开,这是一条充满市井气息的小街,街上挤满了贩夫走卒。这条街向来是繁华之地,紧邻夫子庙和秦淮河,氤氲着六朝的金粉和烟水气。到了辛亥革命前夕,这里桨声灯影依旧,历朝历代流连此地的文人骚客,已改换为一波又一波新式旧式的军官,“英雄”便是其中的一员。同盟会的秘密据点之一就设在状元境西头的一家货栈里,“英雄”等人在此进行着秘密工作,也在此贮存南来北往的军火。由此可见,状元境虽是边缘地带不显眼的小街,却在历史的旋涡中生发着独特的故事。作者对这一个别之处的关注,消解了单线历史的全局性描写、全景化书写的局限。
“英雄”经营的货栈里,伙计炮制的土造炸药不慎爆炸了,怕引起清朝巡警的注意,货栈里的人员都躲了出去,连着两三天平安无事后,大家才敢返回。闲逛时,“英雄”听着街边的二胡声忽然变得激昂起来,仿佛预示着什么一样,果然,两名返回的伙计刚跨进货栈门就被巡警团团围住,拼死抵抗之下仍然伤亡惨重,只有“英雄”逃过一劫。他寻着二胡声找到张二胡家里,躲了一夜。清朝灭亡,民国时代随之开启,南京光复,“英雄”也侥幸地成了司令。叶兆言将这样成败都带着些“意外性”“不小心”的人物称为“英雄”,将历史分析的兴趣与着眼点放在偶然事件上面,而这一系列偶然事件的串联,集中展现了民国历史背景下边缘人物的命运起伏,实现了单线历史的复线化书写。
三、大写历史的小写化
新历史主义者将历史看作一种叙事话语,认为主流的历史叙事在权力编码下,形成了带有宣传与教化色彩的宏大历史述说,被称为“大写的历史”,否认了“以叙事的形式再现的历史有如真实历史一样的实在性”[12]。如果要触摸真实的历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就不能只关注正史文本,而需要重视“边缘、次等文化”[13],深入文学文本、地方志、档案材料等历史细部,“用厚描的方法考察横断面的历史”[14]。因此,新历史主义者将目光转向那些被正史遗落的、边缘地带的“小写的历史”,以此来颠覆“大写历史”的叙事模式。《状元境》搁置传统历史小说常写的战争场面、社会变革和英雄人物的大起大落,转而书写“英雄”的风流史与失意史,关注历史的个别性和偶然性,并对小人物的个体命运进行观照和审视,实现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小写化。
(一)隐退宏大历史的细部书写
“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15]叶兆言在叙述战争的宏大历史时,采用了“压缩”“隐去”的叙事技法。如“英雄”发迹之后成为司令,这一过程必然涉及战争和革命,而作者却有意隐去了这些宏大历史叙述,将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压缩为寥寥几语:没几年却发迹做了个什么司令。作者将叙事重点放在“英雄”的风流史和失意史上,“英雄”成为司令后终日流连于秦淮烟花之地,“公务之外,司令的精力便用在美人身上。当年南京的头面人物,商会的财神,翰林出身的耆儒,老名士,风流教主,有的慷慨送银子,有的做诗填词捧场,有的牵引着往风流的场所跑,游画舫,逛青楼,南京凡是略有些名声的香巢,不多久就让英雄司令访了个遍”[16]。荒淫度日的“英雄”在大敌当前时难以应战,手下离心、心腹背叛,甚至遭到昔日红颜知己的背弃,陷入了失意之中。透过革命党司令“英雄”醉生梦死和失意潦倒的个人经历,可以看到革命党的软弱、妥协和空有“英雄气”的一面,体现了作者挖掘历史真相、反思战争的责任感。
小说中还有一处对战争的描写,避开了双方交战的前因后果和对战争进程、战争场面的描写,而是从沈三姐让张二胡替她买零嘴儿这一处生活细节写起。张二胡知道外面炮火连天,不愿外出,但沈三姐不依不饶,无奈之下他才起身出门,然而兵荒马乱之下,沿街的店铺无一开张,只得无功而返。小说放大了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把宏大的历史事件用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不再将战争和权力争斗的大事件作为叙事的重点,而是从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着手,对历史细部里的零星插曲进行独特的开掘。
(二)小人物个体命运观照和审视
小说的另外一条故事线写了民国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张二胡和沈三姐)的命运起伏和悲欢离合。张二胡是个本分木讷的民间艺人,因善于拉二胡结识司令,在司令府谋了一份差事,这才有机会认识泼辣大胆的姨太太沈三姐。沈三姐本是妓女,后做了司令的姨太太,她不甘在司令府寂寞度日,便与大大小小的军官纠缠不清,后来意外败露了私通之事,被“打发”给张二胡做老婆。“下嫁”给张二胡后,沈三姐还像姨太太一样养尊处优,对待懦弱的丈夫盛气凌人,与泼辣跋扈的婆婆针锋相对,甚至彻夜与地痞无赖赌博厮混,张二胡为此常年受到邻里的嘲笑,后来他经商发迹后返回状元境,仍有地痞无赖嘲笑羞辱他。面对杨矮子的一再挑衅,张二胡一改往日小心翼翼的样子,愤怒地大打出手。张二胡揍了杨矮子之后,沈三姐感到十分痛快,特意备了酒菜,又让侍女去剁了当地特色的盐水鸭来下酒,为丈夫张二胡庆祝,庆祝这个状元境中出了名的窝囊男人从此能雪洗耻辱、扬眉吐气。不仅如此,沈三姐看到原本软弱木讷的丈夫,为维护自身尊严奋起还击,便从心底接纳了张二胡,不再与车行里的马夫厮混,甚至在染病去世前展现了温柔、宽容与体谅的一面。
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小说多为帝王将相做传,《状元境》从偏僻的历史边缘地带,用极为丰富细腻的笔墨描写了民间世俗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如沈三姐才嫁给张二胡时,躺在床上养病,张二胡的寡母起初还照料她的起居,但很快就看不惯她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尤其见不得张二胡为她“买零嘴”“倒马子”,于是张二胡的母亲与沈三姐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争吵,这种满是污言秽语的争吵和张二胡两头受气的“窝囊”,成了状元境这条巷子里邻人之间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笑料。小说对民间艺人、妓女、寡妇等小人物的个体命运展开书写,展现他们晦暗纷乱的非理性世界和人性中的闪光之处,构成丰富具体的小写历史,让微弱沉寂的历史事件发出了声音。
四、 结语
叶兆言的新历史小说《状元境》有意识地开掘民国时期的南京历史,以作家独有的细腻敏感捕捉主流之外的历史光影,并展开丰富的想象与独特的阐释,构建了虚实相生的新历史小说叙事。小说通过司令、职业军官、商户以及普通市民等不同立场的人物的视角,揭示了盘根错杂的矛盾线,再现了纷繁复杂的战争历史。并且从状元境这一边缘地带展开叙事,关注个别的历史人物和偶然的历史事件,丰富了小说中的历史图景,完成了单线历史的复线化书写。小说搁置了传统历史小说常写的战争场面、社会变革与英雄人物建立的功勋,转而书写英雄的风流史与失意史,从中提炼出战争失败的原因,并对这一位空有“英雄气”的司令报以惋惜和悲悯,体现了作者深挖历史、反思历史的责任感。小说另一方面集中书写小人物的个体命运、悲欢离合,关照和审视普通人的俗世生活与心理状态,实现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小写化。
参考文献
[1]欧阳一菲.叶兆言小说的城市空间美学研究[J].当代文坛,2023(6):135-140.
[2]尹林.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叙事人称的嬗变[J].文學评论,2023(3):61-69.
[3]井敏.叶兆言小说中的悲剧美学研究[D].西安:长安大学,2021.
[4]王饶梦.浮世沧桑——论叶兆言小说的历史叙事[D].昆明:云南大学,2020.
[5][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
[6][7]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J].文史哲,2001(5):26-32.
[8]安婷.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新时期战争小说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21.
[9][10][16]叶兆言.枣树的故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2,10,6.
[11]蒋述卓.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1.
[12][13] 金永兵.论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旨趣及其文化影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69-77.
[14] 胡作友.在史实与文学之间穿行——解读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1):89-94.
[1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