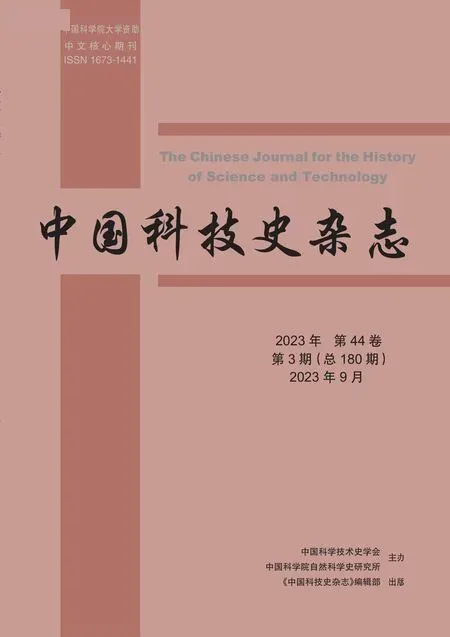清代进口钴玻璃颜料smalt的中文名称、贸易来源与应用历史
刘梦雨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北京 100009)
smalt是一种以钴玻璃研磨而成的蓝色颜料。smalt一词来源于意大利语smaltare(熔融)([1],页352)。这一名称反映出它的基本制备工艺:将钴矿石、石英砂和草木灰混合后,加热直至熔融,所得的类玻璃状物质经过研磨、筛洗,即成为粉末状蓝色颜料[2]。
smalt大约问世于15世纪的欧洲,广泛应用于16—18世纪的各类美术品,同时也用作陶瓷的着色釉料([2],页113—115)。它长期被视为天然石青和青金石唯一的人造替代品,直到19世纪法国化学家合成了群青,其生产与应用才逐渐衰落。
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表明smalt也曾传入中国,其在清代中国文物中的检出近年屡见报道,日益引起研究者重视。但是,关于这种颜料在清代中国的贸易及应用状况,尚无研究成果问世,甚至连其中文名称也尚未确定。
本文意图探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为这种颜料的历史研究做出初步探索:一,清代人如何称呼smalt?二,smalt何时进入中国?能否明确其应用时段?三,smalt的来源与贸易渠道怎样?四,smalt在清代有怎样的具体应用?
1 smalt、钴玻璃、钴蓝釉和钴青料
smalt是一种钴显色材料。Co2+离子溶解在玻璃态硅酸盐中呈现蓝色,为制造玻璃、釉料和颜料提供可能。要讨论smalt,就有必要先厘清几个与钴显色材料相关的概念。
狭义上的“青料”一词,特指青花瓷所用的颜料;广义上,“青料”泛指以钴为着色元素的蓝色色料,用于制造玻璃和釉。钴青料并非某种特定物质,而是一类色料的统称,因此历史上存在多种不同称谓,所指代的具体材料也不止一种[3]。
钴玻璃是用钴青料、石英和助熔剂制成的蓝色玻璃。古代中国的钴玻璃制品既有本地生产,也有国外输入[4]。
钴蓝釉是以钴青料发色的蓝色釉,实质也是钴玻璃。中国古代的钴蓝釉最早见于唐三彩,明清时期的霁蓝釉、洒蓝釉、孔雀蓝也都属于钴蓝釉。
smalt是钴玻璃研磨成的粉末,可作为蓝色颜料使用,由于Co2+离子的配位数变化,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褪色([2],页120)。
有学者认为钴玻璃和smalt是原料和成品的关系[5],这种说法易令人误会工匠是购进钴玻璃作为原料制造smalt的。实际上,smalt通常直接以钴土矿或zaffre(1)一种通过焙烧钴矿石获得的深蓝色物质,其成分是不纯的氧化钴或砷酸钴。见参考文献[1]第409页。为原料生产,钴玻璃是这一生产过程的中间产物——得到钴玻璃之后,再将其研磨为细粉,就是smalt。
2 科学检测案例所见smalt的应用范围
近年来,经由科学检测在中国文物中发现smalt的案例不断见诸报道,涵盖建筑彩画、壁画、彩塑、彩绘器物、家具、石刻等等多种文物类型,在漆器中也有应用(2)有文献提到Julie Chang在一件清代中国漆器中分析出了欧洲生产的smalt,但该结论尚未正式发表。。故宫[6,7]和清西陵的多个建筑彩画案例表明,这种颜料在清代皇家营造工程中有稳定使用。
就时间范围而言,年代较明确的案例主要集中在清代中后期,少量来自清早期,尚未发现年代更早的案例(3)已发表文献中有些案例被认为是明代的,如常熟彩衣堂建筑彩画、山西长子崇庆寺彩塑等,但其年代均为文物主体断代,彩绘层的断代尚存疑问。。就地域范围而言,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和华东地区,同时也有一些案例来自西南地区[8]。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既有分析检测工作主要基于近年来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样本在时代和地域上并非随机均匀分布,因此,就以上案例判断smalt应用的时代和地域范围,未必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但目前至少可以认为,清代中后期的北方地区,smalt作为彩绘颜料曾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且已知的时间上限不晚于乾隆初年。
3 smalt的中文名称
清代的中国人到底如何称呼smalt?回答这个问题,是获取其相关史料的首要条件,也是对其展开历史研究的第一步。
3.1 “花绀青”考辨
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smalt的中文名是“花绀青”,称之为“中国人自己给它的名称”[5],并倡议恢复这一“历史上的中国名称”[5]。这一看法是否可靠呢?
清代匠作则例中有数量可观的彩画作工料及价值则例,既然smalt作为建筑彩画颜料在清代皇家营建工程中有大量应用,就必然出现在当时针对这些营建工程而编修的则例里。但是,“花绀青”一词却并未见于存世的任何一种则例——实际上,此词甚至未见于任何现存的中国古代文献。
古代汉语中只有“绀青”一词,用于表示颜色,而非颜料。《辞源》对“绀”字的解释是“天青色,深青透红之色”[9]。“绀青”一词多见于佛教文献,形容佛之发色,例如唐代释法琳《辨正论》:“如来……顶有肉发,其发绀青。”又如《八闽通志》:“取南烛木茎叶捣碎,渍米为饭,染成绀青之色,谓日进一合,可以延年。”[10]
“花绀青是smalt的历史名称”这一观点,唯一的依据,就是万希章的《矿物颜料》一书。但此书出版于1936年,并不能证明清代的情况;而即使在民国文献中,花绀青也并非smalt的通行称谓。1911年出版的《汉译麦费孙罕迭生化学》中也提到了smalt:“钴之化合物,若与玻璃融合,则令之现极蓝色。此种玻璃若系粉屑,则可用为一种颜料,名曰洋青(smalt),钴盐之晶体。”[11]此书系由英文直译,书中将smalt译为“洋青”,而未提及花绀青。
那么,万希章书中的“花绀青”一词从何而来呢?
实际上,“花绀青”是一个日文词汇。这个词源自日文中更古老的“绀青”一词。日文“绀青”词义与中文不尽相同,在日文中,它可以指深蓝色,也可以指深蓝色颜料(4)近代以来,日文中“绀青”一词指称颜料时,通常指普鲁士蓝,日英词典一般也将 prussian blue释为“紺青”。但这显然是晚出的语义,因为普鲁士蓝1782年左右才传入日本。。平安时代的《新猿乐记》中就有一则从中国进口“绀青”颜料的记录[12],这里的“绀青”指的是蓝铜矿,即天然石青[13]。
日文中的“绀青”,并不指某种特定成分的蓝色颜料,而是指某种特定色相的颜料。江户中期的绘画文献《画筌》中有这样的记载,“绀青……颗粒磨细就制成了群青(「紺青…これを摺(す)って群青を出す」)”[14],说明绀青和群青的区别在于色度的差异,二者的区别类似于“大青”和“二青”,成分相同而色度有别。江户以来,由西方传入日本的几种蓝色颜料——smalt,普鲁士蓝,乃至更晚出的化工颜料钴蓝(cobalt blue),在日语中都有过被称作“绀青”的情况,这显然是因色相而命名颜料的做法。
smalt在江户时代由荷兰人带到日本[13],其日语命名一度并未统一,出现过“绀青”“花绀青”“花绀蓝”“澄绀青”等种种称谓[13]。江户时代的《物类品骘》一书最早记载了这种颜料,并对其性状作了准确描述:
花绀青……是从欧洲传来的,比起绘画颜料里使用的扁青,质地有所不及,前人有称其为“玻璃屑”的,原因不详。(5)中文为笔者翻译。[15]
从这段文字的描述,可以确凿无疑地判断这种颜料就是smalt。日后,随着现代化学工程术语的规范化,花绀青这一译名最终在日语中固定下来,成为和smalt一词完全对应的日语词汇(6)20世纪的日-英、英-日词典均以“花绀青”和smalt互释。例如岩波《英和大辞典》(1970):“smalt. n.花绀青(色),花绀青色の绘具。”此外现代日语中一般用“岩绀青”指称天然石青,而用“绀青”指称普鲁士蓝。。
1895年刊行的黄遵宪著作《日本国志》,很可能是最早使用“绀青”一词指称颜料(而非色彩)的中文语例:“长门国物产:……岩白绿青、岩绀青、岩空青、岩白空青……”(7)长门国,日本古代令制国之一,在今山口县。“岩绀青”也是一个日文词汇,指的是天然石青颜料(即蓝铜矿)[16]。作为最早将现代日本书籍和文化译介到中国的先觉者,黄遵宪在此书中大量使用了日语借词,以表达当时中文中不存在的诸多名词概念,是早期日语词汇进入中文的最重要文献源流之一[17]。
明治维新以来,由于日本学者大量研读和翻译西方著作,日语词汇发展迅速,形成了巨大的新词词库。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进步学者大力提倡向日本学习维新经验,大批中国人赴日留学,同时大量日语著作得以译介到中国。近代西方知识体系和日语中的新词一同迅速进入中国,汉语因而在这一时期内大量吸收了日语借词。作为颜料名称的“花绀青”,很可能就是这一时期进入中文的日语外来词。
对于这一猜想,可兹佐证的文献之一,是1930年译介到中国的日文著作,水津嘉之一郎的《化学集成》,书中提到:
花绀青(smalt):将纯粹之砂及钾与氧化钴共置于炉(与玻璃窑相似)中而熔融之,则得一种类似玻璃之物,粉碎之,即为花绀青。[18]
这是目前所见日文中译书籍中提到花绀青的最早案例(8)但并不表示花绀青一词最早是随着这本书的译介而进入中文的。实际上,1915年出版的《工业药品集成》中已经使用了这一词汇,说明其进入中国时间应当更早。。值得注意的是,原书在“花绀青”一词之后加注了英文原名,说明当时在日文中,花绀青也仍是一个以西文为语源的新词汇。此外,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文译著《最新化学工业大全》中,也提到了smalt,将其称为“花绀蓝”([19],页62)。这也反映出smalt的日文名称当时尚未完全固定。
因此,“花绀青”一词很可能是随着《化学集成》等一批日文科学书籍的译介而进入中文的。尽管当时汉语中对smalt已自有称呼,但是,和其他很多同时期进入中文的日语借词一样,在这个动荡的语言环境里,这些日源外来词仍然暂时在中文里得到一席之地,与种种其他译名并存。这也是20世纪汉语吸收日语外来词的典型过程:一些日语借词经过长时间的淘漉,最终在汉语系统中作为规范词汇固定下来(9)例如“社会”“政治”“科学”等。;另一些则在存在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其他译名取代而退出了汉语系统(10)例如“邮便局”(邮局)“论理学”(逻辑学)等。。“花绀青”的情况属于后者,但又略有特殊——因为smalt这种颜料本身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导致花绀青这一译名来不及完整经历汉语系统对外来词的选择过程,就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历史词汇,只沉淀在民国时期的极少量文献之中。
因此,“花绀青”这个产生并消亡于20世纪的日语词汇,与清代中国人对smalt的称呼并无关系。要探讨smalt在清代的中文名称,还是应当回到清代文献中去寻找证据。
3.2 smalt的中文名称及其变迁
要得知smalt的中文名称,一种可能的途径是将传世文物与其做法则例相互比对。但这种实例极为罕见;此外,则例记载的可靠性也仍然存疑(11)则例作为一种官修文本,多有历代辗转传抄的现象,因此清晚期的则例很可能已经与当时的实际状况脱节,参见参考文献[20]。。
幸运的是,一份清代文本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最直接的答案——1843年中英签订的《五口通商章程》所附关税税则。这份税则规定了英国对华贸易中48种主要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以中英文两个版本同时发布。
现将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Tariff of Duties on the Foreign Trade with China
T.M.C.C.
Imports
……
Smalt per 100 catties 4000(12)这四位数字分别对应T.M.C.C,即两、钱、分、厘(T-Tael,M-Mace,C-Candareen,C-Cash),货币为银两。
……
今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关英国出进口货物议定应完税则分类开列于后
计开
……
进口颜料胶漆纸札类
……
洋青即大青 每百斤 四两
……[21]
税则中的蓝色颜料只有smalt一种,加之税率数额的对应,确凿无疑地证实当时smalt在中国被称为“洋青”或“大青”。
这份关税税则的起草者是罗伯聃(Robert Thom,1807—1846),英格兰人,长期生活在中国,供职于怡和洋行,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精通中文的西方学者。在1843年的中英谈判中,时任英方全权代表的璞鼎查委派罗伯聃拟定了这份税则[22],他对中英两种语言的精通,保证了这份文本的用语准确性。
“洋青”一词在清代中国的使用,也能在中文文献中找到证据。“洋青”一词屡见于多种清代则例,已有研究者注意到,乾隆三十三年(1769)《物料价值则例》中记载的洋青价格,与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smalt在广州的市场价格相吻合[20]。这一命名的逻辑并不费解,smalt作为较早从外洋进口到中国的蓝色颜料,其呈色和形态均接近传统颜料石青,因此很自然地被称作“洋青”。
这一译名在清前期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官方文献——《粤海关志》中也得到了印证。收录在《粤海关志》中的六卷《税则》,记载了当时从广州入关的各种洋货税额,也即保留了一份康熙至道光年间进口商品的详细名目。其中“颜料”类目下记载:
大青每斤税六分三厘。……二青每斤税三分一厘。[23]
按照古代颜料命名的一般规律,“大青”和“二青”是两种成分相同、颗粒粗细有别的颜料。考虑到《粤海关志》编修于道光年间,这两种进口蓝色颜料只可能是smalt(13)另一种当时可能存在的进口颜料普鲁士蓝的色彩及形态更接近靛蓝,不大可能被译为“青”,也很难分出两种颗粒度。实际上它在光绪年间被译为“洋蓝”。。
此外,还有更多史料能够提供旁证。1843年以来,清政府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大都附有协定税则,并以两国文字颁布。这为smalt的中文译名提供了一系列来自各个时期的语料证据。清代来华传教士编纂的英汉辞典等著作中,也能见到smalt一词的中英对译情况。这些传教士长期在华生活,熟悉中国人当时实际使用的语汇,加上兼通西方语言文化的优势,使得这些著作成为19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中较重要的文献证据。兹将上述材料整理如表1:

表1 smalt在不同时期文献中的中文名称
表1为smalt在19—20世纪这一时段内的中文名称变迁,描画了一个大致清晰的脉络:有清一代,smalt始终被称为“洋青”或“大青”。民国初年,随着大量科技类外文著作译介到国内,“花绀青”等种种新译名进入中文,曾短暂出现多名并存的混乱状况,但其中仍然包括“洋青”这个沿袭自清代的传统名称。
4 smalt的贸易来源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smalt是一种进口自欧洲的钴玻璃颜料。然而,在中国文物中发现的smalt是否来自欧洲,实际上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因为钴矿在世界范围内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同样具备生产钴玻璃的条件。因此,讨论其贸易历史之前,有必要先辨析中国文物中smalt的产地。
研究证实,18世纪中国作为釉料使用的smalt的确来自欧洲——其组分特征(高Ni,高As,低Mn)与德国萨克逊州Erzgebirge的钴矿一致,而与中国钴源的元素特点(高Mn,低Ni)不符[24]。
对于作为颜料的smalt,同样可以用元素分析的方法揭示其矿产来源。既有研究对21件分布在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中国古代smalt样品的检测结果表明,其主要元素成分和质量比都与欧洲smalt颜料非常相似[8]。针对故宫临溪亭天花彩画smalt样品的检测发现,其元素分布也符合这一结论[7]。这证实了清代中国的确曾经从欧洲进口smalt。
那么,smalt的进口贸易始自何时?从哪些国家进口?贸易路线、贸易量和贸易价格又如何呢?
英国是清前期西方对华贸易的第一大国,要探寻smalt的早期进口情况,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档案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档案》一书,在1635—1834年间的档案里,smalt最早出现在1774年的广州进口货物价格表,分为一级品和二级品,价格分别是100两/担和24两/担([25],卷5页195)。这是有关smalt销往中国的最早文献记载。此外,1792年的一份清单记录了smalt的一次具体交易,来自一艘丹麦船,进口价格为11两/担,总价值2228两([26],卷2页202)。值得注意的是,从1774—1792年,短短18年间,smalt的价格出现了大幅下降,很可能与贸易量增加有关,侧面反映出该时期内中国对smalt的需求不断扩大。
虽然记录不多,但smalt并不是贸易量很少的稀见商品——有研究者根据东印度公司贸易档案指出,从1778到1795年内,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将smalt从伦敦大量运往中国,出口量之大,竟致在1795年左右造成了英格兰本土的原料短缺[27]。也有学者指出,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smalt都从伦敦运往中国,这一贸易活动一直延续到19世纪[3]。清政府为了限制散商在广州的活动,曾经颁布过一张货物表,限定表中货物只能由行商进出口,散商不得经营,其中就包括smalt[28]。
此外,19世纪的美国也向中国出口smalt。1844年签订的《中美五口贸易章程》附有一份海关税则,反映出当时中美间主要进出口贸易品种类,其中就有smalt[21]。
1840年之后,随着清朝对外贸易规模连年增长,smalt的贸易量也逐步增加,需求渐趋旺盛。除了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外,在1844年中美协定税则、1844年中法协定税则、1858年中英协定税则、1858年中法协定税则、1902年中英协定税则等一系列海关税则中,均包含了smalt的税率,说明smalt在1844—1902年期间始终是稳定存在的对华贸易商品。
1859年起,中国近代海关开始编制出版贸易统计册,详细记录各个港口具体商品的进出口数量和价格。smalt从1859年起就出现在进口商品的统计清单里,并从此持续不断,屡见于上海、天津、宁波、福州、广州、厦门、香港、淡水等诸多通商口岸的贸易统计册中,年度交易量持续增长,从数千至数万斤不等,量大时可达9万余斤(1899年天津进口记录)[29]。
表2摘录了1859—1865年海关贸易统计中smalt的交易数据。从中可见,在当时,smalt的交易相当活跃,除了大量的进口贸易,也存在相当规模的复出口和转口贸易,在各种进口颜料类商品中,是贸易持续时间较长、交易量也较大的一种。其进口价格大体保持平稳,反映出稳定的供求关系。

表2 1859—1865年旧海关贸易统计册中smalt的进口记录
5 smalt在清代中国的应用历史
“洋青”这一名称的确认,使基于中文史料的考察变为可能。对于smalt在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应用历史,需要研究的内容很多,本文仅就其应用概况作初步探讨。
smalt传入中国之后,有两方面的应用,一是作为颜料,二是作为釉料。
5.1 作为颜料的应用
smalt在中国的应用案例已有许多发现,但由于彩绘颜料层很难精确断代,要判断smalt在中国的应用时段,仍需从文献记载考察。
清代史料中,有关“洋青”应用的最早记录,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一份奏折,开列了养心殿等工程所用的彩画颜料清单:
……洋青二斤五两,此以每斤各二两八钱计,银为六两四钱七分五厘。[30]
这里洋青的价格相当昂贵,而用量仅为二斤五两,是这份清单中用量最少的几种颜料之一,可见洋青当时还是一种稀见的进口颜料。但毫无疑问,在康熙年间,这种颜料已经进入中国,并应用于建筑彩画。
雍正年间颁布的《工程做法》,作为官方规范性质的工程专书,已将洋青列入画作颜料,见于多种彩画类型。例如:
鲜花天花:洋青圆光,三绿岔角……[31]
苏式五墨锦白粉地仗方椽头:见方二寸五分,每十个用……洋青四分……[31]
洋青菱杵米色地仗方椽头:见方二寸五分,每十个用……洋青四分……[31]
此后,“洋青”一词见于雍正到光绪年间的多种则例(表3),一些价值则例还记录了洋青的价格。

表3 清代匠作则例中关于洋青的记载 (14)在不同地区有不同价格。下同。(15)乾隆三十三年刊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16)光绪三十二年刻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表3提供了几则关键信息:
(1)洋青在则例中不仅应用于彩画作,也用于油作和装修中,后两类应用尚未发现实例,值得关注。
(2)乾隆时期的则例中出现“洋青”次数最多,而科学检测案例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乾隆时期彩画案例。结合前文所引日本最早记载smalt的《物类品骘》一书(成书时间为1763年,即乾隆二十八年),可知乾隆时期smalt已经传入日本,且有相当规模的应用。由此可见,乾隆年间是smalt应用的兴盛时期。
(3)虽然则例中的物价与实际市场价格未必完全一致,但从表3仍可大致判断,从清早期到清晚期,洋青价格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康熙年间还相当昂贵的洋青,到乾隆年间,价格已大幅下降。不难推知,清中期以来,其进口与应用规模都在快速增长。
关于smalt作为颜料的应用状况,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有人认为smalt颜色较浅,且易褪色,因此必须与其他颜料混合使用,或只能用来打底,这一看法是不全面的。实际上,smalt的呈色由其中Co和其他金属元素的含量比例决定,除了淡蓝色,也可能呈现相当深沉的蓝色甚至蓝紫色。就实例所见,smalt的确存在单独使用的情况;就保存状况而言,历经数百年而色泽仍然鲜艳的样品也不在少数。例如,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有一组清代木胎彩绘三大士像(图1),使用的蓝色颜料就是单一的smalt,多处取样证实并无其他蓝色颜料混杂其中,颜料颗粒平均饱和度较高,呈现相当鲜艳的深蓝色(图2)。这组小像并非贵重文物,造型与用料均非上乘,其用途也近于家庭日用品,这恰恰反映出一个重要事实:smalt在民间的应用曾经相当普遍,并不是皇家工程或高等级佛教建筑才能够使用的罕异舶来品。

图1 中国营造学社旧藏清代木胎彩绘三大士像

图2 中国营造学社旧藏三大士像中的smalt颜料(文殊菩萨坐骑表面蓝色彩绘)
smalt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应用状况,从1932年出版的《矿物颜料》一书可以窥得一二:
花绀青为美丽青色颜料。群青人造方法未发明以前,亦颇盛行,自人造群青价廉产出后,始嫌其价值昂贵,被覆力小,用途渐少。[34]
可见直到人造群青大量应用之前,smalt在中国仍然有一个“颇盛行”的阶段,除了自用,也往日本出口[35]。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相似:“此物往昔之用途虽广,惟自人工制造群青以来,销路大减,现时仅供给绘画颜料之用。” ([19],页62)这一描述也提示了 smalt在绘画颜料之外,还存在其他更广泛的用途。
5.2 作为釉料的应用
smalt在欧洲除了用作绘画颜料,也被用作给玻璃上彩的釉料, 这一做法至迟在乾隆年间已经传入中国。马戛尔尼使团的随队医生基朗(Gilan)有一篇记录中国医学、外科和化学的笔记,题为《基朗医生眼中的中国医药、外科与化学发展现状》(Dr.Gillan’s Observations on the state on Medicine, Surgery and Chemistry in China),文中谈及了瓷器的釉料:
我被告知,他们过去使用的原料是自产的钴料,但现在有大量的smalt (是一种玻璃粉末,以一份商业上称为zaffre的钴矿灰和两份火石粉混合并熔融而制成)从欧洲运送给他们。[36]
而更早些时候,景德镇的制瓷工人很可能已经懂得利用这种材料。1712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曾经记录下他所见中国工匠制备青料的方法:
首先把它埋入窑内深半尺多的砂砾层里连续煅烧二十四小时,然后研磨成极微细的粉末。和其他色料不同,钴料不是在石板上研磨的,而是在一个没有上釉的大陶钵里用瓷杵捣碎。(17)原文为法语,引文系笔者由英文转译。英译本见参考文献[27]。[37]
虽然殷弘绪没有明确使用smalt称呼这种青料,但这里的描述与smalt的制备工艺完全吻合:将原材料(氧化钴)和砂砾(二氧化硅、碳酸钾)混合煅烧后,生成钴玻璃。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南窑笔记》关于吹釉(18)陶瓷施釉工艺之一,与洒釉同义,将釉料均匀喷洒在釉地上。的记载中,提到了各种低温釉色:“吹洋红、吹矾红……吹洋青、吹油绿、吹古铜等色,皆系炉内颜色。”其中蓝色者有“吹青”“吹粉青”“吹洋青”三种,其中的“洋青”很可能就是smalt。
匠作则例中也记载了洋青作为釉料的做法。 《宁寿宫照金塔式样成造珐琅塔一座销算底册》,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制造梵华楼内一座珐琅塔的工料则例”[38],其中记录的青色珐琅配方中就有“洋青”:
配青色七斤八两 每斤用
顶元子(19)国产氧化钴青料。二两 计十五两
洋青二两 计十五两
……
买办
洋青一斤十四两 计银一两一钱二分五厘
顶元子十五两 计银三两一钱八分七厘
这里的洋青是釉料,而不是釉下彩料。有研究表明,当时的瓷器同时使用两种不同的青料:釉下彩普遍使用中国国产钴青料,而蓝釉则使用欧洲进口的smalt[3],推测这是两种青料的不同性质和发色特征决定的。
这里附带对“苏麻离青是不是smalt”的问题作一辨析。明代文献中出现的“苏麻离青”一词,作为一种烧造青花用的釉下彩料,其成分和来源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有不少研究者因其发音与smalt相近,而将二者混为一谈,甚至将smalt直接翻译为“苏麻离青”。但这种望文生义的理解缺乏科学论证,且将smalt音译为“苏麻离”三字也嫌牵强。近年已有学者对这一误会加以辨正,指出15世纪初欧洲尚未开始生产smalt,苏麻离青作为永宣时期已在应用的青料,就不可能是smalt[39]。目前许多研究者倾向认为苏麻离青是一种来自西亚地区的青料,经由苏门答腊、爪哇或吐鲁番中转贸易而到达中原。这一青料在明朝中期以后可能受海禁政策影响而不再输入中国(20)(清)梁同书《古窑器考·明窑合评》:“至成化其色已尽,只用平等青料。”,工匠们越来越多地改用国产钴青料——清代称顶元子、碗青或石子青——作为青花的釉下彩料。而smalt进口到中国之后,在瓷器中主要用于调制蓝色色釉,而非釉下彩。
至于smalt和苏麻离青在发音上的些许近似,从语源学的角度,与其猜测二者是同一词汇,远不如猜测它们是两个同源的词汇更为合理。实际上,早在1936年已有日本学者指出,“苏麻离青”“苏渤泥青”“撒卜泥青”及smalt等词汇可能都是来自一个同源词的不同形式(21)这一观点参见:中尾万三《支那陶瓷の青料考》,刊载于《陶瓷讲座》1936年第9卷第1—81页。中尾在文中说这一观点是他的前辈学者盐田力藏提出的。转引自杨连陞为约翰·亚历山大·波普《阿得比尔寺藏中国瓷器》一书所撰写的英文书评,刊载于《哈佛亚洲学报》1958年第21卷第3、4期合刊。。smalt这一词汇在英语中出现得很晚,只能追溯到1558年,是意大利语中的smaltino的借词(22)见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malt词条。。西方颜料史学者早已指出,不应简单地将意大利语中smaltino一词的所指等同于smalt;来自smaltare(熔融)这一词源的一系列词汇指称的实际是多种玻璃质颜料([1],页352)。欧洲和西亚历史上都曾出现过若干种含钴的蓝色颜料或玻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但smalt一词的所指是有限的,它特指一种从16世纪开始兴起,在欧洲得到广泛应用并对外传播的人造钴玻璃颜料。不应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钴玻璃颜料一概归入smalt名下。
历史颜料的分类和命名,是一个需要放在历史语境下考察的问题。一种颜料的定义,与成分、工艺、时代和地域等诸多因素同时相关。倘以化学成分作为甄别古代颜料种类的唯一标准,就落入了现代思维的误区,这是历史和考古学者应当竭力避免的。
6 结论
在综合查考已知科学检测实例和文献证据后,对本文开头提出的几个问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smalt在清代中国被普遍称为“洋青”和或“大青”。民国时期曾短暂出现若干其他译名,其中包括“花绀青”一词,但此词实为20世纪初才进入中文的日语借词,清代并无使用。
(2)就文献史料和科学检测案例所见,smalt的应用仅限于有清一代,尚未发现年代更早的案例。smalt最早通过贸易渠道进入中国的时间当在清初,至迟不会晚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此后其应用一直延续不绝,直至民国时期。其应用时段下限尚不明确,但不早于1940年代。
(3)smalt在中国已知最早的应用实例是康熙年间的养心殿建筑彩画工程。雍正年间,“洋青”已经作为彩画颜料进入官方规范性质的《工程做法》,但用量很有限。到乾隆年间,smalt的应用才开始兴盛。根据各时期物料价值则例的记载,康熙以降,洋青的价格明显呈现逐步降低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进口数量和应用规模的不断增长。
(4)科学检测所见中国文物中smalt元素分布特征与欧洲钴源相符,对贸易档案的考察也证实了清代中国曾经从国外大量进口smalt。这一贸易活动有确切记载的时间上限不晚于1774年,进口来源地包括英国、美国及丹麦、法国等多个国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下半叶,smalt的进口贸易始终活跃,规模迅速发展,且存在大量转口和复出口贸易,反映出当时中国市场对这一商品的稳定需求。
(5)实物和文献两方面的证据表明,smalt在中国不仅作为颜料用于建筑彩画、壁画、彩塑和器物彩绘,也作为釉料用于瓷器、珐琅等手工业制品。作为一种供应稳定、价格低廉的蓝色颜料,无论在皇家营造工程还是民间手工业中,其应用都曾兴盛一时。
致 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刘畅、姜铮两位老师的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