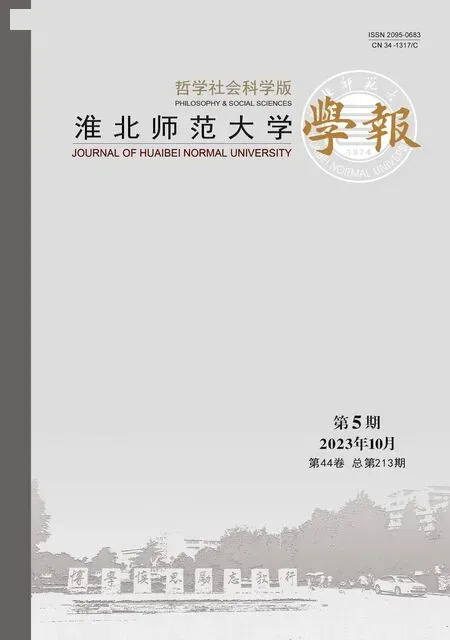论布克哈特的历史知识观
李 慧
(阜阳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是19世纪瑞士文化史家和艺术史家,他所著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不仅奠定了西方史学对文艺复兴研究的基调,也确立了‘文化史’这种既有别于实证主义又不同于历史哲学的历史研究方法”[1]。自1860 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首次出版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布克哈特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他的文化史方面①相关研究成果参见:Karl J.Weintraub, Visions of Culture: Voltaire, Guizot, Burckhardt, Huizinga, Ortega Y Gasse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 pp.115-160; Felix Gilbert,“Jacob Burckhardt’s Student Years: The Road to Cultur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47, No.2(1986), pp.249-274; Felix Gilbert, History: Politics o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Ranke and Burckhard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Michael Ann Holly,“Burckhardt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Past”,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Vol.1, No.1(1988), pp.47-73; Richard Sigurdson,“Jacob Burckhardt: The Cultural Historian as Political Thinker”,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52, No.3(1990), pp.417-440;黄洋:《布克哈特和他的文化史研究——以<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王大庆:《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研究:兼评<希腊人和希腊文明>》,《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并大多停留在对其文化史著作的介绍、评价层面,而对其文化史所蕴含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较少,缺乏系统性的论述。实际上,布克哈特在从事文化史研究之余,通过反思历史和历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这些理论观点除了体现在他的三部文化史著作《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希腊文化史》中,还散见于他生前的讲座和未刊手稿中,后被整理出版为:《世界历史沉思录》《历史讲稿》《布克哈特书信集》等。本文旨在以布克哈特的著述为基础,结合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书写的文艺性三个方面梳理布克哈特的历史知识观②“历史知识”(Historik)一词诞生于近代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为了说明历史学自成一门学科,近代德国历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历史学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反思,代表此类反思的理论就被称为“历史知识理论”,比如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胡昌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受近代德国学术传统影响,布克哈特在从事文化史研究之余,通过反思历史学形成的关于历史学性质、任务、方法的理论思考,本文称之为布克哈特的“历史知识观”。,深化对布克哈特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一、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联系与区别
19 世纪以来,历史学的科学化尤其是自然科学化成为一股强劲不衰的趋势。首先是兰克标榜“如实直书”,他指出历史学家应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消灭自我,通过对资料的搜集、甄别、考证获得历史真相;然后是实证主义史学家主张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在获得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总结历史规律。因此,对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关系的认识,是衡量历史知识观的重要标准。
布克哈特认为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友好的关系,原因在于:一是,自然科学本身就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与其他学科对历史学的控制或利用相比,自然科学并无意支配历史学;三是,自然科学能够客观地认识世界,这是历史学需要效仿的。汤普森曾在《历史著作史》中指出布克哈特和法国历史学家泰纳十分相似,他们都把历史看作是某些稳定因素和时空的相互作用,都在历史上寻找“典型”的东西,并将布克哈特归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2]。实际上,这种划分并不恰当,尽管布克哈特承认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友好关系,但他十分清楚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区别,具体包括:自然界使得每个物种作为一个整体获得最完美的发展,对个体需要无动于衷,而历史以个体为中心;自然界中存在着界、属和种,历史上则有民族、家庭和群体;自然界在造物时依据几种原始类型,如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显花植物、隐花植物等,而各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不同类型的民族,是因为它们在各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自然界里的物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历史的本质则在于变化[3]21-22。自然和历史的诸多不同,必然导致两者研究方法的不同。作为一名文化史家,布克哈特更多将历史学视为一门人文学科,反对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他的文化史著作没有采用任何的自然科学方法,因此,布克哈特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史学流派。
布克哈特对自然和历史的区分植根于德国学术传统,并和德罗伊森、狄尔泰对该问题的思考形成呼应关系。德罗伊森是布克哈特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的老师,他在《历史知识理论》开篇就指出“自然与历史是两个最广泛的概念,人们借着这两个概念,掌握世间一切现象”[4]7,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自然倾向于空间性,历史倾向于时间性;自然界的变化是按周期重复的,历史变化则是在重复中不断累积生长,以及自我提升的;自然中的动植物是没有个性的,可以被肢解、破坏、利用以及消耗;而历史中的每个自我都是完整个体,每个人的言行都与他人相关[4]7-11。既然如此,那么在研究自然和历史时就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德罗伊森认为与自然科学的“说明”不同,历史研究方法的特色在于“理解”,“理解”贯穿于历史研究的整个过程,好像一个心灵潜入另一个心灵一样,将思想赋予历史事实。
狄尔泰是布克哈特在巴塞尔大学的同事,属于布克哈特的学术后辈。1867 年,狄尔泰前往巴塞尔大学应聘时,布克哈特十分欣赏他的才能,并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他(指狄尔泰)在做学生时就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他具有发动的力量,就像与他谈话时立刻显露的那样;他不仅有才智,而且有对世界、历史、文学和艺术的真知灼见;他给人带来一个发光中心的感觉”[5]。狄尔泰在历史哲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沿着康德的道路,提出并论证了人文科学是如何可能的。具体来看,他使用“精神科学”来概括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种科学,并指出历史学是精神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它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以人的精神生命作为研究对象,后者研究的是无精神生命的自然界;前者认识的起源和基础在于内部经验,后者依据的是外部经验,因此,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应用于历史学[6]。
当然,与德罗伊森、狄尔泰等人相比,布克哈特对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分是零散的、不系统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本身对历史哲学兴趣不大,他的很多思考都是有感而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所生活的时代仍处于思辨历史哲学阶段,而对历史学的反思主要是20世纪的史学理论所面临的任务。继狄尔泰之后,包括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在内的新康德主义学派继续论证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以及历史学的方法论问题。
二、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
自诞生之日起,历史学就表现出科学化与艺术化两种倾向。一方面,历史学不同于文学艺术,它旨在弄清历史事实和过程,追求客观真实;另一方面,历史学又离不开文学艺术,它需要借助想象、猜测来还原历史面貌,以及通过艺术性的描写发挥教育功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史学发展过程中,这两种倾向几乎并行不悖地存在着,期间并未发生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随着“历史学的世纪”的到来,历史学的科学化被提上日程,“所谓史学的科学与艺术之争,也正是在这个世纪提出的”[7]。在19 世纪,大部分历史学家宣称历史学具有客观性,最著名的当属兰克在《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序言中提出的历史的任务在于“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8],即“如实直书”。在此背景下,布克哈特反其道而行之,指出历史“是所有科学当中最不科学的一门学问”[3]77,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具体表现为:
其一,原始资料的相对性。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中,布克哈特将历史文献区分为原始资料和整理性资料两大类。受兰克影响,他十分重视原始资料,认为“原始资料把事实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只有在直接接触原始资料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才能与被阅读对象直接结合,从而产生正确的化学反应”[3]17-18。不过,在布克哈特看来,“原始”一词是相对的,由于历史文献处于不断丢失和被发现的过程中,当最原始的资料丢失时,最直接相关的资料便开始发挥“原始”的作用,另外,随着新文献的发掘和整理,以往公认的原始资料也有可能被推翻[3]18。由此可见,原始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它的相对性必然会影响到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其二,研究者的相对性。这包括研究者的出身、性格、年龄、治史兴趣及方法等。首先,每个历史学家总是生活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的,很难摆脱他所处的时代和地区的影响,“即使是最古老的文献,也每每能附着当时的同情和憎恶;即使是关于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关于埃及和亚细亚的历史,也能完全陷入当时的党派偏见和错综复杂的争吵中”[9]。其次,每个历史学家都是思想独立的个体,“在研究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走出自己的路子。每个人所走的道路体现了他的精神思路,因此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进他的研究课题,并且根据自己的思路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方法”[3]4。最后,即使是同一个人,他也不能够完全摆脱自己的治史兴趣、年龄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大部分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认识周围的事件的,“当历史越来越接近我们的世纪和我们的价值观时,我们会发现一切都变得更‘有趣’,实际上,只是我们更‘感兴趣’[10]。另一方面,“当我们评价与自己相关的人或事的时候,我们的年龄以及阅历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到了生命的暮年时,我们才能够对所接触的人和经历过的事做出最终的判断。此外,这个最终的判断又依我们寿命的长短,即我们有生之年是四十还是五十岁,可能会截然不同。对我们来说,这个判断性的结论只有一个非常主观的而非客观的真实性”[3]239。这里的“主观的而非客观的真实性”即表明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既然历史研究很难做到兰克所追求的“如实直书”,那么不同于兰克主张历史学家应尽可能地消灭自我,布克哈特认为历史学家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赋予历史研究以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也是他的文化史著作能够成为经典并始终无法被超越的原因之一。
其三,文化史研究的相对性。在布克哈特看来,不同于以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文化史应该尽可能地提供细节,通过无数细节描绘出一个时代的画面,进而反映时代精神;它应该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出结论,允许自己提出暂时性的假设,这决定了文化史研究带有更多的相对性。对此,布克哈特有着十分清楚的认知,比如,他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开篇就写道:“任何一个文化的轮廓,在不同人的眼里看来都可能是一幅不同的途径;而在讨论到我们的文化之母,也就是直到今天仍对我们有影响的这个文化时,作者和读者就更不可避免地要随时受个人意见和个人感情的影响了”[11];再如,在《希腊文化史》中,他认为自己对古代希腊文化的研究是“在具有相对重要性的材料的引导下所进行的小心谨慎的主观研究,另一个人还是很可能会在材料上做出相当不同的选择,对这些材料进行不同的处理,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且,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还会绘制出一幅(差异更大的)更为细致和宽广的图画”[12]。
针对19 世纪历史学所推崇的科学精神,布克哈特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指出历史“在任何时候都是对一个时代在另一个时代中所发现的值得注意的东西的记录”[13],他把作为事实的历史和作为知识的历史区分开来,历史知识不仅包括对历史事实的考证,还包括对其做出的陈述、解释以及评价。在这里,布克哈特不自觉地卷入了关于历史知识性质的讨论,这是20 世纪的史学理论才需要面对的论题。从以上论述可看出,布克哈特基本赞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不过,他毕竟生活在19 世纪这个注重事实的伟大时代,时代氛围决定他不可能陷入历史相对主义的极端。在他看来,尽管“纯客观的历史不可能,但是我们并不能放弃这种努力,我们要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此要)学多种外语。我们要摆脱现今新闻小说的影响,以慎重的态度研究历史。我们要有一颗相对静止、稳定,不为外界所扰的心灵以从事历史研究”[14],追求历史客观性始终是布克哈特文化史研究的宗旨所在。
艾伦·梅吉尔认为存在四种不同意义上的客观性,分别是:(1)“哲学或绝对意义上的”(philosophical or absolute sense),它源自于在现代哲学传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理想原则,即“如实地呈现事物本来的面貌”,并追求一种不受任何扭曲的忠于现实的知识;(2)“学科意义上的”(disciplinary sense),它主张将特定研究群体之间的共识作为评判客观性的标准;(3)“相互作用或辩证意义上的”(interactional or dialectical sense),它认为客观性是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构建的,从而为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留出空间;(4)“程序意义上的”(procedural sense),它旨在实践一种客观的研究方法,反对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结果的人为操控[15]。虽然艾伦·梅吉尔对于客观性的区分主要是从一般哲学层面而言的,但它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客观性仍具有启发意义。相较而言,兰克追求的历史客观性更多是“哲学或绝对意义上的”,而布克哈特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则属于“相互作用或辩证意义上的”,他在坚持历史客观性的同时,更多地看到了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三、史学也是一门艺术
在19世纪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命题被提上日程。虽然当时大部分历史学家主张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历史学的艺术化倾向,即便是兰克也认为“史学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亦是一门艺术”[16]。作为兰克的学生,布克哈特在反对将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的同时,强调历史学和文学艺术在性质上相通。1842 年,在致友人威伯德·贝什拉格(Willibald Beyschlag)的信中,他写道:“对我来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总是诗歌,是一系列最美丽和最富于艺术性的事物”[17]49。通过将历史视为诗歌,布克哈特延续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历史和文学之争。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和文学的区别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具体事件,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带有普遍性的事,因而诗歌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18]。在某种程度上,布克哈特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在他看来,诗歌是一种高级的表达形式,不仅能够提供关于人类精神本质的洞见,还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间内是传达信息的唯一形式,能够为历史学家在理解时间方面和民族方面的问题上提供启发。另外,布克哈特认为诗歌提供给诗人的刻画手法要远远优于历史学家所能支配的手法,因此,历史学家需要向诗人学习。
作为文化史家和艺术史家,布克哈特认为历史不仅是诗歌,还是建筑、雕塑和绘画等艺术形式。如同诗歌一样,艺术往往是一个时代留下的关于人性最好的和最崇高的表现形式,是人类历史的最辉煌成就的总和,能够反映民族精神或者时代精神。以建筑为例,它是国家或个人有意识地表现自己的结果,“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和一个时代的建筑整体实际上就是相关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内涵的外部表现形式”[3]71,从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到中世纪的科隆大教堂再到现代的摩登大厦,转变的不只是建筑的外形,更是各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既然历史和文学艺术在性质上相通,那么在书写历史时就可以借鉴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虽然布克哈特没有系统论述过历史书写的文艺性,但他不仅在和友人的通信中多次谈到该问题,还通过他的文化史写作践行着这一原则,具体表现为:
其一,重视直觉想象力的作用。在1842 年致贝什拉格的信中,布克哈特写道:“我全部的历史作品,就像我对旅行的热情,对自然风景的狂热以及对艺术的热爱,都源自我对沉思的巨大渴望”[17]49。同年,在致卡尔·费森尤斯(Karl Fresenius)的信中,布克哈特写道:“对我来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诗歌。不要误解我,我并不认为它是浪漫的或是虚幻的,所有这些都是毫无价值的,但它犹如一个蚕蛹蜕变般、不断获得精神启示的奇妙过程……可以通过沉思来掌握”[17]51。可见,对布克哈特而言,历史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活动,他希望通过“沉思”而不是批判或者推断获得历史知识。布克哈特所谓的“沉思”类似于兰克提出的“直觉移情”,有“观察”“想象”“感知”“领悟”等多层含义,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审美方法。从实践来看,他的三部文化史著作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希腊文化史》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文学作品,是文学经验和历史沉思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想象力的结果。但历史学毕竟不同于文学,对历史的想象应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相较而言,在撰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时,出于多方面考虑,布克哈特刻意控制着自己的想象力,而在发表关于希腊文化的系列演说时,他则让自己遨游在希腊神话中自由想象,这也是导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经面世就受到好评,而《希腊文化史》发表后立即遭到德国历史学家强烈批判的原因之一。
其二,强调历史作品的可读性。布克哈特认为历史学家应面向公众写作,通过文学化的写作手法,使其著作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历史学的教育功能。他之所以反对德国专业的历史学派,原因之一就在于除兰克外的德国历史学家的著作只在学者们中间流传,几乎没有任何的公众影响力。在这方面,兰克要聪明得多,他擅长使用高超的文学形式来呈现艰深的学术研究,其《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和《教皇史》就是历史表述的典范著作,一经面世就俘获了大批读者。布克哈特认为兰克的历史表达艺术是从法国历史学家那里学来的,法国历史学家能够将学术研究和优美的体裁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他们的著作既能摆在学者的书斋中,也能放在侍女的梳妆台上,只不过兰克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受兰克和法国历史学家的影响,布克哈特“发誓将终生尝试晓畅易懂的写作风格,坚持以趣味性而不是枯燥的事实完整性为目标”[17]45-46。与以事件为中心的传统史学不同,布克哈特的文化史以人物为中心,通过对人物性格、内心活动和情感世界的描写,他为读者呈现了一大批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比如野心勃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君士坦丁大帝;精于深思熟虑、老谋深算的暴君;骇人听闻、凶暴残忍的雇佣军首领;充分意识到个人能力并将这种能力发挥到极致的人文主义学者等。在语言方面,布克哈特擅长使用散文化的语言,用词朴素自然、简洁明净,节奏时而紧促时而舒缓,张弛有度,阅读他的作品,有时像在阅读一部历史小说,能够感到强烈的戏剧般冲突,更多时候像是在阅读一篇散文或诗歌,给人一种美学的体验。
其三,追求历史作品的画面感。在1842 年写给贝什拉格的信中,布克哈特还写道:“我的历史著作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易读,甚至是令人愉悦的,但是如果没有内在的图景跃然纸上,那它就注定是失败的”[17]49。可见,布克哈特在强调历史作品的可读性的同时,还追求历史作品的画面感。柏林大学求学期间,布克哈特就发现自己之所以无法对兰克史学入迷,是因为兰克史学是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的历时性研究,是外部的和事实的,而他想从事的文化史则是横剖面的或者结构性的,旨在恢复分散在事件中的内在精神力量,他希望抓住一个特定的时刻,通过大量看似毫不相关的细节,描绘出一个时代的画面,并植入精神。这种写作方法主要源自于他对艺术的爱好,对艺术的爱好使他对图像十分敏感,并多次在和友人的通信中谈及图像的重要性。比如,1844 年在致赫尔曼·绍恩堡(Hermann Schauenburg)的信中,布克哈特写道:“此刻的我如此心烦意乱,以至于主观的抒情诗已经远离我。我想要的是图像”[17]74;在读了尼采的《人性》一书后,他在回复尼采的信中写道:“众所周知,我从来没有进入过真正的思想圣殿中,但值得高兴的是,我的一生都是在圣殿的大厅和庭院中度过的,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在那里图像具有支配意义”[17]191。对布克哈特而言,历史不仅是一种诗意的活动,还是一种纯粹的视觉行为,书写历史犹如绘制历史画。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为例,该著作从暴君到雇佣军首领,从教皇到人文主义学者,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的男男女女,从政治到宗教、文学、艺术、道德、社交,无所不包,布克哈特的贡献在于他将大量细节构成了一个具有内部结构、连贯性和意义的整体。迈克尔·霍利认为,布克哈特的写作方式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创作绘画的方式十分相似,他是从画家那里学会如何去看以及如何去想象的[19]。布克哈特通过无数细节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肖像,从近处看,这些细节是清晰且毫无意义的,但当从远处看时,这些细节又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壮丽的现实景象。
总之,布克哈特反对专业化的历史写作,主张借鉴文学艺术手法撰写历史,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著作总是能够给予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让读者去感受、体验以及经历过去发生的一切。他的这种写作方式相继受到了后现代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关注。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将布克哈特视为继米什莱、兰克和托克维尔之后的19 世纪历史学家的代表,认为不同于米什莱按照浪漫剧、兰克按照喜剧、托克维尔按照悲剧,布克哈特是按照讽刺剧模式书写历史的[20];安克斯密特在《崇高的历史经验》中认为布克哈特反对19 世纪德国历史学家专业化的历史写作方式,强调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即主体与客体、现在与过去的融合[21]。尽管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他们都指出了布克哈特历史书写的文艺性。
结语
在历史知识性质问题上,布克哈特和尼采的观点极为相似。1870 年前后,尼采曾聆听过布克哈特“论历史研究”的演说,并发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①又译为《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等。一文,对历史学的性质进行反思。在该文中,尼采极力反对历史学家标榜的历史客观性,在他看来,“纯粹的历史客观性就像是一群太监。似乎任务就是监管历史,以便使什么东西都不能出来”[22]。与此同时,尼采认为历史作品应该由有经验、有性格的人来书写,历史写作和艺术创作十分相似,它“首先需要一种伟大的艺术才能,一种从某一高度出发的创造性眼光,对经验数据的热心研究,对一种既定类型——客观性的自由阐发”[23]。布克哈特和尼采对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书写的艺术性的强调,不仅预示着“历史主义的危机”,还开启了历史相对主义的先河,基于此,有学者将两人共同视为历史相对主义和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奠基人[24]。后现代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在论证自己的理论时,都曾关注过布克哈特。后现代主义犹如一场狂风暴雨,给历史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如何应对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冲击,重塑历史客观性与科学性,是当前史学界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鉴于布克哈特和后现代史学理论之间的关联,从史学理论角度探讨布克哈特,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布克哈特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还对于当下思考如何超越后现代史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