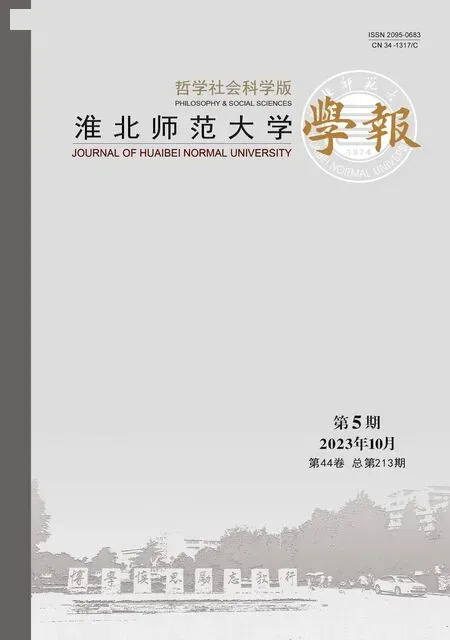《太平经》自然观念发微
萧 平,张 磊
(1.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湖北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14)
《太平经》是中国道教初期的重要经典,也是道家哲学思想向道教宗教理论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文献。《太平经》一书内容全面而驳杂,它对以往道家所涉及的重要理论均有所关注,如“道论”、“德论”、自然观念等,并均对它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理论改造与创新。其中,《太平经》对自然①《太平经》中“自然”一词使用了170余次,可能是道教典籍中使用“自然”概念最多的一部经书。参见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下文凡引用、统计《太平经》原文内容,且不做特殊标记者,皆依据此版本,不另作脚注,只标注章节。观念的理解饶有新意,它改变了过去道家由“道性自然”[1]出发去建构自然理论的思维模式,转而以“元气”为基础进行自然思想的建构;由于视角的变化和理论系统的革新,使得“自然”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在这场自然观念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太平经》也暴露出一些逻辑不自洽的问题,亦值得学者关注。本文尝试围绕上述三个问题对《太平经》的自然观念进行分析与阐述。
一、“元气”与“自然”:自然思想的理论建构
《太平经》频繁将“元气”与“自然”连用,作“元气自然”或“自然元气”,其中“元气自然”出现了10次,而“自然元气”出现了22次,“自然”与“元气”两个词组合起来使用竟然有32 次之多,这还不包括在同一个句子中并提“自然”与“元气”的情况。可见“元气”在《太平经》中占据重要地位,②据笔者根据《太平经合校》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太平经》中“元气”概念使用了100次,远胜汉代的其他典籍。并成为该书发展、构建自身自然观念的理论基础。《太平经》虽不反对“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根,但它也把“元气”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认为只有“元气”行道或守道方能产生天地万物。
夫道何等也?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故元气无形,以制有形,以舒元气,不缘道而生。自然者,乃万物之自然也。不行道,不能包裹天地,各得其所,能使高者不知危。(《行道有优劣法》)
“道”是万物之根源,“不可得名”,这些理论都基本上延续了老子的思想。然而“道”虽是构成天地万物的终极本原,但从质料层面来说,“道”毕竟过于抽象,因此《太平经》借用了“元气”来说明天地万物的生成。其目的并非是要将原有的宇宙生成论、存在论简化为颇具经验色彩的构成论,而是要借助“元气”这一概念完成其自然观念的塑造。首先,“元气”在《太平经》中颇具物质属性。李家彦认为“元气”是由经验产生的实体概念。[2]因而“元气”虽怳惚无形,却能“制有形”,即“清者著天,浊者著地,中和著人”(《以乐却灾法》)、“一气为天,一气为地,一气为人,余气散备万物”(《夷狄自伏法》),可见,在此层面上“元气”全然被视作了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质料。诚然,这里的“质料”还不能完全等同于物理意义上的“材料”,因为它是“三气共一”①即《太平经·令人寿治平法》所言“三气共一,为神根也。一为精、一为神、一为气。此三者,共一位也,本天地之气。神者受之于天,精者受之于地,气者受之于中和,相与共为一道。故神者乘气而行,精者居其中也。三者相助为治。”的结果,但《太平经》又言“夫人本生混沌之气,气生精,精生神,神生明。本于阴阳之气,气转为精,精转为神,神转为明”[3]附录739,“混沌之气”乃原始未分之气,“阴阳之气”乃分阴分阳之混沌之气,而“元气”即为“阴阳之气”中之“主阳”之气,所以“元气”之本质仍是“质料”,只不过此“质料”乃一种中国传统哲学所独有的生命基质,“是通天地万物之命”(《来善集三道文书诀》)者。《太平经》对“元气”质料特性的强调,凸显了“元气”的无目的性,进而肯定了“元气”自身的自然属性。而由“元气”作为质料所构成的天地万物也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该特性,这是朴素经验思维下的必然结果,为万物自然提供了理论前提;其次,“元气”作为原初的、物质的宇宙质料,尽管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但是却不能独自发挥作用,而是必须要“行道”或“守道”才能产生天地万物,即“不行道,不能包裹天地”。值得一提的是,“以舒元气,不缘道而生”这两句话疑有脱误,②杨寄林将此段句读为:“故元气无形,以制有形,以舒元气。不缘道而生自然者,乃万物之自然也。”认为“以舒元气”是说“元气循道而将自身疏散于有形物体”,但这却无法解释“不缘道而生自然者”。另外《太平经》明确指出“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难道还有不因道而生者?这种句读恐有误。参见杨寄林.太平经今注今译[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44.“不”前疑脱“无”字,这样才能与前文“无不由道而生者也”相照应,更能凸显“道”之于“元气”的优先地位。既然“道无不导,道无不生”[3]附录754,因而“道”“寂静自然”(《阙题》)、“不施自成”(《阙题》)的特性也理应成为了“元气”构成万物以及万物存在运动的法则。尽管在外在形式上看,《太平经》在“道”生万物过程中援入“元气”概念,并未打破原有的生成论模式,但于自然观念的构建上言,其意义却是巨大的,它将以往抽象的“道法自然”观念,通过以“元气”为媒介的方式,将其变得更加直观化与具体化,实现了“自然者,乃万物之自然也”的直接承当。
另外,《太平经》以“元气”为基础构建自然理论,不仅体现在“元气”形成万物的生成过程中,还体现在人“复归于朴”的修养过程与价值追求中:
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和三气兴帝王法》)
然天下人本生受命之时,与天地分身,抱元气于自然,不饮不食,嘘吸阴阳气而活,不知饥渴,久久离神道远,小小失其指意,后生者不得复知,真道空虚,日流就伪,更生饥渴,不饮不食便死,是一大急也。(《守三实法》)
元气包括了“太阳、太阴、中和”三种性质的气,分别产生了“天、地、人”。其中人作为万物之一,根源性地禀受了纯粹的元气并与天地相分离。可见,人的形体作为一种“物”,本质上就是一种“元气”,生命的最初始状态正是因为同然于这种本源性的元气,因而能够呼吸元气中的阴阳之气,不需要饮食而存活。显然这里强调了“元气”之“自然状态”对于人生命的价值,而这里的“自然状态”——一种初始的、本源性的存在状态,也就是老子口中的“朴”。但人生存于世间,久而久之远离神道,真道远离人体,因而产生饥渴饮食的需要,此“是一大急也”。由此可见,《太平经》对人生命本质以及价值追求的理解,仍然没有脱离老庄、黄老的思想框架,然其创新处在于以撮引“元气”的方式,将旧有的生命哲学、政治哲学转捩为宗教性生命炼养学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元气”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之前,无论老庄也好,还是黄老也罢,都倡导一种以“守静”“因循”为核心的精神体道方式来达至自然状态,然而此种“方式”一方面由于缺少“确切意义上的知识”[4],另一方面则由于境界刻画上的玄远,因之很难讲自然原则转化为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亦难以进行“实践把握”①这里的“实践把握”在笔者看来不仅仅是森舸澜所理解的“与西方知识论相反的,在主体与世界接触中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与行动”,还应包括接触世界后的体会(验证或反馈)。以道家之“自然”为例,“自然”不是某种特定的原则,“自然”需要在具体的情形中以自觉的方式通过主体行为加以显现,这是森舸澜理解层面上的“实践把握”,但这是不够的,“实践把握”还应包含该主体对自身行为所产生影响的现实体会。因为如果缺少了后面一层,价值境界很容易演变为境界上的玄思。参阅森舸澜.无为:早期中国的概念隐喻与精神理想[M].上海:东方出版社,2020:导论5.。然而,引入“元气”观念的《太平经》便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所谓:
道之生人,本皆精气也,皆有神也。(《分别形容邪自消清身行法》)
夫天道生物,当周流俱具,睹天地四时五行之气,乃而成也。(《分解本末法》)
人生皆含怀天气具乃出,头圆,天也;足方,地也;四支,四时也;五藏,五行也;耳目口鼻,七政三光也;此不可胜纪,独圣人知之耳。(《分别贫富法》)
《太平经》将道本论、气化论、五行学说乃至天人感应论都通过“元气”加以汇通,并集中于人的生命、身体上展现。此时《太平经》对“人”的理解已不同于老庄的“贵精”“养神”,而是注重“三者相助为治”②《太平经·令人寿治平法》曰:“神者乘气而行,精者居其中也。三者相助为治。故人欲寿者,乃当爱气尊神重精也。”可见,此“三者”指精、气、神。;亦不同于黄老侧重“身体的政治意涵”[5],而是强调“人命最重”“寿最为善”,《太平经》亦成为了重视形神相卫与和谐的生命学说。也正因如此,《太平经》的养生“复朴”之法,不再一味关注于“道”(“精神”),而是变成了关注更为直接的“元气”(以气为本的精气神之全体),即“通元气,行自然”。又如《包天裹地守气不绝诀》言“子欲不终穷,宜与气为玄牝,象天为之,安得死也”,“玄牝”一词出自《老子》,本“形容‘道’的不可思议的生殖力”[6]98,而在此却言称“元气”,同时此句中的“天”若祛除宗教成分亦可解作“自然”③《庄子》文本中便常“以‘天’代‘道’”,言“自然”之义。如“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庄子·齐物论》)、“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庄子·养生主》)等中“天”皆为“道”之义。再如《庄子》中“天均”“天倪”“天理”“天府”等概念均指“道”之境界。庄子以“天”代“道”的作法之目的有三:(一)有意消解“道”的实体性;(二)“天”作为世间最大之自然物,是万物之总名,以“天”代“道”即表明“道”在万物,凸显万物自然之义;(三)“天”在传统思想中具有至上性、神圣性,以“天”代“道”可突出“道”之本根性与崇高性。,可见“象天地元气自然法”(《三合相通诀》)成为了《太平经》指导人养生的修养准则和终极追求。由于“元气”最直接与现实的呈现是人的整个生命体,相较于单纯强调抽象的“道”(“精神”)而言,身体的表征无疑是更直观、更容易“执守”的,“夫神明精气者,随意念而行不离身形。……则不病不老,行不遇邪恶”(《右分别太平文出所宜所不宜诀》),“本天地元气,合阴阳之位,邪恶默然消去”(《阙题》),因之更利于人进行全方位的“实践把握”;同时,养生直接指向的是人的生死,“故人欲寿者,乃当爱气尊神重精[止]也”(《令人寿治平法》),因而也更容易激发人复返自然状态的内生动力。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太平经》虽未取消“道”的本根地位,但是其自然观念的构建却不再围绕“道”而展开,而是以援入的“元气”概念为核心,通过构成论与修养论(包括境界论)两个维度进行塑造。在构成论维度,《太平经》通过强调“元气”的物质属性和其“行道”的特性来凸显自然观念;在修养论维度,《太平经》则通过整合各类学说,改变人的修养方式,由“保此道”转变为“抱元气于自然”(《守三实法》)、由“归精神乎无始”[7]转变为“养身以道”(《冤流灾求奇方诀》),以达至“长生久视”的目的,亦彰显了自然观念。
二、原则义与实体义:“自然”的双重意蕴
“自然”是道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但“自然”并非独立的实体性或对象性存在者(物),它最初只是对存在状态的描述以及对存在状态之根据的描述,包括“道”“天地”“万物”“人”的存在状态,后来被提升为一种理想的价值,天地万物包括人只有处在自然的状态下才是最优的,只要遵循“道”就必然体现为“自然”。然而《太平经》中的“自然”,由于理论建构的变化,其含义相较于以往道家对“自然”的理解,虽有相同之处,但更有较大地革新,下面对《太平经》中自然观念的内涵作简要梳理:
首先,《太平经》中的“自然”指一种独立的价值或原则。
然,助帝王治,大凡有十法:一为元气治,二为自然治,三为道治,四为德治,五为仁治,六为义治,七为礼治,八为文治,九为法治,十为武治。(《六罪十治诀》)
《太平经》将“自然”与“元气”“道”“德”等同视为“帝王治”的手段或方法,①至于“自然治”缘何是高于“道治”“德治”,而次于“元气治”,其原因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解读:一是综合“元气”与“自然”的关系,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论,“元气”在《太平经》中确实处于比“自然”更优先的地位,这是“元气治”高于“自然治”的原因,而“自然治”高于“道治”“德治”大概是《太平经》接受了“道法自然”“德者,成和之修也”等老庄传统的说法;二是《太平经》中的概念确实存在冲突与矛盾,此详见本文第三部分。可见此处的“自然”显然是一种独立的原则或方法,而“自然治”则当指的是顺应天地万物的本性所达到的最佳治理状态。就如《以乐却灾法》中所言:
故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即三光明,地乐则成有常,五行乐则不相伤,四时乐则所生王,王者乐则天下无病,蚑行乐则不相害伤,万物乐则守其常,人乐则不愁易心肠,鬼神乐即利帝王。(《以乐却灾法》)
这里的“乐”当然不是一种情感上的快乐或喜乐,而是指和乐,“系指自然界到人类社会所呈现的一种协调和谐的理想状态”[8]36。在这段材料中,“元气”“天”“地”“五 行”“四 时”“王 者”“蚑 行”“万 物”“人”“鬼神”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物或存在者,“自然”与这些概念并列,已然不是老子哲学意义上的“自然”。并且“自然乐则物强”,说明“自然”达到和谐状态后的直接受益者是“物”(万物),“自然”与“物”当属两者,就此可以断定“自然”是名词。根据“自然”与“天”“地”的位置分析,这里的“自然”显然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作为实体存在的“自然界”,因而它只能指代一种客观存在的原则或规律,本质上是指万物的本性以及万物按照本性发展的存在状态。由此亦可看出,《太平经》的“自然”还是与老庄思想中的“自然”存有内在联系,只是《太平经》有意凸显了“自然”的客观规律义,而相对淡化了它的个体本然义。
其次,《太平经》中的“自然”还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本质是一种“气”。“自然”的这层内涵必须与“元气”结合起来理解,这是《太平经》依靠“元气”来构建自然观念的必然结果。
元气,阳也,主生;自然而化,阴也,主养凡物。天阳主生也,地阴主养也。……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阙题》)
“元气”与“自然而化”对举,“元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原初基质,主生长万物。因而“自然”便不能解释为规律义,“自然而化”亦不可理解作“按本然固有的情状与态势来化成”[8]519。考察整段对阴阳的探讨,不难看出,“阴阳”应与“天地”“日夜”等一般,都是同时存在的,并不存在先后关系,即非先“生”后“养”,由此可知,阴阳乃并生,这种阳施阴化的模式本就是《太平经》中极为重要的原则或定律。②杨寄林认为,“自然”指本来固有的情状与态势,《太平经》认为其属阴,职在教育。“元气”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无形实体,《太平经》认为其属阳,职在化生。此句实说阳施阴化的本原与定律。参见杨寄林.太平经今注今译[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1605.又因为《太平经》常以“阴阳”指代“自然元气”,仅《太平经钞辛部》中便有21 处,如“天上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③根据《太平经》的思想“自然元气阴阳”并非实指三种物体(“气”),而是指“自然元气”两种“气”,“阴阳”只是对“自然元气”的“复指”,以表明“自然”“元气”各自的性质。经文中言“各从其俗”,一方面是说人们对天文、地理、人物的命名各有不同、各从其俗;一方面也是说对构成万物的原初基质“气”的指称也有不同、各随其俗。杨寄林亦持此观点,他在《太平经今注今译》中言该卷经文“旨在阐发以‘自然元气’为本原的阳施阴化的普遍定律”,可见一斑。等。故而,在这里“自然”不是一个副词,而是指某种实体性存在,即“气”。事实上,《太平经》确乎认为“自然”亦为“气”之一种,如《三合相通诀》言:“元气与自然、太和之气相通,并力同心,时怳怳未有形也,三气凝,共生天地”,便十分明确地指出自然之气④杨寄林在“自然”之后补充“之气”两字加以解释,指处于本然状态的无形实体。参见杨寄林.太平经今注今译[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335.与元气、太和之气为“三气”。再如“元气自然,共为天地之性也”(《名为神诀书》),“元气”与“自然”是相对独立的两种实体性存在,本质上都是“气”,共同作用才产生天地之性。如果“自然”不是一个独立性的实体性存在,那么这里就无法使用“共”字。《太平经》中有诸多这样的例子可加印证,如“自然元气,同职共行”(《太平经钞壬部》)、“事出自然元气相加,得成熟”(《有知人思慕与大神相见诀》)、“元气自然乐,则合共生天地”(《阙题》)。
《太平经》将“自然”理解为“原则”与“实体”(“气”)是极富创见性的,尤其是以“气”解“自然”更是发以往之未有。然而《太平经》缘何会淡化“自然”的个体本然义,强调原则义?又创造出实体义呢?究其原因,乃与其理论建构与思想宗旨有关,《太平经》是一套以“道”为本根、以“元气”为基础、以“自然”为重要原则、以“养生”为现实目标、以“治平”为终极目的的学说体系,正如上节所提到的那样,“自然”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元气”学说来加以构建的,因之“元气”较“自然”而言具有逻辑优先性,这在《太平经》的表述中亦有体现,综核经文不难发现,除了上述提到的《太平经钞辛部》中21处明确将“自然”放在“元气”之前外,①《太平经钞辛部》中的21处“自然元气”之所以“自然”处于“元气”之前,也有可能只为了和“阴阳”对应而为之。而非《太平经》在处理“自然”与“元气”关系时有所混乱。其他地方不管是合称还是在同一段落中前后并称,都是“元气”在前而“自然”在后,②虽然作为合成词的“元气自然”只有10次,但除此之外,同时提及“元气”与“自然”的则多达12次。这似乎也表明“元气”显然是高于“自然”的,还有一则材料更能说明此问题,即“眩乱于下古者,思反中古;中古乱者,思反上古;上古乱者,思反天地格法;天地格法疑者,思反自然之形;自然而惑者,思反上元灵气”(《三急吉凶法》),典型地说明了“自然”是次于“元气”的一种存在状态。然而,“元气”所赋予“自然”的哲学意蕴又是双向的:一方面它代表着天地万物自然之形的本质,是个体本然状态(即“自然状态”)的根据与表征;另一方面它又要“守道”“行道”以化生万物,是自然之则的现实呈现。同时,两种意蕴之间又是充满矛盾的,过分强调客观性质的自然之则就会消解个体之自然;而强调个体之自然则会容易让客观性质的自然之则变作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太平经》又有着明确的哲学宗旨,即“惟人居世之间,各有所宜,各有所成。各不夺其愿,随其所便安。……天亲受元气自然,从其教令,不敢小有违之意。”(《病归天有费诀》),因而囊括“教令”的自然之则,才是它首要关注的对象。但若仅着眼于此,又会抹杀个体的存在价值,亦不符合其“养生”的主观诉求,因而“自然”的个体本然义也需要被“保留”,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太平经》选择用“自然”的实体义将“自然”的个体本然义“固化”并彰显出来。因为“自然之气”本身就是气的自然状态,具有是其所是、从其自身的属性与能力,当它一旦进入万物化育的过程中,即代表着万物先天地具备这种能力与属性,且不可被后天剥夺,因之“自然”的个体本然义在万物身上以另一种形式(即“‘自然’的实体义”)被固定与留存。并且这种处理方式还淡化“自然”个体本然义与“自然”原则义之间的冲突,因为“自然之气”亦属“气”,运化时亦要遵循自然之则,二者之间便不存在不可弥缝的龃龉。所以,《太平经》一再强调“自然之气”属“阴”,“阴”以辅“阳”,“阴”隐而不显却又实际发挥作用,从“原则义”上讲,它非经验实有,故而是“隐”、是“阴”;从“实体义”上讲,它旨在维护个体自然,而个体自然亦要以成就全体之自然为目的,故而是“辅”、是“阴”。可见,《太平经》的自然观念是道家思想在汉代元气说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理论学说,具有鲜明的调和性。
三、“道”与“自然”:自然观念的内在矛盾
《太平经》中的自然观念极富创新性,系统亦极为庞杂。就内容上言,它统合了道家本根论、汉代气化论、阴阳五行说乃至天人感应等;就性质上言,它是道家哲学思想、道教神学思想以及融合了儒家名教思想的产物;就发展上言,它是道家自然观念发展过程中一次系统地理论革新。也正因如此,《太平经》在构建自然观念时,出现了内容上的冲突与逻辑上的不自洽。
这种“抵牾”集中暴露在“自然”与“道”的关系处理上,《太平经钞壬部》中有明确的论断提及两者的关系:
天畏道,道畏自然。夫天畏道者,天以至行也。道废不行,则天道乱毁。天道乱毁,则危亡无复法度。故自然使天地之道守,行道不懈,阴阳相传,相付相生也。……道畏自然者,天道不因自然,则不可成也。故万物皆因自然乃成,非自然悉难成。如使成,皆为诈伪,成亦不可久。夫天地虽相去远阔,其制命无脱者。(《太平经钞壬部》)
“道”作为道家思想理论系统中(包括道教理论)最高的存在与最普遍的原则,理应具有至上性,这是道家、道教之所冠之以“道”的根本原因。但《太平经》作为道教经典又提出“天畏道,道畏自然”的观点,明确将“自然”位于“道”之位次之上,这两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老子·第二十五章》中的“天法道,道法自然”[9]353,但《太平经》又与之不同:一是将“法”改为了情感色彩浓厚的“畏”;二是“天畏道,道畏自然”有明显地将“天”“道”人格神化的倾向。①“天”与“道”的人格神化倾向不仅体现在此处作者以颇具情感色彩的“畏”来表达“天”与“道”、“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还体现在《太平经》的其它经文中,如“故天称神,能使神也。神也者,皇天之吏也”(《阙题》)、“夫皇天署职,不夺其心,各从其类,不误也”(《九天消先王灾法》)、“神者,道也。入则为神明,出则为文章,皆道之小成也”(《天平经佚文》)、“夫道乃深远不可测商矣,失之者败,得之者昌。欲自知盛衰,观道可著,神灵可兴也”(《知盛衰还年寿法》)等。如果说“道法自然”还能解释做“道纯任自然,自己如此”[6]173的话,而人格神的“道”与表达“恐惧”“敬服”含义的“畏”的结合,却很难让人将“自然”理解作“自己如此”,只能解释为“天”(“人格神”)膺服于“道”(“人格神”)、“道”(“人格神”)遵循“自然”。继而,“自然”这一法则成为了促使天地之道正常运行、万物“相付相生”的前提,可见《太平经》于此处将“自然”理解为一种最高的原则或规范,是天地之道运行的一种规范或规律。然而这一将“自然”视作凌驾于“道”之上的准则的做法,非但与道家思想的基本理念不符,而且也与经文中的其它文本存在差异,如“自然守道而行,万物皆得其所矣”(《安乐王者法》),如若将“自然守道而行”中的“自然”诠释为“自然之气”则又会引出“[元]气”与“道”之间的矛盾。
《太平经》曾着重强调“道”的生化作用:
道无所不能化,故元气守道,乃行其气,乃生天地,无柱而立,万物无动类而生,遂及其后世相传,言有类也。比若地上生草木,岂有类也。是元气守道而生如此矣。自然守道而行,万物皆得其所矣。天守道而行,即称神而无方。……凡事无大无小,皆守道而行,故无凶。(《安乐王者法》)
“道”无所不能化意味着“道”是一切“化”的原则。“元气”也必须遵循“道”,才能让“气”运行发展,从而生化出天地万物。天地万物从质料的构成上来看,都是“元气”的产物,但天地万物在形成的过程中又不得不遵循着一种普遍的原则“道”,所以最后的结论是“凡事无大无小,皆守道而行,则无凶”。既然“道”在“元气”之先,然而又为何会出现前文所引《六罪十治诀》中“元气治”在“道治”之前的情形呢?按照道家“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9]5的理论逻辑,“道治”本应成为至善之治,而在“道治”之前再加上“自然治”与“元气治”,确实使得人们在理解上出现了混乱。同理,如若将上文中“自然守道而行”中的“自然”理解作“自然之气”,虽然暂时规避了其与“道畏自然”的矛盾,但又会陷入到“[元]气”与“道”的矛盾之中。《太平经》中提到“元气”“自然之气”“太和之气”三种不同属性、不同功能的气:
气者,乃言天气悦喜下生,地气顺喜上养;气之法行于天下地上,阴阳相得,交而为和,与中和气三合,共养凡物,三气相爱相通,无复有害者。(《三合相通诀》)
天道常有格三气。其初一者好生,名为阳;二者好成,名为和;三者好杀,名为阴。……初生属阳,阳者本天地人元气。(《三者为一家阳火数五诀》)
元气,阳也,主生;自然而化,阴也,主养凡物。(《阙题》)
可见,“元气”与“自然之气”虽有不同,但也只是在功能(“生”“养”)与属性(“阳”“阴”)上有所差异,论其本质与在生化万物的作用上二者并无根本性差别。所以从“元气”“自然之气”“太和之气”在“生”万物作用的层面上看,以“主生”的“元气”概括三者亦无不可,或许这也是《太平经》言“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各有自祖始”(《三五优劣诀》)的真正原因。因此“元气”与“道”的矛盾一定意义上也是“自然之气”与“道”之间矛盾的折射与体现。
至此不难看出,《太平经》对“自然”与“道”的关系确乎缺少一个十分清晰的解读,也似乎颠覆了道家“道法自然”的传统认知。上述关于自然观念建构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背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太平经》内在逻辑上的混乱,但是也显现出《太平经》内容在理解上的张力。《太平经》自称“大洞极天之政事”,所论乃“拘校天地开辟以来,天文地文人文神文皆撰简得其善者,以为洞极之经,帝王案用之,使众贤共乃力行之,四海四境之内,灾害都扫地除去,其治洞清明,状与天地神灵相似”(《件古文名书诀》),这足见《太平经》所论之内容、所涉之领域的包罗万象,此特征也先天地决定了《太平经》中所用概念的多义性。以“道”而论,就本体论言,“道”有本根义,即“夫道何等也?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守一明法》);从生化之维言,“道”有生殖义,即“道者主生,故物悉生于东方”(《兴衰由人诀》);就化育之维言,“道”有变化义,即“夫道者,乃大化之根,大化之师长也”(《天咎四人辱道诫》)。如果说以上含义还是对原始道家思想的继承,那么“道”的原则义,则无论是在表述上还是在思想倾向上都要更偏向于儒家,如“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合阴阳顺道法》),这显然与《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讲法同出一辙。此外,“道”还有宗教观念上的神圣义,如“道者,天之心,天之首”(《利尊上延命法》)、“道者,乃皇天之师”(《天咎四人辱道诫》),明显具有将“道”人格化的倾向。“道”之含义在文本中,与上文所探讨的“自然”含义以及所涉及的“元气”内涵频频绾合,便足以窥见《太平经》思想内容的周彻与繁复。另外,该书亦不太可能由一人完成,《太平经复文序》中言“皇天金阙后圣太平帝君……故作太平复文,先传上相青童君,传上宰西城王君,王君传弟子帛和,帛和传弟子干吉”[3]附录744,这种道教内的传承体系虽往往不太可信,但它却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即该书应不是一时一人所作,而是“各家著录的书”[3]前言2,乃“集体编写”[10]。因之,其思想又凭添驳杂。所以,在某些层面出现抵牾与冲突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故而亦无需过分牵合以求圆融。
结语
《太平经》作为早期道教的经典,一方面延续使用了早期道家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另一方面又对这些概念的内涵进行改造,如将“道”“天”等人格化,同时杂糅了阴阳五行、方术等内容。在自然观念上,《太平经》对早期道家自然观念亦有新的发展与改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引入当时盛行的元气学说,并以元气说为基础,构建自然观念;第二,高度关注“自然”概念,并对“自然”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赋予了“自然”以新的涵义;第三,由于该书性质原因,《太平经》在构建自然观念时,“自然”与“道”之间产生了矛盾与抵牾。
《太平经》作为道家理论再发展的经典著作,在道家自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太平经》自然观念的塑造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与神秘主义特征,这与偏重内在精神的庄子以及强调工具理性的黄老思想已有赫然区别,与原始宗教色彩浓厚的老子思想也有显著不同,这种转变代表着道家思想形态的更新与发展。但在其背后,也体现出《太平经》对道家自然观念的开豁与综合,“自然”实体义与“抱元气于自然”的修养理论所体现的人文关怀可以看作是对庄子理论精神的延续;“天”“道”人格神化以及“自然”的原则义所折射出的政治意蕴又是对黄老政治哲学的深化;而“道畏自然”等所透露的思维方式①《太平经》通过“道畏自然”的方式,用“自然”来消解限制“道”作为人格神的绝对权力,反映到现实中即是“君”也要遵循自然规律。这种方式与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思维模式如出一辙,都是通过“推求”的方式进行的,尽管其内在意蕴有所不同,但却不可忽视其思维路径的一致性。关于老子“推求”的思维方式的分析,可参见张磊.论《老子》的宗教精神[G]//詹石窗,等.中华老学:第八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3:74-86.明显又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可见,《太平经》尝试对人文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进行调和,也意图对道家既有思想的进行综合,尽管在某些理论细节上《太平经》处理得并不完美,但是却不能否定它在道家自然观念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同时,《太平经》自然观念的构建与生发也是道家思想兼容并蓄的结果,它广泛吸收儒、阴阳等各家学说,在拓宽了道家思想在养生与经世方面的现实意义的同时,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另外,《太平经》亦是原始道家向原始道教转型的标志,其对传统理论的理解、诠释、创新方式亦对今日之学术发展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