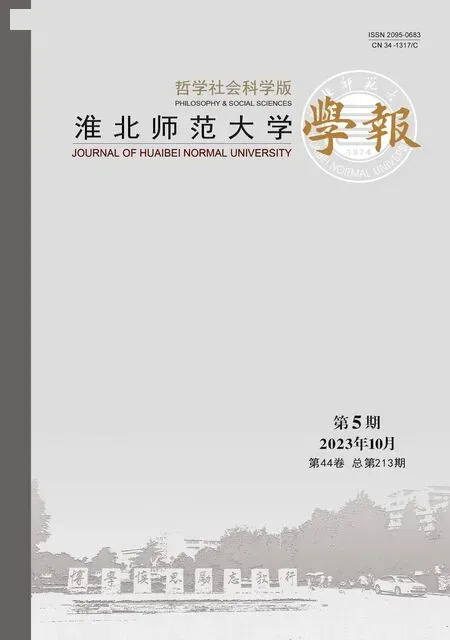周敦颐“礼先而乐后”思想诠释史谫论
杨抒漫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中国礼乐文化起源甚早,礼乐的作用主要有二:其一,修治身心,与刑、政互补而共成一均衡的社会治理体制,“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1]634,“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1]1076;其二,标示政权的合法性及其权威,“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1]1001,这里的“器械”除了指兵器,也包含与礼乐相配套的礼器、乐器,在当时是特定统治集团的专属之物,施礼用乐便是在展现统治权力。礼乐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修齐治平方略,中国先民较早地放弃宗教、巫术等非理性、非人文的统治术,故而作为理性和人文精神之集中体现的礼乐之出现有其必然性,礼乐也反过来促进理性和人文精神的蓬勃发展。
除了礼乐制度本身随时代而变化,思想家们对礼乐的认识也多种多样。先秦时期,儒家支持礼乐,道家、墨家反思礼乐,法家有礼法并重和重法轻礼两派。作为先秦思想总结者的荀子用六个字概括了礼乐各自的作用:“乐合同,礼别异。”[2]至汉代,王充认为:“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3]这是对先秦儒家礼乐观的扬弃。其后,礼乐的哲学演绎长期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直到宋代理学兴起。作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率先以天理、阴阳、中和等元素解读礼乐,并且,有别于常见的礼乐并重思维,周敦颐认为“礼先而乐后”:“礼,理也;乐,和也。礼,阴也;乐,阳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4]25对此,康有为评价道:“礼先乐后,精粹之言。”[5]本文要探讨如下三个问题:“礼先而乐后”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它对后世学者有怎样的影响或曰后世学者对之进行了怎样的阐释,它究竟是不是“精粹之言”。探讨上述问题的终极意义在于寻找一条最具现实意义的理解礼乐关系的思路。
“先”“后”两范畴的多义性决定了“礼先而乐后”的双重含义:第一,“先”“后”意味着重要性的高低之别,礼比乐更重要。第二,“先”“后”意味着事物到来的次序,这又可划分为两种情况:当礼乐作为政教手段时,应先制礼,后作乐;当礼乐作为政教理想时,只有圆满推行礼制,方可上达真正的乐教,乐教在实现难度和境界层次上高于礼教。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学者对“礼先而乐后”的诠释正沿着上述思路展开。
一、礼重于乐
这一诠释取向可进一步细分为两条路径:第一,礼者,理也,礼具有形上属性,故而礼比包括乐在内的一切形下教化方式更为重要,该路径以程朱为代表人物;第二,礼与乐被转化为内在的诚敬与和悦,诚敬比和悦更重要,若两者难以兼得,应舍和悦、取诚敬,舍乐而取礼,该路径以吴澄为代表人物。
(一)礼乐与体用
程朱理学将天理视为最高范畴,礼与理的对应关系决定了礼重于其他一切治道。关于礼,伊川论述道:“其形而下者,具于饮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极于无声无臭之微。”[6]668伊川对“无声无臭”的定义为“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6]4,其中虽没有“天理”二字,但天理的精神贯穿始终,因为“其命于人则谓之性”一语化用自《中庸》“天命之谓性”[7]17,所以,这里的“其”指天,在理学语境中,便指天理。
礼与理的对应关系并不意味着礼完全等同于天理,而是如伊川所说,礼具有形上和形下的双重面向。这一思想为朱熹所继承,朱熹认为礼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7]51,上承作为本体的天理,下应作为发用的人事。对此,朱子的学生问道:“先生昔曰:‘礼是体。’今乃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似非体而是用。”朱熹答曰:“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纸糊,此便是体;人摇之,便是用。”[8]101就具有节序万事万物的功能而言,礼是体;就其在日用伦常中的应用而言,礼是用。能与天理汇通的礼重于乐。
程朱将礼视为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之中介的观点渊源于周敦颐。虽然程子最先将天理作为本体,但在周敦颐著作中已然出现将礼、理、本体三者相统合的倾向。《通书·礼乐》曰:“阴阳理而后和。”作为连接太极和具体事物的范畴,阴阳兼具形上和形下意蕴,这在《太极图说》中有所体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4]4-5朱熹曰:“非有以离乎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耳。”[4]1不可以离却阴阳而言太极,也不可杂于阴阳而言太极,阴阳关联着又区别于太极。朱熹又曰:“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4]4相比于真正的形而下之器,阴阳二气显然无法为吾人的感官所把握,因此,阴阳既有向下化成可感世界的潜质,也可向上归入太极。当周敦颐说“阴阳理而后和”时,虽不与朱熹的看法完全相合,但显然是将阴阳作为形上、形下之介质,程朱对这一观点进行拓展,使得指称阴阳协调状态的“理”及其化身“礼”获得了高于包括乐在内的一切形下之物的意蕴。《通书·礼乐》还提到“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这里的“理”是名词,而非指称阴阳协调状态的形容词。濂溪所说的万物各得其理,似乎是对万物各自特殊属性的绝对肯定与放任,实际上,“万物各得其理”一说出现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这四对伦常关系之后,因此,为万物所应遵守之理是人世伦常与秩序即“礼”的扩大化,反过来说,人世之礼源于万事万物的共理。总之,在周敦颐看来,人与物皆化生自阴阳二气,且依循同一套理则,由此可推知人、物禀受同一本体,这演变为程朱所说的天理。伊川认为“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蚁知卫其君,豺獭知祭。礼亦出于人情而已”[6]180,将蜂蚁卫其君、豺獭知祭祀作为动物知晓天理的佐证,而忠、孝均是人世伦常和仪则,即人世之礼,这些礼根源于人的真淳无妄的情感,例如敬君与爱亲,这些情感在儒家看来皆是道德情感,是人性的生动体现。又因为人性来源于天理,所以,上引伊川之语的内在理路为:天理衍生出人性、人情、礼制,动物亦因与人同禀阴阳二气、同禀天理而具有与人世之礼相符合的行为,与人共同构建和豫的世界图景。
周敦颐使礼和理具有了初步的超越性质,程朱对此进行了合理发挥,明确以天理为本体,并将礼提升到天理的地位,礼与乐不再是同一层级的概念,乐是具体的政教手段,礼则是天理在人间的化身,“所以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今复礼,便是天理”[8]1079。礼高于乐,故而礼先乐后。
(二)礼乐与敬和
身历宋元两朝的理学家吴澄曾作《敬铭》与《和铭》两篇文章,在解释两者的先后次序时,吴澄说道:“敬与和二者不可偏于一也。然愚观偏于敬而失之离者鲜,偏于和而失之流者多。盖敬者必和,和者不必敬。借使偏于敬,而不能济之以和,犹不失为狷介;苟偏于和,而不能主之以敬,则必堕为不恭。……敬胜则离,和胜则流,固也。然与其流也,宁离。矧未必果离邪?圣贤雅言敬,而罕言和,岂无意哉?……吾于二铭,以敬为先,而和为后,亦周子之礼先而乐后之意云。”[9]338吴澄认为,周敦颐“礼先而乐后”可归结为敬先而和后,礼使人敬,过于讲求敬,便会造成人际疏离与行为准则的僵化;乐使人和,过于讲求和,则会弱化人伦秩序,使和气泛滥。这些论述都可追溯至《礼记·乐记》中的一段话:“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1]1085在《乐记》中,礼乐呈现并列关系,二者若操之过当,皆有失范的风险,所以应当使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制衡。《论语》中有子的话表达了与《乐记》相似的观念:“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7]51与此不同,在吴澄的论述中,寓意礼的敬高于寓意乐的和,敬者必然和,和者未必能敬,当两者难以兼得时,合理的应对措施不是取各自之长补对方之短,而是放弃和,独取敬,即“与其流也,宁离”。吴氏认为这是先圣之意的必然推论,“圣贤雅言敬,而罕言和”。实际上,圣贤并未罕言和,上引有子之言即为一例;圣贤亦未将礼、敬置于乐、和之前,而是强调二者的协作关系。所以,吴澄的观点距离先儒甚远。其距离周敦颐、程朱等近儒的思想也较远,具体地说,程朱将周敦颐的礼乐先后关系转变为诚敬与和悦的关系,吴澄则在一定程度上将程朱的观点进行了绝对化处理。
首先看程朱如何以诚敬与和悦两范畴转化周敦颐的“礼先而乐后”思想。朱熹指出:“礼乐固必相须,然所谓乐者,亦不过谓胸中无事而自和乐耳,非是着意放开一路而欲其和乐也。然欲胸中无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则自然和乐,而周子亦以为礼先而乐后,此可见也。”[10]1564除此之外,朱熹还对学生说道:“周子静则礼先乐后,程子敬则自然和乐。和乐礼乐,非尔所及,但时时收敛,将身心摄入静敬中,正心诚意,久之自有进步处。”[10]2266-2267程子的“敬则自然和乐”与濂溪的“礼先而乐后”一脉相承,这使得作为化民成俗之政教手段的礼乐退居幕后,作为行为状态和情绪感受的诚敬与和悦则走到台前。朱熹仅言“程子曰敬则自然和乐”,却没有指明是哪一位程子发此议论,《二程集》未载此言,《宋元学案》《理学宗传》《全宋文》等书在引用此语时,也未注明是哪位程子所言。不过,作者问题并不构成读者理解这句话时的阻力,因为程颢、程颐对诚敬与和悦之关系的见解有很多共通处。明道在评论《乐记》“中心斯须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入之矣”[1]1140时说道:“此与‘敬以直内’同理。谓敬为和乐则不可,然敬须和乐,只是中心没事也。”[6]31虽然敬、和不相等,但二者是一体共在关系,和不是敬的结果,不是次于敬的存在,而是敬的同位者。伊川曰:“申申是和乐中有中正气象,夭夭是舒泰气象,此皆弟子善形容圣人处也。严厉时则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时亦著此四字不得。”[6]216申申夭夭是对孔子燕居状态的概括,夭夭指和乐,申申则兼具和乐与中正。何谓“中正”?伊川认为:“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6]577若要达到中正之道,应当约束情感使其合于中道,诚敬己心使其远离邪僻,这都可以经由克己复礼而达成,前者表现为圣王缘情制礼,以礼节情,后者则正如伊川在《周易程氏传》中所说,“君子处己有道,以礼制心,虽处豫时,不失中正,故无悔也”[11],礼可以节制并匡正人心中的负面倾向,从而实现中正与诚敬。所以,礼是中正之道的要素,圣人之“申申夭夭”便是礼与乐、敬与和的结合,过于严敬或过于和悦皆不符合申申夭夭之旨。可见,伊川也如明道一般将敬、和视为一体关系。朱熹的观点与二程相同,他认为:“不和乐,不庄敬,如何行得礼乐!”[8]604并指出:“不是别有一个和乐。才整肃,则自和乐。”[8]861
其次看吴澄如何对程朱的观点进行绝对化处理。吴氏认为敬必然能使人和,学者若能专务于敬,那么和悦感将不期而然地到来,但这一因果关系反过来便不再成立,“敬者必和,和者不必敬”。由此可见,吴澄不像程朱等人将敬、和视为一体共在关系,而是以敬为第一位的存在,和只是敬的必然结果,不具备促进并强化敬的功效。过度的和容易流为狎昵,过度的敬容易流为死板,狎昵与死板皆于修养有害,但在持有严肃修养论的吴澄心中,死板终究优于狎昵。元代吴海《林和字叙》一文持类似观点:“礼乐相资,而礼虽不可无乐,而乐必由于礼,盖礼先而乐后也。……不患其不能和,患其不由礼也。不惟礼而惟和,吾惧其流而不知其极也。”[9]192不难看出,这样的观点过于绝对化,未能继承圣贤礼乐双修、敬和并用的智慧,甚至未能延续圣贤在面对礼、乐与敬、和难两全时提出的互补理论,是对周敦颐、程朱思想的扭曲。
二、礼先于乐
用“礼先于乐”解读周敦颐“礼先而乐后”思想,主要指礼制和乐教没有重要程度上的区别,但两者在修养中或在政教中的实现顺序有先后之别。
(一)礼乐与修养
前文曾提及程朱将礼与天理相对应,发展周敦颐的“礼先而乐后”思想,这时的礼与乐不是同一层级的概念,两者有形而上、下之分,礼重于乐。当礼与乐被转化为敬与和,同指人的修养状态时,程朱并不认为二者有轻重、缓急、先后之分。然而,后世一些学者在讨论作为修养状态代名词的礼乐时,扭转了程朱原意,继而得出礼先于乐、先有敬后有和的结论。
试举一例,伊川认为敬、和一体共在,真德秀则从伊川的相关言论中解读出了相反的意思:“必有自然之序,然后有自然之和,故圣人曰‘礼乐云’而不曰‘乐礼’。周子所谓‘礼先而乐后’,程子所谓‘无序则不和’,皆此意也。”[12]真德秀的这段话含有逻辑错误,因为,程子所说的“无序则不和”指秩序的缺失将破坏和乐,却不等于“和乐仅能出现在秩序之后”。实际上,程子强调秩序与和乐的共在关系,并不认为先有自然之序、后有自然之和,而是将敬、和皆视为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一存俱存,一毁俱毁。伊川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6]1135“无序而不和”中的“而”表示并列关系,人一旦叛离仁道正理,便会既失序,且不和,同理,若人能体悟天理,便会既有序,且和乐。这在朱熹的论述中也有所体现,朱熹既认为“须先是严敬,方有和”[8]518,似以敬为因,以和为果,实际上,朱子认为敬是“不待勉强如此,是他情愿如此,便自和”[8]518,敬则“自和”,二者之间没有严格的先后顺序,甚至可以说,若内心勉强、不和,便不会有敬(包括内在的严敬端正和外在的恭敬庄肃)。可见,真德秀对程朱皆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进而误解周敦颐的礼先乐后之说。类似的情况不为少见,例如黄百家认为:“程子谓敬则自然和乐,可以知礼乐之先后矣。”[10]488薛瑄认为:“尊卑贵贱各得其序,自无乖争,失序则争矣。以是知礼先而乐后。”[13]
清代陈沆《近思录补注》中的一条注文也曲解了周敦颐之意,其文曰:“治法不外乎礼乐政刑,二者之中,又是礼先而乐后。记曰:‘礼由阴来者也,乐由阳作者也。’淡者阴静之发,和者阳动之为,故先淡后和,亦主静之意。”[14]这段话首先引用周敦颐“礼先而乐后”之语,次将“淡”与礼之阴静相配,将“和”与乐之阳动相配,试图论证礼先乐后之旨。其中,“淡”相当于“敬”。但是,周敦颐并不认为淡在先、和在后,而是认为淡、和二者都是音乐的属性:“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4]29既然如此,以“先淡后和”论证“礼先乐后”的思路便是错误的,按照濂溪的原意,礼乐有先后,但同为乐教在人心中之投射的淡与和(或曰敬与和)不分先后。
还有一些学者采取调和主义的立场,既点明敬、和的一体关系,也试图论证敬先于和。例如陈淳认为礼乐一体,盗贼亦擅长统合礼乐、敬和:“盗贼至无道,亦须上下有统属,此便是礼底意。才有统属,便自相听从,自相和睦,这便是乐底意。”[15]50但是,礼乐终究有实现顺序上的先后之别,先有秩序,后有和乐:“长先少后,便相和顺而无争。其所以有争斗之心,皆缘是无个少长之序。既自先乱了,安得有和顺底意?于此益见礼先而乐后。”[15]50
真德秀、黄百家、薛瑄、陈淳等人在论及礼乐“先后”、敬和“先后”问题时,将作为内心情感状态的“乐”视为守礼的结果,却忽视了周敦颐常将“乐”作为与天道合一的高级乐趣,“孔颜乐处”即是这一思想的最佳表达。一切礼都是天道的变现,与天道合一的至高之乐则促使人守礼,或与礼一时俱在,难道能说“孔颜乐处”是遵守秩序和礼制之后才能获得的心境并由此推断出礼先乐后吗?当然不能。需要补充的是,《通书》所说的“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虽然点明理与和之间的先后关系,但迥异于陈淳等人的观点,因为濂溪的意思是宇宙的整体和谐只有在万事万物皆符合天道的情况下方可达到,作为主体内在情绪和修道体验的“孔颜乐处”不等于万物整体的和乐,亦不必待到万物皆“得其理”时才能实现。总之,认为礼、乐与敬、和在修养过程中的实现顺序有先后之别,这是对周敦颐思想的片面引申。
(二)礼乐与政教
关于礼制和乐教究竟何者最先出现在圣王政教史上,《通书》曰:“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4]28“乐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太和焉。”[4]30先制礼以成善政,后作乐以宣德音,乐主要是对圣王功绩的歌颂、对天地之气的感通。这是对《乐记》的承续,《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1]1091且载子夏对魏文侯说道:“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1]1123“大当”之世先制礼以纲维众兆,后作乐以歌颂功绩。关于《乐记》的成书年代,众说纷纭,但大多数人肯认它是对先秦儒家音乐思想的记录。可见,尽管周敦颐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礼先而乐后”的人,但相关思想早在先秦已然出现。治乱更替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也是思想家们思考历史哲学时必须注意的背景,“大当”之世必然由乱世变化而来,这暗示着圣王制礼的原初意图:闲邪存诚,化乱为治,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礼、乐在圣王政教中的先后顺序。
关于为何要在“大当”之世制礼作乐,《白虎通》曰:“太平乃制礼作乐何?夫礼乐所以防奢淫。”[16]虽然礼乐皆能防止奢淫,但只有礼能直接规制邪僻淫靡的行为,其效果的强弱直接表现于被教化者的言行举止,其施行有政刑作为保障。乐的教化作用较为间接,音乐能促使人进行自我陶冶、自我教化,却难以直接地、快速地在天下这样广阔的范围内制止不良行为。或许正因如此,思想史上一直不乏质疑音乐教化作用的人。例如,柳宗元认为圣王在天下安定、礼教昌隆以后作乐,乐是对圣王功绩的歌颂,却不具有移风易俗的功能:“圣人既理定,知风俗和恒而由吾教,于是乎作乐以象之。后之学者述焉,则移风易俗之象可见,非乐能移风易俗也。”[17]1281柳宗元还认为乐未必由圣王所作,而是圣王对百姓心声的收集与音乐化重现,恰如乐府采诗制曲,“乐之来,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圣人作也。圣人以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圣人饰乎乐也”[17]1281。明代也有人认为:“先王功成而作乐。故乐者,所以象成也,非乐可以定功而著成也。乐之缀兆,视乎功烈隆卑而已,使衰乱之世,奏至德之音,能风乎俗,复崇古之盛乎?否哉!”[18]1007音乐是对先王功业的艺术化记述,它并没有迁化风俗的功效,在乱世奏咸池、云门之乐并不能收到拨乱反正的效果。有学者在反驳上述观点时写道:“风之于天下,惟无有倡之者,始于微近,克于昭著,遂靡然而成俗。风之所趋,气不为之变乎哉?风可移乎气,谓治忽不出于声音之间者,是非达乐之情者也。”[18]1007这一反驳的效力十分有限,因为在其论述中,乐教是由微至著、由近至远的教化方式,若希望依靠乐教实现天下敦和,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花费相当多的精力,乐教移风易俗的最终效果或许优于礼教,其效率却不及礼教。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在古代政教领域中,礼教比乐教有着更强的推行力,应以礼为重于或先于乐的存在。这在周代官制中有所反映,《尚书·周官》曰:“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19]清代郝懿行《书说》曰:“成周礼、乐合为一官,俱掌于宗伯,乃止曰‘掌邦礼’者,礼先而乐后也。……谓之‘和’者,盖以乐言也。礼辨上下、定民志,等威辨而后情谊洽,以此见礼、乐二者,其用本不相离,神人以和,礼亦通于乐也,上下有序,乐亦通于礼也。”[20]礼乐本不相离,周代宗伯掌管礼乐,但《周官》中的这句话只说宗伯掌礼,未言其掌乐,何也?郝懿行认为,这正与周敦颐“礼先而乐后”一语遥相呼应,体现了周政对礼的高度重视。
三、乐重于礼
《尚书》中有一段被后人视为“礼先而乐后”之历史原型的记载,此即虞廷命官。舜任命官员时,先任典礼之官伯夷,后任典乐之官夔,礼先乐后。对此,南宋王炎解说道:“礼先乐后,故先夷后夔。乐作,则治功成矣。”[21]南宋黄震也认为周敦颐“礼先而乐后”与虞廷命官之事暗合,他认为:“《通书》称礼先而乐后,……愚谓此与虞廷命官终以典乐之意合。自鲁生有积德百年,然后礼乐可兴之说。”[22]前文从濂溪关于礼先乐后的观点中推导出制礼以治天下、作乐以颂功德、先有礼后有乐的结论,综合王炎和黄震的观点,可以获得更深层次的看法:“礼先而乐后”指先有海晏河清、礼教昌隆,而后才可兴发乐教,乐教的顺利推行标志着国家治理已进入高级阶段,君近尧舜禹汤,民近羲皇上人。在这一意义上,乐教的价值远胜礼教,乐重于礼。
周敦颐关于乐重于礼的思想可在一定程度上追溯至《礼记·乐记》。虽然《乐记》没有明确将乐教置于绝对高于礼教的地位,而是认为礼乐刑政四者殊途同归,但是《乐记》中隐伏着乐重于礼的倾向。《乐记》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1]1086“乐由天作,礼以地制。”[1]1090“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1]1093-1094内心的自觉认同优先于外在的强制性准则,天道高于地道,仁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重于义,那么,源于内心的、适配天道的、象征仁的乐比源于外部的、适配地道的、象征义的礼更加重要,境界更高,也更加难以实现。另外,《乐记》认为乐配静、礼配文,“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1]1086,周敦颐倡导主静之说,对应着“静”的乐教自然会得到濂溪的高度重视。
乐重于礼不仅可在治国理政层面成立,也可在个人修养中成立,孔子曰:“立于礼,成于乐。”[7]105礼使人安立于人际往来中,并挺立起自身德性,对乐的畅达和彻悟则使人进入大成的极致之境。宋儒更是将“成于乐”视为与天理混融一体之境,“到得‘成于乐’,是甚次第,几与理为一”[8]931。尽管孔子早已确立了对乐的高度赞扬,但一些后世学者拘泥于严肃的道德修养论,认为礼教重于乐教,规矩重于感通,扭转孔子所确立的传统,认为圣贤重礼不重乐。例如,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提到清人姚际恒对孔子“立于礼,成于乐”的错误理解,姚曰:“礼乐固皆由中而出,然自有先后本末重轻之分。如‘礼云乐云’‘如礼何如乐何’之类,此先后也。如‘立于礼成于乐’之类,此本末也。”[23]200姚际恒提到的“礼云乐云”和“如礼何如乐何”分别化用自《论语·阳货》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7]178和《论语·八佾》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7]61,这两句话反映了孔子对礼乐之本的探究,而非对礼乐进行先后排序。姚氏以本末关系理解“立于礼,成于乐”,更是大错特错。姚际恒从礼乐先后的角度出发,误读了《论语》,我们可以据此猜测他亦未能领悟周敦颐“礼先而乐后”思想中的乐重于礼的面向。并且,或许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判《乐记》为伪书,认为《乐记》“先乐后礼,本乐末礼,重乐轻礼”[23]200,又因为道家反对礼制,姚氏进一步推导出《乐记》是彻头彻尾的道家之书。实际上,若能仔细研读《乐记》,便会发现它并不将乐教视为凌驾于礼教之上的存在,而是认为乐教能帮助人达到更为超迈高邈的心灵境界。博学如姚际恒,竟会对《论语》《乐记》《通书》有一连串的误解,且如此排斥乐教,这或许与其反理学的立场有关。理学家多重视《乐记》,也重视音乐在润养性情、教化百姓中的作用,为理学家所崇扬的光风霁月的胸襟也带有与乐教一脉相承的从容洒落之感。若如姚际恒一般将特殊的学问取向和思想立场引入对礼乐关系的思考中,既错会孔子,也错会濂溪,还错会《乐记》,最终错会中华礼乐文明,上文分析过的种种误解足以说明这一点。
结语
礼乐一体,在修齐治平的实践方略上,礼重于乐;在修齐治平所达到的境界上,乐重于礼——这是周敦颐“礼先而乐后”思想的基本内涵。其他学者在诠释“礼先而乐后”时,所走的道路或是对濂溪思想的合理发挥和忠实再现,或是对其思想的误解甚至扭曲。合理发挥者,指程朱以天理升华礼,礼高于乐,又以敬、和转化礼、乐,礼乐一体;忠实再现者,指郝懿行等人将古时官制与“礼先而乐后”相结合,礼先于乐,乐重于礼;误解甚至扭曲者,指吴澄、真德秀等人割裂敬与和的关系,认为和是敬的结果,而非敬的同位者,礼重于乐,若二者难两全,应舍乐而取礼。这些观点源于不同的学术立场,分别以哲学的、历史的、工夫论的眼光看待礼乐关系。其中,第一条思路减损了礼乐的实践价值,几乎使礼乐成为天理论的附庸,但推进了礼乐的哲学演绎;第三条思路割裂礼、乐关系,但对于在敬、和之间有所偏滞的人来说,不失为一条切近的修养方法;惟第二条思路最能揭橥古代礼乐文明之政治实践意义,所惜于哲学思辨方面有所欠缺。一方面,于某些方面有所长却于其他方面有所短几乎是一切诠释著作的必然困境,诠释者难以确切知晓原作者的本意。另一方面,有时正是这种看似偏颇的诠释路径造就了优秀的诠释者,因为他们将既成的经典视为可资借鉴以开新篇的鲜活思想资源。
不过,本文并非单纯讨论诠释学问题。由于礼乐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的实践学问,所以,对待礼乐的最佳方式是在实践中理解之、发展之。如今,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古老礼乐文明的活化,“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盛大庄严、气势恢宏,礼序乾坤、乐和天地’、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庆祝活动‘气势恢弘、大度雍容,纲维有序、礼乐交融’”[24],可谓礼乐焕发新生机的典范。在更大的层面,礼乐的别异、合同之效可以帮助构建秩序井然又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照可知,周敦颐的“礼先而乐后”不完全是“精粹之言”,因为当代中国人的实践证明:礼乐一体,并非先后轻重有别。总之,探究“礼先而乐后”的诠释史,其基本目的是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礼乐文明,其根本目的则是帮助我们思考如何让礼乐精神以新的姿态绵延于当代中国、如何让其引导吾人走向既诚敬又和乐的修养境界。
——长春市第一中学学校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