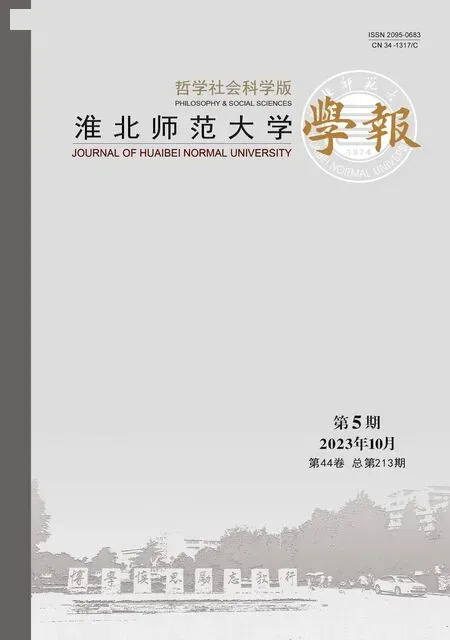安徽公立女学堂创办若干问题考辨
王耀祖
(淮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中国近代女学肇始于19 世纪40 年代外国传教士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半个多世纪后,国人自办的新式女学方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一省女学的设立既反映了该省教育的发展程度,更体现了其风气开化与“启蒙”程度。近年来,女子教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然而就安徽女子教育史研究而言还处于起步阶段,不仅一些影响极大的女学未得到充分重视,甚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①如关于安徽省国人自办的首所女学,学界即有不同的看法,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皖政辑要》认为全省公共的首所女学堂和女师范学堂分别是陈维彦在芜湖创办的公立女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刘廷凤在安庆创办的女师范学堂(三十三年〔1907〕四月),而地方最早的公私立女学则分别是歙县公立端则女学堂(三十一年〔1905〕正月)与巢县私立新民女学堂(三十一年〔1905〕二月);([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52《女学堂》,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539页。)二、《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则认为安徽首所女学是张振埙等创办的竞化女学堂(三十二年〔1906〕)。(《各省第一所女学堂一览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32页。)。作为全省开办较早、影响巨大乃至有“始基”之誉的安徽公立女学堂,文献关于其创办时间、创办人、名称与性质等关键问题均存在着分歧或模糊之处。本文作为对安徽近代女子教育研究的尝试之作,之所以选择安徽公立女学,基于三点考量:其一,其为全省首所省属公立性质的女子学堂,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对安徽尤其是皖南女子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安徽近代妇女启蒙运动和教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其二,尽管此学堂对于安徽的女子教育意义重大,然而学界目前尚无人、无文专论;其三,比较而言,对于该学堂,近代报刊有一定的报道,尚可藉此梳理、揭示其大致面貌。
一、创办时间②按:本段文字出于方便,采用帝王年号纪年、夏历纪月,并根据需要将公元纪年、纪月标于后。报刊后括号内所标之年份为该报刊最早记录安徽公立女学堂的年份,而书籍后之年份为书籍成书之年份。下同。
有关安徽公立女学堂记载较早且权威的文献主要有七种,分别是《申报》(1906)、《东方杂志》(1906)、《学部官报》(1907)[1]389-390与《皖政辑要》(宣统末)、陈惟彦《宦游偶记》(1913)①按:陈澹然“题词”云“癸丑,同客都门,吾乃促成斯记”;陈惟彦“自序”云“癸丑长至前五日”。陈惟彦撰,徐建生编次:《强本堂汇编》,铅印本,民国六年(1917)。《强本堂汇编》4卷,包括《宦游偶记》2卷、《著述偶存》1卷、《寿考附录》1卷。、《安徽教育月刊》(1919)[2]1-16、民国《芜湖县志》(1919)。就女学堂创办之年份,均认为系光绪三十二年(1906),但具体到月份则有三种看法:第一,闰四月二十七日(《申报》);第二,七月(《学部官报》《皖政辑要》);第三,八月(《安徽教育月刊》)。且在表述上有“成立”(《申报》)、“创办”(《东方杂志》《宦游偶记》、民国《芜湖县志》)、“创立”(《学部官报》)、“开办”(《皖政辑要》《安徽教育月刊》)等不同说法,因这些表述意思较近,这里不做具体区分,均认为都是创办(开始举办)的意思。
下面分述之。
《申报》:安徽公立女学堂成立 芜湖大通督销陈劭吾观察、巡警局黄润九观察等集资创一安徽公立女学堂,学额八十名,幼稚生二十名,学费每年洋银四十八元,定于本年八月初一日开校。上月二十七日,官、绅、学、商界在湖南会馆会议此事,输捐颇为踊跃。李伯行京堂认捐洋三千元,为捐款中最巨者。公举陈劭吾为总理,李仲絜、张伯纯、李光炯为副总理。现已在城内选择大厦,并购地建造幼稚园。[3]
《皖政辑要》:女学堂,公立,在芜湖城立铁锁巷,三十二年七月由陈维彦开办。以江苏驻芜米厘为常年经费。学生五十七名。[4]539
《安徽教育月刊》:本校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开办,原名安徽公立第一女学。[2]1
《学部官报》因以表格形式出现,《宦游偶记》、民国《芜湖县志》只说年份,均不列。《东方杂志》虽未说明具体日期,但将女学创办的报道刊载在第三年第九期(即光绪三十二年,发行时间为该年八月二十五日,公历1906 年10 月12 日)的“教育”栏内,即在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之前,已经创办。[5]《学部官报》与《皖政辑要》所言“三十二年七月”开办,较为清楚,毋庸多论。
《申报》的报道虽较为复杂,但也较为详实。通过研究,可将该段文字分为两层:“芜湖大通督销”至“李光炯为副总理”为第一层,“现已在城内选择大厦,并购地建造幼稚园”为第二层。以《申报》刊载之该新闻稿为分界,两层对应两个时段,即过去——“上月二十七日”至报道日;将来——报道日至八月初一日。过去(历史)是对已经发生事情之追溯性描述,它无可改变,只能据实叙述。将来是基于当下对未来可能发生事情之预测,它充满着变数(后来校舍地址变更与开学日期推迟都证明了变数的发生)。此两时段之关键时间成为女学堂发展史上的重要日期,在此可称之为发起日与开学日。
发起②按:《申报》虽标示“安徽公立女学堂成立”,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诸如学堂管理、招生规则、课程标准、教职员聘任、运行经费等并未制订或解决,实不能算作成立,而谓之发起更为合适。:“上月二十七日”,即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七日。发起之日,学堂创立者在湖南会馆组织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涵盖官、绅、学、商界的筹划大会。会上组建了筹备创设学堂的管理机构,陈劭吾(即陈惟彦)为总理,李仲絜(即李榘)、张伯纯、李光炯(即李德膏)为副总理;开展了募捐,且较为成功,李伯行(即李经方)捐款最多——三千元大洋;确定了学堂名称、招收学额、学费、开校日期以及拟定校址、附设幼稚园等。
开学:原拟于本年八月初一日(9 月18 日)开校[6]。然而,根据《申报》的续报,直到八月初七日都未能开学,原因是在新租定的河南江口校址上建造的讲堂尚未竣工,“开学之期须缓数日”。[7]此后,《申报》关于女学开学的报道就此停止。遍查其他报刊,也未见记录。但结合《申报》“须缓数日”开学与《安徽教育月刊》八月“开办”之语,可知在该月中下旬还是最终实现了开学。
前有发起日,后有开学日,中间似乎还应有重要的成立日。而《学部官报》与《皖政辑要》所给出的日期恰好可以予以说明。1907 年,《学部官报》第38、39 期刊载了基于罗振玉等在皖学务调查的报告——《奏派调查安徽学务员报告书》[8]③按:罗振玉等在皖调查学务,《申报》亦有报道,见《调查学务员赴宁》,《申报》1907年5月31日,第2张第11版。罗振玉本人主编之《教育世界》也载有《安徽学务调查总说》(第153号,1907年7月)一文。。报告中谓安徽公立女学堂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所言日期与后来成书的《皖政辑要》一致。前者所言基于对学堂的实地调研,后者基于官府档案④按:《皖政辑要》谓“是书编纂均以案卷为据”,“凡例”,第2页。,两者均较为可信,加之互证,几无可疑之处。而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申报》又刊载了《安徽公立女学开校有期》的文章,内谓“芜湖安徽公立女学堂成立等情已纪前报,……兹又由官、绅禀请江督,在苏米捐项下月拨银二百两作常年经费。刻下业已租定河南岸民房为校舍,报名投考者实繁有徒,职员、教员照章一律延聘女士,准于八月朔日开学,所聘女士皆海内名媛。女学之兴不难拭目俟之”,显然是对“安徽公立女学堂成立”(五月初五日〔6月26日〕)的后续报道。此次报道对常年经费、校舍、报名投考、教职员延聘等都有了交代,毫无疑问这些重要问题是经过了筹备组织再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此次会议据报道日期推算应在七月初,于女学堂的创办意义巨大,故被《学部官报》《皖政辑要》视为学堂的“创立”或“开办”日期。
《申报》《东方杂志》《学部官报》《安徽教育月刊》与《皖政辑要》《宦游偶记》,就体例大致而言不外乎报纸、杂志与书籍(志书)三类。报纸讲求实效性,故于时间精确性较高;而杂志在于纪事,志书在于追述历史,于时间均有不甚考究之弊;但因《学部官报》《安徽教育月刊》《皖政辑要》所采资料为当时的学校、官府档案,故亦可弥补其不足,具有较强的精确度。所以,通过对《申报》《东方杂志》《安徽教育月刊》《学部官报》《皖政辑要》的梳理及互证,所确立的安徽公立女学堂的发起、成立、开学等时间,是基本可信的。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安徽公立女学堂发起于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七日(1906 年6 月18日),七月初成立(8月底),八月中下旬(9月底—10月初)开学。
二、创办人
关于创办人,较早出现的文献给出了五种说法:第一,陈维彦(《皖政辑要》)①按:《安徽省教育大事记:1896—1995》(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持此看法。;第二,程继彦等(《东方杂志》);第三,陈劭吾、黄润九等(《申报》);第四,陈惟彦、李宗棠、李德膏(《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1934 年)[9]415②按:《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页)于学堂创办人之观点源于《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李光炯等(民国《芜湖县志》)③按:《芜湖教育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页)承袭此观点,但后又谓李光炯、阮强等。。五种说法可整合为有两类情况,第一二三四种为一类,第五种为第二类。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类中差异只是详略之分,而类间不同则是根本的。
先说第一类。前四种观点之所以作一类,因其均首指一人——陈惟彦。《东方杂志》之“各省教育汇志·安徽”谓:“大通督销程观察继彦等创办女学一所,名曰安徽公立女学堂,并附设一幼稚园,所需经费由李伯行京卿独立担任。”[5]从所称官职及事件来看,除了简略外,与《申报》基本一致。皖中南口音多前、后鼻音不分,致陈、程读音相同,而继、维易产生拼写之误;劭吾乃陈惟彦之字,故程继彦、陈劭吾、陈维彦,均指同一人。查徐建生所辑《寿考附录》内他人追述陈思想事迹之文章、陈自著《宦游偶记》《著述偶存》以及《清史稿》等均作陈惟彦,故陈维彦应作陈惟彦。《宦游偶记》“丙午(1906)正月奉委督鹾皖岸”,陈惟彦自注谓:是年兼监督芜湖皖江中学,创办安徽第一女校。[10]12可见,无论陈本人,抑或他人(前四种观点之作者)都对他创办安徽公立女学堂这件事持肯定态度。除此之外,也可以结合陈惟彦早晚年的事迹与思想,来推断其中年创办女学堂一事的可信度。
陈惟彦(1856—1925),字劭吾,安徽石埭(今安徽石台县)人,曾出任贵州黎平府知府、江苏道员,1904 年被两江总督周馥委派任南京厘捐局总办,1906 年初被任命为皖岸盐务督销局总办。时人评论其“为政实以兴学、育材、藏书、课士、劝农桑、教树艺、戒缠足、禁鸦片,汲汲开文化、厚风俗,为根本要图”[11]43,《清史稿》本传以“良吏第一”赞誉之[12]12563。
早年贵州为官时,陈惟彦即提倡“禁缠足”与女子教育,“敦尚礼教,兴女学,禁缠足”、“立《幼学分年课程》”[13]49,尤为关心妇女与幼童两类弱势人群。不但如此,他还专门发布《劝兴女学不缠足示》,厉行女学、严禁缠足。在这篇令示中,他认为即便一普通人,“照得气质欲求变化,……固尽当读书”。就女子而言,其一,女子“聪颖不亚于男”,有能力学习,故“圣贤立教之心不以男女而或异”;其二,上古即有重视女子教育的传统,“师氏之号著于《周南》,姆教之从详于《内则》”;其三,女子受教育后端庄有礼、勤俭持家,必能德懋贞顺、言语得体,“容工必兼德言,女子亦岂宜费学”;其四,女子受教育于家庭极有益处,“为夫者内得贤助,家道藉以昌隆;为子者训懔慈帷,襁褓已就模范”;其五,就现实状况而言,女子不学,“性多愚蠢”,“上既不足相夫……下更不能课子。甚至伤风败俗,靦不知非”。因此,他倡言、敦行女学,谓“岂可贱女贵男,弃而不教?视之俨同化外,使之下等野蛮。不特大失先王阴教之规,抑且隐兆家庭无形之祸”[14]48-49。诚然,陈氏早年虽对理学家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持批判态度,但就女子受教育之目的而言,他却未能突破相夫教子之陈陋偏见。
晚年,陈惟彦致力于里族慈善事业,创设体仁堂,以“施济之道,男女自应一视同仁”,收留救助幼长孤寡贫困女子,并谓“俟经费稍裕,另设女院,一律收养”[15]11;兴复育婴堂,捐资创办崇实高等小学等[11]43,以实际行动,践行其发展教育、兴女学、禁缠足之主张。以设立陈氏固本义庄为例,义庄“每年收入除纳税及开支薪费外,约提储十成之三为开办族学及其常年经费,其余即以资助族人教养婚丧之用”,发展资助教育于此可见一斑。在对家族求学子弟资助时,特别指出女童或童养媳肄业女校之资助一视同仁;且为矫正社会重男轻女之偏见,专门对“贫苦之家产女无力抚养者”按月资助,但是若“贫女既受资助,其家复将女溺死或虐待致死或卖为婢女者,送官究治,并追缴其所受资助之全额”。他还把资助与提倡禁缠足结合起来,“贫女曾受资助者不得缠足,违者得干涉之”,“族人嫁女实系极贫者助费拾元,缠足者不助费。族人嫁女查系天足或曾缠足而经解放者致送贺仪肆元”,族人弱冠而无力婚娶者,若“所娶之妇查系天足或曾缠足而经解放者另送贺仪肆元”;[16]49-52虽家贫,而“三十岁以下妇女缠足者,概不资助”[17]48。对外如此,对内亦持同等态度,如其制订家训时,谓“女学为兴家之基。世谓女子无须于学,此谬论也。粗习书算所益已为不鲜,渐明义理则保全尤多。故女学略同于男子”[18]85。
通过对陈惟彦早晚年言行和思想轨迹的梳理,可以发现他对女子和女子教育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其知天命之年任皖江中学监督、创立女学既是延续、践行早年言行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其晚年思想发展脉络的重要一环。因此,陈惟彦创立女学是可能的,也是在理的,而上述诸文献所载正是对历史事实的追述与尊重。
据《申报》记载,女学发起日,除陈惟彦外,尚有几名重要人物,黄润九等为募资人,李伯行为捐资最巨者,而李仲絜、张伯纯、李光炯三人被推选为副总理。黄润九,名家伟,江西人,道员,曾任芜湖巡警总办,时任芜湖警察厅长[19]。李伯行,名经方,李鸿章长子,时任皖省铁路总理,督办芜广铁路(芜湖至广德)[12]4441-4442,[20]。此两人均为政界代表。李仲絜,名榘,曾任芜湖招商局总办,时任芜湖商会总理[21],为商界代表。张伯纯,时任皖江中学堂副监督[22]。李光炯,名德膏,时任安徽公学、徽州公学监督[23]。后两人均为学界代表。而此时陈惟彦不仅担任皖岸盐务督销局总办,且兼任皖江中学监督,跨政、学两界。因史料所限,我们无法一一考察他们在女学发起过程中的具体贡献;但据不久后刊发的《奏派调查安徽学务员报告书》记载,学堂成立初,管理层“总理”一职有陈惟彦、李榘、李德膏、阮强等4人。李榘、李德膏继续担任总理,可见他们在女学堂创办过程中的贡献是一贯的,地位仅次于首创者陈惟彦。而黄润九、李经方、张伯纯分别主要以募资人、捐资人及副总理的身份见载,足见他们在学堂筹设过程中亦起了重要作用。至此,可以认为,在女学堂发起、创办过程中,陈惟彦、黄润九、李经方、李榘、张伯纯、李德膏等人均发挥了作用,但贡献大小是有差异的,故排名亦应有先后之分。陈惟彦作为发起兼创办人,应居首功;而李榘、李德膏、张伯纯、黄润九、李经方等人,依次排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第二类观点认为创办人是李光炯,不能说错误,但却不完全符合史实。若谓其为创办人之一,自然可以;但若以其非首功之个体囊括其他全体,则甚不合宜。民国《芜湖县志》仅列李光炯为创办人,除了因时间原因所致史实错位外,可能还有一层原因——李光炯在安徽新教育中的地位。李德膏(1870—1941),字光炯,安徽枞阳人,1897 年江南乡试中举,后弃科举从吴汝伦游,深得吴器重;随吴汝伦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襄助创办桐城中学;受聘湖南高等学堂时,与卢仲农共创安徽旅湘公学;旅湘公学规模略具,即迁芜湖改名安徽公学①按:《皖政辑要》谓安徽公学“光绪三十年二月由绅士李经迈德膏在湖南开办,名曰旅湘公学。三十一年迁回芜湖,更名安徽公学”(第503页)。“李经迈德膏”应为两人,“李经迈”字季高,安徽合肥人;“德膏”应为“李德膏”,字光炯,安徽枞阳人。后《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芜湖县志资料选编》(第2辑)(芜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芜湖县印刷厂1989年,第3页)等不加考订,以讹传讹。,先后礼聘刘师培、陈独秀、谢无量、苏曼殊、柏文蔚、江炜等人讲学其间,安徽公学也因此成为清末民初安徽中等学校中最为活跃与著名者,这些都与李光炯的贡献密不可分。民国后,李担任安徽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安徽省教育界享有较高的声誉。[24]随着李在安徽教育界地位与声誉的不断提升,许多与之有关的事迹可能会被有意或无意放大,其原本之形象反被不断增添的光环所遮蔽,以致无法辨认。这种现象在历史研究中常会碰到。然朱光潜在为其作传略时并未有片言提到创办女学堂一节,于此可见其在女学创办中并非居首功者。
至于《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与《芜湖教育志》认为创办人还有李宗棠、阮强,显系错误。因为无论是首倡人、抑或筹备人,均未见李宗棠、阮强之名。当然,阮强对女学的发展亦是有贡献的。自女学创立,他先后担任总理(在五名总理中排名最后)、监督兼教员[1]390,直至1922 年发生学潮[25]。因担任校长时间最长,加之其人格与学问,对学堂前期的发展贡献较大,致有“开山道河”之誉[9]415,但却不能因为此认为他也是创始人。
三、学堂名称与性质
目前从已查阅的相关史料来看,关于女学堂的名称也存在着一些出入。《申报》《东方杂志》《安徽白话报》[26]、民国《芜湖县志》均谓“安徽公立女学堂”,且谓“名曰安徽公立女学堂”(《东方杂志》)、“原名安徽公立女学堂”(民国《芜湖县志》),亦见此谓确凿。《学部官报》所刊载《奏派调查安徽学务员报告书》在第三部分“安徽全省学堂名目表”、第四部分“调查省内外各学堂分表”分别称“公立第一女学堂”和“安徽公立女学堂”。前者称谓“据去年学务公所调查”,即1906 年安徽学务公所调查编册入档的官方材料。后一称谓乃当时罗振玉等人亲赴学堂调查所得。[27]362《皖政辑要》在编撰该学堂条时,以“女学堂”为标题,下谓“公立”,并未给出具体名称。《安徽教育月刊》称之“安徽公立第一女学”,创办人陈惟彦在《宦游偶记》中谓“安徽第一女校”,而《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1934)曰“芜湖女子公学”[9]205①按:《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关于安徽公立女子学堂的记载,错误较多,如谓创设于光绪三十一年(应作三十二年,前已辨明,此不赘述),民国三年(应系二年)改为安徽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等;而对于“芜湖女子公学”之名,遍查史籍未见此称呼,不知所据,此处列出,不在本文分析之列。《芜湖教育志》谓女子公学(第342页),估计来源于此。。
从三个名称在文献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来看,《申报》与《东方杂志》报道于1906年,《学部官报》1907 年,陈惟彦《宦游偶记》1913 年,《安徽教育月刊》与民国《芜湖县志》1919年。可见,安徽公立女学堂这一名称出现最早,其次是公立第一女学堂、安徽第一女校、安徽公立第一女学。从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层面而言,出现较早的价值较高,可信度较大;但若考虑到当事人则另当别论。依常规而言,当事人的叙述又具有较大的可信度;但是,也要具体分析。陈惟彦的《宦游偶记》作为其从政事迹的汇编不是其当时的创作,而是其晚年以回忆的方式所作的追述。这一点在《强本堂汇编》陈澹然的“题词”中说得很明白:“癸丑,同客都门,吾乃促成斯记。”陈惟彦“自序”更谓:“国变以还,都成隔世,宦游陈迹,渺然相忘。比来京师,端居稍暇。陈子晦堂(陈澹然)敦促记之,乃就其可忆者笔之简端。吏事纷纶,不过百之一二。人地时日,弥复遗忘。一鳞一爪,聊以示后昆云儿。癸丑长至前五日。”癸丑年即1913 年,此时据办理女学堂已7 年之久,在这7 年中世事纷繁速变,同时一近花甲老人,记忆难免模糊;且晚清所有学校尚称为“学堂”,改称“学校”是入民国的事,“女校”称谓显系历史错位。再者,《宦游偶记》重点在于追忆宦海经历,就其体例而言无暇兼顾其他,故《宦游偶记》中对创办女学堂事仅在注释中出现。另一著作《著述偶存》,是其往日为官时所作书、记、跋之汇编,涉及兴学之事甚少。所以,经陈氏回忆所给出的“安徽第一女校”这一名称,是值得商榷的。作为由芜湖官、绅、学、商届众人参与创办、有着较大影响的学校,开办前创办人群体对于学堂名称肯定有过商讨。对此,作为发起和创办人的陈惟彦应亲历其事,甚至“安徽第一女学”有可能就是他当时所提议的名称。因其提议,记忆深刻,至晚年创作《宦游偶记》时,未加多思,随笔写下,也不无可能。
“安徽公立第一女学(堂)”与“安徽公立女学(堂)”比较,多出“第一”二字。查《奏派调查安徽学务员报告书》之“安徽全省学堂名目表”所列省城、八府及五直隶州60州县学堂名目中,并无女子学堂。但参考其他史料,可知在该女学堂前,安徽省至少已出现了三所国人自办的女学堂(见表1)。省提学使司尚不知有其他女学的存在,公立女学的创办者们估计也未必知晓。其他女学,在1906 年的学务公所调查中并未见登记,后依据官方档案编纂、至宣统末成书的《皖政辑要》始著录,可知它们的影响并不大。另外,公立女学的创办群体在全省乃至全国均有着一定的影响,加之其以“全省公立”面貌出现,较其他诸女学堂或县公立、或私立,影响当然较巨,至有“始基”之誉[1]390。综合以上诸因素推测,学堂成立后一度以安徽第一女学自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仅就全省女子教育出现时间而言,固不可自封第一。

表1 安徽省国人自办女学堂一览表(1906年前)①按:公立端则女学堂、私立新民女学堂资料来源于《皖政辑要》(卷52,第539 页)。竞化女学堂资料来源于《申报》(《安庆学务》,1906年1月31日,第2张第9版)与《东方杂志》(《各省教育汇志》,第3年第5期,1906年6月16日,第98页)。
1919年,由安徽省教育厅编辑印行的《安徽教育月刊》第18 期以大篇幅(16 页之多)刊载了《安徽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报告要项十三条》一文。该文以报告的形式刊发在教育厅主办的刊物上,同时结合其对二女师历史及现状的熟悉程度,虽未署名,但可以推断出作者或为教育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或为二女师教职员。在追述二女师历史时,文中称该校“原名安徽公立第一女学”。此名称估计有两种来源:第一,官方档案,即晚清时期提学使司的存档,而能接触到政府档案材料的应该是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第二,学校档案,但在该校的档案记载中到底初名为何,已不可知。而此时安徽省已出现两所女子师范学校,正在酝酿建立第三所[28]。先更名为安徽公立女子师范学堂的公立女学堂,不得不根据全省女子师范统筹发展之需要,再次更名为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与此前的所谓唯一公立相比,地位已大不如前,所以作此文之作者(若为该校教职工)大有因地位下降而产生失落之情结,在追述其历史时特加“第一”二字以凸显其往日之辉煌。
但是,无论如何,最后还是选择了“安徽公立女学”名,不然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报刊杂志——《申报》《东方杂志》,不可能数次报道时均谓此名;而罗振玉等人调查学务时,陈惟彦正担任女学第一总理,其他重要参与创办人也尚在学堂任职,所以根据调查而刊于《学部官报》的学堂名称及现状,毫无疑问是经他们所认可的。
根据安徽公立女学堂的名称,可知此女学堂性质为公立。何谓公立?参考1904年1月清廷颁布并施行的全国性学制系统——《奏定学堂章程》,谓“由官筹费……名为官立中学”,“地方绅富捐集款项,得按照《中学堂章程》自设中学。集自公款,名为公立中学,一人出资,名为私立中学”[29]。《安徽省教育大事记:1896—1995》也谓:“清末,安徽中学堂分为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类。政府办的学堂称为官立(分省立、府立、州立、县立和数县联办的共立),由地方士绅、宗族或公众团体集资兴办的称为公立,由个人出资或由外国教会经办的称为私立。”[30]可见,其官立、公立与私立性质之区分,乃以学堂创办时筹款来源而定,但是对学堂创设后日常运行之经费则未作说明。
就安徽公立女学堂的情况来看,据《申报》所载,其所筹经费包括开办经费和常年经费两种:开办经费“约五千余金,李伯行京卿倡捐三千金,嗣官、绅、学、商各界继捐者颇为踊跃”;常年经费“由官、绅禀请江督,在苏米捐项下月拨银二百两作常年经费”,[6]《皖政辑要》也称“以江苏驻芜米厘为常年经费”。《学部官报》谓:开办经费系由官绅捐助;常年进款由米厘局拨银二千四百两,又学膳费二千五百二十元。[1]390从其开办经费来看,既非政府,也非个人出资,而是从社会募捐所得之公款:应是公立。从常年经费“驻芜米厘”来看,乃援引皖江中学、安徽公学之例[31],显系地方公共捐税,学堂又带有官办的性质。据此,可以认为安徽公立女学堂其性质为公立官助。事实上,当时安徽的公立学校大多都存在这种情况,以中等学校为例,1908年以前全省公共公立中等学堂仅有两所,除安徽公学外,还有第一公学,虽曰公立,但其常年经费均有官府米厘一项,此外还有田租、捐款等,经费来源较为复杂。[4]503-504盖当时教育经费尚未独立,且较为紧缺,单单依赖任何一项经费都很难保障学堂的正常运转,所以不得已采取了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官立与公立,就有相互交叉之成分,有时甚至难以区分。所以,若完全以创办经费来源,而不考虑开办后之常年经费,遑论学堂性质,不但无法解释复杂的历史,甚至因简化历史而曲解历史。
显然,仅靠募集捐款很难保证经费的稳定性且势难持久,“遂不免要求地方公费之补助,但地方公费各有所归,必无闲款可以指拨,即有可归学务上动用者,亦已为官立、公立各学堂所挹注,必无余力再及于此。其结果遂以无补助而至停办”[32]。创办后的一段时期内公立女学虽未至停办,但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援例以“驻芜米厘”作常年经费,其实业已拨济皖江中学与安徽公学,此时势难再有余款,所以尽管获安徽巡抚冯煦应允,然拨款一事却迟迟未见下文,最后甚至见诸报端,方得以解决。[31]不可否认,官费的投入对于公立学堂的稳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官费的介入必然导致学校自主权尤其是人事和办学自主权的丧失,从而致使学校失去了自身特色,直至最后成为官府辖下千校一面的另类“官立”学校。
四、余论
至此,有关安徽公立女学堂创办时的若干历史问题,大致已基本清晰。然而,结合这些问题和当时的现实背景,以及后来女学的发展状况,还有较为重要的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就学校创立和建设本身而言,安徽公立女学堂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从其幸运来说,它主要是由官绅创办的①按:陈惟彦、黄润九、李经方是典型的旧式官僚,李榘以及后来一直担任校长的阮强为旧式乡绅;而李德膏虽思想趋新,有过出国考察教育的经历,但其主要精力在安徽公学上,且从对安徽公立女学堂一些零散的文字记录来看,他的确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这些人尽管是旧式官绅,但思想尚为开明,个别还有出国考察新学的经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学校较容易争取到官府的政策扶植和经费资助,有利于学校发展的连续性。但这亦是不幸的根源。由于这个传统,民国以后至20 年代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该校领导管理层仍为旧式官绅所把持,校长和国文主任被称为“老圣人”“大贤人”[33],秉持的教育理念依旧未脱传统的牢笼,如教育目的,不过为养成“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主中馈”、“无违夫子”、遵从“三从四德”的“良妻贤母”;训育以灌输传统旧道德为依归,训育主任“天天写几句由列女传抄下的格言,贴在自修室墙上”;教材陈旧腐败,如国文“尽是‘曾子固列女传序’、‘桐城古文学说与白话文学说之比较’一类的材料”,教法完全是注入式的,严禁学生接触新思想,学校教育、学生发展与当时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完全脱节。[34][35]其后,该校学潮不断,一定程度上导源于长久沉闷、落后的教学管理理念与社会形势发展不相适应。当时安徽仅有的另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情况更糟,乃至时人以“地狱”形容皖省女子教育之处境[36]。对于此糟糕状况,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全省教育会及部分知名教育人士应负有主要责任,如1919 年4 月全省师范学校第二次联合会议,虽倡导女子师范亦应注重经济主义的教育方针,但依旧“定家事为主科……以为小学校职业教育实施之准备”[37],仍将女子教育定位为家庭教育之偏见。如此成见,无怪乎以女子教育为代表的安徽新教育发展之步履维艰。
第二,安徽公立女学的创立和发展状况是当时安徽新教育的缩影。安徽新式教育在近代一直处于落后地位,这已是学界的共识;就女学教育而言,这一点亦可作为佐证。从《安徽省国人自办女学堂一览表》可以看出,安徽最早的女学堂——公立端则女学堂出现于1905年初,但是只有学生12人,经费来源于祠堂公款和学费,充其量只能算家族私塾,称不上现代学校,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紧接着产生的两所女学堂亦是如此。只是到了1906 年下半年安徽公立女学堂的成立,才能算作全省的新式女学堂;而此时全国绝大部分省都已有了新式女学堂②按:各省数据来源于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各省第一所女学堂一览表》(第632页)。《各省第一所女学堂一览表》所列20省份,有15个省的首所女学堂创办于1906年以前,2个1906年,2个1907年,1个1908年以前。其成立时间先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风气开化及新式教育发展的程度。。所以,在全国而言,安徽新式女子教育也是比较落后的。
1907年,全国开“女禁”后,安徽女子教育整体发展仍甚为迟缓,经费投入不足是主要原因。在公立女学堂成立后的第三年,即因经费问题,“势将停办”[31]。进入民国,这一形势仍未能好转。据1912 至1915 年4 年教育统计数据(见表2),在所有省份中(不含特别区),安徽教育经费投入几乎垫底,不仅远远落后于江苏、直隶等教育发达省份,甚至落后于广西、贵州、云南等偏远省份,仅高于陕西、甘肃、新疆,排名倒数第四,还不及江苏省(排名第一)的1/7。即使剔除人口基数因素(当时安徽省人口比江苏省少1 千余万,约是其2/3),与江苏省的差距仍比较大。若对比人口相近的邻省江西,经费支出也不到其一半(44.83%)。足见民国初安徽教育经费投入之可怜。

表2 民国初期皖苏赣教育基本状况对照简表(1912—1915)[38]
安徽新式教育的落后,除上表所反映的学校数、学生数和经费投入等指标外,还体现在学校分布不均、教员师资与资产有限、学生学业程度低等诸多方面。这在女学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1908年,《皖政辑要》统计当年女学,全省可考者仅8所[4]575①按,该书统计不全,如竞化女学堂未包括在内。,且均集中在省城周边及皖南地区,皖中北部几乎空白。至20 年代,安徽省60 州县中,设有女子小学的也不过一二十个;就学校程度而言,除第一、二女子师范学校外,全为初等水平,主学制内的中等女学居然为零(省立女子工艺传习与蚕桑女校虽系中等,但不在主学制之内)[39]。学业方面,初期,安庆女师有学生百数十名,仅年长数人国文、习字尚能及格,其他仅有蒙学程度[40];至1920年,办了十余年,二年级的师范生竟然英文字母还不认得[33]。省城女学尚且如此,其他州县女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