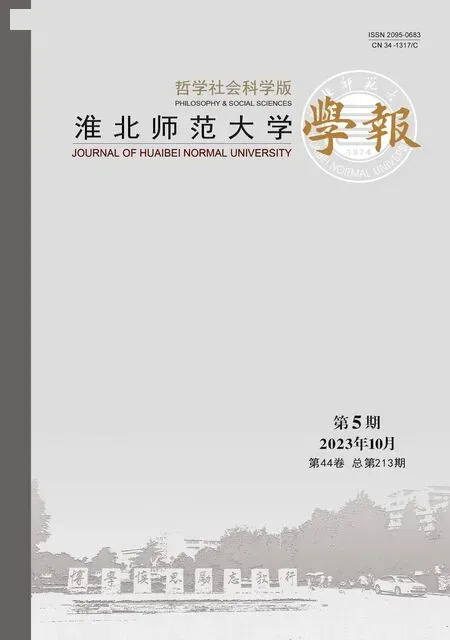经济修辞学研究关涉的主要内容(下)
吴礼权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
三、语言资源配置与修辞效果实现的矛盾关系
在古今修辞实践中,语言资源的配置有三种基本而有效的方案:一是“增量配置”,二是“减量配置”,三是“适量配置”。无论是采用哪一种配置方案,最终的目标预期都是直指修辞效果。如果语言资源配置方案不符合修辞的最终目标预期,那就会产生资源配置与修辞效果之间的矛盾。因此,为了避免语言资源配置与修辞效果实现之间的矛盾,修辞者(修辞主体)就必须切合说写当时的特定情境,围绕所要表达的主题或主旨,选择有效的语言资源配置方案,以恰当的修辞手法建构修辞文本。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我们不仅需要解决个人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问题,还需要推动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为此,我们就必须跟他人沟通,交流信息和思想,协同行动。跟他人沟通,方式方法有很多。但是,从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来看,最直捷、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方法就是以语言为工具。因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不是体态语等其他工具所可比拟的。以语言为工具跟他人进行的交际沟通,对于表达者(说写者)来说,都是要讲究效果的。因为大凡是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开口说话或提笔写作,都会有一种情感冲动,这就是如何把话说好,把文章写好。因此,可以说,任何以语言为工具进行的交际活动,包括口语交际和书面语交际,从广义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修辞行为。事实上,修辞分两类:一是“积极修辞”,二是“消极修辞”。[14]36“积极修辞”重视语言技巧的运用,常常运用特定的修辞格建构修辞文本,追求超乎寻常的表达效果(如“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等等);“消极修辞”着重于在语法与逻辑上下功夫,力求表达符合语法规范、逻辑条理,使所达之意无歧义,所传之情不含糊,也就是“讲清楚,说明白”的境界。
也许有很多人认为,“讲清楚,说明白”并不是难事。其实,并不然。事实上,“讲清楚,说明白”是一种很高的修辞境界,是“消极修辞”的极致。要想实现这一修辞效果,修辞者(修辞主体)在语言资源配置上是要颇费一番心力的,并非可以一蹴而就。不过,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有时候修辞者虽然可以“讲清楚,说明白”,但真的讲清楚了,说明白了,可能又跟达意传情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预期(修辞效果)相矛盾。因此,如何在“讲清楚,说明白”与修辞效果(表达的终极目标预期)之间寻求平衡,就需要修辞者在语言资源配置方面具有高度的智慧。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人民日报》1972年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宴会上的祝酒辞)
上引文字是1972年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宴会上的祝酒辞片断,一共三句话。作为外交辞令,这三句话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政治意涵。从经济修辞学的视角看,这三句话中的每一句,都可谓“增一字则太多,减一字则太少”,堪称语言资源配置的经典方案。第一句与第二句都是“消极修辞”,第三句则是“积极修辞”。从句法上分析,第一句“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是一个并列复句,由两个分句构成,每个分句都是一个主谓结构的判断句,采并列对峙的格局呈现。如果基于语言的经济原则,这两句可以采用语言资源的“减量配置”方案,写成“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或是“中国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也可以不基于语言经济原则,而基于逻辑优先原则,采用语言资源的“增量配置”方案,写成“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或“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即在两个分句的后一分句中都增加一个副词“也”字。但事实上,修辞者周恩来没有采用这两种方案,而是采用了语言资源的“适量配置”方案,让前后二句不仅在句法结构上完全一致,在字数上也完全相同。只是“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前后位置有所不同,一个是前句的主语,一个是后句的主语。之所以如此,是修辞者周恩来作为中国的总理希望通过这两个句子在句法结构与字数上完全相同相等的语言事实,暗示修辞接受者尼克松这样一层政治意涵:“中国与美国是平等的大国,应该相互尊重。中国是礼仪之邦,重视待客之道。今天您飞越太平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既是美国人民的代表,也是我们的客人,因此我先赞美美国人民,后赞美中国人民”。第二句“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也没有运用任何修辞手法,只是直白的理性表达。但是,从语言资源配置上看,也是非常高明的。特别是时间副词“一向”的配置尤其高明,充满了丰富的政治意涵,不露痕迹地暗示了中美两国曾经有过的美好过往,这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精诚合作、密切合作,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那段历史,对美国曾经给予中国的帮助不卑不亢地表达了真诚的感谢。可见,这一句的遣词造句在语言资源的配置上也是恰到好处的,达到了不可增减一字的境界,属于语言资源的“适量配置”。反之,如果在语言资源上采“增量配置”方案,详述中美两国共同抗日的情谊与历史,则不仅冲淡了宴会的主题,也有违当时中美两国的基本政治立场。至于第三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则是运用了“推避”手法建构的修辞文本,是一种“积极修辞”。从经济修辞学的视角看,这一句采用了语言资源的“减量配置”方案,将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那段生死搏斗的历史,以及国共内战期间美国极力帮助国民党的历史,以推避之辞“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而一句带过,让身为客人的修辞接受者尼克松不至于感到尴尬,使宴客的气氛不至于受到影响。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事关两国战略安全与世界安全的首要大事,尼克松访华是全世界头号重大政治事件。尽管“新中国在建立的过程中和建立之后,美国都进行过百般阻挠和打压,这是周恩来和尼克松都心中有数的”,但是“宴会上为了友好气氛的营造是不便说得太明的”[10]166。如果修辞者周恩来在宴会时把话说得太明,即将中美两国过往的历史讲清楚、说明白,那就很难实现祝酒辞修辞效果的终极目标预期,《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也许就签不了,中美外交关系的新局面就打不开。可见,在修辞活动中,有时语言资源的“增量配置”或“适量配置”并不是最佳方案,反而是“减量配置”可以发挥以少胜多的效果。这就是语言资源配置与修辞效果实现的矛盾关系最典型、最鲜明的表现,值得我们深究。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五年,诸侯及将相相与共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史记》中的这段文字,记载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秦王朝在天下各路诸侯及反秦力量的联合夹击下灭亡后,新一轮的群雄角力也就上演了。在这场角力赛中,最终跑在最前面的是项羽与刘邦。由此,决赛便在二人之间展开。由于项羽刚愎自用,力量逐渐削弱,结果在决赛中终于不敌刘邦。刘邦由弱变强,最后一家坐大后,各路诸侯及其手下将相都见风使舵,纷纷投靠刘邦。于是,项羽死后不久,大家都拍马逢迎,劝进刘邦即皇帝位。其实,刘邦心里也明白,他们之所以要劝自己做皇帝,都是有私心的。因为一旦他做了皇帝,大家都可以封王拜爵,出将入相。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叫双赢。刘邦当然想当皇帝,不然他就不必在秦朝灭亡后与项羽殊死相搏那么多年,也不会为了自己活命而连亲生女儿也要推下车去,更不会在其父被项羽绑架要胁时无耻地说:‘我翁即汝翁,若要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可是,当各路诸侯及将相都劝他当皇帝时,他却再三推却。其实,各路诸侯及将相都不傻,知道刘邦这是在装。所以刘邦越是推却,他们就越是劝进。最终,当气氛被推高后,刘邦这才俯允大家的劝进,装得非常谦逊的样子,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诸位如果一定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国家,那么……’甲午年(即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刘邦便在汜水之阳宣布即皇帝位了”[15]360-361。
读了《史记》的这段历史记载,也许很多人都会不免心生疑问,刘邦非常想当皇帝,为什么嘴上就不肯说呢?被属下将相们死活谏劝,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借口与台阶,有了一个水到渠成的表达机会,为什么开口后却只说了半句话呢?其实,这就是刘邦语言资源配置的高明之处,他的半句话实际上是运用了“留白”手法建构的修辞文本,采用的是语言资源的“减量配置”方案,是经济学上所说的以最少的投资博得最大利润的成功案例。从上下文语境看,这句话如果说全了,应该是:“诸君必以为便国家,吾则为之(即:诸位如果一定认为我做皇帝有利于国家,那么我就即皇帝位)”。如果这样说,从遣词造句来看,达意传情非常清楚明白,可谓达到了“讲清楚,说明白”的境界。但是,这样的表达,却不符合政治修辞的原则,不利于树立其正人君子的形象,反而暴露了其小人嘴脸与急于上位的内心世界,显得没有谦让之德与自知之明,让人觉得他不配当皇帝。事实上,刘邦作为修辞者(修辞主体),在表情达意时,没有足量配置语言资源,而是采取语言资源的“减量配置”方案,只说出预设前提:“诸君必以为便国家(即:诸位如果一定认为我做皇帝有利于国家)”,而不说出在这个前提下的结论:“吾则从之(即:那我就即皇帝位)”。这样,“既能显现他谦逊的品德,又能给手下人以更多猜测想象的空间。做领导的要有一种本事,就是让属下猜自己的心思,而且越是猜不透,他的地位就会越高越稳固。如果做领导的被属下看透了一切,就不可能有什么神秘感了,属下就不会对他心存畏惧。而属下对他不心存畏惧,他的位置如何还能做得稳?”[15]362除此,作为修辞者,刘邦减量配置语言资源,只说半句话,还有一个高妙之处,就是“它作为推论前提是以国家利益为借口的,这样就更能遮掩其想当皇帝的真实内心世界。给人的感觉是,他做皇帝是为国为民,而非为他自己。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岂能不更有迷惑性?”[15]362由此可见,刘邦最懂经济修辞学,是语言资源配置的能手,能当皇帝有其必然性。不过,这里我们还要强调指出一个问题,就是刘邦说半句话是一种修辞行为,太史公司马迁记录刘邦说这句话的史笔也是一种修辞行为,运用的是修辞上的“飞白”手法。他明知刘邦“便便国家”的说法不通,却要原样照录,其意是要通过刘邦说话口吃的形象凸显其心口不一(明明内心急于做皇帝,但表面却装着不愿意)的伪君子形象。如果说刘邦说半句话的修辞行为(“留白”)是语言资源的“减量配置”,那么司马迁原话直录的修辞行为(“飞白”)则是语言资源的“增量配置”(多写了一个句法结构上不需要的“便”字)。但是,不论是司马迁的“增量配置”,还是刘邦的“减量配置”,事实上都非常好地实现了达意传情的终极目标预期,即最好的修辞效果。反之,如果刘邦不采用语言资源的“减量配置”方案,不说半句话,而是把话说全了,要想实现其终极修辞目标预期(即既顺利地当上了皇帝,又凸现了为人谦让、有自知之明的君子形象)则不可能;司马迁在记录刘邦的话时不采用语言资源的“增量配置”方案,即不多写一个“便”字,就很难写出刘邦内心的秘密,将其心口不一的伪君子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可见,语言资源配置与修辞效果实现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要使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修辞者(修辞主体)必须适应接受者(修辞受体)与说写当时的特定情境,然后确定一个恰当的语言资源配置方案。
解决语言资源配置与修辞效果实现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语言资源配置与预期修辞效果的和谐统一,方法有很多。上面我们所举的例子,都是采用“适量配置”或“减量配置”方案来实现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案也很有效,这就是“增量配置”。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即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宋·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
上引这首词,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写与丈夫赵明诚离别相思之苦的作品。其中上片末句:“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其要表达的真实语义,如果用宋代词人柳永优雅的说法,就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七个字;如果用老百姓的大白话来说,就是“老公,我想死你了”,也是七个字。然而,女词人李清照却用了十一个字,明显不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李清照的语言资源投入明显过多,属于语言资源的“增量配置”。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李清照的修辞是失败的。事实上,李清照运用“折绕”修辞手法,将简单的意思说得迂回曲折,虽然显得有些辞费,但从最终接受效果来看,明显是令人满意的。因为这种曲里拐弯的婉转表达,符合中国传统诗歌崇尚“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美学追求,更符合词人作为中国封建时代一个大家闺秀羞于言爱的心理特征。从诗歌接受美学的视角看,这样的表达更能激发出读者“二度创作”的热情,有利于诱导他们思索体味。这样,就使作品的审美价值得以大大提升。诗词是文学作品,要给人以美的享受,是要讲接受效果的,而不仅仅是为了清楚明白地表情达意。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成败论英雄”,李清照的修辞是成功的。因为李清照的语言资源配置虽有些靡费,但实现了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预期——让人获得一种味之不尽的婉约之美,这是接受效果的最大化。[16]385也就是说,李清照的“折绕”传情,虽然付出了相当大的语言资源成本,但是它实现了修辞的终极目标预期,这就是既婉约含蓄地表达了对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之情,秀了一把个性化的“小爱”(夫妻间的隐秘之爱),又巧妙地借自己著名女词人的特殊身份,其作品广泛传播而必将成为社会公共产品的潜在条件,秀了一场普世化的“大爱”(男女间的本性之爱),放大了作品的审美价值。可见,语言资源配置与修辞效果实现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经济活动中成本与利润的关系。有时候,它并不追求以最小的成本博取最大的利润,而是以修辞的终极目标预期为指归,采用语言资源的“增量配置”,不惜成本也要实现终极目标预期。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这是成本投入与利润获取之间的矛盾;从经济修辞学的视角看,这是语言资源配置与修辞效果实现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关键看修辞者的修辞价值观与语言资源配置的智慧。
以上我们所讲,都是古今中国人的修辞实践,下面我们来举一例外国人的修辞实践,看看他们是如何处理语言资源配置与修辞效果实现之间的矛盾的:
来当兵吧!当兵其实并不可怕。应征入伍后你无非有两种可能:有战争或者没有战争,没有战争有啥可怕的?有战争后又有两种可能:上前线或者不上前线,不上前线有啥可怕的?上前线后又有两种可能:受伤或者不受伤,不受伤又有啥可怕的?受伤后又有两种可能:轻伤和重伤,轻伤有啥可怕的?重伤后又有两种可能:可以治好和治不好,可治好有啥可怕的?治不好更不可怕,因为你已经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一则征兵广告[5]517)
上引这则广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发布的一则面向美国适龄青年的征兵广告。虽然在文体上属于广告的范畴,但跟一般的商业广告与公益广告却有本质的区别,这就是它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因为征兵广告的发布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它的发布者是一国的军方。因此,征兵广告的撰稿人跟商业广告或公益广告的撰稿人就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不是寻常的“自然人”,而是属于典型的“政治人”。他所拟写的征兵广告在语言文字上的所有经营努力,在性质上也跟商业广告或公益广告不同,不能视为“日常修辞”,而是“政治修辞”的性质。[16]389-390
作为政治修辞文本,这则征兵广告完全可以立足于国家利益,直截了当地表明美国政府的立场与态度,简明扼要地宣示其主旨,以这样一个口号形式来呈现:“来当兵吧,保家卫国,消灭法西斯,是每一个美国青年应尽的义务”。如果真的这样写,从表达的角度看,当然没有问题。因为这样的表达,属于“消极修辞”,不仅表意清晰,而且文字简洁明了,达到了“讲清楚,说明白”的境界,而且语言资源的配置比较节省,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但是,从接受的角度看,效果恐怕就要大打问号了。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国民的国家意识并不是那么强烈。至于年轻人,恐怕也不会有太多人具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神圣责任感与“面对危难,舍我其谁”的崇高政治觉悟。因此,征兵广告以讲大道理的方式说服美国年轻人踊跃当兵,恐怕是行不通的。事实上,这则广告的撰稿人是头脑清醒的,他没有这样跟广大美国适龄青年一本正经地讲大道理,而是通过语言资源的“增量配置”,以“层递”修辞手法建构了五个“二难推理”游戏文本,化严肃为轻松,有效地消解了美国人普遍的怕死心理,打消了美国广大适龄青年害怕上战场的恐惧感,由此达到了征兵广告所要达到的最好效果。[16]390
仔细分析一下,这则征兵广告所玩的逻辑推理游戏并不复杂,只是一种“二难推理”(dilemma)的巧妙运用。作为政治人同时也是作为撰稿人,“为了论证‘当兵并不可怕’的观点,吁请人们报名当兵,广告撰写者连续运用了五个‘二难推理’来作为论据。第一个‘二难推理’是:‘应征入伍后你无非有两种可能:有战争或者没有战争,没有战争有啥可怕的?’属于‘A或B,若A,则C;若B,则D。所以,C或D’格式。如果依格式还原 为完形‘二难推理’结构,就是:‘应征入伍后有战争(A)或者没战争(B),如果有战争(A),则可怕(C);如果没战争(B),则不可怕(D)’。但是,为了打消应征者怕死而不愿当兵的心理,撰文者有意玩了一个花招,将两个‘选言支’中可能导致负面心理暗示的一个‘选言支’(即‘如果有战争,则可怕’)省略了,只将具有正面意义的一个‘选言支’写出,且以反问句的形式呈现。这样,既奸里撒混,让应征者忽略了应征当兵后存在的危险,又加强了正面意义的一个‘选言支’(即‘如果没战争,则不可怕’)的说服力。第二个‘二难推理’是:‘有战争后又有两种可能:上前线或者不上前线,不上前线有啥可怕的?’也是属于‘A或者B,如果A则C;如果B则D。所以,C或者D’格式。依格式还原为完形‘二难推理’结构,就是:‘战争有上前线的(A)或者不上前线的(B),如果上前线(A),则可怕(C);如果不上前线(B),则不可怕(D)’,同样是以省略负面意义的‘选言支’(即‘如果上前线,则可怕’),强调正面意义的‘选言支’(即‘如果不上前线,则不可怕’)的方式,给应征者以心理安慰,鼓励他们勇敢应征当兵。第三个‘二难推理’是:‘上前线后又有两种可能:受伤或者不受伤,不受伤又有啥可怕的?’还原为完形‘二难推理’结构,就是:‘上前线有受伤的(A)或者不受伤的(B),如果受伤(A),则可怕(C);如果不受伤(B),则不可怕(D)’。为了打消应征者怕受伤的心理,推理中将具有负面意义的‘选言支’(即‘如果受伤,则可怕’)省略了,只写出具有正面意义的‘选言支’(即‘不受伤,则不可怕’)。第四个‘二难推理’是:‘受伤后又有两种可能:轻伤和重伤,轻伤有啥可怕的?’还原为完形‘二难推理’结构,就是:‘有受重伤的(A)或者受轻伤的(B),如果受重伤(A),则可怕(C);如果受轻伤(B),则不可怕(D)’。但撰文者在实际写作中省略了其中的一个‘选言支’:‘如果受重伤(A),则可怕(C)’。由于这个具有负面意义的‘选言支’被有意隐去,应征者只能看到正面意义的‘选言支’(即‘受轻伤,则不可怕’),心理的恐惧就减轻了,应征当兵的勇气自然就会提升。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二难推理’是:‘重伤后又有两种可能:可以治好和治不好,可治好有啥可怕的?治不好更不可怕,因为你已经死了’。这个推理若还原为完形‘二难推理’结构,便是:‘受重伤有可以治好的(A)或者治不好的(B),如果受重伤可以治好(A),则不可怕(C);如果治不好(B),则更不可怕(D),因为人已经死了’。这个‘二难推理’与前四个都不一样,两个‘选言支’都完备。但是,对于具有负面意义的‘选言支’(即‘如果治不好,则就死了’)进行‘技术处理’,说成是‘如果治不好(B),则更不可怕(D),因为人已经死了’,以出人意料的幽默,让应征者的恐惧感化为乌有。这样,五个作为论证观点的‘二难推理’便都具有正面意义了,从逻辑上看就严密地论证了‘当兵并不可怕’的观点”[17]168-169。除了创造性地运用“层递”修辞手法,采用语言资源的“增量配置”方案,建构了一个由五个“二难推理”构成的修辞文本外,这个征兵广告还在“层递”修辞文本中内嵌了五个“设问”修辞文本,分别是:“没有战争有啥可怕的?”“不上前线有啥可怕的?”“不受伤又有啥可怕的?”“轻伤有啥可怕的?”“可治好有啥可怕的?”这五个“设问”修辞文本,虽然在语言资源配置上没有任何量的增加,仅以反问的语气呈现,但是,由于它以“激问”的形态呈现,答案都在其设问的反面,不仅可以启发接受者思考,同时还有加强语气的效果,可以大大提升接受印象,对提升“当兵并不可怕”观点的说服力也有重要作用。可见,这则征兵广告语的篇幅虽然有些长,对语言资源的配置显得有点靡费,但最终的接受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若以成败论英雄,这则征兵广告无疑是最成功的。这里,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语言资源配置与修辞效果实现之间的矛盾关系。不过,我们也同时看到了语言资源的“增量配置”方案在解决这种矛盾中所发挥的作用。
四、语言资源配置的可能性与修辞可能性边界
在经济活动中,不同的稀缺资源有不同的配置可能性。而不同的配置可能性,就会有不同的“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PPF,表示“在技术知识和可投入品数量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经济体所能有效率地得到的最大产量”[6]13)。同样,在语言活动中,不同的语言资源也有不同的配置可能性。而不同的语言资源配置可能性,则会有一个修辞效果最优化的极限,类似于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我们姑且将之称为“修辞可能性边界”(rhetoric-possibility frontier,RPF)。为了说明这个概念,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个例子: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诗经·豳风·七月》)
上引文字是《诗经·豳风·七月》的第五章。“全诗是写秦地农民农事生活的,描写他们一年四季不是耕种,就是打猎,不是盖房,就是制衣、酿酒,不是采桑叶,就是挖野菜,总是忙个不停,辛劳备至。上引第五章是写仲夏五月开始的节候变化,包括蝗虫、纺织娘、蟋蟀的活动情况,以及屋主人为了迎接老婆孩子入住新房,欢度新春,而忙着堵地洞、熏老鼠、塞窗户、填门缝的劳动场景”[16]376。其中,第一句、第二句是六个字,是两个句法结构完整的主谓句,“五月”和“六月”分别是两句的状语,为了与第三句至第六句的句式协调一致,都置于主语之前了。第一句的主语是“斯螽”,谓语是“动股”,为动宾结构;第二句的主语是“莎鸡”,谓语是“振羽”,亦谓动宾结构。第三句至第六句,分别是:“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从上下文语境看,每句的主语都是“蟋蟀”,是依时间节令顺序写蟋蟀活动的。但是,这四句的前三句的主语“蟋蟀”都没有出现,直到第六句,描写蟋蟀活动的全部内容要结束时,“蟋蟀”作为主语才“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写呢?第三句至第五句为什么不加上主语“蟋蟀”,使之成为六言句,像第一句、第二句那样呢?如果这样,那么第六句“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主语“蟋蟀”就可以蒙上省略,可以写成“十月入我床下”,成为一个六言句,可以保持跟前五句相一致的字数,形式更趋整齐划一,更符合诗句形式上的要求了。不过,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诗经》的体制是以四言为主,如果出现六个六言句的连续铺排,那么就明显破坏了《诗经》整体上以四言为主的体制,与周秦时代诗人们所追求的审美价值观不相符了。这样,诗人在诗句安排上的任何修辞努力都是白费了,因为它跟诗人修辞的终极目标预期背道而驰。相反,诗人让第一句、第二句以六言形式呈现,第六句以八言形式呈现,虽然也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体制要求,但却最大限度地使四言句的数量达到了八句的规模,使非四言句的数量压缩至只有三句,从而实现了诗歌在整体上以四言为主的终极目标预期。可见,“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三句,都是我们所说的“修辞可能性边界”。因为从语言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它们都达到了省无可省的句法极限边界。“五月”“六月”“十月”都是表时间的状语,跟其后的四句是一个时间连续序列,不可能省略;“斯螽”与“莎鸡”是两种动物,不能合而为一。所以,既不能承前省略一个,也不能蒙后省略一个。“蟋蟀入我床下”六个字,则更是省无可省。如果没有“蟋蟀”在此句出现,那么前三句“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的主语都无着落,意思就不可理解了;如果“入我床下”不在此句出现,或是另成一句,那么在语义上都令人费解。因此,我们认为,“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作为《诗经·豳风·七月》中一个“修辞可能性边界”的范例,表面上看只是我们今天语法学上经常论及的寻常现象:“探下省略”,实则是两千多年前周秦诗人的修辞创造。因为在这首诗中,“前三句主语‘蟋蟀’省略,不仅可以使前三句保持四言成句的整齐格局,而且还有设置悬念、引人入胜的审美情趣。很明显,这样的语言资源配置,既体现了‘语言经济’的原则,又提升了诗歌的审美价值,可谓实现了接受效果最大化的修辞目标”[16]376。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胜利的浪头把一些人推上了领导者位置,挂了“帅”,如果能诚恳虚心地珍惜这种机缘,向可以学习的人学习,也许早就出“师”了。可惜有些人花了过多的精力去教训人、排斥人,而不肯自认“略输文采”,因此寒来暑往,还是两袖清风,一无所获,仍然是“只识弯弓射大雕”。正如棋盘上的“帅”一样,在小小的“田”字小天地里,趑趄不前,起一点象征性的“领导”作用,还提心吊胆防别人的“将军”。
“师”和“帅”,仅一笔之差,但要使自己从空头的“帅”变为充实的“师”,就得下一注决心和费一番手脚了。(泽群《“帅”和“师”》)
上引文字是一篇杂文中的片断,该文刊载于1957年6月6日的北京《大公报》[13]508,“旨在批评当时某些领导干部当上领导后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加强学习”[10]362。但是,对于文章所要表达的这层意思,作者并没有选择语言资源的“适量配置”方案,以“讲清楚,说明白”为终极修辞目标预期,而是为了强化语意印象和警醒世人,选择了语言资源的“增量配置”方案,通过“析字”修辞法,“别出心裁地选取‘帅’‘师’两个形体近似的汉字,并借机生发开来,不仅有力地阐明了领导干部应该加强学习,做充实的‘师’而不要做无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空头之‘帅’的深刻道理,而且由于形式巧妙,特别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给接受者以深刻的印象,文章的震撼力也就特别强,所以将近三十年后的1985年4月23日的《杂文报》还特别地转载了此文”[10]362。可见,同一个意思、同一个道理虽然有两种不同的语言资源配置可能性,但由此产生的“修辞可能性边界”也有所不同。对于该文所要表达的主旨,如果“适量配置”语言资源,遣词造句简洁明了,那么其“修辞可能性边界”(即修辞效果最优化表现)就是“讲清楚,说明白”;而该文作者运用“析字”修辞法,通过“增量配置”语言资源,其所抵达的“修辞可能性边界”就完全不同了,既将所要表达的观点“讲清楚,说明白”了,又别具一种促人思考、令人回味的审美情趣。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可谓达到了效益最大化。
其实,在语言活动中,特别是在汉语表达中,不仅可以通过运用诸如“省略”“析字”之类的修辞法使语言资源的配置有不同的可能性,还可以通过选词择句,使语言资源的配置有不同的可能性,进而实现言语交际的终极目标预期,直抵“修辞可能性边界”(即修辞效果最优化表现)。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地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鲁迅《呐喊·头发的故事》)
在上引这段文字中,作者鲁迅没有运用任何修辞手法建构修辞文本,都是平实的大白话叙事。但是,在遣词造句时却在两个动词的配置上下了一番功夫,可谓是“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14]9。这两个动词,一是“踱”,二是“撅”。在现代汉语词汇库中,跟“踱”词义相近的词有“走”“跑”“行”等。也就是说,在语言资源配置的可能性方面,作者鲁迅有选用“踱”“走”“跑”“行”等词的多种可能性,但是最后他选择了“踱”,而不是“走”“跑”“行”等其他词义相近的词,这完全是为了应合此文特定的情境,凸显当年北京市民对于双十节挂旗的消极态度。可以说,“踱”在此情此景中“一字写尽了当时北平市民对于双十节挂旗的非自发活动的虚应故事、漫不经心、消极敷衍的逼真心态和生动情状。而与‘踱’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走’‘跑’‘行’等动词皆不能企及动词‘踱’在此情境中的独特修辞效果”[10]345。“撅”字的使用也一样,是作者在“撅”“挂”“插”等词义相近的几个动词之间进行了认真选择的结果。“撅”字之用,“也是通过一字而写尽了北平市民挂旗时那种心中老大不乐意、行动没精打采的生动情状,表达婉约且极具讽意。若是换上与‘撅’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动词如‘挂’‘插’等,表达上就不可能达到上述效果”[10]345。可见,鲁迅上引这段文字在表达上能够直抵“修辞可能性边界”(即修辞效果最优化表现),事实上是跟其认真评估了“踱”“撅”及其相关动词的使用可能性密切相关。
一般说来,在修辞活动中,词义相同或相近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被选择的可能性往往较大。相对来说,虚词的使用则少有这种被选择的可能性,这是因为虚词跟其他实词的搭配往往具有强制性。比方说什么量词跟什么名词搭配,就是固定的,没有可被选择的空间。如量词“滴”只能跟名词“水”搭配,量词“株”只能跟名词“树”搭配,量词“块”只能跟名词“石头”搭配,等等。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修辞的特定目标预期,这种搭配关系也可以被打破。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最近又读到几篇文章,是谈“五四”的,也有谈相关问题的,有长有短,有深有浅,都是得些启发……我读到的几个文章是谈“民间立场”的,虽然冠以“五四”的名望,我以为是有悖于“五四”风貌的。譬如,有个身体结实的人走进一个村子,四处打听,问“你们这里谁最厉害?”有人告诉他是某某,于是,这人便提着拳头上门把某某打了一顿,之后又转悠着去下一个村子了,我觉得,这种行为不是“民间立场”。(穆涛《时代烙印还是时尚趣味》)
在上引文字中,作者“谈到关于对五四持‘民间立场’的文章时,选择了量词‘个’来修饰中心语‘文章’,而谈到关于对五四持主流传统立场的那些‘得些启发’的文章时,则选择了量词‘篇’。同样是修饰‘文章’,一个选择量词‘个’,一个选择量词‘篇’,说明作者没有对量词使用不当的嫌疑,而是有意所为,即是说,选择量词‘个’来修饰‘文章’是作者的一种修辞行为”[10]350。也就是说,作者这里选择量词“个”来修饰名词“文章”,是要通过对寻常量词“个”的选择性配置,以此实现该文特定情境下的修辞目标预期,即通过“量词‘个’的使用,婉曲地传达出作者对于少数所谓对五四持‘民间立场’的人的文章的否定态度”[10]350。因为“对于文章,中国人向来都看得很神圣,古人有‘文章乃经国之伟业’的说法,唐代大诗人杜甫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名句,因此说到文章人们总是很严肃,总会中规中矩地选择固定的量词‘篇’来修饰”[10]350。可见,语言资源的配置可能性与“修辞可能性边界”之间是有特殊关系的。“个”与“篇”都是汉语中的普通量词,但是作为一种语言资源,一旦配置到特定的语境中,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修辞效果,所抵达的“修辞可能性边界”(即修辞效果最优化表现)也有差异。我们之所以赞赏上述引文的作者对量词“个”的配置,是因为其“别出心裁地选择表示物件的量词‘个’来修饰‘文章’,在表达上既新颖奇特,又别具深沉婉约的韵致,表达自己否定态度和厌恶情感只通过一个量词的选择就实现了,真可谓是‘一字见褒贬’”[10]350。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堪称是资源盘活的神来之笔。
前文我们说过,语言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包括语音资源(如汉语语音中的声、韵、调等)、词汇资源(如汉语词汇中的各种实词、虚词以及词的等价物——成语、谚语、歇后语等等)、语法资源(如汉语中的各种语法规则,各种句型、句式等等)、修辞格(即人们在语言实践中创造的各种有表现力的表达式与表达方法)等。比方说,我们根据汉语语音的特点,在语言表达中,特别是诗词创作中,利用相同韵母与不同声调的配置,就可以营造出一种韵律上的“同声相应”(押韵)与“异音相从”(平仄相对)的听觉形象美感。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就是对汉语语音资源的盘活。又比方说,我们掌握了一定的汉语成语、谚语、歇后语等熟语,根据题旨情境的需要,在说写表达中适当予以运用,就可以极大地提升我们说写表达的生动性、形象性、优雅性。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就是对汉语词汇中熟语资源的盘活。又比方说,我们掌握了相关的汉语修辞格,有意识地在语言表达中加以灵活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我们说写表达的生动性、形象性、准确性、圆融性,还能增加我们说写表达的审美情趣,提升修辞文本的审美价值。
有关汉语语音资源的盘活,也就是极尽汉语语音资源配置的各种可能性,直抵汉语语音“修辞可能性边界”(即声律效果的最优化表现,如“同声相应”“异音相从”等),中国古代的诗人与词人都有过大量实践,成就非常突出,这是众所周知的,无庸我们在此赘言。有关汉语词汇资源的盘活,也就是极尽汉语词汇资源配置的各种可能性,直抵汉语词汇“修辞可能性边界”(即表情达意效果的最优化表现,如“褒贬系于一字”等),在中国古人的炼字实践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中国现代很多作家在此方面的表现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如上面我们所举到的有关动词、量词的创造运用,就是最好的例证。有关汉语修辞格资源的盘活,也就是极尽汉语修辞格资源配置的各种可能性,直抵汉语修辞格运用的“修辞可能性边界”(即传情达意效果的最优化表现,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等境界),在中国古今作家的修辞实践中更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上文我们举到的“省略”“析字”等修辞格运用之例,就是成功的案例。有关汉语语法资源的盘活,也就是极尽汉语语法资源配置的各种可能性,直抵汉语语法“修辞可能性边界”(即基于语法规约的表达效果最优化表现),也有很多途径。比方说,汉语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句式,如肯定句、否定句,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把”字句、“被”字句,等等。这些句式存在于汉语语法系统之中,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就是汉语的一种资源。为此,我们完全可以有意识地利用这些不同句式,充分挖掘其在不同语言情境中的各种配置可能性,从而实现达意传情效果的最优化表现,直抵句式资源配置的“修辞可能性边界”(即句式在语法功能之外的外溢表意效果)。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狱,到清朝末年才被从新提起。最起劲的是“南社”里的几个人,为被害者辑印遗集;还有些留学生,也争从日本搬回文证来。待到孟森的《心史丛刊》出,我们这才明白了较详细的状况,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
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而最有趣的,则莫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鲁迅《隔膜》)
上引两段文字,有两个否定句的运用,一是前一段的末句:“其实是不尽然的”(“是”在这里是副词,表示“确实”之义,不是表示判断的系词。“的”是助词,与副词“是”配合,加强否定表达“不尽然”的否定语气),一是后一段的开头一句:“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堪称是极尽汉语否定句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实现了修辞效果的最优化,抵达了否定表达的“修辞可能性边界”。因为这两段文字,从表意的主旨来看,是各有侧重的。前一段文字的主旨,是要对以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清代的文字狱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的观点予以否定,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作者在这段的末一句作结论时,没有选用肯定句,说‘其实是错误的’,而是用了一个否定句:‘其实是不尽然的’。两相比较,很明显,用否定句比用肯定句效果好。因为学术问题很复杂,任何人没有十分的把握、没有掌握充足的材料是不可轻易地下决断的结论的。所以,对于文中提到的清代文字狱的起因,用肯定句表达:‘其实是错误的’,就显得语气过重,口气生硬了点,不易为接受者接受。而采用否定句‘其实是不尽然的’来表达,就显得语气轻,口气缓,表达上显得婉转,因而也就易于为人所接受”[10]369。后一段文字的主旨,是要肯定故宫博物院印出《清代文字狱档》的学术功德,但是作者却先用了一个否定句:“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然后再接一个肯定句:“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从上下文语境看,作者这样配置肯定句与否定句是有其深刻含义的。因为第一句中“故宫博物院的故事”是指1932年至1933年间故宫博物院文物被盗卖一事。“这件事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态,完全可以用肯定句这样措辞:‘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很令人气愤(或很难令人敬服)。’但是,如果选择了这样一个肯定的措辞,那么第二句‘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就显得突兀,文势上转得过于生硬”。而采用否定句与肯定句共现的形式,前句以否定句表达,“就显得语气较轻,口气较缓,措辞婉转”[10]369,后句以肯定句表达,语意转接才显得自然而不生硬。由此可见,鲁迅极尽了汉语肯定句与否定句资源配置的可能性,抵达了汉语句式“修辞可能性边界”(即句式表意功能的最优化表现)。
五、结语
以上论述的四个方面,只是经济修辞学研究所关涉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经济修辞学的研究还会涉及到语言资源配置的短期效益与潜在收益问题。如我们日常语言生活中对称谓语的选择使用,从经济学视点来看,属于语言资源的“潜在投资”;写作中对文章结构布局的安排(诸如倒叙、插叙、补叙、伏笔、呼应等),属于语言资源的“分配投资”;说写表达中开篇与结尾模式的选择,属于语言资源的“先期投资”与“追加投资”;叙事过程中的起承转合(衔接连贯)等,属于语言资源的“调剂投资”。这些说写表达中的诸多现象,从本质上说都是修辞行为的表现,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都跟语言资源配置所要追求的效益(最佳修辞效果)有关,可以基于“投资-收益”的经济学原理予以阐释。可见,这些方面的问题也是可以纳入经济修辞学研究的视野,可以算是经济修辞学研究所要关涉的内容。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