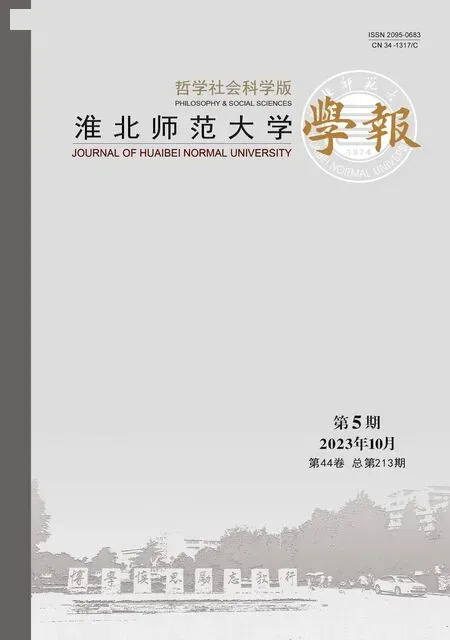儒道身体观的生态智慧
魏 微
(安徽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2)
西方生态哲学研究善用身体视角揭示生态问题。如蕾切尔·卡逊就曾在《寂静的春天》中运用农药毒素由饮食、水土侵入人体的过程来诠释人类身体与生态环境的强关联性。[1]生态关怀是中国哲学的固有维度,然而,国内学者却鲜有从身体观出发探索中国哲学的生态智慧。实际上,“重身”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以身体观为切入点展开研究,也更易凸显生态问题的普遍性和生态关怀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尝试从生态视域下的儒道身体观出发,读取儒道身体观在生态问题上和而不同的智慧,以求为当今正确认识、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性应对生态问题带来启发。
一、身以爱物:生态视域下的儒家身体观
儒家重视身体的社会属性与道德色彩,在儒家思想中,与自然和谐共处是人身体力行修养自身的内在要求,个体总在使言行举止合乎社会期待与道德要求的过程中实现对自然的关爱。生态视域下的儒家身体观可以用“身以爱物”来概括。
身体在儒家语境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儒家语境里,身体的基础涵义是肉身、躯体,是有着活的机能的人生存于世的物质性有机体。《荀子·荣辱》:“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2]55“丧终身之躯”即人的活性的灭失,这里的“躯”就是指物质性的身躯、身体。由于身体的存续与运转标识着个体生命此世的存在,儒家也会用身体来指代人的生命。如《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233《孟子·万章上》曰:“大孝终身慕父母。”[4]191“终身”是终其一生、终其生命的意思。儒家亦用身体指涉个体自身的行动。《孟子·尽心上》:“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4]291“身”与“性”“假”并举,指不是性中本有或假借手段,而是亲身躬行。除此之外,身体还是一个人彰显身份的载体。《论语·微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3]274“不辱其身”即不辱没他的身份。
不难看出,儒家在言及人的身体时,往往带有鲜明的社会性指向。在身体指代生命的情况下,孔子将“恕”作为用以充实个体此世生命的具体内容,“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与“人”的对举反映了“恕”的动作发生在人我之间,个体“终身行之”的“恕”实质上是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所要达成的期望,是社会对个体提出的将心比心、由己及人的要求。“终身慕父母”也是在“己”与“人”之间,更精确地说,是在“己”与“亲”之间,所以“大孝”同样是在社会关系中体现自身对社会期望的符合。在身体指向身体力行的实践时,汤武的“身之也”带有了亲身躬行本就是美德的内在含义,而这种认可与赞誉,亦来源于社会的评价。同理,在意指身份时,“不辱其身”也即使自身能体现的所处社会地位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价值评价不至于辱没、丧失。可见,儒家语境中人的身体不是简单的物质性有机体,而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属性,甚至是道德属性。
那么,儒家所主张的身体保全与维护,就不会仅仅停留在保存个体活的有机体的物质性层面,而是更多地关注其延伸出的社会性与道德性。如《论语·泰伯》记载,曾子得了重病,将弟子召集起来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3]112曾子向弟子展示自己的手足肢体,表示自己一生小心警惕,不曾招来祸患,也即通过身体的完整健全来表示自己成功遵循了在社会生活中生存的法则,以此告诫弟子要谨慎修身,将自己塑造成符合社会要求的人。又如《孟子·告子上》:“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4]248在这里,孟子讲到人对自己“尺寸之肤”的爱,实际是在用人对自己身体发肤理所应当的呵护来说明人也应用同样不假思索的态度来保护自身的善性。
身体完整康健的状态所表征的个体对社会秩序的遵守和道德品质的健全,也要通过身体力行的履践来不断贯彻与完善,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视角下,关爱自然作为必要的内容被包含在内。《大学》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5]儒家的这一修身路径实际已容纳了关爱自然的行动。如杜维明所说,儒家在这一路径中论及的“家”“不仅意味着家庭,而且意味着自然界和更广大的宇宙”[6]。即“家”并不局限于由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社群,而是将自然万物也视为“家庭成员”,将人与自然乃至宇宙构筑的整体视为家园,个体若要达成社会对自身的要求,合乎家、国、天下对自身的期望,就必须对自然也承担责任,建立起人与自然的良好关系。这就要求人将仁、善的行动也有序地施加于自然,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4]298。如《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4]5,《荀子·王制》:“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2]165,孟荀对待自然都秉持了惜物、节用的态度,认为人应给自然留有充分的生长机会,从事农业生产也不能剥夺自然繁衍生息的权利,而这也正是通过善待自然的身体力行的实践彰显仁爱的道德品质。
总之,生态视域下,儒家主张通过与自然友好相处的身体行动来实现并彰显富有伦理意义与道德意味的生命价值,建立的是“身以爱物”的身体观。它延伸了身体的社会属性,将对自然的关怀包孕在了社会对个体的塑造和个体完善道德自我的过程中。科尔曼指出,一个社群的联合靠的不是利益、体貌或种族,而是“互相扶持感、共同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一致的价值观,以及由来已久的家园归属感”[7]。儒家“身以爱物”的身体观有助于通过人在道德方面的自我完善与满足合群需求的身体行动,使善待自然、仁爱万物成为普遍流行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共识,凝聚起共同体的力量,发挥人类群体对生态和谐的能动作用。
二、守身自然:生态视域下的道家身体观
相较于儒家重视身体的社会属性,道家更关注身体的自然属性及其体“道”意味。在道家思想中,身体与自然本应交融为一,人对身体自然状态的持守与尊重、顺应自然本性是内在一致的,都是合乎“道”的表现。生态视域下,道家的身体观可概括为“守身自然”。
在道家语境下,身体同样有着丰富内涵。与儒家相似,道家语境中身体的基础涵义是肉身、身形。《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8]44,《庄子·在宥》:“堕尔形体”[8]354,《庄子·大宗师》:“外其形骸”[8]244,“形”“形体”“形骸”都指向了人的物质性的肉体、身躯、身形。值得注意的是,“形”在道家文本,特别是《庄子》文本中频频出现,它更直接地指向了物理意义上的身体轮廓与形状。在此基础上,道家语境中的身体也常常指向人的生命。《老子·四十四章》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9]234“身”与“名”“货”对举,名声与财富都是身外之物,是不为生命所属的东西,“身”则是人直接经验生命的活的身体,是对举之中最不能舍弃之物。在指向生命存在时,身体也可以表征为生命存在的姿态与取向。《黄帝四经》载:“是故君子卑身以从道,知以辩之,强以行之,责道以并世,柔身以待时。”[10]“卑身以从道”即以谦卑的身姿跟从“道”的指引,“柔身以待时”即以柔弱的身姿等待恰当的时机,身体所标识的是人以怎样的姿态安顿自身与对待外界。
可以看出,与儒家显扬身体的社会属性不同,道家更关注身体的自然属性。《庄子·齐物论》中颜成子游感叹南郭子綦形如槁木,就是通过观察他“隐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丧其耦”[8]44的形貌体态,视觉经验到了他无欲无神,只剩下物质性的躯壳。在这一呈现下,身体被还原为仅拥有生理特征的机体。“堕尔形体”“外其形骸”也表达了相似的内涵。“堕”与“外”乍看之下与“名”“货”对举中对“身”的爱重相左,实际并非如此,堕形体、外形骸并不与爱重生命矛盾,它是用身体语言来体现“吾丧我”“忘仁义”,即摈除了身体的伦理意义,剥离了身体“在社会关系之中”的意味,还原为其自然存在。而这一对身体自然属性的还原与显像,被道家赋予了体“道”的意味。“道法自然”是道家一贯遵循的原则,体认“道”、践行“道”,就需“卑身以从道”,就需如“道”一般法乎自然。
于是,道家提出的基于身体的生命养护,也就更注重使身体保持自然,复归于“道”。理查德·舒斯特曼指出,“道家也强调‘修身’(somatic cultivation),而且它以‘守身’(protecting the body)来解释‘修身’”[11]。道家的“修身”不是如儒家一般,通过身体力行实践种种能在伦理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道德品质,而是“守身”,即守住身体最自然无杂的状态。《老子·十章》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9]93道家欣赏婴儿的身体,将充满浑然之气又柔弱的婴儿之身视为身体修习的理想之境,也正是因为婴儿的身体最为纯粹,最未受任何外力磋磨损害,是最合乎自然的身体,也就最能体现人对“道”的复归。
自然之身的一大特点即与周身的自然世界没有绝对的边界,人体“道”而“守身”的同时,也必然要用同一原则,即“道法自然”的原则,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庄子·齐物论》:“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8]91置身焚烧的大泽而不感到炽热,河汉冰凝也不觉得寒冷,这不是因为至人有非凡的特异功能,而是因为至人明白自身的存在和自然的存在都有着“道”这一共同的源头,自己的身体与周身自然并无隔阂。在此,庄子并不着意于塑造一个超凡神秘的形象,而是要表达体“道”之人的行动必将自然与人视为整体,正如至人的身体与大泽河汉是一个同感共振的整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8]77身体与环境交融为一、相互寓托,人与自然既然是生命共同体,那么,个体用怎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身体与生命,也就会用怎样的方式对待自然,即个体在体“道”“守身”的同时,也同样用尊重、顺应的态度守护自然。一方面,人守护自然之身,能使自然不在人的妄动中遭受破坏。“致虚极,守静笃”[9]121,道家认为人应以虚静守住身体原有的精魄,这同时也是在一体两面地节制身体的行为,使心无妄念,身无妄动。“少私寡欲”[9]134也是让人避免因私欲残损身体与生命本然的活力与特质,同时避免对可欲之物的大加掠夺与侵害。从而,“慎守女身,物将自壮”[8]348,自然自会按照自身的特性与节律生息演变,壮大繁荣。另一方面,人顺应自然的本然特性,也能让自身不至遭受自然的反噬,从而更好地保全身体,周全生命。如《庄子·养生主》中,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8]110,不仅如此,“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8]112,为文惠君赞“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8]116。解牛的顺利流畅、挥洒自如皆因庖丁的身体动作顺应牛的自然肌理,生态语境下,庖丁解牛不伤及刀刃,也寓意着人以依循其自然特征与本性的方式对待万物,不伤害自然万物,方能不殃及自身。
概之,在道家眼中,自然不是与人分而对峙的他者,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的自然之身与周身世界是有机的整体,道家对待自身的态度与对待自然的态度是一致的,即道家注重持守保留人的本性与本然生机的自然之身,也用同样的“道法自然”原则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生态关注下,道家秉持的是“守身自然”的身体观,它更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凸显了人与自然水乳交融、休戚与共的关系。
三、“救”与“观”:儒道身体观的生态智慧
学者李义雷曾针对一个极端的假设提出疑问:孟子和庄子同坐在河边,他们都发现了一个即将溺亡的婴儿漂在水面上,此时,孟子和庄子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柯克兰借用它类比生态问题,将问题转化为如果水面上不是婴儿,而是濒临灭绝的仙鹤,甚至是处于生态危机中的地球,孟子和庄子会作何反应?他得出的答案是孟子会因他的恻隐之心而奋不顾身地施救,庄子则顺应造化,袖手旁观,也就是说,在面对生态危机时,儒家会采取人文主义者的做法展开营救,而道家则不会采取行动。在柯克兰预设的场景中,目击者与濒临危险的生物是相互独立的,但实际上,人不仅是“目睹”更是“身处”与自然的种种关系里,所以,柯克兰的答案并不准确。柯克兰对这个问题的生态化引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道的立场,的确,儒家乐意践行道德责任,向失衡的生态伸出援手,道家则倾向于“无为”,但是,道家的“无为”并不意味着不为所动。从生态视域下的身体观出发,“身以爱物”的儒家与“守身自然”的道家分别给出了“救”与“观”这两种不同智慧。
儒道文本中都曾出现与李义雷的假设类似的场景,但其内涵却迥异。《孟子·公孙丑上》:“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4]72孟子预设了幼儿快要坠井的意外,认为每个人看到这样的场景都会惊惧同情。孟子指出的道德情感是现实的援助行动发生的先决条件,而在“不忍”的道德情感动因之上,儒家也有着明确、理性的道德自律指向。“救民于水火之中”[4]135是儒家素有的胸襟与身体行动的倡导,在儒家看来,人的正义与仁善意味着以解除他人的困厄为己任,是否能由不忍人之心出发付诸挽救他人的行动也关系着人格的进阶与社会责任的履行。生态问题下,本着“身以爱物”的身体观,儒家发展道德情感与道德自律的范围从人与人的交往扩展到人与自然的交往,自觉地使自然成为了伦理关怀的对象。即儒家发挥身体的社会属性与道德属性,彰显自身对他人、他物的责任,在帮助自然与挽救生态问题的过程中丰满自身的生命意义,在仁与善由人及物的推扩中实现生命价值,儒家的“救”从自发的情感出发,得以向挽救面临危机的自然与危机中遭受困厄的人的自觉行动落实。
《庄子·达生》记载:孔子在吕梁畔“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8]582在庄子的寓言里,孔子遣弟子救沉浮水面的人,却发现他只是在游泳,并非有溺水之危。这一场景与孺子入井相似,结局却有了“反转”,也正是这一“反转”显示了道家与儒家不同的态度。水中人是庄子笔下的得“道”之人,身在水中却不会被水淹没、伤害,依然怡然自得,因为他与水火不侵的“至人”一样,体会到“道”的统通下自身与自然的圆融一体,消弭了身体与水的边界。从中可见,道家更倾向于在付诸干预前,先判断好眼下的情境究竟是反常的危机还是自然“是其如此”的正常情况。《庄子·至乐》:“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8]547-548正如滑介叔将自己的身体与周身的世界视作整体,将身体的变化视为天地运化的正常现象,安然接纳,道家认为有些情况只是人在持有自我中心主义视角时所认为的反常,而实际上却是大化流行的正常表现。“万物并作,吾以观复”[9]121,道家主张审慎克制身体的妄动,在复归于“道”的省思中体会身体与环境的有机联结,在身体付诸行动前先从客观的生态整体性层面去观察与判断出现的情况是否为自然的进程,被视为危机的情境是否只是自然秩序的一般呈现。
质言之,生态关注下,儒家持有“身以爱物”的身体观,面对生态问题时,重在“救”,即积极地对生态危机展开身体力行的营救,而道家“守身自然”的身体观则在生态问题下指向了“观”的反应,即在身行之前先从人与自然整体性存在的高度冷静观察、观测事情的本然,客观评价与判断。儒家用“救”的行动对待生态危机,实际也是在挽救生态平衡的行动中完善道德,通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承担责任来模铸自身,它体现了儒家在自我实现过程中对自然万物的关切,是朴素的关爱自然的伦理主张,亦是由关爱自然的路径彰显人性光芒。道家之“观”则以人与自然共构整体性世界为认识与行动的前提,其通过身体与自然融而为一表达的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在、相互寓托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跨越古今的生动解析,谋定而后动的行动策略也颇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而究竟何种情况、何种程度达到了静“观”之后必要干预的境地,则需在流变中结合具体情境加以考量。
儒道“救”与“观”的生态智慧为我们当今处理生态问题带来了深刻启示:
首先,对于生态问题乃至生态危机,人类不能袖手旁观,应充分发挥主体性,身体力行地担当生态责任。儒家之“救”与道家之“观”,本质而言都是生态关注下人对危机作出的反应。儒家施“救”,显而易见,指向了发挥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的主体性和身体处于环境之中的能动性,是对人担当生态责任的呼告。而道家的“观”,其实也是在发扬作为生存主体的人的观察力、判断力。“观”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在真正辨识到非自然的、反常的现象时,道家也不会一味放任。正如《老子·二十七章》言:“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9]169,挽救危机并非只能是儒士的义举,在以是否合乎于“道”为尺度明确了危机的情况下,救人救物也是道家明确的主张。基于身体视角,无论是儒家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出发,还是道家以自然为法,都对人类承担生态问题的责任提出了要求。而今,人类越来越认识到生态问题是关乎文明演进的重要问题,科技与工具的发展也使人类改造世界的力量日益强大,担当生态责任更成为不容推卸的使命。
其次,达成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共识,以命运与共的身姿构建人与自然共在共进的至美之境。儒家对生态问题的“救”发源于人类社会对个体的要求,是伦理责任由己及他、由人及物的推扩。同时,儒家善于“身传”,“身传”是自孔子起孔门弟子及其后人习得知识、理念、信条的重要形式,张祥龙就曾形容《论语》中曾子教导弟子的言论、行事充满了强烈的“活的身体感”[12]。这样的“身传”更易于社会共识的结成,在以身作则的伦理关切中使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良好关系被人类群体所认同。它敦促人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投诸一致的渴盼,凝聚关爱自然、保护环境的社会共识,聚集个体的作用力为群体力量,以命运与共的身姿追求将生态和谐囊括在内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最后,正确认识自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探索科学理性的生态治理之道。“知也者,争之器也”[8]126,道家并不是要取消一切认识,而是警惕带来混乱纷争的机械的、割裂的知识。正如将身体与自然视为同感共振的统一体,藉由身体感知自然,道家主张的是用有机联系的视角认识生态问题。道家之“观”以这种客观的、联系的认知方式为基本内涵。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乏用人类中心主义方式看待人与自然关系,为求物质满足与经济快速发展而与自然决裂的阶段。在这种非客观的、不理智的认知之下,自然沦为人索取与奴役的对象,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危害了生态平衡,终使人类遭到反噬。而今,人们汲取历史的教训,越来越强调以科学的态度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生态和谐。道家之“观”带来的正是以整体性的视角认识自然,以客观的态度应对生态问题的启示,亦析出了以生态平衡、稳定与和谐为原则,尊重自然主体性、顺应自然规律、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治理之道,指向了在应对生态问题上认知与实践互促并进的道路。
梁漱溟先生曾言:“人都是要求善求真的,并且他都有求得到善和真的可能。”[13]儒家经由身体行动使道德关怀的范围向自然扩展,形成善待自然的社会共识,主张在危机发生时采取积极行动。道家融身于自然,尊重、顺应自然,重视对真的再现,提醒人冷静自持,客观看待生态问题。生态视域下,儒道共同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认同与渴望。以身体观为着眼点,儒道思想所主张的一己之身在现实生态问题中如何行动、作何反应得到了更为明晰的呈现。它突破了儒道生态智慧言必“天”“道”的形而上困局,展现了儒道思想对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更具体、更富行动力的建言,亦藉由在世的身体指明担负生态责任是每个个体都不容推卸的使命,且需在切身行动中照见人与自然相偎相依、美美与共的文明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