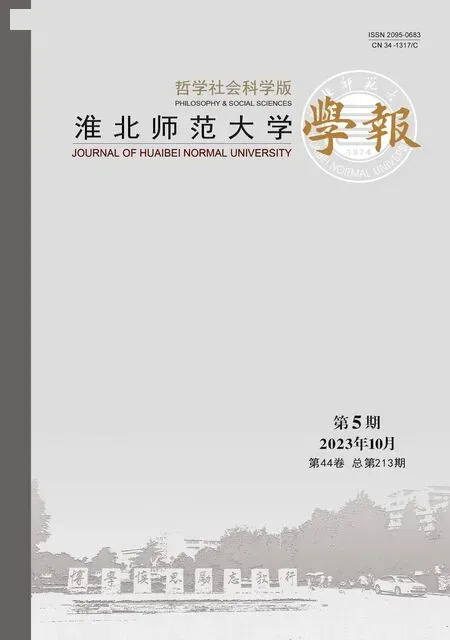明清士人《史记》阅读考察
——基于科举应试视角
张小伙
(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阅读史作为书籍史研究的最新趋势,目前逐渐为学界所关注。阅读作为一种私密性与公共性交织的人类活动,是书籍生命周期的最后一环。目前阅读史的研究取径与范式尚处于探讨阶段,许高勇、戴联斌、王龙、韦胤宗、王余光、张仲民等学人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阅读史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则是共识,从研究实际出发,阅读活动的发生必然立足于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与特定人群,尤其是经典文献,对于特定阅读群体的分析,强调除了关照文本自身外,还需要注意社会视野之中文本的生成、获取等物质条件,这些属于阅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经典文献阅读,不仅是知识再生产的途径,无疑也是形塑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由此阅读史研究必然横跨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等领域,而这也正体现了阅读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学界阅读史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晚清民国,与此前书籍史研究集中在晚明清初类似,这种特殊时段本身就充满了各种研究的特性,即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带来的新质与新变。因而对于晚清民初的阅读史研究而言,报刊这一新媒介的出现无疑带来了阅读上的巨大变革,这方面目前受到较大关注,此外明清小说阅读史、以日记为中心的个人阅读史也在积极开拓之中。经典文献阅读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梳理阅读史传统资源,构建阅读理论,更在于其现实关照层面。经典的活力蕴含于阅读之中,阅读风气又是一个时代整体精神风貌的具体展现。目前关于《史记》阅读史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本文以明清时段为限,期于从宏观上对当时《史记》阅读面貌有一概观。选取士人群体作为观察视角,而具体阅读群体考察则着眼于普通士子身上,士子通过科举的桥梁进入士人阶层,实现身份与地位的上升。因而本文所指士人群体即广义上涵盖了科举备考士子,只是在其内部划分为精英士人群体与普通士子群体。选取这一群体作为考察对象,一方面是他们与书籍的密切联系,阅读活动的发生当然建立在识字基础上,虽然目前关于明清识字率研究的结论分歧较大,士人群体无疑是识字人群最大构成部分;另一方面普通士子阅读既受时代整体阅读风气的影响,成为精英士人批评的对象,同时无形之中也参与形塑当时的阅读文化。
一、阅读的消极性:“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
明清科举时代,利禄的敲门砖无疑是时文,这种文体具有“功利性、文学性、工具性、规范性、与时俱变等多种性能,但最根本的是其经学性”[1]。普通士子自小所读之书究其根本都是为了写作时文,在这种功利心态的催化下,以“以记诵时文为速化之术”[2]128变得理所当然,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古文阅读受到一定的冷落,成为兴趣所在有余力则为之的选择性阅读。在这种局面下时文与古文的关系变得难以调和,以至于水火不容。“今之为时文者,父兄师训无不望其速成,其肯多费时日于典籍乎?是古学之亡,亡于时文之视为分途也。”[3]
士子纵然排斥以时文导向为主的阅读,也无法将精力过多投入《史记》《汉书》等古文阅读中,兼习尚难能可贵,而实际的情况往往却是被当作异类看待,其中父兄的影响不可忽略,如方以智言:
耳而目之,当世极崇高尊显,鲜不由此。此不过为利禄资,安用是博学深造也?贤父兄训其子弟,亦曰努力事此,早自争达,以博富贵,它何计焉?有好古者起,博闻强记,推本经史,讲求古今之成务,则群怪之,其道甚远,又无当于世资也,徒敝敝耳,虽有不可读之语,且将安用之?父兄者惟恐其子弟为之友,靡岁月,不即策高足,误矣误矣。彼其事渔猎,颇知学者,亦以为采获章句,为诡世逢时技耳,岂曰多读书,固有所谓儒者经术,树道德,建功绩乎?[4]71
又如李邺嗣言:“自海内不尚古学,学者治一经、《四书》外,即能作制义,中甲乙科。后生有窃看《左氏传》、《太史公书》,父兄辄动色相戒,以为有害。遂使举俗尽若避世中人,初不知曾有汉、晋,若此三十年。”[5]这种局面下往往导致“父之训子,师之教弟,猎采词华,埋头呫哔,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穷年皓首,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6],在强大的阅读导向面前,士人甚至“不复问词赋以为何物。而稍名能词赋者,一切弁髦时义而麾弃之,以为无当也”[7],更有甚者“问以本经,犹茫然不知为何语”[8]100。在这种心态下某些士人也将阅读古文视为一种妨碍[9],然而造成这种局面并非一朝一夕,从明清时人论述来看,至少在明初科举勃兴初期,士人较为遵守程朱理学,“多用宋儒注疏中语,无论子史,即六经语稍僻、字稍粗、音稍聱者,不得轻入”[10],而且“其能者颇于经义有所开阐,而行身植志,亦不苟同于流俗之人”[11],也兼及阅读《史》《汉》古文,如李调元《制义科琐记》载:“国初,试题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系人伦治道者,出以课士,当时题目无多,士专心于大且要者,用功有伦序,得以余力及他经子史。”[12]此时科举与学问尚能有效调和,谨守程式的同时,有余力从事学问研究,徐阶言:“国家以文取士,百八十年于兹。在宣德以前,场屋之文虽间失之朴略,而信经守传,要之不抵牾圣人。”[13]冯梦龙也曾回忆年幼时所见“古风”,《史》《汉》等书阅读风气兴盛。[14]
经与史在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相表里的关系,经史类书籍阅读也即是为学之必然要求,这是科举兴盛之前读书人阅读观念上的共识,科举时文本质上也是对经文的一种阐发,故而“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15]因而士人知识来源在传统语境下植根于经史之中,但明清科举制度打破了这种秩序,在部分士人群体中经史阅读逐渐演变成拟题背诵,应付科举,知识来源失去了根基,阅读目的变得功利,学术与仕途分离,经史都不读,更无“于经史之外博极群书之理”[16]。这种风气蔓延于明清两代,龚鼎孳即认为明后期文章风气的卑弱其根本就在于经史阅读的匮乏[17]1575,因而悲叹:“今世之课业者以古文为戒,以经史为蠹,望而远之,禁而绝之,诵疲薾靡弱之时文、臭腐游腔之滑调,虽有奇材,亦沦没而莫救。呜呼,可胜痛哉!天非生才之难,而成才之难。”[17]2547
此风气之肇始则是房稿与坊刻时文的流行。所谓房稿,即“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玄录》始”[18]643,“而旁有批点,则始于王士驌房仲”[19]。顾炎武于此言:“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间,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18]643士人于是走捷径而专心于背诵时文,不仅本业经书可束之高阁,何况《史记》《汉书》等较为艰深体量也巨大的古文。黄宗羲曾回忆儿时读史的艰辛,言曰“忆余十九、二十岁时,读《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盖两年而毕。然赋性鲁钝,一传未终,已迷其姓氏者,往往有之。”[20]70束书不观之风在阳明心学兴起后,愈演愈烈,即王夫之言:“万历中叶,姚江之徒兴,剽窃禅悟,不立文字,于是经史高阁,房牍孤行,以词调相尚。取士者亦略不识字,专以初场软美之套为取舍,而士气之不堪,至此极矣。”[21]王士禛记载了一则关于《史记》的笑话:
莱阳宋荔裳(琬)按察言幼时读书家塾,其邑一前辈老甲科过之,问:“孺子所读何书?”对曰:“《史记》。”又问:“何人所作?”曰:“司马迁。”又问:“渠是某科进士?”曰:“汉太史令,非进士也。”遽取而观之,读未一二行,辄抵于案,曰:“亦不见佳,何用读为?”[22]
此事亦被收录进清人独逸窝退士所编的《笑笑录》一书中,以一则笑话的形式呈现。清人张棡与友人宋燕生在闲谈中也说到了一件类似的事,载于张氏日记中:
宋君云:天下学问之最孤陋者,无如中国北边之京官。昔人云问太史公是何科进士?《史记》是何科朱卷?今殆有甚矣。有某翰林向某官借阅《汉书》,甫四五日便送还,某官问已览毕乎?其人摇首曰:此书某不见有一点好处,其中文理荒谬令人费解者甚多,自今而后吾不欲观之矣。[23]
从这些记载来看,可知在科举面前,士人的阅读一以其为归宿,除此之外的书不仅不读,甚至都不知道《史记》《汉书》等典籍为何物。归有光也曾有过类似的描述,其言:“盖今举子剽窃坊间熟烂之语,而《五经》、《二十一史》不知为何物矣,岂非屈子所谓‘邑犬群吠,吠所怪也’欤”[2]929,更是痛惜道:“今科举之学,日趋简便。当世相嗤笑以通经学古为时文之蠹,而史学益废不讲矣。”[2]36针对这种局面,归氏感叹:“嗟夫!诚使学校之官,修明经史,而略其末流,使士不求准式于《五经》、《四书》、《史》、《汉》之外,天下士风庶几少变,而人才可观矣。”[2]285黄宗羲更是直言:“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20]70钱大昕亦批评士子只为应举之文,而经史束之高阁[24]760。这些描述虽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阅读风气,也说明了科举制度严重挫伤了士人阅读史书的积极性。
因而在这种风气下,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强调经史之于时文的重要性,冀以扭转学风,引导士人广泛阅读,如尤侗从时文本质出发,强调经史阅读的重要意义[25]。孙万春亦言:“盖古人《廿一史》熟于胸中,出笔自言之有物。”[26]陈子龙则侧重史书的劝戒功能,君主应该多读史,曰:“至于善恶之迹、劝戒之事,皆在诸史,所当纵观。盖经言理,理犹玄远;史记事,事更昭明。”[27]万斯同认为读书有先后,先经后史,以通经史之学,言:“大凡儒者读书必有先后,当先经而后史,先经史而后文集。……诚使通乎经史之学,虽不读诸家之集,而笔之所至无非古文也。何也?经者,文之源也;史即古文也。”[28]方以智更直言:“文下《十三经》,而《史》《汉》为可观,下此不逮矣。”[4]38黄宗羲亦强调文必本之六经,而熟读三史八家,“读书当从六经,而后《史》《汉》,而后韩欧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发为诗文,始为正路。”[20]355
广泛的经史阅读是士子为文的基础,而房稿与坊刻时文危害之大亦可洞见。正如李光地所言:“坊刻出,而八股亡矣。如人终日多读经史,久之,做出古文,自有可观。若只采几篇《左》、《国》,数篇韩、柳,手此一编,以为样子,欲其能作古文得乎?”[29]在这种目的下,尚能阅读经史的士人,往往寻章摘句,也不过是“借字句以供笔端耳”[10],其目的不在于学问,而“举子于场前揣主司所命题,而预作之”[30]更是弊端丛生。顾炎武对于“拟题”之弊,有详细论述[18]648。李贽亦早注意到这种现象,士人“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誉录生,即高中矣”[15]233。
从科举制度层面而言,二场三场考试要求士子进行广泛的经史阅读,“他文皆可诵习古人成法以为楷模,惟策则全取实学”[31]678,具体而言“论观其才华;诏、诰、表、判,观其词令;策问观其政术,咸善焉则为臣也道立才通,而令脩政举矣”[32]。但这两场考试长期以来不被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设计之初的价值[33]。如此带来的后果往往就是“迩来士子事攻章句,于子史时务略不经心,二场三场殆成虚设,虽初试或习而一经之外,皆如面墙,以是抡魁所得不尽硕士”[16]。海瑞对于这种现象感到担忧:“近时举业习时套,独第三场五策议论时务经史,较前两场稍可得人。主试者每以卷多,日有限,头场不预取数者不复检看,是以末场虽有极工者,头场非时套不能美俗观,因之不蒙选录。”[34]从明清时期经史策的出题来看,其中涉及《史记》的内容也颇多,如万历三十八年会试策问第三道:
史以事辞胜,亦兼道与法而有之。夫断木为棋,捖革为鞠,亦皆有法焉,而史其可以无法欤?近世之论者,侈言古文,曰:迁、固而下无史矣,欧阳氏之《五代史记》,君子深叹焉,以谓可与迁《史》同风。其信然与?宋、辽、金三史,修自胜国,《元史》修自圣祖,编缀丛杂,卷帙浩烦。其间国统之离合,纪载之得失,亦可得而悉数之欤?[35]
又如乾隆庚寅科湖南乡试策问第二道:
史家之体多矣,而纪传之叙载为详,为纪传者亦多矣,而司马迁、班固为首;故言史法者,宗《史》、《汉》而已。夫《史记》之纪五帝、三王,援据《尚书》及《帝系篇》,不敢多入异说,盖其慎也。然扬子云犹云“子长爱奇”,乃后人补述,或反溢于子长之外何耶?……孔子或谓不当入世家。屈、贾、鲁、邹或谓不当同传。进游侠,退处土,前人并以是讥迁,能断其功过?《史记》西域之事,何以附于博望?……[36]
殿试策问中亦常有涉及《史记》的内容,如咸丰十年殿试策问:
汉司马迁作《史记》,变编年之例,历代史书,相仍不改,或为本纪、世家,皆有所本,惟列传则创自迁,能约举其说欤?迁书之前亦有名《史记》者,见于何篇?公侯传国,始称世家,孔子独列世家何义?刘知几谓《史记》周以上多阔略,秦汉以下始条贯,其信然欤?《史记》网罗放失,综其终始,又能于作事中寓论断,能举其一二否?……[37]
从上述题目可看出,经史策中对于《史记》的考察,更多侧重于史书的体例、史法与史评等方面,而对于具体史实则有所忽略,因而对于此类知识的获取往往有捷径,而不必辛苦阅读《史记》等原典。举业书中就有指导士子做策技巧的内容,如明代李叔元等辑《新锲诸名家前后场贞部肄业精诀》卷四“作策要诀”云:
答史疑,亦不过一二说。如问迁、固,只说自圣人笔削之后得。如二子纪事,虽不敢望圣经,亦在可取之域。若合古今作史者致问,只须言后世作史者多无才学识,或略以私心,或失之太僭,分作一两段辨析。前辈此类策甚多。[38]768-769
策题大概有二体:一问时务,一问经史。然二者未尝不相关。问时务者,必引经史为证;问经史者,未尝不因时务而发。先须体认二体,然后详看所问何者为纲领,何者为正问寔事处,何者为浮泛引傍事处,何字为血脉,何字为眼目,须要识得话头,以此探主司之意,主一己之说,则区处不难矣。[38]770
清人杭世骏概括时人阅史有三个目的,其中一个即是标举纲目应付策问之用,如其言:“夫今之剽猎于史者有三:记琐微者,腾客座之谈助;掇丽藻者,资韵语之润色;标纲目者,供举场之策问。若与之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斟酌百度,缉熙王猷,则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39]这种标纲举目式的阅读,反映了士子务求简便,读史未能抱以为学的正确态度。章学诚教导士子作策之法亦感叹:“元、明以来,试士专重《四书》文义,策对经旨,俱守学校成说,史事空作议论,亦多依傍宋儒之言,其道犹未尽善。”[31]679因而章氏强调士子要广泛阅读经子史集,摘录记纂,而非仅标举纲目,汇以成编,作为策部之资粮,因而家中有余资者,《十三经》以及《史记》《汉书》等诸史不可不购藏。
要而言之,明清科举制度造成了士子阅读的功利性以及阅读面的狭窄,《史记》阅读的社会文化基础被严重削弱,被视为科举之害,整个时代的阅读面貌则具有浓厚的举业色彩。经史阅读传统被时文背诵取代,士子在父兄的教导下不准阅读举业之外的书籍,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些士人竟不知《史记》为何书,李光地归结为“时文之坏,由于不肯看书”[29]。无论“明廷还是清廷,对于官方所接受的那些关于四书、五经和正史的书籍的出版和传播,都报以鼓励的态度,因为这些出版物皆是科举科目和文士学习的基础”[40],但房稿与坊刻时文更受士子青睐,有识之士意识到这种学风背后的巨大危害,试图极力挽救,不断强调经史阅读的重要意义,即使对于时文写作也可以提供极大的帮助。而科举在制度层面虽然要求士人进行广博的经史阅读,尤其对于二三场考试,但主考官的不重视以及试题本身的趋简性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因而在科举“指挥棒”下,整个社会的阅读风气趋于功利性,特别是普通士人的阅读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对待《史记》阅读,一方面想读的人不被父兄理解,一方面不想读的人面对科举策论的实际需要,标纲举目,务求简便记忆,以为举业之助,当然这些论述只是一个阅读侧面的概括,实际的阅读情况比这复杂得多。
二、阅读的趋简性:《史记》阅读文本的选择
《史记》在明初流传稀少,新刊本亦不多见,顾炎武即言:“当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问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8]78即使在出版印刷业发达的建宁地区,《史记》亦不多见,正德年间建宁郡守张文麟云:“建宁称为书籍渊薮,近时刻书者,专事时文,假名公巨卿之名目,投所学小生之嗜好,以此谋利。至于古书,多弃事不省。间有刻《史记》者,君子伟之。”[41]而宋元旧本又多在藏书家手中,秘而不传,明中后期以来新刊本数量才逐渐增多,为《史记》阅读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在具体阅读中,普通士子为应举的需要,阅读文本的选择具有多样性,但往往并非原典阅读或全书通读,根据阅读需求的不同,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展开论述。
从史学方面来看,《史记》等正史浩繁,但科举策论又需要士人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储备,“倘若士子对古今的历史没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就可能被策论试题难倒,答卷可能就会文不对题,直接遭到淘汰了;又或者在论证时无法引用史实来加强议论,使得论点单薄,无法吸引考官的注意”[42]249。在这种情况下简要易读的纲目体史书成为明清时期历史教育的重要教材,其发轫即是朱子《资治通鉴纲目》,其编纂“并非出于史家之识见,更多地是要把他的哲学思想流注和映射于历史当中,借历史之现实彰显与突出其天理思想之合理性”[43],以《春秋》笔法,明确其正统褒贬。其后袁了凡《历史纲鉴补》、顾锡畴《纲鉴正史约》以及吴乘权《纲鉴易知录》等书也成为应举士子必读的参考书。除此之外《通鉴节要》《通鉴辑览》以及《历朝捷录大成》等书也颇受士子青睐,其中《历朝捷录大成》系列书,据沈俊平统计在明代就有四十四种版本刊[42]438-440,与此书性质一样的《古今历代十八史略》系列书在明清时期版本数量亦极多,可见其背后需求之大,而对于《史记》等正史原典的阅读则往往不被重视,陆陇其批评这种现象:“史则略窥苏紫溪、陈眉公纂本,而不知有紫阳、涑水《全书》。至于《十三经》、《二十一史》,不能举其名者比比也。”[44]余怀对此也感叹学风日薄,曰:“世有《通鉴集要》、《笺注》、《少微》等书而人并不观朱子《纲目》矣。世有朱子《纲目》,而人并不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矣。世有《资治通鉴》,而人并不观《二十一史》矣。学问之道日趋于薄可叹也。”[45]王昶曾概括学古文失者有三:“于史也,亦以考亭《纲目》为上下千古,不知溯表、志、传纪于正史;又或奉张凤翼、王世贞之《史记》、《汉书》,而裴骃、张守节、司马贞、颜师古、李贤之注最为近古者缺焉弗省。其失也,在于俗而陋。”[46]明代国子监在教学中关于史书的阅读也仅仅要求在读经之余兼看《朱子纲目》而已[47]。谢若潮《帖括枕中祕》中关于史书阅读,即强调“史以《通鉴辑览》为宗,历代名臣名儒传不可不阅。《历朝捷录》则在所必读者也”[48]。清人胡方对家族子弟一方面要求:“《左传》《国语》《国策》《史记》《汉书》,文章取材之薮,皆不可不熟。《史记》《汉书》卷帙太繁,选其最佳者读之,余摘录之可也。”同时也觉得“《二十一史》浩博难穷,看朱子《纲目》亦了”[49]4087。陆世仪关于读书,强调“识货”,因而史书阅读“以朱子《纲目》为主,参之《资治通鉴》,以观其得失,益之《纪事本末》,以求其淹贯,广之《二十一史》,以博其记览。然约礼之功,一《纲目》足矣,《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犹不可不读,《二十一史》不让可也,备查足矣”[50],在陆氏这里《史记》等廿一史只是备查的“工具书”。张岱回忆余姚阅读风气,“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51],由张氏记载可知,《纲鉴》等举业参考书的阅读风气之盛。
从学习古文的方面来看,为了方便《史记》阅读,明清出现了众多简编本、评选本等,如张洪《史记要记》、张之象《史记汇》、李元阳《史记题评》、许应元《史记抄》、唐顺之《荆川批选史记》、茅坤《史记钞》、项笃寿《史记论赞》、庞尚鹏《史记略》、凌迪知《太史华句》、穆文熙《史记节略》、凌稚隆《史记评林》、凌稚隆《史记纂》、钱锺义《史记摘抄》、邓以赞《史记辑评》、吴见思《史记论文》、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苎田氏《史记菁华录》、牛运震《史记评注》、王拯《归方集评点史记合笔》、吴汝纶《史记读本》等等。除此之外宋代以来的古文选本例如《古文关键》《古文真宝》《文章正宗》等在明清也广泛流传。这些本子一方面促进了士人的《史记》部分篇目阅读,特别是“评点者从《史记》词句、章法、叙事、写人等方面一步一步把读者引入它的艺术境界,使更多的人了解《史记》,认识《史记》,并且提高自己的阅读鉴赏水平”[52]。另一方面其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坊刻古文选本对原文的随意删减,造成阅读上的碎片化,“不问文之可删不可删,止取词句可通用者则存之,稍不可用者尽删之。或去其头面,或去其筋节,或去其波澜。不知头面去则由来无可考矣,筋节去则神气不相续矣,波澜去则情境不生动矣,读之何益乎?”[53]149坊刻古文选本最常见删节方式即是“每篇之中,去其首尾,专留中间一段,谓为精华在是”[54]。就《史记》而言,史赞和诸序最受坊刻青睐,而其他佳篇多不得入选,如此士人的《史记》阅读往往不得其法,缺乏对于《史记》的整体感知。科举书中对于《史记》的阅读要求一般是依自身喜好选择若干篇目熟读,清人司徒德进《举业度针》即言:“揣摩非精熟不能,只在西汉、《史记》、唐宋八家中择取十数篇,为自己性情所酷好者,置之案头,朝夕读之,读到烂熟时,不觉浩气自在喉间流出,落笔便不犹人矣。”[55]谢若潮《帖括枕中祕》要求“《汉魏丛书》多秦汉以上之书,亦宜摘读。外此如《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书皆宜节读以博其趣”[48]。总而言之,在“世之习举业者读古文,所重不过取移用于时文而已”[53]150的阅读心态下,《史记》阅读文本的选择往往趋于简便性与功用性。由此士人对于《史记》的阅读方式往往为割取抄节,以为时文之资,因而经常将史实弄错,张冠李戴,杨慎对此种现象极为不满。[56]
普通士子难以通读《二十一史》,现实方面的原因是其卷帙太多,一般士人群体难以全套拥有,至于偏僻的地方则更难以获得,如郭休《读史备忘序》言:“诸家全史,非学士大夫尚不能有,偏州下邑、乡闾里巷之士,谁得而观之?所得观者,盖不过少微《节要》尔。少微编年之书,主国政之始末,至于其人之贤否、爵里出处,盖不得而兼备矣。得此以参考之,于学者之所助岂云少哉?”[57]又如谢肇淛自叙:
余自八九岁即好观史书,至于乱离战争之事,尤喜谈之,目经数过,无不成诵。然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纲鉴要略》而已。后乃得《史记》、《汉书》及朱子《纲目》,读之凡三四过,然止于是而已。后得《二十一史》,则已晚矣。然幸官曹郎冷局,得时时卒业也。[58]
鉴于这种现实情况,王士禄曾上奏,意欲调整《二十一史》次序,将《史记》单行,同时淘汰重复,得十二正史,便于士人能通读历代正史。[59]2502-2503王氏的建议虽未被采纳,但从侧面反映出正史的浩繁使得士人望而却步,而在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下,史书阅读又是士人的必修课。但王氏将《史记》移出正史行列,易以苏辙《古史》,却是顾此失彼,《古史》对于《史记》虽有补正考订的价值,但却无法取代《史记》,王士禛即认为两书应兼采而不能偏废[59]4967-4968。不论是现实上的书籍难以获取,还是心态上的畏难,普通士子的《史记》阅读趋向简便是时代环境造就而成的。
三、阅读的功用性批评:从目的到方法指导
《史记》阅读目的在科举时代,多为时文之用,在这种阅读心态下,《史记》作为史学著作的本质被忽略,不顾史实,仅仅关注字句层面,即所谓“借字句以供笔端耳”[10],明清两代史学的衰微即是一种体现,这一点在明代较为明显,而清代乾嘉考据学兴起后,士人阅读《史记》则又逐渐侧重其史学面向,到清代晚期内忧外患下史学与致用重新联系起来,与此同时西学东渐带来的巨大冲击也在促使时人重视史书阅读,希冀从中汲取历史经验以应对时局。
钱大昕注意到士子读《史记》仅为科举之用,而难通大义。[24]546洪亮吉则批评当时的读史风气进入了两个误区,一则过于强调春秋之法,而忽略史实;一则以举业为目的,以一字一句为师法:
近时之为史学者,有二端焉。一则塾师之论史,拘于善善恶恶之经,虽古今未通,而褒贬自与。加子云以新莽,削郑众于寺人,一义偶抒,自为予圣。究之而大者,如汉景历年,不知日食;北齐建国,终昧方隅。其源出于宋之赵师渊,至其后如明之贺祥、张大龄,或并以为圣人不足法矣。一则词人之读史,求于一字一句之间,随众口而誉龙门,读一通而嗤虎观。于是为文士作传,必仿屈原;为队长立碑,亦摩项籍。逞其抑扬之致,忘其质直之方。此则读《史记》数首,而廿史可删,得马迁一隅,而余子无论。其源出于宋欧阳氏之作《五代史》,其后如明张之象、熊尚文,而直以制艺之法行之矣。[60]
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劝戒士子阅读《史记》以习古文而不能仅作八股之用:
诸生为文,将欲传世乎?抑欲取科名乎?如欲传世,则班、马、《左》、《国》俱在,何不学为古文,学为《史记》,而区区以八股是为乎?即欲以八股传,而仅于八股中讨生活,恐亦万万难作佳文。[26]5919
王闿运对于读史仅从文章入手极为不满,言曰:“今之读史,但知体例耳,乃是作文之一端,亦无关学。学能通经,自知文体。”[61]王氏强调治经方是为学之道,因为“经典博奥,子史简浅故也。儒者乃以博通子史相夸,则视为词藻,无关学矣”[61]。而史学是用以应世,因而王氏对于史书的阅读侧重治乱兴衰以及关注其史体、史笔等方面。吴汝纶亦批评时人读史只为文章之用,而忽略史实,云:“今之读史者,但溺于文辞之间,即纪传中所详著之事迹,莫有为之深心考究者,又安怪其视表如赘疣而漠不经意也。”[62]
张之洞批评明人以评点时文的方式阅读《史记》,认为这是一种恶习,其言曰:“明人恶习,不惟《史》《汉》,但论其文,即《周礼》、三传、《孟子》亦以评点,时文之法批之,鄙陋侮经,莫甚于此,切宜痛戒。《史》《汉》之文法文笔原当讨究效法,然以后生俗士管见里语,公然标之简端,大不可也。卷端止可著校勘考证语,若有讨论文法处,止可别纸记之,读诸子同。”[63]114张之洞强调《史记》阅读应该史学性与文学性兼备,“语其高,则证经义,通史法;语其卑,则古来词章,无论骈散,凡雅词丽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无待于言”[63]94。
面对如此阅读风气,精英士人群体批评之余,逐渐关注家族成员阅读实践,从教育根本入手,引导树立正确的经典阅读理念。与普通士子往往以纲目体、简编本史书甚至坊刻古文选本代替《史记》原典阅读不同,精英士人群体在教育家族子弟时,对于《史记》原典的阅读越来越重视,这种情况的出现即是对于当时《史记》阅读风气一种反拨的体现,以至于具体到如何阅读,这可以从当时的家训家书中反映出来。明人许相卿为子弟制定读书规划,其中关于读史的要求为:
史学工夫,虽不必如读经精熟,亦须虚心审察,至于一事之初终,一人之姓名、爵里、世系、谥号,皆当考求强记。又须随事分类,如当时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纪纲之张弛、制度之因革、国本之虚实、天命人心之离合、君子小人之用合进退、刑赏之公滥、经费之奢俭、税敛之轻重、兵力之强弱、戚宦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风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逐项写出,又可以备“达政”中参用。[49]1902
其所列参考书目中没有《史记》,而将《史记》放入“学文”之中,强调其文学的一面,因为许氏认为《史记》“议论或驳而不纯”,但亦要求“成文者,通读”,但许氏本人就曾批点《史记》,著有《史汉方驾》一书。清人傅山要求子侄除经书外,“《史记》、《汉书》、《战国策》、《左传》、《国语》、《管子》、骚赋皆须细读。其余任其性之所喜者,略之而已。”[49]3522汤斌要求自己的儿子读古文,“以《左传》《国语》《国策》《史记》为主,八大家正当多读,东坡文、韩、欧,却当缓之,不知亦有理否”[64]。郑板桥告诫其弟:“《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史》《庄》《骚》,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而已,只此数书,终身读不尽,终身受用不尽。至如《二十一史》,书一代之事,必不可废。”[65]5同时对于具体阅读方法而言,郑氏反对一眼即过式的过目成诵,而是强调韦编三绝式的勤读一书之最精华部分,即如《史记》为例:
《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会为最。反复诵观,可欣可泣,在此数段耳。若一部《史记》篇篇都读,字字都记,岂非没分晓的钝汉![65]14
方东树强调:“若欲学文,则经史外以《国策》、《史记》、《汉书》、屈子、《庄子》、韩文为最要,必须通贯。”[66]同时亦认为要以经世致用的角度去读《史记》八书,“致用之学,史尤切用”。庄受祺也侧重读史的实用一面,因而需要常读,云:“《通鉴》《史记》《汉书》常置手眼,此习事也。处处作我设身处地观,不要当作纸上空言。”[49]6629而具体阅读《史记》应该从其“委曲繁重、读时多致头昏之处,得其暗中运气之法”[49]6635。潘宗洛则讥笑村学究教人读《史记》,却只选《五帝本纪赞》等类,而“洋洋大篇如《封禅书》《货殖传》者断然不读”[49]4202。而唐彪在教授子弟读书作文时,提出了阅读《史记》,以“挨年次月”为纲领[53]139-140。曾国藩教育其子阅读,列出了具体的方法,即看、读、写、作四者[67],对于《史记》阅读的具体方法则为“看”,即广泛阅读,强调阅读广度,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读”,为读经史的方法,高声朗诵,强调阅读深度。曾国藩于四书五经外,择《史记》《汉书》《庄子》、韩文、《通鉴》《文选》《古文辞类纂》《十八家诗钞》等八种为士子必读书。曾氏日记中亦有大量阅读《史记》的记录,跨度从少年至暮年,可见其对于《史记》的热爱。康有为在《桂学答问》中强调读史以《史记》、两《汉》为重,“能通三史,则经义、史裁、掌故、文章俱备矣”,而读史时间规划上,康氏认为:“新学读史日一、二卷,其后渐习,日可三、四卷。《史记》一百三十卷,《汉书》一百二十卷,除表三十卷不能遽读,皆百卷。”[68]其他著史则一日三卷,如此三年可读完二十四史。
有些士人家庭还会传授与课读《史记》,这与推荐阅读的引导意义来说是一种更为直接的阅读实践,具有培养阅读习惯的重要意义,与一般家庭不同,这种家庭多是传衍多代的诗书世家,而且家中长辈多长于史学,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家庭阅读氛围。邵廷采十二岁从其外祖父受《史记》,其言:“年十一,从府君受先正制义。府君卒,明年,先君鹤间公去之石门,庭训旷废,乃从外祖陈蜀庵先生学。蜀庵先生性嗜佛,往往为谈说禅学,然受《左氏春秋》及司马迁《史记》则自蜀庵先生始。”[69]梁启超亦曾自述八岁时其父课读《史记》。[70]此外也有母亲角色的参与,如乾隆时期才女陈端生口授其子《史记》,言:“丁郎读书,颇有父风……今因病中,不能抄录诗文,后当寄阅。来字询所从师,十二岁以前,经书、《史记》、《文选》、《唐诗》、《庄》、《荀》等书,皆贞口授,温背熟习。”[71]陈端生为清乾隆时期的著名才女,其创作的《再生缘》是现今所知最早由女性执笔的弹词作品。此书“以其情节构造上的完整性、用词造句之典雅生动,以及在古典文学中罕见的女性激越之声,而赢得评者一致赞美,奉之为女性弹词小说之经典”[72]。因而陈氏能口授其子《史记》《文选》等书,而一般女性往往只能课读《孝经》《论语》等基础读物。
要而言之,明清时代《史记》的阅读往往无法摆脱与科举时文的关系,因而导致重文轻史的倾向,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当时整个时代的史书阅读风气,受到了时人的关注与激烈批评。因而一部分有识之士在教育家族子弟时,一方面强调对于《史记》原典的阅读,另一方面在具体阅读方法上予以指导,冀以从学习古文与史学的角度去阅读《史记》,而不仅仅关注时文教育,这种转变伴随着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而逐渐显现。
结语
回顾明清时代《史记》阅读诸面向,不难发现科举的制度性约束对于史书阅读的极大伤害,不可否认《史记》文学经典地位在明清两代的最终确立或许能说是得益于科举制度下文章学的发展之力,即如六经、《史记》都以一种文学性阐释趋向而得以发挥更大影响,但阅读上的两极分化呈现得更加明显。精英士人群体能够一定程度摆脱举业带来的消极作用,坚守传统经史阅读,博而返约,跨越科举知识的桎梏,因而我们才能看到一种颇为矛盾的局面,一方面“史记学”在明清两代繁荣发展至清中后期臻于顶峰;另一方面普通士子群体作为学术传承的后备力量却在《史记》阅读上表现得极为消极,深受阅读风气影响。明中后期由精英士人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虽然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普通士子的《史记》阅读兴味,“弘治末,颇知习《左传》、《史记》矣”[73]的局面开始出现,但士子在功利性的阅读心态下依然是以举业为归依,由消极性阅读返归功利性下碎片化阅读。这种上下失衡让我们能从侧面了解到《史记》作为经典文献在明清社会语境中另一种存在样态,经典文献的冷遇或许再往下层社会探寻更能表现得明显,其背后的阅读兴味更注重于娱乐性与实用性,小说戏曲与日用类书的繁荣即是证明。当然本文的阅读史考察是基于科举制度下精英士人对于普通士子群体的《史记》阅读批评,因而更多的是负面揭露,具有一定的偏向性,但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存在。
阅读史的考察本身面临着诸多难题,首先是阅读本身具有私密性与瞬时性,其次阅读史相关材料的搜寻较为困难。近年来书籍史的研究转向开始侧重于阅读层面,使得相关研究成果陆续涌现。从研究的可操作性来看,对于阅读心态以及阅读特征等方面的揭示应当是现阶段较为合适的选择,也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的基础。阅读群体、阐释技巧以及阅读深层次意义反馈等方面研究需要更多关注。对于《史记》这样的经典而言,研究成果丰富但鲜及于此,一方面受制于传统研究范式的束缚,另一方面可能没有注意到阅读史这一研究层面,因而阅读史的考察充满了研究的可能性,也需要更多学者的开拓。经典阅读的意义不仅在于个人更体现了群体的价值塑造。《史记》在明清时代士人的阅读中面临着一种窘迫的局面,这种局面源于科举制度的阅读导向性约束,同时也与时代风气,特别是学风、士风的关系密切。经典的意义展现离不开阅读,这也意味着阅读史的考察具有一种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