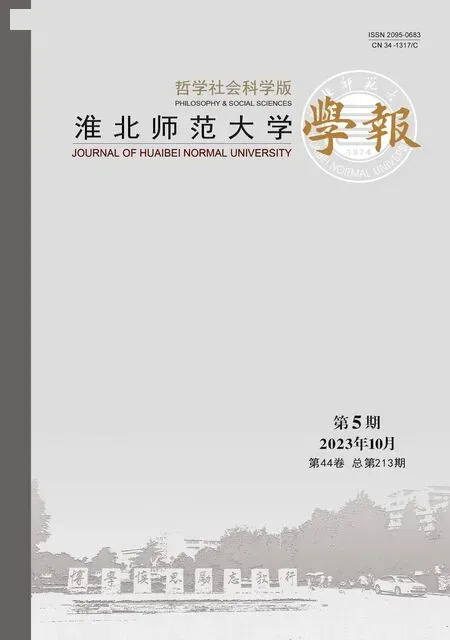《洛丽塔》中水域和汽车意象内蕴与亨伯特的悲剧根源
孙 睿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洛丽塔》(Lolita)以“一位白人鳏夫的自白”形式讲述了一名欧洲中年男子和一个美国少女之间的畸形恋情故事。小说自1955 年出版后,因其禁忌主题而一度备受争议,但纳博科夫华丽的文笔和作品复杂的蕴意逐渐吸引了评论界的关注,小说也早已被公认为是一部后现代经典之作。几十年来,国内外的评论家们从伦理道德、精神分析、叙事学、文化研究等诸多角度对其作出了丰富的阐释。作为一位具有鲜明艺术风格的小说大师,纳博科夫笔下丰富的意象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要点,如森德罗维奇所言,纳博科夫的作品,“只有通过细究其中的语言、思想、意象和典故,以复现他那错综精细的艺术思维网络,才能得以切近”。[1]约翰·英厄姆关注到《洛丽塔》中的雷电等天气意象和花园等圣经意象,探讨了纳博科夫对弗洛伊德式“原初场景”的戏仿。[2]克里斯托弗·林克解读了小说中的伊甸园意象,讨论了其中呈现的诱惑和背叛叙事。[3]杨振宇聚焦于小说中狗的意象,分析了作品如何借此意象来强化不同场景中的情感色彩。[4]森德罗维奇从《洛丽塔》中隐含的蝴蝶意象入手,阐述了纳博科夫个人美学中的道德与艺术议题。[1]亚历山德罗夫和拉特利奇都关注到小说中与水有关的意象,认为其中蕴含着对魂灵、彼岸等超自然存在的指涉。[5-6]不过,对于小说中的汽车意象,目前还缺乏关注,也还未有将水域意象和汽车意象进行串联与统合的研究。本文认为,水域和汽车意象在小说中组成了一条极其重要的叙事线索,是解析男主人公艺术家式人物形象的一把钥匙,暗藏着其毁灭性结局的根源和演进脉络。水域指向亨伯特对永恒世界的渴望,他将此审美想象投射到现实中的女孩洛丽塔身上。汽车则象征着物理世界中的动力,借此动力,亨伯特试图将他的想象世界拽入到物理现实中,通过占据洛丽塔的肉体来实现他所渴望的永恒。在唯我的、形而上的想象世界与客观的、线性时间的现实世界的碰撞中,亨伯特的毁灭是注定的。他的个体悲剧也在深层意义上体现着一种普遍性的人类悲剧,是人的经验存在与超验渴求之间永恒冲突的一个缩影。
一、水域意象:对永恒世界的渴望及艺术投射
水域意象随小说开篇而出现,亨伯特童年时期在海边的初恋经历是他成长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塑造了他人格中对永恒的渴望,那片蓝色海域成为这一渴望的标记。当中年亨伯特遇到洛丽塔后,水域再次以湖水的形式出现,成为他将旧有的渴望投射到洛丽塔身上这一行为的注解。小说中海水和湖水这两个水域意象,串联起了亨伯特始自童年、贯穿一生的超验渴望,也象征着他对幻想世界的诗意投射。
亨伯特叙述的开篇就告诉读者,洛丽塔有一个“前身”,如果没有这个“最初的女孩”,“可能根本就没有洛丽塔”,这个先前的故事发生在里维埃拉“海边的一个王子国度”,他父亲在那里拥有一家豪华酒店。[7]9“王国”在英语中是kingdom,而亨伯特此处特意使用了princedom,将“国王的领地”改写为“王子的领地”,暗示出成人世界前的纯洁美好之意。海边的童年生活风景优美、物质富足,亨伯特感受到的是一个令他处处满意的“明亮世界”:“壮丽的米拉纳酒店像私有的宇宙一样围着我旋转……外面是一个更大的湛蓝宇宙,波光粼粼。从围着围裙的洗锅工到穿法兰绒的权贵,人人喜欢我,人人宠爱我。”[7]10在这个“湛蓝宇宙”中,13 岁的亨伯特和同龄的安娜贝尔相爱了。不过,这对小情侣“彼此间灵魂与肉体每一分子相融合”[7]12的两次企图都未能成功,第二次的场景尤其给亨伯特留下深刻印象,在他即将“占有”他“心爱之人”时,两个满脸胡须的游泳人——“海的老人和他的兄弟从海里走了出来,嚷嚷着粗俗的鼓励话”。[7]13被意外的闯入者此番打断后,亨伯特和安娜贝尔再未有机会续写这一篇章。四个月后,安娜贝尔就病逝了。
爱人的离世使得小亨伯特第一次深刻体会到凡尘人间的莫测易逝和残忍无情,正是这种体验激发了他对成长的拒斥和对永恒的渴望,他感叹道:“让我一个人留在我青春期的公园里,留在我长满青苔的花园里。让他们永远围着我玩耍。永远不要长大。”[7]21实际上,当时那两个游泳人向亨伯特叫嚷的“Mais allez-y,allez-y!”[7]53颇具预言色彩。这句法语口语通常表示“去啊”“干啊”或“加油啊”等鼓励之意,在亨伯特描述的性语境中显然是个庸俗的调笑之语,但其字面意义“往前走”则在小说整体层面上形成另一重张力,切中了亨伯特今后悲剧人生的命门。“往前走”即是示意一个人做出物理空间上的移动,同样也意味着人对于线性时间流逝的顺从。亨伯特称这两个游泳人为“海的老人和他的兄弟”,而在希腊神话中,“被称为海的老人的正是能千变万化并能预见未来的普罗提斯(Proteus)”[8]。纳博科夫通过这一影射,巧妙地暗示出此情节的预言性:这两人实际上预先告诫了小亨伯特一个庸常真理,即人的成长和世事的变迁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但其“告诫”在亨伯特这里被呈现为一种打断和搅扰,这一负面情形则预言了亨伯特将会在此点上受阻、不能顺畅应对这一人生课题的命运,他对这两人的反感和怨恨也预示着他今后对凡尘变化的抗拒和妄图与之对抗的荒谬人生。
失去安娜贝尔后,亨伯特不愿“往前走”,他渴望一种凝固的时间和永恒的占有,而变故发生前的那片蓝色海域,则化作一个悬置在凝固时间中的幸福天堂,令亨伯特耽于其中。由此,水域意象与亨伯特对永恒和不朽的超验渴望产生深度关联,前者成为后者的一种符号。事实上,将亨伯特的这一经历放置于海边,将他的超验渴望与水联系起来,这样的设定恰到好处。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水因对生命的孕育而常被与超验性和精神性的层面联系起来,古罗马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就把世界本源“太一”描述为“流溢”着的。[9]纳博科夫的叙事设定,回应着水的意象本身在西方文化中的内涵,使得安娜贝尔插曲与亨伯特对永恒世界的渴望之间的关联更加鲜明。
对亨伯特而言,海边的安娜贝尔具象化了他对那个永恒世界的无限眷恋,而洛丽塔则是安娜贝尔在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化身。亨伯特称,安娜贝尔那“海边的四肢和火热的舌头一直缠绕着”他,直到他“将她化身到另一个人身上”之后,“她的魔力”才终于被破除。[7]15亨伯特第一次见到洛丽塔时,很明显,他看到的并不是洛丽塔本人,而是他失去的旧爱:“一股蓝色的海浪在我的心下涌起,在一小片阳光里铺着的垫子上,半裸着的、膝盖跪地转过身来的、我的里维埃拉的爱人正透过墨镜凝视着我。”[7]39亨伯特在洛丽塔的肉身中看到的是安娜贝尔,“蓝色的海浪”指向的正是那个凝固时间中的不朽世界。亨伯特内心的渴望随即找到了出口,转移到了洛丽塔身上,正如他感叹的那样:“这个洛丽塔,我的洛丽塔,已经具体化了写作者[指亨伯特自己]的古老欲望,因此,在一切的一切之上唯有——洛丽塔。”[7]45洛丽塔被审美化为一个能指,其意义“只能借助它对另一个能指‘安娜贝尔’的指涉”而获得。[10]
洛丽塔成为安娜贝尔的“化身”,而她家附近的沙漏湖,也成为里维埃拉海域的对应物,指向超验世界和想象领域。在浪漫主义美学中,水因其“神圣”和“流动性”,是诗人灵感源泉的象征和创作过程的隐喻。[9]小说中,这片湖水正是亨伯特展开种种创作式想象的布景,映照出他对洛丽塔的一种审美性的占有方式。洛丽塔的母亲夏洛特曾提过湖边野餐的计划,亨伯特就在对湖水的想象中谋划着种种借口来摆脱夏洛特,从而只和洛丽塔共处——“和我的小仙女一起跳进树林”[7]54,由此再续他在里维埃拉的浪漫前缘。亨伯特和夏洛特结婚后,他数次设想着如何彻底移除夏洛特这个“妨碍”,这片湖水又成为他在想象中施行“一场轻快沸腾的谋杀”的“完美”场景。[7]86亨伯特的此类幻想充满了对细节的考量,显示出一种艺术创作式的疏解之道,借无比生动的虚构来展开现实中无法上演的故事,以满足自己的欲念和渴望。
除了沉溺于种种虚构外,亨伯特还另以典型的艺术方式——日记写作和诗歌创作——来“占有”洛丽塔。他自称是“私下里的诗人”,为洛丽塔“茫然的浅灰色眼睛上乌黑的睫毛,为她短短的鼻子上五个不对称的雀斑,为她棕色四肢上金色的绒毛谱写了一曲情歌”。[7]44在现实世界中,夏洛特横亘在亨伯特和洛丽塔之间,使他不能随心所欲地与后者交往;但在用纸笔构筑的审美空间里,亨伯特则可以放心地让洛丽塔成为他“王子国度”中的唯一臣民,而不必顾虑任何阻碍。在幻想世界中掌控全局的亨伯特得意地将自己比作“古老花园里那些肿胀发白的蜘蛛”,称“我的蛛网布遍整个房子,我像个狡猾的巫师,坐在椅子上倾听一切。”[7]49
不过,正如湖水惯常的宁静那般,水域意象指涉的超验渴望和艺术幻想归属于一种静态维度。无论是日记里的唯我式的占有,还是设想中的完美谋杀计划,它们都只停留在亨伯特的想象领域。尽管他的湖中谋杀幻想流露出些许疯狂和失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暗合着福柯所指出的水在欧洲文化中与非理性和疯癫相联系的一面[11]),但他在畅想完这个谋杀计划后,便立即声明自己不能那样做,因为“诗人从不凶杀”[7]88。换言之,直到现在,亨伯特只是沉浸在他那由幻想构筑的艺术世界中。在这个形而上的王国里,他把洛丽塔审美化为一个投射自己渴望的容器,通过想象的、诗意的方式“安全地独占”[7]60她,以此来切近自己所欲求的那个完美世界。
二、汽车意象:现实世界中的动力和掌控象征
水域意象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初始框架和参照,阐释了主人公亨伯特的人格中最鲜明的欲念和渴望,也注解着他对洛丽塔的迷恋背后的渊源和种种艺术性的“占有”表现,属于一个静态的审美领域。而汽车意象的引入,则象征着亨伯特进入了行动的世界,其也成为推进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借助汽车提供的物理动能,亨伯特试图将自己对永恒和不朽的渴望从形而上的世界拖拽出来,“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
在此前的唯我主义式的想象中,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欲望虽然给他的现实生活造成了一定的紧张,但他尚且还能维持住一种外在的平衡。然而,夏洛特的车祸打破了这一切。现实中的这场意外事故神秘地应承了亨伯特幻想中的谋杀恶念。这一刻,想象的领域似乎被一股来自现实的力量破开,形而上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似乎在此处汇合。亨伯特在得知夏洛特的车祸情况后,激动甚至癫狂地说:“我看到了命运的代理人。我已经触摸到了命运的肉身——和它那垫高的肩膀。”[7]103造成夏洛特死亡的工具——汽车——以一种来自物质世界的机械动力,给原本沉溺于静态艺术王国中的亨伯特呈上了一种狂妄的行动力,如他所言,“宽厚的命运与我庄重握手,将我从呆钝中带离”[7]103。
汽车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是物理动力的标志,昭示着人类创造性的天才智慧和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自20世纪初福特汽车公司成立并发明了流水线生产模式以来,汽车得以大规模量产而走入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中,成为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随着启蒙理性对自然世界的祛魅,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把对自然的无限统治权作为目标,意欲“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12],“工业化的成功”又进一步“加强了进步的观念”[13],在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强化中,人对于科学进步的威力和自身的能动性都产生了极为膨胀的信念。作为现代科技的典型代表、同时又是前进和动力的载体本身的汽车,其意象中自然也隐含着人出于对进步的乐观和对动力的依赖而产生的傲慢和盲目。在《洛丽塔》中,汽车既是亨伯特将自己的幻想世界拖拽到客观现实中来的动力工具,又影射着他在这一行动中盲目、自负的掌控心态。
夏洛特死后,亨伯特以洛丽塔继父的身份成为她的监护人。他得意洋洋地开着夏洛特的车从学生活动营地接走了洛丽塔,之后便展开了他们“遍游美国的大旅行”[7]145。汽车提供了一种深度的私密空间和流动的生活方式,使得亨伯特能最大程度地避开别人对他们二人情形的怀疑。此前,他只能在想象中将洛丽塔“安全地独占”,而现在,在由汽车和旅馆交织的漫游旅途中,亨伯特对洛丽塔的占有计谋终于得逞。“沿途数不清的汽车旅馆在霓虹灯下宣告着它们的空缺”,随时准备着为包括“最堕落、最精力充沛的情侣们”在内的各色人等提供住处,亨伯特故作姿态,以一个旁观者的口吻感叹道:“啊,温文尔雅的司机们滑驶过夏日的黑夜,假如舒适小屋统统在突然之间褪去颜色,变得像玻璃盒子一样透明,那你从完美无瑕的高速公路上一眼望去,能看见怎样的寻欢作乐,怎样的欲望扭曲!”[7]116-117“舒适小屋”(Kumfy Kabins)是小说中出现的众多汽车旅馆的名称之一,指代着他们旅途中由汽车串起的每一个下榻之处,而亨伯特驾驶的这辆汽车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更加私密和流动的“舒适小屋”,满载着他的“扭曲欲望”奔窜在美国的大地上,“玷污着那片迷人、可靠、梦幻、辽阔的国土”[7]175-176。亨伯特欲望达成后的满足姿态和自恋情绪溢于言表,“温文尔雅的司机”和“完美无瑕的高速公路”显示出他对汽车生活的无比满意与认同。在这场结合了“目的性和无终点性”的巡游中,亨伯特得以“逃避美国法律对他的不伦之恋的惩处”,“跟他心爱的小美女永远栖居在青春的性爱王国”。[14]
汽车成为亨伯特将洛丽塔束缚在自己身边的有效工具,这种生活方式也助长了他内心掌控欲的无限膨胀。亨伯特手中握着的方向盘给了他一种幻觉,似乎洛丽塔的人生也可以像这样彻底由他掌控和独占。在漫游途中,他一边用电影、音乐剧、旅游景点、通俗杂志、零食和漂亮衣服等等拿金钱置换的消遣来控制洛丽塔,一边对她严加看管,严格限制她的日常行动,对她和外界任何可能的接触都充满戒备,在种种令人窒息的束缚下将洛丽塔变成他实际意义上的囚徒。洛丽塔曾数次央求,想和同龄伙伴一起去旱冰场玩,亨伯特极不情愿地同意了一次,而当洛丽塔进入冰场后,他“守在汽车里,混在其它车头朝向搭帆布顶篷的户外溜冰场的(空)车群中”,紧紧地监视着那些“旋转的滑冰人群”[7]160。小说对其他车辆的“空”特意加了括号以示强调,使得场景更加栩栩如生,也令亨伯特荒唐的控制狂形象跃然纸上。事实上,亨伯特不仅常对路人疑神疑鬼,其敏感和猜疑之盛更是到了出现幻觉的地步。歇斯底里的猜疑和神经质般的幻觉,不仅显现出一种心智上的癫狂,也透露出其行径之中的悲剧底色。但处于癫狂中的亨伯特对此毫不自知,依然紧紧依附在汽车带来的掌控幻觉中。起初用汽车接走洛丽塔时,他就激动地宣称:“在命运的巧妙协助下,我终于将这妙不可言的生活欲想成了现实”[7]113;在将洛丽塔频频占有后,他更是高呼自己获得了“超越尘世间任何快乐”的至高幸福,陶醉在他自己“选定的天堂”里[7]166。
汽车作为一种动力的符号,既象征着亨伯特的行动力和能动性,也影射出他极度膨胀的自我意识和掌控欲望。在汽车旅行中,亨伯特自认为已成功地将想象世界拖拽到了现实领域中,其傲慢和狂妄的姿态一览无余。不过,狂妄往往是毁灭的前奏。人仰仗工具理性而产生的膨胀和傲慢,本身就是一种幼稚。机械动力的加持并不能使人类变得无所不能,人所创造出来的工具,也并非永远都“听从”人本来的意愿,就如夏洛特的车祸事故所示,汽车本是为了方便人类生活、助长人的行动能力而被创造出来的,但它也可以对人的生命造成威胁。汽车失控的破坏性维度在美国文学中屡见不鲜,如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车祸就被设定为主人公毁灭的导火索。在《洛丽塔》中,汽车意象内含的这一维度也隐隐指向亨伯特接下来的毁灭结局。
三、幻想与现实的碰撞:毁灭的必然
亨伯特“欲想”而成的“现实”势必好景不长,因为当他将自己的超验追求拖拽到经验生活中后,他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现实世界中的两个致命敌人。第一个敌人是他人的主体性。在亨伯特想象中的唯我王国里,他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一经汇合,他自行授予的特权就立马烟消云散了。汽车象征的能动性在此依然具有强烈的隐喻意义。显然,亨伯特不是唯一一个拥有汽车的人,在漫游旅途中,奎尔蒂也一路开车跟踪着他。亨伯特下车查看漏气车胎的那次,奎尔蒂的车就停在不远处,亨伯特决意去会一会这位神秘的跟踪者;然而,当他走向后者时,一辆大卡车突然驶来,掩护住了奎尔蒂,而此时在亨伯特车里的洛丽塔也启动了引擎,亨伯特不得不转身折回去阻止洛丽塔,趁这个间隙,奎尔蒂溜之大吉,亨伯特意识到洛丽塔“发动汽车就是为了阻止”他走向奎尔蒂。[7]228-229亨伯特想要揪出奎尔蒂的意图被同样开车的奎尔蒂本人、掌控了汽车方向盘的洛丽塔、以及那辆凑巧路过的大卡车司机合力挫败。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向亨伯特表明,在现实世界中,他的主体性与其他人的主体性并无二致,他们交织成网且互相制约,而他只是这个网络中最微小的一部分,绝不是他自己的想象世界中那个端坐在蛛网中央、掌控着每一条丝线的操控全局者。后来,洛丽塔从亨伯特身边逃离,亨伯特苦寻无果后,他写了一首长诗,诗的结尾是“我的汽车蹒跚跛行,德洛丽丝·黑兹/最后一段长路最为艰难/我将被抛入腐草之地/余下的只有铁锈和星尘”[7]257,“蹒跚跛行”的“汽车”正是亨伯特此刻状态的自我隐喻,暗示出他已体会到自己受他人主体性制约的无力感。
亨伯特遭遇的另一个敌人,则正是他的妄念所意欲克服的对象本身——时间。时间的流逝是物质世界中不可避免的基本事实,也是他欲想的永恒世界所根本对立之物。亨伯特曾将那些让他无法抗拒般着迷的“小仙女”定义为“9 岁到14 岁之间”的一些少女[7]16。汽车旅行开始时,洛丽塔大约12 岁,正是在亨伯特借助汽车旅行将洛丽塔独占的过程中,那个“小仙女”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而又不可挽回地消失了。这是亨伯特永远无法征服的绝对敌人。实际上,从他把对永恒的渴望从想象领域中拖出来、并放置在那个小女孩身上的那一刻起,他的失败就已经是注定的了。当亨伯特最终再次见到洛丽塔时,17 岁的洛丽塔已嫁为人妇,并怀有身孕。线性时间的力量和他人的主体性此时都具象化地呈现在洛丽塔的肉身存在之中:一方面,洛丽塔年岁的增长和身体的成熟使得她已超出了亨伯特所定义的“小仙女”,这是岁月流逝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洛丽塔现在身怀另一个男人的孩子,她曾因奎尔蒂而逃离亨伯特,后来发现奎尔蒂对自己并无真情,她又自行离去,最后与年轻朴实的迪克相识并结合,过着普通夫妻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她遵照自己的意愿而行动的结果。
小说中两人的重聚是最具情感张力的场景之一,亨伯特痛心泣血般的内心独白不能说不令人感动,他写到,“我坚持要让这个世界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洛丽塔,这个洛丽塔,脸色苍白、已被玷污、还怀着别人的孩子的洛丽塔……仍然是我的洛丽塔……”,哪怕是到她人老珠黄、残花败柳之际,“只要一看到你那苍白亲切的脸、一听到你那年轻喧闹的声音,我仍会为你如痴如狂、柔情万般,我的洛丽塔。”[7]278然而,华丽的文字修辞下隐藏的不过是亨伯特人生幻灭时刻的最后挣扎,他拼命地想要说服这个世界——也说服自己——他曾将洛丽塔束缚在自己身边的那些时光是幸福真诚的。通过塑造可歌可泣的爱恋,亨伯特试图为自己过去这段妄诞且罪恶的人生抹上一层正面色彩和积极意义。在这个危机关头,亨伯特依然将最后一丝妄想系于他的汽车上,他恳求洛丽塔和他一起回到“那辆旧车”上去,他们“从此将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7]278无疑,亨伯特得到的是洛丽塔斩钉截铁的拒绝。当亨伯特最后一次哀求洛丽塔时,他的话语已变得嗫嚅:“你真的很确定——嗯,不是明天,当然,也不是后天,但是——嗯——将来有一天,随便哪一天,你不会来和我一起生活吗?”[7]280问话中“劝诱性的‘随便哪一天’和三个‘不’字”,暴露出提问者本身就已预设了一个“否定的答案”。[15]亨伯特的幻灭在此刻已是无处遁形,他过去几年间独占洛丽塔的所有“努力”在这一刻全都化作幻影,眼前的现实也直白地宣告着他把对永恒的渴望强加在现实世界中这一尝试的荒谬与徒劳。
小说结尾处,亨伯特杀死了奎尔蒂。评论家们常将奎尔蒂解读为亨伯特的二重身,认为“这两个角色本质上是极为相似对应的,是硬币的两面”[16],亨伯特对他这个“兄弟”的谋杀既是一种隐喻性的自我惩戒,也是“将罪恶投射到奎尔蒂身上以逃脱自我谴责”[17]的手段。不过,亨伯特对奎尔蒂的恨意显然也能被解读为一种报复和发泄。可以说,在这一谋杀行动中,亨伯特完成了他对时间和他人主体性的一种象征意义上的报复。通过杀死奎尔蒂,亨伯特一方面亲手创造了时间所能带来的终极威胁——死亡,另一方面也在单个的个体身上象征性地消灭了他人的主体性。亨伯特谋杀奎尔蒂时的情形——楼上楼下的追逐、摔跤和翻滚、突然的钢琴弹奏、激烈的长篇对话、高声的诗歌诵读、一连串打中却无效的子弹等等——所有这些荒谬离奇的事件呈现出一个超现实的谋杀场景,它们也正是亨伯特施行他那高度戏剧化的复仇仪式的一部分。
亨伯特的种种矫饰姿态下隐藏的是他的绝望和穷途末路。杀死奎尔蒂后,亨伯特开着他的那辆旧车一路逆行、飙车、闯红灯,并称这是最接近“消除基本物理定律”的行为,是“一种精神上的瘙痒”。[7]306这意味着他已彻底放弃挣扎,走向毁灭的漩涡。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此前所仰仗的动力,永远无法将他带到他欲想的目的地,因为那个地点仅存在于他自欺欺人的幻想世界中。如果说在这终局的灰暗里还有任何一点光亮,那便是他迟来的领悟和忏悔。在停车等待警察到来的片刻,亨伯特回想起他曾有次听到山崖下的小镇上传来的“孩子们嬉戏玩耍的悦耳声音”,在那片“既恢宏又微弱、既遥远又魔法般贴近、既直白又天赐般神秘”的混音中他辨认出了“清晰而生动的笑声、棒球拍的噼啪声或玩具火车的哐啷声”,那一刻他终于“明白那令人绝望痛楚的事并不是洛丽塔不在自己身边,而是她的声音不在那片和音里面”[7]308。亨伯特“在此处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偷走了洛丽塔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青春”[18]。洛丽塔原本也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在那片嘈杂又和谐的人间旋律中,过着普通但安定的生活。然而,亨伯特的忏悔来得太晚了,洛丽塔的青春已逝,她的一生也由此改写,奎尔蒂的生命已无法挽回,而亨伯特自己几十年来生存的意义也已然倾覆了。
结语
《洛丽塔》中的水域和汽车两个意象,是透视亨伯特毁灭性命运的注解。水域指向亨伯特投射在现实中的女孩洛丽塔身上的超验渴望,汽车象征着他试图通过占有洛丽塔来将超验想象拽入现实之中的盲目行动。在线性时间和他人主体性的客观现实下,亨伯特的妄念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他的悲剧根植于他对超越死亡限制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和他试图跨越艺术领域与物理世界之间鸿沟的行径,闪烁着一种普遍性的人类悲剧底色,是人的经验存在与超验渴望之间永恒冲突的缩影。
这种超验渴望也正是艺术家创作的激情和动力之所在,伟大的艺术也正是因此而能给困在线性时间和物质皮囊之中的人类带来一丝抚慰。亨伯特对永恒世界的渴望,实际上是纳博科夫笔下所有艺术家式角色所关涉的一个核心议题,也应和着纳博科夫本人的艺术家人格中拒斥线性时间、体验“没有时间意识”带来的“狂喜”、享受“和太阳、岩石融为一体”的“真空”[19]的性情与追求,正如菲利斯·罗斯所言,“抵达理想化的世界,超越‘平凡现实’中的庸常和有涯,是纳博科夫所有的小说人物及他本人所共有的一种激情”[17]。不过,望向永恒的艺术追求其前提是要对现实世界抱有清醒的认识,只有承认人类的境遇,接纳生命的有限,才有可能在有限与不朽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抵达艺术的彼岸;而盲目拒斥现实、试图消弭艺术与现实的界限,最终只能是像亨伯特一样堕入癫狂,招致毁灭。
纳博科夫曾写道:“有创造力的作家必须仔细研究他的对手——包括全能的上帝——的作品。他不仅要具备与生俱来的重组能力,还要具备与生俱来的改造既定世界的能力。为了充分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应该认清既定世界。”[20]纳博科夫对于艺术创作的这一意见,体现出他清醒的现实认知和强烈的艺术自觉,也折射出他的艺术与亨伯特的“艺术”之间的区分:亨伯特正是那种充满想象力、但拒绝直面“既定世界”的艺术家,他不是在“改造既定世界”,而是在扭曲它,他妄图将自己的想象引入现实领域中,以至最终摧毁了自己和他人的人生。小说通过亨伯特的悲剧,从侧面展现出这种偏执、妄诞的艺术立场所蕴含的致命危险,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纳博科夫对艺术创作作出的一记生动点评。
——《洛丽塔》的叙事心理学解读
——论《洛丽塔》中亨伯特的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