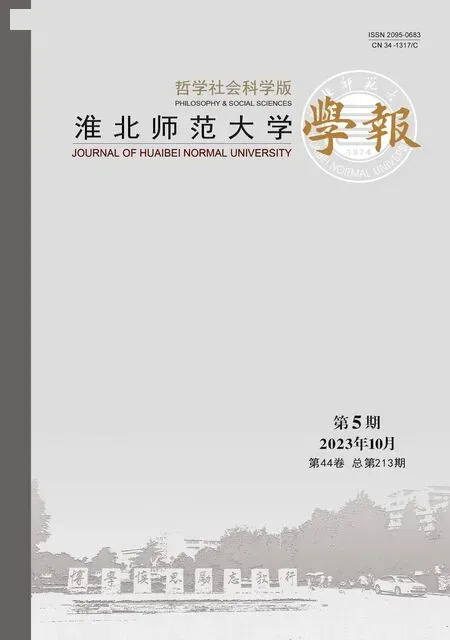《左传》“春秋笔法”的罪郑叙事
李建明
(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福建 漳州 363105 )
《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其思想倾向一般不通过议论性文辞来体现,而是在史事的简略记述中显示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又称“微言大义”,从《春秋》的一些用词和叙述中可以体会到这种微言大义。而在“以礼解经”的《左传》中,一些人物的生平记叙更能体现这种书法。
《左传》开篇到齐桓公称霸之前,郑国在历史舞台上频频亮相,几乎主导着重大历史事件的进程。有的学者因此认为郑庄公是齐桓公晋文公之前的霸主,比如朱东润先生编选的《左传选》,第一篇就是《郑庄小霸》。郑庄公确实让郑国迅速崛起。不过,反复细读《左传》文本,可以发现,《左传》这样写的目的是为了突出郑国是削弱周天子权威的罪魁祸首,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是由郑庄公开启的。
一、郑庄公的无亲叙事
《左传》一开篇就有“郑伯克段于鄢”,写的是郑庄公与弟弟共叔段兄弟阋于墙的故事。“庄公寤生,惊姜氏,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姜氏厌恶郑庄公,是因为出生时难产,而对另一个儿子共叔段,又极其溺爱。对此金圣叹评点道:“庄公寤生,便名为寤生;段居京城,便谓之京城大叔。只两人称为相形处,便极其不堪。有才口妇人,实实有此事。当时亦只是摇弄唇舌,后来便成极大是非,可恨可痛!庄公闻呼其寤生,哪不恼?后又闻呼段为京城大叔?哪有不恼?姜氏之为祸首如此。”[1]8姜氏此举不仅愚蠢而且顽固。《左传》的叙述者对她很厌恶。在隐公元年特意提醒:“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周幽王的王后本来是申侯的女儿,生了儿子宜臼被立为太子。后来周幽王宠爱褒姒,就立褒姒为皇后,褒姒的儿子伯服就被立为太子。申后和宜臼被废以后逃回娘家申国。申侯违背周礼,联络犬戎发动政变。这在《竹书纪年》中有记载:“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九年,申侯聘西戎及缯。”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等攻克镐京,杀了周幽王和太子伯服,褒姒下落不明。周幽王时年二十四岁。十岁的宜臼被申侯拥立为王,即周平王。这场联合外族篡弑的主谋是申侯,西周由此灭亡。西周首都镐京成为一片废墟。《诗经·王风·黍离》即表达了这种亡国之痛:“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镐京的灾难,在西周就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浩劫,文武成康之庙化为灰烬,长出了禾苗。毛诗云:“《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2]344诗中表现了一个神志恍惚、哽咽不已的亡国者形象。这是西周空前的劫难,由于事关周平王弑父篡权,只能为尊者讳,隐去这段伤心史。但是《左传》在写郑庄公时,还是点出他的母亲是出自申国,让人们去联想申侯和他女儿的所作所为。如果说申侯与周平王的母亲毁灭了西周,那么,申侯的另一个女儿则导致骨肉相残。她讨厌寤生,居然多次请求郑武公立段为太子。好在郑武公鉴于历史,没有违背周人的嫡长子制度,没有同意姜氏的非分要求。对此金圣叹一针见血地指出:“须知‘爱共叔段,欲立之’七个字,反面便是‘废庄公,而杀之’六个字。读书人须要眼光穿出纸背,只为此等句。易储大事,只为小小爱憎起,妇人胡可复与语!”[1]8如果郑武公耳朵软,听信姜氏的挑拨,郑国就会变成第二个成周。
问题是姜氏没有从此醒悟,郑武公去世后,寤生即位为郑庄公。姜氏作为母亲,非但没有为寤生分忧,反而把郑武公去世看成是为小儿子捞好处的机会。她立即为段请制。从行文可以感到姜氏的盛气凌人。姜氏为什么会这种态度,主要是欺负郑庄公年龄小。根据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二《郑世家》的记载,郑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请公,欲立段为太子,公弗听。是岁,武公卒,寤生立,是为庄公。”[3]1759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出,郑庄公即位时才十三岁,弟弟段十岁。而且可以看出,一直到丈夫咽气前,姜氏还在大搞废长立幼的勾当,应该说,武姜如此对待寤生是极不公平的,这导致了寤生从小学会了恨。所以当姜氏颐指气使地要郑庄公把制地给段时,才十三岁的郑庄公回答道:“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金圣叹对此评点道:“兄代有国,弟得食邑,足矣,何必有择而请。且兄代有国,弟得食邑,分也,何必代为之请哉?姜氏代为之请者,必欲得制故也。必欲得制者,据其要害,以便图庄公也。咄咄老妪,那复可堪!庄公才即位,姜氏便请制,写出老妪眼光射定,刻不能待。姜氏才请制,公便接口,将‘制’一顿,写出孽子机警迅疾,狭路不容。”[1]8“制”地势险要,是军事重镇,盘踞制地,占领郑国就如探囊取物。姜氏用心险恶,她太小看了郑庄公,要知道在仇恨长大的孩子心眼特别多,因此没有上他母亲的当。姜氏退而求其次,要了京邑这个富饶的地方。并且称段为京城大叔。姜氏对郑庄公心怀叵测的一系列行为,导致庄公对她也只有恨和提防。
太叔段住在京邑逐渐羽翼丰满,生得孔武有力。《诗经·郑风·叔于田》和《大叔于田》,按照《毛诗注疏》,都是写他的。虽然现代有的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但是证据不足,我还是取《毛诗》说法。
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无饮酒。岂无饮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适野,巷无服马。岂无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特指太叔段,《毛诗序》云:“《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国人说而归之。”[2]388段年轻英武,人们崇拜他,他极容易滋生出野心。还有一首《大叔于田》:
大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袒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戒其伤女。
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在薮,火烈具扬。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纵送忌。
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薮,火烈具阜。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
《毛诗》云:“《大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孔颖达正义:“叔负才恃众,必为乱阶,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经陈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袒裼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举,是得众也。”[2]390太叔段孔武有力,又得到京邑人民的拥戴,这对庄公是一个威胁。金圣叹认为这两首诗是写共叔段打猎之事,哀太叔之冤。并说:“孔子于《春秋》,既书郑伯克段之文;于《诗》,复留国人爱段之咏,然后知圣人之恶郑伯,盖有如此之甚。援两经以明太叔之不反,而太叔之冤大白。白太叔之冤者,非欲反狱庄公;吾亦深恶姜氏之生二子而不能养,而无端参差,几杀其一,为万世之鉴戒也。孔子之恶郑伯,恶其无以长一国也;吾之恶姜氏,恶其无以长一家也。”[1]12-13金圣叹认为太叔段是被冤枉,可以再探讨,但是他对《左传》的书法理解确实比一般人要透彻。《左传》对于郑庄公是深恶痛绝的,这从他与臣下议论太叔段可以感觉到,这确实是一个阴险的人。
从郑庄公继位到共叔段外逃,这中间经历了二十二年,从此中可以看出郑庄公对弟弟算计的蓄谋已久,连身边的亲近大臣都不知道他的心机。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面对身边的谋臣祭仲的提醒,他先是怪罪于姜氏,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等到祭仲再一次提醒他,他才说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话,与上文“虢叔死焉”相照应,并且表明是自找死地,不是他干的。真是老谋深算又毒辣。因为这时我们才明白,郑庄公有意养共叔段之骄,纵共叔段之欲,让他自我膨胀,达到自我毁灭的地步。这是他设下的陷阱。
“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面对共叔段的肆无忌惮,郑庄公表现得无动于衷,甚至公子子封说出“欲与大叔,臣请事之”之类的话来激他,他都无动于衷,他深藏不露,等待时机。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一举击破共叔段的密谋。而《左传》在此时居然发表了一段评论,这在叙事学上称为“叙事干预”: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所谓“郑志”,是指郑庄公之志——杀段。林云铭《古文析义》分析道:“然则庄公何以必杀之而后快?盖庄公猜刻残忍之人也。前此立段之请,出于姜氏,其怨母甚于怨弟久矣。请制、请京,弓影之疑,都认作有心轧己。因思不陷段于恶,必不能及其母而快其私。故祭仲之说行,犹可以全兄弟之义也,而公弗顾。子封之说行,犹可以全母子之恩也,而公弗欲。直伺修战守之备,有涉于篡夺形迹,毋论袭郑不袭,有期无期;只消用两个将字,一个“闻”字,便把夫人一齐拖入浑水中,无可解救。此公之志也。”[4]27林云铭洞烛其奸。“郑志”二字是全文的主脑。既然庄公志在杀段,因此共叔段逃跑以后,他终于可以对付姜氏了。“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几十年的怨毒终于喷涌而出。“既而悔之”,表现了郑庄公快意报复后一点悔意,犹如冰冷的寒夜中的一粒闪烁的灯火,在颍考叔的开导下,又上演了一幅“阙地及泉,遂而相见”的闹剧,“遂为母子如初”。《左传》的叙述到此没有停止,又加了一段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这一段看上去是在赞颂,其实不然。颍考叔的纯孝,正反衬出庄公的不孝。汪基的《古文喈凤新编》中对此评论十分精彩:“郑庄之恶,固在志于杀弟,尤在忍于绝母。故始纵弟以甚其罪,所以彰其母爱之非。后直置母,而重其誓,正以泄其恶己之恨。虽得考叔引之于道,以成其悔,究未闻释弟之罪,以慰母心,庄诚伦教之罪人哉!《春秋》书法,犹但在兄弟著而不悌。《传》更于母子着意,使人自得其不孝之实于行墨间。左氏真得素王心法,不愧称为功臣。”[4]31从书写技法上揭示主旨,暴露出郑庄公的伪善与丑恶。
二、郑庄公的无君叙事
郑庄公在家中对弟弟和母亲充满了仇恨,对于国君,则展现了他的狼野之心。《左传》隐公三年记载了周郑始恶一事。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5]27
周平王是郑庄公的君主,而且年龄也比郑庄公大许多,本来周平王用谁为卿士,这岂能容许郑庄公插话,可是郑庄公却为此质问平王,平王吓得矢口否认。由此可知郑庄公的气焰嚣张。郑庄公视周为敌国,公然挑战周天子的权威,首先破坏周礼规范。所以吴闿生在《左传微》中云:“周纲之坠,郑伯罪之首也。曰‘周郑交质’‘周郑交恶’,其伤之至矣。”[6]当代有学者为郑庄公的无君辩护,说周天子不顾念郑桓公开国元勋的功业,打压郑庄公,过河拆桥也不对。
那么,郑桓公是一片丹心报天子的忠臣吗?
郑庄公的爷爷郑桓公友,是“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幽王以为司徒”,“二岁,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3]1759。后来,冯梦龙在写《东周列国志》时,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郑伯友的英武和忠义。正因为如此,郑伯友的儿子掘突继续在朝中与德高望重的卫武公同为平王卿士,到郑庄公,已经连续三代都是周平王的辅政大臣了。为什么平王要撤换郑庄公呢?
郑国祖孙三代并非三代忠良之士,而早在郑武公时候,周平王就对郑国充满了恼恨。
郑桓公友虽然与周幽王共生死,但是他在西周灭亡前,就开始为自己谋私利。
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3]1758
司马迁这段话来自《国语》卷十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替》,《国语》里面说得更露骨:“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7]郑国借来了虢、郐的土地,很快就露出狰狞的面目,据《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记载:“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豪杰、良臣、辨智、果敢之士,尽与其姓名,择郐之良田赂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场郭门之外而埋之,衅之以鸡貑,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而尽杀其良臣,桓公袭郐,遂取之。”[8]653用这种诡诈的方法取得了郐国的大片土地,并在那儿发展成为“新郑”,为以后扩张打下了基础。
西周灭亡后,经过一番周折,周平王来到东都洛阳,本来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周平王此时还小,加上是弑父上位,底气不足,在他看来是到了郑武公的地盘,因此,对郑武公的行为不会有什么节制。而郑武公作为平王的卿士,更加有恃无恐地利用职权发展自己的力量。周平王二年(公元前769年),郑武公继承他老爹遗志,一举灭掉了借给他们土地的郐国。又过了两年(公元前767年),郑武公灭了东虢国,虢叔死在首都制。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借给郑国土地,而且都是姬姓。行如此悖礼之事,周平王非但没有惩罚他,而且把制赐给了郑国。公元前764 年,郑武公又灭掉胡国,且手段卑劣,据《韩非子·说难》载: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8]266
为了得到土地,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幸福,这不仅是一种无耻的政治权谋,更是一种人性的沦丧。
郑武公在频频得手的时候,国力迅速提升,营造都城新郑,据考古发现,新郑城墙的周长四十五里,而周天子的都城洛周长也只有九里。这是明目张胆地僭越,真不知道周平王如何咽得下这口恶气。
好在郑武公终于死了,于是平王想趁郑庄公年轻时拿下他的权位,给虢公。哪知郑庄公根本不把平王放在眼里,还气势汹汹地对平王问罪,而平王居然在郑庄公面前软了下来。为了平息郑庄公的怒气,周平王居然提出了互换人质,这样,周天子与郑庄公变成了地位同等的诸侯,这是周王朝有史以来的莫大耻辱。本来,郑庄公应该推辞或者谢罪,怎么能如此目无尊长呢?也许周平王只是放低身段,做出一个姿态。可是,他没有料到郑庄公居然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周平王低估了这位奸雄。
公元前720 年,周平王驾崩,而王子狐在周平王之前已经去世,于是王孙林登基,史称周桓王。周桓王一登基就任命虢叔为卿士,做了周平王想做没有敢做的事情,确实表现了一种英气。气急败坏的郑庄公就在当年春天割了周王室的麦子,秋天又把成周的稻子也抢了。郑庄公以一种地痞无赖式的方式恶心周天子。
《左传》忍不住来一段议论。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温、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繁》、《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5]27-28
这一段话责备平王不能以礼驾驭臣下,以至为祸惨烈。本来“周郑交恶”全是郑庄公无礼,但是郑庄公这样一个无君且穷凶极恶的棍徒,不值得让君子责备。这是《春秋》责备贤者、皮里阳秋的一种写法。
郑庄公割了成周的麦子和稻子,不会就此打住。过了几年,隐公六年(717),据《左传》记载:“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这是周、郑交恶以来,郑庄公第一次朝见天子。这是否意味着他从此洗心革面呢?不是。因为郑国结怨于陈国,而陈国与周天子比较亲近,他怕周天子来讨伐他,所以朝见周天子缓和一下。“王不礼焉”,周桓王对他不予理睬,周公黑肩劝谏周桓王不要这样,周桓王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因为周桓王伤其父以质郑死,且见郑伯久专朝政,心中疑惧。隐公八年(715),郑庄公与齐国一起如朝见王,这次周天子以礼相待,还任命郑庄公为王左卿士。郑庄公得到这个官职后,就公报私仇,宋国与郑国曾经有过“东门之役”,于是,在隐公九年,以宋国不来朝见天子为由,就“以王命讨之,伐宋”,没有捞到便宜,第二年,郑庄公就联合鲁国和齐国,终于打败了宋国,并把侵占的宋国土地全都给了鲁国。《左传》再一次出现君子对郑庄公的评价:“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5]69《左传》是不是真的在称赞郑庄公改邪归正呢?且不说郑庄公打着“以王命讨不庭”的旗号,开启了齐桓公“尊王攘夷”的称霸思路,就郑庄公不贪土地这一点,让人怀疑。原来,郑庄公的目标一是讨好鲁国,好得到“许田”,二是想灭掉许国。在打败了宋国以后,郑庄公以许国不来帮助他们这支“以王命讨不庭”的正义之师为由,继续联合鲁国和齐国一举灭掉了许国。郑伯攻打许国的真正原因是许国靠近郑国,想吞并许国。打下许国后,齐国人想把许国送给鲁隐公。鲁隐公说:“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国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5]74鲁隐公反对灭掉许国。由于鲁国和齐国都不想要,于是就把许国的“战后重建”的事宜给了郑。为了掩人耳目,郑伯没有直接把许国吞并,而是让许国的大夫百里侍奉许庄公的弟弟许叔居住在许国国都的东边,并且还装模装样地说:“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岂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无滋他族实逼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5]74-75郑庄公以兄弟失和为据,表明自己对许国没有野心,但是一个对亲兄弟都敢于严惩的国君,为什么会对一个异姓人仁慈呢?说了这番充满安抚和恫吓的言语后,接下来就剥夺了许国的自主权。他派公孙获驻扎在许国国都的西边,明明是监视许国,却堂而皇之地要公孙获不要与许国相争。他知道一时不能吞掉许国,因此满是退让之词。《左传》再一次让君子来评价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5]76言下之意是郑庄公一生无礼,只有这次可以称得上知礼。《礼记》中把是否知礼作为区别人与禽兽的唯一标志。换言之,郑庄公是一个禽兽,这也是《左传》在“周郑交质”中不责郑庄公却责备周平王的原因所在。因为人怎么能与禽兽去计较呢?
郑庄公暂时控制许国后,就与鲁桓公做交易。要用周天子的“祊地”(《公羊传》作“邴”)来换取鲁国的“许田”。郑庄公在隐公八年就想以泰山的祊地换许田。鲁隐公没有同意。这是符合礼的。公元前711年,郑庄公给鲁桓公送去了白壁一双,生意成交了。这是周天子不能容忍的。郑庄公为什么念念不忘许田,这就要了解一下“许田”。关于这一点,杨树达《春秋大义述》中解释:“桓公易周田,讳而系之许。”并引《公羊传》:“许田者何?鲁朝宿之邑也。诸侯时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鲁朝宿之邑也,则曷为谓之许田?讳取周田也。讳取周田则曷为谓之许田?系之许也。曷为系之许?近许也。”[9]“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许田与祊地一样,也是属于周天子的,因为“许田”距离许国和郑国都比较近,郑庄公有了这块土地,就可以继续扩张。郑庄公的行为严重违背周礼。何休的《公羊传》中直言“郑伯无尊事天子之心,专以汤沐邑归鲁,背叛当诛也”[10]。郑庄公,又一次突破底线,周桓王盛怒之下褫夺了他的卿士一职,郑伯从此就不去觐见周天子。周桓王想起以前的郑伯割麦子等恶心事情,于是,周桓王纠集诸侯讨伐郑国。《左传》桓公五年记载:
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
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5]106
郑国部署周密,郑伯早就等周天子送上门来。这在《东周列国志》中有更详细的描写,可以参看。在射王中肩后,虽然郑伯假惺惺地派人慰问周天子,但是,周天子的颜面从此扫地,“礼崩乐坏”的时代正式拉开帷幕。而导演就是这个是无君的郑伯。
三、《左传》对郑伯自身招来的恶果的叙事
《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可见其无亲;《周郑交质》,揭露他的无君。无君无亲的人,就是一个最无礼的衣冠禽兽,他的所作所为,必然会得到报应。
《左传》书写了郑伯朝中奸邪横行。《诗经·郑风·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这首诗的主旨,《毛传》认为是“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焉。”孔颖达疏云:“作《羔裘》诗者,刺朝也。以庄公之朝无正直之臣,故作此诗,道古之在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风刺其今朝廷之人焉。经之所陈,皆古今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朝无贤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也。”[2]402诗歌描写了羊皮袍子质地如何鲜艳漂亮,借以赞美穿这种润滑光亮的衣服的官员有正直威武的品质气度,是国家的栋梁。可是,一联系到郑国的现实,满朝穿着漂亮官服的人,有什么节操和贤良呢?
这是有事实依据的。《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辀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颍考叔能够感化郑庄公与母亲和好,却为了争一车而死于子都之射。因此,张昆崖在《左传评林》中感叹道:“能舍肉而不能舍车,能化庄公而不能化子都,何其孝匮而类,有所不能赐也。”清初大散文家魏禧在《左传经世钞》中说:“考叔位卑,而与大夫争车,故子都逐且怒之耶?”[4]108在争车这件事情上,颍考叔没有表现出一种谦让的君子之风,但是子都居然在颍考叔登上城墙时,射死颍考叔,则更可恨。而作为一国之君的郑伯处理此事更有趣:“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颍考叔死于非命,他佯装不知,并且作掩耳盗铃之计,这是郑伯的伎俩。
朝中缺少正人君子,他的后人也乏善可陈,《左传》比较细致地写了郑伯子孙的衰亡。
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 年)夏,郑庄公去世,太子忽即位,是为昭公。不过他只做了几个月就逃走了。几年前,齐僖公想要把自己的女儿文姜嫁给太子忽,文姜,就是那个与哥哥齐襄公姜诸儿乱伦的那位女子,被太子忽推辞。太子忽解释道:“人各有耦,齐大,非我耦也。”文姜后来嫁给鲁桓公,不守妇道,太子忽不娶文姜确实明智。以后他又一次拒绝齐僖公的另一个女儿,则让人遗憾。鲁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北戎进攻齐国,齐僖公向郑国求援,太子忽帅兵救齐,大败戎师,齐僖公又一次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太子忽又一次推却道:“无事于齐,吾尤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昏也。民其谓我何?”表现了一种侠义之道。当时祭仲劝谏道:“必取之。君多内宠,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三公子指公子突、公子亹、公子仪。其中公子突很得郑庄公的欢心,公子突是宋国大贵族雍氏的女儿所生,加上宋庄公在作为公子的时候曾经逃难在郑国。郑伯与宋庄公十分要好。要不是祭仲反对,郑庄公差点就传位于他。太子忽这次拒婚,郑人作《有女同车》,《毛传》云:“《有女同车》,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婚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2]410这是有事实依据的。郑伯去世后,公子突加紧了行动。
宋雍氏女于郑庄公,曰雍姞,生厉公。雍氏宗,有宠于宋庄公,故诱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厉公而求赂焉。祭仲与宋人盟,以厉公归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卫。己亥,厉公立。[5]132
公子突阴沉暴戾,做了几年国君,觉得不太惬意。《左传》桓公十五年记载道:
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夏,厉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5]143
郑昭公回来当上国君三年,被高渠弥暗杀。《左传》桓公十七年载:“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5]150昭公在位三年,不能去其所恶之人,结果反而招来杀身之祸。第二年,公子亹去参加齐襄公的婚礼,祭仲劝他不要去,公子亹还是去了齐国,公子亹因为与齐襄公的私人恩怨,被齐襄公所杀。于是,祭仲立公子仪为君,在位十四年,史称“郑子”。鲁庄公十四年(680),郑国的顶梁柱祭仲去世,远在郑国边境栎邑的郑厉公在宋国的支持下,立即杀回郑国。郑子派傅瑕迎敌,傅瑕被郑厉公俘虏,表示愿意归顺郑厉公,并表示放他回去,他就做内应。郑厉公放傅瑕回去,傅瑕回去不仅杀了郑子,连郑子的两个儿子也一并杀了,于是,他打开国都大门迎接郑厉公。《左传》在此时追叙了一件事情:“初,内蛇与外蛇斗于正南门中,内蛇死。”然后再插叙:“六年而厉公入。”随后夹叙鲁庄公的君臣对话:
公闻之,问于申繻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
所谓的妖,是由于公子仪太过于惧怕郑厉公而招致。公子突,是君之妖,傅瑕,就是人臣中的妖怪。
郑厉公一直流浪在外,最后回来做了国君,也没有给公子亹、公子仪追封谥号。对于活着的人,他决不原谅那些有二心的臣子。
厉公入,遂杀傅瑕。使谓原繁曰:“傅瑕贰,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吾愿与伯父图之。且寡人出,伯父无里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贰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臣闻命矣。”乃缢而死。[5]198
郑厉公杀傅瑕可以理解,怨恨伯父,致使伯父自杀,这就显得暴戾无常。接着,郑厉公又治理“雍纠之乱者”,杀祭仲的党羽。郑厉公从此坐稳了大位,但是从祭仲被宋人要挟立公子突开始,四个公子争夺君位,致使郑国元气大伤,郑国从此一蹶不振。郑厉公弟兄们的举动酷似当年郑庄公对付弟弟共叔段。郑庄公的儿子们的内耗,让郑国的有识之士痛心不已,于是作《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闉阇,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藘,聊可与娱。
关于此诗,如果不明白背景,是很容易看成爱情诗的,但是《毛传》云:“《出其东门》,闵乱也。公子五争,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孔颖达疏:“作《出其东门》诗者,闵乱也,以忽立之后,公子五度争国,兵革不得休息,下民穷困,男女相弃,民人迫于兵革,室家相离,思得保其室家也。”[2]440这种解释是可信的,当然有的学者更认为“出其东门,有女如云”是比喻郑国国君之多,“虽则如云,匪我思存”,意思是国君虽多,但是没有一个像样的。这种解释也能自圆其说,总之,这首诗是针对郑庄公的四个儿子争夺君位而作。郑国一片狼藉,而齐国、晋国、楚国、秦国正在崛起。郑国的内乱的起源则在于郑庄公的无亲无君的无礼之举。所以《春秋》隐公元年特意书“郑伯克段于鄢”,其实,就是把礼崩乐坏的始作俑者,归到郑伯身上。
左丘明对“春秋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成公十四年》)《春秋左传》通过材料筛选、细节描写、词汇选取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的主观看法。这在对于郑庄公的书写上,极其精彩。研读关于郑庄公的故事,可以更加深入体会所谓“春秋笔法”,这不仅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而且也是一种文章写法,寓褒贬于曲笔之中,体现了《左传》以礼解经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