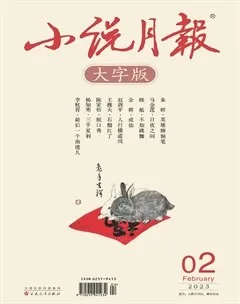最后一个渔佬儿
太阳落山的当儿,福奎想起该去收一趟滚钓了。他猫起身子拱出船棚,站到堤坡上,野狗觅食似的有所期望地嗅着那带点咸味的江风,仿佛凭他这只闪闪发光的像是刚刷上了油漆的鼻子便晓得有没有大鱼上钩。
他的船棚搭在堤岸下一条小水沟上,远远望去像座坟墓。这儿的死人没有被埋到地底下的。坟地上是一座座齐腰高的青砖小屋,盖着瓦片,还开了小窗,考究得叫活人都羡慕。福奎的船棚是茅草苫的。他穷得恐怕死后也住不上那样的屋子,只配缩在草窝里升天。
当然这会儿他离死还远。他精壮得像一只硬邦邦的老甲鱼,五十岁了,却还有小伙子们那种荒唐劲头,还能凭这点劲头搞上个把不大规矩的婆娘。他的赭红色的宽得像一扇橱门似的脊背,暴起一棱棱筋肉,像是木匠没把门板刨平;在他的右边肩胛骨下,那块暗红色的疤痕又恰似这橱门的拉手。这块伤疤是早先跟人家抢网干起仗来,被对方用篙子上的矛头戳的。
福奎提了一只盛满蚯蚓的甏子,朝沙滩尽头的江边走去。他光着上身,只穿了条又肥又大还带点碎花的土布裤衩,走起来十分凉爽,跟光屁股一样滋味。他睡觉也总喜欢赤条条的。光着睡舒坦、爽气。这条裤衩是阿七给他的。那几年他是她守寡后的头一个相好。她本来会嫁给他的,只因为他太穷了,穷得连裤衩都问她讨,才没嫁成。
江水退潮了,他的船搁浅在远离水边的沙岸上。他那双光着的大脚扑哧扑哧地踏着松软的沙土。沙滩整整晒了一天,这会儿还有点烫哩。不过福奎的脚底板厚得像是请鞋匠给掌了两块皮子,已经不大能觉出冷暖了。他走到船旁,背起一根拴在船板窟窿里的繩索,把船拖下江里。
这条平底小船比福奎的个头儿大不多少,躺下身去,每每叫他想到这家伙做他的棺材倒挺合身的,再加个盖儿就成。
他荡开船去,在船尾躺下身来,摊开两条毛茸茸的粗腿,左右开弓,蹬起双桨。葛川江上的渔佬儿都会玩这套把戏,为的是能腾出手来下网、收钓。福奎熊掌似的大脚此刻比猫爪子还灵巧。他扯开那对蘑菇蛋似的脚拇指,勾住桨柄,两条腿一屈一伸,桨板一起一落……
夕阳像在江上撒了一把簇新的金币,江面金光耀眼。
船到江心了。离小船不远有一个毛竹罐:做的漆得红白相间的大浮筒,顺着水流往下数,一共有八个这样的浮筒,每个相隔三十多米,一溜排开。这就是福奎两个多钟头前布下的滚钓。他使劲蹬了几下船桨,靠向滚钓的第一个浮筒。
滚钓顺水布放,收钓也得顺头收起。在一条长几百米的只有单股电线那样粗细的尼龙绳的一端,拴着一块大石头,它沉在江底,以免滚钓漂走,凭借那些浮筒的浮力,尼龙绳从江底斜着升起,浮出水面;绳子每隔三五尺又系着一个猪尿泡做的小浮标,远看像一串水里冒起的气泡,浮标下垂着装有钓钩的尼龙鱼丝,长的有十多米,短的只有两三米,因为鱼群游来有深有浅,滚钓是专为钓大鱼的,它的钓钩比一般人在河里用钓竿钓鱼所用的钓钩要大得多,穿上蚯蚓,就像套上塑料软管的衣架钩子,鱼上钩的话,这只钓钩上的浮标就会沉入水里,渔佬儿凭这个便知道该收哪只钓钩,而别的空钓则不必牵动,假如上钩的是一条特别大的鲤鱼或者花鲢,它拼死挣扎,全部钓钩就会一齐向它滚来,它越是翻腾,钓钩便扎得越多。这就是滚钓的厉害。
可惜,这厉害家伙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了。葛川江的污染一年比一年严重,两岸的渔佬儿又只捕不养,眼下江里的鱼怕是还没对岸的西溪自由市场上搁着卖的鱼多,更别提什么大鱼了。
福奎的船顺着那一溜浮标往下漂着。有几个浮标半沉半浮,上下跳动。他收起几条不到半斤重的小鲳条子,心里很不痛快。为这么几条小玩意儿是犯不着下滚钓的。他撒一网也不止这点收获。这年头连鱼都变得鬼头鬼脑了,小鲳条子居然也潜下深水里去咬钩,并且居然也咬上了。福奎对此很不理解。他从钓钩上摘下小鱼,又在钩子上重新穿上了蚯蚓。
这时,福奎远远望见西岸船埠头走下一个穿得挺招眼的女人,她下到一条小舢板上,身子一扭一扭地朝他这边摇了过来。福奎眼力不错,老远就看清了这是阿七。他甚至能猜到她一准是到西岸找官法师傅去的。
西岸是省城滨洲的南郊,是个风景很好的疗养区,也是滨洲南郊最大的居民点。早些年,葛川江这段江面上少说有百把户渔佬儿,光他们小柴村就有七十来户,大都常年泊在西岸,一早一晚下江捕鱼,就近卖给西溪新村的居民;白天则补织渔网,修整滚钓。那日子过得真舒坦,江里有鱼,壶里有酒,船里的板铺上还有个大奶子大屁股的小媳妇,连她大声骂娘他都觉着甜溜溜的。那才叫过日子呢!而顶要紧的是,那时候,他柴福奎是个有脸面、有模样的汉子,受人敬重,自己也活得神气。西岸的居民们唯独对他不用“渔佬儿”这个带点轻蔑的称呼。他甚至还跟疗养院里养病的一位大首长交了朋友。那回官法师傅领来那位大首长到他船上挑了几条刚钓上的大鳜鱼,使得他有机会跟大首长一起喝喝老酒,拉拉家常。
官法师傅在疗养院当厨子,是小柴村人的本家。有这层关系,小柴村的渔佬儿常有用着他的地方,都拿他当大,打了鱼总给他送几条去。官法师傅吃鱼从不花钱,对此街坊们都羡慕不已。日子一长,自然有人求上门来,求官法师傅替他们牵线买鱼。官法师傅社会责任感很强,一向助人为乐,当然愿意为大家包揽鱼虾生意。起先,江里有的是鱼,足够供应所有的西岸居民,官法师傅的作用还不很突出,只是难得有一两回因为坏天气鱼打得少而有幸露一手。直到后来,鱼一年比一年少了,少得每天街口的鱼摊子刚摆起一根烟的工夫就得收摊了,这光景,官法师傅可大有作为了。他干脆取缔了街口的鱼摊子,叫渔佬儿们每天一早把鱼筐抬到他家里来,由他做主,该卖给谁和不卖给谁,甚至鱼价也由他定,仿佛他家就是国家的物价管理机构。久而久之,街坊们背地里给这位热心肠的大师傅起了个不大好听的外号——渔霸。
福奎和官法本是堂兄弟,早先十分要好。这两年,因为江里打不到鱼,小柴村的渔佬儿全都转业了,剩下他自己一个,偏偏又手气不好,官法也做不成“渔霸”了,他俩之间没啥生意上的来往,特别是阿七插了一杠子,从他的窝里爬到了官法的床上,弄得老哥儿俩见了面彼此都很不自在。官法像是有点歉意,他则觉着自己矮了一截。就这样,他俩渐渐疏远了。
阿七的船离他越来越近。他已经能看清她身上穿着的簇新的短袖衫的白底上那一个个深蓝色的圆点儿了。
前些日子,他听村里人说阿七常在对江官法那儿过夜,总有点将信将疑。阿七今年四十岁了,十年前她男人死在江里,此后她一直打算改嫁,却总没嫁成。她名声不好,村里人又总爱对她捕风捉影,那些糟踏她的话不大靠得住。今天,他可是亲眼看见她从西岸过来的,还打扮得这么招眼,她仿佛觉着自己还是个大姑娘似的……八成是这么回事。无风不起浪嘛。
福奎正想着,忽然觉出手上刚拎起的那根钓丝有点分量。没等他收上鱼来,靠近他船旁的阿七对他嘲笑起来:
“哟!福奎,”她指着他船里那堆小鲳条子,“好大的鱼呀,今儿你可发了!嘻嘻……”
福奎脸红起来,真后悔刚才忘了拿草帽把这堆鱼盖起来。对葛川江上的渔佬儿来说,钓这种小不点儿的鸡毛鱼,就像没本事的狗偷自家窝旁的绒毛小鸡填肚皮,实在是很丢脸的。特别是在这个女人面前。他低下头,迟疑地拎起手里那根钓丝,心里赌咒着,老天爷给点面子吧,这回可别再出洋相了……
“哟!鲥鱼!”阿七抢在他头里惊叫起来,激动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天哪!该不是龙王显灵,你时来运转了吧……我说福奎,好多年没听说这江里还有鲥鱼了,我都差不多把鲥鱼的样儿给忘了……真够瞧的!它少说有三斤重哩……这回可叫我说中了,今儿你可真是发了!”
“我脑子不糊涂。”福奎也得意起来,“你刚才是挖苦我来着。”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那是给你冲冲晦气呢!”
“你倒嘴巧……”
“可不是巧吗!我一来,你的手气也来了。我话还没说完,你就钓起了这家伙……福奎,别不知好歹。今儿还有我一份功劳哩。”
说着嘴的当儿,福奎收拾好钓钩,掉转船头,随阿七一起往回划了。滚钓还留在原处。还有几条咬上钩的鱼来不及收起来。葛川江上的渔佬儿有个迷信的说法,以为有了意外的收获就不该再往下收了,免得越收越不景气,把先前的手气全给败了。留着好手气下回用,福奎也信这话。
“这条鱼能卖十块钱呢,福奎。”
“我不卖。”
“不卖?”
“留着自家吃。”他这是真话。他至少有五年没打着过鲥鱼了。刚才钓上它的那一瞬间,他愣了一会儿,简直没敢认它。鲥鱼是葛川江里最名贵的鱼种,肉嫩、味鲜,眼下自由市场上起码能卖三块钱一斤。要是每天能打着这么一条鲥鱼,哪怕就一条,他倒真能发了。可惜呀,如今鲥鱼稀罕得很,几乎在葛川江里绝迹了。这家伙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不过有一点他是明白的:这也许是葛川江里最后一条鲥鱼了,就像他本人是这江上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最后一个渔佬儿享受最后一条鲥鱼,这倒是天经地义的。他相信自己有这个口福。这条鲥鱼他要留着自己独个儿吃了……也许,应该叫阿七也尝尝……瞧她这会儿馋的,像只猫儿似的……
福奎斜过眼盯着阿七那一扭一扭的屁股。她站着摇橹,舢板紧挨在他的船旁。他躺在船尾,还像先前一样用脚蹬桨。他的脑袋斜对着她的屁股。这娘儿们曾跟他一起过了八年。起先当然是偷偷摸摸的,她不敢留他过夜,因为她的宝子把她看得很紧。爹死那年,宝子已经懂事了。她只比宝子大十六岁,她当妈的时候真还是个小姑娘哩。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不愿在他眼皮子底下胡来。直到后来宝子娶了媳妇,小两口跟她分开过了,她的名声也臭开了,她才破罐子破摔,公然养汉了。约莫有一年光景,他俩每夜都一起睡,来往毫不避人,俨然是一对正经夫妻,就差在人家面前提起“我那口子”如何如何了。那时候,村里人都认可了他俩,都等着喝他俩的喜酒了。尽管是续娶、改嫁,酒总归要喝的。
“你老盯著我干吗?我没穿裤子吗?”
福奎把脸掉开了。不知怎么搞的,好像阿七对他施了什么妖术,弄得他这个半截入土的人还老想些不安分的念头。此刻,要不是隔着船,他真想把她按倒在地,拿拳头对着她说:嫁给我,阿七,别再跟官法鬼混了!我老了,一个人在江里打鱼太孤单了,咱俩做个伴吧……
可是话到嘴边他又改口了:“这阵子,官法……还好吧?”
“哟,你怎么晓得我今儿去找官法了?”
他支支吾吾地答不上话来。他觉出自己好像在吃醋。在他这年纪上,跟人吃醋总不大像话。你这老东西中了什么邪!他骂自己,没沾过女人吗?
“病是好些了,”阿七告诉他,“可心病难除啊!打从咱村的人都改行上岸种地,官法当不成‘渔霸了,他就没早先那么虎生生了,就跟吃不上奶的娃儿似的。早先官法在街坊们眼里不比他们的疗养院长官儿小多少,眼下可比臭狗屎还不如了……他常闹病,提早退休了。如今一个人闲在家,孤单单的,只好成天价灌黄汤,灌得脸孔越来越干巴,像块揩屁股的草纸,又黄又皱……有个娘儿们照顾他就好啰!”她停下手里的橹把,直起身子,迟迟疑疑地说,“福奎,有件事儿……该问你讨个话。”
“啥事儿?”他也收住脚,任小船自己漂着。
“宝子成家后,我也挺孤单的……官法要我跟他去做伴。”
他差点没嚷嚷起来:我不孤单吗!我也巴望有个娘儿们做做伴呀!……不过他马上想到,他能跟官法比吗?人家是国家的人,老来生活有着落,吃穿不愁,而他连个像样的窝都没有。
“这些年你待我不错,这事儿我不瞒你。”
“我不管。”福奎有点恼了,“你爱嫁谁嫁谁,我管不着!”
“你不用跟我翻脸!”阿七也火了,索性扔下橹把,两条胳膊往腰上一叉,像要跟他干仗似的,“凭良心说,我待你不薄。我三十守寡,等了你十年,别的不要,只指望你能攒些钱盖幢屋,日子过得像个人样儿。可你偏不听,偏逞强,充好汉,像守着你爹坟似的守在这江里,打那点小鸡毛鱼还不够一顿猫食。你倒撒泡尿照照你这穷模烂样的,连条裤衩都买不起,大白天穿姘头的裤衩,你也不觉着丢脸!你不听我的话,弄得越来越潦倒,还有脸跟我要态度……我可不能老给你当姘头!有本事,你盖幢屋,明媒正娶嘛!"
“你嫌我穷……”他有点委屈地说。
“嫌你穷又怎么的?你是自作自受!再说,眼下穷可不是桩光彩事儿,不比早些年了。我说福奎,人家能富,你怎么就富不了呢?有本事你也富富嘛!”她放下胳膊,重新操起橹把摇了起来,“说实在的,我可没受穷的瘾。我这辈子够苦的了,我得享点福了。跟着你睡草窝,喝西北风,我没这胃口。”福奎不再还嘴了,没精打采地蹬起桨来。天色越来越暗,江面上升起灰蒙蒙的水汽,像是整个天地都被洗去了颜色。
“你啥时候过去?”他问。
“快了。不过我走以前还想帮你一个忙。”她像是舍不得跟他分手似的,亲亲热热地看了他一眼,“福奎,你帮我拉扯过宝子,我忘不了你的情分。”
“别提这些了。”他刚才被她数落得垂头丧气,此刻心里才好受起来。阿七还记着早先的情分哩。
“我走了,公社味精厂就缺一个打杂的。我跟队长说了,他答应让你顶我的缺,只要你自己再找大贵求个情,这事儿就成了。到厂里干,活儿轻快,又有固定收入,比在这连根毛儿都不见的江里打鱼牢靠多了。听我的话没错,福奎!人老了,总得有个靠头。”
大贵是社管会委员,也是福奎的表外甥。不过福奎从没沾过他什么光。
船到岸了。顺着东溪往上,到小柴村还有三里路。阿七得摇着船回家。福奎因为夜里还要再收一趟滚钓,就把船划进了他的船棚。他拴好船,把那条鲥鱼和一逐小鲳条子统统扔进鱼篓,走上了东溪的堤坡。他步行,走得比阿七的船快,不一会儿就赶上她了。
“阿七,到了家,你也来尝尝鲥鱼。”
“好,我一定来。”她在水上应着,哧哧地笑着。
福奎加快步子。他得赶紧到家,把鱼烧好。鲥鱼最好清蒸,光搁几片葱叶就成。路过人家的菜园子,福奎顺手拔了几根小葱。他边走边理,掐成一截一截,握在手里。
小柴村紧贴在东溪的北岸,溪上有条新架的拱桥,过了桥便是公社所在地大柴村,眼下倒更像个镇子了。桥的两旁,河埠头那些木桩上拴着好多渔船,横七竖八的,像是躺了一地死人。多半的船都常年不用了,有的已经霉烂,有的散了架,有的船帮上长满了青苔和寄生螺,仿佛它们几百年前就被扔在这儿了。
福奎的手上鱼腥味很重,到家的时候,那把葱叶像是已经跟他的鱼煮开过了一样。他的家只是一座小草棚子,是拿竹片夹上麦草苫的。这地方瓦房叫“屋”,草房叫“舍”,而福奎的连“舍”都算不上,村里有些富足人家的猪圈都苫得比他的草舍考究。福奎好不费力地用肩膀撞开门板,呼的一声,门框往下一坠,险些碰着他脑袋。这扇门要关上可不容易。他扔下鱼篓,用脚使劲顶起那根蛀掉了底脚的门柱子,就势把门推上。他屋里没蚊帐,敞着门的话,夜里蚊子怕是会把他吃了。
时候不早了,鱼得赶紧剖洗。福奎坐在水缸旁的一块大橡树桩上,唰唰地刮着鱼。他的草屋只分两间,一间睡觉,这一间是灶间,连做带吃。除了吃饭、睡觉,他什么也不需要。灶间里堆满了杂物,破渔网挂得满墙都是,西边墙脚下长出了几簇带花点儿的蘑菇。一只胖得圆滚滚的大黑猫蹲在锅台上,不动声色地盯着福奎手上的大鱼。它在这儿常有鱼吃,而这户人家啥也没有,老鼠都不屑光顾,所以它清闲得很,享福得很。
一只蜘蛛从梁上吊下来,正好落在福奎的鼻尖上,怪痒痒的。他抹了一把,蜘蛛溜上去了,可是没等他把洗好的鱼放进锅里,那家伙又落下来了,在他脸上爬了一圈,仿佛对他这张黑不溜秋的老脸很感兴趣。
这当儿,外边忽然响起手扶拖拉机的突突声,越来越近,最后在他家门外停住了。来者是大贵,他的表外甥,一进门便像个大喇叭似的哇啦起来:“好哇,二舅,听阿七说您今儿钓上一条鲥鱼。好多年没吃到鲥鱼了。我那塘子里养不活鲥鱼。今儿借您的光,来尝尝。”
福奎很不情愿地把他让进屋来,心里一个劲地骂阿七嘴快。
“鱼蒸上了吗?”大贵坐到床上,朝灶间那边使劲抽了抽鼻子。
“不忙……先做饭。”福奎咕噜了一句,走进灶间,呆呆地盯着那条搁在大盘子里的鲥鱼。他不是小氣鬼,换作任何一个村里乡亲来跟他分享今日的口福,他都乐意,而偏偏对大贵,他一百个不情愿。他忘不了这个表外甥敲过他竹杠,敲得好狠啊!
那是前年春天的事儿。那回他倒霉透了。他的滚钓被不知哪条瞎了眼的轮船卷跑了,一个钓钩也没留下。他咒天骂地,把自己都骂糊涂了。等到脑袋清醒下来,他又得为钓钩犯愁。他跑了好多地方,却到处买不到他这号的钓钩。在大柴村,生产资料门市部的营业员告诉他,这号背时货早就不生产了,眼下葛川江的渔佬儿都上了岸,成了庄稼佬儿。人家不会专为他一个户头生产那玩意儿。“拉倒吧,老爹!”那营业员好心开导他,“如今的渔业生产讲究科学化、现代化。在江里下滚钓打鱼,这方法实在太原始了,何况这些年江水污染得厉害,鱼都死光了。你看人家大贵,承包个鱼塘,好生养着,塘里的鱼就跟下饺子似的,一伸手就能捞上几条。去年他赚了八千块,自家买起了拖拉机。你呢,老爹?”他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他也实在琢磨不了什么“科学”呀、“污染”呀、“原始”呀。这些让牛去琢磨,它们脑袋大。照他想来,江里的鱼跟果木树一样,也分大年小年,没准明年又多起来了呢。早先,他手气好的日子,一天能钓百八十斤,最大的,一条就能卖二十块钱。说不定挺过这几年,早先的好年景还会再来。就这样,他去找了大贵,因为他知道大贵手头有一副钢火很好的上等钓钩,八成新的,正经是十八里铺大老胡的手工货。“大老胡死了,三个儿子都进城当工人了,他们家的祖传手艺也就到此为止了。”大贵看了他一眼,好像在等他琢磨琢磨大老胡的死跟他有什么关系。“说真的,二舅,这兴许就是大老胡留下的最后一副钓钩了,我想留着当个纪念……您知道吗,往后这玩意儿值钱得很,没准能进博物馆呢……啥叫博物馆?啊,就是把七老八古的玩意儿统统堆在一幢房子里……啥?啧啧,您可真是土包子!打个比方说,要是您手头有一根姜太公用过的钓鱼竿,或者哪怕是托塔天王拉的一堆臭屎,您也能发大财了……当然,大老胡才死不久,这副钓钩还不能算是出土文物,比不上姜太公的钓鱼竿值钱,不过报纸上说,眼下外国人都肯花大钱收买这号断子绝孙的手工制品……说到头来,这副钓钩我得留着,除非……那回五喜拿六条大鲤子来换,我都没答应呢。”大贵最后那句话他听明白了。那以后两个月里,他一共给大贵送去了十条大鲤鱼,才算把那副钓钩换到了手。跟听生产资料门市部那个营业员的开导一样,大贵这番指点他也多半琢磨不了。博物馆、出土文物、外国人如何如何,这些都离他十万八千里。他能琢磨的,就是吃饭、睡觉、下滚钓,还有到时候叫人家敲一下竹杠……
葛川江的渔佬儿八辈子碰不上一桩了不得的大事儿,所以,没有比被人家当作孱头敲了竹杠更叫他们觉得丢脸的了。被人骗了耍了,还可以装傻,权当没觉出有这码事儿。可认了敲诈,你就没法装模作样了,因为敲诈总是明着来的。当一回傻子总比当一回孱头脸面上好受一些。
有过那样一回来往,今儿再让这龟孙吃他的鱼,喝他的酒,还给他看那副不吃白不吃的无赖相,这光景,福奎那点肚量可包涵不了。人家打你巴掌,你却弯下腰去亲他的屁股,这倒真够得上孱头了。
不过渔家从没有轰客人出门的道理。福奎揭开锅盖,为难地瞅着那条上面撒着些葱叶的鲥鱼。
黑猫跳上锅台,战战兢兢地凑近鱼碗。
“啥!你也想尝鲜?”他抓起老猫,想从窗口把它扔出去,可转念一想,反倒把鱼扔给了它。
今儿能帮他打发走大贵的,看来只有这畜生了。这倒也爽快!他宁肯自己也不尝。黑猫大口大口地撕咬着鲥鱼,仿佛福奎自己在撕咬着大贵。他兴奋得浑身打战。
他走进隔壁屋里。大贵问道:“鱼蒸上了吧,二舅?”
“屁!叫猫叼去了。”
“啥?”大贵像个炮仗似的蹦了起来,忽地冲进灶间,差点踩着饕餮而食的老猫。
“哎呀呀,该死的畜生!”他刚抬腿,那猫便倏地溜了,那鱼都被它撕烂了。“二舅,您怎么搞的……哎呀呀,太可惜了……这该死的猫,换作我的话,非把它宰了不可!”
无论如何,鱼是吃不成了。大贵没精打采地跟福奎闲扯了几句,败兴地走了。
福奎望着大贵的手扶拖拉机蹦蹦跳跳地开上了大桥,快活得哼起小曲儿来。不过他哼得不成调儿,倒更像哞哞的牛叫。
他把小鲳条子都洗了出来。等一会儿阿七来了,他只能拿这些来招待她了。小鲳条子味儿也不错,只是刺多了些。他把盛了鱼的盘子放进了锅里,坐到灶膛跟前,点着了柴火。
火烧得不旺。他慢腾腾地往里添柴,一边等着阿七,一边想着心事。
等到了九点多钟,还不见阿七的影儿。她说好要来的,怎么能变卦呢?
他等不及了。今晚还得去江里收一趟滚钓。他匆匆吃下凉饭,提着马灯出了家门。
村子里好多人家在乘凉,有说有笑,还有广播喇叭里缠缠绵绵的越剧,不时地被一阵阵狗叫淹没。从江那边吹来咸丝丝的夜风,吹得福奎破褂子底下的整个身子舒爽极了,像一只娘儿们的小手在轻轻摩挲着他。
这娘儿们正在前头等他。从他家往江边去,要经过阿七的小屋。尽管夜里很黑,她还是老远便认出了他像头公牛的身影。
“你俩怎么喝这么久?酒当药喝?”她问。
“喝个屁!”
“你俩没喝?”
“我跟谁喝来着?”
“大贵呀!他没去你家?”
“嘻嘻……去是去了,屁也没尝着!”
阿七疑惑地盯着福奎这副孩子气的兴奋面孔,听他有聲有色地说完刚才作弄大贵的详情细节。
“你真糊涂!”她正要开口大骂,忽又心里一软,可怜起他来。她今天是存心安排大贵去福奎那儿“尝鲜”的,为的是让福奎借此机会跟大贵提提去味精厂顶她缺的事儿。这可是个现成的机会。吃了他的鱼,喝了他的酒,想必大贵不会不答应的。老福奎能把这事儿办妥了,往后有个牢靠的着落,她就可以放心走了。常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她当了他八年姘头,尽管名目不正,好歹总顶得上一日夫妻了。“福奎,”她还抱着一线希望问道,“你跟大贵提过顶缺的事儿了吧?”
“提个屁!我可不想到工厂去受罪。”福奎没把她的好心当回事儿,“照着钟点上班下班,螺蛳壳里做道场,哪比得上打鱼自由自在?那憋气的活儿我干得了吗?”
他说的是实话。葛川江上打鱼,老大的天地,自由自在,他从十四五岁起就干这门营生了。叫一个老头儿改变他几十年的生活方式,他一定很不情愿。对这种生活,他习惯了,习惯得仿佛他天生就是个渔佬儿,在他妈的肚子里就学会撒网、放钓了。
阿七是个明白人,知道让一条狗去啃草地或者让一头牛改吃荤腥,都是办不到的事儿。她眼巴巴地望着福奎朝江边走去,去碰他的运气……
夏夜的葛川江很像一个浑身穿戴得珠光宝气的少妇。福奎老远望见对岸新铺的江滨大街那一溜恍如火龙的街灯。这些日子,一过晚上七点,仿佛有神仙作法,眨眼工夫,这条火龙唰地亮了。这奇景常叫福奎想,城里那帮照着钟点干活儿的孱头还真有点能耐。
他来到江边,点起马灯,把小船划出了船棚。岸上那片草虫咕咕的叫声越来越远,渐渐被扑通扑通的水声盖住了。这声音是一群小鸡毛鱼搅起来的,它们团团围着小船,跟随着他的灯光,一同往江心游去,仿佛虾兵蟹将簇拥着龙王。每天夜里,他要是照准它们撒一网的话,他如今的日子不会弄得这么寒酸。城里人嘴馋,鱼苗苗也照样买了吃。哪怕他每天只撒一网,他也能挣些钱的。可是他绝对不肯撒网捕小鱼。他想得挺美:既然他是这条江上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那么,江里的鱼就全都是他的,他要等这些鱼长大了再捕。到那时候,从前的运道就会再来,从前的日子还会……从前样样都称心,他还跟大首长喝过酒呢。
不过,从前可没有对岸那条火龙。他每夜都数那一溜街灯,却从没数准过究竟是多少。他对这些街灯很感兴趣。尽管当初铺路的时候,炸药把江岸的山崖崩得惊天动地,把江里的鱼都吓跑了,但他得认了,如今西岸这富丽堂皇的气派,委实叫人着迷。
他划到了江心,顺着滚钓划了个来回。整串滚钓上一无所有。那些浮标全都懒洋洋地漂在水面上,一动不动。
福奎也懒洋洋地躺下身来,乱蓬蓬的脑袋枕着船尾的坐板,一双光着的大脚插进船头的板空里。他想,要是死的时候也能这么安安稳稳地躺着,那就好了。他情愿死在船上,死在这条像个娇媚的小荡妇似的迷住了他的大江里。死在岸上,他会很丢脸的,因为他不能像别的死鬼那样住进那种开着窗户让死鬼透气的小屋子。他会被埋到地底下去,埋他的人会用铁锹把坟堆上的土拍得很结实,叫他透不上气来。而死在江里,就跟睡在那荡妇怀里一般,他没啥可抱屈的了。
那群小鱼依然尾随着他的小船,好像还越聚越多了。
福奎搬过那只甏子,一把把地往江里撒着蚯蚓……
从前,“喂鱼”这个词是渔佬儿的耻辱。不过,从前的好多规矩眼下都不管用了。
【作者简介】李杭育,20世纪80年代起专注写作,“寻根派”代表作家。以“葛川江系列”小说闻名文坛。著有《故事里有个兔子》《江南旧事》《唱片经典》《公猪案》《醒酒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