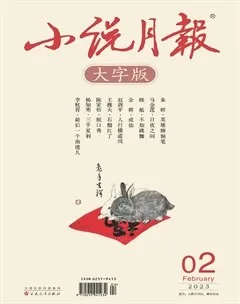脱口秀
一
“上台,你讲得可以再慢一点。”夏未说。
“我讲那么慢,别人会认为我脑子不灵了。”杜明说。
“你怎么会这样理解别人,别人是冲你来的,自然不会以为你那样的。”她说。
其实,杜明在意的不是别人,正是夏未,因为现在他心里边全是她。他认为自己虽然是个讲段子的人,人家讲他是个脱口秀演员了,但在他自己看来,他不过是把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情说出来而已。
“可不可以再讲得细一点?”夏未又说。
他听她的,他认为她是真正懂他的。
她有时会在他上场前拍拍他的肩,就好像他是一个上去比赛的选手似的。只不过,这是一种表演,是个台子,而下边是一些观众而已。
他在网上火了,她认识了他,然后,他们就走得比较近了。
她没有告诉他,自己的父母有想來看一看演出的想法,但她阻止住了。她不认为那是他们能接受得了的。尽管她对他是认可的,但毕竟父母是有一套自己固定看法的人。
“好吧。我上去了。”他说。
他以前在读书考学时,以及在回忆时,没有想到以后会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
“干我们这行,全凭一点感觉,哪天感觉不好了,可能就讲不下去了。”他对她说过。
夏未说:“你不要这样想,其实你能讲,那是因为你肚子有货,我敢说,你是一个真正特别的脱口秀演员。”
他在台上,每想到她讲的这种话,都觉得她不仅懂他,而且她是真正支持他的。
对我的支持将会特别重要。他想。
他看了一下观众席,有一点恍惚。她的后边有灯,所以有点逆光,他认不太清,但他知道她坐在那里。
“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是……”他顿了一下。
观众有人在打口哨。就好像他们认为这里边有个什么机关似的。
“我认为本来那个男的能做得更好,在关于奋斗这个主题上,我认为至少可以把奋斗理解成让自己变得更精致一些。”他说。
下边又有点起哄。
“当然了,我没有说变成流氓。”他又说。
他看不清她了,她盯着舞台在看呢。
杜明又说:“我们现在被成功吸引得太严重了,恨不得人人都要成功。”
他听到自己喉咙里说:“郑成功吧。”
下边有笑声,但不够友好。
二
别墅的地下车库入口有台阶,边上有花,是紫色的,杜明看得并不仔细。
“为什么要在这儿放花?”他问夏未。
这时,车子已经开进车库了。
“因为生活需要品位。”她说。
在客厅,老夏对有些不适的杜明起初印象并不好,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
年轻人应该大大方方的。
“可他是个有名的人。”女儿曾经对老夏这样讲过。为了让双方的见面有个好的结果,女儿是做了些工作的。
“你讲得不错嘛。”老夏说。
“父亲看了你不少视频。”夏未对他说。
他喝果汁,边上有小狗在转,他感觉家里有旋转木马似的,果然在平台上有个旋转木马,那儿是二楼,老夏端着一杯茶,指着旋转木马说:“夏未喜欢,我就在平台上放了一个。”
看着夏未去了厨房,他马上意识到自己跟夏未谈恋爱,能给她更好更富有的生活吗?不过,他又想,她不是已经有很好的生活了吗?
“有些想法还是好的。”老夏对杜明说。
“对了,你现在讲的这些事情,都是你自己考虑过的吗?”老夏问。
“我没有写稿的习惯,对于脱口秀表演来说,临场发挥实在是很重要的。”他说。
这时,夏未从厨房回来说:“杜明在美国学过呢,不是那种随口说的人。”她的意思是,他是有见地的。
“一个海归,但做了脱口秀演员。”老夏说。
“他现在算是明星了。”她说。
“不能这样讲。”他对她和她父亲说。
他听到一阵鹅的叫声,心想怎么别墅里还有鹅呢?
在顶楼,也就是四层,没有露台了,只是一个小一点的房间,那里有一只又像是鹅又像是鹤的东西。
“养这东西干吗?”他问夏未。
夏未说:“我爸爸很看重你在海外留学的经历呢,他公司里也有不少海归,做投资的,做风投没有海外留学的背景很难立足呢。”
“可我学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杜明说。
在客厅,夏未妈妈打量了杜明很久,然后对他说:“你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公司。”
“脱口秀是我的爱好。”他说。
“可以把爱好变成一个公司。”她妈妈说。
“妈妈的意思是一个IP(成名文创作品)啊,一个创意公司。”她说。
他额头冒汗,觉得商人的家庭考虑问题跟别人是不大一样的。
“东面有鹅。”他嘀咕道。
“你看到了?”她妈妈问。
他不得不正视她妈妈,眉清目秀,一点也不倦怠,尽管她妈妈声称自己才从外面购物回来。
“喜欢这鹅吗?”她妈妈说,拉长了“鹅”字的声音。
“它可以称为鹤。”他说。
“丹顶鹤或者白鹤,因为我没有看清它的冠,但它是白的,这个我确定。”他说。
夏未妈妈问:“你是在英国留学的吗?”
他说:“在美国。”
夏未说:“他不在英国。”
“我们吃一点虾子,晚上。”她妈妈说。
“虾子成对才好呢。”他说,用了一种很调侃的口气。
“就好像你吃对虾似的。”她妈妈笑着说。
“我喜欢社会新闻。”老夏在喝了一口红酒后对他说。
“我掌握不少这方面的消息。”杜明说。
“是的,他必须掌握,不然在现场不来劲。”夏未说。
“很资深啊,看你们处的,你对他的表演也能分析了。”
夏未看了一下妈妈说:“那是啊,他说得可好了。”
他听她讲,就好像他也可以不存在似的,就好像在说另一个人似的。
“有人越野跑,许多人,来了一场暴雨,然后许多人冻死了。”他说。
“什么情况,没有预报吗?”她妈妈问。
她爸爸问:“赛事组织者干什么去了?”
杜明已经坐在回去的车上了,夏未在边上打盹儿,他捏了一下她的手,说:“你注意到没有,社会新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谈的。”
他这么讲的意思是,在谈到越野马拉松选手被意外冻死时,她的爸爸妈妈是反感他那样来解释这个事情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件特别丢脸的事情,一场马拉松,居然有人冻死了。
“我们不说这个了。”她说。
车子已經驶回了主城区,别墅区在身后很远了,那里有灯火,有旷野的风,有郊区的奇特味道。但是,那里的她的爸爸和妈妈,似乎对一个海归的高才生讲起了脱口秀是持极大的怀疑的,不是怀疑他的选择,而是怀疑他能不能解释好一个又一个社会新闻。
“你爸爸对社会新闻挺感兴趣的。”他拍了一下她的手说。
三
两家人见面,地点选在宁国路的酸菜鱼馆,在没去之前,杜明还跟夏未讲,能不能不要在这种地方吃饭,他的意思是他自己多少是个演员,而夏未的家庭更是显赫,双方父母见面选在一个吃鱼的地方是不是有点怪异。
“就因为你叫杜明?”她问。
“那是我的艺名。”他说。
“可是真实的意思,不就是你想到一个比较合你意的地方吗?”夏未说。
他低头,在手机上回复了一条信息,他看夏未的眼影,有点绿中带红的妩媚,有这样一个女友,虽然很高兴,但他是有压力的,毕竟对方是来自一个富商的家庭。
“我爸爸是考虑你们家的。”她说。
“因为我们是穷人家吧。”他说。
“那怎么可能?记住,你现在也是一个腕儿呢。”她说。
“我只是小有名气吧。”他说。
“杜先生你不要这样谦虚好不好?”夏未说。
他们把车子停好,其实她爸妈就喜欢吃这些东西,酸菜鱼也算吧。
“我爸说,你们是西南人。”她说。
他心想他们指的是他妈妈,他妈妈确实是西南人。
“但我是本地人,本省人。”他说。
店面是深黑色的,大门很沉重,给人一种特别庄严的感觉。据说后面杀鱼的地方也很大,这家店很有名的,别看只是一个吃酸菜鱼的地方。
“以前我吃鱼,觉得腥气重。”他说。
他们已经坐在包间里了,她爸妈打电话来,说马上就要到了。
“我现在想讲一讲我在海外的事了。”他指的是他要讲在国外学东西的情况,那样会吸引人吧。
“一个海归本来就不必非得在投行对吧?”她说。
“可你妈还说我可以IP开发的,然后做概念文化公司呢。”他说。
她爸妈进来了,想不到老夏跟他说:“刚才我在车上还看你的视频,有个东西讲得,怎么说呢,有点问题。”
他有点摸不着头脑,问:“叔叔,您的意思是我讲得不好?”
老夏坐在木椅上,喝了口茶说:“那倒不是,你讲了一只熊在地里,发呆,你记得吧?”
他想了想,是有这么个节目,抖音上的。
“我意思是,熊要有个熊样。”他说。
她妈在边上说:“老夏,我说吧,杜明是在讽刺熊样呢。”
“就是打败了也要败得像个样子。”女儿夏未在边上说。
老夏有点不服,认为这样表达没有什么意思。菜已经安排好了,显然老夏是来吃过很多次的。
“要了很不错的黑鱼,用青菜配着烧,就是要削出那种劲道,小鱼,你知道吧,只有把鱼削出好片状,才有劲道。”老夏说。
是的,他在等他的家人,只有他母亲来,父亲不会来。父亲在这种场合是不会出现的。
“不知道你妈喜不喜欢这种地方?”夏未妈妈说。
杜明说:“不是讲我们是西南人吗?”
“西南人?”夏未妈妈反问。
他不想强调自己是本省人,西南人指的是他妈妈。
他妈妈推门进来,这是双方第一次见面。他妈妈不是那么敏感,她比较爱低头。
“我介绍一下,这是夏未爸爸和妈妈。”他抚着妈妈的胳膊,对她讲。
妈妈抬头看了看对方,眼神中迅速有了一种异样的东西,但她掩饰住了,坐下来,对夏未妈妈说:“你显得好年轻。”
老夏比较大声地咳嗽了起来,看了看手表,对夏未说:“喊服务员来。”
服务员进来了,老夏说:“快点起菜吧。”
他坐在妈妈边上,妈妈坐在老夏边上,然后那边是夏未妈妈和夏未,她妈妈和老夏坐在一块儿。他明显感觉到妈妈有那么一点不自在。
“听说你是西南人,所以点了酸菜鱼。”夏未妈妈说。
她是重复这个话了。
“我是西南人。”妈妈说。
“培养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夏未妈妈说。
“哪有,只是一个跑龙套的。”妈妈说。
他听妈妈讲自己是个跑龙套的,是有点抵触的。
“阿姨,杜明是个角儿了。”夏未说。
正说着,一个戴白帽子的厨师,端出一个盘子,后边跟着一个小推车,上边有一条鱼,他们是来现场杀鱼的,鱼已经去了内脏,现在可以片鱼了。
“酸菜鱼,就是要现场来片,这样才新鲜,宁国路这个店在本省是做得最好的。”夏未爸爸说。
杜明的妈妈始终还是要讲话的,她坐在老夏的边上,先前的不自在已经消散了,现在她激灵了一下,对儿子说:“不如你讲一下吧。”
她这是在鼓励儿子,她对儿子讲脱口秀是有信心的,有时她甚至认为这是最了不起的艺术了。
“你看,师傅已经发抖音了。”杜明说。
这时,那个推小推车的女服务员笑了一下,因为还没有拍呢。
“哦,不是发抖音是在发抖。”杜明说。
“你是要吃它的。”夏未在边上提醒道。
“那又怎样,不能调侃了吗?”杜明说。
一把刀子就这样把鱼给片成了两半,中间是嫩嫩的鱼背。
“杀鱼是一门手艺,全看你们支不支持这种手艺的残忍和美的并存了。”杜明说。
杜明妈妈看着老夏把烟灰点了点,其实饭店里抽烟是不好的,但老夏习惯了,他就是要吸烟。老夏双手置于胸前,在看表演。
“不是杀鱼的,是在表演。”夏未说。
夏未指的是她的男朋友杜明,杜明还能讲什么?他看见他妈妈还是对身边的这对男女有一些反应过度的漠然,这怎么说呢,可以讲,就是一种吃饭时的不合时宜的冷漠,这怎么回事?
“已经换了。”老夏说。
杜明知道,老夏讲的是已经换了草鱼,这里先前的一场争论,因为真正的酸菜鱼,必须用草鱼,黑鱼不行,黑鱼的卷容易在酸菜乳酸的作用下,打不开。
“打不开?”这个脱口秀演员说,“就是这肉打不开它的肉体,这样做不出那种西南的风格。”
“此处有掌声。”夏未曾经附和,这发生在换鱼之际,而换鱼是因为杜明的妈妈说的“哪有用那么好的鱼做酸菜鱼的道理”。
夏未妈妈说:“我们听西南人民的。”
老夏勉强地笑了,于是那条黑鱼在小推车下边的桶里,在水里游荡,他们虽然没吃它,但要买下它,支付费用。
有音乐,脱口秀演员说:“杀下的鱼,被片成了鱼片,以这么残忍的方式,说明了自然界的残酷,现实是,它们好吃。”
有时,要等待,等待观众的反应,但是,他看到的是妈妈居然有一些愤怒。
“您以前是忙什么的?”夏未妈妈问杜明妈妈。
杜明妈妈说:“我懂得鱼的道理并不比你们多。”
她这是在岔开话题呢,脱口秀演员想,未必吧。妈妈说:“可是,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选在这个地方吃饭,告诉我,因为我是西南人。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天下哪里没有酸菜鱼,这还能是理由吗?”
“就像在哪里都能看到脱口秀,何必要上抖音呢?”夏未说。
“有一口很大的池子。”杜明对老夏说。
“什么池子?”老夏问。
他说:“是演出场所啊,脱口秀要有一个池子,然后演员站在池子里,对四周的观众演起来,没完没了。”
“关键要能转化,要有模式。”夏未妈妈说。
讲生意的事,杜明妈妈就低头了,她看着筷子。鱼已经片完了,送到后厨那里了。杜明妈妈对着杜明说:“现在你要给在座的表演了吗,在吃饭之前?”
“刚才,你问我以前做什么的?”他妈妈问夏未妈妈。
夏未妈妈刚才讲到了要女儿的男朋友考虑把脱口秀的表演IP化,要做公司,开视频公司,然后进科创板,是有可能的生意经。
“我以前可是很忙的。”杜明妈妈说,然后她朝夏未爸爸友好地、专注地看了一眼。他摸了摸手表,对黑漆漆的包间木门那儿喊道:“服务员!”
“你们都不懂,酸菜鱼不是靠鱼。”他妈妈说。
“靠什么?”夏未问。
“既然你们说我是西南人,吃起了酸菜鱼,那我跟你们讲,换鱼也不行。”她有点恼怒地拍了桌子一下。
“性情中人。”夏未妈妈说。
杜明妈妈说:“靠酸菜。”
“这个道理还不简单吗,但凡让荦素在一起成为经典,都靠素菜,怎么可能靠鱼呢。否则,红烧鱼怎么讲,水煮鱼怎么讲,清蒸鱼又怎么讲?既然是酸菜鱼,靠的是酸菜。”她又补充道。
老夏坐在那儿,明显,关于鱼,他先前换了鱼,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杜明妈妈讲了,靠的是酸菜,那么有必要争论这个吗?
“这是一种全国流行的菜了。”老夏终于忍不住对大家说。
他没有对杜明妈妈专门来讲,而是对大家,因为他认为有必要重新端正一下吃饭的气氛,这样来讨论,完全在于他们过于强调了杜明妈妈的西南人身份。
“全国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老夏说。
“其他地方的人不懂酸菜,至少是不知道最秘密的地方到底在哪儿。”杜明妈妈说。
“我妈妈的意思是,酸菜非常重要,那我要讲的是,只有把酸菜弄对了,你的鱼才对,不然你残忍地片了一条鱼,然而它还是不对,要让鱼遇到对的酸菜。”杜明说。
杜明妈妈把椅子向后挤了一下,然后对夏未爸爸说:“你们要搞清楚酸菜不可能了。”
“为什么啊,阿姨?”夏未问。
夏未妈妈已经对这个女人非常有耐心了,但是对方居然不依不饶,要把西南关于酸菜鱼的一切都在这儿摆出来。
“酸菜要装在坛子里,埋到土里,至少一年,要经过四季。”杜明妈妈说。
“她以前到底做什么的?”夏未妈妈发信息给女儿,女儿拿起手机,白了妈妈一眼。
四
隔了两天,夏未到杜明所住的北辰小区家里去,他妈妈在那里,据杜明讲,妈妈不同意他和她再相处下去了。
“你妈不能这样考虑问题吧。”她说。
“妈妈没有想到,原来是这样的。”他说。
其实他们讲的事情就发生在那天在酸菜鱼店吃饭过后,当场夏未没有看出来,直到散场,她爸爸让她妈妈不要让杜明妈妈把那条黑鱼拎回家时,事情才突然爆发起来了。
当时她妈妈说:“拎回去又怎么了,一条鱼何必浪费呢?”
杜明妈妈已经走到外面了,只不过杜明没有替他妈妈想一想,在吃饭当中,他妈妈已经多次不适应跟这样一对男女讲话了,一个是商业人士,一个是满口的风格啊,IP啊,她只是一個西南女人,一个住到儿子这里还不大习惯的西南女人。
不过,杜明还是让妈妈把那条黑鱼拎回了家,因为人家夏未妈妈也许并没有看不起她的意思,看样子也知道一条黑鱼拎回去还是可以吃的,尽管它不适合做酸菜鱼。
那条黑鱼并没有吃,而是养在一只脸盆里,他在电话中对夏未说:“你过来看一看,其实一条黑鱼何必非要让她拎回来呢?”
“这不是我妈妈的问题。”她说。
“那是我妈妈的问题?”他说。
“是我爸爸的问题。”她说。
说到爸爸,说到老夏,问题就在这人身上,他跟这条鱼关系可大了,正是他先点的黑鱼,然后这个懂酸菜鱼的西南女人来了,他就换成草鱼了,一番好意,给懂的人点的,可是他们在吃饭中就特别不自在了。
“我爸爸不是那种人。”她说。
“我认为你爸爸做得也挺好的啊,讲话都很注意了。”他说。
她到他家时,他妈在阳台上弄衣服,她小心地走过去喊了她一声。
“你来了。”杜明妈妈说。
“来了。”她说。
“她是来看你的。”杜明说。
“我不需要看。”杜明妈妈说。
她到卫生间那儿,看到脸盆里的黑鱼,对他说:“怎么还养着?干脆吃掉啊。”
“我们能吃它吗?”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阳台。
“我问过我爸了。”她说。
“怎么讲的?”他问。
“他说他跟你妈以前是认识的,但只是过去啊。怎么想到这么巧,居然因为我们现在又遇上了。”她说。
“可不要因为我们,我们又不是因为他们认识的。”他说。
杜明妈妈已经从阳台那儿回到客厅了。
“还有什么演出啊?”她问。
“还要录一期,比赛用的。”他说。
“你现在还是要说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杜明妈妈说。
“他讲得挺实在啊。”夏未说。
“小夏,你支持杜明,我是看出来的。但是,你们那个家庭,我们杜明,你觉得合适吗?”杜明妈妈说。
“我爸爸讲了,其實他还是很高兴又遇到您的。”夏未说。
“不要提你爸爸。”杜明妈妈说。
“以前您很红。”夏未终于有些怪异地说。
这个说法让杜明有点突然,怎么讲起妈妈往事来了,这是我们能讲的吗?
“我只是一个跳舞的。”杜明妈妈说。
“我们去河边走走吧。”夏未提议。
“外面风大呢。”杜明说。
杜明妈妈答应跟他们出去走一走,她说:“反正我只是来一下,说的是见你的父母,但我也想过,看一看杜明现在的生活,说实话,小夏你挺好的,只是你们那个家庭,对杜明是一种压力。”
“妈,我没有压力。”杜明说。
“你讲话像个艺术家。”杜明妈妈说。
他们已经来到河边,河水有点波浪,风吹的缘故。
杜明走在后边,夏未和他妈妈走在前边,不断有行人迎面走来。
“过两天我就回去了。”杜明妈妈说。
“大西南是个好地方。”夏未说。
“我爸爸说了,对于当年的事,他是觉得好的。”夏未说。
杜明妈妈摸了摸头:“你们不懂,那时我是什么啊,我只是一个跳舞的。”
“可我爸不就是在那儿认识您的吗?”夏未说。
夏未又说:“我爸说了,他一直记得您这个朋友。”
外边有点发黑,有月亮,但有时挂在云中。“还是说说你们吧。”杜明妈妈说。
“我真的觉得杜明会成为一个最好的脱口秀演员。”夏未说。
“他真的说得那么好?”杜明妈妈问。
夏未说:“阿姨,您又不是不上网,您没看到他那些很火的视频吗?”
“看了一些。”杜明妈妈说。
“现场也看过吧。”夏未说。
“我还用看现场吗?他是我儿子,我一直看着他说话呢。”
“阿姨,可是,那还是不一样的。我是说一个演员,必须在舞台上,那才是真正的脱口秀表演,生活中不完全算的。”夏未说。
“嗯,生活。”杜明妈妈讲了一句。
五
杜明站在池子中央,他环视四周,曾经自己像是在月亮的背面,又或是在火星上,永远的火星。因为双方父母见面的原因,他和夏未的关系出现了一点问题,妈妈已经回西南了,妈妈跟夏未应该单独谈过一次。显然他妈妈是反对他们在一起的,因为他妈妈不接受那样一个家庭,并且他相信妈妈一定会对夏未说,“你要爱护这个杜明,因为他会是一个明星”。
他打了个响指,观众中居然有人吹了口哨。他铁定地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
他说:“对不起,我的婚事被搞砸了,也许你们要说,哎呀,一个脱口秀演员能有什么婚事啊,不是都交给段子了吗。”
他顿了顿,想起夏未跟他讲的,“你会是一个伟大的演员”。
可是他想妈妈是不是也拿这一点来将夏未的军呢?因为话说得多了,大家也就都信了,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他偶尔也会想起夏未妈妈说的“你要做一个伟大的上市的公司,一个说话的大公司”。
下边的口哨声又来了,因为在他并非故意设计的空当处,观众有点不耐烦了,当然热爱他的观众会误以为他在有意地拖延时间,要求他们有更多的掌声,或是善意的口哨声。
他说:“但是,我最近找了个对象,不幸的是,我搞的这个对象,今天没有来吧。”他朝池子四周张望了一下。
他有一种小丑的感觉,并把这种感觉传导给了观众,池子里有了一些异样的不屑。然而,他知道脱口秀演员就是这样,你可以重新把他们给激将起来。
他说:“是这样的,我们的父母见了面,你们猜怎么着,原来我妈妈跟她爸爸认识。”
观众中有人站了起来,这也太奇怪了吧。在这一刻,他很害怕夏未会突然出现在池子四周,不过他不用担心,他妈妈定是用什么办法把夏未给拦住了,妈妈是前几天回西南的,她走时跟夏未说了什么啊?
他说:“我妈妈是个舞女,他爸爸就是在我妈妈跳舞的那个舞厅里,一个很有名的西南舞厅,认识的我妈妈。”
他又说:“一个舞女,一个专门跳舞的女人也就是我的妈妈,居然在他儿子的女朋友的家里见到了年轻时和她跳舞的男人。”
那个男人叫老夏。
那时,她是红极一时的沙女,在西南太有名了,都知道她。她是一个最吸引人的沙女,是一个职业的沙女,在那里跳魅惑的舞蹈。
舞厅是昏暗的,老夏找她跳,他们就认识了。但是,他们发生了什么故事呢?那时虽然她有名,但是,那是一个有问题的舞厅,时常会因为灯光,因为秩序而被停业整顿。那些漂亮的女孩子都在那里跳舞,就像今天的互联网,潮男潮女们在那里相识。
老夏给她钱,给她买东西,他们不算恋爱,因为她是沙女,也就是说老夏给她的是小费,在当时,有人知道她和老夏的关系,不过有人认为他们能成为朋友,没有什么意思。
他其实知道他妈妈和老夏认识,也就是妈妈跟他讲的这么多。他之所以要拿来讲,是因为他感到他的人生受到挑战了,妈妈是沙女的事情,在今天这个即将成为伟大演员的脱口秀表演中,成为一个他绕不过去的坎。
他说:“因为她是我妈妈。”
“妈妈是个沙女。”他笑了一下,他看四周,都静了。他不认为别人是在听他讲段子,而是因为他停顿下来时,时间退回到几十年前,而那时,因为生活所迫,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做沙女。
“可是,她热爱跳舞。
“就像我今天喜欢脱口秀。
“喜欢做一个伟大的演员。”他用手在空气中捶了一下。
“这有什么错吗?”他问。
“妈妈回西南了,她说了,我不能和她年轻做沙女时认识的一个男人的女儿交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她讨厌那个男人,包括他的一切。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时伤害了她。”
如果有人要问,老夏真的伤害杜明妈妈了吗?该怎么回答呢?
也许夏未能夠讲出一点点,不然为什么她听了杜明妈妈的话,真的没有来找杜明呢?
“妈妈说,我们不是一种人。
“你们听到没有,我妈说了,我们和老夏以及他的家庭,不是一种人。
“是两个样子的人。”
有人用手电在池子中晃了一下。
“他把你妈妈怎么了?”他似乎听到有人在这样问。然而,他是一个一心要成为伟大脱口秀演员的年轻人,他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之所以讲这个,是因为他要让他的观众明白,妈妈有一段做沙女的故事。
这个故事不仅打动我,同时它压抑了我,以及我的人生。他想。
他始终在看池子四周,像在月亮背面看宇宙的边际,不过没有夏未的身影,“我们需要冷静。”他说。
“她舞跳得很好。
“这就是最基本的了。
“她年轻时非常好看。
“她是一个西南的沙女,那么多人,挤在舞厅里,灯光昏暗,然而,毕竟美丽的人生无法遮蔽。”
六
在乐山大佛斜对的那个路口,有一家鱼店,吃的就是岷江里边的鱼。最好吃的鱼必须是刚刚从江里捞上来直接养在水池里的。夏未去的时候,天色阴沉,饭店里有几个人在吃饭,因为饭点儿已经过了,所以人比平时要少。
“这里的鱼才是最正宗的。”老板说。
“我看这鱼挺活的。”夏未说。
老板看这个年轻的女子气度不凡,当然了,她身上那种独特的气质总是能吸引人。
乐山大佛从饭店的角度能看到大部分,但有一部分被山尾给挡住了,有小船可以划向大佛的脚下,只是她不明白,为什么游人要划船过去,到了大佛的下边,其实根本看不到大佛。
“这条鱼很不错呢。”老板说。
老板迅速地杀鱼,她看着小船一点点地接近那尊大佛,山多大啊,人硬是在那里刻出了大佛,这是多大的决心啊。
这里向前边一拐,有一条路可以到眉山,那是苏东坡的家乡,苏东坡是她喜欢的,她记得跟杜明讲过苏东坡。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杜明说。
“《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你喜欢哪一篇?”她问。
她不记得他是怎么答的了,记不起来了。
杜明妈妈坐在木桌旁,夏未猛地想起,这个妈妈是一个沙女。其实她们就是去看红沙舞厅,然后再来这儿吃饭的。
“鱼要这样做。”杜明妈妈指着后边杀鱼做鱼的人跟夏未说。
“烧得厉害。”夏未说,夏未讲的是发烧时的杜明。
“小时候天热,我就在地上坐着给杜明扇风,用一把芭蕉扇,那时他一学习,就忘了,什么都忘了。蚊子咬他,他也不知道,所以我就给他摇扇子。”杜明妈妈说。
“难怪学业那么好。”
“不然呢,一个穷家庭,怎么可能考上学,还能去美国留学。”杜明妈妈说。
杜明妈妈很平静。
“这味道很香。”杜明妈妈指着挂在墙上的泡菜对夏未说。
“四川人真会做菜。”夏未说。
“还是讲讲发烧吧。”杜明妈妈说。
“是啊,烧得很呢,碰了个钉子,谁知道会发烧,而且退不下来。”夏未说。
“钉子?”杜明妈妈问。
“是啊,是碰了一个钉子,他在那儿,有人推搡他,然后他头一歪,在黑黑的过道里,谁知道会有钉子呢,划了头皮,他都不知道。”夏未说。
“一定是上锈了。”杜明妈妈说。
“酸菜鱼上来了。”老板喊了一声。
又是酸菜鱼,那一次老夏和杜明妈妈首次见面,就是吃的酸菜鱼。
“没办法,西南人,就好吃这个。”杜明妈妈说。
一股清香,有辣味,但更多的是香气,鱼已经片得很薄了。
“确实烧得太高了。”
“不怪你,也不是没去医院。”
“可是,谁能想到碰个钉子会发烧,烧成那样。”夏未说。
夏未觉得很奇怪,跟杜明妈妈一起吃鱼,居然对鱼刺都不那么害怕了。
“我跟你说了,鱼已经片得很薄了。”杜明妈妈说。
其实她记得她跟杜明妈妈在发暗的、门都朽坏了的红沙舞厅里,她看到杜明妈妈的样子,有一种飘的感觉,就好像能回到当年,她是在舞厅里最受欢迎的女人。
“所有人都围着你转?”夏未问。
杜明妈妈说:“我不过是跳得比别人更勤快一些罢了。”
“什么意思?”夏未问。
杜明妈妈说:“就是我每跳一下都用心,不像有些女人,省力气,做个样子,我不是,我是跳每一个动作都用心。”
外边天色阴沉,仍可以看到有小船向乐山大佛划去。
“看,有人上去了。”夏未对杜明妈妈说。
“是啊,都想上去看一看。”杜明妈妈说。
一辆小车从饭店门口开过,不知为什么传来尖厉的喇叭声,好像要打破这沉寂的午后。
“我转得好,旋得好。”杜明妈妈说。
杜明妈妈没有化妆,但从她眉眼里仍能看到当年那动人的风尘之美。
“你喜欢跳舞吧?”她问。
杜明妈妈夹起一块泡菜,在眼前晃了晃,泡菜发出一种透明的琥珀色。
“怎么烧也退不下去?”杜明妈妈说。
“医生说了,还是一个感染的问题。”夏未说。
她同时记起的是,杜明曾跟她讲的,在苏东坡的作品里,总有一种要张扬开来的东西,不论是明月、西湖,还是旷野、大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热爱生活吧。”她模糊记得好像杜明是这样说的。
难怪他能做脱口秀演员,他有一种对必须要讲的东西的热切喜欢。她想。
“他小时候话少。”杜明妈妈说。
“干什么要推他,干什么!”杜明妈妈眼中含着泪,对着夏未有些愤怒地说。
“人们好像气极了,不知怎么引起的,反正讲着讲着,有一种东西,隐隐的,就在现场失控了,有人扬言,要叫他完蛋。”夏未说。
显然,他讲的段子,让人愤怒了。
七
“我给你擦擦脸。”夏未说。
“我怎么那么热啊?”他说。
“你发烧了。”夏未说。
夏未到卫生间蘸了毛巾,水是凉的,但只要一贴到他脸上,毛巾马上就热了。
“跟你说,你去看一看那些红沙舞厅。”他说。
夏未让杜明把身体向里让一让,这样她可以坐在床边跟他讲话。
他没有动,他眼前一亮,尽是西南那整齐的菜地,望去,都是趴在地上的人,他们在一遍一遍地翻土里那些美味的菜头。
终将要埋到地里。他想。
封在坛子里,然后埋到地里,成为泡菜。他又想。
“你这也是的,怎么就发烧到这样呢?”夏未说。
他收回思绪,想起亮光中的妈妈,在舞厅里跳舞的脚步,他对她说:“妈妈很不容易。”
“可是,你最近说她,说得太多了。”她说。
“可我永远也说不尽,这是我最想说的。”杜明说。
“可也不能只讲她啊,生活还无比广阔呢。”她说。
“可我妈妈不容易。”他说。
这个他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可以一直讲下去。但不知为什么,连他自己也觉得讲得太多了,听得太多了,也就认为有那么一点不对了。
“还是先好好休息吧,把发烧的事情解决掉。”夏未说。
电话响,手机响,网络上也跳出許多东西,现在他生病倒下了,连媒体都不相信,一个这么杰出的脱口秀演员居然倒下了。
“没有人真的会相信你发烧。”她说。
“我没有吧。”他说。
他没有看温度计,她只是笑了一下,给他端了一杯水,他没有喝。
实在是太严重了。他在心里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状态简直差到极点了。
“你不会有事的。”她说。
“我跟你讲了,到四川去看看,看看那里的红沙舞厅,当年妈妈跳舞的地方。”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他侧过脸去,她想她会去的。
在一条长长的通道里,不知为什么,有几个人跟在后边,他想应该是不满意今天的演出的,但没有必要跟得那么紧吧。
“后边有人。”她小声地说。
他有点摇晃,显然他是愤怒的,对于表演,对于池子,对于现实,他觉得今天真是不对到极点了。
其实也就一个人,冲过来推搡他,他就撞到了墙上,墙上有一枚生锈的钉子。然后,他的额头热辣辣地疼了一下。
那个人骂了几句什么,但很快被保安制服了。
她扶着他,他有点晕眩,朝出口方向走去。
原刊责编 大 风
【作者简介】陈家桥,男,1972年生,安徽六安人。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至今已发表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篇,小说集四部,计七百万字。现任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