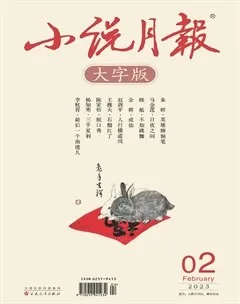人行横道线
碰撞并不剧烈,仿佛刚一接触,汽车就刹住了。他在倒下去的瞬间,还清清楚楚听见有人喊了他一声“郑县长”。他离开县长这个岗位已经很多年了,即便是一种社会称呼,他也很少听见了。现如今,“郑道清”这个爹妈给的名字,或者说,这个身份证上的名字,其实只有那些水费啊电费啊等七七八八的收费人员叫了。年纪差不多的熟人或者朋友,多半叫他“老郑”,而家里人则清一色叫他“老头儿”。开初,只有老伴儿跟儿子叫“老头儿”,儿媳妇跟孙子还叫“爸爸”、叫“爷爷”,可老伴儿一走,儿子儿媳妇开始闹离婚,孙子又考到了外省的大学,“爸爸”“爷爷”这样的称呼也很少有人叫了。
有人喊打“122”报警,有人喊打“120”找急救中心……这之间,奇怪地夹着几丝有些耳熟的乡土音。他甚至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就一翻身在斑马线上坐了起来,看了看围在身边的人,似乎想找一找藏在那一片喧哗中的乡土音。但一阵要命的疼痛立刻从大腿根袭来,撕破他一张嘴巴,发出吱吱啦啦的响声来。肇事者从车上下来了,一张脸胡子拉碴的,恓恓惶惶走到跟前,叫一声“郑县长”,便弯腰把他抱起来。先后两声“郑县长”,听不出来一点别扭,他隐约地意识到这个肇事者跟自己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关系,非亲即故吗?仿佛也不是那么简单。他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忍住疼痛,顺从地搂住肇事者的脖子,依偎在肇事者胸前,半躺半坐到了车上。肇事车也没有一点迟疑,打着应急灯,驶离了人行横道,往医院开去。而人行横道线上,一堆人也渐渐散去,没有人喊警察,也没有人叫救护车,这场车祸不外乎一次意外事件。
郑道清的意识很清楚,医生几根指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又无边无际地跟他聊,他应答起来一点不糊涂。医生接着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又量了量他的血压,听了听他的心脏,这才转到他的腿上,捏一捏,按一按,整得他又咧开嘴巴,一阵吱吱啦啦叫。最后,医生埋头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单子,递给胡子脸:“伤到股骨头了。”又仿佛自言自语道,“去照个片确定一下。”胡子脸到窗口交了钱,便走加急通道,把郑道清推进了CT室。
躺在冰冷的CT床上,郑道清看着一架机器摇来摇去,明显感觉到了一种宿命。他那时候还很小,跟父亲一起回山东老家。父亲随大军南下留在地方上工作后,就没有回过山东老家。乡里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人,两只手在郑道清脸上摸来摸去,就说他的腿弱了一些。一句话模棱两可的,却在郑道清心里留下了一道阴影。还青春年少,正是蹦蹦跳跳的时候,他就远离了一切体育活动。好不容易熬到了知天命,仿佛一切都有了定数,他在县长的位子上,来来去去有四个轮子抬着,前前后后有大秘书小秘书管着,两条腿,一双脚,已经不像从前那么重要,仿佛成了一种装饰,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那时一疏忽,他就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被疯狂的泥石流伤了一条腿……
原以为,不管多神秘的谶语,只要显现了,也就解了。殊不知,过去这么多年了,这两条腿一双脚的事情就像埋伏在他人生路上的一只老虎,一下又蹦了出来,而这一次却袭击了另一条腿……
郑道清从CT室出来,直接就住到了骨科病房里。胡子脸跑前跑后,拿着一把白花花的单子回到病房,站在郑道清跟前,已透着一脸倦容。仿佛是一种怨愤,又仿佛是一种怜悯,郑道清突然说了一句:“你怎么不取了我的命……取了我的命,大家都利索……”
胡子脸苦阴阴的,眼里噙着泪水,却不吭声不吭气的。
郑道清闷了一阵,接着问了一句:“你是新安县的人吧?”
胡子脸眼睛亮了一下,点了点头应道:“鄢久云是我爹。”
郑道清有些茫然地看着胡子脸,迟疑道:“我在新安县一辈子,认得的人太多,這个名字倒是听说过的,只是对不上号……”
胡子脸慢吞吞地道:“我说沟底村,您就该想得起来了……”
郑道清躺在床上,不易察觉地震了一下,接上道:“我想起来了,你爹是沟底村的村主任……前些年,我在家门口还跟他碰过面……我怎么会不晓得沟底村呢,那个地方差点要了我的命……”
换股骨头,这可是大手术。
郑道清躺在床上,医生护士在病房进啊出啊,抽血化验、心脏监测、血压测量、体温检测,大大小小十多项术前准备,包括股骨头选用,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是塑料的还是合金的,没有三五天工夫,显然是不行的。这期间,儿子从外地出差回来了。一进门,儿子在郑道清床上半边屁股坐下,接过胡子脸递过来的矿泉水,拧开盖,喝了几口,便抹抹嘴巴跟郑道清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说私了就私了啊,还是应该报一个案的……”
胡子脸听出来这其实也是说给他听的,便直戳戳地道:“我负全责,就是警察来了,也要划分责任……”
郑道清在一旁接着道:“事情已经出了,报案有什么用,警察来了,这条腿还是断了,没有必要报案……”
儿子接着道:“我知道肇事者是新安县老乡,也不容易,可感情不可以代替法规啊。”
胡子脸说:“我听郑县长的,没有必要报案……”
郑道清抬起一只手无力地挥了挥:“算了,算了,出了事情,就叫警察,也是一个麻烦,再说吧,现场不撤,人多,车也多,造成拥堵也不好……”
儿子说:“原则问题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这是大事故,不是小碰小擦,不能什么事情都和稀泥,打感情牌……”
胡子脸说:“也要讲感情……”
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僵持不下。这时候,一个老人急急忙忙走了进来,站在郑道清床前,颤声颤气地叫了一声:“老县长……”
郑道清愣磕磕的,听胡子脸喊了一声“爹”,这才反应过来:“你是老鄢……鄢久云……鄢主任……”
鄢久云说:“想不到我儿子……把你另一条好端端的腿也撞断了……”
郑道清的儿子跟胡子脸差不多年纪,只是一张脸要白净得多,这工夫仿佛找到了同盟军,抢过话道:“还是应该打‘122报案,哪怕拍几张照片,取几个人的证词……”
鄢久云摇了摇头,低声低气,却又坚决地说:“我不同意报案……报案会有更多麻烦……”
回过头来,老鄢就冲着儿子厉声厉气吼道:“你眼睛瞎啊!”
胡子脸蔫头耷脑道:“我一看见郑县长上了那人行横道线,就想到我们沟底村的事情。他是我们的大恩人啊!不知为什么,一下就紧张起来,竟然踩错了刹车……”
郑道清挥了挥手道:“过去的事情不要说了,我要是不当县长,就不会负责,也负不起这个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我既然在这个职位上,碰到了,就要管到底,我不可能躲,躲也不是我的为人……只是你们沟底村那一次泥石流,我没有想到,竟然成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病房里的空气一下凝重起来。大家不吭声不吭气的,仿佛都陷入沉思,回到了十多年前那个雨骤风狂的夜晚。
那一年,新安县一年一度的烤烟现场会在全县最偏远的一个乡镇召开。郑道清中午从县里赶过去,掰着指头跟全县的乡长镇长们算了个账,讲了个话,大意是烤烟生产问题虽然多,包括对土质的影响、对生态的影响,但现如今,离开了烤烟,乡镇财政就更穷,发工资都会成为问题,更谈不上发展,所以,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一种无奈的选择。大家一要清醒,二要下决心,必须稳住这根苗,戴枷跳舞也要跳,还要跳好,跳精彩。没有简单肯定,也没有简单否定,实事求是,大家听得很投入。气氛好,郑道清也来了兴致,原来一个半小时的讲话,竟然讲了两个半小时,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也没有人叫散会。会场上清风雅静,大家似乎都听入迷了。直到哪里电视声音开大了一点,《新闻联播》的声音传到会场上,会议才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最后一顿饭叫“会餐”,照例是要上酒的。郑道清坐在主桌,各乡镇的一个挨一个来敬酒,他即便一人抿一口,加起来也有几大杯。或许是借着酒劲儿,看天上黑乌乌一片,他说明天早上要开会,还是带着一班人马往县里赶。一路上大雨如注,两个雨刷器疯狂摆动,司机才勉强看清楚路面。出发得晚,又跑得慢,临近子夜,郑道清一拨人才走到一个叫沟底的村。正要穿村而过,司机眼尖,忽地看见路中间躺着几块大石头,便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雨还在下,只是比先前收敛了一些。郑道清跳下车,跟后面几辆车招了招手。看县长带头在雨中不管不顾的,除司机留在车上,一拨人跟着跳下车,冲到几块大石头跟前,冒雨清理出一条道路来。这时候,郑道清在雨中一淋,酒也完全醒了。凭着一种直觉,他往山坡扫过去一眼,便看见大股大股的雨水哗啦哗啦从山坡冲下来,隐约中,带着一面山坡东垮塌、西滚落,不时有一股一股浑浊的泥石流泻下来,整个山坡仿佛都被雨水浸透了,胀饱了,快兜不住一身附着在骨干上的皮与肉了。滑坡啊!郑道清一下子反应过来,毫不犹豫地指挥车开进村去,有警报器的拉响了警报器,没有警报器的拼命按喇叭,他则带着一拨人闯进村里,挨家挨户敲门叫人。一瞬间,整个村庄瑟瑟缩缩,从混沌中醒了过来。喊醒一家人,郑道清就叫他们跟着几辆车往外跑,有打着赤脚只套了一件汗褂的,有光枝裸杆只穿了一条短裤的,人越聚越多,在几辆车打开的灯光映照下,形成一股仓皇的人流,拼命往村庄的另一头跑去。郑道清跟小秘书走在最后,挨家挨户检查着,看整个村还有没有人家没叫到。这时候,他感觉整个大地一震,只听狂风骤雨中一阵沉闷的雷声轰隆隆滚动着,一面山坡便往沟底扑了下来。郑道清跟小秘书还没跑出村子,就被一股泥石流追上了。他被扑倒在地上,裹住了大半个身子。小秘书到底人年轻,被泥石流打了一个趔趄,往前窜两窜,总算从死亡的阴影里摆脱了出来……
整个沟底村被埋在了泥石流下面,但沟底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五六百号人都跑了出来。
尽管做了很多次手术,还是没有能够完全恢复,郑道清的左腿瘸了。场合上不好看,组织上因此找郑道清谈话,说这种情况他其实是可以调到市里殘联担任理事长什么的,但现任理事长还不到退休年龄,腿上的问题似乎比郑道清还严重一些,言下之意,郑道清是可以有别的选择的。私下里,一遇天气变化,尤其阴雨天气,郑道清那条腿还针扎一样有刺痛感。思来想去的,郑道清不得不选择提前退休。县里市里很给面子,念他的功,还一级一级往上报,省里最后给他发了一个奖状,弄了一个什么称号,算对他仕途的一个总结。不在任上,车没有,秘书也没有,两条腿,一双脚,又显得格外重要起来。而这时,他发现这腿这脚不仅支撑他的身体,还支撑他别的东西。县城是一个圈子社会,他只要走出家门,遇到老部下,或者老熟人,虽也哼啊哈啊,却总感觉他们目光怪怪的。很长一段时间,他躲在家里,怕出门,也怕见人。他想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他需要一个陌生的环境。儿子在市里上班,总算有了一个理由。他跟老伴儿卖了县里的房子,又在市里买了一套房子。房子在新区,远离有那么几个熟人的老城区,跟儿子的家也不在一起。一个星期天,他跟老伴儿不声不响地搬了过来。他在这座新的城市获得了一种新的自由。一城的陌生人,出出进进,看起来热闹,而其实互不相干,哪怕缺胳膊少腿的,大家也能视而不见。他感觉自在而快活。每天早晨,他吃过早餐,便跟老伴儿一起出门,走到半边街上,街对面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从桥上到河对岸,那岸边有一个很幽静的花园,他跟老伴儿在花园里散一散步,打一打太极拳,差不多一个上午的光阴就过去了。只是到了半边街上,他还要往上走一百多米,才有一座人行天桥,一上一下,再踅回来,这才算过了半边街,而这工夫,他已经沁出一额头的毛毛汗。反正是锻炼,反正是消磨时光,他也不觉得有哪一点冤,只是上下人行天桥的工夫,那条瘸腿有一种隐隐的疼。他需要老伴儿拉一拉、推一推,他没有一点怨气,老伴儿有时候说两句怪话,他还要开导她,说这就是现代城市的节奏啊……
郑道清几乎忘了那条瘸腿,仿佛那是胎中带来的,他只有心安理得接受,没有记忆,也没有痛苦。直到有一天,有人在半边街上小心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喊了他一声“老县长”,这才把他沉睡的记忆和麻木的痛苦重新唤醒……
这个人就是沟底村的老村主任鄢久云。
当时,郑道清回过头来,盯着眼前这个人愣了愣,不大肯定地嘟哝了一句:“你是……新安县沟底村的……村主任……老鄢主任……”
郑道清记得很清楚,他当年被泥石流裹住大半个身子,就是这个老鄢村主任带着两个村民,把他从泥石流里扒出来的。
鄢久云默默地点了点头,看郑道清还有些疑惑,便抬起手来,指着边上一群高楼道:“我们住在移民新区……我们沟底村没有了,大家都参加了国家生态移民,搬到了移民新区……”
郑道清一听,眼睛亮了一下:“我跟你们沟底村真的有缘啊!”他指了指边上一片旧一点也低一些的楼房说,“我就住在你们边上,大家成了邻居啊。”
鄢久云听了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两只手拉住郑道清两只手道:“我们现在还叫沟底村呢,哪怕原来的沟底村没有了,可在移民新区,一个村一个村的,我们还叫沟底村,大家还选我负这个责……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那晚要不是你把大家叫起来,不说房子,连五六百条人命都要被埋葬……”
郑道清挥了挥手道:“别提,别提,我的职责……”
鄢久云说:“我们沟底村的人记情啊,我们也很苦恼啊,这么多年了,我们却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听说你七十大寿的生日就这几天,我们沟底村的人想给你办一台酒……”
郑道清把手从鄢久云手中抽了回来,带着一种少有的豪气道:“免了,免了,我怎么可能让你们给我做寿酒……我不搞这一套……”
鄢久云愣在那里,竟不知说什么好。
郑道清转了话题道:“老天爷的安排,我又碰上你们沟底村的人……老实说,我搬到市里,都因为这条腿。不在位无所谓,可在位子上,残废了,人家看你的眼光,就奇奇怪怪的……”
鄢久云说:“难为老县长了,我们要怎样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啊?”
郑道清又挥了挥手道:“你们已经报答了。我看见你们搬到了移民新区,有了自己的幸福生活,我心里高兴,也很满足,感觉这条腿值了。哪怕残了、废了,也有一种骄傲,它毕竟换了五六百条人命……这是我从前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那天,老村主任一直搀扶着老县长,上天桥,下天桥,送到半边街对面,目送老县长,走到河对岸那个幽静的花园,这才回到移民新区家中。
那以后,郑道清再也没有看见过鄢久云。那次相遇后,郑道清像变了一个人,一下感觉到一种振奋,来来去去的,瘸一条腿,也不遮不掩。一天,有个似曾相识却又无从回忆的人在半边街遇上郑道清,懵里懵懂指着他那一条瘸腿道:“听说你当了县长啊,咋搞成了这个样子啊?”郑道清笑了一下,指着边上移民新区高高的楼群亮声亮气地说:“你看那些高楼,那里住着一个村的生态移民,我这条瘸腿就是为了救他们落下的。千值万值啊!一条腿残疾,换五六百条人命……”
那几幢高楼成了郑道清一条瘸腿的纪念碑。他在半边街上来来去去的,哪怕跟老伴儿打一打醋,买一买酱油,只要一抬头,看见那几幢高楼,他就心底敞亮,浑身充滿一种力量。
跟老村主任分手不几天,郑道清跟老伴儿大清早吃了早餐出来,走到半边街,却见一条黑白相间的斑马线又鲜又亮地横在了街头,几大步就可以窜到街对面,不用走人行天桥折腾……
那一瞬间,他心里一热,眼泪都要迸出来。这座城市仿佛知道他的艰难,那么善解人意,又那么体贴入微地接纳了他。而那天,他愣了一下,正好他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如果作为生日礼物,还有什么礼物比这条人行横道线更好啊!他弯下腰去,几乎要匍匐在地,吻一吻这片多情的土地,亲一亲这座美丽的城市。那个早晨,他在河边那个幽静的花园打太极拳,却怎么也调不好呼吸,他想这个沟底村的老村主任有点像他的福星,不管是机缘巧合,还是上苍安排,他搬到半边街这么多年了,这里从来没有人行横道线,而沟底村的人一来,这条线就画出来了,而且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画了出来……
郑道清往回走的工夫,走过人行横道线,慢慢悠悠地,还不时看一看等在边上的汽车,感受一回斑马线的特别,又神圣,又威严,这跟他那些年当县长的味道比起来也差不了多少啊。
不知不觉地,郑道清那天竟然走到了移民新区。但他到底没有走进新区里,他不知道自己来干什么,找老村主任?看沟底村的生态移民?怕他们忘了他这个救命恩人吗?想到这一层,他就觉得自己有一点不对劲了,便掉过头来,往自己家走去。
那次相遇,郑道清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跟鄢久云要一个电话号码,哪怕苦闷了,孤独了,能够说一说,约一约。原本挨邻则近,他却再也没有跟老村主任相遇过。城市也莫名其妙的,同一幢楼,同一个单元,甚至比邻而居,也常常不知所踪。老村主任哪里去了?多少年过去,他几乎把这个人遗忘了,却一下又在人行横道线上找了回来,而代价是另一条腿……
病房里,护士给郑道清量血压,一边量,一边说郑道清别的指标都很好,换了股骨头,恢复两三个月,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了。郑道清躺在床上,看不出来另一条腿也有毛病,她只管拣好听的说,虽懵里懵懂,郑道清听了,心情却格外好。
“老鄢啊,你这些年去了哪里啊?”郑道清找话头跟鄢久云聊起来,“我们上次在半边街分开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你。”
“他能去哪里啊。”胡子脸接过话去,替爹回应道,“他十天半月的,总要带一些人去一趟原来的沟底村。泥石流把沟底填平了,他们在那里种树。搬迁出来了,还想搬迁回去,我看只有等下辈子……”
鄢久云瞪了一眼儿子,回头跟郑道清说:“大灾大难啊,这么多人,都国家买单,我们也不好意思啊,趁还能够动一动,回去种几棵树,做一点弥补,也给国家减轻一点负担……”
几个人正说着,郑道清的儿子到走廊上打电话回来了。他板着一张脸,一进门就冷飕飕地道:“我思来想去,还是打了‘122报警,大事故不可以私了……”
“这本来就是私下的事情啊……”老村主任道。
胡子脸这时忍不住嘟囔了一句:“那斑马线是我们悄悄画来送给老县长的啊。”
郑道清跟儿子一听,都张着嘴巴,眼睛定在空中,大半天没有缓过神来。
鄢久云不紧不慢地说:“我叫这些年轻人半夜里去画的……不是您七十大寿吗。往年,我们有田有土,还养猪养鸡,送一点新米,砍一块肉,杀一只鸡,也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意,现在进了城了,真不知道送哪样好……原来的沟底村没有了,可现在的沟底村还在啊,我还是村主任,在自己家门口画个线,走个捷路,也犯不了哪样法啊。”
“难怪哟……难怪哟……我说怎么会这样巧,遇到你了,弄一个斑马线给我做七十大寿……”郑道清这工夫总算醒豁了,连声嘟嘟哝哝的,“这是城市啊,不是你原来那个山旮旯啊……”
鄢久云说:“城市也是人住的地方啊,山旮旯也是人住的地方啊。”
郑道清的儿子这工夫还在梦中一样,跟胡子脸瞪圆了眼睛道:“你们说的这些该不是真的吧……”
胡子脸板着脸道:“都这个节骨眼儿了,你都报了案了,我们还扯谎聊白的,有哪样必要啊……这些年,这斑马线淡了、旧了,大白天的,我们还维护过好几次……”
郑道清的儿子仿佛还没有醒过来,自言自语道:“就没有人发现这是一条假的斑马线……”
胡子脸一脸认真地纠正道:“这就是一条真的斑马线,什么东西只要大家都在使用,都在遵守,它就是真实可信的……”
郑道清的儿子总算嚼出一点味儿来,一字一句道:“人行横道线是一种行政强制性措施,只有国家有关部门画出来的人行横道线,才具有法律强制性,擅自施画,涉嫌违法啊。”
胡子脸说:“你都报了案了,我还有哪样说的,只有准备坐班房去……”
郑道清半躺在床头,一听有人要坐班房便冲着儿子嚷道:“我不认这个账啊,谁叫你报的案啊……”
鄢久云接上道:“我还真不知道交警会怎么判啊……我们负全责还不行吗……”
郑道清的儿子木木地说:“这还不是哪个负责哪个不负责的问题……”
这时候,一个交通警察胳肢窝夹着一个包走了进来。郑道清一看,是个小伙子,便欠了欠身子,算打了个招呼。交通警察掏出一个小本子,晃悠悠地说:“我听报案的人说,你们已经撤了现场,事故责任也明确了,没有哪样扯皮的,我给你们做一个笔录,备个案吧。”
胡子脸苦阴阴地说:“我们负全责……”
郑道清的儿子一旁插进来道:“现在关键的问题……这个斑马线是他们自己画的……”
警察停下手中的笔,狐疑地看着 他,大半天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肇事者自己画了一个斑马线?”
郑道清的儿子木木地点了点头。
警察挂一丝笑道:“我出警一天跑晕了头。只听说先前有城建画斑马线,后来有城管画斑马线,再后来有交通运输局画斑马线,现在又归到了我们交警来管这些设施,还真没有听说哪个人有吃雷的胆子敢自己画一个人行横道线来玩儿的。要都这样,这个城市还要哪样交通,都一家门前画一个人行横道线好了……”
郑道清的儿子嘟嘟囔囔道:“问题是……这个事情……它就發生在我们身边……”
警察的脸沉了下来:“行人走在违法的斑马线上被撞了……那……这行人也违法啊……”
郑道清的儿子绷紧一张脸道:“行人不知情啊。”
警察一针见血地说:“法律只讲事实,不知情,只算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因素,并不能够改变违法事实。”
大家一下都愣住了。
警察回头跟胡子脸道:“这个故事很幼稚啊……你作为肇事者,既然愿意负全责,就不要东推西推啊。”
胡子脸低下头去,一声不吭,仿佛默认自己是那个编故事的人。
警察接着道:“老实说,我一天忙得很呢,如果你不认这个账,还要编故事找理由开脱自己的责任,你们就只有打官司了。”
胡子脸抬起头来大声道:“我说了我愿意负全责啊。”
交通警察打了一个停止手势,递过去几页纸道:“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了,你在这上面签个字。”
胡子脸接过文件,在当事人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字,郑重地双手交给了交通警察。交通警察这工夫总算有了一点笑容,大大咧咧道:“这才算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嘛。”
警察接着把这几页文件递给了郑道清。郑道清半躺在床头,如梦如幻的,也在当事人后面颤巍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临出门,小伙子正了正大盖帽,胳肢窝夹紧皮包,又回过头来叮嘱郑道清道:“他如果还跟你编那些天花乱坠的东西,想逃避自己的责任,你给我打电话……”
郑道清手术很顺利。而且,医生看他另一条腿瘸,还给他在新的股骨头上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刚刚能够下地,胡子脸便扶着郑道清在医院走廊上来来回回地走,希望他能早一点康复。郑道清后来转到康复科,不需要胡子脸搀扶,也不需要拐杖支撑,完全可以自己走了。他感觉两条腿走起来比先前还要协调一些,只是在外人看起来,他那走路的姿势有一点怪。因祸得福啊,这是郑道清当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郑道清的儿子还惦记那条斑马线。云里雾里,不弄个水落石出,他显然不甘心。可真相呢,他找交管局,交管局说城管局画的;问城管局,城管局说建设局画的;问建设局,建设局说交通局画的;问交通局,交通局说交管局画的。转了一圈,他又回到了原地。事实上,大家都可以画,只是不知道哪条斑马线是哪一家画的,便只有一家推一家。
郑道清也很认真。他几个月后从医院出来,走到半边街斑马线跟前,居然一扭头,趔趔趄趄往人行天桥上走去。胡子脸追上去,追到天桥的台阶上。郑道清回过头来,指着胡子脸的鼻子道:“这个礼物我不能接受……我不知道则罢,知道了,我必须有错必纠……要不然,这跟受贿有哪样区别……”
胡子脸委屈地说:“交警不也认可了嘛……”
郑道清倔倔地道:“我知道了真相,就不能自欺欺人……我不但不接受这个礼物,而且我强烈要求你们沟底村的人,必须把这个礼物收回去……”
胡子脸说:“都生米煮成熟饭了,我们怎么收回?”
郑道清一字一顿道:“你给我把它抹掉,抹不掉,就把它铲掉。”
胡子脸一下子被堵住了嘴,找不到一句应答。
郑道清缓了口气接着道:“你这两天就把它铲掉……我刚从医院出来,多走一点路,多上下人行天桥,锻炼锻炼,其实更有利于康复……”
看郑道清不依不饶的,胡子脸只好点着头,一迭声道:“行,行,行……好,好,好……”
郑道清拍了拍胡子脸的肩膀,带一点笑容道:“我们都是明人不做暗事啊……一时一事,错了就改嘛……不怕犯错误,就怕一辈子犯错误……”
看来,那斑马线已经成了老县长的一个心病,不除不行,只有除之而后快。胡子脸跟他爹鄢久云打了个电话,老鄢跑回新安县,还在不停地种树,听儿子这么一说,他一句话也没有回,便挂了电话。
半夜,胡子脸提两桶黑色涂料,叫上当初一起画斑马线的一个村民,大摇大摆来到半边街斑马线跟前,借一街炽白的街灯,怎么一刷子一刷子画的,还怎么一刷子一刷子涂,只是不用取直,也不管长多少,宽多少,原来黑白相间的图案,现在见白就抹,黑一片就成……
只是还没有抹到一半,突突突来了两个骑摩托的巡警,把他们逮了个正着。胡子脸迷头迷脑的,还不知轻重地道:“这是我们沟底村的人送给郑县长的礼物,我们自己画的,他不收,还非要我们抹掉……”
一个巡警说:“你说是你画的,有证据吗?我们用证据说话……”
胡子脸嘟哝道:“我没有证据……但我不是疯子……”
另一个巡警则直直地指着胡子脸,不大耐烦地说:“你不要跟我装疯卖傻的……跟你直说了,有人举报你,说你前些日子在这里撞了人,心里还耿耿于怀,迁怒于这条斑马线,嫌这条斑马线碍事……”
事情到了这一步,胡子脸一下傻了眼。猛然间,他像发现了什么奥秘似的,打了一长串的哈哈。他这一出,搞得两个巡警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两个人连刷子、油漆等作案工具,一起被巡警带到了派出所。第二天,派出所又将案子转到了交通管理局。事情很清楚,交通管理局很快做出行政处罚,一是明确了胡子脸损坏道路交通设施的事实;二是责令胡子脸限期恢复被其抹黑的斑马线……
损坏公物,照价赔偿,一点也不含糊,胡子脸心服口服。拿着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他竟像拿着入学通知书一样高兴,又拉着尺子,画着线条,将夜里抹黑的斑马线一刷子一刷子画了回来。没有被抹黑的斑马线也有些旧了、淡了,他一鼓作气又填一回漆。整个斑马线都一色的新,他这才拿着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跟郑道清交涉。郑道清拿着盖了红戳戳的文件看了半天,只苦阴阴地笑,却什么也没有说。他显然还有哪一个地方不能释怀。
不几天,智慧城市建设全面启动,半边街人行横道线升级。人行横道两端安装了红绿灯,还配了读秒显示器。这一来,这条斑马线被镶上了一道大金边。种种现代设施一上,也笼统一罩,围绕这条斑马线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一下子土崩瓦解,如烟如雾般,散淡了,也逃逸了。直到这工夫,郑道清心里那道过不去的坎儿才算过去。
他心安理得地在半邊街人行横道线上来来去去。
他走路的姿势虽然不像从前那样瘸了,但两条受尽伤害的腿一前一后划动起来,还是显得有一点怪。
原刊责编 安殿荣 张金秋
【作者简介】赵剑平,仡佬族,1956年生,贵州遵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创作多年,先后在《人民文学》《收获》《民族文学》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二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困豹》(人民文学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赵剑平小说选》(作家出版社)。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六卷本《赵剑平文集》。多次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人民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