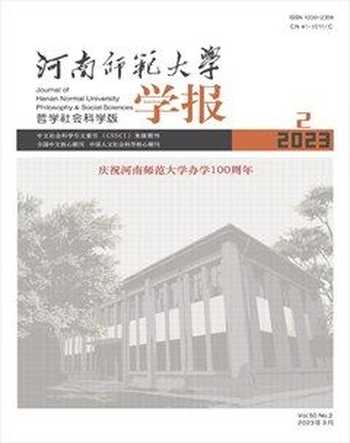论竟陵派“性情”说与“真诗精神”观
李永贤 周道河
摘 要:明代诗人对“真诗”的追求多强调主体“性情”之真,他们因对于“性情”的理解不同而产生出相异的诗学主张。钟惺、谭元春论“真诗精神”,分别从德性与才性两个方面对主体“性情”提出要求:一、主体德性之正,强调诗歌所表现的情感不能违反儒家伦理之道,是对“风雅”精神的继承;二、主体才性之奇,强调诗歌应展现出文采之奇秀与语言之简练,是对道家自然观的阐发。为了获取“真诗精神”,他们认为需要用“养气”的方式涵养主体“性情”,进而通过虚静内心和饱读诗书的路径加以修炼。“养气”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主体之“性情”与古人相合,德性与才性相融并呈现出“厚”的状态,便构成了“真诗精神”的外在特征。
关键词:竟陵派;性情;真诗精神;养气
作者简介:李永贤(1967—),男,河南新乡人,文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ZW119)
中图分类号:I20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3)02-0091-09
收稿日期:2022-11-16
钟惺在《诗归序》中提出:“真诗者,精神所为也。”[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90页。]对于“真诗精神”的理解,邬国平将其指向“幽情单绪”,认为钟惺、谭元春“向往幽事寂境的清思孤怀,缺乏阔大雄壮的气概和向未来进发的意气”[邬国平:《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0页。]。戴红贤认为:“‘真诗精神决非诗人的自然个性,而是主体对其自然个性进行锤炼、陶冶的艺术个性。”[戴红贤:《从“独抒性灵”到“真诗精神”:袁宏道、钟惺“性灵说”离合关系探析》,《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郑凯歌认为:“钟惺所谓的真诗‘精神指的是诗人、时代的核心风格及主要成就,即身份与本色。”[郑凯歌:《钟惺“真诗精神”说及其诗学史意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陈广宏认为:“‘精神是一种真正能够共享而又统摄发用之变化的本源性存在。”[陈广宏:《竟陵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1页。]李瑄认为:“‘精神指向超越物质层面的意志范畴。”具有“超卓”“遍在”“永恒”的特点[李瑄:《〈楞严经〉与竟陵派文学思想的指归》,《文艺研究》,2019年第8期。]。本文从“性情”入手,分析钟、谭所谓的“真诗精神”。自台阁体以降,明代文学发生的“场域”由宫廷逐渐走向社会,其内容也从政治教化缓缓转向主体抒情,就其本质而言,复古、公安、竟陵诸派都是主情、尚真的,只是由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个人才情,以及经历不同,诗人们对于“性情”的理解存在差异,才有了在“真诗”探寻道路上的不同思考。
复古派所言之“性情”,是为了“批判古典诗歌创作中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倾向,力图保持和恢复古典审美理想和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廖可斌:《明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57页。]。李东阳“将诗的自然抒情与诗的声律联系起来,提出了格调说”[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3年,第3页。],前、后七子沿着李东阳的道路走向了文学复古。随着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的发展,诗人关于“性情”的观念从板滞走向圆融,“诗学的发展也从单一走向多元,出现了‘人自有诗的诗学繁荣局面”[李永贤,孙达时:《儒学转向与诗学变革:明末清初诗学发展之一面观》,《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在王学左派的光芒之下强调“独抒性灵”[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开始越过诗歌“格调”说的藩篱,使自我俗世的性情率然表现于诗歌之中。在晚明思想收束[黄卓越认为,晚明思想上的转折大致发生于万历二十七年/万历二十八年。参见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60页。],以及士人心态转变[左东岭认为,从公安派到竟陵派,其心态由开放走向保守,就“性情”而言,则表现为对于德性的再度关注。参见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52-573页。]的背景下,钟、谭主张“真诗精神”,对于“性情”又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内容分四部分,第一、二部分从“性情”(德性与才性)分析“真诗精神”的内涵:一方面,钟、谭强调诗歌在情感上不能违反儒家伦理,比公安派更加重视主体德性;另一方面,钟、谭积极探寻诗歌的语言及文采,又沿用了公安派对主体才性关注的一些做法。第三部分论述钟、谭对如何获取“真诗精神”的理解。最后一部分则论述“真诗精神”的外在特征。
一
钟惺、谭元春二人对于德性的强调,一方面是对诗歌因王学左派“无善无恶”说带来的空疏无物之风的矫正;另一方面是对诗歌在公安派末流自然率性影响下过于强调俚俗之风的反拨。曹淑娟曾指出:“性灵论者因同时主张新奇乃真人性情的自然流露,故能自行发展出兼含正、奇的观念,避免过度强调奇的流弊。”在具体的论述当中,该文将公安派和竟陵派统之以“性灵派”,与复古派所标榜的性情之“正”相对立[曹淑娟:《孤光自照:晚明文士的言说与实践》,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0页。],此一观点似过于绝对。因为就诗歌内容而言,竟陵派已从德性的角度对“性情”进行了正邪善恶的区分。虽然公安派与竟陵派都注意到了民歌的“性情”之真,但是他们对于性情的理解截然不同。钟惺《秣陵桃叶歌并序》云:“予(伯敬)初适金陵,游止不过两三月,采俗观风十不得五。就闻见记忆,杂录成歌。此地故有桃叶渡,借以命名,取夫俚而真,质而谐,犹云《柳枝》《竹枝》之类,聊资鼓掌云尔。”[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57页。]袁宏道《叙小修诗》云:“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8页。]比较两人关于民歌之“真”的观点,袁宏道认为民歌“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而为“真声”;钟惺则以“俚而真,质而谐”为择取标准,认为语言上的俚俗本色与内容上的质朴相协调才是“真诗”。就内容而言,钟惺所言的“真诗”对诗中所表现的“情欲”设定了一个范围,即在德性的范围内表现个人之情性,以便诗歌在内容上不违反儒家的伦理道德。谭元春认为诗歌“了然于心,犹不敢了然于口,了然于口,犹不敢了然于手”[谭元春:《谭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68页。]。作诗虽强调“心手相习”“志气相随”[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94页。],但是,若“苟为无本,而以无忌惮之心出之”,则只能算是“横议”而已,“胸中真有,故而能言其所欲言,即所谓中伦之言,了然于心,又了然于口与手者是也”[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17页。],可见,诗人唯有做到胸中有“中伦之言”,才能做到心手相应。再如,钟惺认为战国之文有“雄博高逸之气,迂回峭拔之情”,虽能见其才情,但内容上“于先王之仁义道德、礼乐刑政无当”[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94页。],因而舍之。可见,竟陵派对诗文的内容有格外的注意,即不能违反儒家的伦理道德,个人的才情不能逾越德性的范围。
钟、谭二人编撰《诗归》也反映了此一观点。民歌多有儿女之情的描写,但是,民歌自然而发的情感也有正邪善恶之分,钟、谭对诗歌内容的性情之“正”给予鼓励:“媚而正,不伤性情。”[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页。]“性情极邪之言,装裹得极正便妙。”[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2页。]“不负心之言,性情亦正,歌中最难得。”[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0页。]对针砭时弊的诗歌,主张“周旋”的妙用。如《诗归》评沈佺期与崔湜关于金城公主与西蕃和亲所作的应制诗:“如此丑事,何劳群臣作诗应制?唐时君臣廉耻意气尽矣!每读之气塞。沈佺期、崔湜二诗,粗能回护。中寓伤讽,得诗人之意,然终不如勿作耳。”[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8页。]“周旋可谓极得体矣,然多此一番周旋,益觉损威中国,举动何可不慎。”[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页。]因“天威在上”[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3页。]而不得不作应制诗,然和亲之“丑事”有损“君臣廉耻”,更“损威中国”,若直接说破则不能“回护”,若敷衍了事则不能得“诗人之意”,处于两者之间,只能运用“周旋”与谨慎的修辞,以便让诗歌达到既“得体”又不违反道德伦理的审美效果。此外,诗歌在抒发个人情志的时候,亦需“择地而出”[谭元春:《谭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68页。],追求“风雅”。如,评论孟郊之诗:“仁孝之言,自然风雅。”[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07页。]“苦调自深厚中出,去风雅不远。”[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08页。]总的来说,无论是民歌中的儿女之情,还是对时事的讽谏规劝,抑或是个人的幽怨感激,竟陵派均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30页。]。这是对“德性”之正的坚守,也是对于“风雅”精神的继承。
二
钟、谭二人对于才性的关注,一方面源于他们早年受公安派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他们性格的孤僻狷介、落然寡合。此外,竟陵派所交之人,也多以奇士称之,如钟惺称周伯孔“慧性俊才,奇情孤习”[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7页。],称唐君平“落落然奇士也,生有绝才高志”[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0页。];再如,称与谭友夏有交的杨修龄,性格“落落然”[谭元春:《谭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605页。],称程子“风趣落落,然俊爽不可羁绁,而天机敏妙”[谭元春:《谭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610页。],等等。竟陵派对于才性的独特追求,在诗歌创作上集中体现在文采的奇秀与简练两个方面。《诗归》选虞舜时期《卿云歌》《八伯歌》《帝载歌》,认为“三歌与《明良》同为虞歌,然《明良》和雅有典谟气,三歌奇秀有骚些气。予(伯敬)选古诗虽意在存古,然去时太远,而昭然六经者,姑舍之,亦文士之习也”。[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页。]“《明良》和雅”,就内容而言属德性之正,其“典谟气”更接近典谟训诂的“六经”,由于它只注重内容的雅正,而缺少文采,所以不能入选;“三歌”文采“奇秀”,有“骚些气”,所以“三歌”可以入选。《诗归》选诗多注重诗歌语言的“字奇”“字奥”“语奇”[据统计,《诗归》中共有20处评语中提到“字奇”,5处评语中提到“字奥”,30处评语中提到“奇语”,6处评语中提到“语奇”。]等,也关注诗歌的对法、叶法、章法之奇等。谭元春《诗归序》云:“古人进退焉,虽一字之耀目,一言之从心,必审其轻重深浅而安置之。”[谭元春:《谭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66页。]古人对于字句的审视是为了表现其内心之才情,竟陵派对语言之奇奥的追求,正是他们“奇情孤习”[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7页。]性格在诗歌观念中的体现。
钟、谭二人亦追求语言上的简练,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诗评中。譬如,“唐人神妙,全在五言古,而太白似多冗易,非痛加削除不可,盖亦才敞笔纵所至”[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7页。]。“斩截有力在一‘即字,每文字简妙处,似有脱文,而解人读之了然”[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7页。]。“尚简”的诗语如何体现才性的奇崛?《诗归》云:“古人数字,便如一篇大文章;今人一篇大文章,不当数字。古人不全说出,无所不有;今人说了又说,反觉索然。则以古人简而深,今人繁而浅。”[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页。]相对“今人”文章的“繁而浅”与“索然”无味,“古人”文章则“简而深”,人们往往在“古人”文章浅易的表达中,领略到深邃的情思内涵,进而让自我的“灵心”在领悟之际得以展现。正如谭元春所说:“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一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谭元春:《谭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66页。]“自出眼光之人”的自我才性唯有在体悟到古人“性灵”的时候,方能得以顯现。
在谈及为何追求诗歌语言“尚简”的原因时,钟惺《文天瑞诗义序》指出:“《诗》之为教,和平冲淡,使人有一唱三叹,深永不尽之趣。……然秦诗《驷驖》《小戎》数篇,典而核,曲而精,有《长杨》《校猎》诸赋所不能赞一辞者。以是知四诗中,自有此一种奇奥工博之致。”[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39页。]在钟惺看来,《诗经》风格上的“和平冲淡”可“使人有一唱三叹,深永不尽之趣”,简练的语言可以达到丰富的表达效果;《诗经》风格上的“奇奥工博”,则指“典而核,曲而精,有《长杨》《校猎》诸赋所不能赞一辞者”。他在《诗归》中也多称赏诗歌语言所产生的意外妙处,如“其语言之妙,往往累言说不出处,数字回翔略尽”[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2页。]“妙在一篇中,语意有落落不属处”[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7页。],等等。
语言“尚简”是对诗歌言约义丰的追求。所谓“诗,道性情者也。发而为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非谓其事之所不可无,而必欲有言也”[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33页。],同时也是对比兴手法的继承。钟惺《简远堂诗近序》曰,作诗需“性情渊夷,神明恬寂,作比兴风雅之言”[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4页。],其中的“比兴”便是就语言的表达方式而说的。总的来说,钟、谭二人对诗歌语言“奇秀”“尚简”的追求,既是表现个人才情的需要,也是继承比兴传统的需要。至于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文心雕龙》曾云:“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第352页。]语言“尚简”近乎“隐”,意在追求“文外之重旨”;辞采“奇秀”近乎“秀”,意在追求“篇中之独拔”。“隐”与“秀”当然不能刻意为之,只能“自然会妙”[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第356页。]。可见,在才性的表现上,竟陵派还是受道家自然观的影响较大。
三
钟、谭二人认为诗人必须凭借“养气”的功夫来涵养主体“性情”,方能获取“真诗精神”。有论者指出:“‘养气关涉创作主体主观修养和精神状态的培养,它凝为情,发为志,散而为文。”[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56页。]钟惺告诫周伯孔要“多读书,厚养气”[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8页。],告诫王永启要“读书、观理、养气”[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66页。]。谭元春称赏蔡敬夫是“惧以养气,气以养智”[谭元春:《谭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506页。],等等。按照钟、谭二人的理解,“养气”的过程,可分为“辨气”“积气”“行气”三个部分。
(一)“辨气”。钟、谭二人认为每一篇诗作中都有不同的“气象”,对这些“气象”进行分析的过程就叫做“辨气”,它是人们获取“真诗精神”的主要条件之一。古人“性情”以“气”的方式寓于诗歌之中,“辨气”的过程就是感受诗歌气象的过程。钟、谭二人在《古诗归》中认为左思的诗歌“气和语厚”[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4页。],陶渊明的诗歌有“一段渊永淹润之气”[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8页。],谢灵运的诗歌“气清而厚”[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5页。],等等。诗人所禀之气不同,诗中所寓之“气”也就自然有别,钟惺曰:“陈正字律中有古,却深重;李太白以古为律,却轻浅。身分气运所关,不可不知。”[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页。]“身分气运”不同,诗歌气象就不同,“真诗精神”的具体表现更会随之相异。钟惺《韵诗序》曰:“语有《三百篇》,有汉郊祀、乐府,有韦、曹诸家,而要不失为彭举。夫风雅后,四言法亡矣。然彼法中有两派。韦孟和,去《三百篇》近,而韦有韦之失;曹公壮,去《三百篇》远,而曹有曹之得。彭举幽,在远近之间。彭举诸体诗,轻重古今,出没正变,有王、孟之致。”[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5页。]时代已经发生变化,诗歌作者也并非一人,故《诗经》之后的四言诗便会呈现出和此前不一样的“气象”,所谓汉郊祀为“事鬼之道也。幽感玄通,志气与鬼神接”[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页。];韦孟四言诗“肃肃雍雍,有雅颂之音”[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页。]而气“和”;曹公“直写其胸中、眼中一段笼盖吞吐气象”[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3页。]而气“壮”;彭举“有王、孟之致”而气“幽”,等等。
“辨气”的目的是说明诗人才性之于“真诗精神”的重要性。诗人写诗应循着自我灵心,去找寻与之相应的表达方式,正如汉郊祀“不学雅颂,自为幻奥之音”[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页。];韦孟将讽谏寄于家世的叙述之中;魏武帝之诗不失“魏武身份”[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4页。],等等。如果诗人一味恪守单一的法度、靠定某一派别,而不求作诗的变化,最终往往会与“真诗”失之交臂。钟惺认为:“诗文有创有修,不可靠定此一派,不复求变也。”[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页。]此外,“辨气”的本身还要有“不膈灵之眼”[谭元春:《谭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66页。],这一过程也是对主体灵心的发现与修持。
(二)“积气”是对“气”的涵养,也是一个悟道的过程。主体唯有在长时间的“积气”中涵养性情,才有获得“真诗精神”的可能。“积气”的途径,一方面依靠主体内心的虚静,另一方面则需要主体博览群书以厚植学养。
第一,依靠主体内心的虚静。首先,诗心的“觸发”源于现世中的人事变迁,钟惺曾说:“夫诗必有资,取精用物之谓也。”[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23页。]其次,诗人在俗世的纷扰之外构建了一个诗意空间,正如钟惺《诗归序》所说:“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90页。]然而,如何调适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呢?钟惺认为:“风雅世务,达人不分为二。”[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35页。]这本是赞赏蔡敬夫的语言,对于伯敬来说,此种境界是达不到的,因而他在《蔡敬夫自澧州以诗见寄和之》中感叹道:“何以尘务中,穆如清风咏。乃知寄托殊,形神本渊净。以兹暇整情,何纷不可定!”[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页。]如果内在性情“渊净”,即使有俗世的纷争又能怎样呢。
然而,晚明党争激烈,诗人主体的性情很容易被损伤。钟惺《汤祭酒五十序》指出:“诸凡摧抑人才,破坏元气,滋议论而伤国体之事,即不以先生(汤宾尹)一人终,实以一人始。”[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61页。]《告雷何思先生文》亦云:“方今景象,底滞痿蹶,已成一不快世界,中复虚羸,度之运数,必有快人居其间。势必用一番更张,露一番精采,恐必将有一等伤元气之人与伤元气之事迎之。”[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633页。]为了使主体自我的精神和元气不受损伤,诗人必须从中将自己抽离出来,钟惺在晚明党争之中秉持“一无依傍的立场”[陈广宏:《竟陵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9页。],即是典型的表现。
此外,明代科举出现了“士商互动”的现象。与钟惺同乡的李维桢,曾为商人撰写碑铭之类的文章达百篇之多[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8-543页。];明代中后期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则又为文人结社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邱仲麟:《中国史新论:生活与文化分册》,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第267-316页。]。在与文人或者商人往来的过程中,诗人往往会写一些应酬性的诗歌或者程式化的墓志铭,这种“为文造情”的书写往往会给自我性情带来负面影响,谭元春就指出:“今人惯喜作寿诗,予谓性情所乘,万不可以此损伤。”[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4页。]那么,诗人应该秉持一种怎样的处世态度呢?钟惺《简远堂近诗序》云:“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虚心直躬,可以适己,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4页。]显然,在钟惺看来,个人应该和世俗保持一段距离,保护自我的真性情不被社会所浸染。他在《诗归》中也指出内心之“静”的重要性,如评《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荡涤放情志”句所言:“未有居心不净,而能放者。”[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诗人只有在扫除外在的喧杂和内心的杂念之后,才能由静其心,进而达致抒发情志的目的。
第二,依靠主体的博览群书。《文心雕龙》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第14页。]圣人的文章中蕴含着伦理之“道”,人们可以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涵养德性。当然,“真诗精神”追求的是德性与才性的融洽,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占有”,个人的才性不能被束缚在古文之中。晚明“正文体”的出现是知识界重建思想秩序,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一种象征[张德建:《正文体与明代的思想秩序重建》,《文学遗产》,2019年第1期。],钟惺认为,“正文体”的根本在于“平日博于读书,深于观理,厚于养气”之后“得其才情神志”[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65-366页。],“读书”与“观理”不应止于圣贤所述之文,也可兼及佛道之学,如此才能达到且“博”且“深”的境地,才能厚养其气。除了阅读古人之文以外,编撰古人之诗文,也可达到浸润主体性情的目的。《诗归》的编撰在于“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89页。]。缪鉞曾指出:“诗之质有三,一曰深远之思,一曰温厚之情,一曰灵锐之感。”而“人固有生而具温柔敦厚之情者,然其情真矣,未必能深;深矣,未必能广。……欲情之深而且广,必多读古诗人之作,以古人浓挚之情引己之情,浸润激荡,日大以长,如雨露之润草木,肥甘之养肌理。至于有深远之思,则必识通今古,学贯天人,胸襟超旷,阅历深宏,所谓真本领也。”[缪钺,缪元朗:《古典文学论丛》,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06-409页。]诗人因现实的遭遇而触发情感,但由此所产生的现实之“情”与古人“性情”并非完全符合,况且诗人的当下之“情”只不过是一念之感而已,并非浓厚之情,所以,要想达致浸润主体性情的目的,就必须借助古人诗歌中深厚情思的移情作用。钟惺曰:“无彭举之才、情、识、诣,百七章中,必不能无断缺补凑。”只有具有一定的“识”“诣”的诗人,才能将自己的“气”培育深厚,他的“才”“情”才不会受到体制的束缚。钟惺告诫伯孔要“刿心于唐以上之所至”,要“多读书,厚养气”,作诗要达到自然无痕,才能避免走向“其情事合前人者已十之一二……其口语堕近人者亦十或三、四”[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7-308页。]的错误之路。
无论是上述哪一种养气的方法,“积气”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都需要主体用内心的“诚”去坚守。钟惺《赠唐仲言序》云:“(唐仲言)五岁以后所出为诗文及注古之为诗文者,皆其心所授于其口,其口所授于人之耳与手者之积也。其类既多,其体既备,其立意又皆以该且核为主。……然能使人之为仲言诵多且久于其自为诵,数十年中如一日,如一人者,仲言之诚所为也。”[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67-368页。]唐仲言因为心“诚”,且常年积累,最终才达到了“自为诵”的境界。再如,钟惺《送钱先生归娄东序》说他自己与钱先生之事,“精神往来,合为一身。中心达于面目,意气通乎神明。诚至而巧生,医王所用之药,仍是众工所用,而神存心手,变化出焉”[钟惺:《隱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6页。]。钱先生之所以被称为“医王”,主要在于其内心的极“诚”,用医者的诚心感之于患者,所以,他的用药虽然和别人没有多大区别,但是由于能与患者取得精神上的相通,因此常常能取得药到病除的效果。喻之于诗,虽然面对同样的古诗文,抑或是同样的自然风光,只有以心感之的心诚者才能和它们取得精神上的共鸣。
(三)“行气”。“行气”是“真诗精神”的呈现环节,谭元春曰:“气之所为,不可使复泄也。诚以蕴之,惧以守之。其诚弥积,其惧弥深。惧日以深,而气日以达。一旦不得已而用于世也,则非我欲其然也,气自然也。”[谭元春:《谭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506页。]创作主体的内心之“气”经过“诚以蕴之,惧以守之”的积累之后,便会“自然”地流露于诗歌的创作之中。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行气”需要以“积气”为基础,“气”唯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自然地倾泻出来,不可强而为之。《古诗归》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云:“此古今第一首长诗,当于乱处看其整,纤处看其厚,碎处看其完,忙处看其闲。此隆古人气脉力量所至,不可强也。”[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因诗人所积累的“气”比较隆厚,他才能将“乱”与“整”、“纤”与“厚”、“碎”与“完”、“忙”与“闲”和谐地统一起来。钟惺《诗论》云:“趣以境生,情由日徙。……以予(伯敬)一人心目,而前后已不可强同矣。”[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59页。]对于《诗经》的体悟,他会因前后所积之“气”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不可强求其同。其次,若强而为之便“有痕”,创作主体唯有在涵养之气达到一定状态的时候才能做到无“痕”。钟惺认为:“‘我辈诗文到极无烟火处便是机锋,此语甚深,可思也,痕亦不可强融。”[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50页。]最后,诗人所禀之气行于诗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不能刻意为之。钟惺认为:“极奇莫如造化,妙在皆由自然。”[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2页。]当然,“自然”之中也有“偶然”之意,所谓“偶然妙想,偶然妙舌,深求则失之”[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9页。],元气“偶然吐出”[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98页。],常常会造成诗歌“偶然真境”[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7页。]的出现。
可见,“行气”是一个触物起兴的过程。当主体所涵之“气”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诗人经常会触物起兴,因外在事物的触发而激起灵感的闪现,进而将所体悟的“真诗精神”呈现出来。触物起兴发生于自我与外物相融的时刻,一如伯牙学琴:
伯牙學琴于成连,三年而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未能得也。成连曰:“吾之学不能移人之情。吾师有方子春在东海中。”乃赍粮从之。至蓬莱山,留伯牙曰:“吾将迎吾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伯牙心悲,延颈四望,但闻海水汩没,山林窅冥,群鸟悲号。仰天叹曰:“先生将移我情!”及援琴而作此歌。[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20页。]
伯牙师从成连三年,学的是作琴技巧,此时的物与我、人与琴是分开,而非融合的,“不能移人之情”而多刻意为之。援琴作歌则需要在“精神寂寞”处,谭元春评“精神寂寞”四字云:“大道妙艺,无精神不可,然精神有用不着处。‘寂寞二字,微矣,觉‘专心致志四字至此说不得。”[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页。]“精神”如同摩诘诗中处于“有无中”的山色,不再以全然的理性看待外物,主体的主体性似乎在慢慢消失,诗便于此时发生。相较于“精神寂寞”,“专心致志”在这里显出了太多的目的性和主体性。喻之于诗,诗歌发生于“精神寂寞”处,主体之情与外在之景相融,诗歌与诗人相融。在诗人与外在事物的接触之际,其内心的感情油然而生,就像伯牙因成连“旬时不返”,其悲切之情从胸中油然而生一样,并与“海水”“山林”“群鸟”相融合,这便是“移人之情”,然后援琴作歌,则自然就能做到诗与乐相融、主与客浑融。
情与理相融的极致不是用理性的语言表现,而是用外在的物象呈现的,所以,“行气”需要落实在具体的物象之上,即“真诗精神”需要通过诗歌意象呈现出来,这就涉及一个“取象”的过程。对于“象”的选取,钟惺《蜀中名胜记序》云:“要以吾(伯敬)与古人之精神,俱化为山水之精神。使山水文字不作两事,好之者不作两人,入无所不取,取无所不得,则经纬开合,其中一往深心,真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97页。]所谓“出乎述作之外”,在于通过山水寄托“吾(伯敬)与古人之精神”。再如,钟惺《寄吴康虞》云:“旧识南中半,公还自古人。意于林壑近,诗取性情真。”[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02页。]可见,竟陵派诗人的“取象”范围应以“山水”“林壑”为主。
竟陵派诗人所选取的物象多为细小之物。《唐诗归》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云:“少陵不用于世,救援悲悯之意甚切,遇一小景、小物,说得极悲愤、极经济,只为胸中有此等事郁结,读其诸长篇自见。”[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5页。]评《苦竹》云:“每一小物,皆以全副精神,全副性情入之,使读者不得不入。”[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1页。]杜甫咏物诗“生其性情,出其途辙”[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5页。],其咏物诗虽然都出自“性情”,但是由于所咏之物不同,所以寄托的情感也就不同。至于选取“小物”“细物”的原因,一方面,“就小物说大道理,古人往往如此”[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页。];另一方面,“豪则泛,细则真”[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7页。],将感情寄托到细小的事物中,才能显得真切具体。
总之,“行气”的过程与“真诗精神”的呈现相关,诗人通过这一程序将自我的涵养之情“外化为作品的气脉和节律”[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56页。],外化为诗歌中的“一片真气浮动,无一毫境事碎琐参错”[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2页。]。所谓“活则深,板则浅”[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2页。],写诗不是材料的堆积,如果诗人不懂得“行气”之法,他的诗作便了无生气,正如《古诗归》评张华曰:“古今极博人,下笔出口多不能快。人谓司马迁高才,恨其不博,予(友夏)谓使其极博,恐胸中腕中反不能如此。试观张茂先诗,有何首高妙动人处?《答何劭诗》《杂诗》已被选而复汰之,味不足也。”[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6-147页。]
四
诗人通过“养气”的功夫涵养性情,但是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获取“真诗精神”,这就不得不说一下“厚”与“真诗精神”之间的关系了。从主体“性情”的角度来看,钟、谭二人所谓的“真诗精神”是对德性之正与才性之奇的追求。那么,才性与德性之间,一奇一正,如何才能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呢?钟惺《东坡文选序》云:“昔铜台妓有妙于音而性恶者,魏武帝欲杀之而难其才。乃选数十百人,一时俱教。久之,有一人音与之齐,即杀恶性者。此所谓有东坡文,而战国之文可废之说也。”[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95页。]在德性与才性之间,他更重视德性的有无,即魏武帝“杀恶性者”之意。但是诗文创作离不开主体的才性,正如魏武帝欲杀“妙于音而性恶者”却“难其才”,所以,他对才性也很珍视。那么,如何在这一两难之境中做出取舍呢?一方面,就德性而言,应对有才而“性恶者”,修养其德性,使之存善去恶而又保有其才。另一方面,从才性的角度来说,则需修持主体的“灵心”,使其与德性相谐,并达到“厚”的状态。如钟惺《与高孩之观察》曰:“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第(伯敬)尝谓古人诗有两派难入手处:有如元气大化,声臭已绝,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诗十九首》《苏李》是也;有如高岩峻壑,岸壁无阶,此以险而厚者也,汉郊祀铙歌、魏武帝乐府是也。非不灵也,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51页。]“诗至于厚”则“无余事”,追求的是主体德性与才性的相谐,“妙合无痕”[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页。]而达到的“厚”的状态。就作诗的门槛来说,有“灵心”才能作诗,强调的是个人之才性;而个人才性需要与德性融合并达到“厚”的状态,才能获得“真诗精神”。进一步来说,“厚”的取得是以古人精神作为导向的。钟惺认为作诗需“尽其才以达于古人”[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21页。],谭元春《汪子戊己诗序》认为,“汪子以抑塞之奇才,闭门十余年,与古人精神相属”[谭元春:《谭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87页。]。他们均强调主体性情要符合古人之精神[李永贤《论清初诗歌选本中的诗学反思》指出:“明末竟陵派以提倡性灵为号召,反对复古派的丧失性情”,其追求的性灵以古人性情为归。参见李永贤:《论清初诗歌选本中的诗学反思》,《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而“真诗精神”的核心便是德性与才性的相融与相谐。
由于时代不同,主体的才性与德性会各有偏向,所以,主体通过“养气”功夫所获取的“真诗精神”便存在差异。由此而创作的诗歌或偏于德性呈现出“平而厚”的风貌,《诗归》多以“平”“和”[《诗归》与“平”有关的评语,如“平调不肤”“壮语平调”“平平浅浅”“平遠”;与“和”有关的评语,如“气和”“清和”。]等字评价诗歌风貌上的平和。当然,偏于德性并非忽视才性,譬如,评宋之问《途中寒食》云:“此诗可谓平极矣,何尝不动奇眼。”[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页。]评语说的是诗歌应在风貌平和之中拥有奇思奇想。或偏于才性而呈现出“奇而厚”的风貌,《诗归》多用“奇”“奥”[《诗归》中与“奇”有关的评语,如“雄奇博厚”“幽奇深秀”“正理奇调”“奇险”;与“奥”有关的评语,如“清奥”“奇奥鲜秾”。]等字来评价诗歌风貌的奇奥。同样,所谓“奇”也离不开性情的朴厚,其原因在于“刻生于朴,奇生于厚”[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页。]“妙在奇奥处从朴野出”[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竟陵派诗人所强调的“厚”不只是文学风格论的范畴,在更大的程度上属于心性本体论的范畴。在他们看来,“厚”是对心性本源之完整不可分割性的描述,是德性与才性的完美融洽,李瑄认为:“‘厚不是审美的中正深婉,而是本体遍照万物时的涵容状态,是虚静感通与浩然充满的统一。”[李瑄:《〈楞严经〉与竟陵派文学思想的指归》,《文艺研究》,2019年第8期。]可见“真诗精神”是创作主体主客未分、物我相冥状态的诗性展现,所谓“才不由天,以念所冥为才”[谭元春:《谭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66页。]“未有不幽恬渊净,而可谓真挥霍弘才者”[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35页。],“冥”与“幽恬渊净”正是对主体性情达到“厚”时的准确描述。当主体经过“养气”功夫而使得性情达到“厚”的程度时,便接近于“道”了,谭元春《王先生诗序》云:“夫性情,近道之物也,近道者,古人所以寄其微婉之思也。……王先生欲以古人之道,安于性情而行于诗。”[谭元春:《谭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80页。]言性情为“近道之物”,接近“性”之本体。正是在此基础上,陈广宏认为公安派与竟陵派论诗有表现理论与形上理论之分[陈广宏:《竟陵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4-326页。],以突出竟陵派“真诗精神”的超越性质,此一观点有其合理性。然而,诗歌必然是涉文字的,若全然涉“道”,如何用语言文字去表现诗人“与道交融的无言境界”[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台北联经出版社,1981年,第82页。]?显然,竟陵派诗论中的“性情”概念是包含有“情”之发用的,所谓“古人所以寄其委婉之思”“以古人之道,安于性情而行于诗”,实则包含了性情之“性”与“情”两个方面,只是“性”与“情”两者之中以“性”之本体为主,因而其诗论以形上理论为主而兼有表现理论,其性情可近“道”而不等同于“道”。而“性情”涉“道”的部分就是对“真诗精神”的一种阐释:就德性而言是儒家之伦理,此为本;就才性而言是道家之自然,即主体之“灵心”。
也斯曾说:“我抬头看见一朵云无言远去,而我仍走在人来人往的灰尘的路上。”[也斯:《山光水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13页。]或许这也是钟、谭二人所面对的境况吧!在一个逐渐世俗化的社会中,主体之“性情”难免不被周遭的喧嚣所侵扰,诗人渐渐失却了作诗所需要的那份纯粹与天真,拥有的只是处理世俗琐事所需要的世故与理性,如此作诗便如黄茅白苇般毫无生机。如若仍有“真诗”存在,则需暂时抽离于世俗之当下,涤清内心之杂念,或平心读书与古人之精神相合,或虚静其心在山光水影中体悟自然。在不断的读书、观理之中厚养其气,等待某一刻灵感的出现,从而完成一首诗的写作,如此方能获取“真诗”,正如钟惺所云:“平心以读书,虚怀以观理,细意定力以应世,然后发而为言,有物有则。”[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17页。]主体之性情不为外在之喧杂所困扰,不为传统之诗法所束缚,以自我之灵心与古人精神相沟通,等候偶然的一刻,将领悟到的“精神”通过诗歌传递下去,以此抵挡时间的虚掷与浪费,或许这就是钟、谭二人期望的“真诗精神”吧!然而,期望落到实处时,由于钟、谭二人受性格、遭遇以及社会思想等因素的影响,所谓的“真诗精神”在其实际创作中则偏向“幽深孤峭”的一面。
The Theory of “Temperament” and “True Poetry Spirit” by Jingling School
Li Yongxian,Zhou Daoh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
The poets in Ming Dynasty mostly emphasized that “true poetry” is the truth of the subjects “temperament”,and they had different views about poetics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emperament”.Zhong Xing and Tan Yuanchun comprehend the “true poetry spirit” through the pursuit of the subjects virtue and talent.First, the integrity of the subjects virtue emphasizes that the emotion expressed in poetry should not violate the Confucian ethics, which i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pirit of “elegance”. Second, the subject of remarkable talent, emphasizing that poetry should show the beauty of literary talent and language concise, which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aoist view of nature. In order to obtain the “true poetry spirit”, they believed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the subjects “temperament” in a way of “nourishing qi”, and then cultivate it through the inner peace and full reading of poetry.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nourishing qi” is to make the “temperament” of the subject conform to that of the ancients. Virtue and talent are integrated and present a “thick” state, which constitutes the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true poetry spirit”.
Key words:Jingling school;temperament;true poetry spirit;nourishing qi
[责任编校 海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