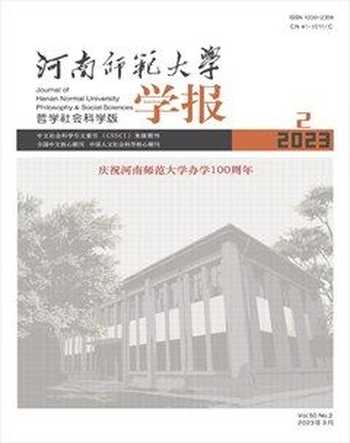从清修《四裔考》看乾隆时期清廷的世界秩序观
摘 要:“四裔”是古代中国对周边族群或国家的笼统的称呼,在今天看来自然已不恰当,不过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称呼体现出中原地区的族群看待周边族群时常有的以自我为地理中心和文明中心的态度。这种世界秩序观对史书纂修有重要影响。乾隆朝官修《清通考·四裔考》所记包括有朝贡义务的属国和西洋互市国两类,对属国的书写凸显出清方作为宗主国的优待,以图巩固臣属关系,同时将远西各国来华求互市也描述为“输诚称贡”。《四裔考》对这两类国家的书写共同体现出清廷对中原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坚持,这种态度延缓了清廷对当时日新月异的新世界及世界关系的真正了解。
关键词:世界秩序观;《四裔考》;历史书写;属国;互市国
作者简介:刘骏勃(1990—),男,陕西西安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主要从事史学史和文献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项目(22VJXT005)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3)02-0114-08
收稿日期:2022-03-01
世界秩序观通常指一族或一国对于其自身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系统认识。在中国古代,一般来说,农耕便利的地区事实上要比其他农业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更早进入文明,而这类农耕便利的地区总是少数,从地理上看一般处于其他后进地区的包围之中,因而这些地区的人民逐渐就会产生一种观念,即认为自己所处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据学者研究,商代就已出现了“中商”“中土”与“四土”“多方”的称呼[王爱和:《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4—95页。]。这一观念经过周人的继承和强化,在现存先秦典籍中有许多体现,如周代的五服制度、《春秋》三传中的言与事、孔孟对夷狄的言论等,成为后来“中国”意识及“华夷之辩”等思想的重要源头。葛兆光指出:“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那个时代,也许更早些时候,中国人就在自己的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一个‘天下,他们想象,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大地仿佛一个棋盘一样,或者像一个回字形,四边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华夏或者诸夏,诸夏之外是夷狄,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与南夷北狄相对应的‘中国概念。在古代中国的想象中,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蠻,文明的等级也越低。”[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第44页。]显然,中国古代这一想象中的世界秩序观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地理上的“中国中心观”,同时或者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上的“中国优越观”,两者相互支持,互为表里,并在具体层面表现为朝贡制度。
这一世界秩序观在古代的舆图、职贡图等图像中有最为直观的表现,同时在历代史书中也有反映,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记载模式。在《史记》中,表现为《匈奴列传》等几篇单行的传,在《汉书》中也是如此。后来逐渐有了专门的名称,如《梁书》中的“诸夷”、《南史》中的“夷貊”以及《晋书》中的“四夷”等,并且依照“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类目进行划分。在卷次上,这类内容亦逐渐有了固定的位置,一般都列于全书末尾“叛逆传”之前。除了纪传体正史外,这一世界秩序观也影响着其他体裁的史书的撰写,尤其典志体史书在这方面有突出的体现。作为典志体的开山之作,杜佑的《通典》最末《边防》一门,虽不以“四夷”等命名,但二级类目却分别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可以说实际上就是一篇“四夷传”。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有《四裔考》,虽改换了门类名称,但从其序文可知正是对《通典·边防》的继承,并由此形成一种典范。作为马氏《通考》的续作,乾隆朝官修《续通考》和《清通考》中均继承了《四裔考》的门类设置。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清朝时“四裔”的范围较前代已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在《清通考·四裔考》[乾隆时期修成的《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及民国时刘锦藻所撰《清朝续文献通考》中均有《四裔考》,除特别说明外,本文中单称“《四裔考》”或“清修《四裔考》”时均指《清文献通考·四裔考》。]中有明确的体现,但另一方面,清修《四裔考》中又表现出对此前中原统治者一贯秉持的世界秩序观的某种继承,这种态度使《四裔考》对所记两类国家的历史书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变动的“四裔”与不变的“中心”
在《文献通考》中,马端临使用了“四裔”的名称,而非先秦以来常见的“四夷”。《说文》云“裔,衣裾也”,段玉裁据玄应所引改为“衣裙也”,古注中又有“边也”“表也”“远也”等训释,最明白的是《方言》注云:“边地为裔,亦四夷通以为号也。”[均见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64页。]可见在四边的意思上“四裔”和“四夷”基本等同,但因为“裔”本身有“边”的意思,所以隔了一层,某种程度上消去了“夷狄”等直接含有歧视、侮辱意味的字眼,这可以从清修《四库》删改“夷狄”等字,但不改“裔”字得到证明,所以乾隆朝官修《续通考》和《清通考》均保留了《四裔考》的类名。在《通典》及《文献通考》中,“四裔”之范围东有朝鲜、日本等,南有牂牁、夜郎等,西则吐蕃、西夏等,北则匈奴、鲜卑等。清朝开疆拓土极多,从前所谓的“四裔”中有不少已变为版图之内的郡县。《清通典·边防》序言中曾举例说:“如挹娄、靺鞨、三韩为今黑龙江宁古塔诸处,早为内地;乌桓、鲜卑、蠕蠕、库莫奚、突厥、鞑靼为今蒙古四十九部及喀尔喀诸部地;邛都、筰都、冉駹为今两金川地;鸡笼山为今台湾府地;南诏为今大理府地;吐蕃、朵甘、乌斯藏为今西藏地;白兰、吐谷浑、党项为今青海部地。”[嵇璜等:《清通典》卷9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08页。]由于清修《续通考》所记是各前代情况,“第历代史册惟就一朝形势以为畦畛,据事直书,用志沿革”[嵇璜等:《续文献通考》卷23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33页。],无法表现出清朝四边之局面,因而这一任务只能交由《清通考》来完成。《清通考·四裔考》在序文中详细列举了当时的“四裔”局面,以见与前朝之变化:“三代以降,中原幅员视主德为广狭,四裔远近亦随时转移……试举今日四裔全势揆之,东则朝鲜、日本、琉球;南则安南、南掌、广南、缅甸、葫芦及海中暹罗港口柬埔寨、宋腒朥、柔佛、亚齐、吕宋、莽均、达老、苏禄、文莱、马辰,旧港曼加萨、噶喇巴之属,更远而为意达里亚、博尔都噶尔亚、英吉利、干丝腊、荷兰、佛朗机、瑞国、嗹国之属;西则东西布噜特、安集延、霍罕、纳木干、玛尔噶朗、塔什干、巴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之属;北则俄罗斯、左右哈萨克、齐齐玉斯、谔尔根齐之属,固已跨越四瀛之界,广远绵邈,什百前代矣。”[嵇璜等:《清文献通考》卷29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79—580页。]可见,随着对周边认识逐渐扩展和政治局势的变化,“前代所列为四裔者,今则尽隶版图”[嵇璜等:《续文献通考》卷23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33页。],“四裔”这一概念所指的范围在清代已和前代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在“四裔”范围不断变化的同时,《清通考》中对“四裔”的态度则更多体现出对中国古老的世界秩序观的继承。清朝统治者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入主中原后对已入版图之内的各民族力倡“夷夏平等”,但对仍在版图之外的“四裔”则仍以传统的朝贡制度加以对待,实际上是将原先的汉族与周边的世界秩序观推广到以满清为代表的中国与“四裔”的关系中,其要点则是中国仍为“天下之中”,所不同者仅在于满族已从原先周边的一分子转为中心的代表了。
实际上,随着明末以来中西交流的增加,传统世界秩序观中的要点之一——地理上的“中国中心观”已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关于世界地理的新知识,直观地反映在当时绘制的许多世界地图中,使许多传统中国学者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对新知识的全方位接受是众所周知的,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在接受地理新知识的同时,为了维护中国高于“四裔”的世界秩序观,选择从另一要点——“文化优越论”的角度对中国的优越性进行解释。如清初李光地就曾说:“所谓中国者,谓其礼乐政教得天地之正理,岂必以形而中乎?譬如心之在人中也,不如脐之中也,而卒必以心为人之中,岂以形哉?”[李光地:《榕村集》卷20《记南怀仁问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09页。]本来,这种“文化优越论”向来是和地理中心论连在一起的,如杜佑《通典·边防》序言云:“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杜佑:《通典》卷185,《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2页。]这里“受气正”即是李光地所谓“礼乐政教得天地之正理”的另一种表达,而“居土中”则隐然为“受气正”的自然原因,这在中国传统儒生看来是一个合理的链环。然而当地理上的中心论受到质疑甚至不得不放弃之后,这一链环被打断了,因而李光地不得不越过地理的因素,直接从礼乐等文化方面论证中国的优越性,同时用心脏和肚脐位置的比喻对地理中心论做出回应,实际上是为了夺回一点中国优越论的主动权。
与李光地等放弃地理因素而专从文化上论证中国优越的方式不同,当时另有一些学者面对新的地理知识仍然坚持認为中国是世界地理的中心,即全面坚持了世界秩序观的两个层面。清修《续通考·四裔考》就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四裔考》序言开篇即云:“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我国家统一函夏,四裔宾服,列圣经营,宅中驭外。”[嵇璜等:《清文献通考》卷29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79页。]其中所称“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尚符合“裔”字的本义,而随后又不忘添上一句“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这本不是字义可涵盖的,但对三通馆臣来说,这一推论却必不可少。就当时的知识而言,已绝不可能忽略“海外诸国”,但如何定位诸国则关系重大。对三通馆臣来说,“中土居大地之中”的基本观念是不能改变的,在此前提下,只有将“海外诸国”顺着“缘边滨海而居者”一起划为“四裔”,才不致与“中土居大地之中”的基本观念发生冲突,“四裔考”这一门类的名称也才能够成立。这篇序言最后说:“马《考》旧分东、南、西、北四面,王圻《续考》增东南、西南二面,分隶之处,悉多牵率。今南洋诸国由南方迤及西南,日本、琉球由正东迤及东南,新附布噜特、安集延、巴达克山、爱乌罕诸部由西北而及正西,皆壤地相接,难为强晰。爰以环瀛之大,总分四正方位云。”[嵇璜等:《清文献通考》卷29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80—581页。]这一安排也隐含深意。王圻《续文献通考》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分四面的基础上增以东南、西南,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清通考》指其“悉多牵率”,声称因为南洋等隅均由正南、正东等迤逦而及,故仍以四正区分。其实“壤地相接,难为强晰”本是地理常态,既然为作书志,本当区分详考,故三通馆臣所言并非全部的原因,实际上采用四正划分背后也隐含着用四正以突显中心的考虑。
《清通考》中使用“四裔”的名称,一方面继承了马端临《文献通考》的名目,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朝廷意识的映射,其与李光地做法的不同,某种程度上也隐约体现了清廷在这一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其实,康、雍时期成书的《明史》中关于其他国家的记载有《外国传》和《西域传》两篇,而没有采用类似“四裔传”等名称,其中《外国传》既有朝鲜等藩国,也有意大利等欧洲诸国,显然,《外国传》的名称所体现的涵义要比“四裔”等更为平等。而修《清通考》的乾隆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在《四裔考》之外另立《外交考》,“《皇朝通考》讫乾隆五十年,我为上国,率土皆臣,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7,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0781页。]。“理藩而已”云云,将乾隆时期“上国”心目中的世界秩序表露无遗。
在“理藩”的观念下,《清通考·四裔考》所载各国全被清朝视为藩国,不过诸国具体又可分为两类,序言说:“爰举献琛奉朔及互市诸国,稽其山川风俗之未登曩乘者,著为斯考,仰见我朝声教暨讫之远,诸藩部倾心内附之诚。”[嵇璜等:《清文献通考》卷29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80页。]可见这些“四裔”中,有些属于“献琛奉朔”者,即有明确的朝贡、册封等政治义务的属国,有些则属于“互市诸国”,即没有政治义务,仅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四裔考》对这两类国家的书写也显示出各自的特色,以下以奉正朔的朝鲜国和仅有互市的远西各国为例略加分析。
二、“优柔东藩”:《四裔考》对属国朝鲜的书写
朝鲜是清廷朝贡秩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清廷最为重视的藩属国。《清通考·四裔考》对朝鲜的记载独占两卷,相较于那些合在一卷中的若干国家,记载自然也最为详细。众所周知,崇祯十年(1637,清崇德二年)朝鲜被清朝武力征服,于汉江城外三田渡奉印称臣,自此奉清朝正朔,遵行朝贡等一系列制度,正式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但朝鲜国内此后却仍然以“小中华”自居,尊周思明,尤其是士人之间深受程朱理学影响,仍用崇祯、永历等明朝年号。为了扭转这样的情况,使朝鲜真正臣服于清朝,清廷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减少贡品额数等。作为政治措施的配合,文化措施也是重要方面,《清通考·四裔考》中对朝鲜的记载就体现着这一意图。
首先,通过对征服战争的书写,将清廷(后金)塑造为行仁义、得天命的一方,将朝鲜被征服描述为天命所归的过程。最初,朝鲜作为明朝的属国,《四裔考》中云“我太祖高皇帝肇兴东土,附近诸部落以次服属。朝鲜北境与我接壤,犹纳贡于明,上亦未之较也”[以下《四裔考》中关于朝鲜的记载均见嵇璜等《清文献通考》卷293、29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随后在萨尔浒之战中朝鲜出兵助明,在这次战斗中,朝鲜主帅姜弘立(清朝文献避讳作姜宏立)败降后金。为此,努尔哈赤致信朝鲜国王李珲,《四裔考》记载其书云:“尔以兵助明,吾知非尔意也,迫于其势有不得已。且明曾救尔倭难,故报其恩尔,原与我国无仇。今擒尔统兵官属十人,念王之故,特留之。王其与我合谋以仇明耶?抑既已助明,不相背负耶?其详告我。”这一书信的内容与《清太祖实录》所载大同小异,但《实录》随后记载有朝鲜官方的回复,拒绝了努尔哈赤“合谋以仇明”的提议,称“大明与我国犹如父子……吾二国各守边疆,复乎前好,乃为善也”[《清太祖实录》卷6,天命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实录》,第1冊,中华书局,1986年,第85页。]。然而《四裔考》则完全没有记回书之事。随后“天聪元年……太祖高皇帝上宾,不遣使吊问,以是诸罪声讨,正月壬午大军薄义州,克其城”。其实这只是借口,真正的理由则是天命七年(1622)明辽东游击毛文龙兵败后退入朝鲜,后居于朝鲜椵岛(后改名皮岛)牵制后金,《清太宗实录》说:“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清太宗实录》卷2,天聪元年正月丙子,《清实录》,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1页。]这次战争中后金主帅阿敏连下义州、安州、平壤等地,朝鲜仁祖李倧避入江都(江华岛),派人与后金议和,两方先在江都约盟一次,后在平壤又约盟一次,约为兄弟之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盟誓之间,后金主帅阿敏曾“令八旗将士分路纵掠三日,财物人畜,悉行驱载”[《清太宗实录》卷2,天聪元年三月乙酉,《清实录》,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9页。],这是见于《实录》的,但《四裔考》则略去了这一事实,称“往江华岛涖盟,三月庚午,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和议成。上遣使谕阿敏曰:朝鲜既经和好,毋得秋毫扰累。阿敏复与李觉盟于平壤。上命分兵驻义州,大军振旅而还”。从《实录》来看,皇太极对阿敏的这一敕谕显然是针对他纵兵劫掠而发的,但《四裔考》略去纵兵劫掠的事实,只保留这一敕谕,读来仿佛皇太极宽仁为本,提前警告阿敏,而劫掠之事好似未曾发生一般,《四裔考》在此的书写显然有特定的取舍。
平壤盟约后朝鲜与后金兄弟之国的关系维持了十年,对此,《四裔考》中留下了许多朝鲜方面越境不法的记载,如“潜入我境窃参,猎取禽兽,又杀我国人,互市勒价,夺取马匹牲畜,隐匿我国罪犯,渐减岁贡额数”等,而对后金则多记载皇太极派人耐心晓谕。两国关系的重大变化发生在天聪十年(1636),当时“十六国四十九贝勒会集盛京,复与内诸贝勒议”,拟共尊皇太极称帝,同时“上谕,朝鲜国王吾弟也,宜令知之”,于是遣使者至朝鲜要求共同推戴。然而朝鲜的态度却不配合,后金使者“英俄尔岱等至朝鲜,倧不见,与内外诸贝勒书,不纳。变易常礼,诡令至彼议政府议,又设兵防守。英俄尔岱等疑之,即率诸使者夺民间马突门出。倧闻,遣人持报书追付,又以书谕其边臣,令固守城垣,预为设备,且有‘丁卯年误与讲和,今当决绝之语”。使者将朝方情态回报皇太极,“诸贝勒大臣共阅,众皆怒,请兴兵灭之。上曰,先遣人谕以利害,令其以诸子大臣为质,彼许则已,否则再议征伐可也”。此处又突显皇太极对朝鲜宽厚晓谕的态度,而事实上战争已是势在必行了。该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十一月起兵征朝鲜。在记载战争经过时,《四裔考》有意突显清方得天之助,十二月“丁酉,次临津江。先是,江水冰泮不可渡。车驾未至前三日,天骤寒,冰坚。是日大军安驱渡江,众兵无不惊骇”。用类似神迹的故事表现清军征伐的合理性,而朝方则一再奉书请成,最终朝鲜于崇德二年(1637)在三田渡向清军奉表投降。《四裔考》详细记载了李倧“率其群臣伏地请罪”的受降窘态,而清廷则表现出“王既知罪来降,朕岂念旧恶”的宽厚态度,并且抄录清廷对这一战争的碑文,以凸显清朝宽仁的胜利者的形象。
三田渡盟约之后,朝鲜正式成为清朝藩属国,遵行相关朝贡、受封等礼制,这一时期《四裔考》的书写重在突显清廷对朝鲜方面的优遇。清朝在藩属关系中对朝鲜的优待包括减少贡品、增加赏赐、优待使团、从宽执法等许多方面,《四裔考》中除了大量礼节贺表的记录外,对这些方面也作了详细的记载。例如原本根据三田渡的盟约,朝鲜自当年(崇德二年,1637)起就须向清朝每年缴纳贡物,而皇太极为表宽仁,在当年二月曾下谕“尔国穷苦,朕已知之。丁丑、戊寅两年准免贡物,己卯年秋季始照例入贡,表尔忠诚”,免除了朝鲜两年的岁贡。此后又多次减损岁贡额数,如顺治甫登基,即“颁诏于朝鲜,并赉太宗文皇帝遗敕往谕,减岁贡内红绿绵纟由
各五十疋,白绵纟由
五百疋,紵布三百疋,布二百疋,腰刀六口,龙席二领,花席二十领。前逮系逆臣崔鸣吉、金声黑尼等及逃犯林庆业家属均予释放”。康熙三十二年(1693)皇帝下旨:“朝鲜国克殚恭顺,顷复输应军需,进鸟鎗三千杆,忠顺可嘉。嗣后年贡内黄金百两及蓝青红木棉,永著停止。”雍正六年(1728)“二月减朝鲜贡稻米三十石、江米三十石,每年止贡江米四十石,以供祭祀,著为例”。除岁贡外,作为藩国,朝鲜向来还需向清朝使臣馈赠仪物,所赠本也有一定额数,雍正十三年(1735)弘历甫登基,即“谕礼部曰,大臣官员之差往朝鲜者,向有馈送仪物之例。朕以厚往薄来为念……其照旧例减半,著为令”。并严禁在馈送正礼外的行贿索贿行为,“嗣后务宜遵朕前旨,凡陋规所有都请、别请等项,悉行禁革。至使臣回京之日,奉天将军及山海关监督查验,倘正礼外多携礼物者,严劾之”。在回赐方面,清朝秉承“厚往薄来”,对朝鲜每加格外之赏赐,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加恩赏赉,并御书匾额以赐,用昭优眷,御书匾额‘东藩绳美”。这类赏赐的记载在《四裔考》中比比皆是。
除岁贡和赏赐往来外,清朝与朝鲜交流中的另一主要方面是犯越案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四裔考》的记载总是突显清廷从宽执法,以示怀柔的态度。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月,朝鲜民韩得完等二十八人违禁越江采参,擅放鸟鎗,伤奉差绘画舆图官”,朝鲜国王李焞的判处是“韩得完等二十八人俱拟立斩,约束不严之咸镜道节度使尹时达等降革有差,国王焞罚银二万两”,而康熙下旨“韩得完等为首六人立斩,余二十二人从宽免死,减等发落”。又乾隆二十九年(1764),“朝鲜民人金凤守、金世柱等杀死内地披甲常德”,刑部等议金凤守当斩,且认为“朝鲜奸民屡次越境生事,皆王约束不严所致,应交部议处”,而乾隆则下旨“金凤守等从宽改为监侯,该国王免其议处”;乾隆三十年(1765),“以越江行窃人犯金顺丁等俱缓决,及案内疎防各官拟罪从宽……民人朴厚赞十犯越境滋事,秋谳缓决,案内疎防各官拟罪从宽”。可以看出,清朝从康熙到乾隆一直对犯越案采取从宽执法的态度,《四裔考》中对清、朝往来之间的这些能够反映清廷特别优待的行为总是详加记录,以凸显宽仁藩主的形象。
《四裔考》的书写之所以有如此的取舍侧重,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清文献通考》修成后要颁行朝鲜国中,因此使朝鲜君臣读后对清廷感恩戴德自然成为书写的主要目的。不过,相对于上述《四裔考》的取舍侧重,朝鲜方面更关心的是《清文献通考》中所记载的本国政治变动中的名分问题。按,康熙五十九年(1720),朝鲜肃宗李焞去世,长子李昀即位,是为景宗。由于李昀举止怪异,无法亲自裁决政事,故以金昌集等四人为首的一些老臣请求以其弟李昑代理听政,相臣赵泰耇等声称金昌集等为谋逆,金昌集等四人先遭流放,继而赐死。雍正二年(1724),在位仅四年的李昀去世,其弟李昑即位,是为英祖,英祖甫即位就为之前的金昌集等人平反昭雪。由于景宗时朝方已将对金昌集等人的定性汇报给清廷,故清廷依据朝方当时所言,在《四裔考》中记载云:“朝鲜国议政金昌集、中枢李颐命、左议政李健命、判中枢赵泰来等谋逆,事发伏诛。”后来直到道光元年(1821),朝方才注意到《清文献通考》的这一记载,国王李玜遂请求清廷加以修改。《清宣宗实录》载:“国王李玜奏言……四臣咸得昭雪,而冤诬之辞,尚留简牍。恳恩饬查更正。下礼部议。寻奏,《通考》所载系据李昀奏报……今既肫诚吁恳,为祖雪冤……应请删去此条,以昭传信。从之。”[《清宣宗实录》卷27,道光元年十二月辛巳,《清实录》,第3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479—480页。]清廷应朝鲜的要求删改此条,并重新刷印一部《清文献通考》颁给朝鲜[《清史稿》卷526《属国一·朝鲜》云:“(道光)二年,颁给《文献通考刊正》一编。”见《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14592页。]。此时四库本和武英殿本《清文献通考》流传已久,显已无法修改,因此这一改动没有在通行的四库本和殿本中体现出来。虽然如此,但这一例子却反映出《四裔考》中的历史书写带有促进朝鲜和清朝友好关系的目的。
总之,《清文献通考·四裔考》作为清廷敕撰之书,其中的内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记录,更有着配合政治考虑的特殊的文化功能,况且其书既要颁行朝鲜,则亦需考虑朝鲜君臣阅读之后的感受。《四裔考》在书写上突出清朝征伐之得天命、皇帝之宽仁优遇等,力图使包含朝鲜君臣在内的中外所有讀者从中感受并认可清廷征服朝鲜并作为宗主国的合理,以达到从文化上巩固朝鲜藩属国地位的目的,背后最根本的则仍是以“上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
三、“输诚称贡”:《四裔考》对远西“互市诸国”的书写
相较于朝鲜这样的东亚近邻,清廷对远西各国的书写更能反映特定时代之下对世界认识。自郑和下西洋以来,中国逐渐对远隔重洋的世界其他国家有了一定的了解,明末众多欧洲传教士相继踏足中土,带来的新知识更开启了国人了解世界的新篇章。清朝入关之后,中外之间的交流较明末又有发展,《清通考·四裔考》中对远西各国也有比此前更为详细的记载[以下《四裔考》中关于西洋诸国的记载均见嵇璜等《清文献通考》卷29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与朝鲜部分相比,《四裔考》中对远西各国的记载在总体结构上有很大不同。由于此前史籍对朝鲜国基本情况的记述已很详细,故《四裔考》对朝鲜仅用十余字作了最基本的介绍,随后即开始记载从天命年间以来的两国交涉情况。而对远西诸国,《四裔考》中用了不小的篇幅介绍各国的基本情况,然后再记录诸国与中国之间的往来。所记的西洋诸国包括意达里亚(附厄勒祭亚、罗玛尼亚等)、博尔都噶尔亚(附伊西巴尼亚、热尔玛尼亚等)、英吉利、干丝腊、荷兰、佛郎机、瑞国、嗹国。其中最详细的是对列在首位的意达里亚(意大利)的记载,总计约四千字,其余诸国则较简略。《四裔考》对意大利的记载分为两大部分,先述其国山川、政教、习俗等,后记其与中国的交流,两部分篇幅大致相等。其中对山川习俗的记载,其材料基本源自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职方外纪》。罗马大学(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汉学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和马西尼(Federico Masini)两教授指出:“《清朝文献通考》关于对意大利的记述,实际上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艾儒略书中的话,另有几段补充文字,也是从卷二欧洲总论中摘取来的。”[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4页。另可参Federico Masini,“LITALIA DESCRITTA NEl QING CHAO WEN XIAN TONG KAO”,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1989.Vol.63 (4),pp285-298.]相较原书,《四裔考》删去了《职方外纪》中意大利部分的许多内容,同时在记述的顺序上也有所调整,并将《职方外纪》总述欧洲的若干文字也插入到意大利条之下,该条下所附的厄勒祭亚(希腊)、罗玛尼亚(罗马尼亚)等九国的材料也都全部源自《职方外纪》。由于采用了传教士的记载,《四裔考》对意大利等远西各国的叙述较《明史·外国传》要详尽许多,同时也体现出编纂者对新世界、新知识的一些态度。
西洋人进入中国,带来的新鲜事物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偏重实际,包括西洋器物本身、对器物的解说以及对本国情况的描述;第二类则是理论上的新知识,诸如天主奥义及地球五大洲的地理知识等。对中国士人来说,这两类新鲜事物所造成的冲击是不同的。《明史·外国传》说:“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张廷玉等:《明史》卷326,中华书局,1974年,第8459页。]正代表了清代士人对这两类事物的不同态度:面对实实在在的西洋人与物,纵使不欲承认亦无法否认,而那些与古不合的论说则被认为是“荒渺莫考”。稍后于《明史》不久的《四裔考》对西洋的书写也秉持了这样的观念。以意大利为例,这部分材料虽来自《职方外纪》,但既非照录,亦非简单地就原文删节,而是特意调整了原有的记述顺序。具体来说,《职方外纪》意大利部分先述罗马城情况,包括大渠、大殿、教皇、名苑、铜鸟、城中七山,此后分别叙述罗马之外的勿搦祭亚、勿里诺湖等,最后是意大利三岛。而在《四裔考》中则先述罗马大渠、城中七山、勿搦祭亚城、勿里诺湖等情况,以“此意达里亚山川形势之大较也”作结,然后再叙述习俗,如教皇、婚姻、物产、名苑、铜鸟、小学中学大学之分科、老幼养育、赋税、司法等情况,以“其国人来者自述其政教风俗之概如此”作结。其材料不仅限于《职方外纪》意大利条,还加入了该书欧洲总论条中的若干内容。可见,三通馆臣并非简单转引《职方外纪》,而是根据需要对材料进行了重新组织。可以说,这种重新组织反映出三通馆臣对西洋人自述其国的情况是有一定的了解意愿和行动的。
这种了解最为突出的是对西洋诸国先进技术的关注和赞赏。如《四裔考》记英吉利时称“土产则有大小绒哔叽、羽纱、紫檀、火石及所制玻璃镜、时辰钟表等物,精巧绝伦”,记荷兰称“巨舟、大砲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窗,置铜砲,桅下置二丈巨铁砲,发之可洞石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砲,即其制也”。尤为典型的是表达了对于西洋历法的肯定:“先是,钦天监按古法推算康熙八年十二月置闰,南怀仁言雨水为正月中气,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即为康熙九年之正月不当闰,置闰当在明年二月。上命礼部详询,钦天监官多直怀仁言,乃改闰二月。”历法在传统中国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推算与改动都极为慎重,而不少钦天监官员支持南怀仁这一情况,证明西洋历法较古法更为精确的事实已受到广泛承认。在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条后,三通馆臣加按语总论西洋技术说:“若其《几何原》《测量法义》诸书籍,以考核天文独为精审,而又勤于测验,巧制彝器。本朝璇玉所窥,亦资其用。俾殊方异能之士服官专司,实足补郭守敬诸家所未备。”显然,这些实用的新知识是中国人愿意接受和吸收的。
但同时,对西洋学问的排斥在《四裔考》中也极为明显。就在前引“实足补郭守敬诸家所未备”这句之后,三通馆臣紧接着就说:“惟天主一说,则但使自沿厥俗,勿俾流传,致淆闻见。屡奉圣明饬禁,意至深远。此诚我朝仁育义正之怀,收其人必尽其用,安其俗不存其教。”除这样的总论外,《四裔考》在记载各国与中国交流的情形时,特别注重对清廷历次禁止传教情况的记录,单在意大利条中就记康熙八年(1669)“凡直隶各省开堂设教者禁”;五十六年(1717)“再行严禁,毋使滋蔓”;五十七年(1718)“再行禁止”;雍正二年(1724)“西洋人先后来广东者……年壮愿回者附洋舶归国,年老有疾不能归者听,惟不许妄自行走,衍倡教说”。对于其他一些有关世界地理的新学问,《四裔考》也表现出坚決的排斥,其典型代表为五大洲说。在《四裔考》意大利条的结尾,三通馆臣加按语说:“至意达里亚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第敢以中土为五洲之一,又名之曰亚细洲,而处其所称第五洲曰墨瓦蜡泥加洲者,乃以其臣墨瓦兰辗转经年,忽得海峡,亘千余里,因首开此区,故名之曰墨瓦蜡泥加洲。夫以千余里之地名之为一洲,而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洲,以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矣。”对三通馆臣来说,所谓五洲之说,与《四裔考》开篇宣称的“中土居大地之中”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图景,也就是与以地理上的“中国中心论”为一个支点的传统的世界秩序观绝不相融,这样的新学问是馆臣绝不能认可的。因而馆臣首先将其来源追溯到中国固有的邹衍的九州说,以表示一种轻视,随后用一个“敢”字生动体现了对传统秩序观的坚持和对异说的决然否定。
不过,这种排斥和否定却建立在一个较为尴尬的前提下,那就是《四裔考》显示出清朝士人对西洋各国的具体情况、各国关系、来华意图等多方面问题都还缺乏清晰深入的认识。例如,康熙十七年(1678)葡萄牙使团曾入京献狮,为轰动一时的大事,近一百年后的纪晓岚说当时“馆阁前辈多有赋咏”[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5页。但纪氏误记为康熙十四年。],但《四裔考》里述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时对此只字未提,却在意大利条中记载称其国王“阿丰肃遣陪臣本多白垒拉奉表贡狮子”,似属张冠李戴了。葡萄牙献狮意在换取清廷对葡方在澳门贸易问题上的解禁,这一目的在献狮后确实达到了[也有学者指出:“献狮与开放澳门的陆路贸易仅仅是时间前后关系,并不表明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见何新华:《康熙十七年葡萄牙献狮研究》,《清史研究》,2014年第1期。],但对清廷朝野来说,献狮更多被解读为是该国“仰风慕义”“输诚称贡”“向化来归”的表现,也即远西之国认同“上国”世界秩序观的证明。事实上,这种解读对确切了解当时各国意图是有遮蔽的。从《四裔考》的记载中可知,清廷对西洋各国遣使来华大都做此解读(传教除外),同时秉持传统朝贡制度中厚往薄来的做法,对各国大加赏赐。如意大利条记康熙谕该国(实际当是葡萄牙)“地居极边,初次进贡,具见慕义之诚,可从优赏赉”,荷兰条记载康熙谕“惟尔荷兰国……僻在西陲,海洋险远,历代以来,声教不及。乃能缅怀德化,效慕尊亲,择尔贡使,赴阙来朝,虔修职贡,朕甚嘉之。用是加赉文绮白金,以报孚忱。至所请朝贡出入,贸易有无,虽灌输货贝,利益商民,但念道里悠长,风波险阻……著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尔其慎乃常职,祗承宠命”。言辞间的“上国”心态,恐怕并非外交辞令所能全部解释。可以说,这一时期清朝无论皇帝或士人都未能深刻认识到西洋诸国不惜远涉重洋来华的真实意图,而是一厢情愿地将之纳入传统的世界秩序观中。无论从地理角度、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看,当时对整个世界的认识都存在很大的不足,在这样一个根基未稳的前提之下,不仅排斥的态度不可能达到目的,就连正面的肯定或赞赏也未必能有预想中的效果。
四、结语
在东亚较小的范围之内,清朝是朝鲜等国事实上的宗主国,因此这时清廷所持的世界秩序观不仅在理念上成立,在事实上无疑也成立。不过,清廷显然不满足于仅在东亚达成这一秩序,面对远西“互市诸国”,虽然实际上不存在册封等政治关系,但却不妨碍清廷也将它们定位为“慕义来朝”的“四裔”,并对它们采取和朝贡体系中同样的赏赐。这样一来大清国仍是中心,而所有的国家都被纳入到清廷的世界秩序观之下。
如果说清廷对“四裔”的赏赐秉持了传统的“厚往薄来”的做法,那么可以说清朝士人对“四裔”的了解则体现出“厚来薄往”的特点,甚至可谓“有来无往”。除了对近邻诸国了解较深外,对远西各国仅有的若干知识亦多是靠“四裔”来华之人的自述,而缺少我国往彼处者的实际见闻。甚至对于近邻之国也有了解不确之处,如认为朝鲜三韩之“韩”与“汗”音相近,认为即三王之汗;认为俄罗斯即北魏时乌洛侯,“侯字乃俟字之误,即俄罗斯转音耳”[嵇璜等:《清文献通考》卷300,《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51页。],致使国人对“四裔”的了解程度远不及外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四裔传》的书写对象与其说是“四裔”本身,不如说是纂修者对“四裔”的某种想象。《四裔传》值得关注的地方更多不在其记载了“四裔”的什么内容,而在于其书写者如何形成这一关于“四裔”的记载与认识。
On the Qing Governments View of the World Order in Qianlong Reign from the SiYiKao Compiled in the Qing Dynasty
Liu Junb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SiYi”(四裔) was a general name for the surrounding ethnic groups or countries in ancient China, which was naturally inappropriate today. However, in the long river of history, this name reflected the attitude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Central Plains towards the surrounding ethnic groups, which often took themselves as the center of geography and civilization. This view of world order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books. The SiYiKao(《四裔考》) compiled by the officials in Qianlong reign included two categories: the vassal countries with tribute obligations and the mutual trading countries in Western. The writing of dependent countries highlighted the reasonable an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as a suzerain country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isters and subordinat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described the visits of far western countries to China for trading as paying tribute. The writing of these two kinds of countries in the SiYiKao jointly reflected the Qing governments adherence to the traditional world order view of the Central Plains. This attitude delayed the Qing governments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apidly changing new world and world relations at that time.
Key words:view of world order;SiYiKao;historical writing;vassal countries;mutual trading countries
[責任编校 王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