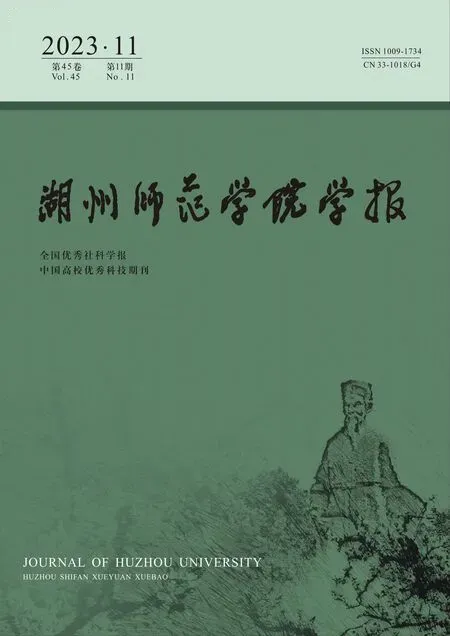《性自命出》道德教化思想*
吴凡明,郑 楠
(1.湖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2.湖州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郭店楚简的出土,使儒家及其学派思想重新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关注。郭店楚简所表达的思想恰好介于孔孟之间,蕴含丰富的孔门后学的教育思想,对于构建儒家教育思想的连续性、系统性具有重要意义。《性自命出》篇可视作郭店楚简教育理论中的人性理论总纲,简文以教为主旨,强调人性是教化的哲学前提,心是教化的施力点,情是教化制定的现实依据,此中不仅有深刻的哲学意涵,且其道德教化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不论是对道德教育理论的丰富发展,还是对社会现实生活中道德问题的解决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道德教化的人性论基础
儒家的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对人本质的探索之上的,人性论是儒家教育实践的哲学基础。《性自命出》首段言:“性自命出,命自天降”[1]136,“性”来自由“天”所赋予的“命”中,“命”本身无形体,是“天”在人身上的体现,但只有当其具有一定的形体和属性时才能形成人,“性”就是这种外在的形体和属性,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性”实际上来自最高的价值实体——天。学界针对此处由“天”“命”所延伸出的性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是道德形而上学的看法,认为这里的“天”是绝对性、先验性的道德与义理,是道德性的,由这种“天命”所出的“性”必然是善的;另一种观点是把简文中的“天”当作自然界的必然性,与郭店楚简《穷达于时》篇中的“时命”一致,强调外在环境对人性的陶冶、塑造,透露着朴素的自然人性论思想。以“天命”说“善性”的观点可能受到宋明理学道德形而上学的影响,但彻底的自然人性观也让“性”有了生物学意味[2]143。实际上,《性自命出》强调存养、充实的天命之性,既不是孟子那里预设为善的性,也不是荀子所主张的纯粹的生物性欲望,其“性”承认情感和欲望的合理性,且其本质上意赋、彰正天命,皈依于天命之义理的内生规定,得以“呈现”可能的道德形上意味。
“四海之内,其性一也。”[1]136性即由天命所赋予,四海之内万事万物皆有其性,性具有普遍一致性。“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1]136牛形体庞大、雁脖子修长与人的喜怒哀悲皆是天生的自然特性,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具有普遍性意义,不论人类或动物,即使在不同时空,他们的“性”都是一样的。但是,人的自然属性不是人的本质属性。人首先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其身体肌理遵循着生物发展规律,其性格情感符合生物特征,这是人的自然属性。自然属性是作为个体的人得以生存和延续的前提条件,但它不能成为人的本质属性,因为本质属性是事物区别于他物的特有属性,动物也有喜怒哀悲之情,这类自然属性只能表明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和共同性,而不能从根本上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6这就说明人还具有相应的社会属性,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性自命出》言:“人而学或使之也”[1]136,基于人的自然特性,通过教化和积习使个体获得道德,社会属性在此过程中逐渐丰盈。相比于其他万物具有固定的性(其可能性与现实性是一致的),人性通过教化则具有种种可能性,人的自然属性是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属性则是发展的最终方向,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就在于内在德性的生成和发展。《性自命出》的人性观未直言性善与否,它尊重人之自然本性,但强调外物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因此在其形成相应的社会属性之时发挥道德教化的引导、规范功能,从而使人性之中的道德性得以生成展开,此即遵从人性内在倾向性,也是人性持之以恒追求的终极目标。
《性自命出》上篇集中围绕人性的自然属性展开论述。“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1]136喜怒哀悲是一种生理现象,是人天生之情,喜怒哀悲之气则是人之性,是生命表现的内在规定,它是情外现的前提和依据,是上天所赋予的自然状态。“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1]136好恶是人之本性,物是好恶的对象。“所好所恶”是个体的意识或情欲表现,具体活动中的好恶是人性面对周遭事物的当下反应,乃是人性原始状态的最初发见。“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1]136此处可看出简文并无性善或性恶的判断,而是认为人本质之中包含善与不善,究竟哪一部分得以发挥出来,并成为主导人生的方面,取决于后天的“势”的作用。此外,简文还指出“性”的变化发展与后天的熏陶、习染紧密相关,“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出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1]136。这里详细论述了性在各种条件下的影响,其中动和逆是性的本然特征,是人一般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其余五项均是后天因素促使性产生的发展与变化,且此处无论内在还是外在存养动性的内容,均没有道德的、情感的判断,具有明显的自然人性论倾向。但是,《性自命出》中的“自然性”并非仅仅作为“消极”“被动”的待加工物质,它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性自命出》言:“仁,性之方也。”[1]138“仁”为二人,简文将“仁”作为个体后天发展形成的社会属性,以其为人性之方。《论语·雍也》:“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4]494方有“道义”“准则”的意思。陈宁训释“方”为“道”(道路)或“向”(方向),并将此句疏解为“仁是人性发展的方向,人性有生之”[5]177,即“仁”是性的方向、准则,道德属性是人性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把道德性的“仁”作为人性的发展方向,实际上揭示了人性的道德规定性,人性具有趋善的本性。“仁”是一种道德情感,有着辨明善恶的主动性,由此,人性不仅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也具有道德选择的能动性。《性自命出》中的自然之性与社会道德之性并非相互对立,后天道德教化对自然之性的扩充、调整源于事物内在发展的需求,彰显着人自身的主动性;也正因道德之性以自然之性为基础,自然之性自身才有可能向道德方向收敛。正如唐君毅说:“一具体之生命在生长变化发展中,而其生长变化发展,必有所向。此所向之所在,即其生命之性之所在。此盖即中国古代之生字所以能涵具性之义。”[6]27-28人之为人的本质不仅在于初生之时命,还在后天对包含着绝对道德和义理之社会属性的无限追求,如此方能使人性内在倾向性得到充分发展。
因此,《性自命出》人性论在讨论人的本质问题时,把人的本质看作是人后天对于“仁”的无限追求,形而上的道德最初为自然之性所统摄,通过道德教化向自然之性倾注道德认知,形成道德意志,形成内在的道德之性,从而使天道义理成为性之本质与行之根基。
二、道德教化的理想人格
《性自命出》规定了人本质之中“仁”的内在倾向,仁是至真至善,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标准,达到最高层次的“仁”乃为圣人。但学仁成圣是一个梯级性的道德生成过程,众人心无定志,君子心主身,圣人身心合一,因此简文将君子作为现世的理想人格标准,以圣人为至高至美的道德理想人格,构建具有层次的理想人格目标[7]87。儒家学说中德仁兼备的人首先是君子,君子是成圣成仁的基础。《性自命出》中的第15至20简集中论述教化,在阐明道德教化的主体、对象以及教化内容后,提出教化的目标:“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1]137此处的君子与这些道德品质之间可能存在两种关系,其一道德品质为君子的定语;其二君子一词包含众多道德品质,君子与道德共存,但两种关系都表明简文将培养具备德性德行的君子作为道德教化的目标之一。“君子”概念和内涵在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存在一个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在西周时期,君子主要是指周天子以下的贵族阶层[8]10-12;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创建仁礼之学的过程中,在平民化的基础上将“君子”这一概念进一步提升为形容道德人格的概念,“君子”概念由社会地位上的内涵逐渐开始向道德内涵转化,最终确立了“君子”这一理想人格范式[9]15-19。孔子认为君子人格的内涵至少包括仁、智、勇三者,“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10]194。“仁”是主轴,“智”“勇”是行“仁”的必要素质和能力,缺其一,人格不能独立。待其内在道德品质外显时,孔子则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0]70。君子应集内在精神“仁”与外在规范“礼”于一体,即“文质彬彬”,此外孔子还从持志、好学、社会责任等方面对君子人格提出要求。《性自命出》在继承孔子的思想上对君子提出“美情、贵义、善节、好容、乐道、悦教”的品质标准,要求君子在修身过程中,使人情更为真诚美妙,使仁义价值更高,坚持修善节文,保持仪容整齐,行事乐顺天道,悦于受教。仁义、修善、仪容、顺道、积习都继承了孔子的君子修身思想,在此基础上简文提高了“人情”在修身环节的地位,在君子人格修养过程中对情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文用“美”“好”“乐”“悦”等明显具有心理色彩的词汇作为君子品质的定语,要求君子在修身过程中真情无伪,将道德要求提升为审美需要,将“真”“善”“美”三者合一;同时,《性自命出》承认人的喜怒哀悲等情欲存在的合理性,但因人性之中有仁的内在倾向性,君子需要通过教化和“反善复始”使原始的人的情欲外显时适度中正、清澈平和。对人情的高度关注实际上体现出儒家在道德教化过程中更为注重人本身,重视道德情感在君子修养过程中的导向性和能动性。简文对道德情感的关注还体现于对人道的践行之中,只有通过实践检验、磨砺才能使道德情感更为坚实、稳固,“君子执志必有夫广广之心,出言必有夫柬柬之信。宾客之礼必有夫齐齐之容,祭祀之礼必有夫齐齐之敬,居丧必有夫恋恋之哀。君子身以为主心”[1]139。以心主身,持志远大,言行诚信,举止合乎礼仪,与人交往真诚无妄,由道德情感自觉转化为道德行为。《性自命出》将学做君子作为推行道德教化的有效途径,将其放在提高道德境界的枢纽位置,要求君子身心统一,实现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二者之间的双向反哺,将君子人格设立为普通人在现世实践之中所追寻的人格标准。
圣人是儒家最高的道德理想人格,君子重个人品德的修养,而圣人则道德功业并重。圣人从君子之中分化而来,既具有高于君子的道德境界,又教化、引导人民下学而上达,为国家培养众多德才兼备的君子。《性自命出》言:“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训之,体其义而节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1]137。圣人对经典作品进行类比,加以条理综合,再结合民情、社会背景适度调整教材内容,然后又以之对人民实施教育、教化,君子人格就是在此教化过程中养成的。圣人的根本在于教育,如此才能使政教合一,才能使后世皆而仁,这也是儒家所追求的功业成就,正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0]75。具体而论,简文设立的圣人理想人格较为隐蔽,通过对人性论中道德性的显露、生成来展明对个体“仁”的无限追求,圣人人格则不言而自显。《性自命出》言:“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1]138仁是人性发展的方向,实现“仁”,人的道德品质也就实现了终极发展,人自然也就成了圣人。“圣”是一个虚悬的理想,“仁”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道德境界。“仁”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具有最高的德性意义。孔子并不轻许谁具有“仁”德,因为在孔子的伦理体系中,仁是全德和至德的统一,是最高的道德理想。因此,简文“性之仁”是人性趋于至善的理想之境,仁为人性情的内在方向,因其后天笃守善道、臻于圣人境界,向内把人性中所蕴藏的德性充分唤醒,向外学习社会中的道德礼仪,如此成仁成圣。就“仁”自身而言,它是人的一种自觉的精神状态[11]84-87,它要求成己而同时成物,浑然与物同体,全体呈现仁自身。而人之所以能开辟仁这一内在人格世界,是因为仁内在于每一个个体生命之中。但仁可以无限的展现,没有界限。《性自命出》作为孔门后学弟子的著作,在人性论上虽与其有细微差异,但总体上依旧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以仁为人性本质,通过教化展现出对学问、道德的无限追求,即对仁的无限努力。若仁为杯水、溪水、江水,圣人则为海水,圣人与仁一致,是一种无限追求,具有无上限的道德境界。不同于通过学习修养即可成之的君子人格,《性自命出》通过立足于人性的仁之倾向,借助道德教化使学者自觉建造内在人格世界,在此中生出无限的道德要求、责任,仁之水汇入圣之海,使圣人这一理想人格既是落地的,又是高悬的,使圣人既拥有绝对性,又具有普遍性,人们在追求成圣的同时,又向居于道德至顶的圣人顶礼膜拜。将圣、圣人作为道德教化终极理想目标,将学做君子作为推行道德教化的有效途径,培育具有层次性的道德理想人格体系,既能满足学者当下的道德情感需要,又能使其自觉生发出更高层次的道德要求,形成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观,成就人性中至高至善的美德。为充分激活人性内在的道德性,实现教化的理想目标,简文构建了内外兼修的道德教化路径,内在以人情为出发点,激发自觉向善向德的内驱力,外在借助依情而立的礼乐制度规范、引导个体生德。
三、道德教化的具体途径
《性自命出》以人性内含的仁德本性作为本质规定,其建构的至高至善的道德理想人格目标是对君子与圣人的理想追求。如何实现道德教化的目的,实现理想的道德人格目标,这一问题关涉道德教化实现的工夫论视域。《性自命出》篇从三个方面、两条路径全面诠释了如何实现道德教化。所谓“三个方面”就是以情导之、心志引之、礼乐相成,“两条路径”是指由外而内的工夫和由内而外的工夫。“以情导之、心志引之”属于内在的工夫论,“礼乐相成”属于外在的工夫论,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性自命出》的道德教化的实施路径。
首先,《性自命出》提出将“以情导之”作为道德教化的开端。简文言“道始于情”,直接将“情”作为践行人道与追寻天道的开端。在道德教化方面情是起点,由此向外探索;义是终点,个体开始向内发展[12]232,“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1]136。“情”是一种自发和自然的反应,而“义”是合宜的反应,两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人情既是道德修养的开端,又是教化的终极追求。人情是道德教化的现实依据,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的制定皆以人情为前提条件,“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训之,体其义而节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1]137。圣人根据自我中正平和的情感与其所察见的人情制作教化之方,使其符合社会普遍的内在道德需要和审美要求,由情而出的教化对人之心志产生影响,从而使心取性是以定志取之,这就可以确立人之德性。教化的实施以教育者的教育热情、受教者的学习渴望为载体,即以人情为着力点。“始者近情,终者近义”[1]136,道德教化在了解人性论的基础上,以情为起点,就能使外发的性符合义,再反过来由外而内地以义来规范、引导人性,人情构成了道德修养的重要基础。中正平和的人情是道德教化所追寻的理想,人性通过心与外物的接触转化为外在的情,只有促使个体情感达到合理中正的状态,引导其成为具有理性意识的经验或惯性的习惯,情才能转化为道德之性。以人情作为道德教化的开端能保证教化目标的方向性,唯有如此才能使内在的性受到道德的浸润,长久以往,由性而发的情被赋予道德光辉。《性自命出》具有极为浓厚的重情色彩,性外显为情,以情立教,人情不仅是道德教化的开端,还贯通于教化的其他路径之中,此外“情”自身独有的特性也使其成为德性生发的端口。
“情”具有可变性,它受控于外部刺激的性质以及主体对外界做出的反应,是产生道德意识最初的一步,也是使德生于性的最后一步。简文指出道德修养是一个涉及“情”与“义”的能动过程,情感被理解为一种随着知义的发展而获得提升的道德意识,“出”“入”表明了情的内在性和义的外在性。“终者近义”说明《性自命出》不仅仅将情作为道德教化的开端,而且将其贯穿于教化的整个过程。“义”是适宜适当的“情”,当个体将道德认识付诸日常生活实践中,进而形成内在的道德意志并获得“义”时,情又将引导个体向内寻求,通过反善复始来达到天道。郭店楚简《五行》篇:“善,人道也;德,天道也。”[1]100外在的德行只是善,而内在的德性才是“德”,即“天道”,在心性上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必须先正心诚意、真挚诚恳。其原因在于:情与性具有内在一致性,“信,情之方也,情出于性”[1]138。性来自天道,那么情的本质也在于天情,因此只有主体真挚诚恳,性才能具有与天道融合为一体的可能。因此道德的导入以个体的情感为基石,只有当人的情感、情绪产生反应,才能对事物产生作用,潜移默化地转化成为性,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或行为习惯。朱小曼指出:“教育应把人的发展提升看作重要的教育目标,而关注人的情感发展是教育中的一个源性、根基性问题。因为只有情感才是真正属于个体的,它是内在的、独特的,是人类真实意义的表达。”[13]172情感是心与外物接触过程中产生的内心体验,立足于真实的情感和情感的真实之中,领悟、体认道德的实践精神本性,完善人的生命本性,缔造更高层次的生命价值。但人情的运作不是孤立的活动,它需要心的发动、引导、约束,“哀、乐,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1]137,“情”与“性”通过“心”来互通,由于主体“心”所做出的反应不一致,外在的情感、情绪表现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其次,“心志引之”在教化途径中充当承上启下的角色,只有通过心志调动、引导,充分发挥个体的自觉性和能动性,才能保证人情的合理中正,进而发挥礼乐制度的积极作用。“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1]136简文阐明人性由发动到运作再到成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性能否得到发展关键在于心的启动与志的方向。从前文知人性具有向仁的倾向性,道德教化的目的就是帮助个体获得“仁”,既如此,仁又如何获取?简文言:“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求其心有伪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以伪也,可知也。其过十举,其心必在焉。察其见者,情焉失哉?恕,义之方也;义,敬之方也;敬,物之节也;笃,仁之方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出于性。”[1]138“仁”非天命所直接赋予的,而是在“求心”过程中获取的。即在道德教化过程中充分激发人心的主体性、能动性,使心逐渐不受外界干扰,并生出一种与主体行为一致的道德感情倾向,不断提升个体的道德境界。与外在的德性积习一致,内在德性的自觉唤醒也依赖于心的运作,“永思而动心,喟如也。其居次也久,其反善复始也慎,其出入也顺,始其德也”[1]137。长久的对本心本性的追思、省察,会触动内心对性之善的部分复返。归其省思的时间越久,对性之善的返归就会越发诚谨,这时个体内复德性、外发德行的过程就越顺畅,这也是个体道德的开始。人性中虽有善因,但人的先天特征或者本质难以自动实现发展,需要“心”与“物”二者之间反复交往、磨砺,使“心”达到不受干扰的状态,推动主体行为与情感形成一种道德定式,充分激发出“性”内在的道德性。此外,在道德教化过程中若要充分调动人之情,也需要心的运转,若心不取,性不出,情便无由生。性生于天命,情生于性,心的外在反应体现为人之情,三者构成性—心—情的逻辑结构,心能动地沟通内在的性与外在的情,人性外显为情,而情依附于心,情转化为性需要心的筛选、引导,因此个体道德的养成、人性的存养都依赖于心的运转。简文下篇重点论述心术,强调由心见性与心主身,既强调人性中道德的养成需要心的牵引,又以个体的外在礼仪举止见其心性发展,生德于心方能使德践于行,道德品质的养成与道德行为的落实都需要心的引导。“心”在道德养成过程中充当如此重要角色,其关键点在于其不仅单向度地对人情做出反应,还通过与物的接触而反作用于人情本身,这个过程就需要“定志”。
“志”是指学习、修道以及践行道德的志向,“心”被外部刺激驱动可能积极活跃或消极活跃,定志使得心在获得积极活跃时得到道德情感上的满足,并且向着更高层次的道德水平前进;如果是消极活跃,人逐物而动,呈现被外物欲望主宰、随习气流转的状态,而定志可增强个体不依赖于外物的自主自由性,进而在反复学习、实践中,心逐渐达到不受外物干扰的状态,当其生出一种可以自然而然地与主体行为相一致的情感倾向时(本我真实的人情遵循“仁之方”而实现),人性之中内在的道德倾向性便得到了发展。
“凡心有志也,无与不可。志不可独行,犹口不可独言也。”[1]136“心”是人的精神活动,“志”是人的主观意识,“心”需要“志”的引导,通过“志”来筛选外物的影响,而“志”则需要“心”的体认与运作,没有“心”的主体能动性就难以存在“志”,有“志”而无“心”则只能是空荡荡的口号,“心”的重要性体现在能够调动外在行为来完成“志”。“目之好色,耳之乐声,譬陶之气也,人不难为之死。”[1]138人以其情求取自己的心合于这样的情性并按自己意愿而为,本无可厚非,但若人之好美色佳音偏于恶的倾向,导致产生“譬陶之气”,人的心灵由于郁结而受阻,从而导致性情的不能发或发之不应而过度,从而造成人性偏失,甚至出现极端,则是因为人心未实现执着定向,没能适当地取其情性而发之,以致背离了本真自然之性情。“心亡定志”,人之性若以不定之志取之,可能会使朴素自然之性沾染不良色彩,天生之性被毁掉,所以要用适宜的物事和适中的手段来正确引导人之性,如此才能发挥人心定志、定向的功能,使情和畅自然地生发并与本情一致。人心以合宜的方式定向后,才能使由性中自然生发的情适中,外显的情稳定中正地体现内在的性。由此,道德教化的实施需要调动人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心的能动性,在道德积习中为心定志,为人性中道德的唤醒和生成提供动力和方向。有情而无心志,与兽类的生理反应无所区别;只有心志而无情,如同冰冷的机器人,则是对人性的泯灭。因此在道德教化中离不开心志的引导,既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又促进人情获得适度发展,培养有血有肉的高道德人才。
最后,“礼乐相成”是教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外在手段。情、心志皆是通过启动个体的内在自觉性而运作,礼乐制度则是从外在规制的角度对人之道德的显现、生成进行约束与引导[14]141-145。圣王制定的礼乐制度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所遵守的行为准则,使得人的喜怒哀悲之情能“发而皆中节”,进而陶冶人性,成就君子人格,这便是礼乐教育的意义[15]304-319。礼,外在的节制,是人们之间的视听言动。性情是内在本质,礼是个体性情的外化。由性而情,由情而礼,再由礼而悟情体性,体人之性,体物之性,最后显发天道,实现天人物我之合一[16]105。“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礼作于情,或兴之也。”[1]137《性自命出》在“教”之后明确提出“礼”,且突出了它与“情”的内在联系:一方面,“礼”生于人之“情”,是“情”的实体表现;另一方面,“礼为动人情而为之”[17]69。礼的制作是从人情开始的,以合宜人情为目的,并根据外在事物的具体形态因时因势地优化处理方案,最终,人们的共识便成为礼仪。道德教化的目的是将德性根植于人性,需依赖人心这个中介,而生于人之情的礼天然具有此项优势。圣人从本性之情中生出礼示范于世人,世人通过学习、遵循外在行为规范进而将其内化于心,又因礼来源于人之诚情,因此人在学习过程中自觉调动真情来理解、接纳礼,在主体意识与外在规范的接触磨合过程中,个体内在形成具有鲜明个人特色且符合社会规范的有生命力的礼。“笑,礼之浅泽也。乐,礼之深泽也。”[1]137与人交往过程中所获得的美好心情皆是因为礼的润泽,礼主体对象的行动和礼节与其本情通达一致,就能够获得良好的情绪体验。礼受到情感的陶冶、塑造,而后再反作用于人之情本体,赋予情感一定的外在表现形式,引导、规范人之情自然而然地符合人伦道德,因此礼教能够直接接触到人之心、人之情,又因其由情而生使得教化过程更贴合实际生活。以礼作为教育手段,既能提高受教者的自觉性,又能获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礼教注重规范性和约束性,乐教则重在主体性和引导性。《性自命出》认为乐教在进行道德教育方面具有速度快和稳定性好的优势,可在潜移默化中帮助个体定心志、导情感,提升道德修养。“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求其心有伪也,弗得之矣。”[1]138乐教不仅能使学者速“求其心”,而且能使个体自觉地追求仁义忠信的道德修养。人们听音乐赏舞蹈,在进行听、闻、观等感官体验的同时,亦感同身受于表演者的情感与意念,把握音乐所承载的旨趣,并与自身的主观意念融合在一起。音乐既满足了我们的感官需求,又引发出我们真诚的道德感。关于乐教的内容,简文指出:“凡古乐动心,益乐动指,皆教其人者也。”《赉》《武》 乐取,《韶》《夏》乐情[1]138,要以《韶》《夏》《武》等 “古乐”“益乐”教其人。自然感官欲望作为“性”的一部分在道德上可能是不合宜的,但是好的音乐会对道德修养产生积极的影响。古乐出自人心,其中寄托着真诚的情感,这种音乐既能够感动听者的内心,又能激发意志,人长期、反复接受良好音乐的陶冶,自然就可以内生德行。“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通。通,愠之终也。”[1]138同时,乐不仅能够引发个体的情感,也能使个体情感得到合理的疏导,使人的性情得以平顺和畅,这是道德修养的开始。抒发内心情感、追求美好精神享受是人的天性,而满足人这种天性需求的最佳方式就是乐。人们出于天性的喜爱来赏舞听乐,并从中得到感官的满足;同时,乐舞强大的德性精神更能自然而然地深深触动观赏者的心灵,使之升华为道德理念[18]230-245。《性自命出》高度重视乐在抒发情感、培养德性方面的教育作用,认为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从人性中自然地流出的情感,这些人类的情感是最真实可贵的,化而为音乐则感染力最强,故以乐教为重要教育手段,既能够关注到个体的情感发展,又能使道德根植于人性之中,促进情感与道德和谐共生。
《性自命出》在天道与人道、天命与性情、宇宙自然与性情之间搭建起一个互通的平台,并使之畅通无阻:人的本性意志与天道的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两者相互互动,因而人能够借助现实的道德践履,进一步锻炼自己的个性意志,在日用与世俗中居仁由义,反己内省,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简文系统地论述了“性”“心”“情”三者在道德履践中的逻辑与状态,正视了人的原初本质、本性,强调心的本体性、差异性、可塑性和发展性,进一步提升心在儒家哲学理论构架中的主体作用。以教来贯通性、心、情,当个体独有的善恶真伪之性、喜怒哀悲之情与肃穆、辽远的天、命相碰撞的时候,在敬畏、自守之中,主体性得到升华、超越,在身心统一的基础上敛身归心,赋予心以主宰的地位,构建缘情立教、内外兼修的道德教化路径。但外在的礼乐制度根植于人情,其最终也归依于内在的审美体悟,如此使得内外和谐、天人和谐,个体达到体认天道、复归天命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