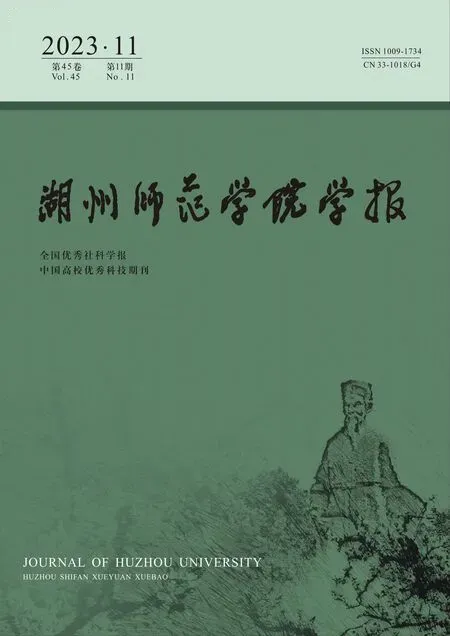13—14世纪的丝路与布料文化*
——以“纳石失”为主要考察对象
邱栋容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13—14世纪,是蒙古民族势力崛起的时代。在蒙古人所征服的广大欧亚地区,随着丝路沿线商业和通信的发展,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联系更为紧密,因而13—14世纪可谓“蒙古治世”(pax-mongolica)。沿丝路一带建立起的驿站制度与商道,极大地促进了海、陆丝绸之路上各国的交通运输和商贸经营活动,物质往来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与碰撞也日益频繁,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审美追求互相濡染,而蒙古作为当时的权力中心,其喜好和倾向更是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布料自汉代以来,便是在丝路上的珍贵通货。其中,沿丝路传入中国西域的“纳石失”,是一种备受元代蒙古贵族喜爱的波斯布料。“纳石失”在中国境内的风靡,使其于14世纪又被意大利的商人、旅行家沿丝路携至欧洲,成为皇家、贵族、教会中精英人士的流行服饰。作为打造衣冠的原料,布料既是必不可缺的生活用品,又是体现审美观念的鲜明文化符号,一定程度上亦能折射出民族的精神性格、文化心态与等级秩序。本文拟以13—14世纪波斯布料“纳石失”的东来与西传过程为主要考察对象,讨论丝路拓通与多民族交融背景下,东西审美选择和文化取向的互趋现象及具体发展过程。
一、“纳石失”的词义与隋唐时期的初步东传
“纳石失”是起源于波斯,用波斯传统工艺制作,且往往带有西域特色图案的织金锦。“纳石失”是波斯语词Nasij的音译,语源出自阿拉伯语[1]63。Nasij实际上是“nasij al-dhahab al-harir”的略语,其中“nasij”本为动词“编织”义,后成为织物、织布的指代名称,“dhahab”意为“金”,该词合意为“织金布”。这一名称到了元代,被蒙古人音译并压缩,最终在文献中记录为“纳石失”,在汉语文献中亦可见纳失失、纳什失、纳赤思、纳阇赤、纳奇锡、纳赤惕、纳瑟瑟等多种异写形式,在清代这一外来词被统一音译为“纳克实”。外国旅行家用各自的语言记述,因此在外国文献中经常可见Nasij,同时亦有Nasich、Nasie、Nachiz、Naciz、Nasis等多种写法。
波斯地区很早就开始生产织金锦。最早的考古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末,阿富汗北部巴尔干附近的提利亚(Tilly-Tehe)发现的一座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古墓,苏联考古工作者发现尸骨的服饰上有各种黄金饰品,皮质衣服上有金线加珍珠的刺绣。这可能就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金缕”[2]65。
从现有的吐鲁番文书当中,可以看出波斯织金锦约在5世纪就已传入中国西域。据文献记载,最早少量进入中原的织金锦,是在6世纪后以贡品形式传入的。《梁书》中载道:“普通元年(520),(滑国)又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3]812《隋书》中亦记载:“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4]1596唐代以后继续有金锦入贡,《册府元龟》中记载开元四年(716)七月,“大食国黑蜜牟尼苏利漫遣使上表,献金线织袍、宝装玉洒地瓶各一”[5]11237;开元十五年(727)七月,“突厥骨吐禄遣使献马及波斯锦”[5]11239;天宝四年(745),“罽宾国遣使献波斯锦、舞筵”[5]11243。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了织金锦残件,使用的是捻金织法,很可能正是当时皇室存留的波斯贡品,能够被藏存在专门放置唐朝皇室之物的法门寺地宫中,可见此时的统治者已经对织锦产品十分珍爱。
文献中明确记载的织造中国金锦的第一人,是隋代的何稠。《隋书》中记:“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踰所献者,上甚悦。”[4]1596此为中国仿制波斯锦的初步尝试。隋唐时期,西域捻金工艺渐经丝绸之路传入新疆地区,为回鹘织工习得并擅长,又经回鹘传入中原,中国渐渐开始正式学习生产加金产品[6]47。不过中唐以前,技术尚未成熟,因此即便是奢侈铺张的玄宗皇帝,也仅仅在府库存有两件织金锦浴袍。晚唐之初,加金技术逐渐精进,织金衣在富豪之门渐趋泛滥。到辽金宋时期,生产技术进一步精细,文献中有关织金锦的记载愈见增多。织锦文物亦有考古实证,不过主要出土在辽墓和金墓,宋墓中尚未发现织金文物。直到元代,由于蒙古贵族的喜爱和生产条件的成熟,织金锦才真正进入生产和穿戴的全盛阶段。
二、元代“纳石失”的传入、生产及其西域特色
蒙古人最早接触到金锦,应该是在蒙古兴起时期,《松漠纪闻》记载:
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又善结金线,相瑟瑟为珥及巾环。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尅丝,甚华丽。又善捻金线,别作一等背织花树,用粉缴,经岁则不佳,唯以打换达靼。[7]31-32
“熟锦、熟绫、注丝”这些丝织物都是用金线织造,所用的原料和织金锦相同。“打换”是北方俗语,即进行交换。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亦记载:
忽毡(Khojend)的阿合马、异密忽辛的儿子,还有阿合马·巴勒乞黑(Ahmad Balchikh)等三人,决定共同到东方各地旅行,并在收集了大量的商品——织金料子、棉织品、撒答剌欺(zandanichi)及其他种种他们认为适用的东西之后,便登上旅途。[8]90
可见此时蒙古人已经对织金锦产生兴趣和需求,但游牧民族本身不具备成熟的工匠和稳定的材料来源,手工业的技术局限于加工皮、毛、木、骨等物品。因此在蒙古发展初期,主要是通过贸易交换来购入回鹘生产的织金锦。
13世纪是蒙古民族势力崛起的时代。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三次西征,攻占了中亚、西亚的主要城市。伊斯兰的服饰艺术和装饰风格给了蒙古人巨大的视觉冲击,富丽奢华的服饰图案和金碧辉煌的织锦样式与游牧民族粗犷豪放的审美观念相契合。在带回的战利品中,包含大量波斯、阿拉伯地区生产的“纳石失”,受到了蒙古贵族们的广泛喜欢。此后一段时间,织金锦的来源主要依靠战利品和邻国的贡品、礼品。《蒙古秘史》中记载,自1211年后,蒙古军队征伐金国,每攻打下一座城市,都会尽力将其金、银、金缎、纹缎驮去,归顺的国家与友好邦国也会定期送上织金锦(1)具体可参见:《蒙古秘史》,余大均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8-419、422、427页。。
但仅仅依靠掠夺和进贡远远不够,尤其在“纳石失”成为蒙古宫廷礼服“质孙服”及其他服饰的原料之后,消耗量一直在急剧增长,因此蒙古人自身生产“纳石失”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于是他们在后来的征战中,除了直接掠夺金、银、锦缎等财富,还占领金、宋两国的织金工厂,并开始掳掠来自中亚的大批能工巧匠,将他们集中起来用作官府的匠户。
为稳定生产“纳石失”,蒙古统治者还特设专门的生产机构。《元史·百官志》中明确记载生产“纳石失”的共有五个局院,即工部的两个别失八里局、纳失失毛段二局中的纳失失局、储政院的弘州纳失失和荨麻林纳失失局。
别失八里局,至元十三年(1276)设立于大都,工匠来自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负责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另一个别失八里局信息不详,大概亦用作织染“纳石失”,工匠应该也来自别失八里。纳失失毛段二局,《元史·百官志》仅记其有“院长一人”。尚刚、赵丰等学者皆认为该局即是窝阔台命令镇海家族世代管理的局院。《元史·镇海传》记:“收天下童男童女及工匠,置局弘州。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及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命镇海世掌焉。”[9]2964可见其织金锦的生产都由西域工人进行。
弘州(今河北阳原)纳失失局和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西之洗马林)纳失失局,于至元十五(1278)年正式成立,《永乐大典》对该局院的设立和变迁信息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弘州、荨麻林纳失失局,至元十五年二月,隆兴总管府别都鲁丁,奉皇太子令旨,招收析居放浪等户,教习人匠织造,纳失失于弘州荨麻林二处置局。其匠户则以杨提领管领荨麻林,以忽三乌丁大师管领弘州。十六年十二月奉旨,为荨麻林人匠数少,以小就大,并弘州局秩从七品,降铜印一颗,命忽三乌丁通领之,置相副四员。十九年,拨西忽辛断没童男八人为匠。三十一年,以弘州去荨麻林二百余里,输番管办织造未便。两局各设大使、副使一员,仍令忽三乌丁总为提调。大德元年三月,给从七品印受荨麻林局。十一年,徽政院奏改受敕,设官仍旧制。各置大使一员,副使一员。[10]3180
弘州、荨麻林纳失失局经过合并和拆分,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回回人忽三乌丁大师成了二局的总管理者。二局的工人也都来自西域。据《元史·撒纳传》记载:“至太宗时,仍命领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9]3016这些阿儿浑军和回回工匠都是从撒马尔罕以及不花剌(今布哈林)区域迁来的。关于此处居住的西域织工,拉施特的《史集》中也有相关记载:“在此城(上都)附近有另一城,名为荨麻林(注:Symaly);此城大多数居民为撒麻耳干人,他们按撒麻耳干的习俗,建起了很多花园。”[11]335《马可·波罗行纪》中亦写道,在马可·波罗离开天德州(约今内蒙古土默特旗)之后,“由此州东向骑行七日,则抵契丹(Cathay)之地。此七日中,见有城堡不少,居民崇拜摩诃末,然亦有偶像教徒及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以商工为业,制造金锦,其名曰“纳石失”(nasich)、毛里新(molisins)、纳克(naques)。并织其他种种绸绢,盖如我国之有种种丝织毛织等物,此辈亦有金锦同种种绸绢也”[12]134-135。可见在这些“纳石失”生产机构当中,不论是工匠、设计师,还是管理人员,均为西域人。也因此,“纳石失”在元代文献中一直沿用波斯名称。
“纳石失”与中国传统金锦在制造流程上基本相同,即都是先以金箔拈成金线,再将金线与丝线在织布机上相交织成。它们区别在于,“纳石失”的织造使用的是波斯的特色工艺。金线制作的方法,可分为片金(平金)和捻金(圆金、撚金),前者做法是将黄金打成金箔,黏附在作为背衬的棉纸或者动物皮上,再切割成极窄的长片,即虞集所说的“缕皮傅金”[13]242,这是我国古代传统的加金工艺;后者则是以丝线为芯,将片金线搓捻缠绕在外,此为西域的传统工艺。唐宋时期,捻金工艺经回鹘织工传入中原,但捻金织锦在加金产品中的比例始终较小。元代“纳石失”虽然仍以片金居多,但大量西域织工的迁入,使得捻金技术较之唐宋更为精进。
除了织法为波斯特色工艺,“纳石失”风格与图案也充满西域风情。唐宋的织金工艺一般为部分加金,装点为主,尤其宋代重视在工艺品上反映本色花鸟,在加金多用“明金”方法,即彩绘勾金。而元代一反宋代写实自然的纹样形式和恬淡雅致的纹样色彩,追求波斯织物的华丽风格与金碧辉煌的装饰效果,崇尚在显花部分大面积用金。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元代皇后像册》,能够看到“御用领袖纳石失”的形象。每位皇后的领口与前襟结合处即是纳石失,可以看到金线几乎布满了整个锦面,仅存的一些隙地只是花纹的轮廓线。这与唐宋的用金尺度有着鲜明的对比。“纳石失”上的主图多为人首兽身或翼兽,周边附有缠枝植物纹或是复杂的几何图案,底部一般有带状或是锁状的花纹,还会绣上一些波斯文字,整体看来花纹繁密而留白少。图案样式规整,上下左右处处对称,显得十分规范化、程序化,与中国传统的织物风格迥然相异。此外,“纳石失”在西域金琦织工的手下,还超越了中国平面化、单层次的传统纺织技术,出现了多层次纹样重叠组合的新样式。这些布料以多种具象花纹为浮纹,以细密规则的几何花纹为底纹,形成双层结构,显得更加繁丽豪华。
三、织金服饰“质孙服”与蒙古民族的尚金风气
早在蒙古征战时期,成吉思汗就对织金衣物十分珍爱,《史集》中记载,成吉思汗在“足资垂训的言论”中有:“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qabā),吃鲜美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11]392他还曾坐在阿勒泰山上说,要将自己的妻妾、儿媳和女儿们“从头到脚用织金衣服打扮起来”[11]393-394。在获得相当的金银财富后,蒙古军队用“纳石失”织就了精美的织金锦帐。行军打猎时,在草原上可见上万个金帐连绵千里,富丽堂皇,用作朝会的织锦大帐甚至可以容下官员万人。马可·波罗曾记录脱脱与纳海争战的景象,言“金锦美丽幕帐无数,俨若富强国王之营垒”[12]444。蒙古君主不仅生前要穿戴、使用“纳石失”,还下令死后要用它来遮覆棺椁、装饰车马。《元史·祭祀志》载:“舆车用白毡青缘纳失失为帘,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9]1926足见蒙古民族对“纳石失”的热爱程度。
元朝建立以后,生产机构开始规模性地织造“纳石失”,数量能够基本满足皇室宗亲、文武重臣等的需求。“纳石失”在宫廷祭祀、丧葬场合中多有出现,用作天子冕服、百官朝服、命妇服饰等服装的装饰布料,但这些服饰中的“纳石失”都是小范围的零星应用,主要起点缀装饰的效果。真正大规模的消耗,是用来制作宫廷礼仪服饰“质孙服”的材料。
据《元史·舆服志》记载,天子质孙的冬服第一等,夏服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与百官质孙的冬服第一等,夏服第一等、第二等,所用布料均为“纳石失”。“质孙服”(亦称“只孙服”“只孙衣”)是元代宫廷中的一种异常华丽的礼仪服饰,《元史·舆服志》的解释为:“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庭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9]1976不仅其布料是使用昂贵的“纳石失”,服饰上的装饰也同样价值不菲,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形容其样式为“只贯大珠以饰其肩背膺间”[14]376。马可·波罗亦言“此种袍服上缀宝石、珍珠及其他贵重物品”[12]183。这些用以装饰的珍珠、宝石、珊瑚等,大概也都来自中亚地区[15]44。
“质孙”实际上是蒙古语Jisun的音译,其原义为“颜色”。在蒙元内廷举办的大型宴饮上,为使场面整齐划一,上自皇帝大臣、勋戚近侍,下至乐工卫士,都会统一穿着同色质孙服,今人将之称为“质孙宴”或“诈马宴”,二者意思相同,只是前者为蒙古语,后者为波斯语。最早有关“质孙宴”的记载出自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描写的是1229年窝阔台即位时的宴饮场面:“那一整天,直至晚上,他们快乐、友爱地共同议论。同样,一连四十天,他们每天都换上不同颜色的新装,边痛饮,边商讨国事。”[8]217服饰的华美挥霍尽显出宴饮的奢侈铺张,统治者对布料毫不吝啬的消耗,展现出元朝建立初期的强大国力。
元代亲历质孙宴的文人对华丽的织金服装多有诗文记述。如袁桷《装马曲》中有:“伏日翠裘不知重,珠帽齐肩颤金凤。”[16]855张昱《辇下曲》记:“只孙官样青红锦,裹肚圆文宝相珠。羽仗执金班控鹤,千人鱼贯振嵩呼。”[17]2068周伯琦《诈马宴》序言:“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只孙,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杖,列队驰入禁中。”诗中描写质孙服“高冠艳服皆王公,良辰盛会如云从。明珠络翠光茏葱,文缯缕金纡晴虹”[18]345。郑泳《诈马赋》记曰:“若其只孙之衣,古制无之,惟织文之暗起兮,却绮绣之彰施。三朝三易,一日一色,或蓝而碧,或绛而赤,轻绯深紫,间错缘饰。必具名而请奏兮,始蒙恩而有锡。数五五爲三袭兮,欲相周而不相杂。□□□秩秩而称身兮,又特命之殊异,带瑕英之璀璨兮,冠火齐之□□。”[13]870
西方的旅行者亦对质孙宴上的服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加宾尼出使中国时记录了1246年推选贵由继任新合汗的大会时举行的质孙宴:“第一天,他们都穿白天鹅绒的衣服,第二天——那一天贵由来到帐幕——穿红天鹅绒的衣服,第三天,他们都穿蓝天鹅绒的衣服,第四天,穿最好的织锦衣服。”[19]60同行的本尼迪克特修士叙述中的服装则略有差异:“本尼迪克特修士告诉我们,他们两人如何看到大约五千位王公和贵族,当他们在第一天集合起来推选皇帝时,全都穿着金色衣服。第二天,全都穿白色锦绣衣服。但是,他们在第一天和第二天都没有达成协议。第三天,他们都穿红色锦绣衣服。这一天,他们达成了协议,并进行了推选。……在这些使者中,也包括本尼迪克特和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这两位修士。由于必需之故,他们在僧袍外面穿上织锦衣服,因为,如果不是穿着合适的衣服,没有一个使者能被准许觐见选出来的和加了冕的皇帝。”[19]98-99《马可·波罗行纪》亦载:“大汗于其庆寿之日,衣其最美之金锦衣。同日至少有男爵骑尉一万二千人,衣同色之衣,与大汗同。所同者盖为颜色,非言其所衣之金锦与大汗衣价相等也。各人并系一金带,此种衣服皆出汗赐,上缀珍珠宝石甚多,价值金别桑(besant)确有万数。此衣不止一袭,盖大汗以上述之衣颁给其一万二千男爵骑尉,每年有十三次也。每次大汗与彼等服同色之衣,每次各易其色,足见其事之盛,世界之君主殆无有能及之者也。”[12]179
百官外番的质孙服都必须由皇帝钦赐,只有受赐质孙服的官员才能参加质孙宴:“与燕之服,衣冠同制,谓之质孙,必上赐而后服焉。”[20]177“凡群臣预御衎者,冠珮服色例一体,不混殽,号曰只孙,必经赐兹服者,方获预斯宴,于以别臣庶踈近之殊,若古命服之制。”[21]2555《元史》中记有三条限定质孙服使用及赐予权力的敕令:“(1308年9月)禁卫士不得私衣侍宴服,及以质于人。”[9]546“(1332年10月)敕:‘……其或质诸人者,罪之。’”[9]812“(1336年)六月丁丑,禁诸王、驸马从卫服只孙衣,系绦环。”[9]835统治者禁止了质孙服在宫廷大宴外的穿戴和私下的质卖流通,也限制了诸王、驸马等赐予下属质孙服的权力,将其使用和赐予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只有受到皇帝宠信的勋戚大臣才有资格受赐,因此对于被赏赐者而言,质孙服意味着极高的荣耀。华美奢侈的服装也因此成为彰显尊贵王权、区分臣子尊卑的制度工具。
元代贵族的尚金风气,也带动了民间的审美转向。按照元代制度,“纳石失”的生产仅限在官服作坊进行,只准蒙古宫廷中的皇室与其达官、近侍使用,但是局院的匠户往往趁劳役之暇,用自家器具自制物料。一旦管理松弛,民间的私织、私贩织金锦的风气就会大涨,尽管政府法令频频,仍然屡禁不绝,民间仍有大量的穿金现象。杨瑀《山居新语》中记载:“余屡为滦阳之行,每岁七月半,郡人倾城出南门外祭奠,妇人悉穿金纱,谓之赛金纱。”[22]226赵丰对中国、蒙古及俄罗斯境内元代丝织品的遗迹考古情况进行汇总,发现“沿着丝绸之路走,凡有保存丝织品条件的地方,都有纳石失的出土和存在”[23]320。在物料不足的情况下,民间甚至还出现了熏银充金的假织金锦,足见元人对织金产品的酷爱。
织金锦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开始生产,且已经发展出较为精细的织金技术,但为何直到元代才真正大规模地开展生产和投入使用,成为宫廷重要服饰,并形成民间尚金的风气呢?原因大概有三。首先是游牧风俗的影响。蒙古人作为游牧民族,常年逐水草而居,为了尽可能在迁徙过程中保留固定的财富,最方便的选择是携带高价值而又轻便的物品,织金锦以金线织成,又能够穿戴在身上,最适合作为游牧民族的财产贴身保存。其次是审美观念的传染。一方面,蒙古与女真长期交流碰撞,二者的生活环境和民俗习惯都十分相近,因此也受到女真人衣冠服饰、帷帐帘幕大量用金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西征过程中,蒙古又见识到波斯、阿拉伯地区繁复华丽的织锦袍服,基于蒙古民族的文化水准和装饰爱好,对极富视觉冲击力的金锦布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喜爱。再次是物质财富条件。唐宋时期的织金锦,均是部分用金,装饰为主,而元代“纳石失”布料则是大面积的用金,金线成为面料的主体,这种奢侈挥霍,只有通过征战和贸易得来无数黄金才可以实现,也因此只有在国力强盛、资源富饶的元朝,才有大量生产“纳石失”的条件。
元朝覆灭以后,质孙服在明朝仍然被沿用。洪武元年二月(1368),朱元璋为显示新朝在文化上对“中国正统”的继承,颁布了革除“胡服”令,《明太祖实录》中记载了诏令大致内容:“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服变易中国之制。……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不得服两截胡服,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24]525然而在如此严厉的诏令之下,质孙服却成了“漏网之鱼”。
曳撒(yì sǎn)是明代服饰代表之一,其读音来源于“一色(yì shǎi)”的变音,实际就是元代的质孙服。刚开始它也被称作“质孙”,但随着时间推移,“曳撒”成为最为广泛的称呼。明代笔记中有关于织造质孙服的记载:“又有所谓只孙者,军士所用。今圣旨中,时有制造只孙件数,亦起于元。时贵臣凡奉内召宴饮,必服此入禁中,以表隆重。今但充卫士常服,亦不知其沿胜国胡俗也。只孙,元史又作质逊,华言一色服也,天子亦时服之,故云。”[25]366尽管盛大的质孙宴无法再现,但元代宫廷宴饮的辉煌和质孙服的奢华成为明代统治者、百官、士大夫崇慕的对象,“士大夫宴会必衣曳撒”“章服虽颁,而杂用只孙之服”“召对宴见,君臣皆不用袍,而用此”。蕴含在衣冠中的权力和殊荣也得到传承,明代绣有蟒、飞鱼、斗牛等纹样及饰襕的质孙服,都属于皇帝的御赐,只有皇恩赏赐才能有资格穿用[26]13。不过,明代曳撒主要继承的是元代质孙服的断腰袍样式,面料已不再使用西域“纳石失”,纹样也都恢复汉族传统。现有资料中仍然可见存在部分由织金面料制造的曳撒:万历帝师于慎行在癸未、甲申年(1583—1584)三次扈从圣驾前往上陵,万历赐其“大红织金曳撒、鸾带等物”[27]5164。但融合东西元素的“纳石失”还是在明代逐渐销声匿迹,“这种特殊丝织物随蒙古族政权织造了将近一百年,曾经反映到游历家马可波罗眼目中,因之也反映入世界各国人民眼目中。但是这种丝织物,竟和元代政权一样,已完全消灭”[28]221。
四、“纳石失”的西传及其影响
13—14世纪是“蒙古治世”(pax-mongolica)的时代。蒙古人在征战过程中,打通了世界的网络联结,使得丝绸之路上的沿线国家,在商业贸易、交通道路、宗教信仰和知识观念上都展开多元丰富的交流,真正建立起了一种“全球性”的文化。尽管没有受到蒙古的统治,但欧洲的文化体系亦受到了蒙古人的冲击:“看起来,欧洲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除新的战争方式、新机器和新食物发生改变外,甚至在日常生活最世俗的方面也得到改变。”[29]13这一点也体现在布料文化上。
“纳石失”在宫廷宴饮上的光彩夺目,让西方的传教士、商人、旅行者都大开眼界。威尼斯的马可·波罗的纪行与佛罗伦萨的弗兰西斯科·佩戈洛蒂(Francesco Pegolotti)的笔记当中都记录了这种华丽的布料,这些文献材料引起了欧洲读者的兴趣。昂贵奢华的织金锦在宫廷与民间的风靡现象,折射出了蒙古的强大国力,让正值黑暗中世纪的欧洲对蒙古文化产生了无限的艳羡。而东西贸易道路的畅通,又让欧洲人由对远东帝国文化的向往,转为对东方具体的丝绸、香料等奢侈品的热切追求。“自13世纪末期开始,中国丝绸大量出现在意大利的交易市场上,尤其是跨国贸易中。在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北部城市卢卡和热那亚的贸易交易文献中,出现了大量关于中国(Catai)丝绸的交易记录。”[30]43“纳石失”作为名贵的东方布料,在这一时期也跟随着其他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出口到了欧洲。
精致华美的丝绸改变了欧洲人对蒙古人“野蛮”“未开化”的刻板印象。欧洲一直将蒙古民族称为“鞑靼”,对其词源考察可发现其为贬义:“鞑靼,译写为西文是Tatare。然而后来多讹写作Tartare。Tatare一词在法语中有‘地狱,来自地狱的魔鬼’之意,今在法国诸州尚以此名指恶人。这与欧洲人认为蒙古人是来自地狱的‘上帝之鞭’也可相互印证。欧洲人对于蒙古人的恐惧在‘鞑靼人’这个称呼上可见一斑。这些游记中谈及的‘鞑靼’和‘鞑靼人’也说明了在欧洲人眼中蒙古人是陌生而可怕的。”[31]16而在织金锦进入到欧洲市场后,西方的文献史料中大多将这种美丽的布料以“鞑靼”来命名:“从欧洲到中国的大量关于13世纪和14世纪的史料都提到一种‘鞑靼布’,即意大利史料中所说的‘panni tartarici’。学者们最近确认,这些纺织品是手工提花织机织成的丝织品,并织有金丝,即阿拉伯和波斯文献中所说的‘nasi’和‘nakh’。”[32]405精致的“纳石失”织金锦改变了欧洲对蒙古人的刻板印象,“鞑靼”这个词汇不仅开始脱离凶悍、恐怖的原义,还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艺术的象征意义:“意大利作家但丁、薄伽丘和英国作家乔叟用‘鞑靼绸’‘鞑靼布’和‘鞑靼缎’等词汇,作为世界上最精美衣料的术语。当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命令制造同其嘉德勋位最相配的150根吊袜带时,他指明要把它们染成‘鞑靼蓝’。”[33]6可以说,织金锦让蒙古在欧洲完成了由野蛮、凶悍到华丽、艺术的整体形象蜕变。
“纳石失”在欧洲不仅仅是饱受欢迎的商品,其绚丽的纹样也推动了意大利艺术的嬗变与更新。14世纪,意大利的丝绸设计中融入了大量“纳石失”的图案和纹样:“法尔克在梳理中世纪晚期意大利丝绸艺术嬗变的同时,指出意大利丝绸在进入14世纪之后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在设计上大量采用来自异域文化的四肢动物、飞翔的鸟类及丰富的植物花卉纹样,尤其是一种弯弯曲曲的藤蔓装饰完全打破了中世纪意大利丝绸画面中的宁静感。”[30]43织金锦还进入了欧洲的绘画艺术当中,成为画家们描写的重要对象,甚至在许多西方传统宗教主题的绘画当中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14世纪意大利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既提到了进口的鞑靼丝绸,也提到了意大利制造的东方风格的丝绸。诸如西蒙·马尔蒂尼(Simone Martini)的《圣母领报》(1333)或保罗·威尼斯诺(Paolo Veneziano)的《圣克莱尔与圣母加冕的多联画》(14世纪60年代中期)等作品,都忠实地再现了最珍贵的东方丝绸。西蒙·马尔蒂尼(Simone Martini)在处理马提亚天使的衣饰时对那些细小的、布满金色碎花纹饰的鞑靼丝绸进行了令人钦佩的图像化处理。……保罗·威尼斯诺(Paolo Veneziano)将圣母和基督的形象描绘在一种丝绸服饰里,其中的每一个元素,从人物的衣服到背景的帘子,都让人立即联想到鞑靼丝绸(Panni Tartarici)。”[30]185-186
尽管在13到14世纪,欧洲丝绸的进口数量和质量较从前的时代都有了巨大的飞跃,但东方纺织品仍然属于奢侈品和珍稀品,因此进口的织金锦在西方也同样被权贵垄断。欧洲部分国家在这一时期颁布了奢华禁令,对东方奢侈品持有和使用的分量按照身份登记进行划分,织金锦也自然被纳入受管制的物品清单当中。于是就如质孙服在元朝具有权贵象征性质一般,穿戴蒙古织金锦在当时的欧洲也成为精英、贵族和教会人士的身份标志。此外,由于其珍贵性,丝绸还被赋予了相当神圣的象征性意义,在宗教活动、典礼仪式等庄重场合多有用途。目前有记载的“鞑靼布”使用于欧洲精英葬礼上的案例有十个:
(1)坎格兰德一世(卒于1329年),维罗纳。
(2)阿方索·德·拉塞尔达(卒于1333年),布尔戈斯:拉斯乌埃尔加斯圣玛利亚修道院。
(3)鲁道夫四世公爵(卒于1365年),维也纳。织金锦被认为是有其他母题的“鞑靼布”。
(4)哈特曼主教(卒于1286年),奥格斯堡:重复的雕像图案,带有波斯故事中巴赫拉姆·古尔和阿扎达(Bahram Gur and Azada)的图案。
(5)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卒于1307年)被人裹以金布抬去下葬(见注17),但不清楚这是不是“鞑靼布”。
(6)桑乔四世之子佩德罗一世·德·卡斯蒂利亚(Pedro I de Castilla,1319年卒),布尔戈斯:重复的鸟类图案。
(7)葡萄牙的布兰切(Blanche of Portugal,卒于1321年),布尔戈斯:图案与6 号相同。
(8)坎格兰德一世(卒于1329年)。
(9)布拉加大教堂大主教唐·贡萨洛·佩雷拉(Dom Goncalo Pereira,卒于1348年):图案如(6)、(7)。
(10)波希米亚国王鲁道夫一世(卒于1307年),布拉格。[34]97
13—14世纪蒙古人的征服与统治,极大程度上推动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的自由交融。由上述材料可知,在隋唐时期初现于中原的波斯织金布料“纳石失”,在13世纪蒙古西征过程中,被酷爱金属及华丽饰品的蒙古统治者沿丝路正式引入中国,并依靠强大的国力搜刮原料、俘获工人,建立起规模化的生产机构。宫廷与民间形成了尚金的风气,以“纳石失”为原料的宫廷服饰“质孙服”还成了蒙古官员的权力符号,元代文人与域外旅行者对此多有记录。贸易交通的发达,使蒙古的强势文化沿丝绸之路进行传播,“纳石失”又随旅行家和商人西传进入欧洲,华丽与精致的纹样使其不仅受到欧洲人的喜爱,从而改善了对蒙古“野蛮”“未开化”的刻板印象,还成了欧洲精英的专属风尚,并进一步融入了欧洲的艺术、宗教等文化领域。“纳石失”在丝绸之路上的两次传播,成了蒙元时代各民族文化交融繁盛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