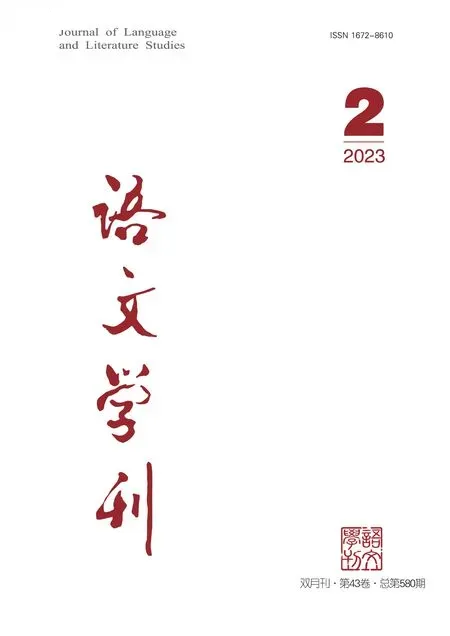张戒转述《文心雕龙》是否原文考论
○李明高
(莒县刘勰文心雕龙研究所,山东 莒县 276599)
近日,偶读张戒《岁寒堂诗话》,联想到文心学界诸多名家曾经因此而展开的《隐秀》篇补文真伪的论争。这场论争,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因为被绝大多数专家认可的观点已经被其弟子乃至再传弟子普遍接受并广泛传播。但读过《岁寒堂诗话》,颇觉有些话不得不说。
从哪里开始说呢? 还是先从张戒转述《文心雕龙》开始吧。
一、张戒是如何转述《文心雕龙》的语句
南宋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言:
《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段师教康昆仑琵琶,且遣不近乐器十余年,忘其故态,学诗亦然。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刘勰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若他人之诗,皆为文造情耳。沈约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论,其实一也[1]9-10。
此段文字忠实于原著,如果说与诸版本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张戒所引三家之言,笔者并未加引号,如此而已。为何? 因为需要对张戒所引三人之论加以分析,然后再定,不可先入为主,误夺他人之声,误解著者原意。这也是笔者为何将其原文摘录作为论文之始的原因。
二、张戒转述《文心雕龙》引发的论争
由以上录文可以看到,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所引刘勰之言共有两处,一是“刘勰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一是“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
张戒可能没有想到,仅仅是因其文中两句,说到底,仅仅因其文中“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这十二个字,引发了一场有关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真伪的论争。
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被认为是《文心雕龙》研究作为一门专学的开山之作,他对《隐秀》篇的态度对后学影响自然亦深。
《文心雕龙札记》,是据黄侃先生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所辑。1919年,黄侃先生的论文《文心雕龙附会篇评》《文心雕龙夸饰篇评》发表在《新中国》杂志第1卷上,《文心雕龙札记夸饰篇评》发表在《大公报》上。其后,黄先生有《文心雕龙札记(题词及略例、原道)》《文心雕龙札记(征圣、宗经、正纬)》《文心雕龙札记(辨骚、明诗)》等文章发表在《华国月刊》等刊物上,1927年,辑有二十篇札记的单行本印行,1947 年,将《文艺丛刊》所发的十一篇札记与原来的合辑,共三十一篇札记,汇为一本印行,1962 年中华书局整理印行单行本。
“案此纸亡于元时,则宋时尚得见之,惜少征引者,惟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此真《隐秀》篇之文,今本既云出于宋椠,何以遗此二方?然则赝迹至斯愈显,不待考索文理而已知之矣。”[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隐秀》)
1943年,蒙文通先生在第5 期《图书集刊》发表《馆藏嘉靖汪刻<文心雕龙>校记书后》言:
“所云‘阮华山得宋椠本《隐秀篇》全文,明人矜为秘笈’者,纪昀以《永乐大典》所收旧本校勘,凡阮本所补悉无之,知出伪撰。晚季黄侃又以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二言为阮本所无,而宋椠之诬,遂有定谳。”[3]
1963年第1 期《新闻业务》刊发了振甫(注:原署名如此)先生关于《隐秀》篇的文章,先生言:
“可惜这篇的原稿残缺不全。据黄侃考证,它在南宋时还是完整的。因为南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里引了这篇中的话:‘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这两句在本篇中没有。可见南宋人还看到全篇。”
1979年,詹锳先生在《文学评论丛刊》发表《<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鉴于“《隐秀》篇在另外的地方还可能有脱简”,“认为‘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两句,也一定是《隐秀》篇的原文,这两句究竟应该补在什么地方,则是无法确定的”。詹锳先生考证的结论是:《隐秀》篇补文为真《文心雕龙》原文。
1980年,杨明照先生同样是在《文学评论丛刊》发表《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质疑》,认为:“南宋初张戒《岁寒堂诗话》上所引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两句,无疑是原本《隐秀》篇里的话。残缺了的《隐秀》篇没有它,倒不稀奇”,等等,针对詹先生所运用的论点逐一予以反驳。
其后,詹先生发表《再谈<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对所运用的论据进行了再次阐发。
1982年,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一书《引证第五》重申其观点,“今本隐秀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风劲秋草’朔字一段,出明人伪撰,故无此二句。盖是篇宋世犹全,张氏得引之也。”同年,詹锳先生《<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一书出版,书中《<文心雕龙>的隐秀论》,坚持《隐秀》篇补文属于原文的观点,并对该篇的文学理论进行了探讨。
1983年,刘文忠先生在《文心雕龙学刊》第一辑刊发《试论刘勰的鉴赏论与鉴赏观》,认为:“张戒《岁寒堂诗话》引《文心雕龙·隐秀》曰‘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这两句话虽不见于今本《文心雕龙》,也不见于《隐秀》篇补文,但属于《隐秀》的佚文是毫无问题的,因南宋时《隐秀》篇全文尚存。张戒所引的两句《隐秀》原文,对我们理解《隐秀》的主旨很有帮助。”
1984年,刘文忠先生在《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发表《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兼与詹锳先生商榷》,提出:“《隐秀》篇在南宋时尚未散佚,张戒《岁寒堂诗话》所引《隐秀》篇的两句话‘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不见于现存《隐秀》篇的原文,以情推之,当在所佚一页之中。但补文中并没有这两句话,阙文不过十字,且分五处,这两句话无法在补文中安置,这是补文真伪最启人疑窦之处。詹先生的考证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该问题的探讨,还有其他学者参与,大多认为张戒引文系《文心雕龙》原文,《隐秀》篇所补之文系伪作。即使是校勘成果富有千万字的王利器先生,其《文心雕龙校证》一书在此问题上亦覆前辙。
纵观这场论争的焦点,集中于一处,即《隐秀》篇补文真伪问题。在其中的诸多论据之中,张戒所引(姑且如此称谓)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是至关重要的论据。从诸位先生的论文来看,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尽管双方均坚持张戒所引的这十二个字是《文心雕龙·隐秀》篇原文。笔者以为,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拿出令人信服的依据,即使是正方,就像刘文忠先生所说,“詹先生的考证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詹锳先生同杨明照先生一样,认为张戒的这十二个字“也一定是《隐秀》篇的原文”。对此,文心学界是普遍接受的。通过张少康等先生所著《文心雕龙研究史》可以得见:“南宋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曾引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佚文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4]
如果历史地考察对于《文心雕龙·隐秀》篇的态度,清代学者纪昀的观点不容忽视。纪昀在《文心雕龙辑注》中眉批:“此一页词殊不类,究属可疑。‘呕心吐胆’似摭玉溪《李贺小传》‘呕出心肝’语,‘锻岁炼年’似摭《六一诗话》周朴‘月锻季炼’语。称渊明为彭泽,乃唐人语。”此段文字,《四部备要》本《文心雕龙》如此。纪昀眉批的文字,《文心雕龙汇评》还辑有后面一段文字:“六朝但有征士之称,不称其官也。称班姬为匹妇,亦摭钟嵘《诗品》语。此书成于齐代,不应述梁代之说也。且《隐秀》之段,皆论诗而不论文,亦非此书之体。似乎明人伪托,不如从原本缺之。”“癸巳三月,以《永乐大典》所收旧本校勘,凡阮本所补悉无之,然后知其真出伪撰。”[5]
《四库全书》介绍《文心雕龙》言:
“是书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至明弘治、嘉靖、万历间,凡经五刻,其《隐秀》一篇,皆有缺文。明末常熟钱允治称得阮华山宋椠本,钞补四百余字,然其书晚出,别无显证,其词亦颇不类。如‘呕心吐胆’似摭《李贺小传》语;‘锻岁炼年’似摭《六一诗话》论周朴语;称班姬为匹妇,亦似摭钟嵘《诗品》语,皆有可疑。况至正去宋未远,不应宋本已无一存,三百年后乃为明人所得。又考《永乐大典》所载旧本,阙文亦同。其时宋本如林,更不应内府所藏,无一完刻。阮氏所称,殆亦影撰,何焯等误信之也。”[6]
可见,纪昀的眉批与《四库全书·文心雕龙》之总目提要基本一致,这也属正常,因为纪昀作为《四库全书》三名总纂官之首,其观点同样体现于该书,是十分合理的。如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持的观点与作为总纂官之首的纪昀相左,那么,关于《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真伪的讨论可能会在清代就发生了。但后起的这场论争,很显然,坚持《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系伪作的观点,承袭了纪昀的看法,同时又对纪昀的论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当年,黄侃先生认为《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系伪作,遂“仰窥刘旨,旁缉旧闻”,另作《隐秀》新篇,不可谓不用心良苦。然而,黄侃先生以及师宗其言的众多学者用来否定《隐秀》篇补文的张戒《岁寒堂诗话》转述的那十二个字,真的是地地道道的《文心雕龙·隐秀》篇原文吗?
这是笔者捧读张戒《岁寒堂诗话》时所产生的一个疑问。
三、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是部什么样的书
考察一部书所引的语句,是否忠实于原文,首先要考察它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这是基本前提。如果是一部完全摘录众书的类书,像《太平御览》,基本可以信任地说,引文忠实于原文,但如果不是一部忠实于原著的摘录众书之类书,而是一部表达作者个人观点之著作,尤其像诗文评之类,那么,化用、引用贤者语言的情形都可能会存在。
我们先看看《四库全书》是如何介绍张戒其人及其书的:
臣等谨案:《岁寒堂诗话》,宋张戒撰,钱曾《读书敏求记》作赵戒,传写误也。考戒名,附见《宋史·赵鼎传》,不详其始末,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戒,正平人,绍兴五年四月,以赵鼎荐,得召对,授国子监丞。鼎称其登第十余年,曾作县令,则尝举进士也。又载,绍兴八年三月,戒以兵部员外郎守监察御史,是年八月,守殿中侍御史,十一月,为司农少卿,旋坐疏留赵鼎,改外任。十二年,罗汝楫劾其沮和议,党于赵鼎、岳飞,特勒停。二十七年九月,以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不言所终,殆即终于奉祠矣。初,戒以论事切直为高宗所知,其言当以和为表,以备为里,以战为不得已,颇中时势,故淮西之战,则力劾张浚、赵开,而秦桧欲屈己求和,则又力沮,卒与赵鼎并逐,盖亦鲠亮之士也。是书通论古今诗人,由宋苏轼、黄庭坚上溯汉魏风骚。分为五等。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始明言志之义,而终之以无邪之旨,可谓不诡于正。其论唐诸臣咏杨太真事,皆为无礼,独杜甫立言为得体,尤足维世教而正人心,又专论杜甫诗三十余条,亦多宋人诗话所未及,考《说郛》及《学海类编》均载此书,仅寥寥三四页,此本为《永乐大典》所载,犹属完帙,然有二条此本遗去而见于《学海类编》者,今谨据以增入,庶为全璧。《读书敏求记》本作一卷,今以篇页稍繁,厘为上下卷云。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7]
张戒为宋高宗时人,所持政见与赵鼎、岳飞相同,而与秦桧相左,故遭贬谪。《钦定四库全书·集部》收录张戒《岁寒堂诗话》,将其列入诗文评类,可知是一部评述诗文的著作。因此,该书引用刘勰之言亦属正常。稍需留意的是,《岁寒堂诗话》并非原本,而是后人辑录而成。
四、对张戒转述段落的分析
欲言张戒《岁寒堂诗话》转述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是否《文心雕龙·隐秀》篇原文,需要对张戒《岁寒堂诗话》加以全面分析,尤其是要对张戒转述的十二个字所处的段落详加考察,揭示其语境,进而对这十二个字做出客观分析。这是上述论争的正反两方都没有考虑到的问题,也正是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即摘录该段落而不仅仅摘录十二个字的原因。
该段落“《国风》《离骚》固不论……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评论自汉魏至大唐乃至当朝诗人,尤其是对当朝文人苏、黄的评论,是需要勇气和胆略的,其所主张的,与刘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观点相类。该句与《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真伪无涉,不予再作分析。
首先,该段落“《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所引“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出自《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8]张戒所引《诗序》为直引,引文与原文相合。
其次,该段落“刘勰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若他人之诗,皆为文造情耳”,出自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9]张戒所引“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并非《文心雕龙》原文,而是镕铸了刘勰的观点,自出己词,其手法显然不是直接引用,而是化用,尽管前面所言“刘勰云”,但言刘勰之大意,并非《文心雕龙》之原文。
再次,该段落“沈约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原文存在两种版本。宋本《文选》如此。百衲本《宋书》、今本《宋书》之《谢灵运传》言:“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10]张戒所引若出自《文选》则为直引,若出自《宋书》则非严格意义上的直引。
第四,该段落“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出自欧阳修《六一诗话》:“圣俞(梅尧臣)尝语余曰:‘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11]梅尧臣之言也收录于元代所修的《宋史·梅尧臣传》中:“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人,侍读学士询从子也。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用询阴为河南主簿,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与酬倡,一府尽倾。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精思苦学,繇是知名于时。宋兴,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尧臣者,盖少也。尝语人曰:‘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世以为知言。”[12]张戒所引梅尧臣言,尽管文字上没有多大出入,但显然次序颠倒了,原本作“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在张戒笔下成了“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直引。
最后,来看该段落“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文心雕龙·隐秀》篇言:“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这是原文——并非“补文”的开头一段。在整个《隐秀》篇找不到张戒转述的那十二个字,而恰恰《隐秀》篇在现存元代孤本至正本中缺文,张戒转述的那十二个字为原文中语的观点由是而生。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综合对该段落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张戒在该段所引的五处,其中只有一处是严格意义上的直引,另外两处尽管文字上有出入或者次序上有颠倒,但也算得上是引用,剩余的两处引用刘勰之言,“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显系张戒转述,并非原文,另一处即是那十二个字,如果按照校勘中一律的原则来下结论,那么,这十二个字也一定不是原文引用,比照亲子鉴定技术中的用语模式,可以说,这十二个字不是《隐秀》篇原文的概率为99%。但问题是,恰恰缺乏版本上的对比,关键是能否科学地判定这十二个字百分之百的是或不是《文心雕龙》原文呢? 还要综合张戒《岁寒堂诗话》全书引用他人言词尤其是刘勰之言的情况而论。
五、《岁寒堂诗话》其他转述《文心雕龙》之处
对于张戒《岁寒堂诗话》还有没有其他地方转述《文心雕龙》,众多学者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或者已经考察过了,大概认为没有,或者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尚未见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在阅读《岁寒堂诗话》时,就产生过这样的疑问,直到认真读过几遍,方知张戒转引刘勰之言不止上述两处。
为研究张戒转述《文心雕龙》的情况,将其与张戒转述《诗序》之处一同加以比较,以便更为清晰地看到转述的情形。
《岁寒堂诗话》言:
“故曰‘言之不足,故咏叹之。咏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观此诗闻捷书之作,其喜气乃可掬,真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子美此篇,古今诗人,焉得不伏下风乎?忠义之气,爱君忧国之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言之不足,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其词气能如此”。
以上三处,我们可以看到,张戒引用《诗序》,也并非完全直引,有的是直接而引,有的摘句而引,有的是化用而引。化用而引,可以说,尽管能找到言词的母本,但已经离开母本很远了,变成了撰写者自己的言辞,若从己出,这样的引用,当然不能用其作为校勘原本的直接依据。依据张戒《岁寒堂诗话》校勘《诗序》是这个样子,同样的道理,如果依据张戒《岁寒堂诗话》校勘《文心雕龙》,也不能用来作为校勘原本的直接依据。
《岁寒堂诗话》另有两处引用《诗序》,与《文心雕龙》所引基本相同:
《岁寒堂诗话》言:“《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世儒解释终不了。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文心雕龙·明诗》言:“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 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另外,《岁寒堂诗话》有两处明显化用《文心雕龙》之言:
《岁寒堂诗话》:“柳柳州诗,字字如珠玉”[1]14;
《文心雕龙·程器》:“孙武《兵经》,辞如珠玉”。
“字字如珠玉”,与“辞如珠玉”有何差别?无非是将“辞”变成了“字”,然后加以叠字而已。倘若用张戒的“字字如珠玉”作为定本,来校勘《文心雕龙》,是否可以呢? 答案是否定的。
《岁寒堂诗话》:“其言近而旨远,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1]18
《文心雕龙·宗经》:“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文心雕龙·比兴》:“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出自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尽管没有标明“刘勰云”,正是出自《文心雕龙》,无非是分别在句首加了个“其”字而已;相反,本文开头所录的那段——众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段文字,有两处确切标明“刘勰云”,却未必是《文心雕龙》原文。仔细琢磨,应该是这么个道理。
六、从张戒转述是否符合刘勰本义加以考察
“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张戒尽管言明系“刘勰云”,通过前面分析,已经基本可以断定这十二个字并非《隐秀》篇原文,但若仔细分析,这十二个字是否符合刘勰《文心雕龙》本义呢,也即,张戒转述是否忠实于刘勰本义?
首先,从刘勰用词习惯来加以分析。张戒所言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是否符合刘勰行文习惯呢? “情”“在”二字于《文心雕龙》中多有出现,但二字连用的,全书中未见一处;“状”“溢”二字《文心雕龙》中亦多有出现,但二字连用的,全书中也未见一处;句中“词外”二字连用,《文心雕龙》全书中并无一处;句中“目前”二字连用,《文心雕龙》全书中也并无一处。如,同样是言“目前”,《文心雕龙·神思》篇所言为:“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语言。就此而言,无论是其用词习惯还是语言风格,都与张戒所言的“目前”迥然而异。综合观之,张戒转述的十二个字,其中四组两字连用者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均未出现,而于《隐秀》篇所谓“佚文”中出现,不符合刘勰用词习惯。当然,若咬定这几字连用在刘勰《隐秀》篇中独一处,仅仅出现在《隐秀》篇缺文,其他地方没有,倘若如此,单凭这方面的分析,的确是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排除,这只能算是一个参考。
其次,从刘勰定义习惯来加以分析。张戒所言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是否符合刘勰定义习惯呢?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这是定义较细的一类,运用一字来诂训一字的,也不在少数,如:“论者,伦也”,“说者,悦也”,“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等等。如果对刘勰定义文体的方法加以全面而综合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者也”句式是刘勰通常采用的模式,“曰”字句尽管出现,但往往不是定义。如果对此还不能有清晰的认识,我们来看“者也”与“曰”一同出现的几个段落:
“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
“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
“录者,领也。古史《世本》,编以简策,领其名数,故曰录也。方者,隅也。医药攻病,各有所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术者,路也。”
仅举如上三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曰”字句式,通常用来表述,而非定义。张戒转述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对于“隐”“秀”的定义方式,不符合刘勰定义的习惯;相反,《隐秀篇》既有的“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对于“隐”“秀”的这种“者也”定义句式与刘勰《文心雕龙》中其他的定义方式完全相同。既然《隐秀》篇在篇首已经定义过“隐”与“秀”,那么,在《隐秀》篇全文之中,惜字如金的刘勰有必要第二次定义言“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吗?按照常理,不会出现重复定义。
再次,从刘勰隐秀本义来加以分析。张戒所言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是否符合刘勰隐秀本义呢? “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很难在《文心雕龙》中找到它的出处,前面已经从刘勰行文习惯上分析过。从义理上来看,张戒所言的“情在词外”,若从《文心雕龙》中追索其源,虽与“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隐秀》)有些相似,但非刘勰本义,刘勰本义“隐”所指向的为“文外之重旨”,也就是刘勰所讲的“义生文外”,言辞之外的意旨,与刘勰在《神思》篇所言的“思表纤旨,文外曲致”相类似,与张戒所言的“情”“词”之间并无多大关联。《隐秀》篇从头至尾不以探讨“情”与“辞”为主,因为刘勰已经在《情采》篇探讨过“情”与“辞”,刘勰在《隐秀》篇着墨较多的是“意”与“辞”。再来看张戒所言的“状溢目前曰秀”。“状溢目前”,刘勰有过类似的表述,如“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极形貌以穷文”等等,但仅仅“写物图貌”,把事物形象地刻画出来,还不能称之为“秀”,因为刘勰所言的“秀”是“篇中之独拔者也”,是篇章之中异常精美的格言,展现的是“卓绝”之美,正如唐代皎然在《诗式》中所言:“至如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争衡,可以意冥,难以言状”,仅仅能“写物图貌”是不能称作“秀”的。刘勰在《谐讔》篇所言的猜物谜,“或图象品物”,就与张戒所言的“状溢目前”相似,能根据形貌的叙述来猜测出物品来,能说不是形象地刻画吗? 但做到这一点还非常不够,“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谐讔》篇),甚或“降及品物,炫辞作玩”(《颂赞》篇),这些不但不是刘勰所倡导的,而且是刘勰所反对的。再如,当前时尚的“走秀”,看上去倒很符合张戒所言的“状溢目前曰秀”,但这样的“状溢目前”能算得上是刘勰“隐秀”之本义吗?显然不是。
既然张戒所言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不符合刘勰隐秀本义,那么,这样的言辞是怎么来的呢? 依笔者之见,与张戒在《岁寒堂诗话》所引的梅尧臣的那段话有关:“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这段出自欧阳修《六一诗话》的言辞,应当是张戒“状溢目前”的根源。而其“情在词外”,则来源于皎然的《诗式》。皎然在《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一文中言:
评曰:客有问予,谢公此二句优劣奚若?余因引梁征远将军记室钟嵘评为“隐秀”之语。且钟生既非诗人,安可辄议? 徒欲聋瞽后来耳目。且如“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积雪”,旨冥句中。风力虽齐,取兴各别……情者如康乐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辞似淡而无味,常手览之,何异文侯听古乐哉! 《谢氏传》曰:“吾尝在永嘉西堂作诗,梦见惠连,因得‘池塘生春草’,岂非神助乎?”[13]
将刘勰“隐秀”论归于钟嵘名下,显系皎然误记。只不过,通过这段文字,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张戒的“情在词外”显然来自皎然的“情在言外”,无非将“言”改为“词”而已。
可见,张戒《岁寒堂诗话》转述刘勰之意的那十二个字,如果用刘勰本人的观点来加以归类的话,那只能是“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撮题篇章之意”(《文心雕龙·序志》),算不上是引用原文,只能说是“撮题”大意而已,而且,这“撮题”大意的真正对象不仅包括刘勰之言,还包括梅尧臣之言。
七、从张戒著述的方式来考察
如果能够考虑到张戒《岁寒堂诗话》著述的方式,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试将本文开头所引的那段拆开来看:
《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
刘勰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若他人之诗,皆为文造情耳。
沈约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
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
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论,其实一也。
上述“五云”,单一而言,其来源前文已分析,但如果从宏观上来考量会发现,将“刘勰云”一定看作是《文心雕龙》中的语句,可能是读者的错误,因为作者张戒并没有这么写过,而是读者理解上的偏差。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张戒明确指出来自《诗序》,但后面的“四云”,只是列举了姓名,而并未明确著作名称,如“梅圣俞云”的内容就不是梅圣俞作品中的言辞,而是出自欧阳修《六一诗话》,既然如此,那么,“刘勰云”也未必就出自《文心雕龙》,前面已经分析过,只不过是“撮题”而已。古人的这种著述方式,其本身可能是严谨的,如,清代宫梦仁所撰《读书纪数略》(有的版本标作宫梦仁编),条目“辞赋十家”“四方歌”均注明来自《文心雕龙》,“书标七观”注明系“《文心雕龙》引孔子言”,但条目“六义”“四子”标注的是“刘勰”,并未直接标注《文心雕龙》,尽管这些内容也融汇自《文心雕龙》。如“四子”条:“买臣忍饥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苏秦握锥而愤懑,班超执笔而慷慨”,若依照将《岁寒堂诗话》“刘勰云”理解成一定系《文心雕龙》原文的逻辑,《文心雕龙》何时有过“买臣忍饥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苏秦握锥而愤懑,班超执笔而慷慨”这样的原文呢? “撮题”而已!
倘若说举清人所撰《读书纪数略》不足以为例的话,读宋代叶适所撰《习学记言》则同样会看到这样的撰述方式。《习学记言》卷三十三《梁书》条录:“刘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言:铨叙一文易,弥纶群言难,自谓文之枢纽极于此。”[14]刘勰《序志》篇言“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但未言“自谓文之枢纽极于此”,刘勰《序志》篇只言:“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叶适所引,并非原文!
前面提及的唐代皎然《诗式》之《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征引《谢氏传》曰:“吾尝在永嘉西堂作诗,梦见惠连,因得‘池塘生春草’,岂非神助乎?”钟嵘《诗品》在评宋法曹参军谢惠连时引《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皎然《诗式》所引也并非钟嵘《诗品》原文,只是化用而已,这本是古人著述的一种方式,然而,有研究《诗式》者,却因此而步入误区,认为,“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一句为“隐”,一句为“秀”,为今本《文心雕龙·隐秀》篇所不载。这样一来,似乎又找到一条《文心雕龙》佚文,何其误也!
如果按照张戒引用《文心雕龙》即出自原文的逻辑,那么,如何认识清代冯班所言的隐秀呢? 冯班在《严氏纠缪·诗法》中言:“诗有活句,隐秀之词也;直叙事理,或有词无意,死句也。隐者,兴在象外,言尽而意不尽也;秀者,章中迫出之词,意象生动者也。”[15]冯班所论隐秀,其言大意,出自刘勰《文心雕龙》,但其表述,实乃自出机杼,并非引用《文心雕龙》原文。
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内篇》所言:“故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于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其于文辞思过半矣。至于不得已而摘记为书,标识为类,是乃一时心之所会,未必出于其书之本然。”[16]同样的道理,许多人读张戒《岁寒堂诗话》,对其中的“刘勰云”理解为必定系《文心雕龙》原文,这不是读者理解上的偏差又能是什么呢? 依我看,是思维定势所决定的逻辑错误。
《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历来争论不休,运用版本、避讳等方面的考据方法固然能从一个侧面加以例证,但运用张戒所言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作为主要依据来例证《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系伪作的公案,可以由此找到真正的答案:“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是张戒“撮题”刘勰大意,并非《文心雕龙》原文,自然不是《文心雕龙》佚文。
对那些以“情在词外”“状溢目前”八个字作为标题来论证刘勰隐秀论或者古典文艺思想的探索者,在此,也善意地提个醒,以不能确信的言辞来论述原著的主张,应该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试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慎之,慎之!
至于不少专著与论文中谈到的“《文心雕龙》佚文”,也不过指张戒《岁寒堂诗话》“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十二个字而已,在笔者看来,这所谓“佚文”本是子虚乌有的。
谈到这里,联想到学界一大怪象。当前,不仅文心学界,其他社会学界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怪圈,后学师承其上,不敢越雷池半步,所以因袭而传,尽管看上去薪火相因,但后继难有创新,更谈不上突破。似乎,信守师成就是对其师莫大的功业了。果真应当如此否? 一门学问,总是在不断否定之中前进的,正如事物是在矛盾运动之中发展的;无论是普通学人还是名家大师,都是在不断突破中成长起来的,需要突破的不仅是前贤,还包括他自己。像前面提到过的杨明照先生,大学本科时攻读《文心雕龙》,研究生时还是攻读《文心雕龙》,即使成名,被冠为“龙学泰斗”之后,仍然孜孜以求,补充、扩展其既有研究成果,从《文心雕龙校注》到《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再到《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就可以印证这一点。正是因为有了诸多“咬定文心不放松”的学界前辈,才真正促成了文心雕龙学成为世界“显学”的局面。
今天,置身非常繁荣的文心学,面对被专家认为“《文心雕龙》的每一块砖几乎都被人敲过”的现实,面对龚鹏程先生所言“注释、诠析、研究者多如过江之鲫”[17]的阵容,只有静心澄怀,板凳敢坐十年冷,才能走进刘勰内心,真正读懂《文心》。
偶读张戒《岁寒堂诗话》,心有所感,成此小文,正如刘勰在《序志》篇所言:“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