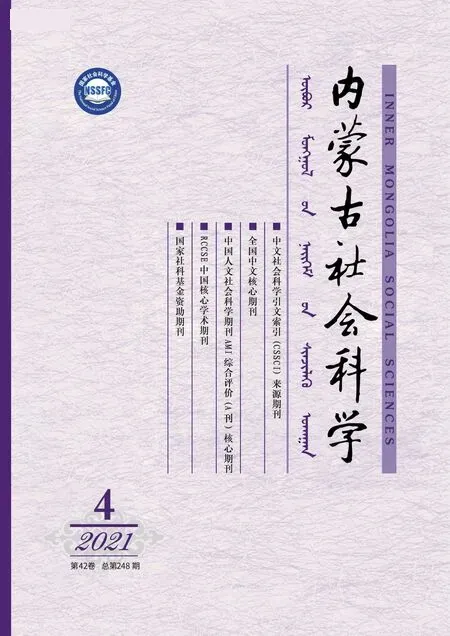论清代科第文化空间中的蒙古族汉诗写作
马腾飞
(嘉兴学院 文法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从文化空间及文学生态的角度看,学界对清代科举有着复杂多元的认识。清代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互摄的重要历史时期,科举为各民族志在仕途的文化精英们划定了统一的文化视野、落实了语言要求、指引了攻读方向,为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视野下,清代蒙古文人的汉诗作品不可视作一般性的文学文本,作为一类特殊的跨民族文化现象以及文学遗存,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交流印记,并保存了鲜活的文化空间与文学现场。这为我们重新审视、评价清代科举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维度,在民族文化交流史料的挖掘上同样颇具意义。
在传统诗文领域,蒙古文人阵容可观,著述弘富,且印证着蒙汉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及文学交流,历来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近年来,清代蒙古文士的个案讨论与群体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清代有汉诗创作的蒙古族诗人已经发现近90位,其中有诗集行世者40多人。深入考察可以发现,他们绝大多数是科场中人,且涌现于清中后期。(1)根据《古代蒙古作家汉文著作考》《八旗艺文编目》等资料统计,清乾隆朝之前有汉诗创作的蒙古文士只有色冷、牧可登、奈曼、保安等寥寥数位,他们虽留有汉诗,但所作不多。这一群体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阶层和时代分布,与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及八旗科举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清代八旗科第与蒙古族汉诗写作的耦合关系
前人研究表明,清前期蒙古族士民的整体汉化程度比较有限,无论是边地的蒙古族士民,还是随朝入关的八旗子弟,均未出现大规模的诗文写作。即便是在乾隆朝,蒙古人中若偶见儒雅知文者,亦会被当作奇人佳话而记载。(2)如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卷四载乾隆初蒙古“敖汉王”事,称其“儒雅颇读书,朝中称为‘敖汉先生’。张少仪《八沟谣》:‘藓垣萝屋出书声,总角儿童读且耕。闻说经帷开毳帐,争呼敖汉作先生。’”昭梿《啸亭杂录》卷九亦载:“敖汉部落为元太祖第四弟某王裔,其台吉额驸彭楚克林沁者,尚简亲王郡主。通文艺,熟习辽金元诸代事。尝与裘文达公谈三史事,裘为之瞪目。然以他书卷询之,彭亦不能骤答也。纯皇帝呼之曰:‘敖汉先生’,见《御制诗》注中。”与此相对应的正是清前期蒙古科举漫长的草创历程。在清初鼎革阶段,蒙古士子均以蒙古文参加考试,清廷对蒙古士子的汉文化素养几无要求。顺治八年(1651),清廷首开蒙古乡试,蒙古子弟与汉族生员分开考试。通汉文者以蒙古语译汉文一篇,不通汉文者仅需作蒙古文一篇。康熙年间,清廷诏令蒙古子弟与汉童生统一试以汉文,同场同题,并不再为蒙古人设单独的生员、举人和进士额数。科举考察内容逐渐向汉文化倾斜是清初以来八旗科举的整体趋势。对蒙古生员而言,他们的科举考试难度不断增加,康熙、雍正两朝的蒙古族中试者额数较前朝大为减少。
但随着政局的稳定,蒙古子弟对科举的热情日益高涨。诞生在京师或驻防地的蒙古八旗子弟更接近传统的汉文化圈,他们享有相对优厚的文化资源,由此成为蒙古科举的主力军。张力均指出:“康熙朝统一台湾后,国家进入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八旗蒙古子弟靠立军功入仕远不如科举容易顺畅……他们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掌握汉文化之中,力求榜上有名,入仕做官。”[1](P.38)乾隆二十二年(1747),科举恢复试帖诗(3)在清人诗文集中,“试帖”与“试贴”两种写法并存,本文表述采用“试帖”。涉及相关书名、诗题、内容时,则依据作品原文。制度,同年,康熙间八旗文试前所加的骑、射考试亦停止,主要教习满、蒙古书及弓箭的八旗蒙古义学也于次年被官方裁汰。(4)八旗蒙古义学主要招收左领下幼童或10岁以上者,教习满洲、蒙古书和弓箭,清廷于乾隆二十三年(1478)裁汰了八旗蒙古义学。参见王风雷《蒙古族全史·教育卷》下,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08页。纵观乾隆朝以来的八旗科举制度改革,以汉语诗赋取士的科举政策得到稳固,富有民族色彩的骑射则越来越被边缘化。咸丰年间钟秀的《古丰识略》记载了归化一地的文教盛况:“按我朝,以八旗重兵,分驻各要地,揆文奋武,所在皆然。自乾隆初,始以右卫驻防,移驻绥远城,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文学之士,争自濯磨,俊义遍于胶庠,汇征登夫皇路,科第甲乙,蔚然炳然。”[2](P.35)归化城为古丰州地,今属呼和浩特地区,《古丰识略》为该地区的首部方志。这段文字描绘了乾隆朝后蒙地八旗文教、科第的繁盛景象。如果说清前期的科举改革倒逼蒙古子弟学习汉文、攻读儒家经典,促进了蒙古族文士的汉化进程,那么乾隆年间的科举改革则为蒙古族文士提供了更为优厚的文学生态。可以说,乾隆一朝是蒙古族科举以及文学发展的重要转折期,蒙古八旗科举与文学之间的耦合关系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体现。
蒙古族的汉文作者并不局限于科举文士,边地王公、世家女眷中也时而得见,但整体看来,科举文人在蒙古族汉文作者中占有绝对比重。据统计,清代中期(康熙至道光朝),蒙古族有汉文创作者30余位,其中高中进士者18人。清代后期(道光朝至清末),蒙古族汉文创作者有40余位,其中高中举人及进士者多达26人。(5)参见多洛肯《清代八旗蒙古文学家族汉语文诗文创作述论》,载《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多洛肯、贺礼江《清代后期蒙古文学家族汉文诗文创作述论》,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清中叶以来,梦麟、和瑛、松筠、博卿额、法式善、托浑布、柏葰、花沙纳等文学成就较高的蒙古文士,均是乾隆朝科举入仕。在整个清代蒙古族的诗文写作中,无论是文人数量、存世著作还是文学成就,八旗科举文人均占有显著夺目的地位。因此,与清代诗坛上遗民隐士、布衣草野、女性闺阁、方外僧道等作家群多点开花的局面不同,蒙古族诗文写作群体的阶层属性略显单一,他们绝大部分属于仕宦文人阶层。
清代蒙古八旗科举还直接催生了一些蒙古文学家族。平步青《霞外攈屑》云:“国朝自顺治三年丙戌会试,至光绪九年癸未,凡百二科,宗室、满洲、蒙古、汉军洎各省,科第传家、清华接武者,偻指未易数。”[3](卷一《繛汋山房睉记》)前人已经注意到,清代“科第传家”者同样包括蒙古族。参考蒙古族中科第显赫的和瑛、法式善、博卿额、恭钊等家族,其汉语诗文创作皆能够传承数代。与汉族诸多动辄绵亘百年的文章巨族相比,这些科第家族的数量、规模、持久性虽稍显逊色,但如果进一步剖析家族内部的文化结构与濡化范式,清中叶以来的蒙古世家与汉族的簪缨名门已经相当接近了。
法式善、和瑛两大家族是蒙古族科举文章之典范。在这两大家族内,祖辈、父兄均能够给予后生晚进殷切的功名瞩望,并将其落实为具体翔实的科场、诗文指导,其文脉家风由此得以传承赓续。法式善自云:“余曾祖管领公、祖员外公皆喜读书,勤于职事。余父始以乡科起家。余祖尝戒法式善曰:‘汝聪明,当读圣贤书,勿以他途进!’”[4](《重修族谱序》P.112)法式善在赠予儿子桂馨的诗中说:“场屋烛七条,杏花红一色。十年风雨声,读书此荣极。汝兹年十九,凡是宜勉力。”[5](《再题礼部所刊会试录登科录后》P.281)其殷切之情,溢于言表。和瑛之孙谦福自幼承家学,自称“先子半世叹商瞿,晚岁获我如绀珠。锦襁绣褓绮罗襦,石麟蜡凤爱无殊。少长亲授诗与书,相期云路骖神驹”[6](《岁腊记梦》P.78),交代自己承诗书之泽,荷家门之望。谦福对子侄同样抱有极大的功名期待,他曾督促侄儿锡珮读书,见其天资聪颖,喜而赋诗以示勉励。“独念累世基,不可无此续。富贵等浮云,儿孙自有福。贻谋金满,不如教之读。六经具根柢,入门寻归宿。譬如构堂室,榱杗先版築。百式烦搜罗,兼收而并蓄。又若贾求售,必先韫诸椟。文字贵清真,要有胸中竹。宋艳与班香,马工兼枚速。掷地铿精金,摩空戛鸣玉。圆若珠走盘,高如建瓴屋。百炼钢始柔,九转丹初熟。鸣则必惊人,飞而定食肉。青紫拾芥耳,余事博科目。”[6](《督锡珮侄读书见其资性聪颖可期成立喜而赋诗以示勉》P.68)此诗凸显了谦福对后辈读书方法及为诗之道的具体指导:涵养上要以儒家六经为根底,见闻上要广泛搜罗各类文献,文字上要出落为清新自然、圆融遽密。可谓反复叮咛、关怀周至。谦福虽声称“青紫拾芥耳,余事博科目”,但当锡珮下笔成文、科第有望时,谦福又作诗云,“果是云霄名桂种,天葩才吐已奇香”[6](《锡珮侄初学为文下笔颇有思致口占志喜》P.69),喜悦之情、折桂之盼跃然纸上。这些细节是当时八旗蒙古家族内部文化教育、科第传承的缩影。
诗文世家的出现标志着传统汉文化在蒙古家族的凝定与持久传承。颇有意味的是,清廷其实一直担忧八旗彻底汉化,官方在八旗科举上亦作了相应改革。《古丰识略》载:“洎道光中年,始停止驻防乡会试,非重武功而轻文德也。国家自入关定鼎,以骑射为先务。帖括章句,原藉以为取士之方。八旗子弟进身之始,不专赖此。”[2](PP.35~36)驻防八旗子弟的科举应试也曾改为文字翻译科,重点扶持满、蒙等民族语言,如驻防杭州的贵成本为道光癸卯(1843)科的举人,于道光三十年(1850)翻译会试及第。有的蒙古文士自此无意仕进,如驻防镇江的蒙古文士燮清,其弱冠时应童子试冠军,文科改制为翻译后,“遂无意进取,日以训迪后进为乐”[7](卷末延钊跋文)。事实上,凭借常规科举入仕似乎更得八旗蒙古文人之心,如衡瑞为蒙古族名臣倭仁之孙,曾以祖荫赏举人,“恒以科名非战取为憾,壬辰春,始获登雁塔入词林”[8](卷末张翼廷跋文)。从以上案例看,清中后期的八旗蒙古文士对传统科举出身之执着并不亚于汉族文士。
龚自珍尝言:“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传人可知。”(《己亥杂诗·五十四》)许承宣《掌院学士徐公寿序》亦言:“国家用人,与人所以见于天下,不岀科名、文章二者。非文章无以重科名,非科名无以见文章。”[9](卷下《掌院学士徐公寿序》)考察清代蒙古文士生平,“科以人重”“人以科传”的态势贯穿始终。科举功名影响了他们的写作范式,并为其文学交流与创作存世提供了保障;热衷诗书的崇文家风又能反哺子弟的科第,鞭策他们绍继祖德、光大门楣。自唐以后,科举与文学的耦合关系广泛见于各个时代,而在清代蒙古族文人群体中的体现最为集中和具体。
二、科第文化空间与蒙古族汉诗创作及文学交流
在科举时代,“学而优则仕”是士子普遍的人生追求。对于八旗蒙古文人而言,科考与为宦经历几乎构成其生涯的全部。自乾嘉以来,博明、法式善、和瑛、柏葰、延清、锡缜等蒙古文人俱是如此,“学”与“仕”的经历几乎贯穿终生。戴璐《藤阴杂记》曾载蒙古族诗人博明事迹云:“人有叩其姓氏者,答云:‘八千里外曾观察,三十年前是翰林’。又云:‘一十五科前进士,八千里外旧监司’。”[10](P.74)博明的仕途人生是诸多八旗蒙古科举文人的缩影,他早年奋战科第,后来多身居要职,其诗文创作既展现了缙绅士大夫的心路历程与宦迹边功,也流露出浓厚的纱帽之气。
柏葰早年不第,于道光六年(1826)终成进士,此后屡掌文衡,五次出任乡会试考官,最终因戊午科场案牵连,下狱论死。柏葰一生的行藏得失与科举关系十分密切。查阅柏葰所著的《薜箖吟馆钞存》,与科考密切相关或带有浓郁科举氛围的诗作随处可见,早年府试、科试阶段的诗作有《府试蜡梅》《科试试院古槐》《阅题名录》《府试盆梅》《府试水仙》等,落第感怀诗有《下第出都宿邯郸》《道出鸣谦驿》等,为官后的典试诗作有《典试山左纪恩即呈郭兰石大廷尉尚先》《试院即目》《辛丑十月考试恩监闱中步龚季思宗伯守正原韵》《戊午秋闱朱桐轩大司农以聚奎堂王衷白诗步韵见示》等,这些诗作或自述胸臆,或步韵庚和,系统再现了他的科举经历及仕途人生。除柏葰之外,蒙古八旗中的许多文士一生与科举结缘颇深,“学”与“仕”的历程体现在诗文创作与文学交流中。
在科考前期的求学阶段,八旗蒙古子弟能够与满、汉文士结为师友,朝廷及地方书院、私塾成为他们重要的文化活动空间。白衣保(字鹤亭,察哈尔镶黄旗人)与国柱(字天峰,博尔济特吉氏,满洲籍)相识于国子监。白衣保回忆曰:“乾隆丙辰,予年十五,蒙恩入国子监学,以东鲁孙在原先生为师,以满洲国天峰为友,师友启迪,学为韵语。”[11](卷首《鹤亭诗稿自序》)纵览白衣保的《鹤亭诗钞》,他与师友孙谔(在原)、国柱(天峰)的赠答唱和之作几乎贯穿全集,如《郊居病中怀在原师》《送在原师二首》《人日怀在原师》《夜月怀在原师》《晚秋怀天峰》《七夕怀天峰二首》《登听涛亭怀天峰》等,可见这一跨民族的文学网络持久而稳定。
与为官后的应酬往来相比,微时文学切磋、酬答结下的文人情谊更为简单、纯粹。如友人云恒焜(6)恒焜字舒翘,蒙古正白旗人,同治三年(1864)举乡试。,“性耽吟咏,情尚风骚,撰帖括之暇,间拟古近体。无不虚心就正,折节求明以期于惬心。贵当而后已,非此以干誉也”[12](卷末景闰跋文)。晚清镇江文人张宝森与延清互为诗友,他在延清《锦官堂试贴序》中写道,“余家贫,以课童蒙自给,子澄时时至至,则清谈不辍。尝约为试帖诗,日或各得数首,每当落日气清,輙踯躅行吟于溪桥竹木间,推敲声病,斟酌分寸,及暝而返,得月则返益缓,或遇严寒,微霰簌簌落襟袖间,肤尽生栗,而吾两人咿唔辩论,尚未休也。见者笑以为痴,而吾两人则弗之顾”[13](P.31)。延清少时驻防于镇江,与当地汉族文士多有来往,友朋之间推敲课艺、试帖是当时地方文人间的日常文学交流。张宝森该序回忆了延清和自己刻苦吟诗、切磋谈艺时的融洽与忘我,刻画了两位清贫书生谈诗成痴的生动情景,同时也彰显了蒙汉文士在科考生涯中结识下的真挚情谊。
在备考科场的求学历程中,依托于父辈的仕途宦迹及人脉资源,许多蒙古文士得以结识各地满、汉文士,或拜其为受业恩师,或与之结为学伴诗友,从而形成文人阶层多元、地域民族各异的文学网络。以晚清恭钊家族为例,这一蒙古家族内的文学名家包括恭钊及其兄恭铭、侄瑞洵、宗侄锡缜、锡纶等。恭铭、恭钊为琦善之子,琦善延请道光壬午进士、海宁文士朱栻之为长子恭铭授课,恭铭早逝后,朱栻之将其试帖诗集《石眉课艺》整理付梓,并亲自为其撰序。锡缜的诗友圈和其父保恒的宦迹亦颇有渊源。锡缜随父任职西安时,始从杨澹人学为古诗文。保恒任职徐州时,又为锡缜的胞弟锡纶延请彭城名士孙运锦为师,随后锡缜与孙运锦结为诗友,并为其诗集撰序。杨锺羲《雪桥诗话》载:“厚庵都护尝辑师友倡和之作为《感旧拾遗集》一卷,中如杨澹如昌朝,湖北大冶县诸生,道光庚子,厚庵侍桓靖公(保恒)官西安,从澹人游,始学为诗古文。澹人寄籍平利,试陕闱久不售,奔走衣食于文字以死。刘子香心龙,江苏吴县人,道光癸卯举人。周弢甫,阳湖诸生。孙心仿运锦,江苏铜山县孝廉方正。刘子迎达善,阳湖人,道光甲辰举人,官登、莱、青道。”[14](P.1575)不难发现,锡缜文学网络中大多是科场中的汉族文人。锡缜《送刘子迎同年达善下第南归,兼寄弢甫》一诗曰:“十年前知刘子名,今年同试来春明。试罢送子吾亦去,南枝北风重行行。吾宗蒙古事骑射,授以书籍视不凝。颇媿与子同岁生,眼向江表青山青。返棹扬州语弢甫,吾今侍宦仍梁城。(卢台宁河县治宁河即梁城所也)梁城濒海三十里,君辈跨鹤吾骑鲸。前年访碑萃墨亭,未过淮浦心怦怦。刘子觏止甚非偶,相期他日不胜情。”[15](卷二)诗中“刘子”即刘达善(7)刘达善,字子迎,原籍江苏,改籍顺天府大兴,道光甲辰举人,曾任祁阳知县、湘乡知县等职。。道光二十四年(1844),锡缜与刘达善同举顺天乡试,此诗是友人下第时的宽慰之作。诗中还提及江苏阳湖诸生周弢甫,亦刘达善所绍结识的挚友。锡缜将二人视为生平知己,平时于道义、学问上互相砥砺。诗中对友人不授予以同情,相期他日重逢。从科第文化空间考察八旗蒙古文学世家,可以具体探索跨民族文学交游网络的形成。

此外,许多仕宦文人均有巡查书院、典试监考之举,蒙古文士亦多有此经历。在他们及第后再次回到书院、试院时,已经由原来的“应试者”变成了“选拔者”,其阶层身份、文人心境的转变同样体现在所作诗文上。他们有的以过来人的身份回顾往日甘苦,勉励后学,有的则记录试院情境,还原科考场景。如和瑛曾任职安徽,作《颍州府试院即事赠诸广文》一诗,诗人以“诸君莫厌官闲冷,我亦三条烛下客。居官共矢玉壶冰,抡才明月倒海索”[18](P.696)之句勉励同僚尽心育才、取才。布彦《听秋阁偶钞》卷四有《初至保定,值县扃试毕,并闻邑侯述试童情事,感而有作》一诗,描绘了保定童试选拔的混乱及冷清,反映出地方文教的薄弱。在此类作品中,更多的是蒙古、满、汉诸同考官的联吟唱和。在漫长的典试过程中,消磨日晷并非易事,但足以成为考官们的诗文创作契机。个人的抚今追昔、同僚间的赠答酬唱成为典试诗作的常见题材。柏葰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充江南典试正考官,有《辛亥秋闱翁遂盦前辈心存用聚奎堂壁间韵见赠奉和》《奉酬杜芝农中堂受田用前韵见赠大作》《前意未尽更成一律》《用聚奎堂壁上韵奉酬舒云溪少农兴阿》数首诗纪之,均是他在典试期间与汉人名臣翁心存、杜受田、满洲文人舒心阿的步韵唱和之作。柏春亦有《和董醖卿观察书院监试感赋》四首,记载了监试的所见所感,颇值一读,如其二、其四诗云。
名山讲席帝京南,济济英髦圣教涵。执卷一时争甲乙,传经几辈出青蓝。朦胧竟误梨云幻(诗题“一树梨花落晚风”乃皮日休《咏鹭鸶》诗也)霡霂犹迟杏雨酣。笑我壮心如见猎,冒寒缩手效庭参。
忆从负笈拜名贤(乙酉在金台书院肄业山长为顾南雅先生)小契文场翰墨缘。锁院钓鳌频毷氉,金台市骏亦缠绵。结来夏课依山斗,分得春膏润砚田。一自瓣香传鹿洞(朱蕉堂师时任顺天府丞),不堪白首说彭宣。[19](P.25)
董醖卿即扬州文士董恂,在京期间屡次担任会试主考官,是柏春的主要诗友。在以上第一首诗中,柏春盛赞了英才济济、青出于蓝的文教盛况,并记录了本场考试的试题,末句用“见猎”形容自己见到试题后的技痒难耐,亦欲小试身手。在第二首诗中,诗人回顾了自己读书求学的经历,追忆科场中与汉人师长名贤结下的翰墨之缘。颔联含蓄交代自己当年曾困于科场,颇有恓惶、失意之感,颈联、尾联深情回忆了自己向诸位名贤商榷风雅、叩问课艺时的勤学历程,并以南宋朱子、西汉彭宣等古先贤比之师长,充满崇敬之情。这两首七律措辞典雅,文采绮丽,深得“庚扬美盛”之诗教,堪称蒙古文士总结、追思科第生涯的代表作。
纵览清代蒙古族的汉诗作家群体,科举为宦经历在他们的生平履历、写作生涯中影响甚大。而与科第文化密切相关的家塾、书院、试院等求学、监试场合成为蒙古、满汉文人交流频繁的重要场所。从他们早年备考应试的辛勤练笔、下第及第的流连咏叹,再到为宦后典试期间的感怀追思、叠韵酬唱,形成了一个以“科第文化”为核心专题的写作情境,由于蒙古八旗身份的特殊性,这一写作情境同样可以看成一个跨民族文人交流的特殊文化空间。其中,各民族文士以汉语诗文为沟通媒介,赠答往来,切磋诗文,结下了深厚的师友情谊与文字之缘,这无疑为清代民族文化共同体建构创造了有利条件,有着积极意义。
三、科举试诗制度对清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影响
科第文化空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封闭结构,而是历朝科举政策影响下科第文人的文化活动及交流场域叠加的总和。科举制度在这一文化空间中处于核心地位,引领着文人的文化视野和备考方向,也左右着文人科考命运的升降沉浮。在科第文化空间中,科举制度的改革不啻为内在“文运”枢纽的转变。纵观清代诸多科举改革,对当世文学影响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当属乾隆二十二年恢复的科举试诗制度。“科举恢复试诗所暗示的君主崇尚诗学的意向及艺术观念,无论对整个社会还是诗坛都是个极为重要的信息。”[20]对于依托八旗科举出身、与科举仕途关系密切的蒙古文人而言,这一制度变革尤为重要。从他们早期生涯的科考选拔到后来的诗歌创作、审美崇尚,均可看到试诗制度带来的深远影响。
科举试诗肇自唐朝,北宋因王安石变法而罢科举诗赋,元明两代延之,至乾隆而复振。在试诗改革实施之前,蒙古子弟原本可通过官生或笔帖式等途径直接取得乡试资格。但自顺治十一年(1654)始,清廷取消了蒙古博士、有品笔帖式等直接参加会试的资格,只有举人身份才可以应考,并要求一律在京参加会试。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颁布谕旨令会试第二场表文改为五言八韵唐律,拉开了科举试诗改革的序幕,并逐渐影响到乡试及以下的各级考试。乾隆二十四年,乡试于第二场今文外亦改加试五言八韵唐律一首,照会试一体办理。乾隆四十七年(1782),诏令试诗由二场移至头场,并颁旨称,“若头场诗文既不中选,则二三场虽经文、策问间有可取,亦不准复为呈荐”[21](P.496)。在整个科考系列中,诗歌的地位显得愈加尊崇。清廷最初下令改考诗歌时,也曾考虑到“边方、北省声律未谐,骤押官韵,恐不能合有司程式”[21](P.357),但同时又表示“至下科会试时,则三年之功自宜研熟,不妨严其去取”[21](P.357)。这意味着,对蒙古科考士子最为重要的乡试、会试均有试诗内容,且录取越来越严格。
试帖诗题前有“赋得”二字,形式固定,格律严谨。其中乡试、会试用五言八韵之体,童试用五言六韵。乾隆间文士阮葵生云:“试帖诗不过八十字耳,而体物缘情,铺陈排比,上之赓扬美盛,下之刻画景物,读之可以见胸襟器识,腹笥才情,孰谓小技未尊乎?”[22](P.431)这是对试帖诗学的精妙概括。清中叶以降,八旗蒙古文士创作了大量试帖诗作,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颇值得注意。其中不乏自成卷帙、以“试帖”名集者,如法式善《存素堂试帖诗钞》一卷,谦福《桐华竹实之轩试贴诗钞》一卷,恭铭《石眉课艺》一卷,延清《锦官堂试贴》二卷、《四时分韵试贴》四卷、锡缜《退复轩试贴诗》二卷、《退复轩试帖未弃草》一卷。此外,另有不少蒙古文士将试帖诗作附于集中或卷末,如博明《西斋诗草》中存有《赋得鸭绿平堤湖水明》(五言六韵得流字)、《赋得牧童遥指杏花村》(五言八韵得春字)、《赋得人淡如菊》(得芬字)、《赋得瓶内白莲》(得鲜字)、《赋得三赋白圭》(得寒字)等,和瑛《易简斋诗钞》中有《赋得鹖旦不鸣》《赋得家在江南黄叶村》等,《太庵诗草》中有《赋得虞美人》(限愁字)、《赋得饲池鱼》(易简斋诗钞作《饲池鱼》)《太平府童试赋得磨兜坚铭》(得言字五言八韵)、《颍州府童试赋得龙华会》(得光字五言八韵)等,后两首当是典试时技痒与考生同题而作的试帖诗。布彦《听秋阁诗钞》四卷,其中前两卷均为试帖诗作。恒焜《臞鹤诗存选刻》卷末附试帖诗五首,分别是《一洗万古凡马空》(得龙字)、《桃花流水鳜鱼肥》(得鱼字)、《寒夜客来茶当酒》(得茶字)、《岁寒三友》(得三字)、《晚来天欲雪》(得来字),其中《一洗万古凡马空》为诗人参加甲子顺天乡试之题。他们平日练笔精勤,创作丰赡,对自己所作的试帖诗比较珍惜,故其作多收于集中。即使是无需科举,凭借祖荫即可获得高位的蒙古文士,亦将试帖诗视为诗学启蒙或群聚研讨的对象,对其产生了极大兴趣。如清末旺都特那木济勒《如许斋集》独列“排律”一卷,均为五言八韵的试帖诗。在文体观照上,八旗蒙古文士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力求提升试帖诗的文学品格,在整个写作生涯中,试帖诗学的影响也每每可见,整体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格律诗学的启蒙与引领。清代试帖诗的体制格式严于前代,且题目多出自经史,或前人掌故、诗句、成语等。对于少数民族的一般文士而言,长达八韵的诗歌形式对其汉文化素养有着极高的要求。在获中科第之前,大多数蒙古文人与满汉及各族士子一样,必须熟谙科考内容流程,钻研时文制艺。清人任联第云:“试帖著为功令,学者童而习之。自乡会试以至词馆,诸公莫不潜心致力于此。”[23](卷首《七家诗辑注汇钞序》)作为当时科举文士“童而习之”的基本功,试帖诗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格律诗学的知识养成。格律诗中最基本的平仄对仗、排比声韵、掌故化用,均可从试帖诗中习得,由此掌握古典诗歌的其他各类体式。在此基础上,许多蒙古文士的诗学天赋被激发,由“知之者”变为“好之者”乃至“乐之者”,如谦福“生平无嗜好。早岁举业之暇,即攻古近体诗。通籍后,尤肆力焉。洎乎引疾家居,藉诗遣日,著作益富”[6](锡珮跋文P.133),恭钊“自束发,从师习贴括业,佔毕之余,学为古今体诗”[24](卷首自序P.63),恒焜自云“自二十入泮后,即事吟哦,家山尊尝责余不务正业”[25](卷首自序)。许多蒙古文士在攻习举业之暇培养出吟咏之才,甚至终身耽于吟咏。
二是咏史、咏物、写景等题材内容的反复摹写。清代试帖诗虽“题之种类咏古、咏物、言景、言情、天文、地理、草木、虫鱼,无所不有”[26](P.278),但整体可凝缩为“怀古咏史”与“写景咏物”两大类。纵观清代蒙古诸科举文人的诗集,其中与试帖诗创作思维、推敲手法相类的写景诗、咏物诗、咏史诗占有海量篇幅,且多出以近体律诗、绝句等大型组诗形式。如法式善有单独的咏物诗集《存素堂诗稿》,列咏物诗240首,每首取一字为题,分咏天文、地理、器物、草木、禽鸟等,其题材内容与试帖诗相近。法式善之孙来秀所传作品今存《扫叶亭咏史诗》《扫叶亭花木杂咏》两首,悉为近体绝句。和瑛长于律体组诗,“至于范水模山,感时体物,颛缉雅颂,撠掖风骚,乃欧梅之替人,夺苏黄之右席”[18](吴慈鹤序P.692),诗集中《分赋赏心十咏》《署圃杂咏十八首》等作,或标明“得某字”,或用五言六韵之体,脱胎于试帖模式的痕迹相当明显。
三是落实了以唐诗审美为旨归的“美盛”诗风。试帖诗能够直观考察文士的文才与腹笥涵养,且其体例整肃雍容、风格平正典雅,宜于鼓吹休明、庚扬美盛,因而成为绝佳的应试文体。回望当时,乾嘉以来承平日久,试帖诗制度带动了点缀升平、润色鸿业的士林风气。在充斥着唐宋诗风之争的清中叶,试帖诗以“唐律”为别名,标明了清廷试图稳固、推扬高华浏亮、宽大宏博的唐诗风神,在这一点上,蒙古文士无疑顺应了官方的诗学审美要求。(9)米彦青研究指出了唐诗影响下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的家族性特色、创作动因及其与蒙汉文化交流的关系。具体参见米彦青《接受与书写:唐诗与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9页。法式善在《同馆试律汇钞序》中点明了君主好尚对文学风气的引领,及试律“总乡、会试朝考馆课”的选拔功能,并郑重指出,“试律一体,虽未足尽其人之材,而总乡、会试朝考馆课诸作,鼓吹群籍,漱涤万态,其至者足以继赓歌扬,拜唐虞三代之风,而其余亦皆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27](卷首序)。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鸣国家之盛”的政治功用。再看谦福《赋得五言八韵》一诗:“试贴传唐代,词场课士资。五言从正格,八韵赋新诗。恰按琴弦奏,相生律馆吹。声谐兼徵羽,音叶备匏丝。焕若修楼手,纷如列彩眉。书城原共拥,笔阵俨同麾。摇岳摛璆管,歌风献玉墀。庚飏鸣盛世,作颂集皋夔。”[6](P.131)此诗将五言八韵的试帖诗作为摹写对象,可谓以“试帖”论试帖,足称工巧。诗中论及试帖诗的历史因革及具体格式、声律、辞采、掌故等要素,最终落实在“庚飏鸣盛世”的功用之上,与法式善的论断如出一辙。
可以说,试帖诗是科第文化空间中最为典型的文学样式,与其相关的试帖诗学从文学启蒙、题材内容、诗歌审美等方面对清代蒙古文士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试帖诗与八股文相类,皆因形式主义颇受争议,但其试帖诗的文学色彩毕竟远超后者。正是试帖诗的存在使“科举求仕”与“文学娱情”在科第文化空间中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为僵化的唯八股取士制度注入了灵思与诗心。因此,对诸多蒙古文人而言,试帖诗绝不仅仅是科举求仕的“敲门砖”,而是他们大力钻研的文学体裁。如谦福在为官后继续保持着试帖诗的写作,《桐华竹实之轩试贴诗钞》收录其试帖诗多达99首。锡珮回忆云:“(谦福)岁辛酉溘逝,遗集裒然。先恭勤公笃友于谊,展卷辄泣,下召珮谕之曰:‘汝叔父一生精力毕萃于斯,胡可湮没?’”[6](锡珮跋文P.133)延清是晚清蒙古诗人中热衷试帖创作的名家,“其所著试律分韵编辑共得一千数百余首”[13](卷末胡俊章序P.57)。时人谓延清《锦官堂试贴》云:“其韵语所造,实乃刓精鉥虑、积累而成,自非率尔操觚者所能学步。”[13](支恒荣序P.30)虽是亲友之间的推誉,但从中亦可见其严谨的创作态度与付出的斑斑心血。从现存蒙古文士的诗文集看,试帖诗学影响着他们整个写作生涯,这正是科第文化空间培育出的思维惯性与专擅领域,同时也充分证实了传统文人的写作离不开其成长环境和具体的文化空间这一论断。
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过详细探讨,他指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汉民族是“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28](P.306),并进一步阐明各民族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28](P.309)。有清一代,汉语是清王朝的官方通用语言,作为传统文学的大宗,汉语诗文依然是清代各民族文人创作的重心,传统儒家诗教依然是官方各族文人的底色。(10)儒家思想对蒙古诗人文学创作影响甚巨,米彦青指出,“蒙古诗人以汉语言文字来表达其独特的民族心理和人生经历的时候,儒家诗歌理论早已经潜移默化指导着他们的诗歌创作了”。参见米彦青《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乾嘉诗坛》,载《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从这一意义上讲,清代蒙古族、满族等各民族文士的汉诗创作本身亦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典型的文学文本,而作为重要的文化媒介,科第在清代蒙古、满、汉等民族文人的文化启蒙与交流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为各民族文士提供了文学性的聚合平台。因此,在传统汉文化的统摄下,正是科举或许也只有科举,在清代民族共同体建构中营构出统一的文化空间,并为各民族文士的群聚切磋、同声相和注入了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