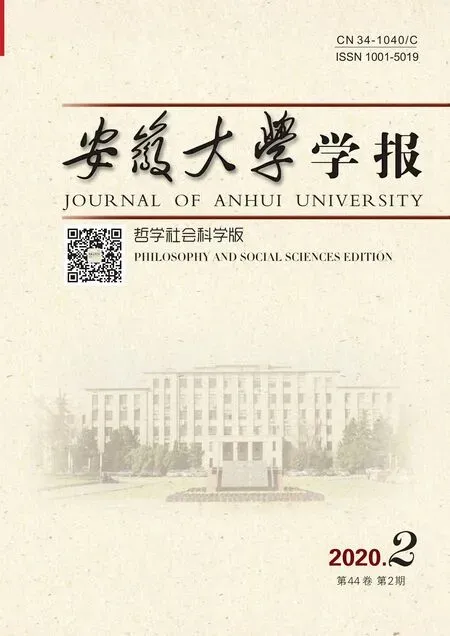方以智《药地炮庄》的诠释特色
张永义
方以智(1611—1671)编著的《药地炮庄》是庄学史上解释张力比较大的作品之一。这部书的核心观点是“托孤”说,意思是说庄子名义上接续老聃之学,暗地里曲传的却是尧孔之道,因此从思想谱系来讲,庄子实为孔门别传之孤。这一说法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庄子相差甚远。
最早提出此说的是觉浪道盛禅师(1592—1659),他也是方以智的得戒师。觉浪本人的著作叫《庄子提正》,在这部简短的作品中,他着重评点了《庄子》内七篇。方以智剃度之后,觉浪就把自己全评的《庄子》转交给这位弟子,并希望由他来完成全书的工作,这也成了方以智此后十年的一项重要任务。两位僧人前赴后继,孜孜不倦,力图证成道家的庄子原本属于儒家的嫡传。这件事情本身,放在晚明以来“三教会通”的大背景下考虑,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
在庄学史上,以儒解《庄》并非始于觉浪道盛和方以智师徒,从郭象、韩愈到苏东坡、王安石、林希逸等等都是如此,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解释传统。但像觉浪和方以智这样把庄子看成孔门真孤,却是前所未有的说法。因为,一旦把这种说法贯彻到底,千余年的儒学史都将面临被重新检讨的窘境。
相应地,觉浪和方以智要想证成自己的说法,也就不能停留在过去那种只言片语式的联想或附会,而是必须花费更多的力气从思想旨趣、精神归宿、言说方式等多角度进行全面的诠释。这大概也是《提正》和《药地炮庄》(下文简称“炮庄”)二书比前人的解《庄》作品呈现出较多的方法论自觉的原因所在。
晚近一二十年,由于庄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药地炮庄》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除了通史性著作之外,杨儒宾2004年发表《儒门别传》一文,较早讨论了《炮庄》中“托孤”说的思想史意义(1)该文收入邢益海编《冬炼三时传旧火——港台学人论方以智》,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稍后,周锋利和彭战果则从三教会通的角度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解释(2)周锋利:《方以智三教会通思想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彭战果:《无执与圆融——方以智三教会通观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邢益海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方以智庄学研究》,是到目前为止最全面最系统的研究此书的专著,里面也有专章讨论到方以智“托孤”说的含义及其与觉浪道盛的关系(3)邢益海:《方以智庄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所有这些,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相对来说,过往的研究大多聚焦在《炮庄》的学派归属及思想史意义上,对此书的方法论特色的讨论尚不充分。事实上,《炮庄》独特的解释方法,是理解“托孤”说的一个重要前提。此书在方法论上的得失,也会影响到对其学派归属和思想史意义的判定。下面我们就结合《庄子提正》(下文亦简称“提正”),从三个方面对《炮庄》一书的诠释特色进行探讨:一是“托孤”的含义,二是《炮庄》的解释技巧,三是“托孤”说在方法论上的得失。
一、“托孤”三义
从《提正》到《炮庄》,“托孤”一词至少包含三种含义:一是道盛、方以智师徒之间的付嘱,二是道盛本人的“自托孤”与“自正孤”,三是庄子托孤于老聃。
就解《庄》而言,第三种含义当然最重要。但是,如果这种意义上的“托孤”里面已经包含了“自正孤”、“自托孤”、师徒授受的成分在内,那么它就不再是纯粹的解《庄》,而是借《庄子》之酒浇自己的胸中垒块。这种做法,用陆象山的话说叫“六经注我”,用妙总尼的话说就叫“庄子注郭象”。因此,谈《炮庄》的“托孤”,就必须把这三种含义结合起来考察。
1.“托孤竹关”
道盛托付方以智解《庄》一事,后者在《炮庄小引》中有一段说明:
子嵩开卷一尺便放,何乃喑醷三十年而复沾沾此耶?忽遇《破蓝茎草》,托孤竹关,杞包栎菌,一枝横出,嚗然放杖,烧其鼎而炮之。重翻《三一斋稿》,会通《易余》,其为药症也犁然矣。(4)方以智:《药地炮庄》(修订版),张永义、邢益海校点,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第8页。下引该书仅标注书名和页码,间或随文夹注。
“子嵩开卷便放”典出《世说新语·文学》篇:“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喑醷”出《庄子·知北游》:“自本观之,生者喑醷物也。”“破蓝茎草”指觉浪道盛的《破蓝茎草颂》,“竹关”乃方以智闭关处,《三一斋稿》是方以智外祖吴应宾的遗著,《易余》是方以智自己解《易》之书。整段话合起来是说,庾子嵩读《庄》开卷便放,自己读《庄》三十年,为什么还要沾沾于此?是因为遇到了恩师觉浪道盛禅师,他把解《庄》的任务交给了自己,于是支鼎烹炮,以《庄》为素材,会通《三一斋稿》和《易余》,因而就有了《炮庄》这部书。
《炮庄》完成之后,方以智做的另外两件事再次证明该书与道盛有着特殊的关系。一是焚《炮庄》稿于道盛影前,二是致陈子升信中称“十年来为他人评《庄》”:
十年药地,支鼎重炮。吞吐古今,百杂粉碎。藐姑犹是别峰,龙珠聊以佐锻。今日喷雪轩中,举来供养,将谓撤翻篱笆,随场漫衍耶?(5)方以智:《冬灰录》,邢益海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 第151页。
十年来为他人评《庄》,乃合古今而炮之,赞谤并列,随人自触,安于所伤乎?业缘难避乎?竿木泥洹,亦何暇更作计较耶?因寄《炮庄》一部,别刻数种,请正。有高兴为批数语见示为望。(6)方以智:《寄乔生》,收于陈子升《中洲草堂遗集》卷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
两条材料都提到“十年”,说明《炮庄》从写作到成书前后一共花了十年时间。《炮庄》完稿于1663年,上推十年,正好是方以智投奔觉浪道盛之年(1653年)。焚稿于道盛像前,表明终于完成了老师的付嘱和愿望。称“十年来为他人评《庄》”,说明编著《炮庄》一书,一开始并非出于方以智自己的计划。这两条材料足以坐实所谓“托孤竹关”的含义。
这是“托孤”的第一种含义。
2.“自正孤”与“自托孤”
除了托付弟子评《庄》外,道盛本人在《庄子提正》中也称自己解《庄》的行为为“托孤”,这更加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道盛的说法是:
时予倚杖灵山,偶与“不二社”诸子谈及庄生之秘,曹子请为快提以晓未悟,故提此托孤以正其别传。即有谓予借庄子自为托孤与自为正孤,谓非庄子之本旨,予又何辞!(7)《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0,《明版嘉兴大藏经》第3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7年,第768页。
《庄子提正》篇幅不长(两万余字),除前序外,正文部分包括《正庄为尧孔真孤》《提内七篇》《提逍遥游》《提齐物论》《提养生主》《提人间世》《提德充符》《提大宗师》《提应帝王》九篇。上面的这段话出自《正庄为尧孔真孤》的末尾。
根据谢明阳教授的考证,《庄子提正》作于顺治五年(1648),文中提到的灵山指太平府当涂县无相寺,曹子指方以智的妹夫曹台岳(8)谢明阳:《觉浪道盛〈庄子提正〉写作背景考辨》,《清华学报》(台湾)新42卷第1期(2012年),第135~168页。。“不二社”是觉浪道盛在桐城浮山所结之社,以禅净不二为宗旨(9)方以智《远祖塔院饭田记》称:“浮山自先外祖三一老人兴复,朗、澹、清三公相续总持,一向洞口云横,草深一丈,剩有意生耆旧,平实接待。壬寅至今,忽忽周甲矣。宗一圆三,竟在此地指天树骨。莲池、博山,合一滴水,天界杖人尝举此为不二社。”《冬灰录》,第37页。,曹台岳大概也是社中成员。在向“不二社”诸子谈完“庄生之秘”后,道盛竟然声称如果有人认为他是借庄子而“自正孤”“自托孤”,不合乎庄子的本旨,他也乐于接受这种批评(“予又何辞”,也可理解为无言以对)。显然,道盛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读者,他的《提正》面里还包含着更深的一层意义。
那么,道盛所要“自正”“自托”的“孤”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弟子大时凌世韶给了我们如下的提示:
吾师浪杖人,惯用吹毛利剑,杀活古今,而横拈倒用,靡不神解……师云:“世界未有不坏,圣人未有不死,独此圣贤之经法与佛祖之宗旨,固不可一日昧灭。”乃知吾师所谓正孤,非直以正庄生所托尧孔之孤,实吾师借此以正自正之孤,用正天下万世佛祖、圣贤之真孤也。(10)《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0,《明版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76页。
大时这段话收于《庄子提正》的末尾,所以文中提到的“圣贤之经法”当然就是指尧舜到周孔的儒家道统(“尧孔”)。大时告诉我们,其师虽然字面上讲的是庄子属于“尧孔真孤”,但暗地里却包含着自己对圣贤经法的推崇。莫非觉浪也像他所快提的庄子一样,身在方外,却心系尧孔?
从大时提供的角度回看《提正》,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推测显然是过虑了。作为虔诚的佛教徒,道盛并没有脱掉袈裟、归宗儒门的打算,他想要表达的其实是,儒佛二家虽然设教各异,但根本之道却是相同的。他说:
虽然,今历数已久,有人能正其真孤,必欲还其宗于尧孔,仍从天下以老庄并称,如儒佛原不同宗而道有以妙叶,亦何不可以并称乎?此正吾平日所谓世人不知“道不同不相为谋”之语,是破人分门别户,实教人必须以道大同于天下,使天下之不同者皆相谋于大同之道,始不使异端之终为异端也。使异端之终为异端,此圣人不能以道大同于天下之过矣。使能同之,则天地日月、四时鬼神无不与之合也,又何更有不同者乎?(11)《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0,《明版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67页。
道盛认为,庄子虽是“尧孔真孤”,但归宗之后,我们仍然不妨以“老庄”并称。这正如儒佛关系一样,两家之道虽然妙合无间,但也不妨儒是儒、佛是佛。过去的学者都误会了圣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圣人说这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排异端,而是希望天下大同,把所有不同的流派都统合到大同之道中来,因此圣人的这句话必须这样理解:如果“道不同”,那么就会带来“不相为谋”的弊病。换句话说,在圣人眼中,只有设教方式的不同,并没有什么正统和异端的区分。
传统上,老庄和佛教都被当成害道的异端而饱受儒者的批评,道盛通过上面这种“横拈倒用”的杀活手段,不仅实现了庄子与儒家的契接,而且也顺带替自己身处的佛门洗却了异端的恶名。这大概就是道盛念念不忘的“自正孤”和“自托孤”的真实意思。他后来发起成立“双选社”(儒佛双选),可以看作是这种“正孤”想法的进一步落实。
3.“尧孔真孤”
把庄子归为“尧孔真孤”,是《提正》和《炮庄》的共同主题,也是道盛和方以智两人着力发挥和阐释的内容。《炮庄·总论中》篇曾把《提正》的要点概括为两段话,第一段侧重于说明“托孤”的含义:
死节易,立孤难。立孤者必先忘身避仇,使彼无隙肆害,乃能转徙深渺,托可倚之家,易其名,变其状,以扶植之成人,然后乃可复其宗而昌大其后。予读《庄子》,乃深知为儒宗别传。夫既为儒宗矣,何为而欲别传之乎?深痛战国名相功利之习,窃道术以杀夺,仁义裂于杨、墨,无为坠于田、彭,即有一二真儒,亦未深究性命之极,冥才识而复其初,遂使后世不复有穷神知化之事,而天下脊脊不能安性命之情,则所学皆滞迹耳。此滴血之正脉,孤而不存,庄生于是有托孤之惧矣。庄生孤哉!二千年知者固少,赏音不绝,未有谓其为孤,又孰能亲正其为真孤哉?(《药地炮庄》,第49页)
“死节易,立孤难”,借用的是赵氏孤儿之典。以譬庄儒,庄子就如赵家遗腹子赵武一样,成了儒门仅存的血脉。庄子之所以自愿选择“别传”的方式,是因为战国时期的儒者大多数都流于名相、功利之途,对天人性命之学已经不再关注。庄子出于深深的忧虑,只好改投到老子的门下,以期能够保留一点儒家圣贤的真精神。道盛认为,两千年来欣赏庄子的人不少,却从来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他是第一个说出“儒宗别传”的人。
第二段与第一段的内容有少量的重复,但主体部分是解释庄子何以成为孔门之“孤”:
庄周隐战国,辞楚相,愤功利而别路救之,以神化移人心之天者也。世儒拘胶,不能知天立宗。诸治方术者,离跂尊知,多得一察,以自为方,终身不返。乃慨然抚心曰:恶乎可?又恶可使若人终不知道德性天之宗乎?夫如是也,又何所借之以自明吾之所存,自行吾之所主乎?于是仍借羲皇、尧、舜、孔、颜,与老聃、许由、壶、列、杨、墨、惠施诸子,互相立论而神化之。其中有主有宾,有权有实。至于纵横杀活,隐显正奇,放肆诡诞,嘻笑怒骂,直指天真,曲示密意,其为移出人心之天,岂可以常情臆见领略之耶?内七篇已豁然矣,究不外于慎独、致中和,而与人物冥声臭,归大宗师于孔颜,归应帝王于尧舜也。世人不知,以为诋毁圣人,孰知称赞尧、舜、孔、颜,无有尚于庄生者乎?天下沉浊,不可庄语,为此无端崖以移之,使天下疑怪以自得之,庄真有大不得已者。庄且自言矣,执浅者,拘迹者,宜其未达也。偷心未死,吾亦不愿其袭达也。大道若辱,正言若反。《六经》,正告也。《庄子》,奇特也。惟统奇正者,乃能知之,乃善用之。或谓《庄子》别行于《六经》之外,余谓《庄》实辅《六经》而后行。使天下无《六经》,则庄子不作此书,作《六经》矣。噫,吾于是独惜庄子未见吾宗,又独奇庄子绝似吾宗。(《药地炮庄》,第49页)
在这段话中,道盛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儒家的精髓在于天人性命之学,但在战国时期,世儒拘胶,日陷于功利之途,儒家真精神有失传的危险,庄子于是乎惧,乃借别路而救正之。这种说法和上段话的意思基本相同。第二,《庄子》内七篇以孔颜为内圣(大宗师),以尧舜为外王(应帝王),落脚点都在《中庸》的“慎独”“致中和”之道。第三,庄书正言若反,有权有实,与《六经》不仅不背离,而且还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庄子》和《六经》的关系,正如佛家宗门和教门的关系一样。禅属于“教外别传”,那么,《庄》当然可以称作“儒宗别传”。
三层意思中,第一条讲庄子的立言动机,第二条是从内容上分析《庄》书与儒家经典的契合处,第三条讲庄子的立言方法。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三条其实也正是《炮庄》一书最常使用的诠释技巧。
以上便是“托孤”一词的三种意涵。撇开“师徒授受”不论,另外两种含义的相互交织,使得读者不得不经常穿越在古今、隐显和虚实之间,这是理解《提正》《炮庄》二书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二、《炮庄》的解释技巧
由于《炮庄》的立论与传统成说相差太远,所以诠释方法至关重要。方以智对此有非常明确的意识,他在《向子期与郭子玄书》中曾说:
《庄子》者,可参而不可诂者也。以诂行,则漆园之天蔽矣。庄子叹世之溺于功利而疚心其始,又不可与庄语,为此无端崖之词,巵之寓之,大小重之,无谓有谓,有谓无谓,使见之者疑愤不已,乃有旦暮遇之者。鹏之与鷽也,椿之与瓠也,豕零也,骷髅也,虫臂鼠肝也,会则直会,不烦更仆,岂特《天道》《天运》为正论,末后叙《六经》而悲一曲为本怀乎?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虽曲为之解,亦终身骈拇而不反者也。况以注名,胶胶然曰我庄子知己也,冤哉!冤哉!(《药地炮庄》,第74~75页)
方以智早年本以博考著称(12)代表性的作品有《通雅》《物理小识》等。,但在解《庄》时却坚持《庄子》“可参而不可诂”。他认为,用“诂”的方法解《庄》,根本无法进入庄子的精神世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庄》书以巵言和寓言为主,到处充斥着虚构的、边说边扫式的荒唐之言,如果不善会其言外之意,单凭词义的训释、事实的考订根本无法理解庄子的“谬悠之说”“无端崖之词”。他甚至说:“然则世之不善读《庄子》者,皆诂《庄子》者之过也。”( 《药地炮庄》,第78页)这足以解释训诂部分何以在《炮庄》中居于如此微不足道的地位。
“参”就不同了。“参”与“诂”最大的不同是,“参”建立在对文本内容的体会和觉悟之上,因此更方便追寻语言文字的背后意思。除此之外,参悟还有一个很大好处,那就是通过一些解释策略,可以很容易地在不同学派或思想传统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譬如“托孤”说中所涉及的庄孔关系,如果用训释的方法处理,《庄》书中对孔子的冷嘲热讽就成了难以否认的事实,但换个角度,它们则可以被看作是呵佛骂祖、正言若反的佳例。对《炮庄》而言,这方面的考虑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方以智对“参悟”的理解,可能部分来自《庄子》本身(13)《庄》书中,谈到得意忘言的文字很多,如“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但从《炮庄》全书的构成来讲,禅学特别是道盛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大别《发凡》这样介绍《炮庄》独特的编排形式:“训词,注之于下。诸家议论,汇之于后。别路拈提,列之于上。”( 《药地炮庄》,第9页)“训词”属于“训诂”部分,附于《庄子》正文之下,篇幅很少。“诸家议论”和“别路拈提”是全书的主体,其中,“诸家议论”平列各家,属于“炮制”;“别路拈提”则类似于禅宗的“参话头”,《庄子》本文及各家议论则相当于各种公案。“诸家议论”和“别路拈提”中,又从内容上随机指点庄子与儒家的共同之处,这接近于道盛经常提倡的“参同”说。
下面我们分别从“参同”“炮制”“拈提”三个方面举例说明《炮庄》的诠释方法。
1.参同
“参同”是指通过参究的方式,悟得诸家思想中的相同或近似之处。觉浪道盛曾有两篇题曰“参同”的文章(《参同说》《儒释参同说》),专门讨论儒佛宗异而道同的问题。他说:“儒者不肯参究,禅者不能遍参,便有儒释之分、浅深之异。使能参透此旨,则学佛自能知儒,通儒自能造佛。”(14)《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25,《明版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41页。“尧舜之十六字,谁不哝哝为千圣传心乎?亦惟佛法乃能深明其幽奥,而不至颟顸。”“人心即心之动机,其显见昭著故惟危,即俗谛也。道心即心之静机,其隐微幽密故惟微,即真谛也。”“是故圣学之功全在精一二字,佛教之功全在止观二字。观自精也,止自一也。”(15)《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26,《明版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44页。这些说法的着眼点都在两家思想的相同之处,譬如儒家的十六字心传,“人心”“道心”“精”“一”,可以很方便地转换成佛教的术语“俗谛”“真谛”“止”“观”。一旦觉悟到两家宗旨无别,那么学佛有助于知儒,通儒有助于成佛,正好可以相互补益。用道盛的话说,就是:“人既有身于天地间,则与天地人物相关,性命身世相接,分之似有彼此之殊,合之实无自他之别。佛祖洞视,则有同体之心。圣贤彻观,则有胞乳之义。帝王总揽,则有统御之宗。故凡厥有生,须当参此三法,是世间、出世间皆不可须臾离也。”(16)《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25,《明版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39页。
庄儒关系更是如此。依照“托孤”说,庄子本属于尧孔的嫡传,他的思想相对于佛教来说当然更接近于儒家,只不过放肆诡诞的文风遮蔽了其真实意图而已。借助于参悟,觉浪在《庄子提正》中随处指点庄儒的相同之处。例如:“夫无己、无功、无名,其果谁乎?尧让天下与许由,庶几似之。”(17)《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0,《明版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70页。这是《提逍遥游》中的一句话,传统上,这则“尧许相让”的故事被解释为贬尧抬许,但道盛并不这样看,他认为,尧本来就是国君,却愿意舍弃君位,正是无己、无功、无名的表现。又如:“养生以何为主?即缘督以为经,率性之谓道也。”“此自善其刀十九年如新发于硎者,是君子之能慎独于莫见莫显之中也。”(18)《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0,《明版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71页。这是《提养生主》中的两句话,善刀养生成了《中庸》“率性”“慎独”的例证。又如:“仲尼曰:‘无所逃于天地间,是为大戒。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恶死?’此决断为臣子之心,与事心之不逾矩处,如斩钉截铁,真孔子万古不易之正论也。”(19)《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0,《明版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72页。这是《提人间世》的一段话,《庄子》本文借孔颜对话说明人间世之艰险和命运之无奈,道盛悟出的却是孔子之忠孝节义及从心所欲不逾矩。再如:“不读《中庸》乎,首提天命之性,即‘未始出吾宗’也。率性之谓道,即‘神动而天随’也。至于修率工夫而莫显莫见,即‘渊默龙见、机发于踵’也。故君子必慎其独以致中和,正‘虚而委蛇,无不藏无不应’也。所谓‘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其上天之载,无声无臭’,非浑沌而何?”(20)《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0,《明版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75页。这是《提应帝王》的一段话,壶子之四门示相经过道盛的参究,均成了《中庸》的注脚。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道盛用来会通庄儒的经典主要是《中庸》和《易传》,这与“托孤”说的基本主张有关。依道盛的说法,战国时期的儒者要么斤斤计较于名相,要么热衷于功利,反而最根本的天道性命之学却无人问津,这是庄子忧危托孤的主要原因。而在儒家经典中,最集中、最系统表达天人之学的正是《易》《庸》二书,庄子接续和发扬的也只能是这两部书:“夫论大易之精微,天人之妙密,性命之中和,位育之自然,孰有过于庄生者乎?”(21)《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0,《明版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69页。换句话说,参究庄儒之同,其实也就是在《庄子》和《易》《庸》之间找到思想承继关系。
与觉浪的《提正》相比,方以智的《炮庄》采取的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思路(22)方以智所受“参同”说的影响,可以参考觉浪《破蓝茎草颂》的下面这段话:“予今年倚杖天界,无可智公从生死危难中来皈命于予,受大法戒。乃掩关高座,深求少林服毒得髓之宗,披吾《参同》《灯热》之旨。喜其能隐忍坚利,真足大吾好山之脉。”(《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0,《明版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662页),只不过篇幅和范围要扩大很多。引证的材料有些出于前人,有些则是方以智本人的看法。我们也摘录数段以资说明:
(1)《内篇》凡七,而统于《游》。愚者曰:游即息也,息即无息也。太极游于六十四,乾游于六龙,《庄子》之“御六气”正抄此耳。姑以表法言之,以一游六者也。《齐》《主》《世》如内三爻,《符》《宗》《应》如外三爻,各具三谛。《逍遥》如“见群龙无首”之用。六龙首尾,蟠于潜、亢,而见、飞于法界,惕、跃为几乎!六皆法界,则六皆蟠、皆几也。姑以寓数约几言之,自两仪加倍至六层,为六十四,而举太极,则七也。乾坤用爻,亦七也。七者一也,正表六爻设用而转为体,太极至体而转为用也。本无体用者,急口明之耳。曰“六月息”,曰“御六气”,岂无故乎?用九藏于用六也,参两之会也。再两之为三四之会。故举半则示六,而言七则示周,曾有会来复周行之故者耶?寓数约几,惟在奇偶方圆,即冒费隐。对待者,二也。绝待者,一也。可见不可见,待与无待,皆反对也,皆贯通也。一不可言,言则是二。一在二中,用二即一。南北也,鲲鹏也,有无也,犹之坎离也,体用也,生死也。善用贯有无,贯即冥矣。不堕不离,寓象寓数,绝非人力思虑之所及也,是谁信得及耶?善寓莫如《易》,而《庄》更寓言之以化执,至此更不可执。(《药地炮庄》,第100页)
这段话摘自《炮庄》卷一的开头,是对《庄子》内七篇结构与《周易》关系的分析。在方以智看来,七篇的顺序绝非随意安排的产物,而是比照着《乾》卦组织的。具体说来就是,《逍遥游》相当于《乾》卦的“用九”,《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相当于《乾》卦的内卦,《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相当于《乾》卦的外卦。“用九”没有具体的爻位,但“用九”就潜藏在其他六爻之中,正如太极和六十四卦的关系一样,太极虽然是体,但却无形,只能潜藏于六十四卦之中。《逍遥游》和其他六篇就是这样的一种体用关系,此即所谓“内篇凡七,而统于《游》”的意思。方以智认为,能够支持其说的除了《逍遥游》那些特殊的数字如“去以六月息”、“御六气之变”之外,还有“北冥”“南冥”“鲲鹏”等名字,《周易》借卦爻象数寄寓天地万物之理,《庄子》则把南北坎离这些变化之道通过寓言的方式呈现出来,两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2)薛更生曰:“冥非海。‘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易》之‘冥豫’‘冥升’,《太玄》拈出‘冥’字,知之乎?庄生亦怕人错认,急忙指注一‘天’字来。夫既已化矣,又何以徙?分明印出后天坎离,岂非剖心沥胆之言?”(《药地炮庄》,第103页)
这段话出自方以智的知交薛正平,可以看作是对上条的一个补充。正平的意思是说,《逍遥游》的“北冥”“南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北海、南海,而是指天道的无形无象;鹏之由北而南也非随意而为,而是象征着文王易中的“离南坎北”。正平提供的佐证材料都是出自《周易》和《中庸》。
(3)谭云:“环中、寓庸,此老巧滑。恐人觑破三昧从子思脱出,遂将《中庸》劈作两片拈提。”(《药地炮庄》,第134页)
“通一不用而寓诸庸”,环中四破,无不应矣。析《中庸》为两层而暗提之,举《春秋》之双名而显怀之,一二毕矣。(《药地炮庄》,第88页)
两段话分别出自《齐物论》注和《齐物论总炮》。注中的“谭云”所指不详,可能是指谭元春。《总炮》则是方以智自己对《齐物论》意旨的概括。两段话都认为《齐物论》的“环中”“寓庸”来自《中庸》,不同的只是方以智的文字更加晦涩而已。所谓“通一不用而寓诸庸”,是对《齐物论》这句话的约写:“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庄子的本义是说道通为一,因此体道的人不走对待之途,而是寄寓在万物之各有其用之中,但方以智读到的却是易道的一在二中、体在用中。“环中”同样出自《齐物论》:“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方以智则用它指代不落四边之“中五”或太极。依据《易》理,“环中”是体是一,那么“寓庸”就是用就是多,“环中四破”就是指体用之一在二中、不一不二的关系。由于“环中”“寓庸”两个语词中分别包含着“中”“庸”二字,方以智认为这绝非偶然之事,它是庄子暗中拆解“中庸”的结果,也是庄子“曲传”尧孔之道的一种明显表现。
(4)支公曰:“正当得两,入三便乱。庄子弄出三个来,你道凿破多少人?”庄子叫曰:“非三不显,岂是我凿?《中庸》开口,早如此矣。”子思曰:“非是我凿,一部《易经》,原自如此。”伏羲曰:“非是我凿,天地之间,本自如此。”(《药地炮庄》,第239页)
这段话出自《应帝王》注,是对“混沌”故事的发挥。支公即支道林。据《世说新语·文学篇》,支道林讲三乘义,条理清晰,听者皆可明白。一旦让听者自相讨论,二乘尚可,一到三乘就乱了。对话中先是借支公之口,追问庄子虚构南北中央三帝,如何免于混乱?庄子回答说,三分之法非我所创,《中庸》开头言性、道、教已是如此。子思则说,《易经》“太极两仪”早已如此。伏羲结之曰,天道本身如此。整段话的风格虽然是诙谐的,但传达的意思却很清楚,那就是《庄子》与《中庸》《周易》一脉相承。
类似的例子在《炮庄》中还有很多,如“素王之孙,家悬一幅《天渊图》,庄生窃而装潢之”、“在《大畜》之《泰》曰何天之衢,今乃培气,背负青天,其取此而放笔乎”、“《人间世》发挥,盖本《易》也”、“斋戒本《易传》来”等等( 《药地炮庄》,第103页、107页、163页、162页),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总之,由上面的这些例子,我们大体上已经可以明白“参同”这种解释方式的特点。
2.炮制
如果说“参同”的目的是发现两家之同,“炮制”则建立在各种观点的不同之上。“参同”的对象是庄子和尧孔,“炮制”的对象则是历代各种《庄》注以及其他与《庄子》相关的言论。
《炮庄》中,这部分的内容叫“诸家议论”。和通常的集解或集释类著作不同,方以智并不打算提供一种全面的文献汇编。他曾明确地说:“自庄生后数千年,评者众矣。或诋娸,或击节,抑扬墫墫,疑始颉滑。火与日吾屯也,阴与夜吾代也,此固剥烂弥缝、旁通正变之冷灶耶?浮山药地,因大集古今之削漆者,芩桂硫,同置药笼。彼且赢粮揭竿,与之洒濯。彼且踉位闻跫,与之謦欬。彼且屠龙削锯,与之作目。彼且犗饵爨冰,与之伏火。彼且甘寝秉羽,与之消闲。随人自尝而吞吐之,愚者不复一喙。果有齑粉唐许藐姑者,不容声矣。”《发凡》亦云:“正论奇论,反语隐语,两末两造,兼通而中道自显矣。”( 《药地炮庄》,第8页、9页)平列各种不同的或者相互冲突的言论,目的是使阅读者由此产生疑愤,并从疑愤中获得对“中道”的觉悟,这既是“炮”之所以为“炮”的含义,也是把《庄子》引归儒家的一个重要途径。
“炮制”一词取自医学,医师制药时常把不同的药材混合一起加工,以便达到降低毒性、增强疗效的目的。对于《炮庄》一书来说,“诸家议论”就相当于种种不同的药材,而各种观点之间的分歧甚至对立,则相当于药材各异的药性及其相生相克。不过,作为一种解释方法来说,“炮制”还包含着禅学的影响。禅是一门觉悟之学,而“悟”建立在怀疑之上。方以智和觉浪都曾引用过古德“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的话,来说明怀疑对于觉悟的重要性(23)参见道盛《青山小述》,《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2,《明版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782页;方以智《冬灰录》,第43页。。怀疑总是与歧解相伴随,作为“炮制”对象的“诸家议论”,正好为阅读者提供了大发疑情的机会。下面几段话都是出自《炮庄》的序跋作者,它们无不强调“炮制”对于怀疑和觉悟的意义:
药地大师之炮《庄》也,列诸病症,而使医工自饮上池,视垣外焉。(《药地炮庄》,第1页)
《炮庄》制药,列诸症变,使人参省而自适其当焉。(《药地炮庄》,第1页)
即因此同异激扬之几,以鼓其疑熏向上之兴,不亦善乎?水穷山尽,自然冰消,不在按牛吃草也。(《药地炮庄》,第10页)
药地吾师,集千年之赞者毁者,听人滑疑何居?正为直告之不信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彼自得之而用其中矣。(《药地炮庄》,第14页)
几段话中,“列诸病症”、“列诸症变”、“同异激扬”、“集千年之赞者毁者”就是这里所说的“炮制”,“自饮”“自适”“自得”“疑熏向上”则是通过“炮制”而获得的自觉自悟。
由于觉悟属于读者个人的体验,《炮庄》“诸家议论”部分并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姑举二例说明“炮制”方法如下:
(1)薛曰:“成心者,现成天地之心,一毫不待加添也。历尽淆讹,一切仍旧。”陶云:“法尘之起灭,等声尘之万殊,究取从来,乐出虚、蒸成菌耳。使之以莫为,宰之者无朕,生灭纷然,寂灭宛尔,此所谓天均乎!受成形则物我立,师成心则是非起。所以然者,不识真君也。真心者,未成乎心者也。妄心者,成心也。”正曰:“两说皆因现量、比量而竖此义也,且问此说现量者成心乎?未成心乎?不见《大智论》曰‘惟善用心即得’,圣学慎独于未发,而明征于中节而已。庄生口吻,原是设难滑疑,使人自奈何之。”(《药地炮庄》,第127页)
这段话出自《炮庄》卷二,针对《齐物论》的“成心”一词所发。文中罗列了三个人的观点:一是薛正平,认为成心即永恒的“天地之心”,相当于人的本心或本性。二是陶望龄,认为成心是人成形之后,处于物我对待中的虚妄之心。三可能是指吴应宾,认为前两说都是从量论立说,如果进一步追问,定“成心”为真、妄之心的这种做法本身是不是也属于“成心”,前两说就会陷入背反之中。“惟善用心即得”,意思是真妄无法截然区分,关键在于用心所在。末后则归结到《中庸》未发、已未问题,慎独于未发而明征于已发大概是说体用不可割裂。三种观点既有对立,又有转进,显然属于典型的“炮制”例子。这段话中,方以智本人并未出场,合乎《炮庄小引》中“随人自尝而吞吐之,愚者不复一喙”的说法。但最后一种观点既出自其外公,又与其一贯主张的“两端用中”相同,所以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他个人的立场。
(2)钱绪山曰:“中而离乎四海,则天地万物失其体矣。或假借圣人之似,而逐外者遗内。或穷索圣人之微,而养内者遗外。”(《药地炮庄》,第229页)
罗念庵曰:“无乐乎专内也,求豫于外则以此先之。故敛摄可以言静,而不可谓为寂然之体;喜怒哀乐可以言时,而不可谓无未发之中。何也?心无时,亦无体,执见而后有可指也。尼山告颜、冉诸子,皆指其时与事示之,未尝处处说寂,未尝避讳涉于事事物物与在外也。”(《药地炮庄》,第229页)
杖曰:“问治天下,呵为鄙人,不太反常耶?反者道之动,此正庄子之不经,而剔出《六经》之大本乎!”(《药地炮庄》,第230页)
这三段话摘自《炮庄》卷三,是对《应帝王》下面这段话的“炮制”: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汝又何为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炮庄》的原文一共六段,这里只摘录了其中的三段。三段话中,钱绪山之语约自《阳明先生年谱序》,罗念庵之语约自《困辨录后序》,都和《庄子》无关。之所以作为“炮制”的材料,是因为绪山和念庵都认为治世治身不应该内外割裂,与《庄子》文本的意思正好相反。最后一段是道盛之说,他也承认无名人的话极为“反常”,只好借助“反者道之动”予以疏通。这几条材料再次提醒我们,不能把《炮庄》的“炮制”理解为普通意义的注《庄》,“炮制”不仅仅是“诸家议论”之间的互相“同异激扬”,而且还有不少对《庄子》本身的批评和改造。这大概就是文德翼所称“《庄》之药,师之炮,同一发毒作用耳”(24)《药地炮庄》,第4页。的意思。
3.拈提
“诸家议论”之外,《炮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别路拈提”,字数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所谓“拈提”,其实就是借用禅宗的公案、机缘或者禅家的风格、术语提点《庄》书,使人获得一种暗示或理解。这种做法的最大特点是不说破,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
拈提也是一种诠释,但与论证无关。其解释效果与读者的悟性、机缘及知识储备有关。同一段话,能够领悟的人可以相悦以解、会心微笑,领悟不及的人则茫然不知所云。
下面以《逍遥游》篇为例,略举数则以见一斑:
(1)一僧问赵州:“狗子有佛性也无?”曰:“有。”一僧又问,曰:“无。”向在浮山,有客语狗子佛性有无话,一日喜《庄子》藐姑射,谓是不落有无,时正犬吠,愚曰:“狗子吞却藐姑射久矣。”(《药地炮庄》,第102页)
这段话是对“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句的拈提。所用赵州和尚公案,参见《宏智禅师广录》卷二:“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有。’僧云:‘既有,为什么却撞入这个皮袋?’州云:‘为他知而故犯。’又有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僧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狗子为什么却无?’州云:‘为伊有业识在。’”(25)集成等编:《宏智禅师广录》卷2,《大正藏》第48册2001号经第20页。赵州称狗子之佛性既有且无,可能是要破除僧人的有无之见,方以智以此暗示也应该同样对待《庄子》的“藐姑射”之山及其神人。
(2)恕中举鲲鹏云:“若道有分别,本出一体。若道无分别,又是两形。毕竟如何评论?”击拂子云:“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药地炮庄》,第103页)
这段话直接借用恕中无愠禅师的话,来破除鲲鹏同异的执着。恕中是明初禅僧,其《语录》卷一云:“鱼以水为命,鸟以树为家。伐却树,鸟获栖迟。竭却水,鱼全性命。且道既伐却树、竭却水,因什么鸟反获栖迟、鱼反全性命?若向这里明得,许你有个入处。若向这里明不得,也许你有个入处。明得明不得则且置。只如庄周道‘北冥有鱼,其名曰鲲。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正与么时,唤作鹏又是鲲,唤作鲲又是鹏,且鲲之与鹏还有分别也无?若谓有分别,本出一体;若谓无分别,又化作两形,毕竟作么生评论?击拂子: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26)《恕中无愠禅师语录》卷1,《卍续藏》第71册1416号经第405页。末句“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又是借用船子德诚启悟夹山之语。
(3)一人传虚,众人传实。说梦固有法耶?圆梦预寻千证耶?过得棘林,方算好手。证龟成鳖,特借三人耶?《鹧鸪天》三起,乃畅快耳。(《药地炮庄》,第109页)
这段话对应于“汤之问棘也”一节。在《逍遥游》中,该节是第三次讲鲲鹏变化。所以,“拈提”中“众人传实”“三人”“三起”均与之照应。其中,“过得棘林,方算好手”,出自云门文偃禅师:“上堂:‘平地上死人无数,过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时有僧出,曰:‘与么,则堂中第一座有长处也。’师云:‘苏噜苏噜。’”(27)普济:《五灯会元》,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31页。“证龟成鳖”见《五灯会元》卷十五“益州青城香林院澄远禅师”:“问:如何是室内一碗灯?师曰:三人证龟成鳖。”(28)普济:《五灯会元》,第938页。
(4)僧问沙门眼,长沙岑曰:“长长出不得。”僧曰:“未审出个什么不得?”岑曰:“昼见日,夜见星。”曰:“学人不会。”岑曰:“妙高山色青又青。”愚曰:“土旷人稀,相逢者少。”(《药地炮庄》,第116页)
此段对应“肩吾问于连叔”一节。方以智所下断语“土旷人稀,相逢者少”,表面上是针对“沙门眼”公案,但隐指的却是肩吾所谓“大而无当,往而不反,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
由于“拈提”本身无法获得确解,这里就不再继续往下罗列了。对《炮庄》的这种做法,方以智同时代的人已经有过疑问和批评,竺庵大成委婉地说:“庄子之言多出杜撰,杖人、药地大惊小怪,引许多宗门中语去发明他,那人且不识庄子语,又如何明得宗门中语?”(29)大成:《读炮庄题辞》(《药地炮庄》第6页)。大成此语是为了说明疑方便可以助发真实义,并非对方以智的正面批评。钱澄之在《通雅序》中则称:“今道人既出世矣,然犹不肯废书,独其所著书多禅语,而会通以《庄》《易》之旨,学者骤读之,多不可解。”(30)钱澄之:《田间文集》,彭君华校点,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227页。这些说法多少可以解释《炮庄》后世流传不广的原因。另外,从上列数条来看,“拈提”似乎也并未有效地支撑起作为全书核心的“托孤”说。
三、《炮庄》在方法论上的得失
以上对《炮庄》的主要内容和诠释方法进行了粗浅的介绍,下面尝试分析其方法论上的得失。
首先,无论是从诠释方法来说,还是从诠释内容来讲,《药地炮庄》都确实提供了新的内容,丰富了道家解释史。
把庄子归宗尧孔虽然并非始于方以智师弟二人,但“托孤”说应该是此类说法中最极端的主张。如果儒家的真精神竟然主要保留在《庄子》书中,那么庄子之后千有余年的儒学史都得接受重新检讨和评介。
把庄子纳入孔门,“老庄道家”这种思想史上的常识也得重新考量。《天下》篇何以老、庄分论,内七篇何以孔颜频频现身,都可以借助或正或反、或权或实的解释技巧,给出立场各异的说法。
到目前为止,庄子与儒家的关系仍然是未定之论。《炮庄》虽然不足以证成“尧孔真孤”说,但也不全是捕风捉影,所以它仍然可以作为一家之言而存在。
就诠释方法而言,“拈提”免不了故弄玄虚之嫌,但强调“悟”对于理解《庄》书的重要性,则是极具价值的洞见。这一点主要与《庄》书性质有关。《寓言》《天下》二篇反复强调的“三言”,是理解庄子思想的前提。隐喻、暗示、反语、吊诡、边说边扫等等,都给人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解释余地,阅读者、诠释者可以很容易地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置入庄子的世界中,实现古今对话。
庄子本人似乎也并不反对这样做,所以才会有《齐物论》中“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的说法。《药地炮庄》无疑正是借参悟的方法尝试与庄相“遇”的作品。
其次,《炮庄》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解《庄》作品。方以智接到《炮庄》任务后,之所以愿意花大力从事此项工作,有一个重要考虑,那就是借此书对治当时嗜奇、好庸的两种学风(即晚明以来所谓的俗儒狂禅)。《炮庄发凡》所说的“尽古今是病,尽古今是药,非漫说而已也。医不明运气、经脉、变症、药性之故,争挂单方招牌,将谁欺乎?婴杵血诚,不容轻白。既已尝毒,愿补《图经》”( 《药地炮庄》,第10页),足以表明,方氏此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庄子》注疏,而是对《庄子》义理的引申和发挥。换句话说,作为诠释者,方以智把自己时代的问题代入了对《庄子》的解释之中。这一点同样可以解释,书中何以经常隐晦地表露出亡国遗恨。譬如,好友张自烈在序中称方氏“较之本穴纪运,十空著经,抑又深隐矣”(31)张自烈:《阅炮庄与滕公剡语》(《药地炮庄》第2页)。本穴纪运、十空著经,指郑思肖不忘故国事。,就是明显的例子。《四库提要》称是书:“大旨诠以佛理,借滉洋恣肆之谈,以自摅其意。盖有托而言,非《庄子》当如是解,亦非以智所见真谓《庄子》当如是解也。”(3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7《子部五十七·道家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56页。姑且不论方以智是否真的不认为“《庄子》当如是解”,就“有托而言”来说,四库馆臣无疑是对的。我们理解此书及其中的“托孤”说,显然必须在充分考虑道盛和方以智师徒背后所“托”之意的前提下,方可得到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