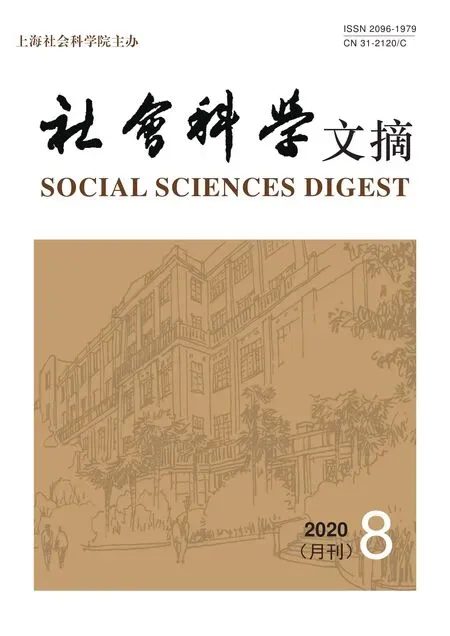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效果:区域差异及制度成因
文/赵婷 陈钊
引言
国际上对于产业政策的存废一直存在争论,但实践中产业政策却在各国的工业化阶段被广泛采用。即使是在早已成为最发达国家的美国,制造业仍然因其在就业、创新、经济带动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而成为产业政策扶持的重点。至于中国大陆,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层面,产业政策始终都是政府积极作为的重要抓手。
虽然中国的产业政策很早就被学者所关注,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发展差异明显的大国,产业政策实施中表现出来的区域差异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吴意云和朱希伟(2015)、张莉等(2017)利用两个五年规划的信息较早地发现,地方与中央的产业政策在越来越为接近。也就是说,不同地区在产业发展的选择上,很可能并没有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的政策。吴意云和朱希伟(2015)的研究也发现,地方产业政策的这种区域特征导致了中国的工业发展过早进入了再分散的阶段。赵婷和陈钊(2019)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地方产业政策向中央趋同的确在近几年来才表现得较为明显,而且,平均来看中西部地区在产业政策的选择上往往违背自身的比较优势。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区间要素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大国,在地区层面背离比较优势而实施产业政策的做法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首先,虽然产业政策的支持者并没能对产业政策该如何实施达成共识(Lin and Chang,2009),但多主张产业政策应该遵循比较优势(林毅夫等,1994、1999;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潘士远和金戈,2008)或视某些条件来确定应遵循还是违背潜在比较优势(Rodriguez-Clare,2007),仅少数主张产业政策应违背潜在比较优势(洪银兴,1997;郭克莎,2003)。其次,产业政策应当违背比较优势的理论依据来自战略性贸易理论,但这一理论却是站在一国的角度看待国与国之间的分工,这与站在一国的角度看待国内地区间的分工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应该借助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在国际上尚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的产业也不应当由国内更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来率先发展。基于策略性分工的理论研究告诉我们,在一国内部进行类似于国与国之间的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策略性分工会造成效率的损失(陆铭等,2004;2007)。
那么,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时遵循或违背比较优势的做法,对于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最终有什么影响呢?在中国内部,地区间能否进行类似于国家间的赶超竞争,使落后产业借助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扶持而获得超越式的发展呢?然而,现有的研究都没能对上述问题提供直接的实证证据。
现有的文献或者从一般意义上指出了专业化分工(Smith,1776;Ricardo,1817;Yang and Shi,1992;Yang and Ng,1993;Ng and Yang,1997)与集聚经济(Marshall,1890;Krugman,1991)的好处,或者从重复建设与地方保护(严冀和陆铭,2003;周黎安,2004)、工业分散或集聚经济的损失(吴意云和朱希伟,2015)说明了中国各地区专业分工不足可能造成的效率损失,或者从竞争的角度研究了产业政策成功的条件(Aghion et al.,2015)。这些研究虽然对回答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有所借鉴,但都没有从遵循或违背比较优势的角度直接对产业政策的效果进行检验。
以下的研究则更接近本文的工作。林毅夫(2002)利用跨国数据研究发现,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实现人均收入的收敛。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利用中国的数据也发现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李力行和申广军(2015)发现如果开发区设立的目标产业符合当地的潜在比较优势,就能显著促进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陈钊和熊瑞祥(2015)发现如果出口加工区设定的目标行业符合当地的潜在比较优势,则更有助于促进该行业在当地的出口。这些实证研究都突出了产业政策或发展战略是否遵循比较优势这一视角,它们所关注的政策影响涉及人均收入的收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出口促进,但这些并不是判断产业政策是否培育出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直接依据。根据战略性贸易理论,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如果能够成功,必须最终能够培育出所扶持产业的竞争力,或让这些产业最终具备比较优势。本文则试图直接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具体来说,本文将检验受地方产业政策扶持的产业是否更可能培育出比较优势,并且,这种可能性是否在产业政策遵循行业的潜在比较优势时会更大。我们会同时用行业补贴与是否属于地方重点产业两种指标来度量产业政策,前者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在行业-地区层面加总而成,后者根据地方政府五年规划的政策本文加以度量(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吴意云和朱希伟,2015;张莉等,2017)。显性比较优势(RCA)的度量来自Balassa (1965),潜在比较优势的度量本论文借鉴Chen et al.(2017)使用Hidalgo et al.(2007)构建的density指标。对产业政策不论采用哪一种度量,我们都发现,只有遵循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才会使所扶持的产业有更快的发展或更可能培育出显性比较优势。我们还发现这一规律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上述规律仅出现在东部地区,在中西部地区却并不存在。进一步的证据则表明,产业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背后有其制度上的成因,东部地区有更高的市场化程度和政府效率,这些制度条件是比较优势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
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从是否遵循潜在比较优势的角度为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来自一国内部的经验证据。特别地,我们考察了遵循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是否更可能让一个产业培育出显性比较优势,这恰恰也是产业政策的主要目的,因而也为政府对产业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科学的指引。其次,本研究借鉴Chen et al.(2017)使用Hidalgo et al.(2007)提出的行业关联度(density)指标来度量潜在比较优势,也发展了产品工业空间这支文献(Boschma and Capone,2016;Boschma and Iammarino,2009;Neffke et al.,2011;Boschma et al.,2013),表明比较优势的演变存在路径依赖,遵循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更有助于培育起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最后,本文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比较优势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发现。Nunn(2007)的研究发现,制度在比较优势的形成中起着越来越为重要的作用,而本文的研究则告诉我们,如果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那么比较优势很可能是难以发挥作用的。
基本发现
本论文首先检验了数据覆盖范围的“十五”时期地方选的重点产业是否符合本辖区的比较优势,以及经过“十五”时期的发展潜在比较优势和显性比较优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鉴于地方重点产业中一部分是来自中央的重点产业,另一部分重点产业与中央重点产业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将地方的重点产业区分为“地方发展—中央发展”和“地方发展—中央没发展”来看各自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区分了东部、中部、西部来看各地区的变化。我们发现在各地区潜在比较优势和显性比较优势都呈现相一致的变动。东部地区发展的“地方发展—中央发展”的重点产业在“十五”期初在东部地区既不具备潜在比较优势也不具备显性比较优势,但是,经过“十五”时期的扶持在东部地区则动态培育起了潜在比较优势和显性比较优势,而东部地区发展的“地方发展—中央没发展”的重点产业在“十五”的期初和期末始终不具备潜在比较优势和显性比较优势。在中西部地区始终具备潜在比较优势的“地方发展—中央没发展”的重点产业,也始终具备显性比较优势,而始终不具备潜在比较优势的“地方发展—中央发展”的重点产业,在中部始终没有形成显性比较优势,在西部的显性比较优势也呈减弱的趋势。那么,产业政策的效果是不是取决于潜在比较优势?是不是遵循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更容易形成显性比较优势?这种效果是否在地区间存在差异?这些都还需要严格的计量检验。
本论文接下来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严格的计量检验,我们将检验以下两种情形:其一,当产业政策扶持的是具备潜在比较优势的行业时,是不是更可能使原来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行业,在受到产业政策扶持之后,更可能具备显性比较优势;其二,当产业政策扶持的是具备潜在比较优势的行业时,是不是更可能使原来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行业,在产业政策实施之后,其区位商变大。前者考虑的是显性比较优势的逆转,后者则考虑显性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
本论文首先使用补贴度量产业政策研究政策的短期效果,发现从全国平均来看,产业政策在扶持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行业时,更可能使行业向着增进显性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并培育出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进一步分区域检验发现这个规律在区域间存在差异,这个规律仅出现在东部样本中,在中西部样本中没有,说明在中西部地区潜在比较优势并没有在产业政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虽然,本论文核心关注的是产业政策的效果是不是取决于扶持的产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同时,本论文在研究产业政策的效果时,还发现中西部地区的潜在比较优势系数大于东部地区,虽然,这个差异只表现出略微的显著性,这意味着在中西部地区或制度环境较弱的地区产业政策的效果更加依赖于是否遵循本地区的潜在比较优势。
然后,本论文使用政策文本度量产业政策考察更为长期的效果。在全样本中我们发现这个效果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借助本文分析进行产业政策的度量存在较大的测量误差,并且产业政策的度量在省份层面变异较小,也可能是因为平均来看,政策的效果的确不取决于重点行业是否具备潜在比较优势。我们无法在文本分析中减少测量误差,但可以通过分样本回归进一步考察政策是否存在因地区而异的异质性效果。而在分样本的回归中,和我们在研究政策的短期效果的发现相一致,我们发现这个效果在东部有,在中西部没有。
上述发现都意味着,在东部地区,遵循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更可能让原本不具备显性比较优势的行业在产业政策的扶持下培育出显性比较优势。但是,这样的规律在中西部地区并不存在。这就很自然地引发出一个新问题:为什么比较优势在产业政策中的作用存在区域差异?我们预判,这与地区间制度环境的不同有关。下文试图从市场化程度和政府效率这两个角度对此加以解释。
产业政策效果区域差异的制度成因
产业政策的成功实施既需要制定出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产业政策,也需要产业政策得到有效的实施,这就需要建立良好的制度来保证政府和企业有效地实施产业政策(Becker et al.,2013)。良好的制度环境一方面能较好的规范政府行为,避免政府的越位和缺位,避免寻租和腐败(Rodrik,1995;2004;Stiglitz and Greenwald,2014),另一方面能激发企业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的创新(吴敬琏,1999;2002)。所以,良好的制度环境一方面能保证政府有效地执行产业政策,另一方面能保证企业将各种产业扶持有效地用于生产领域。余明桂等(2010)发现企业的寻租行为往往发生在制度环境弱的地方,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方,越是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越能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这些财政补贴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也越低。吴一平和李鲁(2017)发现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往往难以有效地约束官员的行为,导致官员不愿或不能识别出有效率的企业,使得开发区政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能力。韩永辉等(2017)发现中国地方产业政策在推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高度依赖地方的市场化程度和政府效率。所以,我们预判产业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背后是制度环境的差异,是产业政策是否得到了有效实施。我们用市场化程度度量各地区的制度环境(樊纲等,2003),我们使用了合成指标市场化指数(樊纲等,2010)。这个指标即包含有企业效率也包含有政府效率,为了进一步区分开企业效率和政府效率,我们使用了分项指标非国有经济占比和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这些指标能更好的反映企业的效率,看企业是否将产业扶持用于了生产领域,是否有效的实施了产业政策,同时我们也使用了直接度量政府效率的指标,既有合成指标政府效率(唐天伟,2009),也有分项指标非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从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重,来看政府是否有效地执行了产业政策。
既然我们预判产业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背后所反映的是地区间制度环境的不同,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按制度环境的不同进行分样本回归,将之前按照东、中西部划分样本变为按市场化程度和政府效率高低进行分组回归,以此来检验是否在更好的制度环境下,潜在比较优势才能发挥作用,使遵循潜在比较优势的所扶持行业更可能培育出显性比较优势。我们发现不论使用哪一种度量,遵循潜在比较优势的政策效果都出现在市场化程度高和政府效率高的组中。也就是说,只有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潜在比较优势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使相应扶持的行业更快地培育出比较优势。为了进一步说明本文基本实证结果中呈现出来的地区差异的确与制度环境有关,我们又比较了各种制度指标在地区间的差异。我们发现这些衡量制度环境的指标的确在东部的均值要显著地高于中西部。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预判。
除了分组回归,我们也使用了交互项,也就是制度变量与潜在比较优势和产业政策进行交互来考察产业政策效果的地区差异,结果和分组回归的结果比较一致,这再次说明制度是导致产业政策效果产生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发现遵循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更容易促进产业的发展,培育出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但这种现象仅存在于我国的东部地区,在中西部地区则没有体现。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产业政策效果在区域间的这种差异源于地区间制度环境的不同,具体来说,只有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效率较高的条件下,遵循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才能促进产业发展,培育起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
本研究为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效果的关系提供了来自于一国内部的证据,对于中国未来该如何更有效地实施产业政策提供了指引。由于中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制度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的研究告诉我们,相对落后的地区,在产业政策实施中,既要遵循本地的比较优势来发展重点产业,也应当加强制度环境建设(加快市场化改革、提高政府效率),只有在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时,产业政策才能够将潜在的比较优势成功转换为显性的比较优势,真正实现行业的发展与赶超。
此外,本文也我们认识制度环境与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发现。与Nunn(2007)发现制度是形成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所不同,本文的研究提示我们,良好的制度也是产业政策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