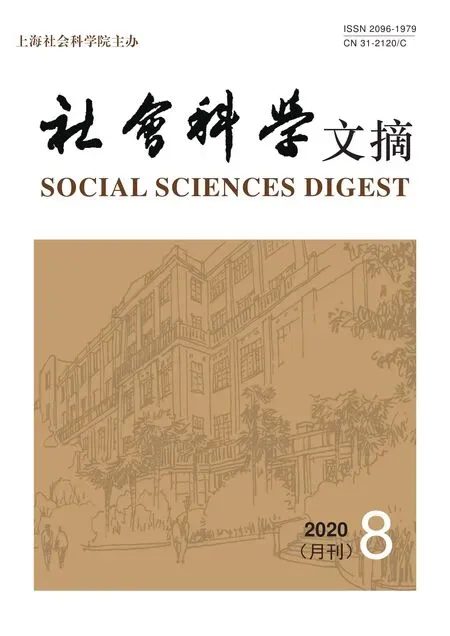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
文/张西平
以自觉的学术态度研究海外汉学
海外汉学(中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标志着中国学术的世界化,正如今日之中国是世界之中国一样,今日中国之学术已是世界之学术。同时,这种外在于我们的海外汉学,由于其研究的特质性,从晚清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尤其在当代,海外汉学著作大量翻译出版,其学术影响已经深深卷入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之中。
不可否认,近代以来汉学研究的成果对中国学术的转型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只要提到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的西域、敦煌研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的中国语言学研究,沙畹(Édouard-Émmanuel Chavannes,1865—1918)及其弟子们的中国历史研究,就可以知道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学术研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但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这些来自东亚和欧美的汉学研究著作,学术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否可以完全认同海外对中国学术的研究呢?或者说我们可以全盘接受海外汉学研究的观点,不加批判地吸收到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之中吗?目前学术界在如何对待西方汉学的问题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完全否认汉学家的学术研究,认为这些汉字家是站在殖民主义立场来研究中国的,所以西方汉学研究是在精神和学术上对中国的又一次殖民,由此国内学术界对汉学的研究便成为一种“自我殖民”,他们称之为“汉学主义”;另一种观点则完全跟随西方汉学家的研究,对其研究成果顶礼膜拜,缺乏必要的分析。这两种态度都有失偏颇。
为此,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研究,这种批评的中国学站在中国学术自身的立场,在一种开放的态度下与海外汉学界展开对话,是秉承着一种学术的态度和精神,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海外汉学的历史展开研究,将其对中国文化的误读给以一种历史性的解释,对西方汉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本位主义给予学术的批判。对当代的海外中国研究也将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吸取其研究之长,批评其研究之短,在平等的对话中推进中国学术的建设和研究。
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我们展开海外中国学研究、展开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开放与包容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对待汉学家的基本文化态度,求真与务实的批判精神是我们审视西方汉学的基本学术立场。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在历时性的西方汉学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展开我们的学术性批判和跨文化视角下的包容性理解,这样一种学术路径其实是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
传教士汉学研究中的文化批判问题
传教士汉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范围,另一部分则隶属于西方思想文化史。我们就隶属中国基督教史这一部分来讨论。在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方法上,学术界经历了“文化侵略模式”“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现代化模式”“全球地域化模式”。就西方学术界来说,在研究的范式上经历了“传教学研究范式”“西方中心主义论: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及帝国主义论”“中国中心观”“后殖民理论的东方学:一种有限的解释方式”。在我们研究传教士汉学时,由于时代的变化,由于1500—1800年期间中西文化关系和19世纪后的中西文化关系不同,这些因素对西方传教士汉学形成了重要的影响。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但是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期来华的传教士,有两个共同点:其一,他们都有同样的基督宗教立场,“中华归主”是其共同的目标;其二,在传教士的汉学著作中,都有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有关这两点,我们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应该从文化上和学术上对其进行说明,这样的学术批判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传教士汉学的特点与问题。
从前者来说,无论是利玛窦还是郭实猎(Karl Gützlaff,1803—1851)都是西方传教士,他们都先后在西方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来到中国。即便是利玛窦,他也承担着为葡萄牙国家利益服务的任务。利玛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通过自己在中国的生活,认识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只能采取“适应政策”。面对中华文化,他采取了求同存异的传教策略,制定了“合儒易佛”的传教路线,从而使基督宗教在中国扎下了根。就此而言,利玛窦、罗明坚等早期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所留下的面对不同文化而采取“合而不同”的文化策略,至今仍是西方文化重要的学术遗产。但我们也应知道,“适应政策”的目的是“中华归主”,这在利玛窦的书信和著作中都有明确的叙述。从宗教学角度看,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在对待来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时,我们需纠正20世纪前半叶的“文化侵略模式”的简单研究模式,但也不需要走到另一端,采取“护教”的态度,不应回避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中的劣迹,而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像郭实猎这样的传教士的问题应给予揭露,对当时西方教会在整体上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结合应该给予批判。目前在传教士汉学研究上,特别是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上,回避西方教会19世纪在整体上与西方帝国势力联盟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从以晚清教案研究为主,转变为以西方教会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贡献研究为主,这是中国学术界从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重大转变。我们应该肯定这个转变的合理性,因为仅从“文化侵略模式”研究不能反映中国基督教史的全貌。同时从马克思的“双重使命论”的观点看,“文化侵略模式”研究忽略了来华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但当我们这样展开研究时,也不可忽视在全球化初期西方教会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问题。
在对西方传教士汉学的批判研究中,不能仅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进行批评,还要揭示出传教士汉学所包含的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一元史观的理论问题所在。作为宗教性立场和作为政治性立场所体现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是不同的,西方汉学中作为政治性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应从学术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同时展开批评,而对于宗教性立场的基督教以一元史观所体现出的西方中心主义,则应从学术上给予讨论和批评,从宗教学上给予分析和理解,从宏观历史进程上给予合理的理性说明。没有这样一种立场,我们便无法全面展开传教士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当代学者王立新将信奉基督教的汉学家的中国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化的设计归纳为“泛基督教论”和“基督教救中国论”,这两条论说都是传教士汉学中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认为西方科技发达就是因为有基督教,如果中国走现代之路,基督教化是唯一的出路。不过同样也不能完全不加分析地使用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完全抹杀传教士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作用。
这些年来,在传教士汉学研究中,我们得到一些教会研究机构的支持,对展开传教士汉学研究起到了好的作用,但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也要保持自己的学术目标和学术立场。教会研究机构支持的研究,在文化倾向上自然从肯定基督教作用的角度对中国基督教史展开研究。从宗教立场上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从学术角度上来看,西方教会在中国近代化大叙事中的双重作用,目前相关研究仍然薄弱,需要继续加强。笔者认为应继续支持在国内外教会研究机构的支持下展开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但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应该有比境外教会研究机构更为广阔的学术眼光和学术立场,更应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和自觉性。这样传教士汉学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才能更为全面、更为客观。我们不需要政治化的批判立场,但对19世纪以来西方教会在中国所引起的问题的学术性批判是不能缺少的。我们不需要丑化一些来华传教士,但也不需要美化他们。我们不需要站在不加分析的单纯政治立场,对西方19世纪教会在中国的行为进行批判,同样,我们也不需要对西方教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只唱赞歌,因为教会本身已经开始自我反省,而一些学者还在无原则地歌功颂德,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中国学术的独立性和自觉性还表现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的方法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选择自身的研究方法。同时,无论是研究议题的设置还是研究的布局,都要从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不能跟着汉学家跑。例如,对传教士汉学来说,中国学术界最缺乏对西文文献的了解和掌握,但当个别汉学家提出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要有一个汉学的转向,即从传教士研究转向中国接受史研究,从以西文文献研究为主转向以中文文献为主时,一些学者为之叫好。欧洲学者提出这样的学术转向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对中国学者来说,毫无疑问中文文献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们相对西方汉学的研究来说所缺的恰恰是西文文献,所不足的恰恰是传教士汉学研究之不足。这些现状表明,一些学者没有从中国自身学术发展的实际出发,确定自己的研究方法。
因此,在传教士汉学研究中,对传教士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在传教士汉学研究上对研究议题的设置、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平衡上,都要有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都应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出发。国内学界应该熟悉海外汉学研究而不盲从,要借鉴而不照搬,这才是一种学术自觉。
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汉学研究著作中的错误
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真理,历史研究的基础是事实。西方汉学家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在常识和专业知识上的错误是常有的事情,对于这些专业知识和常识性的错误,对于他们在翻译中的基本错误,都应该本着学术的精神给予纠正。
目前在中国学术界逐步展开的国别汉学史研究成绩可喜。“有胜于无”,学术总是一步步发展、丰富和积累起来的。国别汉学史作为一个学术史研究的领域,探究的是中国历史文化在域外各国的传播和发展,学派的梳理、人物介绍、历史的沿革、名著的分析是其基本内容。然而,我们必须记住的是,汉学史的书写一方面是我们从事西方东方学研究的一部分,自然要熟悉各国的历史文化对其东方学研究与汉学研究的影响。但是,各国的汉学史毕竟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尽管汉学家们在知识的解释和理解上有着自己的文化特点,但就知识本身而言,它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转述和记载。汉学史的研究不仅是我们对汉学学术发展的梳理,而且也是中国学者与汉学家之间的对话,而不能只是对一些著名汉学家的颂词。
显然,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尚不到位。在对国别汉学史的研究中,在对汉学家的研究中,需要我们努力与汉学家们展开学术性对话。只有这样,中国学术才能在世界上真正展开,对汉学的研究才能从介绍阶段发展到真正的研究阶段。西方一些汉学家便再不能轻视中国学者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些汉学家认为中国学者只能提供历史材料,理论则由他们来建构。在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家著作中只是引用《考古》《文物》这些杂志,很少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就暗含着一种学术傲慢。但在20世纪伯希和与罗振玉、王国维的接触中,并未有这样的态度。王国维去世后,伯希和立即把他的成就介绍给西方学术界,如今一些新秀汉学家忘记了他们的老师们对待中国学者的态度。让东方学回到东方,汉学研究回到其故乡,这是很自然的。中国学者在绝大多数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当西方汉学家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时,当其学术著作在中国出版时,他们就应接受中国学者对其研究的讨论和拷问,对此汉学家们必须做好准备。
走出西方汉学研究的范式,重建中国学术的叙述
批评的中国学不仅仅在于纠正西方汉学家在知识上的差误、在认识上的缺漏,更重要的是要逐步走出汉学家中国研究的一些范式,重建中国学术的叙述。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的国家,晚清之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自然发展历史被西方列强强行打断,这是资本主义第一次全球化发展的一个结果,是西方国家对世界财富的第一次强行掠夺。从大历史观上看,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但这样的历史进程不仅仅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是灾难性的,对于历史与文化、精神与信仰同样是灾难性的。
中国传统文化叙述的模式通过西方汉学接受了西学的学术方式,这样一种转变也促进了中国学术的转型和发展,“六经皆史”,走出经学,以科学实证的方式开始叙述中国历史,是从罗振玉、王国维的敦煌学研究共同体开始起步,以李济等的殷墟考古而完成。但由于中国文明史是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而自行发展起来的一个文化体系,完全套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的文化历史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中国学术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叙述,根据自己的传统和历史给予合理的解释,当代中国学术的重建就应该从梳理西方汉学的研究模式进入中国传统历史叙述方式入手,进而厘清得失,接续传统,融合新知。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笔者试图以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此说明批评的中国学的学术对话的核心所在。
这几年关于新清史的讨论就是一个涉及基本学术立场的重大问题。美国汉学家欧立德(Mark C.Elliot)认为清代不是中国,中国只是汉人的国家,乾隆皇帝不是中国的统治者。汪荣祖先生对这种观点给予严肃的批评,认为“新清史的主要论点,欲颠覆并不存在的中国中心论,意图切割中国,但全不能成立,反而透露西方学术的霸权,甚至隐含质疑中国既有疆域之阴谋。”
以上说明,在对中国历史叙述的重大问题上,一些西方汉学家,包括一些日本汉学家的论述有着严重的问题,在学术上也没有根据。我们需要从学术上加以讨论和研究,以正视听。然而,百年以西方为师,使我们的一些学者只知道学习西方,而不知站在自己的文化学术立场,以分析的眼光来审视海外汉学,而是“以西方学术马首为瞻,缺乏明辨是非与批评的能力”。
这说明汉学家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和研究时,总是容易受到西方知识体系的影响,从而对中国在文明形态和发展历史上与欧美有较大差别注意不够。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海外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的学问和知识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这是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表现。简单地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来否认汉学研究的成就,将我们对世界范围展开的汉学研究的关注和对其著作的翻译说成是“汉学主义”是片面的。我们应该看到一些汉学家为研究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艰辛努力,在近400年的西方汉学研究中,他们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产生了一批卓越的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西方汉学的研究刚刚拉开帷幕,学术界应继续加强对海外汉学的研究。
另一方面,也要和汉学家展开对话,对这种异域的学问做一种跨文化的理解,在学术上展开严肃的对话和批评。无视西方汉学存在的思想应该摈弃,当然,对西方汉学崇拜的时代也应该结束了,一个平等对话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