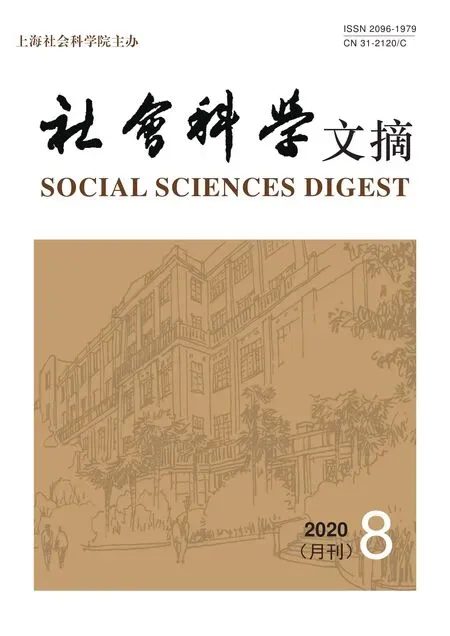发展的机制:以比较优势战略释放后发优势
——与樊纲教授商榷
文/刘培林 刘孟德
引言
樊纲教授最近在《经济学动态》和《管理世界》发表了两篇关于发展经济学研究主题和内容的重要论文。一篇是《“发展悖论”与“发展要素”——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案例》,另一篇是《“发展悖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这两篇论文立足于对现实的观察,提出了不少重要观点,其主要目的在于找到破解“发展悖论”的途径。按照樊纲教授的论述,这一悖论也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的特殊问题:发展中国家处处落后,处处不如人,但还要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具体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因为落后而导致的区别于发达国家的六类“特征性问题”。为了破解“发展悖论”和这些“特征性问题”,樊纲教授的论文进一步指出,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一般意义上的“增长要素”;而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本土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发展要素”,其中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是比较重要的两种“相对优势”。
樊纲教授这两篇重要文章框架宏大,涉及到很多问题。我们赞同其中的很多观点。比如,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从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相对关系的角度入手加以深化。再如,“经济结构取决于要素结构”。又如,“要想有更好的、更高级的经济结构,你需要去努力发展和增长那些优质的要素……而不是像大跃进那样,以为只要大炼钢铁,有了一个经济结构的飞跃,就可以成为强国。由于要素结构没有变化,这种赶超的结果只能是浪费大量资源,并不能真正改变经济结构……最终是不可持久的”。还比如,“我们的确也到了大力提升自主创新的阶段”。
但是我们不同意樊纲教授的另一些观点。比如,他把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仅仅等同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又如,樊纲教授在两篇文章中把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作为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上继起的互不相干的两个事情。
我们认为,樊纲教授这些观点误解了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现实含义,有必要加以澄清。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固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我们看来,比较优势并不仅仅对应着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非不同发展阶段上继起的互不相干的两件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只有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顺利且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这正是破解樊纲教授所说的“发展悖论”的“发展的机制”。
比较优势既要跨国横向比也要跨时纵向比
比较优势所比较的,是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有多种,比如物质资本、土地和矿产资源、劳动力等等。各种要素禀赋中,任意两种都有相对的比例,如物质资本相对于土地和矿产资源的比例,物质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比例,土地和矿产资源相对于劳动力的比例。这些比例就构成了要素禀赋结构。这些要素禀赋结构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物质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比例。
所有这些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有两方面含义。一个是同一个时间点上各国之间的横向比较,比如,2017年各国人均物质资本水平有高有低,美国高于中国的水平,中国高于印度的水平。另一个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间点上的纵向比较,人均资本水平有时高有时低,通常是现在比过去高,未来比现在高,中国2017年的水平高于2000年的水平。当然,也有一些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因特殊原因而导致人均物质资本水平随时间推移而减少,比如战争和自然灾害导致物质资本短期内大量灭失,或人口增速远超物质资本积累速度,都会导致这种现象。
基于上述讨论,可以进一步指出关于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战略的两个含义。第一,比较优势原理虽然因为贸易理论而广为周知,虽然决定着开放条件下国家之间分工格局,但事实上同样决定着封闭经济条件下单个经济体合理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的情形。比较优势所比较的要素禀赋结构,实际上刻画了一个经济体的预算约束和要素相对价格。密集使用相对丰裕从而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是成本最小化的必然要求,是所有要素都能得以充分利用的必然要求。这可以说是经济学当中的铁律,无论分析对象是开放经济还是封闭经济,这个规律都成立。第二,比较优势从来就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概念。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内在地要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物质资本密集度,须随着人均物质资本水平提升而相应提高。
按照樊纲教授的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且只能是劳动密集产业,当这个国家人均资本积累、发展水平提高之后,发展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就不再符合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了。
我们认为,樊纲教授这种看法是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和片面的理解,值得商榷。如果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全部含义仅仅是劳动力丰富、工资低的话,那么,就完全没必要大费周章引入比较优势这个概念。我们不否认发展中国家在较低发展阶段上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劳动密集产业和产品上。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随着发展水平提高,资本积累速度超过劳动力增长速度而导致劳动力逐步短缺的话,并不意味着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彻底消失了,而意味着比较优势的具体体现变化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将越来越具有比较优势,而发展早期所倚重的劳动密集产业将逐渐丧失比较优势。
唯有比较优势战略才能顺利且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
上文介绍了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含义。发展中国家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目的就在于顺利且充分地释放自身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
所谓后发优势的含义,正如樊纲教授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就是“作为落后国家,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或模仿前人所积累的大量技术,学到别人在之前发展过程当中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可以少走弯路,多走捷径”。“就是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通过国际交流,得以把发达国家的知识‘外溢’到我们这个地方,外溢到落后国家的经济当中,通过学习和模仿,尽快掌握人类已有的一些知识,取得较快的进步。”
这个“少走弯路,多走捷径”的技术“外溢”过程,实际上就是相对落后国家模仿相对先进国家技术的过程。模仿过程中,相对落后国家无需像发达国家当初那样,在众多技术路线中试错,在众多技术上可行的产品中识别哪些商业价值更高。通过模仿,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在几十年时间里快速掌握发达国家在上百年甚至几百年里积累的技术和成功的商业模式。而且,相对落后国家模仿这些技术所支付的成本,也会低于相对发达国家当初研发这些技术所支付的成本。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关于后发优势的两个推论:横向看,某时点一国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越落后,则前者所具有的后发优势越大;纵向看,一国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如随着时间推移而缩小,则前者的后发优势会相应缩小。
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确如樊纲教授文章所认为的那样,是两个不同的、相对独立的概念,但两者并非完全割裂的,其共同点和内在的紧密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都是潜在优势,除非通过系统的战略和政策加以利用,否则,两者都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现实的发展动力。二是,一个落后经济体和一个发达经济体之间,在人均资本拥有量刻画的比较优势上的差别越大,则前者的后发优势也就越大。这也意味着,两个经济体之间如果人均物质资本水平相当,则两者相互之间几乎没有后发优势;反过来,如果两个经济体之间相互没有后发优势的话,它们的人均物质资本水平也不会有太大差距。
除这两点外,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之间紧密关系的另一个更重要表现是,只有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顺利地、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则不能。这是因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之下,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技术结构的资本密集度与整个社会的人均资本水平相适应,成本能够最小化,企业能够获得最大剩余,所有的生产要素都能够被充分利用起来,整个社会的总资本能够以潜在的最快速度积累,人均物质资本水平才能以潜在的最快速度提升,从而以潜在的最快速度攀升技术阶梯。相反,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比如赶超战略之下,优先发展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技术结构的资本密集度超越于整个社会的人均资本水平,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成本不能最小化,不能获得最大剩余,难以在竞争性市场中生存。这种情况下,为发展这些超越整个社会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政府必须予以保护和补贴,或授予它们垄断权,或提供低价资本、原材料和土地。这些扭曲创造了租金,刺激了寻租、贪污和腐败。最终,整个社会资本积累速度低于潜在的最快水平,人均资本水平提升速度也就低于潜在的最高水平,该经济体攀登技术阶梯的速度也就低于潜在的最快水平。
由此可见,后发优势只有通过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顺利而充分地释放出来,转化为推动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不采取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那么,后发优势就仅仅是潜在的优势,无法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动力。
没有后发优势可资利用时也应遵循比较优势战略
基于前面的分析,还可以得出更多关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之间关系的逻辑推论。
第一,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只要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战略,就一定能够顺利、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吗?如果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封锁,从而使得后发优势只是镜花水月怎么办?樊纲教授在两篇文章中均指出,中国当前和今后发展阶段上面临着发达国家日益严格的技术封锁。那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否应该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战略?
按照我们的逻辑框架,即使中国今后不能从发达国家模仿任何技术,一切技术都需要自主研发,那中国也应该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不过,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的劳动密集度,要远低于改革开放最初20年的情形了,但显然会高于当今发达国家如七国集团(G7)的水平。
第二,设想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就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利用后发优势,而喜欢一切自力更生,把一切轮子都重新发明一遍。即使在这样极端的情形中,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也会比不遵循来得更好。理由如前所述,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则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政府不需要对经济体系和价格信号进行全面扭曲,资源配置效率始终处于高水平上,资本相对于劳动力而言才能实现最快的积累,从而更快地迈向更高端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否则,反之。
第三,后发追赶国家一旦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后,就不再是后发追赶的发展中国家了,也就不再具有后发优势了。这种情况下要不要继续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更广义地看,当今最发达的美国相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没有任何后发优势。那美国是应该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产品和技术,还是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发展劳动密集产业、产品和技术?答案不言而喻。由此也可以推断,美国最近挑起贸易摩擦以来,力图实现制造业回归,如果说美国大力发展高度资本密集、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业的话,是符合其比较优势的,这样意义上的制造业回归,也是可持续的;但倘若美国试图实现回流的是劳动密集的制造业,我们推断是不会成功的,或者说必须以很大的效率损失为代价,比如政府对劳动密集制造业大量补贴,才能实现。
落后国家快速增长对全球而言是正和而非零和博弈
樊纲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追赶而导致的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是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之一。他也曾经分析道:“落后国家还得增长,还得在已经被发达国家占领、‘瓜分’了的世界市场上‘挤出’一个份额。……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就是研究落后国家在发达国家已经占领市场的前提下,怎么实现增长的问题。”
如果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经济占全球的相对份额角度看,樊纲教授上面的看法是成立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如果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增长,那后者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份额必然会缩小。
但是,相对份额缩小是否构成樊纲教授所说的发展经济学“特征性问题”之一,除了要看相对份额外,还要考虑到全球经济总蛋糕是否增大的因素。这个因素背后的实质,则是发达国家自身技术进步是否停滞。倘若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技术进步停滞或放缓,全球经济总蛋糕增速就会放缓,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相对份额意义上挤占发达国家的市场的同时,是否会在绝对量意义上挤占发达国家的市场,则存在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期,技术未处在最先进水平的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封锁技术输出,则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谈不上任何后发优势。倘若真的如此,发展中国家就发展无望了吗?我们认为,除非发达国家凭借武力彻底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否则,后者即使没有任何后发优势可资利用,但只要采取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也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把所有轮子重新发明出来,假以时日,也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销售其产品。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发展会在绝对量意义上把自身和全球总市场做大;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绝对量意义上的市场规模会因此扩大;技术最先进的发达国家绝对量意义上的市场规模也会扩大;技术未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发达国家绝对量意义上的市场规模是否扩大,则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充分认识到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在持续进步的现实,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对全球而言就更是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了。
正确地看待上述问题,在当前国际关系形势下的重大意义在于,促使发达国家正确对待全球化,正确处理国际关系,以积极的态度和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否则,如果不能正确地看待上述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全球而言是零和博弈,进而以零和博弈思维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限制技术输出,在自己国内生产本可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那么,不仅发展中国家受损,发达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会受损,可以用于研发前沿技术的资源也会减少,长期福利必然也会受损。樊纲教授指出,发展中国家达到最高发展阶段,“成为世界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后,所应该有的态度和做法是:“不可能一个国家制造所有的东西,应该通过开放的世界体系,各国之间专业分工、相互贸易,这样才更有效率。”如果说达到最高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和做法的话,那当今的发达国家就更可以以这样的态度和做法,来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