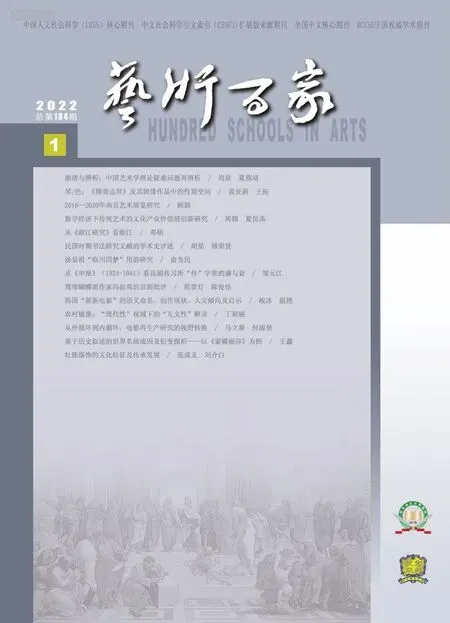从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到“陈奂生问题”*
——论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的现实主义品格
胡一峰
(中国文联 文艺评论中心,北京 100083)
常州市滑稽剧团的《陈奂生的吃饭问题》问世以来,不但赢得了观众口碑和业界肯定,还屡获殊荣,代表滑稽戏剧种参加“中国戏曲百戏盛典”;作为江苏唯一剧目,受邀参加“第五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又作为中国文联特邀剧目,成为在福州举行的“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开幕大戏,还获得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奖项。一时间,把滑稽戏重新带入了当下的艺术生活。这不仅让人想起当年昆曲《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盛举。当然,从“后视之明”观之,《十五贯》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促使人们正视并开掘中华民族的美学宝库。同样,《陈奂生的吃饭问题》这出戏,注定会留在中国戏剧史上,因为它不仅激活了一个剧团、救活了一个剧种[1],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找到了现实题材开掘精神内涵、提升美学品质的新路。这部作品以充满地方感的小人物生活,关照了多个具有强烈现实感和历史感的宏大问题,诸如怎么看待中国农民,怎么看待“三农”问题,怎么看待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什么是我们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基因,以及当代中国人应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迎接明天的阳光。对于一部主要演员不足十人、演出时长不足两小时的滑稽戏来说,它所选择的题材和挑起的担子,似乎有些沉重了。可喜的是,《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不但肩起担子,稳稳抵达艺术的目的地,还不时扭腰抖肩,花样百变,不时给人以欢快的、苦涩的、会心的、解嘲的笑声,不但让人在笑中流泪,还促使人在笑中思考,真可谓意味悠长,回味无穷。
一、艺术地透视改革底层逻辑
《陈奂生的吃饭问题》成功的原因有许多,首先是现实题材创作的一次突破,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一经亮相就在众多扣合时代主流精神的现实题材中显得与众不同”[2]37;还有对“陈奂生”这一经典文学形象的艺术再造,“把他放入近半个世纪以来农民命运的长河里,用独有的喜剧思维,张扬了他原本就具有的幽默性,演绎出种种别样的,令人亦喜亦悲、亦笑亦哭、亦晦亦明、亦思亦叹的故事来”[3];也有该剧从内容到人物形象对时代精神的呼应[4]11,以及对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之间张力的深刻体现和艺术把握。[5]
不过,笔者以为,所有这一切归结起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该剧贯注着充沛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恩格斯所提出的,优秀戏剧作品应该“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反映一定的历史内容,同时具有莎士比亚戏剧的丰富性与生动性”。[6]174现实题材不等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关怀生活的态度,也是关照历史的忧思,要求有别林斯基说的“痛苦的哀号和热情的赞美”,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7]15有的现实题材作品之所以让人感觉乏味,就是因为缺乏精神关照,生活成了一堆碎片的、枯燥的“现实材料”,又怎能给人以美感呢?《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则不然,它虽是一部喜感满满的滑稽戏,但洋溢着现实的关怀和忧思,从而让现实题材在滑稽戏的艺术形态下,得到了符合自身规定性的表达,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感染力,避免了现实生活的浮表化和人物形象的符号化。
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问世的作品,《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对中国改革作出了总体性关照。作品以紧扣主线的简练叙事,折射出当代中国改革乃至民族复兴的“底层逻辑”。这就是陈奂生在剧中反复念叨的“吃饭是个问题,问题不是吃饭,不是吃饭问题”,也是剧中一再强调的吃饭不成问题之后不能忘了“饿肚皮的滋味”。确实,不理解昨天中国人“饿肚皮”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今天中国脱贫的坚定决心,以及为此而付出的不懈努力。陈奂生那句绕口令式的台词,小而言之,直观地反映了一个农民的朴素生活哲理;大而言之,体现了国家和社会不可离弃的忧患意识,以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也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的基础是生存,生存首先就要“吃饭”。在改革的问题上,从决策者到推动者都讲过“改革是逼出来的”。[8]6从底层逻辑来看,逼出改革的,正是吃饭问题。到了“吃饭不是问题”的今天,推动改革不断深化的,也是吃饭问题。这一点,剧作家王宏谈到此剧的“创作初心”时也曾提及。[9]37-39作为普通人的陈奂生,正是在解决个人“吃饭问题”的过程中建立伦理尺度,并用以衡量现状和历史、政策和人心、自我和他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诗比历史更真实”。陈奂生的个体故事,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人集体走过的路同构同质的、浑然一体的,具有以个别透视一般的意义。以此视角分析《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就会发现该剧开场时舞台中央那一大碗米饭,以及舞台上和“吃饭”有关的一切呈现,诸如傻妹刚到陈家时面对桌上米饭的灼灼目光,吴书记到访时长桌共餐的悲喜一幕,都不仅是一种舞美或表演技巧。其实,对于优秀的作品而言,任何技巧总是服从于主题的。当聚光灯让白灿灿的米饭格外引人注目,当这碗白得发亮的米饭刻印在观者的脑海之中,人们在欢笑之余陷入了思索。在陈奂生的身上,我们读到了自己或父辈曾经走过的心路历程。陈奂生的一生都在为自己和家人吃饱饭而挣扎、奋斗,等到吃饭不成问题的时候,这个一辈子饭量没有变过的人,却得了食道癌,吃不下饭了。作为观者,感伤命运之吊诡的同时,也意识到为填饱肚子而苦恼的日子已经翻篇了;但“吃饭问题”没有翻篇,反而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拷问着每一颗有良知的灵魂。
二、从生存之问到伦理之辨
《陈奂生的吃饭问题》整部作品以陈奂生的回忆和讲述为基本叙事方式。这也是近年来不少舞台艺术作品在处理较长历史跨度时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法,话剧《大国工匠》(2018年)中的“郑浩天”、话剧《小镇琴声》(2019年)里的“阿德”等,都是如此。这样的处理把历史和现状交融在同一个时空之中,有利于保持叙述中心和主线的稳定,不过也对作为讲述者的演员以及舞美、舞台调度等提出了较大的考验。《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的主演张怡同时饰演老年陈奂生和壮年陈奂生,而且在台前而非幕后完成角色变换,难度自然更大。我们看到,创作者巧妙地采取了一种相对简洁的处理方式。伴随着“他回忆完了”“他开始回忆了”两块板子来回翻动,陈奂生戴上帽子、直起腰,就回到了从前;弯下腰、脱下帽子又来到了现在。应该说,这样的处理是智慧的,也符合滑稽戏的剧种特征。实际上,该剧发挥剧种优长的地方还有不少。比如,以夸张、变形的手法,对一些剧情作出超现实的处理,相片里的傻妹穿越到现实之中,结尾处陈奂生拉起傻妹去成亲,皆为例证。于是,叙述方式转化造成的视觉隔阂和审美障碍得到了化解,作品的完整度和完成度也获得了提升。更重要的是,现实和历史毫无违和地穿插交融,为这部现实题材的作品凿出了历史感的景深,使精神内涵拥有了舒张的空间。
从1970年初春开始,剧情在2018年春和1970年夏、1979年夏、1988年春、2006年春之间反复穿插行进,众多矛盾和冲突渐次展现出来。虽然从舞台效果来看,该剧并没有明显的场次之分,剧本也只是以“节”作了划分,但从叙事逻辑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上下半场的结构。上半场的中心问题是“怎么吃饱饭”。傻妹嫁给陈奂生,是想让孩子们“吃饱饭”。而且,剧中暗表,傻妹这三个孩子的来路,恐也与吃饭需求有关;陈奂生希望生三个孩子,是为了多分口粮吃饱饭;吴书记深入基层搞调查,是想让乡亲们吃上饭,陈奂生配合王本顺欺骗吴书记,也是为了换几顿饱饭;就连傻妹表达对陈奂生的感情,也是“我会要饭,我要给你吃”。“吃饭”作为一个问题,如一把利刃,始终悬在人们头上。上半场的结束,是傻妹吃生米“胃炸了”,从而把生存拷问推向了一次高潮。
这也如一个信号,转入到了吃饱饭不成问题的下半场。“吃饭问题”依然存在,但变成了“吃饱后怎么办”或说“怎么有道德地吃饭”。也是在这里,该剧完成了一次思想内涵的升华,从生存拷问上升到伦理之辨。大儿子陈两从小受穷,对钱的欲望,终于把他赶上了贪腐之路。延伸来看,陈两作为老大,肯定比弟弟、妹妹更多尝到过和傻妈为了吃饭而经历的辛酸。“穷”能让人挣扎奋起、思变求通,“穷”也会扭曲人的心理,走入“报复贫穷”的误区。人性的复杂性于此得以充分展露。如陈奂生在剧中所言,“是我错了,你妈临死的时候说: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让你们三兄妹吃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只管你们吃饭了,我只顾往你的肚子里塞米饭,塞菜,塞肉,我没给你塞进去一颗良心,做人的良心!我给你留着吃的,留着土地,留着钱,我就是没有给你留徳!”填不饱肚子的时候,所有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吃饱饭;吃饱了之后,就面临千千万万个问题。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发展,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为民族复兴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民族是无法真正复兴的。“吃饱之后怎么办”,成为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一道考题。陈奂生的困惑,诉说的其实是中国人的集体反思。
三、经典文学形象的戏剧再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10]10“陈奂生”是高晓声创造的当代文学史经典形象,自打从作家高晓声笔下站立起来,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赞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天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怀。今天这个时代,和小说“陈奂生”那个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可说是陈奂生的一篇“别传”,[3]或者说,对典型人物的一次再造。而典型人物是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塑造新时代典型的过程,是体现时代之美、生活之美、人性之美,实现新表达的过程”。[12]戏剧“陈奂生”作为从高晓声那里借来的人物,是改编也是再现。他是属于这部戏的“这一个”,又具有文学“陈奂生”的一些基因,也就是王干所说的“陈奂生质”。[12]应该说,张怡可圈可点的表演,让戏剧“陈奂生”在人物形象“跨界”再造中变得更加直观,在保持了人物谱系连续性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艺术感染力,让人看到了舞台艺术对文学形象的丰满。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人潜意识里总有一些农民的影子。中国农民是质朴的,也是狡黠的,他们用充满泥土气的智慧,应付沧桑变幺、风云起伏。陈奂生首先是个农民,有农民的智慧,也有农民的心机。王本顺在他和傻妹手上盖了大章,宣布他俩结婚后,他仿佛预见到了后面的变故,竟连手都不洗,就拉着傻妹到县城,花一块钱把两个人手上的大章照了下来。后来,他与王本顺谈判要地时,果然多了一样“砝码”。如果说文学“陈奂生”更多地保存了传统农民的特质,戏剧“陈奂生”则融合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起带头乃至示范作用的“农民英雄”的故事。在这个陈奂生身上,我们依稀看到了从小岗村严宏昌到华西村吴仁宝的影子,看到了四十余年来中国农民所走过的坎坷奋进之路。在这条路上,农民不再是被动地受历史摆弄的人,也不是“口袋内一个个马铃薯”了,而是积极有为的进取者,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表达着关于是非善恶美丑的看法,努力担当起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无疑,这是一种现代性人格。《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对此的塑造令其具有了充满现代性的美学特质。这也表现在一些细节中。为了养活三个孩子,陈奂生想尽办法,不惜向王本顺和乡亲们双膝下跪、连连磕头;晚年身患绝症,还强撑着筹钱,帮贪污的大儿子陈两退赔赎罪,这一幕幕令人心灵感动甚至震动。陈两、陈斤、陈吨,这三个和陈奂生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是戏剧再创造的产物。高晓声创作的以陈奂生为主角的系列小说中,陈的妻儿出场不多。而且,小说中的妻子有些“呆”,但不“痴”,生了两个孩子,是奂生的骨肉;收养了一个“天落子”,也只是一笔带过。[13]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最讲究祖宗香火,因而也滋长了对血缘关系近乎宗教的崇拜。作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陈奂生能从中超脱出来,甘当“小四”(即傻妹的第四任丈夫),替“别人”养活三个孩子,这本身就蕴含了巨大的戏剧性。如果说,傻妹刚嫁入陈家时,这是出于既成事实的无奈;如果说,傻妹去世后,这是出于陈奂生对亡妻的情义,那么,当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甚至老二陈斤分家而去之后,陈奂生依然对三个孩子不离不弃,履行着父亲的责任,其品格已经超越了传统农民的质朴善良,必须用伟大才足以形容。显然,这种伟大是充满现代性的,它超越于传统乡土社会的伦理规范和世俗道德之上,使陈奂生这一形象经艺术淬炼而焕然一新。同时,也表明《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的主创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抱有指向未来的眼光和心胸。
舞台艺术实践表明,在一部优秀的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气质必然和作品的气韵相协调。《陈奂生的吃饭问题》也是如此。这部作品叙事明快、节奏紧凑,有滑稽戏特有的喧闹,但没有多余的人物或情节。戏剧内在的张力构成该剧唯一的推动力,所有任务的完成都依靠故事本身以及演员在演绎故事时的内在力量,而不是刻意设置的功能性人物或角色。这不但让陈奂生、傻妹、王本顺等主要角色如传统建筑物的榫卯一般,紧紧地咬合在了一起,整体结构稳定而协调,即便是次要角色,也颇为亮眼。比如,陈奂生的女婿刘和平着墨不多,戏却很足。这个懦弱得有点窝囊的男人,过着被动妥协的人生,然而,他的妥协其实是守护心中对妻子的爱,即便默默“掩护”大舅哥的不法行为,也是想把家庭护得“周全”。小人物的可爱和可气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正是所有角色的合力,烘云托月地把“陈奂生”立在了舞台上,也立在了戏剧艺术史上。
陈奂生在舞台上的“新生”还离不开剧种的特色。所谓滑稽,大概含有异于寻常之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这个剧名自带高冷的幽默感。不过,该剧没有像有的戏剧或影视作品那样,依靠过分夸张的言辞或方言,制造刻意的喜剧感,相反,作品的语言是生活化的,方言的运用也是适度的。其中,也不乏围绕“吃饭”二字的金句。比如,“国家干部要吃自己碗里的”,分明是一句警世箴言;陈吨说她老公的“去年打错狂犬疫苗了”,则充满乡村俚语风格。再如,陈奂生和王本顺的斗嘴,用类似“伦理哏”的手法占便宜,还原了乡间斗嘴的俏皮场景。剧中还运用了一些人们熟悉的艺术“套式”[14]169、186-187。比如,吴书记到陈奂生家访贫问苦,王本顺弄虚作假,把张阿大、李幺妹家的鸡鸭送到陈家,制造丰衣足食的假象。吴书记针对疑点连连发问,陈奂生“急中生智”帮王本顺圆谎,让人想起经典传统相声《扒马褂》。而剧中人多次唱起的江苏民歌《杨柳青》,又使人沉浸到了熟悉的民族民间旋律之中。这些“套式”是中国人审美偏好在艺术形式上的凝结,是适合中国的耳朵和眼睛的艺术手法,具有深厚的接受基础。
四、回应“陈奂生问题”之瞩望
《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的结尾是开放式的,一场多舞种“大合跳”,把滑稽戏的特色推向了视觉高潮,也给人留下了思索。全剧演出过程中,乡村大喇叭不时响起,播讲着最新的政策和形势,也提醒舞台上下的人们:陈奂生的人生上下半场紧密联系着人民公社、农村改革、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等农村发展实践。演的是一家一姓的小事,映射的却是国家社稷之大道。“村民陈奂生走了,离开了他又爱又恨的乡土”,但乡土还在。这片乡土的幸福之花,说到底要靠陈奂生那样把双脚稳稳地站在现实大地上的人民,辛勤地播种和浇灌。
全剧接近尾声之际,时空一度融合,陈奂生和“好人吴书记”有一场“餐叙”。吴书记回顾了自己的历史,“我是个要饭的娃娃,在苏北,新四军一开饭就吹号,一听到号声我就跑过去,战士们就给我盛饭吃,后来,这号声就印在了我的心里,我就跟着新四军走了,为老百姓能吃饱肚子,打仗去了……”这也是他当年冒死给老百姓分救命粮的动力。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吃饭”这个底层逻辑的强大力量。吴书记说,“吃饭是人的基本需求,追求富裕的生活也是老百姓的基本需求,不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要我们这些官员有个球用”。其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初心”,《陈奂生的吃饭问题》以艺术的方式把它“演”了出来,而不是“说”出来更不是“喊”出来。而这,本也是艺术应有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呼吁社会找回“初心”的同时,也找回了戏剧这门艺术以及近代以来中国戏剧传统的“初心”。行为至此,又想到剧中另一个细节。陈奂生蹲在屋角,三个孩子进来寻找,却没一个发现。陈奂生愤愤道,“这些傻玩意,没一个想到开灯的”。这里的“灯”,是给舞台照亮的灯,是陈奂生家里的灯,更是人的一盏心灯。心里有一盏灯,才能看清自己的位置,找到回家的路。不论是“怎么吃饱饭”的问题抑或“吃饱了怎么办”的问题,需要回归初心,也就需要点亮心灯。
对于一部作品而言,如果不敢对现实表态,那称不上现实主义;如果甘于做现实的回声,那也不是合格的现实主义。直面正在进行时的历史,是现实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现实题材难写的症结所在。对此,《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的创作者充满对明天的热望又保持了艺术家可贵的节制,以设问的方式表示:“随着城市化的飞快发展,农村土地创造的价值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在遥远的未来,也许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农民最终都会消失,可取代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大哉问!我们不妨称之为“陈奂生问题”或“陈奂生质问”。这是在生存问题解决之后的伦理拷问,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必然之问。而新的伦理规范乃至在此基础上的新社会,必然也只能是在历史和人性的逻辑中生长起来。如戏中所言,“新的一天来临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阳光下走来……”我们期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戏剧艺术,顺着《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开拓的新路,创作出更多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塑造更多具有思想穿透力、审美洞察力、形式创造力的典型形象,弘扬时代主流精神,回应“陈奂生问题”,谱写新时代的文艺新篇章。
——评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
——当小说变为滑稽戏
——分析高晓声代表作《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的形象